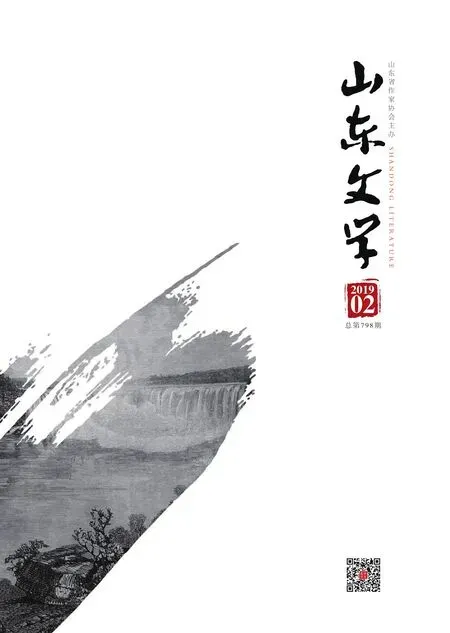归来时仍是少年
2019-11-14
成年人最为难得的品质是在经历无数人生遭遇之后,依然能保持一颗赤子之心,这是一种纯洁的能力,能够在经历沧桑之后仍不失天真,如同粗砺风沙中摇曳妩媚的边花野草。它来自淳朴人性最初的童蒙之光,但更多是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那种对于纯粹光洁之物的理想与向往让他不断地回溯生命与成长的原初情境,在回眸中重新认识自我与现实,进而使之成为汲取能量抵御汹汹时势的不竭源泉。我觉得,云雷的小说集《到姐姐家去》中诸多作品就体现了这种品质。
只要略加留心,就会发现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回忆性的叙事,称之为叙事散文也未尝不可。它们可能只是两个孩童在某个春日上午心血来潮去看望几个村子外出嫁的姐姐,或者秋天夜晚给庄稼地浇水时候少年在寂寞懵懂中生发的性的觉醒;也可能只是记述了童年时候偶尔相遇而终究分离的小伙伴,或者就是某个贫穷老人落魄一生中仅存的模糊印象……除了《红气球》之外,几乎每一篇在开头就设置了一种模式性的时间框架:“那时候。”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我们刚刚脱了厚棉袄,身上很轻松,跑得很轻快。”(《到姐姐家去》)
“那时候我刚从乡村到县城里来上学,什么也不懂。” (《坏孩子的天使》)
“那时候浇地也是很有意思的。” (《流水与星空》)
“我出生时我二爷已经七十岁了,他死时我才四五岁,我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了。” (《秋去春来》)
“那时候七爷住的离我家不远,在我家北边的一个小胡同里。” (《铁匠的女儿》)
“那个新娘子刚嫁到我们村里的时候,人长得很俊俏。那时候我们那里闹洞房的风俗很盛。” (《我与新娘的一天》)
“那个暑假的雨水很多,下的也很大。”(《暑假作业》)
“那时候,父亲在三十里外的果园工作,家里只有我娘、姐姐和我。” (《母亲与菩萨》)
“那时候”的回忆性叙事框架意味着“我”的始终在场,并且“我”是经历了大段时间之后再次复归到某段过去的时光之中。这会带来两方面的美学效果,一方面经过主观过滤,往事与人都烙上了温馨和妥帖的色彩,童年时光在孩童视角中摒除了龃龉、污秽和可能存在的残酷性内容;另一方面,多年后的“我”也会带有后见之明,不自觉地移向今昔对比和对于已逝过去的咀嚼与反刍,从而为简单的情节、人物和结构弥补上自省与反思的深度空间。后一方面正是这些小说的意义所在,它们并不遵循我们对于小说的那些关于技巧和形式的惯性认知。
在云雷素朴无华的娓娓道来中,我们看到一个乡村少年的无邪时光,它们是去故事化的,只是生命中那些零星散碎的场景、人物、若有若无的情绪和隐现不定的思索,而更多旁逸斜出的闲笔用在记述行将消失或者已经消逝的乡村景致、生产劳作方式以及人情风俗,那些吉光片羽的记忆存留因而就具有了“物哀”的意味,构成了渐行渐远的“旧日的世界”和“旧日的情感”。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将那些人、事、物在回忆中风景化、对象化,而是投身其中,成为其有机而无法分离的一部分——它们既是那些人物的故事,也是“我”参与其中的故事。同时,过去也是“我”生命中不能切除的前史,依然作用于现在,并成为型塑今日之我的资源。这是一个在饱经断裂性体验后依然顽强地要保持连续性的自我主体。
因而,我在读的时候尽管不自觉地会联想到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冬冬的假期》或者《风柜来的人》,但我不会将云雷这些作品便利地归束到乡土文学或者怀旧文学之中。固然它们中间确实包含了跨越时空的人类共通性经验与情感,那些文学书写中经久不衰的母题:成长、丧失与变迁。但在所有带有原型意味的书写中,每个书写者都是具体的,他会落脚在实实在在的琐细时空之中,云雷的具体之处就在于他呈现的是从“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迈进过程中底层青年的经历与感受,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同时代人”所特别被触动的地方。
云雷比我大两岁,我们都生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时代的同龄人。尽管他的家乡鲁西南和我的家乡皖西北无论从地理、物候到民俗都有较大的差异,但他这些带有非虚构色彩的作品之于我一点都没有隔膜之感。我们有着类似的时代背景和情感结构,甚至从乡村到县城里茫然无措的“坏孩子”打台球的玩乐方式以及遭遇警醒而成长的经历都很相似。《暑假作业》中写到“我”在假期中不得不回到农村干活,却在同时悬想城里同学的游乐生活,心中愤愤不平,这个心理尤为真实。我想,这是一代人共享的经验。区别于我们时代文学书写中偏向于刻绘阴暗、丑陋、人性恶的主潮,云雷的文字干净、明快、宁静而带有些许的惆怅,留下的是爱与美的慰藉,这里可见他心性中的温柔敦厚。
云雷的小说一直都是经验写作,他没有像那些在文学场中习得了各种奇技淫巧的人们那样在谋篇布局上花费太多心思,而只是在老老实实地摹写最初的那些本真。这是一本我会推荐给我孩子读的书,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再也不可能遭遇我们的那些体验,那些已逝的昔日不可能重来,而它们对于完善一个人的认知、充实一个人的全面人格是多么弥足珍贵:我们不知过往,又如何前行?
“二十多年,我从一个孩子成为一个青年,从不识字到成为一个博士,从一个偏僻的村庄来到一个国际大都市,我已经渐渐疏远了我的村庄和我的父母。我一路前行,跨越千山万水,追逐着自己的梦和理想,不知不觉来到这样一种境地,这似乎是很幸运的,但我却并不感到幸福。相反,我却时常感到荒谬与虚无,站在黄昏的大街上,看到那些匆匆奔忙的人们,我总是会感到莫名的孤单。在以前的很多年里,我总是在追求上进,追求新奇,追求变化,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想要抓住一点永恒,抓住一点寄托,想要将自己有限的生命与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而当我这样想时,却发现要抓住一点永恒是那么难,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在瞬息万变,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我们走在这个世界上,走在人生的道路上,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依靠,我时常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或坏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时常感到无所适从,无法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云雷在《母亲与菩萨》中如是写道。这篇压轴的作品可以视作一次精神成长史的梳理和辩难,他念兹在兹的是人的信仰问题。这可能是我们时代最为切要的精神难题,每个身处变革中的人都必然要遭遇到历史与价值、情感与理性、可爱与可信的冲突,我们物理意义上的老家可能再也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内心深处都有着一个记忆中的精神上的老家,有没有可能从老家的伦理、道德与情感遗产中开掘出前行道路中的基础、依傍与慰藉呢?这是云雷提出的问题,有待于我们这些同时代人共同去探索。
走马兰台,身世浮沉,愿我们在远行万里之后,都仍然记得最初的梦想,因为“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