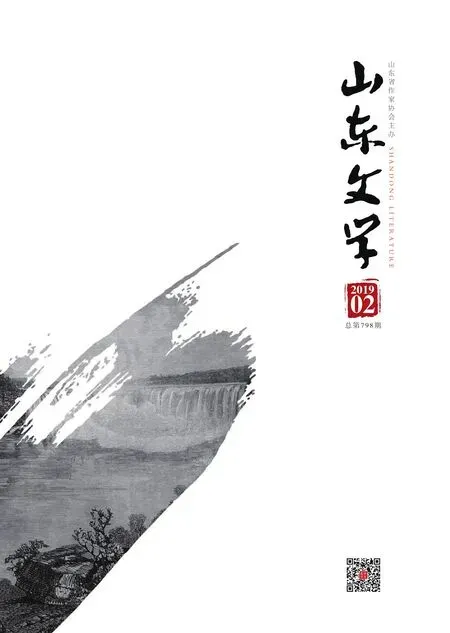燕雀二章
2019-11-14
自从太史公在《史记·陈涉世家》中使用了“燕雀”一词,燕雀这个庞大群体就被打下尘埃,在市井谈笑中遭讥讽和不屑,戴着灰暗的标签,如破帽遮颜的落魄之士,灰溜溜来往于市井与山野,在正史大传的边缘徘徊。“燕雀”指形体小的鸟,常来讥讽目光短浅、胸怀狭窄,甚至卑微猥琐的小人物,与井底之蛙近似。然而我们是燕雀一样的草民,没有见过鸿鹄,那戴着炫目光环的神鸟止步于生动的寓言。在平原丘陵养育的小村落里,我们甚至连鹰、隼、鹞子这样稍微大些的凶猛鸟类都不怎么相识,目光里是燕子的起落,是麻雀的翻飞,是布谷的声声啼唱,是喜鹊展示的高空芭蕾,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名字的鸟,它们在川在野在宇在庐,用灰的黑的羽毛,平平仄仄的啼唱,灵巧的飞翔曲线装点着开阔的大地和苦辣酸甜的百姓日子。
梁间燕子岂无情
在乡村,燕指燕子,雀是麻雀,它们是贴着大地飞翔,依着屋檐生存的鸟类,它们受着农家屋檐的庇护,像农户的成员。燕与雀都形体小,飞翔迅速,不怕人间烟火,愿意和人依偎在一起生存,但是它们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燕子被称为吉祥鸟,是捧在手上、爱在心上、供在梁间的;麻雀被称为老家贼,被驱赶、遭喝骂,甚至在粮米匮乏的年代,它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人们将它作为四害之一进行杀戮。
都是为了那口饭,农人叹息着。
燕子是乡下的绅士,羽毛永远光洁油亮,白衬衣黑西装,斜飞过水面时,不忘撩些水洗浴翅尖。燕子活得精致,它只吃虫,口味刁蛮就免不了劳碌之苦和千里奔波。为了那口鲜活的吃食它南飞北归,年年奔忙。燕子不仅在饮食品味上挑剔,对居住也舍得投血本,衔泥筑巢是它区别于所有鸟类的独到之处,这个出类拔萃的房屋设计师和建筑师常常将巢建得别有风情,在檐下,在梁间,在院角,它择地而居。燕巢也筑得精美,油罐、花瓶、草蓝都被它模仿了去,燕泥井然排列、严丝合缝,绝没有豆腐渣工程。燕巢一般不会筑得很大,够一对燕子居住即可,当燕子孵雏的时候,总是雌雄轮流值守,夜晚,那只不趴蛋的傍在巢的边缘,似乎要掉下来了。燕子幼雏一旦会飞,就要迅速自立门户,家里没有多余的床位。燕巢的形状很有趣,什么样的也有,有的底端细、开口广,像一只大海碗,有的两头翘中间凹像一个金元宝,有的像篓子,有的像陀螺,有的像八仙桌上的香炉。燕子筑巢是用自己的津液搅拌泥土,或许加入了它的津液,那泥就更坚固了。有些燕窝被人类反复炒作,认为是高档补品,血燕呕心沥血的巢穴也就一次次被贪婪的人倾巢掳掠。不过在乡间,燕巢是安然的,谁也不相信那泥巴筑起的燕巢能吃,而且,也决不会去打扰那可爱的燕子。
燕子的洁癖在于它挑主人、选邻家,不是谁家都配有一窝燕子,若是争争吵吵,火药味重,再好再新的房子它都不会去安家。燕子筑巢之前先要 “验窝”,一对燕子在周围反复盘旋考察后,才决定是否在此垒窝。当燕子开始筑巢,这户主人就内心欣喜,甚至暗合手掌口念弥陀佛,她轻言细语、谨慎进出,她把狗儿猫儿驱赶开,甚至对孩子颁布禁令:不许偷看,不许大声说话,不许在堂屋和院落里剧烈活动,不准把伙伴带到家里玩闹。为了燕子的安居工程,孩子们也知趣地避开,回家的时候尽量轻声细语,蹑手蹑脚。乡下人以无比虔诚的姿态和礼节迎接居室里的一窝燕子,一对翩然出入的小燕子给乡下简陋的房舍,萧条的庭院带来许多生机,也给了那些劳苦的人带来莫大的心灵安慰。
燕子的洁癖还在于它的决绝割舍。当它在辛苦垒筑起的燕巢安然居住时,恰巧有调皮的小孩好奇燕窝的构造和神秘,趁它不在,攀着梯子爬上去,用手掀动了它铺在窝里的羽毛褥子,顺便留下了自己涎水脏手的气息。那燕子归来后盘旋哀鸣,它知道巢穴被入侵者动过了,它就这样盘旋着不肯再进窝。一个新窝就这样废弃了,那个春天,一对燕子露宿树枝,它们对这户人家彻底失望,商量着到别处重新筑巢。那户燕窝空空的人家,内心无比失落,比丢失了一件贵重物品都难过。连燕子都看不上他,这日子还有多少滋味呢?
漫长的冬天里,燕子沿着季风的方向飞翔,追逐着温暖和美餐,它的巢穴空荡荡在北方的风里等待。
麻雀原先住在瓦檐里,那里冰凉,它们像流浪者,不筑巢,不储存,混天潦日,看到屋檐下那空着的燕窝,就心动了,那里有细小柔软的动物皮毛和鸟类羽毛,那是多么舒适的一个床铺啊!反正这邻居度假去了,何不借它一用呢。于是,鸠占鹊巢,它心安理得地在燕巢中过冬了。第二年,燕子回来,两家打起官司,叽叽喳喳地在院子上空吵翻天。气性大的燕子骂一阵就走了,被麻雀住过的房屋,它绝不再住进去。这种决绝的燕子人们称呼它为“家燕。”家燕因深知麻雀之流的坏脾气,于是防患于未然,选择将巢筑在农家厅堂里,农家是不允许麻雀进屋的,这一点,家燕知道。家燕居住在屋内,真的成了家里的成员,它很自律,不给家里添一点不便,绝不会把粪便排在窝巢外,厅堂也就始终干净。当幼雏从卵中孵出,幼雏的粪便就由老家燕衔出去扔掉。良好的品行使它们得以跟人类同居一室。另一类燕子叫做“草燕”“游燕”,是不那么自律的燕子,它排便随意,所以不能筑巢于室,而是在屋檐下,麻雀所夺的是草燕的窝。
曾经在一个春天,到农户家闲游,见麻雀和燕子在庭院上空掐架,几只鸟在空中扑棱棱,麻雀灰和燕子的黑白色忽上忽下,互有胜负,也算是一景。住家老人说,燕子的窝冬天里被麻雀占去了,燕子回来要夺回来,可是麻雀住惯了,不打算返还,两家都打了两三天了。后来,问及那燕雀的官司,老人说,因为麻雀泼皮势强,燕子争不过它们,盘旋几圈伤心地飞走了。老人气不过,拿竹竿把燕窝给捅得稀巴烂。老人说,这还有没有公道了,原家住不成,强盗也住不成。他能把燕窝捅烂给燕子出气,却没办法给邻居家那个媳妇挣理,那媳妇的男人外出经商,勾三搭四,一次次要离婚,还把小婆领回家来。哎,老人叹息一声,麻雀都是跟这些人学坏了。燕子走了就走吧,有这样一户邻居,也是留不住燕子的。
蛰居小城,人到中年的我常常被一种梦境里的天籁叫醒,比如春天,我的梦境比南风更早地呼唤燕子归来。某个清晨,我梦中醒来,竟然满脸泪水,耳际还有燕子略带忧伤的啁啾,拉开窗帘,一片灰暗的萧索和模糊的雾霾朦胧于我的眼睑。我把窗帘再拉上,企图重新回到与燕子应答的梦里。用不着翻看日历,我知道,清明近了,每年这个时节,我的梦就多。
我梦见的是小时候,我趴在窗台外收听着广播,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在时光里飘荡。广播线上、干丝瓜藤上、过年挑着鞭炮的竹竿上,几只乌黑的小燕子在梳理羽毛,在兴奋地叽叽喳喳。母亲从里屋出来,念着:“七九河冻开,八九燕子来。”我甜蜜地看着开心的母亲。那是我小时候的春天,燕子在寒凉的南风里归来,母亲把御寒的风门拆下,打开堂屋门,把灿烂的阳光迎进屋。
鱼篓型的燕巢在我家老屋正堂内,在黑漆漆的屋脊上,被常年的烟熏火燎熏染成了我家的颜色。高处的燕子总是最先闻到炊烟里的悲喜和愁乐。怕熏着燕子,母亲做饭尽量少弄出些烟,而且一定要在天黑前把晚饭做完。母亲的炊烟总是在呼唤着我们,也在期待着燕子归巢。这烟火停了,炊烟散落,我们回家吃饭,燕子回窝睡觉,我们和燕子一起进屋。
抬头是燕窝,生灵在高处,家里就更有生机。燕子成了母亲的教科书,“贫贱不怕,要和睦勤劳,要不,连燕子都瞧不起。”于是我们乖巧了许多,言谈举止逐渐从一个个野孩子变得安静起来。燕子来筑巢,是看上了我家的和睦安宁,我们要对得起小燕子对我们的信任和看重,年少的我们尚且不懂母亲借小燕子教习我们礼仪的一片苦心,但是已经能以一片圣洁之心,仰望我们屋顶的生灵。
尽管和许多穷苦的家庭一样捉襟见肘,但父母的和睦一直是我童年里的温暖阳光。记得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在和小芹欢欢喜喜去她家,结果她娘抹着嘴角的血在院子里哭,她爹在屋里大骂。我情绪压抑地回到家,父母正在树荫下包饺子。母亲说今天是入伏,没肉就包素馅饺子吃,得把节气过得像个节日。他们一边包着饺子一边轻声地说话,看我不高兴,母亲就说,嫚,你看燕子在数数呢,你跟它比比谁数得快?于是母亲把燕子的呢喃变成了极快的一到十的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听了哈哈大笑。那个父母在包饺子,我在桃树下和燕子比数数的傍晚,永远烙进我的记忆里。
燕子会改变家庭,也会被家庭改变。家燕虽然品格高,不会把粪便拉在屋里,但是,如果这户人家不讲究,它也就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若不是勤劳的人家,起得比燕子晚,燕子就会毫不客气地将粪便拉到厅堂,因为它没办法及时飞出去。家有燕子,母亲总是早早起床开门将燕子放出去捉虫和打扫自身。爱睡懒觉的我,渐渐在燕子的欢叫中醒来。母亲说,一群燕子在丝瓜架上开会呢,是商量什么事呢?邻居家的燕子孵出小燕雏来了,看看,它们的姑舅姨妈都来看望了。燕子的生动生活实在是比被窝更有诱惑,我渐渐也养成了不睡懒觉的习惯。“哪里有什么家燕游燕,是燕子的品性不一样罢了,就像人一样,当好人自然是辛苦,可是总不能当进不来家的游燕吧。”母亲这样说。“把家燕生生逼成了游燕,能把游燕养成家燕的人家才真正了不起呢!”我那时候听不懂母亲这句话,并不知道这是她是对村上家庭教育的精彩点评。
黄昏时候,燕子好像格外兴奋,它们成群结队在电线上聚集,一次次在庭院上空俯冲,在硕大的白色葫芦花前掠过,在弯弯的眉豆角前啁啾。它们灵动的身影让晚霞更可爱,让炊烟更安闲,让童年的记忆更温馨。
秋叶飘零,燕子匆忙启程,空落落的燕窝让人惆怅。燕行在外的日子,母亲看着空空的屋梁沉思,“燕子走到哪里了呢?”,她也扳着手指数算:“七九河冻开,八九燕子来,快回来了。”屋檐下的冰凌一点点化尽了,屋后根的残雪也钻进了土地,母亲的小燕子啁啾一声,扑进了春寒尚浓的庭院,和母亲的惊喜撞个满怀。母亲的小燕子没有辜负她的期盼,一年年在料峭春寒里返回在梁上,而她自己的小燕子却一个个地飞开了。在县城安家的我和大哥,在京城漂泊的二哥,熬苦了母亲期盼的双眼。我们蜻蜓点水般的归来飘忽不定,竟不如燕子守时,年年和母亲做伴的,竟然是那窝燕子。
“燕子不进愁门,老鼠不坐空仓,”谁家都能养一窝燕子吗?养着燕子的人家或许并不比别家宽裕,也有许多生活的漏洞需要补丁,但是他们常常在无望的时候想到燕子,也没有谁替它张罗,还不是自己建屋、自己打食吗?燕飞千里不缺食,那些穷困的人就在田里刨了一遍又一遍,决不把落漏的果实烂给土地;坡上能吃的能用的野菜草根,都划拉回来,归到粮仓或者草垛,只要能燃起生活的暖,他们都不嫌弃。
老屋拆掉时,我暗自流泪,鱼篓形状的燕窝已经破旧不堪,但是依旧没有空,我不知道住的是当年那对燕子的第几代儿孙。一座新房盖起来,但是,那砖换了,梁撤了,瓦是崭新的,没有淋过一滴岁月的雨水,那是我们的家,没有了母亲炊烟的家,那梁上曾经是我家的燕子,还会再来筑巢吗?
后来,父亲随我们进了城,老家的新屋就像一只空空的燕巢,只剩下一个念想,如今,原先的一梁一椽都不在了,这崭新的家,如何能承载我们沉甸甸的往事?燕子归来寻旧巢,我们的燕子,再来的时候,将依附于哪根屋梁?而我们再回来时,那崭新的房屋能承载什么?母亲的巢已倾,父亲的巢已迁,我们徘徊翩飞,究竟要落在何处?翩飞在天空的燕子啊,难道你也像我们一样寻家不着?
春节回家过年是我和哥哥执拗的坚持,哪怕老屋不在,娘亲不在,我们依然要回到那个烙下刻骨记忆的地方虔诚厮守。我和二哥沿着雪地里的沟畔一直走到西河,我们说起河沿上我家那块承包地和旧日的河塘,那栽着速生杨的地里,承载过我的童年汗水。我们一家人如今在这个村庄没有一寸土地,我们这些“城里人”却年年来这里过最隆重的节日。我还在门外的一墩棘子树前照了相。翻建老屋就像一场洗掠,这丛棘子树是家留下的唯一旧物。
忽然记起,梦里流淌的那首歌是《归来的燕子》,“越过大海,你千里而归,朝北的窗儿为你开,不要徘徊你小小心怀,这里的旧巢依然在。”我们的燕子到哪里去了?燕子你听到了吗?旧巢还在!
我常常听着这首歌,想着明天的路程,明天,会不会遇到那翩飞的燕子,我家曾经的燕子?
老家子
如何说麻雀呢,若是翻经阅典,麻雀决不是寂寂无名之辈,《诗经》《本草纲目》以及文人雅士都对它有所关注,江南才子唐伯虎在《寒雀争松图》中吟道“头如蒜颗眼如椒,雄逐雌飞向苇萧。莫趁螳螂失巢穴,有人拈弹不相铙。”虽是有名,却也难以看出人们对它多喜欢。花鸟绘画师们更多将色彩给了颜色精彩的绶带、锦鸡诸鸟雀,只有《寒雀图》等极少的画纸为小巧而卑微的麻雀留了影。因为麻雀太多,就像沙漠里的沙子,树枝上的叶子,随处可见,甚至多到惹人厌烦,没有好听的歌喉和美丽的羽毛,还专干偷鸡摸狗骚扰庄稼和粮食的勾当,颜值不突出,品行也差强人意,人们凭什么喜欢它呢?
农家对血脉、亲疏关系理得最清,品性好的燕子可以住在屋内,就是农户的自家人,他们叫它“家燕”;修行差的燕子只能住屋外廊下,是人类若即若离的远亲,这游离者就被叫作“游燕”;而雀是绝对屋外的禽鸟,日里在瓦上跳跃,夜晚在瓦下安身,依附一瓣青瓦度日月,叫它“瓦雀”是最恰当的了。儒雅的乡村读书人别出心裁,叫它“宾雀”,“我为主,君为宾,相见欢,且歌吟。”他正酸溜溜地与雀儿调笑,自家半浅不满的粮米却被这毫不客气的宾客呼啦啦吃去半碗,穷儒就恼了,这宾客太大方,不讲礼仪,招待它太麻烦,麻雀也。读书人一甩长袖将麻雀轰走,端着剩下的半碗米煮粥去了。“家燕”与“宾雀”,主家与宾客,农家必须分得十分清楚,但还是“麻雀”的名字最朴素,像农家的儿女一样随意顺口。麻雀,麻雀,农家叫它麻雀时是不是看见它与手里的一匹麻线太相近呢?它的毛色太杂,看不出主色调,黑色、白色、麻色、褐色等诸色在腹部、背部、翅尖斑驳杂陈,远远看去就是灰不溜秋,《本草纲目》对麻雀的研究最细致,时珍曰∶“雀,短尾小鸟也。栖宿檐瓦之间,驯近阶除之际,如宾客然,故曰瓦雀、宾雀,又谓之嘉宾也。俗呼老而斑者为麻雀,小而黄口者为黄雀。”
何谓“老而斑”?哪里有一生下来就老了的麻雀?只能说它面相苍老类似老妪吧,在人类的印象里,这种一生似乎就没有年轻过的麻雀,像是乡间的一个个小丑,可调笑可戏弄,轰不散、撵不走。麻雀以老而丑的貌相,褐而不美的羽毛,躁乱而不佳的声音给自己描绘了肖像,像极了那些天天和它们一起起居的一身补丁的庄户人。“头如颗蒜,目如擘椒。尾长二寸许,爪距黄白色,跃而不步。其视惊瞿,其目夜盲,其卵有斑,其性最淫。”——(《本草纲目》)。时珍是医药圣手,文字也了得,所描摹之麻雀,惟妙惟肖。所有麻雀的短处,都不抵“其性最淫”打击性大。它的“淫”在于对农家的骚扰,各种农作物它常常飞马劫夺,快手偷窃,酿下了一条不可轻赦的罪名。无疑,时珍是带着厌恶的情绪如实转述了那个时代艰辛农人在麻雀面前的焦头烂额。正是因为这一“其性最淫”,成就了麻雀,面对高空飞行的鹰隼,麻雀只是一口食,如此卑微的食物链末端,如果再不泼皮谋生,怕是就日渐绝迹了。麻雀是生存性最顽强的小禽类,低层、卑微就要不得体面,这难怪,活得艰难了,你还要求它有多么高的品格?这世间,有人做得了“家燕”,有人只能做“游燕”,而有人却只能做“麻雀”。有时候,这是人自己的选择,有时候是天的选择。
时珍对麻雀的研究透彻而充分,雀肉、雀卵甚至雀粪便都引来入药,脏腑虚弱、肾冷偏坠、小肠高气、赤白痢、内外目障、男女之病、便溺不利、目中翳膜、小儿口噤、疮疖末破、喉痹乳蛾……麻雀能治的病就像麻雀一样纷纷繁繁,它的药效就像一只只急速飞翔的雀准确抵达一粒粮食一样,准确地抵达人的五脏六腑,将病患斩除。一只勇猛的麻雀像一粒子弹,生是好汉,死亦英雄。
燕子是成对飞翔的,它们是夫妻鸟,长相守、不分离,所说的“劳燕分飞”便是人生最大的不幸。麻雀是群聚的,呼啦啦一大片,像大风刮起的一堆树叶,纷纷扬扬。麻雀与燕子是生活的两个相反层面,燕子是穿燕尾服的绅士,麻雀是披蓑衣的泼皮。它活得粗糙,首先是食性杂,飞娥小虫粗糠糙米秕谷草籽什么都能入口,它所求甚少,也随处可餐,常常在替猪狗鸡鸭清除垃圾,它把它们吃剩的饭渣子打扫干净,是个勤奋的垃圾工。乡下人不喜欢麻雀却也离不开麻雀,粗糙的麻雀就是他们的影子。乡间的事物总是土气,灰不溜秋的麻雀正好是乡下的一枚枚印鉴。土里土气的乡下人不喜欢自己身上的这块标签,于是就将火气迁怒到麻雀身上。其实麻雀和庄户人是刀劈不开的依存关系,哪里有土地哪里就有人烟,哪里就有麻雀。
麻雀是义气的群体动物,你很少看见孤独的麻雀,它们总是一群“呼”地一声起飞,从这棵树到那棵树,从平地到屋顶,从高粱地到地瓜地。它们的叫声也嘈杂,没有好的嗓音,却都忍不住要展示自己,就像那些在坡里锄地的人,在岭上刨土的人,在崖畔扬粪的人,忍不住就喊几嗓子肘鼓戏,给庄稼和黄土听,给路过的麻雀听,给自己的心听。
麻雀卑微却机警,再卑微的生命也值得倾心珍爱生命,或许,它从不觉得自己的毛色难看,那是一种中和色,不鲜艳不张扬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这一点,歌喉婉转的鸟儿不懂,羽毛鲜艳的鸟儿不懂,它们在人间数量稀少,不仅仅因为生殖比麻雀弱,枪打出头鸟的规则,或许麻雀懂得,长期跟人类厮守在一起,它们故意退化到如碎草和干树叶一样的颜色。不出众就是自我保护,这样看来,它们跟那些披蓑戴笠的归隐之士具有同样的智慧。因为群居,所以它们一荣俱荣,有事一起担当,苟富贵莫相忘,谁找到了食物大家均分,它们过着同甘共苦的公有制日子。
麻雀不挑选,它不挑吃、不挑住,喉咙粗糙,皮囊皮实,属于行则简、居则易的一类,何必那么费心呢,筑房造屋,筑好说不定谁来住!它不受那个累,与其当房奴,不如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天下没有不可居住的屋檐。至于吃,它更豁达,它们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地讨论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咱也不改其乐。”看看,麻雀的学堂也不简单,它活出了哲学高度。所以,麻雀有更多的时间唱歌和跳跃,没有千里之志,却也有诗和远方,田野里、沟畔上,稻田、麦田、谷子、高粱,它们用嘴巴一一检阅,用翅膀一一行吟。它们四处巡游,不论贫穷之家的寒薄庭院,还是富贵之宇的雕梁画栋,都有麻雀的脚印,无论丰腴的土地还是贫瘦的地方,都有麻雀的身影。富庶的地方,是它雀生的华丽场,它吃饱喝足绝不留恋,跳闹一会儿就走了;没吃没喝的地方,它咕噜咕噜议论一番牢骚一顿,用短小的嘴巴勾一勾草屑和浮土,这次飞走了,下次还会来。
总以客之名把它拒之门外,乡下人觉得对麻雀有些苛刻,有人就不忍,喊它“家雀”。其实,它就像自己家那个淘气的孩子,你把它撵出去怎么行?燕子是乖巧的,可麻雀也是自己的雀儿,手心手背都是肉,“哎!”她喊一声,“老家子!”麻雀却忽地一声飞上了墙头和树梢。它们没怎么得到过主人这样的称呼,有些不适应,被骂惯了的淘气孩子,你对他好,他就有些不知所措。乡下人太减省,把所有形体小的鸟儿称呼为“翅儿”,他们就叫麻雀为“家翅儿”。乳名叫“老家子”和“家翅儿”的麻雀,但也被许多人叫做“老家贼”,这是两个极端的称呼。“老家子”像是离乡日久的游子,在别处看见了普天下无处不在的麻雀,就以为是自己童年里逮过的那一群,那一只,于是就称呼它为老家的孩子。叫它“老家贼”却充满敌意,手里攥着它的短,动不动就揭老底。每一声“老家贼”都让人想起饥馑岁月里的人雀之争,争的是一口吃食。那时候它的确是将嘴巴伸得太长,无处不在地吃掉了太多农人的庄稼。“家雀儿”的称呼比较优雅和中和,就是家养的雀吧,它是长在家树上的叶子、庭院里蔬菜,猪窝上野草,篱笆上的花朵,这一群去田野里打食去了,另一群又来了,反正它们长得一样,灰不溜秋,谁也分不清,和那些庄稼汉一样,走到哪里也还是那么样,在乡下被叫做庄户人,进城来被叫做农民工。
乡下人在穷的时候是怕麻雀的,谷子泛黄之前它就闻到了成熟的香气,呼啦啦一群群扑到穗子上啄着、抖着,眼看到手的粮食进了麻雀的肚子,空着半根肠子的农人哪能不心疼和咒骂;晒地瓜枣的时节也怕麻雀,那软糖一样的地瓜枣不管晒在瓦檐上还是席箔上,总也逃不了麻雀的嘴巴。人们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对付麻雀的盗食,一个个草人穿着烂衣服,戴着旧草帽,手里还挥舞着破蒲扇,在田地里惟妙惟肖地驱赶着麻雀。可是麻雀精灵着呢,它那花椒粒儿般的眼睛,分辨得出真假,它们照旧在田里吃喝,吃饱肚子后还跑到草人的头上肩上跳舞、唱歌,甚至在它身上留下几泡粪便。沮丧的草人只留给田野一个童话。后来农人用网拦截,在谷子地上扯上一挂轻便的细扣小网,阻挡麻雀与谷穗亲近,可总有胆大心细的麻雀找得到空隙,钻进网里吃现成的。初夏红碎的樱桃,招惹一群又一群麻雀来餐,一口一只,比得上琼浆豪宴;柞蚕出蚕不久,白嫩绵柔的小蚕苗儿是它们的最爱,一口肉,最享受。它们躲在浓密的树叶中伺机猎食。遭了雀灾的庄户人只能愤而杀戮,用火药轰,用大网抓,用尽了办法,最后还得在蚕嫩的时候和樱桃泛红的季节在野地里镇守,专司轰赶。“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难道雀在《诗经》中表演了穿墙而过的杂技吗?是破门而入吃了屋里的东西了吧。看来这家伙在那么久远的历史中就已经是飞马劫夺的胡子本色了。但是若漫长的冬天里,没有麻雀来逗趣,乡村的天空该多么孤寂,乡村的庭院该多么索淡。无怪在大雪封地数日的时候,许多农家会在自己院子里撒些秕谷。平日的争斗也不再计较了,一口食就是一条命,这世间,人得活,雀也得活。土墙的木橛子上,雪天里总是挂着一扎谷穗,过些天,母亲取下轻盈的穗子,再挂几根沉甸甸的上去。
泼皮麻雀活得那么粗糙,它的性子就不免随和吧?大错!它是性烈、高傲的呢,它天性野,不可笼养。一只被抓到手的麻雀能烈性到浑身抖擞,咕咕咕咕颤抖着,一会儿就气绝身亡,简直如武林小说中咬舌自尽的侠士。大多数麻雀在被捕之后选择绝食和自戮,比如头撞笼子等办法结束被拘禁的生命。
乡下孩子最兴奋的事情恰恰是逮麻雀,但是麻雀机警,一般孩子难以得手,孩子们于是用弹弓发射石子射击,但是,他们的乐趣是逮活的,一只被石子从枝头打下的麻雀,再加上自杀行为,孩子们玩雀的愿望总是难以如愿。大人不让孩子们玩麻雀,见到了就会呵斥,据说女孩子玩了麻雀就会手臭,做饭难吃,男孩子将会一辈子手气臭,干什么都不光鲜。大人尤其忌讳孩子掏麻雀蛋,乡俗流传说,人不能吃鸟蛋,尤其是麻雀蛋,若吃了,脸上会长出雀斑。这大约是乡下人对麻雀的不忍和保护。但是孩子们寻求刺激,总是忍不住对麻雀邻居下手。他们最常用的逮活麻雀的办法是晚上找屋角摸。麻雀通常是不裸露在外的,烟囱底、瓦瓣下,小小的地方就能存身,可是也有那新分窝出来的,有那流浪而来的,或者犯了事被族群驱逐的,孤孤单单的两只雀儿在空猪圈屋里宿了。孩子们借来一只手电筒,一人照着,另一人悄悄双手捂住它们。晚上,雀的眼睛几乎是盲的,手电筒的强光一照,它更是颤抖不已,不敢动了。那些被捂在手里的麻雀不停颤抖着,害怕或者生气,常常第二天就死去了。手里有麻雀血债的孩子长大后对自己的孩子喊,别去招惹“老家子”。而那些孩子们已经不像他们小时候一样对麻雀较劲,他们的世界五花八门,小小的灰麻雀引不起他们的兴趣。
走在小城广场上,经常看见一个老人掰碎一些面包渣在喂麻雀,那黧黑的面容,用自来水洗多少年都还是庄户人的样子,就像那一群群麻雀,吃了多少面包都还麻雀。“嘿,这些老家子,吃得肥肥胖胖的,快飞不动了。”老人似乎是跟我说,似乎是自言自语。在这个城市,他的西南乡的大土话,没人愿意搭茬,只有我,和这群老家子听得懂吧。我一停下脚步眼泪就差点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