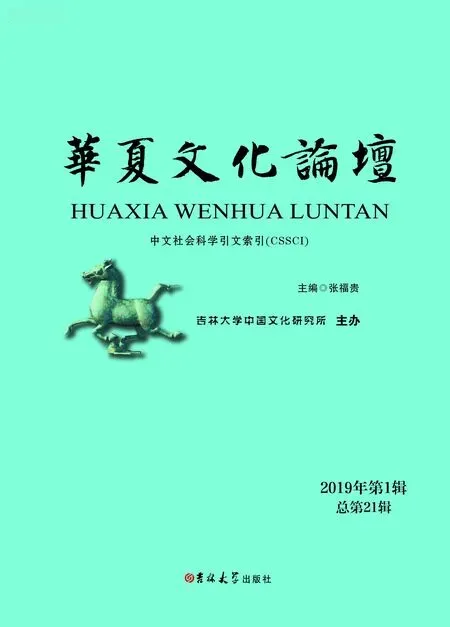“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浅论贯休诗歌的佛禅意蕴
2019-11-13王泓力
王泓力 李 静
【内容提要】贯休是唐五代时期著名的诗僧,其诗歌与佛禅因缘颇深。贯休凭借深厚的佛学修养和艺术才华,真正将禅与诗融会贯通,自发性地推演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思想,使这一命题得以历史地建立。贯休以“中得心源”为本,将禅家的终极境界落到实处,糅合南宗禅的“随缘任心”与北宗禅的“拂尘净心”,追求生命的真性。同时,贯休“外师造化”,在审美活动中崇尚本然如实的“自然”、合规律与合目的的“人情”、流动不息的“圆融”之境,在灿烂的感性中发现生命的真实。
贯休是唐五代时期著名的诗僧、画僧,有“流传三绝画书诗”的美誉,现存诗歌七百余首,他生逢禅门的发展与转型时期,其诗融合了南宗禅与北宗禅的佛禅思想,自发性地推演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一命题,展现艺术之胜境,是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然而,禅宗创立后,佛门虽然涌现了一大批文人士大夫的追随者,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诗僧仍是被忽视的群体,佛禅究竟怎样与其诗歌发生关系,鲜有论者涉及。因此,本文将结合“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一理论,发掘贯休诗与禅的内在联系,探讨其诗歌的佛禅意蕴,展现唐五代时期文学与佛学的发展状况,对诗僧研究进行开拓性尝试。
一、“中得心源”:顿悟与渐修的糅合
(一)心源为本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唐代以来重要的艺术理论,谓以生命之真性观照万物,与造化同游,在天地间自由俯仰,世界自在地呈现,与禅宗的发展渊源颇深,学界已有诸多学者进行剖析,兹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中得心源”为根本,“心源”谓心乃万法之根源,亦指人的真性或“本来面目”,《观音玄义》曰:“夫心源本净无为无数非一非二,无色无相非偏非圆,”道信曰:“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朱良志先生曾指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最根本在于“心与物合的性真”,“确立了‘性'的本体”。“心性”成为“一切原则的原则”,是人性与佛性的凝聚、诗心与真性的融合,禅宗及中国艺术理论的许多重要命题皆由此派生演绎。
据贯休之徒昙域《禅月集序》及赞宁《宋高僧传》载,贯休七岁出家,少有诗名,受具足戒后便开始了游方生涯,曾于洪州开元寺讲训《法华经》《大乘起信论》,在佛学与诗学上造诣颇深。作为精通佛理的僧人,贯休尊“心”为“师”:“若师方术弃心师,浪似雪山何处讨。”(《了仙谣》)“心师”指“我心之师”,《涅槃经》云:“愿作心师,不师于心。”贯休虽广涉儒释道三家思想,但在宗教归属及思想传承的问题上,他的立场非常明确:尊释教,且仍以禅家的心性论为主。贯休又尝以“猿”喻心性,例如:“桓玄旧辇残云湿,耶舍孤坟落照迟。有个山僧倚松睡,恐人来取白猿儿。”(《再游东林寺作五首》其二)此诗作于咸通年间贯休漫游庐山之时,首句原注云:“昔桓玄入山礼远公,遂舍辇,至今在远公堂下。”“耶舍”指白莲社十八贤之一的佛陀耶舍,表达了贯休对庐山慧远及其结社盛事的追忆、敬仰之情。关于“白猿”,《法苑珠林》云:“众生心性,譬若猕猴戏跳攀缘欢娱奔逸,不能瞑目束体端心动意,”因此末句有“守心”之意。心是妙悟的根本,南阳慧忠国师云:“未审心之与性,为别不别,师云:迷则别,悟则不别。云经云:佛性是常,心是无常。今云不别,何也?师云:汝但依语,而不依义,譬如寒月,水结为冰。及至暖时,冰释为水。众生迷时,结性成心。众生悟时,释心成性。”寒山就有“心中无一事,万境不能转。心既不妄起,永劫无改变”,皎然有“积疑一念破,澄息万缘静。世事花上尘,惠心空中境”,至明代《西游记》中孙悟空“心猿”的形象,心本体的塑建已成为影响佛学与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贯休说:“至理至昭昭,心通即不遥。”(《避地毗陵上王慥使君》)从彼岸回归此岸,从出世间返回世间,关键在心,这是禅宗的理论支点与核心命题,正如契嵩大师说:“《坛经》之宗,尊其心要也。”
既然心源为本,就要用心去悟,贯休曾在《题曹溪祖师堂》中写道:“空传智药记,岂见祖禅心。”以“禅心”概括禅宗六祖惠能的禅法,那么,何为“禅心”?那个曾经“破柴踏碓”的惠能写下了一首石破天惊的偈语,同时又指出:“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惠能利用大乘空观对传统禅法进行了改造,只要认识到本心的绝对虚空便可到达西方,实现精神的超越,因而在这“刹那间”也体悟了永恒的境域。这就是顿悟,即惠能的“禅心”。由此,惠能在《坛经·定慧第四》中提出“定慧等学”:“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他为芸芸众生指示了一条去往佛国的通天大道,将传统禅法“由定发慧”的理路改造为“即定即慧”,定慧不二即是“一”“大”“全”“圆”,是宇宙无意识,也正是《维摩诘所说经》所提出的佛性境界——“不二法门”。故而贯休称赞惠能:“非色非空非不空,空中真色不玲珑。可怜卢大担柴者,拾得骊珠槖籥中。”(《道情偈三首》其二)诸色皆空、万物有形,这“空中真色”的佛性乃天地之大本、造化之珍宝。只要领悟到虚空的本体就是禅定,由迷到悟只在本心,不待外求,早已不同于印度那结跏趺坐式的冥想。顺着这一理路,般若空观进入人们的终极信仰世界。然而,中唐之后,禅宗利用大乘空观进行了一场否定之否定的运动,它否定了传统的修行方式,甚至也否定了那个抽象的本体,白云无心,青山在目,大地含情,佛性与人性的界限消失,佛教绕了一圈又回到肯定世俗生活的道路上,终极意义向世俗生活回归,佛性转化为人性,成为人的情感中的一部分,于是,自然主义、自由主义的风气肇开,南宗禅大盛,五宗的时代即将到来,正如贯休说:“唐人亦何幸,处处觉花开。”(《遇五僧入五台五首》其四)
(二)随缘任心与拂尘净心
那超越和绝对的终极境界,应该怎样到达?对此,贯休为我们提供了两条路径:随缘任心与拂尘净心。
先谈随缘任心。宋代诗人李涛曾揭示出贯休与洪州禅的密切关系:“诗学贯休体,心参马祖禅。个中真有得,名下岂虚传。”(《僧本均乞蒙泉稿》)贯休亦自谓:“清高慕玄度,宴默攀道一。”(《寄杜使君》)“道一”即中唐江西洪州禅的宗师。马祖道一于洪州开元寺说法,创立了“洪州禅”,他将般若空观彻底化,提出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到“平常心是道”的理路,消除了佛性与人心的最后的隔阂,将终极意义的信仰构建在世俗伦常之中,认为“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肯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和日常生活,将禅门引向自然主义、自由主义,受到了士大夫的欢迎,在与北宗禅的较量中获得了胜利,刘禹锡、白居易、贾岛等人都与南宗禅宗师多有来往。洪州禅是禅门发展和转型的关键,贯休一生有十余年的时间寓居江西,洪州禅对他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大中十二年(858年)入洪州开元寺研修《法华经》后,贯休写下了很多简洁明快、描绘生活情状的诗作,打上了洪州禅的烙印,如
渔父无忧苦,水仙亦何别。眠在绿苇边,不知钓筒发。(《上冯使君五首》其二)
红黍饭溪苔,清吟茗数杯。只应唯道庇,无可俟时来。树叠藏仙洞,山蒸足爆雷。从他嫌复笑,门更不曾开。(《桐江闲居作十二首》其六)
诗作描写的虽是平平凡凡的日常生活,但它不止于描绘日常生活图景,而是在这些感性经验、具体的观照中达到了解脱性灵、涤荡灵府的超越目的,具有“活泼泼”的生命感,正如贯休说:“行亦禅,坐亦禅,了达真如观自在。”(《戒童行》)洪州黄檗希运禅师说:“汝每日行住坐卧一切言语,但莫著有为法。”日常生活经验取代了宗教仪式,具有了准宗教心灵境界的品格。贯休走上了由马祖道一等洪州禅师开辟的道路,在世俗生活中拾取真性、建立平凡的佛性我,我们看“远寻鹧鸪鸡,拾得一团蕈”(《春野作五首》其二),“薪撮纷纷叶,茶烹滴滴泉”(《赠灵鹫山道润禅师院》),肯定俗世的生活意趣,在寻常日用中参禅悟道,不正是洪州禅的修行方式么?贯休鲜有乏味枯燥的禅理诗,这类禅情诗却占了绝大多数,其动人之处就在于:它超伦理超道德,感性又超感性,准宗教式的人格神已落实为个体的心灵——情感的塑造,成为日常化、生活化的佛性我的建立过程,即“我意识我活着”。
次谈拂尘净心。贯休说:“我有一面镜,新磨似秋月。”(《古镜词》)“庐山有石镜,高倚无尘垢。”(《谢卢少卿惠千文》)心有净、染二分,就需拂尘净心,《四十二章经》云:“譬如磨镜,垢去明存,即自现形;断欲守空,即见道真。”这种拂尘看净的观念恰如神秀的偈语:“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人的心灵就如同明镜,本来清净,“无明”烦恼就像镜上的尘埃,若想去垢存明,就必须通过修行实践。宗密在《圆觉经大疏释义钞》总结北宗禅的思想为:“众生本有觉性,如镜有明性,烦恼覆之,如镜之尘,息灭妄念,念尽即本性圆明,如磨拂尘尽镜明,即物无不极,此但是染净缘起之烟。”这种承认净、染分别的观念,实则承认了佛性与人性的差别,若想证悟佛性,必须恪守外在的修行,这是“由定发慧”“二而一”的渐修的路径。虽然南宗禅发展迅猛、声势浩大,然而在8世纪后半叶至9世纪前半叶,北宗禅的影响尚有余绪。即便贯休在《寄大愿和尚在》中以“终须一替辟蛇人,未解融神出空寂”表示自己对“融神出空寂”式的渐修路数的不认同,然而,有趣的现象是,贯休的几句小诗很有北宗禅的意味:
汀花最深处,拾得鸳鸯儿。(《上冯使君五首》其一)
水蹴危梁翠拥沙,钟声微径入深花。(《春游灵泉寺》)
据胡大浚先生《贯休诗歌系年笺注》考证,这两首诗均作于咸通年间贯休在江浙一带禅游之时。诗人以一条由浅入深的路径,体悟那极致而神秘的佛性。这是贯休对北宗禅法的接受和实践,随物婉转,与造化同游,外在的形式已转化为情感形式,颇有“道不自器,与之圆方”的美感。这类诗只有四例,我们不能凭此把贯休强行划入北宗禅的阵营。山河大地、花月楼台,皆在一心耳。
二、“外师造化”:水流花开的世界
(一)尚“自然”的审美倾向
虞集在《诗家一指》中说:“心之于色为情。天地、日月、星辰、江山、烟云、人物、草树,响答动悟,履遇形接,皆情也。拾而得之为自然,抚而出之为己造。”这段讨论恰道出“自然”之枢机,心源为根本,以生命的真性观照世界,万物自然而然地呈现,与造化优游缱绻,方得天地之大本。前蜀藏书家王锴评价贯休云:“长爱吾师性自然。”(《赠禅月大师》)道出了贯休的僧家本色:“自然”,佛语就有“自然”“自然智”“本来面目”的说法。它决定了贯休的诗美理想。
贯休向往“自然”,即生命真性的开显,展现为不假修饰的、不造作的、自然而然的态度和表达。贯休说“至理契穹昊”(《送崔尚书朝觐》),“文章拟真宰”(《遇叶进士》),认为人要参赞天地化育,语言文字也要效仿天地的运转,自然地表现生命的真实,有如“目即往还,心亦吐纳”,“是有真宰,与之沉浮”,且看贯休说:“好句慵收拾,清风作么来?”(《秋居寄王相公三首》其一)“道情不向莺花薄,诗意自如天地春。”(《春末寄周琏》)诗谓好诗,句如清风自来,兴会之致,自然感发,好比参禅时即定即慧的体验,颇有邵雍“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的境界和韵味。“自然”令贯休性灵舒展,得返天全。他并非强调偶然性,而是根植于文化——心理结构的某种先验形式,是一种合“度”的运动性与自由感。所谓“一切声是佛声,一切色是佛色”,以法眼观世界,岭头白云、曲涧流水,已是活泼泼的新世界,因此贯休感叹道:“支公放鹤情相似”,“溪鸟林泉癖爱听”。
有趣的现象是,贯休一边崇尚“自然”,又一边苦吟:“坐侵天井黑,吟久海霞蔫。”(《闻新蝉寄桂雍》)“高奇章句无人爱,淡泊身心举世嫌。”(《山居诗》其五)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贯休曾以“举世言多媚”(《读孟郊集》)概括当时的社会及文学风气,故而他以僻、新、奇等“忤俗”的风格取向反抗晚唐绮丽的诗风,超越现有的僵硬的秩序,求得真性的回归,因此,他批评好友吴融“或以文害辞,或以辞害志,或以诞饰饶借,则殊不解我意也”,道人所未道,仍是“绕路说禅”的表现。贯休说“逸格格难及”(《观棋》),关于“逸格”,《益州名画录》曰:“画之逸格最难,俦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耳。”它仍以不假人工、迥出天机的自然为根本,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审美判断。然而贯休却并不能完全达到这样的标准,说明他在为诗的才学上还稍有欠缺。退而求其次,只能苦吟罢!
(二)尚“人情”的审美趣味
贯休深受中国文化的滋养,徘徊在世间与出世间,他一边随缘任心,一边又拂尘净心;一面实践洪州禅的顿悟,一面又接受北宗禅的渐修,这不是很矛盾吗?他怎样将两者糅合在一起?
这与情本体的积淀与塑建有关。伽达默尔说:“艺术的万神庙并非一种把自身呈现给纯粹审美意识的无时间的现时性,而是历史地实现自身的人类精神的集体业绩。所以审美经验也是一种自我理解的方式。”作为历史中的个体,贯休需要完成自我理解,以“人活着”为核心,思考“人如何活”的多种途径和可能,他的语言凝聚着历史的积淀,融合着与之同存的一切事物,在境遇中作出真实的回答。因此,尽管贯休身为方外之人,他的独立性中必然潜藏着历史的积淀,即情本体的塑建。《周易》有“类万物之情”,《论语》有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孔子重视内心情感的满足,并将仁学构筑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现实生活中,逐渐形成了重视实用的文化传统;而庄子虽否定为物所役的“物之情”,却仍提倡“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的“无情之情”“性命之情”。这就导致了中国禅并不排斥伦常日用和情感体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成为禅家的常用话头。李翱云:“圣人者,岂其无情也?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别,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情理交融在一起,理性蕴藏在感性生命中,共同塑造着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儒家功不可没。贯休“家传儒素,代继簪裾”,精通儒学,面对百姓罹难、战事纷起的时局,常流露出忧国忧民的情怀:“政乱皆因乱,安人必籍仁。”(《送吏部刘相公除东川》)“男儿须展平生志,为国输君合天地。”(《塞上曲二首》其二)然而,他的感伤和豪情最终都归于平静:“在尘出尘,如何处身?见善努力,见恶莫亲。……安问世俗,自任天真。奇哉快哉,坦荡怡神。”(《大隐四字龟鉴》)禅成为先验的形式,渗透在他的感性生活中,使其情理结构具有了“度”的合理性,贯休成为真正生存于世俗中的和尚,情感体验和寻常日用是“活着”的根本和源泉,洪州禅的“平常心是道”“触类是道而任心”就与心理——情感本体的构建有关。同时,贯休是出色的诗人,他会通过文字表现生命的真性和超越,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所以,无论是随缘任心还是拂尘净心,都是诗人贯休在不同的境遇下展现的生命真性,只是情与理在融合中的比例、节奏、运动不同,即是说,心理——情感本体的内在构成上有差异,并非仅是贯休思想的驳杂。顿悟和渐修的指向皆是那绝对无差别的境界,刘勰说:“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最终都要建设在真实的情感中,林语堂说得好:“当一个人悠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进而,在贯休的诗作中,语言符号的形式美让位于生活的真实,构筑了“人情”之“原美”。贯休说:“霞外终须去,人间作么来?”(《送僧归山》)“孟子终焉处,游人得得过。”(《经孟浩然鹿门旧居二首》其一)“作么”“得得”等口语、叠词的运用,以“真”为准则,闪动着“人情”的光辉,我们从中感受到的不是兢兢业业的苦行僧形象,或吟咏风月的士大夫,而是憨态可掬的长者形象。通俗的语言背后是“人情”,这是贯休最为可贵之处。
(三)尚“圆融”的审美境界
清凉文益禅师说:“贵在圆融。”所谓“圆融”,“圆者周遍之义,融者融通融和之义,若就分别妄执之见言之,则万差之诸法尽事事差别,就诸法本具之理性言之,则事理之万法遍为融通无碍,无二无别,犹如水波,谓为圆融”。圆融是当下证悟的佛性,强调与我共存的世界,是贯穿佛性论、修行论、境界论的重要津梁。这里我们探讨贯休的圆融观。
贯休虽然反复申明三界唯心的道理:“吾师别是醍醐味,不是知心人不知”,(《禅师》)但在创作上,他亦注重与之同存的生命世界,强调“平等不二”“梵我一体”的统一性与通透性。贯休尝云:“对花语合希夷境,坐石苔黏黻黻衣”。(《陪冯使君游六首·游灵泉院》)关于“希夷境”,《老子》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这不可言说的境界正是“不二法门”,是当下证悟的圆满。又如:“真风含素发,秋色入灵台”。(《诗》)“坐来惟觉情无极,何况三湘与五湖”。(《中秋十五夜月》)等等,皆呈现出“梵我合一”的“圆融”境界,当“我”的心性体察世界,世间万物亦以自在的状态进入我的灵府,是贯休在即定即慧的体验中,实现的“物我互观”,这仍是主体的创造和超越,但它不止于心灵的物态化,而着眼于物我的双向流动过程。“共感”是圆融的前提,洞天不在尘寰之外,就在这活泼的感性世界中,花自飘零水自流,我在清风明月间,槿篱茅舍中自有山家风味。
然而,贯休在圆融的体验中,诗人的视点还没有完全失落,我们仍旧可以找出那个隐藏着的“我”在。这仍与当时的禅风有关。马祖道一提出“即心即佛”等命题肯定了人的日常生活,实则承认了个体的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其法嗣南泉普愿曾对门人说:“尔若是佛,休更涉疑。”更是将“我”作为信仰的支点,贯休就以“长忆南泉好言语,如斯痴钝者还稀”表达对南泉普愿的赞赏和认同。所以,无论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关键在“我”,都要归结于己“心”的体悟和创造,如同王昌龄说:“凡属文之人,常须作意。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巧运言词,精炼意魄。”刘禹锡说:“心源为炉,笔端为炭。”贯休说:“寄谢天地间,毫端皆我有。”从心源上悟,再到得物之真,境界生成,我“心”或隐或显,成为潜藏的轨迹贯穿始终,流动不息,周流六虚,圆融无碍,所谓“圆融心海,本无障碍”,“心”是根本和源泉。“外师造化”,仍要回归心源,回到根本。
三、结语
贯休禅法与才学兼备,是诗僧中的佼佼者,元徐琰《跋》云:“若夫禅月国师,又高出一头地。……后人详味其语,正宜高著眼。”晚清胡凤丹《重刻禅月集序》云:“贯休亦奇哉!若夫证圆通于水月,参妙谛于烟云,一字一言,无非棒喝;读是诗者,当爇妙香奉之。”贯休真正将禅与诗融会贯通,他凭借极高的佛学造诣和艺术天赋,在禅与诗不断地交融和渗透中,契合天地造化,复归生命的本明,自觉反抗晚唐的绮丽诗风,自发性地推演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思想,使这一命题得以合理地历史地建立起来。他摒弃了外在的宗教迷狂,始终以具有人情味的“自度”追求终极境界,在灿烂的感性中发现生命的真实,是真正地生活在人间的和尚,亦如贯休高唱:“数声清磬是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天地苍茫间,唯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