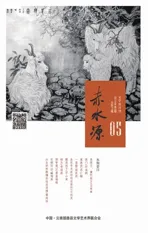怀念一棵树散文
2019-11-13申桂先
申桂先
爷爷的屋前有一块地,地里,除了一些叫不出名的花,还有一棵粗壮的核桃树,据说是三叔栽的。一到四月,树便开出一串串黄绿色的小花,透着一种春意盎然的诱惑和一种期盼。爷爷说,核桃有双花,雌雄同株异花。那长长的穗就是雄花,不结果……那时候,爷爷说的这些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那掉在地上,长长的像毛毛虫的核桃穗,捡拾一把,用水一焯,便是孩提时代的美味。
等待核桃成熟的过程是漫长的,每天仰头望着那高高的树梢,一遍遍问爷爷核桃什么时候才能吃,为什么核桃熟得那么慢呀……问的次数多了,爷爷便说,时间是个顽皮的孩子,你越盯着它它越慢,不如来帮爷爷干活。于是,便不再去看,安心帮爷爷做些琐碎小事。
核桃终于可以吃了!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敲落下来,等不及它晾干裂壳,便用石头砸开那绿色的外皮,再敲开核桃那坚硬的外壳,一点一点地剜着核桃仁吃。吃不上几个,手上,尽染上外皮的颜色,好多天都洗不净。尽管如此,核桃的美味诱惑着我,也顾不得那么多,每天都要去敲几个下来,然后“饱餐一顿”。
爷爷每次吃饭前都要端着碗到核桃树下,双手举过头顶,口里念念有词,如此片刻后,向前躬着身子作揖,然后再回屋开始吃饭。我很好奇,便问爷爷为何这样。一开始,爷爷说我还小,说了我也不懂。后来,时间长了,问得多了,爷爷便拿一条木凳,坐在核桃树下,点上旱烟,长长的吐了一口烟气后,以一种平静的语调开始讲述。
“你奶奶走得早,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生了病,也是拖着。一开始只是有点咳嗽,拖着拖着,就喘不上气来了,没几年就走了。你奶奶走后,每次吃饭我都想起你奶奶,尤其是我做好吃的时候,我都想让你奶奶先吃一口……”,我忍不住打断:“可我没看见奶奶呀,她怎么吃?她走到哪里去了?”“走了,就是死啦,到天上去啦,你奶奶眼睛不好,所以我使劲的把碗举过头,好让她瞧见。死了的人吃饭,我们活着的人是看不见的”,“那,饭菜怎么没有少呢?”,“反正你奶奶每次都吃的,我们活着的人看不见死了的人,但她们能看见我们……”爷爷絮絮叨叨的说了半天,年幼的我终究还是不明白。
爷爷在核桃树下折腾一番后,回屋在桌子对面放上一个碗,碗里盛着一些饭菜,一双筷子搭在碗上,有时候放一碗一筷有时放两碗两筷。爷爷每次吃饭都很慢,时间都很长,爷爷说,一方面是因为奶奶牙不好,想陪着奶奶慢慢吃,一方面也想和奶奶多呆一会儿。
至于有时为啥放两副碗筷,爷爷只说其中一副是为奶奶准备的,至于另一副,便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如果问得多了问得急了,爷爷要么闷声抽烟,半天不说话,要么流着泪,连声叹气。流泪叹气的爷爷让我有些心疼,有些害怕,便再也不敢问。
关于三叔,我是从别人的嘴里听到的。据说,三叔很内向,很腼腆,长得白净秀气,像个大姑娘似的。三叔十五岁那年,到河对岸割猪草,被邻村几个同龄的孩子欺负,以三叔偷他们的猪草为借口,瓜分了三叔割了几个小时的一箩筐猪草,还将三叔打得满身是伤,更可恨的是,还将三叔的裤子扒去,丢在河里冲走,极尽侮辱。三叔回来跟爷爷哭诉,爷爷了解到那些都是邻村有权势人家的孩子,责骂了三叔几句,叹了口气,便作罢。据说,三叔那天晚上哭了一夜,天未亮就上吊自尽了……
据说,自此,爷爷很自责,总说,三叔走了也好,以后重新投个好人家。
我想,爷爷饭桌上的另一副碗筷一定是给三叔准备的吧。
记事起,爷爷就是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以卖香蜡烧纸为生。从街上进货来的烧纸,是没有孔的,需要用打孔器一点一点的打好孔,再裁小,一刀纸捆为一捆,一捆卖了可以赚两角钱。只要不下雨,只要不冷,爷爷总是在那棵核桃树下给烧纸打孔,左手拿打孔器,右手拿一个木锤,一下一下,快而有力。村里的人称这活为打烧纸。打得多了久了,爷爷的手上便会起泡,爷爷也不在意,用针戳破了擦点点药酒,便又开始打。蜡呢,是自制的。先把竹子削成筷状,将前半截裹上烧纸,烧化半锅白蜡,一手拿着一把竹棍,将裹上烧纸的部分放在锅里滚一转,便拿到外面去吹冷,晾干,如此反复几次,白蜡便制成了。如果要制红蜡,烧化半锅红蜡,用制好的白蜡放进去滚一转,拿到外面去吹冷,如此两三次,红蜡便制成。除去材料费,一支蜡烛可赚一角钱。
那时候的我,不喜欢看爷爷打烧纸,时间久了觉得无味,瞌睡都看来,于是便在核桃树下睡觉。睡醒了,爷爷已打了高高的一摞烧纸,然后帮爷爷把它们搬回屋。那时候的我,喜欢帮爷爷把一大把一大把的蜡烛拿到屋外去让风吹冷,只需围着核桃树转几圈蜡烛便冷了,觉得很好玩,很有趣,觉得爷爷好厉害,居然会制造蜡烛。那时候,大伯和我家,夜里点的都是爷爷的蜡烛。每到赶集天,不管生意好不好,爷爷都会买一个饼子或几颗糖揣在兜里回来给我。那时候,只要爷爷一赶集回来,我就偎上去掏他的衣袋。有时爷爷像个调皮的孩子,把东西藏在另外的衣袋里,等我翻找半天很失望的时候,才魔术般的拿岀来,我便会欢呼雀跃。
有时候,爷爷也会在核桃树下看书。搬条凳子,戴上老花镜,在嘴里沾点口水,便开始翻读书页。爷爷看书,总是喜欢读岀声来,是那种拖长了声调的唱读,引得我哈哈大笑,笑过后,偎在爷爷身旁,聚精会神地听。爷爷的书里,有牛郎织女,有祝英台,有孟姜女,还有武松,有诸葛亮……那时候,爷爷在我心里,是天上的神仙,是挂在天空的太阳,是夜晚树梢上的明月,让我崇拜,欣喜,给我的童年注入了无穷无尽的快乐和期待。
不知道爷爷是什么时候老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爷爷不再赶集,甚至很少出屋。也不知,我,什么时候就长大了。忙着在外求学,忙着为生活奔波,甚少回村。
爷爷一个人在那小屋生活了几十年。爷爷走的那个冬天,未就业的我,怀着郁闷颓废的心情回去,未等他入土,便匆匆离开,为就业奔忙。那时的我,不懂离别。
如今,爷爷的小屋已经拆了,那棵核桃树也被大伯砍了,小屋和核桃树的位置,已被大伯家新建了房屋。
从此,那棵核桃树,在梦里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仿佛时光深处,它不曾存在过。可是,它又鲜明地挺拔在心里,随时光疯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