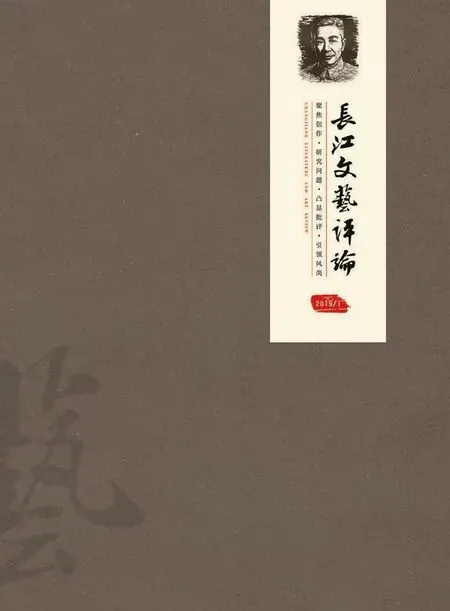一种从物象到墨象的写作
——评《黄斌诗选》
2019-11-13
黄斌化物象为文墨,使诗歌以文字的形式成为独立的艺术存在。他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常从微处切入庞大的历史,呈现鲜活的人生百态,历史与当下共时地存在于诗中,古与今在对照中互相生长。黄斌的诗兼具东西方元素,诗中既有超验式的崇尚自然的浪漫写作,又糅杂了康德式的哲思以及中国古典的道家哲学,中西文化元素的冲突使黄斌的诗呈现出陌生化的诗意。本文拟从中西合璧的观物、诗中的文化符号、共时性的现实书写来探讨黄斌的诗歌艺术。
中西合璧的观物
“观物”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象的,只要是实践主体指向的对象或目的,都被邵庸视为“物”。“观物”不仅是一种态度和认识,它已经具备了贯通于体悟、识察与实践的品格。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万物皆可入象。在黄斌创作的一系列“观物”之诗中,其物象大多是山水之象,隐藏在“物象”之下是古今交织的旖旎画卷。古代山水诗中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发展,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心物关系。而观物者的心态导致了其对抒情范式的选择。黄斌的观物,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传统中的观物思想,另一方面,诗人独具动态的观物视角和心物关系的自然转换,与西方哲学思想相结合,从理性批判的角度审度观物,因此相较于传统的观物,显得更为理性。
《江汉平原的天空》一诗呈现了动态的观察的视角:“走在平原上到处都是圆心/地平线跟着行走旋转/从地平线到头顶和身后,都是江汉平原辽阔的天空”。“地平线”“旋转”“圆心”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对广袤土地的描摹,已经超越了古人对于物象的认知。接下来诗人写道,“它的表情或许冷漠或许闲适恬然”,这即是“天地不仁”,天地无所谓仁与不仁,一切都是人的观感导致。“听”是诗歌后部的语言核心,正是从这一核心出发,激荡出巨大的语晕:
偶尔听到不远处沟渠的流水
在黑暗中响
像听到狗低沉的呜咽闷声退回胸腔
意杨高大的声音命定似的响在高处
流水的“响”通过明喻转换成了呜咽闷声,“闷声退回胸腔”和“响在高处”将内与外、高与低的声音整合,天地间的声音浑然一体。此时诗歌开头的广阔空间被缩至半圆器皿:
我们这些有生命的小个子
连同我们坚硬的器械
时时望着远处和头顶
这个倒扣着的玻璃器皿
这个时时也自己变色的玻璃器皿
这呈现的不仅是物理层面的感受也是内心观感。从开头的以人为圆心的对于江汉平原的描写,到了文末的人被困于天地,从人的大,写到人的小,大小之间,心物关系转换自如,诗人虽未描写个人感受,心情的变化却丝丝入扣,跃然纸上。
在《江城五月落杨花》一诗中,诗人用满城杨花这一景观,将李白、屈原的时代和现代并置,凸显了古今通用的意象:黄鹤楼、奏梅花、吹笛、布谷声滴翠等。诗人写道:“在语言终结的地方音乐开始了/整座武昌城闻奏梅花”。“杨花”这一意象是外部诗情和内部忧伤的结合体,“李白前后的诗人在杨花的身世间行走”,此处的杨花却指向“青楼女子”,黄斌在诗中写道:“杨花坠身入草白衣素身的民间女子/去了青楼”,杨花从单纯的“景象”转变为“青楼女子”,最后指向“弥漫的到处散播的生的忧伤”,这正表现了心物关系的流畅转换——对于“杨花”多重能指的阐发勾连起古往今来诗人的惜春、放浪与忧伤。在结尾处,“我看到麻雀在草地上忘我的吃着杨花的种子/小嘴边满是花絮/像一个贪吃的小女孩嘴边没有抹净的棉花糖”。童趣的镜头消解了之前诗行的沉重,似乎江城五月的杨花仅仅构筑了一个空濛的梦境。
黄斌深谙中国古典物象的神韵,在现代诗的创作中,这些物象被赋予了现实意义和现代色彩,而西方哲学的思辨又使得这种观物脱离了物我之间的羁绊,进入了理性批判的空间。在《荆泉山月歌》中,诗人将月亮写成一个孤独的“自我反驳和自我和解的永恒轮回的形象”。在《献诗——给张志扬》中,黄斌写道:“我那时刚学了点康德不时想着他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还读了一本书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在《咏怀》中,黄斌化古典与现代,将古典意象与西方哲学结合,“在表象的重压下/整个夜晚都是秋雨菊花/我嘲笑着犬儒主义的快乐/坐在楼顶/和秋月比谁更空明”。“表象”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康德就认为,“处于我们之中的、被称作‘表象’的东西与客体的关系的基础是什么”,这一问题“构成了解答形而上学的全部秘密的关键”。“表象”这一西方哲学术语将古典文学中的“秋雨”“菊花”“秋月”这一系列与秋天相关的意象陌生化,这种陌生化来源于中西思维的切换,而诗歌尾处的“犬儒主义”和“空明”又仿佛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古典之美的并置,诗中的文化符号相互勾连,带来东西文化冲突,这种冲突激荡出巨大的陌生的美感。
黄斌熟谙中国古典诗学传统,而西方哲学思潮又给他提供了充分的养料,因此黄斌的诗也呈现出某种崇尚自然的倾向,诗人在描绘自然中传达自己的文学理想和人生态度。《江水》《咏神龙架冷杉》《苞芽》《夜宿归州》等景物诗,都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不同的是黄斌的诗是以中国古典诗歌为本,西方哲学为用。黄斌认为:“西方有关语言和文字的思想,到了德里达这里,似乎和东方智慧开始接近了。另外还有一种接近,即诗和哲学的接近,回到老子和巴门尼德。”诗人见微知著地从家族史、地方史、县志等入手,将写作的触角深入到传统的文化底蕴中。可见,黄斌的诗其底蕴是东方的,同时也受到西方哲学潜移默化的影响。
知同求异的文化符号
在《追问的十四行》中,诗人谈及诗的功用:“诗歌已经间接伤害了生活/一个时代的伟大就是通过物而显现的/渴望发展的精神”。诗作为形而上学的最精练的文字表达方式,它的产生过程即是对物象的转化过程,世间百态最终以文字的形式凝聚在诗中,物象此时已经发展成为留存于符号中需调动想象力来获取的抽象的墨象。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诗人对于文化符号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例如在《四面相》中,沉重的历史通过黄斌的书写凝聚成具有反讽意味的符号:
我无意在今天解读四面相这个现代建筑所展示的空间策略
当年站在四面相上
我看到丘陵湖泊古老的城墙和房屋
从八个方向朝着四面相匍匐
太阳月亮和星辰围绕着它
升起然后落下
“四面相”和《坛子轶事》中的坛子类似,“坛子”和“四面相”都是人造之物。坛子作为与荒野格格不入的景观,“它使凌乱的荒野/围着山峰排列”。“四面相”作为”文革期间湖北省蒲圻县的中心和标志“成为那整整十年的夜与昼/一个中国县城矗立着的精神四面体”。“四面相”与“坛子”都是与周围景观截然不同为了制造秩序而建立的符号。这两首诗一个是从荒野到美学,另外一个则是从日常到政治。
在《面壁》中,诗人并置了“实体与梦想”“物象与泡影”“事物和倒影”三对中西方内涵相似的词语,而在诗歌的末尾,他写道:
甚至还可以说
在哪里不是面壁呢
但是我不
我仍然不能放弃差别
“面壁”是关照内心的表现,这体现了“我”对于中西哲学内部的共通性的把握,但是最后两句强调了“我”的知同求异。这表明黄斌立足于西方哲学,一直在考虑如何在东方写作中寻求一种对人类经验的通用性的符号表达。
“汉字”是黄斌唤醒的符号之一。在《题八大〈莲房小鸟〉》中黄斌写下了:“和尚指使水墨/在国破家亡之后/以墨象代替物象。”与水墨画类似,汉字最终通过书法“以墨象代替了物象”在诗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墨象。
《敬惜字纸》一诗用“写字”串起对母亲一生的梳理。诗人将“字”“每一个汉字发生的故事”“母亲写字”“我发疯似的爱上了汉字”串连起来,勾勒出了母亲的一生。“母亲已经活到汉字里去了。”汉字是母亲的栖身之处,它包括这一行为的内涵,正如写诗也包括了这一行为产生时的所有的遐思。黄斌的诗与书法有共通之处,其诗除了诗中所述,还包括成诗之前蓄势待发的张力。
母亲去世后,我通过“文字”开始了解母亲,也爱上了写字。在诗中“写字”这个行为被赋予了多层含义:写字即是记载,记载即是故事,每个字的来历有着自己的故事,而它一旦被使用,又能去书写新的故事,这些故事在阅读中被唤醒,给人们灵感去开始新一轮的书写。最终诗歌从写字这一行为落脚于字的本体,每一个汉字既是对“她的过去”的记载,也不断地推动我“写字”的行为。对于写字这一行为的持续追求,对于字的敬惜是对历史、对生活的敬重。在诗中,“字”不仅仅是记录的符号,它成为整合了时间的抽象的物象。
黄斌的诗歌创作有两方面的追求:一是为了求真的书写;二是为着“存活”而进行的书写,此处的“存活”并非生存之意,它接近于存在,即文字最终会独立于写字的主体和行为,突破个人化的限制并打破表层含义的束缚,演化成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墨象。
《骨头的秩序》这首诗表面上在写骨头,实际上诗中的骨头和汉字是互文的。被遗忘了历史特征的文字和骸骨一样。骨头的疼痛映射了文字成为墨象的痛苦而艰难的过程,但今天人们使用文字时并不会意识到这些,一切都隐没于集体无意识之中。
如何才能打破固有的符号特征,使其以崭新的面目呈现出来。黄斌一方面用西方哲学的术语入诗,这些词语与古典韵味碰撞,激发出陌生感,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文字艺术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诗歌是使文字成为艺术的途径之一,艺术的诞生是打磨内心的过程,让内心成为一张宣纸,而人类经历的种种最终会以墨象的形式呈现。符号化的墨象是否能唤醒人类对于文字的历史认知,是否能加深人类对于文字历史与美感的认知取决于对内心的打磨。
共时性的现实书写
黄斌的诗歌创作立足于当下,擅长从家族史、地方史、县志或具体而微的人文景观切入,将历史与时间的画卷翻开一角,供人观瞻回想。黄斌的诗具有时间感,并不是因为语言本身的特点所致,汉语本身就是一种当下的语言,对于时态的省略,使得汉语对话永远好像存活在当下。
黄斌诗中的现实性则表现于对世态的“反刍”,历史与现实在“反刍”中被消化,去伪存真,正如黄斌在《咏怀》所写的:
从现在开始,去做一头牛
负重和耕耘都是次要的
主要是得准备四个胃
去反刍这无法消化的俗世
“对世态的反刍”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体现了诗歌创作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反刍”有时间上的延缓性。这二者结合则表现为黄斌诗中疏离的烟火气——对世态的描摹呈现出一种朦胧、醒与梦之间的状态。黄斌诗中的烟火气不是当下的,而是沉淀于文字中的有距离感的现实,这种距离感是经由以下途径实现的:一是共时性结构使得文本突破时间的桎梏,同时又赋予诗歌以厚重的历史感。二是通过山水景观激发出古今共通的感慨,使得当下的烟火气具备厚重的历史韵味。三是梦境的特征呈现出了焦距模糊的当下。总而言之,正是历史与时间使得诗中的烟火气褪去了其原本浓烈的颜色——愁苦变得稀薄,而人生百态却淋漓泼洒、鲜活生动,呈现出一种“庄周梦蝶”般的如梦如醉的状态。
黄斌在《陆水河上的老粤汉铁路桥》对于具体的“烟气”有如下的描写:“火车头像一个巨大的京剧脸谱/呼啸着来了又走/它喷出黑烟被甩在铁桥上空/慢慢变灰变白/变成铁路桥上的云朵”。浓烈的黑烟最终变得稀薄,除去了渣滓,成为一朵白云。黄斌诗中的烟火气是抽象的,是对生活的描摹与刻画,但是黄斌诗中的烟火气没有现实生活中的浓烈,与这火车的浓烟类似,最后变得稀薄,表现为一种有距离感的烟火气。
大多数情况下,黄斌的诗的烟火气循古意而来,用了共时性的结构,借助了历史的古韵,来消解当下的现实,譬如《夜过洪泽》《砖茶吟》《在恩施州看到玉米》《蒲圻县新店镇》等。再浓的烟火气,隔了千年历史,也逐渐变得氤氲稀薄,最终沉淀为诗歌的底色。因此,读黄斌的诗,如品好酒,诗中的醇香正是历史的底蕴:中国的先哲与诗人安居在黄斌的诗文中,庄子的无用之用,阮籍的竹林醉态,桃渊明的辞官、抚木,杜甫、贾岛、唐寅等古代文人墨客在诗中一一地鲜活起来。
在《夜过彭泽》一诗中,诗人描述了凌晨街道旁小摊贩的打烊的场景:
已是凌晨一点街道冷冷清清
建筑破旧
像回到黑白的七十年代
路边的排档刚刚打烊几对夫妻相的男女
在收拾物件和刚刚结束的一天
街对面亮着幽暗粉红灯光的发廊边上
还坐着几个沉默抽烟的男人
这就是我看到的彭泽县
一旦进入历史,平淡无奇的街景顿时激发出了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美感。因为是陶渊明的辞官之地,彭泽深夜的街景变得苍凉、缓钝,历史的厚重感在深夜打烊的街铺旁,通过嵌入酒这一内涵厚重的诗学符号将庸俗的生活激活:
模糊 还带着某种暧昧的气味
像我想象中在这里做官的陶潜
当时很想找一个地方喝酒
并泼酒向地看着酒水把土地浸湿
虽说陶潜的亡魂不在这里
但这里是他个人出发的地方
他在这里与政治划清了界限
并进入了审美
“酒”从酒色转换成我想象中的对于先贤泼酒向地的致敬,最后成为诗酒一体的象征,现实的庸俗转换成历史的雅致,此时诗中的烟火气已经被蒸腾、净化,变成了美的存在。当下的现实进入了历史,又一次成为历史的沉淀与延续,同时诗歌文本也完成了一次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成为了共时性的诗歌文本。
《蒲圻搬运站》则是较为特殊的一首,这首诗借助了梦虚幻、易散的特征呈现并最终消解了诗中的烟火气。《蒲圻搬运站》通过描述记忆中儿时在蒲圻镇生活的经历,带着我们走进一个蒸腾的梦境,梦呓式的叙述使得历史以最鲜活的样态呈现出来。记忆中儿时与少年的岁月被凸显得鲜活、灵动、热气腾腾,悲哀不过是懵懵懂懂的一瞬间,随即被蒸腾的热闹冲散,这应该就是生活原本应该有的样子。
诗中弥漫的烟火气在末尾被大雨冲刷,了无影踪,一切亦真亦幻,正如诗人在开头所说:“蒲圻搬运站不过是我心中的某个地方/甚至可以说它是虚拟的 没有/存在过的 时间为1976年到1985年。”从开始时的蒸腾到结束时的萧索又契合了生命的历程,小镇的历史从固化的文字记载转化成主观的感受与存在,而黄斌诗歌创作的意义正在与此——在对文学史和人类经历的沉思与记录中过滤生活、去伪存真。
注释:
[1]王培友:《论两宋理学“观物”与理学诗类型化主题及程式化表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2]贾玲、李晓婉:《论山水诗主体观物心态的转变对抒情范式的影响》,《天府新论》,2008年第3期。
[3]袁建新、向桂珍:《康德的表象说及其哲学意义初探》,《理论与现代化》,2011年第3期。
[4]黄斌:《老拍的言说》,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