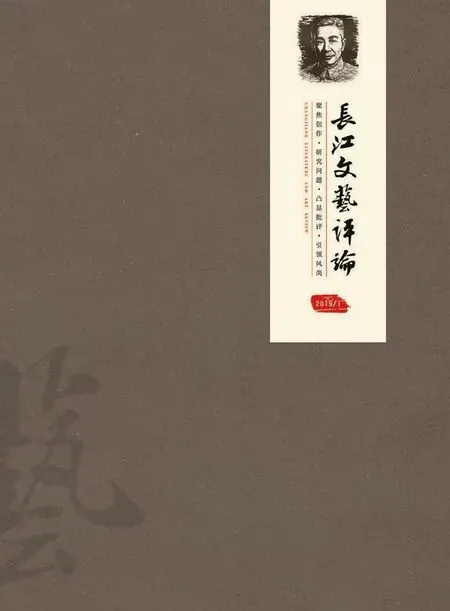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影的观念革新与创作流变
2019-11-13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电影在个体心灵“伤痕”的吟咏中苏醒,在对影像造型“美”的寻觅中进行“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探寻,更在产业改革、市场经济大潮中经受严峻考验而奋进。此间,电影观念的蜕变革新,电影审美风格的变化,导演代际的变迁——从四、五、六代到“新力量”群体,勾勒出了中国电影四十年来的观念革新与创作流变之轨迹。
一、从荒芜中复苏(1978-1990)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时期的文艺界,普遍形成了两大共识:一为以人道主义精神重建人的主体性,另一为告别“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观念,回归文艺本体。新时期电影作为新时期文艺思潮的一支,同样迎来了观念与创作的全面转型,即从摆脱“三突出”“高大全”的“文革”遗风与样板戏窠臼,到人性人情与艺术自觉的“苏醒”。
(一)人的觉醒
重建人的主体性,是新时期初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呼唤失落已久的人道主义精神,肯定人的主体性,塑造人性的真、善、美与人生理想,弘扬自由、个性、民主等精神诉求,是新时期伊始文艺界压倒一切的任务。
开风气之先的是第四代导演。“人的觉醒”是第四代导演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主题。滕文骥在电影《苏醒》(1981年)中,通过批判“极左”政治对个体造成的精神伤害和情感创伤,成为个体自我意识“苏醒”之隐喻。
与“文革”样板戏中的英雄主义叙事不同,第四代导演将镜头对准了一批质朴坚忍的小人物:《乡音》中的青春少女、《北京,你早》里的售票员、《邻居》里为住房问题困窘的知识分子……这些小人物中的正面人物被塑造成理想化的“道德完人”,如郑洞天导演的电影《邻居》(1981年)里,离职老干部刘力行在处理邻里纠纷时,秉持公正、亲和的原则,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以保障邻里的住房权益。这种理想化的人物形象,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启蒙思潮所推崇的“大写的人”,是世俗与精神、理性与情感共存的个体,代表着第四代导演的人格理想。
第四代导演的影片中大量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自知视角和部分限知叙事,表达“我”对历史和现实的主观感受与感性思考,凸显着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小街》(1981年)《青春祭》(1985年)等电影都是以画外音的方式建构回忆性的叙事,叙事者“我”自由出入于历史和现实之间,体现出清醒的主体反思意识和对话精神,使人从历史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发出了作为人之主体的声音。
有意味的是,第一人称画外音的主观叙事方式,与第四代导演所“推崇”的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纪实理论背道而驰,构成了某种意义上可以揭示第四代导演隐秘心理情结的“阿喀琉斯之踵”,凸显着他们的启蒙者视角。如张暖忻导演的《青春祭》中,女知青与傣族农村的生活形态构成了一组看与被看的关系,第一人称的画外音显在地成为了导演主体性表达的途径,其背后所浮现的正是一种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启蒙者视角。这种启蒙者视角,同样显见于第五代导演的创作中,第五代的启蒙者视角体现出了强大的主体意识,这种张扬的主体意识甚至超越了叙事层面,而充溢于象征性的影像视觉造型之中。
与此相应的,第四代导演所聚焦的“个体”,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层面上的“群体”。其所呼吁的“人的主体性觉醒”,在其创作中呈现为不够彻底的“群体主体性”,即李泽厚所主张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主体性,个体的经历背后潜藏着一代人、一个群体甚至整个民族的历史经验与感情吁求,体现出急迫地为人民、为民族“发声”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第四代与第五代在寓言性和象征性上颇为类似,第五代电影中的主体形象是“小我”之中有“大我”,背后往往有整个民族或一代人的支撑,同样表现为一种理性主体性或群体主体性,而“个体主体性”的真正觉醒,则要到九十年代第六代导演的某些电影中才得以实现。
人道主义精神下人的主体性的重新建立,表明中国电影中的人物塑造开始向现实主义回归。第四代导演的现实主义美学显在地受到了巴赞理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等外来电影理论和创作的影响。新时期伊始,过度戏剧化及其引发的虚假成为众矢之的。在这样的期待视野之下,巴赞纪实美学的译介在八十年代初期形成了一个理论旅行的热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第四代导演对巴赞纪实美学的理解存在有意误读的成分,他们“所倡导的,与其说是巴赞的‘完整电影的神话’‘现实渐近线’;毋宁说是巴赞的反题与技巧论:形式美学与长镜头及场面调度说……在巴赞纪实美学的话语下,掩盖着对风格、造型意识、意象美的追求与饥渴”。这样的选择性接受,使得第四代导演的纪实性探索浅尝辄止,转而以诗意、抒情、心理化、散文化风格彪炳电影史。
(二)回归电影本体
告别“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观念,回归文艺本体,是新时期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的另一重要目标。围绕电影与戏剧、文学的关系,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等艺术观念,在电影理论界与创作界展开了热烈的理论争鸣与创作实践。1979年,白景晟的《丢掉戏剧的拐杖》与钟惦棐的《戏剧与电影“离婚”》两篇文章,对长久以来中国传统的“戏剧化”电影观发起了挑战。同年,张暖忻、李陀发表《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更新中国的电影观念,回归电影艺术的本体,呼吁“形成一种局面,一种风气,就是理直气壮地、大张旗鼓地大讲电影的艺术性,大讲电影的表现技巧,大讲电影美学,大讲电影语言”。这一第四代的美学宣言,迅速在实践中得到了回应。第四代导演早期的电影热衷于形式技巧上的探索,但其突破主要体现在电影的叙事结构层面。第五代导演则延续了对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探索,在视觉造型美学上取得了划时代的突破。
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创作中,影像视觉造型具有重要的表意功能,画面仿佛独立出来,凸显于叙事情节之上,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美学价值的审美对象。陈凯歌在拍摄《黄土地》(1985年)时提出,“我们一定要用变革了的语言,讲述起初的历史”,一语点明了第五代创作的两大特征:电影语言革新与民族历史反思。《黄土地》中占据了画面三分之二的黄土高原,打破了习惯的地平线构图,摄影机镜头对其长久地静观和凝视,传达出古老中国沉重而凝滞的历史进程。周传基曾评价本片:“《黄土地》的青年创作者对视听因素的使用证明:他们已经具备了把电影表现手段当作语言符号来使用的能力,这也就是说,不仅扮演人物的演员在说话,画面中一切视觉因素和听觉因素都在‘说话’,在传达信息。”香港影评人李焯桃认为:“相对于传统非写实路线的表现主义舞台色彩,本片以自然光拍摄实景产生逼人的影像实感,再加以浓缩、省略、集中、对比、强化来从事主观抽象地写意、象征、讽喻和抒情,在中国电影真是前所未见。”纪实与写意的结合,使得严肃的历史反思寓于有意味的形式语言之中,凸显出第五代导演强大的主体情绪和理性精神,其视觉造型美学具有典型的象征和寓言意味。
如果说《黄土地》的静观美学尚且浸润着中国式的古典美学精神,黄建新的《黑炮事件》(1985年)则体现出鲜明的表现主义风格,其画面造型受到了新构成派绘画的影响,变形而夸张的背景造型凸显出一种新颖奇特的现代形式感。这种形式上的现代感,与彼时外国电影作品和观念的涌入密切相关。“文革”造成的封闭和延滞,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法国新浪潮、新好莱坞电影与欧洲现代主义电影潮流的影响直到八十年代才开始显现。与此同时,大卫·波德维尔和克里斯汀·汤普森在《世界电影史》中指出,伴随着对电影叙述手法的新认识和新探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欧陆影坛兴起了一股“回到影像”的艺术潮流,强调形式感和视觉冲击力,致力于提供电视所无法匹敌的影像画面,呈现出清晰的现代主义风格特征。第五代的视觉本位与造型美学,或与世界范围内“回到影像”的潮流亦存有内在的关联。
视觉造型美学的崛起,使得“空间性”成为第五代导演早期作品的重要特征。《黄土地》中大量出现的静态构图、定格镜头、近乎呆照的凝视镜头等,不断跳脱出叙事的时间线索,以其构图的空间性传达出隐喻和象征的含义。这种对空间的强调,同样显见于《一个和八个》《黑炮事件》《猎场札撒》(1984年)等第五代早期电影作品之中。视觉造型美学对电影“空间性”的强调,使得电影与作为时间艺术的文学及需要在时间进程中建构冲突的戏剧性进一步拉开了距离,从而强调了“电影作为电影”的本体属性,真正实现了由第四代所提出的“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掀起了中国电影创作的“新浪潮”。
(三)娱乐片大讨论与主旋律电影
八十年代闪耀着启蒙光芒的现代主义思潮与理想主义精神,在八十年代末期被崛起的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浪潮推至了时代的边缘。与之相应,中国电影也从短暂的“新浪潮”中回落,开始面临电影产业的艰难转型与电视的强烈冲击。在此背景下,第五代电影在迎来视觉造型美学的集大成之作——《红高粱》之后,也开始走向了分化的历程。现代电影思潮戛然而止,体现国家意志的主旋律电影与满足大众欲望的娱乐片再次回到中国电影场域,引发了电影观念的变革与电影创作的热潮。
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既激发了理性高扬的知识分子思想光芒,同时也释放了大众的娱乐诉求。在第四代和第五代于体制内创作的艺术电影之外,娱乐片始终存在并受到市场的追捧与观众的喜爱,但却不被彼时的研究者所重视,处于文化精英所主导的主流话语的边缘地带。到八十年代末期,随着第五代的分化与“新浪潮”的瓦解,娱乐片以其显著的市场份额,开始赢得学界与创作界的广泛关注,引发了一场关于“娱乐片”的大讨论。
新时期之初,电影界主张用纪实性、艺术性打破政治对电影的束缚,电影的娱乐性在当时紧迫的历史任务面前并不被理论批评界所重视,甚至被视为庸俗、虚假、堕落的代名词。然而,在电影生产与创作领域,娱乐片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市场份额,并引发了一次次观影与社会讨论的热潮。
1987年的娱乐片大讨论,针对娱乐片的概念、价值与创作方法展开了丰富而深入的讨论。娱乐片及与之相关的类型电影、接受美学等理论,开始进入电影理论界的研究视域。“娱乐片”作为一个并不严谨的学术词汇,体现出了典型的时代特征,这一命名实则是以电影的功能为依据,其与强调电影宣传功能的“主旋律电影”、强调电影启蒙功能的“艺术电影”并立,表明了八十年代的电影观念仍然受到传统的电影功能论的强大影响,并进一步促成了九十年代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三足鼎立的电影格局。经由此次大讨论,中国电影的主导观念开始了由艺术向娱乐的位移,折射出一条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从鼎盛到落寞、退潮的心理历程和文化发展线索,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开始了由边缘向中心的突围。
1987年,主旋律电影被正式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文艺政策、重大革命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的成立,以及重大题材故事片资助基金的设立,表明国家重新将电影纳入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系统之中,以此回应八十年代艺术探索片和商业娱乐片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挑战和颠覆,同时以国家资助的形式挽救彼时遭遇电视冲击而日益萎缩的电影市场。八十年代末的短短三年间,一批主旋律电影相继问世,如《巍巍昆仑》(1988年)、《彭大将军》(1988年)、《开国大典》(1989年)、《百色起义》(1989年)等。这些电影多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的英模片,典型地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重新强调了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但实际上,主旋律电影的初衷,是希望在宣教功能之余,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并以此吸引观众、回收票房。然而,此后的主旋律电影却越来越与政治意识形态挂钩,直到近年来,随着主流大片与新主流大片在市场上的火爆,主旋律电影才真正实现了它的初衷。
二、在变革中坚守(1990-2000)
九十年代,伴随着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电影的产业结构逐渐脱离了国营体制的制约,开始直面市场。然而,此时的电影市场却不容乐观,港台影视剧的激烈竞争,中国电影业市场萎缩,观众锐减,票房不佳。在这一巨大而深刻的文化转型和社会变革之中,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呈现出了新的创作形态。
(一)主旋律电影
九十年代,随着电视、录像厅、游戏厅、歌舞厅等的迅猛发展,电影观众分流严重。有资料显示,当时的电影观众人数“以每年10亿人次的跌幅下降,1990年至1992年跌幅竟达25亿人次,放映场次从3600万减到2500万场”;1994年后,好莱坞电影大片的引进严重挤压了国产电影的生存空间,国产电影产量从1995年的147部,到1996年的108部,再到1997年的84部,经历了一次断崖式的下滑,自1981年以来首次跌落至百部以下。中国电影市场陷入了严峻的滑坡形势,然而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却迎来了高潮,借着1991年建党70周年,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1999年建国5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主旋律电影形成了三次“献礼片”创作的热潮,一批大投资、大制作的主旋律电影开始涌现。
主旋律电影创作的繁荣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八十年代末广电部、财政部设立的重大题材故事片资助基金,引发了第一波献礼片的高潮,并延续到九十年代初期,“1991年全年实际发行献礼故事片26部,约占全年发行国产影片的五分之一”。1996年,党中央在长沙召开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实施电影“九五五〇精品战略工程”,设立电影事业发展专项基金,进一步推动了九十年代主旋律电影的创作繁荣。资金支持之外,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五个一工程奖”(1992年)、“中国电影华表奖”(1994年)等政府奖项,以表彰优秀的主旋律电影创作。与此同时,传统的“百花奖”和“金鸡奖”也开始向主旋律电影倾斜,如《大决战之辽沈战役》获得了1991年中国电影金鸡奖和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离开雷锋的日子》获得了1997年百花奖最佳故事片。诸如此类的主旋律电影获奖作品不胜枚举,一方面体现出奖项评选机制的政策性倾斜,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主旋律电影的艺术品质与群众基础。这一群众基础的获得,即与政府在电影发行、宣传和放映过程中给予的支持性政策相关。
相比八十年代末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领袖人物传记片为主的主旋律电影题材,九十年代的主旋律电影创作在延续既有题材的同时,开始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泛情化”、平民化的趋势,《焦裕禄》(1990年)《蒋筑英》(1992年)《孔繁森》(1996年)《离开雷锋的日子》(1996年)等英雄模范传记片开始成为主旋律电影的重要题材,并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如《离开雷锋的日子》投资仅400万,但却收获了3000万的全国票房收入,在彼时萧条的中国市场创下了国产影片少见的票房成绩。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年)、《周恩来》(1992年)等领袖人物传记片也在凸显领袖政治历史功绩之外,着重塑造了领袖人物平易近人的一面。有学者将其总结为“泛情化”趋势,“一是体现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伦理化处理,遵循这一策略的主旋律电影并不直接宣传政府的政策、方针,也尽量避免政治倾向的直接‘出场’,而是通过对克己、奉献、集体本位和鞠躬尽瘁的伦理精神来为观众进行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从而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合法性。二是体现为对影片主人公的平凡化描写。三是体现在影片的形态上,这类影片大多不是标准意义上的正剧,而是一种情绪意义上的感伤剧”。此种“泛情化”趋势表征着九十年代市场因素和大众趣味对社会主流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个启蒙瓦解、消解崇高的年代,主旋律电影固有的宏大叙事和权威叙事也开始了一个书写方式的转型。
世纪之交,随着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与大众文化的强势崛起,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开始呈现出一种类型化和商业化的趋势。冯小宁的《红河谷》(1998年)、《黄河绝恋》(1999年)在革命、战争叙事中加入了爱情片的类型元素,《冲天飞豹》(1999年)实现了军事类型片与国防主题的统一,与当下的“新主流大片”遥相呼应,叶大鹰的《红色恋人》(1998年)甚至请来了香港明星张国荣担任主角,爱情叙事一度超越了主旋律宣教。“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这一在主旋律电影诞生之时的口号,在历史的迂回后终于实现,并向着多元文化共存与交融的局面不断演化。
(二)商业电影
伴随着八十年代启蒙精神和精英文化的消退,以商品经济、消费主义和娱乐享受为特征的世俗化潮流成为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最为凸显的时代特征。在这一背景下,大众的声音、观众的要求、市场的力量日益凸显出其对电影创作的重要影响,产业研究、接受美学开始进入电影研究的疆域,推动着电影观念的市场化转型。这一历史性转变,同样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推动。1993年,广电部发布《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打破了中影公司几十年来对国产电影的发行垄断,计划经济时代政企不分、统购统销的历史由此结束,中国电影的体制改革向着市场化方向不断迈进。同年,中国电影艺术中心组织召开“中国电影与当代社会”研讨会,围绕“电影如何走向市场”“怎样提高商业片创作质量”等议题展开讨论,从八十年代末“娱乐片大讨论”中“要不要拍摄娱乐片?”,到九十年代开始讨论“如何拍摄好娱乐片?”,电影学界固有的精英主义立场和艺术电影观念也开始向着电影市场化、商业化转变。
1994年,广电部召开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提出由中影公司以票房分账形式每年引进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进口大片由此进入中国电影市场,并以其高投资、大制作、明星化、高度市场化的宣传和营销手段、完善的后电影市场开发等,为国产电影的市场化、商业化运作树立了标杆,同时也给当时的电影创作者们和研究者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黄建新曾谈到,“这两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电影,过去认为电影是个艺术,现在觉得它不是个艺术,如果它是个艺术的话也是个时髦的艺术,它的语言系统和阅读对象老在变”。电影研究领域,学者邵牧君提出“电影首先是一门工业,其次才是一门艺术”的观点,认为“‘首先’和‘其次’这个次序至关重要,因为电影既然首先是一件工业产品,这就决定了它的商品属性是根本的,是第一性的,搞电影首先是一种商业行为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电影既然其次才是一门艺术,电影需要的艺术就必然要服从商业的需要,即为数巨大的文化消费群体的需要,而不能是什么非世俗化的、‘属而和者仅数十人’的艺术”。邵牧君先生的“电影工业论”,实则是在为电影的商业性正名,这与笔者今日所提的“电影工业美学”有所不同,却极为契合九十年代电影观念的市场化转型。
创作领域,由于中国电影制片体系的变化,民营电影制片厂、独立制片、外资合拍等多样化的制片形式打破了国营电影制片厂的垄断,创作者们开始直面市场,接受市场的考验,曾以艺术探索片为代表作品的第五代导演也不例外。张艺谋从《红高粱》初执导筒开始,便十分注重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协调,《代号美洲豹》《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5年)都是商业特征鲜明的类型电影,《菊豆》(1990年)、《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年)等频频获奖的“民俗电影”同样包含着视觉奇观、色彩美学、奇情故事、明星策略等商业化元素。陈凯歌的《霸王别姬》(1993年)更是艺术性和商业性融合的完美典型,影片云集了张国荣、巩俐、张丰毅、葛优等香港和内地明星,由香港汤臣电影有限公司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共同出品,一举摘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大奖,并在当年取得了4800万的内地票房成绩,全球票房超3000万美元,在香港、台湾、日本等地都引发了观影的热潮。第五代中以都市题材、形式探索为典型风格的导演黄建新,在九十年代所拍摄的电影同样呈现出市民化和商业化的转向,《站直啰!别趴下》(1993年)、《背靠背,脸对脸》(1994年)等市民喜剧电影,融合了知识分子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关注和反思,以及市民烟火气浓厚的喜剧色彩,在艺术深度与商业诉求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
冯小刚的贺岁电影则在商业性上走得更远,“贺岁片”的命名,本身即是从商业角度出发的。自从1995年香港电影《红番区》作为进口大片于春节期间上映以来,“贺岁档”等以档期作为宣传营销手段的商业电影运作理念,开始渗入内地电影市场。1997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作为内地第一部贺岁片上映,正式开启了中国电影的“贺岁档”,随后的《不见不散》(1998年)、《没完没了》(1999年)、《大腕》(2001年)等冯氏喜剧贺岁片,以其小品拼贴式的喜剧特色、幽默调侃的京味对白、扎根本土的市民意识,打造了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类型”片,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现实变迁的一面“镜子”,也折射了一条平民意识形态与消费文化崛起的道路。
(三)艺术电影
九十年代,当第五代导演在艺术和商业之间不断徘徊、努力寻求平衡之际,第六代导演的崛起则接续了中国艺术电影创作的流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艰难地寻找文化的突围,在社会剧烈的变革中执着地坚守艺术电影的创作。前文曾提到,“个体主体性”的觉醒要到第六代电影才真正实现,第六代导演倾向于“重归内心世界、个体心灵空间,甚至返回梦想与回忆的源头,以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独白、仿古的情致和雅致精巧复杂的叙述结构动态可感、梦幻迷离的影像语言,竭力造出一片虚幻的影像天地,个体精神的乌托邦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为我们这个时代保留一部分感性,构筑一个本雅明所期许的‘内在世界’、‘居室’和‘文人图书馆’”。
在这种对自我体验和个体心灵反思的自传性电影创作之后,第六代导演开始进一步关注边缘人群体和城市亚文化层面,如《头发乱了》(1993年)里的摇滚乐手、《极度寒冷》(1996年)里先锋艺术家、《小武》(1998年)里的小偷、《十七岁的单车》(2000年)里的城市外乡人等,形成了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目光注视之下的“底层叙事”。这种“边缘化”特征,一方面源于第六代导演追求艺术理想的先锋姿态,一方面是实景拍摄、同期录音、非职业演员、长镜头等贯彻巴赞美学的纪实性影像,另一方面则是非线性叙事、碎片化影像、主观化视角、情绪性镜头等形式感浓烈的实验性影像,呈现出一种个体化的混合式风格。
第六代的“边缘化”,同样也体现于他们在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场域中的生存处境。他们的创作既面临着资金与审查的双重限制,也面临着电影市场上商业化浪潮的冲击。尽管如此,第六代电影仍以其多元化的个性创作在国际影展上频频获奖,以此回收成本,获得继续创作的资金和名誉。然而,在中国电影无可逆转的市场化潮流之下,这一边缘姿态终究难以为继。随着1997年《关于试行“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对电影制片业政策的放宽,及199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青年电影工程”对青年电影创作的经济扶持,第六代开始向体制与市场靠拢。1999年,张元的《过年回家》获得了第十届上海影评人奖最佳新人导演奖,成为张元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型之作;同年,管虎拍摄了纪念北京和平解放五十周年的主旋律电影《再见,我们的1948》,主动寻求与体制的和解与合作。在政策改革与资金扶持之下,第六代影人开始浮出地表,展开由边缘向中心的突围。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这三股九十年代三分天下的力量,在时代的发展中开始互相交流、碰撞,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走向融合与共生。
三、在市场中探索(2000-2018)
新世纪以来,以华语大片为肇端的中国电影的全面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使得电影的商业性、工业性成为主导性的电影观念,由此引发了中国电影创作格局和美学形态的新变革。中国电影形成了一种以“中国电影大片”(包括重工业大片、新主流大片、“合家欢”电影等)为排头兵,带动众多中小成本类型电影的“大鱼带小鱼”的创作格局。
(一)中国电影大片
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走出去”成为迫切的时代要求,电影行业也不例外。2001年12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试行)》颁布,电影“走出去”工程正式启动,与八九十年代主要依靠国际电影节获奖实现电影跨国流动不同,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国际化主要发生在产业与市场方面,以《英雄》(2002年)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大片开始进入世界主流商业电影市场,显示出中国电影企图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建构全球文化格局的雄心。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大片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一为2002年《英雄》所开启的古装电影大片,包括其后的《十面埋伏》(2004年)、《无极》(2005年)、《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年)、《夜宴》(2006年)等,这些电影主打中华文化元素牌,注重写意和诗性的表达,致力于以现代的甚至西方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但其对国际市场与奖项的野心同时也面临着国内学界“后殖民”的批评,其对视觉奇观的强调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电影的故事性与文化内涵。其二为2007年《集结号》所代表的近现代历史题材大片,包括其后的《十月围城)(2009年)、《建国大业》(2009年)、《建党伟业》(2011年)、《智取威虎山》(2014年)等,与古装大片的国际化诉求不同,这些电影呈现出一种向内转的趋势,致力于在赢得国内观众认同的基础上展开叙事,极大地激活了国内电影市场;与此同时,随着近现代历史题材进入大片,以及《建国大业》《智取威虎山》等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中国电影大片开始与主旋律电影相融合。其三为2016年《湄公河行动》所引爆的现代军事动作题材大片,包括近几年的《战狼》(2015年)、《战狼 2》(2017年)、《红海行动》(2018年)等,学界称之为“新主流电影大片”,新主流电影大片是在主旋律电影文化的基础上对多元文化资源的有效融合,从而跨越了中国电影传统里的“三分法”,实现了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与商业电影的主流化,同时不失艺术品质。
尽管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大片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演化,但其在美学特质和审美取向上具有某些共同的属性。在美学特质上,中国电影大片秉持着视觉本位的形式美学观念,如古装大片对色彩、构图、意象等造型元素的强调,延续了第五代导演的造型美学,实现了一种“古典美学传统的现代影像转化”;新主流大片对异域空间、动作奇观、快节奏剪辑、3D特效等的强调,则体现出一种好莱坞“高概念”大片式的视觉风格,致力于以电影技术的进步打造现代化的视觉奇观。在审美取向上,中国电影大片呈现出典型的大众化趋势,如古装大片中所体现出的繁复绮丽、错彩镂金的美,显然区别于中国传统中所推崇的文人化审美,而体现出一种大众文化背景下兼具艳俗和奢华的双重性的新美学;新主流大片则体现出对主流观众的最大尊重,遵循“受众为王”的原则,在创作上尽量满足当下主流受众的期待视野,如爱国主义的民族情绪、视觉奇观与传奇故事、类型化叙事等等。
中国电影大片的的生产和运作受到了好莱坞“高概念”电影生产方式的影响,体现出一些共性特征。如国际化的融资模式与合拍片美学,中国电影大片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两岸三地电影人的共同努力,2003年CEPA协议的签订,使得港人北上拍片成为潮流,香港影人经多年实践而成就的电影商业理念、工业化规范化的管理机制、职业精神、市场意识、平民意识、娱乐精神等电影观念,深刻地影响了新世纪中国电影的风貌;除此之外,中美合拍、中欧合拍、泛亚合拍等多样化的合拍方式,不断推动着中国电影产业走向全球化,在大片之外亦有许多文艺合拍电影,丰富了合拍片美学的表现形式。在电影营销观念上,中国电影大片遵循文化创意产业的“活动经济”和“事件营销”等策略,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进行一种全媒体的整合宣传,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除此之外,中国电影大片的生产和运作还体现出一种以产业链为基础的产业集群特征,不断开拓着纵向产业链(如电影版权、广告、赞助、衍生品开发等)和横向产业链(包括图书、剧本、电影、电视、音乐、游戏、演出经纪、拍摄基地等系列行业),在实践层面进一步释放了电影的商业属性,推动着电影产业研究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研究的显学。
(二)类型电影创作格局与类型中的作者
在中国电影大片崛起的背景下,中国类型电影的创作在探索中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以喜剧电影、青春电影、奇幻魔幻电影、警匪犯罪电影、都市爱情电影等类型为主的类型电影格局。
喜剧创作的潮流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社会大众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喜剧电影作为一种“母类型”,不断与其他类型相互融合与渗透,形成了以《人在囧途》《港囧》《人在囧途之泰囧》《心花路放》等为代表的公路喜剧,以《夏洛特烦恼》《驴得水》《西虹市首富》《无名之辈》等为代表的讽喻喜剧,以《撒娇女人最好命》《陆垚知马俐》《喜欢你》等为代表的爱情喜剧,以《绝地逃亡》《王牌逗王牌》《功夫瑜伽》等为代表的动作喜剧等。除此之外,喜剧作为一种弥散的类型元素,同样渗透进《捉妖记》等合家欢电影、《美人鱼》等魔幻电影、《唐人街探案》等悬疑电影之中。一方面发挥着宣泄情绪与抚慰情感的娱乐功能和商业诉求,另一方面也承担着感性解放的文化功能,并具有强烈的青年文化属性。
青春电影作为一种按题材划分的电影类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类型片,在不同的年代与文化语境中呈现出迥异的风格特征。自2013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起,青春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中迅速崛起,并形成了以《同桌的你》《匆匆那年》《小时代》等为代表的虐恋情深的残酷青春,以《微微一笑很倾城》《谁的青春不迷茫》《闪光少女》等为代表的成长奋斗的励志青春,以《七月与安生》《黑处有什么》《嘉年华》等为代表的挖掘成长心理的文艺青春。在“IP+鲜肉”的青春片热潮退去之后,中国的青春电影逐渐走出了同质化、低品质的困境,不断在题材广度与艺术深度上开拓着青春片的类型边界。
奇幻魔幻类电影成为新式国产大片的一种重要类型。中国奇幻魔幻类电影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主流观众群体的“梦幻消费”或“想象力消费”,《画皮》系列、《狄仁杰》系列、《捉妖记》系列、《西游降魔篇》《西游伏妖篇》《大圣归来》《悟空传》等西游改编系列、《九层妖塔》《盗墓笔记》《寻龙诀》等盗墓衍生系列,以其愈发精良的特效技术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演绎,赋予了奇幻魔幻电影以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
当下中国的警匪犯罪电影创作,形成了《湄公河行动》等主旋律警匪犯罪电影,《唐人街探案》《火锅英雄》等喜剧化警匪犯罪电影,《白日焰火》《烈日灼心》等艺术化警匪犯罪电影几大类型,在类型特征愈发凸显的同时,呈现出不断杂糅进其他类型元素的趋势,在大众性、商业性和艺术性等维度不断拓宽着类型的范式。
都市爱情电影的崛起与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及中产阶层群体的壮大密切相关,并受到好莱坞“小妞电影”的显著影响。从2011年《失恋33天》的意外成功开始,一大批反映都市男女情感的爱情电影迅速风靡。从《北京遇上西雅图》《等风来》《28岁未成年》等典型的以都市年轻女性的成长故事与爱情罗曼史为主的影片,到《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摆渡人》《前任》系列等以刻画都市男性心理见长的影片,都市爱情电影的叙事角度发生了一个明显的性别位移。除此之外,都市爱情电影还热衷于呈现异域空间、进行跨国叙事,以此打造现代化的、时尚浪漫的都市生活体验,满足大众对异域空间的消费欲望,但也面临着同质化、本土化缺失的问题。近年来《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等电影则呈现出一种空间上的本土化转向,为都市爱情电影增添了本土特色与世俗气息。
在对以上五种类型电影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当下中国的类型电影创作呈现出两种明显的特征或趋势。其一为类型融合与杂糅趋势,主要是指以一种类型的核心形式为主导,同时融合其他一种或几种类型元素的电影。其二为类型电影的作者性。近年来在类型中表达作者意图的电影越来越多,如曹保平的《烈日灼心》《追凶者也》,程耳的《罗曼蒂克消亡史》,王家卫的《一代宗师》等等,均取得了不错的票房与市场关注度,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电影市场的扩容与观众的分众,随着2016年“中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的成立与全国艺术院线的不断增设,此类作者性的类型电影与《路边野餐》《长江图》《嘉年华》等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电影将获得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三)中国电影新力量与电影工业美学
类型电影的繁荣离不开中国电影新力量的探索和贡献,作为近年来涌现于中国电影场域中的创作群体,中国电影新力量开始与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分庭抗礼、共享市场,形构着当下中国电影的创作格局。
中国电影“新力量”的命名来自于国家体制。2014年,“中国电影新力量推介盛典”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的主导下,于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隆重推出,并于此后三年连续举办“新力量导演论坛”,加大对青年导演的支持和培养力度。因而,不同于第五代和第六代在诞生之初就具有对体制和商业的对抗性和艺术上的先锋性,新力量导演作为一个被体制所命名的群体,具有“观念上的开放性、意识形态上的包容性、思维上的多元性,置身商业大潮的现实性和世俗感性等特点”。
新力量导演面临着三种新的生存方式。其一为技术化生存,电影制作的技术要求越来越高,技术素养和科学素养成为新力量导演的一种基本能力和重要素质。其二为产业化生存,“制片人中心制”是新力量导演产业化生存的重要内容之一,制片人在电影工业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可,其背后体现的则是对市场与观众的尊重。其三为网络化生存,在媒介文化向着网络化转型和变革的年代,新力量导演不得不重视互联网在电影创作、宣传和营销中的重要作用,以满足当前作为主流观众的网生代群体的观影需求。
此外,中国电影新力量作为一个松散的群体,在创作上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呈现为商业性和艺术性的二元对立或张力。新力量导演中既有滕华涛(《失恋33天》)、金依萌(《非常完美》)、薛晓路(《北京遇上西雅图》)等偏重商业诉求,追求市场效应的商业片导演;也有毕赣(《路边野餐》)、杨超(《长江图》)、韩杰(《Hello!树先生》)等偏重艺术表达,追求艺术深度的艺术片导演。此外,新力量导演中还存在大量试图超越电影艺术性和商业性二元对立的导演,如刁亦男(《白日焰火》)、曹保平(《烈日灼心》)、程耳(《罗曼蒂克消亡史》)等,力图在实现个人艺术表达的同时,也面向市场和观众,追求票房上的突破。这类导演是典型的“类型性作者”或“体制内的作者”,“他们深谙电影产业机制与市场规律,能够有机处理好类型化、体制化、商业性与作者性的关系,但他们在积极探索类型电影创作的同时,也能建立起个人的作者风格和导演品牌效应”,从而超越了电影的工业体制、商业机制与艺术表达的矛盾对立,呈现出一种笔者所提倡的“电影工业美学”。
“电影工业美学”的提出,旨在调和唯经典传统和艺术至上的电影艺术研究与专注市场和产业而忽视了电影艺术特性的产业研究,在工业/艺术这一看似二元对立的情境中,开辟理论的可能性。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浮现,内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体制、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由苏联模式向欧美模式转变的历史进程之中,同时区别于长期占据中国理论界主流的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经典电影理论和以主体位置理论、文化主义思潮等为代表的宏大理论,转而从切实的现实问题出发,在日新月异、风云变幻的中国电影场域内发现问题、联动产研、沟通上下,进行一种大卫·波德维尔意义上的“中间层面的研究”。
作为一个具有体系性构想的原创性理论,电影工业美学的体系建设涉及电影的文本内容、生产机制和传播接受三大层面,这其中包括中国电影大片创作所体现出的技术美,类型电影创作所体现出的功能美,制片人中心制、体制内的作者、剧本医生等制度规范所体现出的协同美,为“常人”和大众服务所体现出的“平均的”、中和的美等。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电影工业美学在强调工业意识觉醒的同时,也呼唤着美学品格的坚守。作为一种与当下中国电影现实紧密联系的电影理论体系之建构,“电影工业美学”本身是动态发展的,它将伴随着争鸣和讨论而前行,并于此间不断发展和完善,以此呼应中国电影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构建。
结语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电影的观念革新与创作流变,我们应该承认电影是艺术和工业的矛盾体,以综合的、宽容的、多元的心态来进行务实求实、接地气的电影工作,建立商业文化背景下的电影工业美学观念,超越习惯的二元对立以追求电影的技术/艺术、工业/美学、技与道的对立统一。
注释:
[1]戴锦华:《雾中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2]张暖忻、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艺术》,1979年第3期。
[3]倪震:《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五代电影前史》,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4]周传基:《〈黄土地〉——成熟的标志》,选自中国出版社编:《话说〈黄土地〉》,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版,第212页。
[5][7]丁亚平:《中国当代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644-683页。
[6]谢苑、易旭东:《大陆电影冲出“围城”》,《国际人才交流》,1994年第5期。
[8]徐迪:《来自电影市场的报告——谈献礼影片的发行》,《当代电影》,1992年第2期。
[9]尹鸿:《在喧哗和骚动中走向多元化——90年代中国电影策略分析》,《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10]黄建新、李少红、周晓文、潘志兴:《调整与选择: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化》,《艺术广角》,1995年第6期。
[11]邵牧君:《电影万岁》,《世界电影》,1995年第1期。
[12]陈旭光:《电影文化之维》,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79-189页。
[13][14]陈旭光:《新时代新力量新美学——当下“新力量”导演群体及其“工业美学”建构》,《当代电影》,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