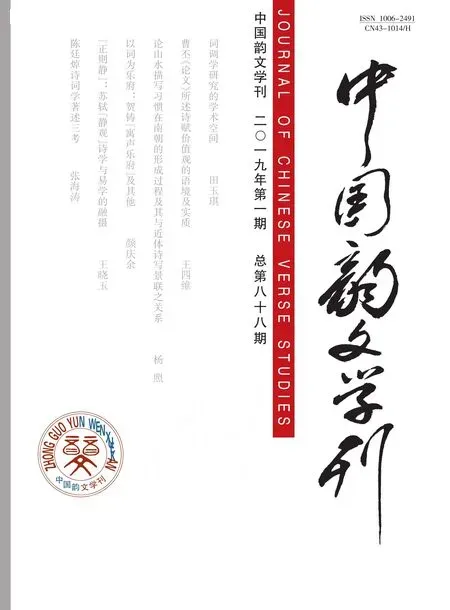以词为乐府:贺铸“寓声乐府”及其他
2019-11-12颜庆余
颜庆余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一 贺铸“以乐府为词”
北宋宣和七年(1125),贺铸卒,友人程俱应其临终嘱托,为撰《宋故朝奉郎贺公墓志铭》。关于贺铸的著述,程俱《墓志铭》曰:“有《鉴湖遗老前后集》二十卷,余为序。尚可考乐府辞五百首,它文数十百篇。方回姓字闻天下。其诗词雅丽,有古乐府之风。”其中记述贺铸词(“乐府辞”)的数量,并评论其风格。贺铸词表现出古乐府的风格,这样的说法出于友人撰写的墓志铭,自然是极为慎重的评论,想必深得作者之意。
民国词家评析贺铸词作,多沿此思路。《小梅花》三首,蔡嵩云称:“体近古乐府,宜径用古乐府作法,软句弱韵,均所最忌。贺作笔力陡健。”夏敬观评其中《将进酒·小梅花》一首:“是汉魏乐府。”《陌上郎·生查子》一首,龙榆生称:“正是乐府诗本色。”又称:“如此风调,不几与南朝乐府相仿佛乎!”《古捣练子》六首,俞陛云称:“皆有唐人《塞下曲》思致。”这些具体词作的评析,似乎都是为程俱“有古乐府之风”一语所下的注脚。
钟振振将此概括为“以乐府为词”,是一种特殊的以诗为词,又考察贺铸词命题的三种类型,包括直接标用乐府诗题、化用乐府诗题和自拟乐府新题。关于贺铸的“以乐府为词”,钟振振理解为乐府诗与曲子词两种传统的结合,乐府诗的传统侧重于题材与内容,曲子词则偏向于音乐和格律,贺铸将这两种不同的传统嫁接在一起,扩大词的表现艺术,是有意义的尝试。与前人着眼于风格不同,钟振振考察的重心是贺铸词的题目,进而关注乐府与词两种文体的不同传统。
关于贺铸的“以乐府为词”,张云的研究踵事增华,从题目、句式和篇章三方面深入考论。与钟振振的言简意赅相比,张云追求详实的论证,多运用统计和对比的实证方法,藉此证实这一现象并分析其成因。题目方面,既沿用钟振振的三种类型,又进而考察题目与内容的关联度。句式方面,既详述贺铸词借鉴乐府诗句的化用、截取、增损、熔铸、袭用的方法,又考察贺铸词使用三字句的独殊性及其借鉴乐府三字句式的叠用、重复和组合的方法。篇章方面,具体分析《古捣练子》《小梅花》《六州歌头》等词作与乐府的联系。
以上引述的评论和研究,无论详略,大抵都是有得之见,颇有启发地揭示贺铸词与乐府之间若干方面的联系。然而,这些评论和研究大抵上都是出于词学的立场,只在词体的范畴内讨论问题,因此不免局限于词体的视野,导致以今视昔的错位和先入为主的偏见,不能正确地理解贺铸的文体观念。如果要讨论贺铸词与乐府之间的联系以及此间蕴含的文体观念,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解释贺铸词集名称“寓声乐府”的含义。
二 贺铸的“寓声乐府”
张耒集中收录一篇《贺方回乐府序》,有曰:“余友贺方回博学业文,而乐府之辞婉绝一世,携一编示予,大抵倚声而为之辞,皆可歌也。”从这段话可知,贺铸词集出于自编,集名包含“乐府”二字。叶梦得为撰《贺铸传》称:“方回既自裒其平生所为歌词,名《东山乐府》。”又称:“予与方回往来亦亟,乃复为之传。”叶梦得记载的《东山乐府》,同样出于贺铸自编,想必就是张耒作序的词集,而集名包含更完整的“东山乐府”四字。不过,张序和叶传提及的集名,大概都只是文章行文中的语辞,不是完整准确的集名。
完整准确的集名,可征诸藏书家的著录。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贺铸《东山寓声乐府》三卷。此本是南宋嘉定间长沙刘氏书坊所刻《百家词》之一种。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亦著录《东山寓声乐府》二卷,卷数不同于陈振孙所藏,又注明“张右史序之”。可知张耒作序的贺铸自编词集,就题作《东山寓声乐府》。
“寓声乐府”的集名,出于贺铸的创造,在词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名称。宋人词集,在“长短句”“琴趣外编”“诗余”“词”等名称之外,大概最常见的就是“乐府”。这里的“乐府”通常指的就是词。贺铸在“乐府”一词前面加上修饰性质的“寓声”二字,似乎是有意强调他所写的“乐府”的特殊性。这样特别的名称,想必有特定的含义。《直斋书录解题》既著录此集,又特意解释集名的含义:“以旧谱填新词而别为名以易之,故曰寓声。”这一解释似是而非。词的作法是倚声填词,除自度曲之外,所倚之声通常是旧有的词调,所填之词当然是新写的词。所谓“以旧谱填新词”,无非是倚声填词的常规方式。贺铸似无必要为常规的倚声填词专门拟造一个特别的名称。陈振孙实际上并没有解释在“乐府”之前加上“寓声”一词的含义。
“寓声”一词,在宋代文献中可以读到相关的用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兵要望江南》一卷,提要称:“其书杂占行军吉凶,寓声于《望江南》词,取其易记忆。”在这段表述中,“寓声”是借用《望江南》词调,书写行军吉凶的内容。杨冠卿选编《群公词选》三卷,自序曰:“若夫骚人墨客以篇什之余,寓声于长短句,因以被管弦而谐宫徴,形容乎太平盛观,则又莫知其防。名章俊语,前无古人。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袪,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盖不但一方回而已也。”“寓声于长短句”,意思是借用长短句的词调。有意思的是,杨冠卿举出贺铸作为“寓声”的代表,并且袭用张耒序中评论贺铸词的“盛丽”云云几句话。宋以后文献中的“寓声”一词,仍然沿用这样的含义。如元李志常所述《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曰:“师作词一阕,寓声《恨欢迟》。”又如明詹詹外史《情史》卷二十一情妖类有一篇《鳖精》,叙述鳖精化为女子邱氏,为舒信道歌词一首,称此词“盖寓声《烛影摇红》也”。可见“寓声”的含义,实际上就是宋代以后极为常用的“调寄”一词。如元人吴镇《梅花道人遗墨》卷下有《题画骷髅·调寄沁园春》,所用词调是《沁园春》,所拟题目是《题画骷髅》。无论“寓声”还是“调寄”,都只是说填词时用了某某词调,并不涉及新旧的问题。
后来朱孝臧刊行《彊村丛书》本贺铸词,对于“寓声”的含义,仍然沿用陈振孙“旧谱”的说法。再后来,施蛰存有专文讨论“寓声乐府”,批评陈振孙和朱孝臧没有说明“寓声”二字的意义,并提出新的解释:“我们研究贺方回用这两个字的本意,似乎是自己创造了一支新曲,而寓其声于旧调。也就是说,借旧调的声腔,以歌唱他的新曲。”把陈振孙的“旧谱”和“新词”,改成“旧调”和“新曲”,可见仍然纠缠于新和旧的问题,而且“新曲”的说法更为谬误。贺铸填词只是选用已有的词调,何尝创造新曲,旧调又如何能够歌唱新曲。
在“寓声乐府”的名称中,“寓声”既已指向词调,如果按照通常的理解,“乐府”指的是词体,那么这一名称的含义就是用了词调的词。词自然是倚声而填成的词,无须强调一首词是用了词调。依此理解,这样的名称似乎构造得重复累赘,因此显得很不合理。“寓声乐府”的含义应该有另外的解释。实际上,可能的解释就存在于“寓声乐府”的名称与贺铸词集的文献形态之间的联系。
贺铸词集现存年代最早的传本,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刊本《东山词》,原有二卷,今残存卷上109首。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此本,称其字迹类似于南宋临安陈宅书籍铺刊本。钟振振考察贺铸词集版本流传情况,指出:“是本各词皆改题目自撰新名,犹存‘寓声乐府’原貌。卷首有张耒序。”这是可以信从的判断。宋刊本《东山词》虽然更改了集名,但在文献形态上保留了贺铸自编《东山寓声乐府》的特征。因此,宋刊本《东山词》的文献形态,有助于正确地解释“寓声乐府”的含义。
宋刊本《东山词》卷首目录依词调名编次,如《小重山二首》《鹧鸪天六首》《减字浣溪沙七首》等;正文却并不以词调名标目,而是另立新题,词调名只在题下小字标注,如《璧月堂》题下小字标注“小重山”,紧接其下的《群玉轩》题下小字标注“同前”,这对应的是目录中的《小重山二首》。这就是陈振孙描述的“别为名以易之”,金李治则称之为“异名”。
另立新题的方式,如前文所引钟振振的考察,大致有直接标用乐府诗题、化用乐府诗题和自拟乐府新题三类。无论哪一类,都属于乐府诗题。值得注意的是书籍版面呈现出的文献特征。乐府诗题是正常字号的标题,而词调名是标注其下的小字,二者之间的主宾关系极为明显。先说第一类直接标用乐府诗题,以《将进酒》《行路难》为例。
将进酒小梅花二首
城下路,凄风露,今人犁田古人墓。岸头沙,带蒹葭,漫漫昔时流水今人家。黄埃赤日长安道,倦客无浆马无草。开函关,掩函关,千古如何不见一人闲。 六国扰,三秦扫,初谓商山遗四老。驰单车,致缄书,裂荷焚芰接武曳长裾。高流端得酒中趣,深入醉乡安稳处。生忘形,死忘名,谁论二豪初不数刘伶。
紧接其下的《行路难》,同用《小梅花》词调,因此标注是二首。宋赵闻礼《阳春白雪外集》评说:“其间语意联属,飘飘然有豪纵高举之气,酒酣耳热,浩歌数过,亦一快也。”这说的正是古乐府的风格。如前所引蔡嵩云与夏敬观的评论,也表现出相似的关注。钟振振评论说:“《行路难》《将进酒》是习用的乐府古题,汉魏以还作者甚众,李白四首最为传颂。而贺铸竟能转用词体出新。”在汉魏以来的古乐府《行路难》《将进酒》的写作传统中,审视贺铸的作品,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思路。“转用词体出新”的说法尤其有意思,似乎是说,贺铸面对汉魏以来包括李白在内的众多作者,为推陈出新,放弃原先的古体形式,转用词体来写作古乐府。如果要替这一段评论下一转语,不妨将钟振振自己的概括“以乐府为词”,翻转过来,即是说,贺铸“以词为乐府”。
再说第二类化用乐府诗题。例如,《陌上郎》的新题出自乐府古题《陌上桑》,题下小字标注词调名《生查子》;《换追风》的新题出自乐府古题《爱妾换马》,题下小字标注词调名《减字浣溪沙》。版面的文献特征与第一类相同。这一类新题一方面是化用乐府古题,另一方面也是取自词的正文,如《陌上郎》依据词的过片“挥金陌上郎”句,《换追风》依据的是下片“当时曾约换追风”句。
最后说第三类自拟乐府新题。这一类新题既不照搬也不化用乐府古题,而是从词的正文摘取有标示意义的三个字。如《横塘路》的新题出自首句“凌波不过横塘路”,题下则小字标注词调名《青玉案》。摘取正文字词,正是古乐府的命题方式,如《长相思》《行路难》等。又如《西笑吟》《凌歊引》《东阳叹》《海月谣》《菱花怨》《江南曲》《荆溪咏》,题中二字摘取自正文,末一字“吟”“引”“叹”“谣”“怨”“曲”“咏”等,则是新乐府的命题方式。
以上三类另立新题的方式,无论是直接标用,还是化用和自拟,都是以乐府诗题为主,以词调名为宾。这一层主宾关系表明贺铸的文体观念可能并不是后人想像的那样。贺铸《东山寓声乐府》是一部“以乐府为词”的词集,这在词史研究的视野中当然毫无疑义。然而,如果转换思路,一部按照乐府诗题编次并且表现出乐府风格的作品集,为什么不能是一部“以词为乐府”的乐府诗集?这样的反问大概会显得突兀,违背一般的认识。在后人的一般认识中,乐府只是诗之中的一类,词则是诗之外的另一种文体,二者的文体层级已自不同,并且从产生年代说,词又晚于乐府。对于这样的认识而言,用词体来写作乐府诗,就只能是不可思议的说法。
对于胡应麟而言,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说法也许是可以接受的事实。胡应麟考察汉唐之间乐府与诸种诗体的关系,驳正世俗的一般认识:
世以乐府为诗之一体,余历考汉、魏、六朝、唐人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近体、排律、绝句,乐府皆备有之。《练时日》《雷震震》等篇,三言也;《箜篌引》《善哉行》等篇,四言也;《鸡鸣》《陇西》等篇,五言也;《乌生》《雁门》等篇,杂言也;《妾薄命》等篇,六言也;《燕歌行》等篇,七言也;《紫骝》《枯鱼》等篇,五言绝也,皆汉魏作也。《挟瑟歌》等篇,七言绝也;《折杨柳》《梅花落》等篇,五言律也,皆齐梁人作也。虞世南《从军行》、耿湋《出塞曲》,五言排律也;沈佺期“卢家少妇”、王摩诘“居延城外”,七言律也,皆唐人作也。五言长篇,则《孔雀东南飞》;七言长篇,则《木兰歌》。是乐府于诸体,无不备有也。
与“乐府为诗之一体”的一般认识不同,胡应麟提出“乐府于诸体无不备有”的观点。胡应麟的观点实际上是在强调乐府作为一种文体的开放性,反对降低乐府的文体层级的说法。由其举证看,胡应麟的观点应可信从。那么,依从这种观点并向唐以后文学推扩,乐府向所有文学体式保持开放,自然也就可以包容词体,即“以词为乐府”。
如果从词史的视野转向乐府的开放性的立场,贺铸《东山寓声乐府》是填入词调的乐府,就不会是不可思议的说法。这样理解贺铸的文体观念,也能与他自定的集名“寓声乐府”的含义相合。“寓声乐府”名称中的“乐府”,所指并不是词,而是乐府。王鹏运引述陈振孙有关“寓声乐府”的解释后说:“即周益公《近体乐府》、元遗山《新乐府》之类,所以别于古也。”(《四印斋所刻词》本《东山寓声乐府》卷末王鹏运跋)所谓“别于古”,是说加上“寓声”“近体”“新”等词的限定,从而区别于古乐府。王鹏运未必能认同“以词为乐府”的说法,但他的以“寓声”来“别于古”的提法是有启发意义的。贺铸集中正好有同题的两组作品可资说明。《庆湖遗老诗集》收录《江南曲》二首,一首五绝,一首七绝,而《东山寓声乐府》收录三首《江南曲》,题下标注词调《踏莎行》。前者有“游倡搴杜若,别浦鸳鸯落”二句,后者有“杜若芳洲,芙蓉别浦”二句,用语和结构都相近。俞陛云对后者评说:“用《江南曲》本意也。”可见这两组《江南曲》都遵循乐府诗的写作传统,区别只在于前者的体式是绝句,后者是“寓声”于词调《踏莎行》。按照贺铸的文体观念,我们应该这样表述:这是三首《踏莎行》(词体)的《江南曲》(乐府),那是两首绝句(近体)的《江南曲》(乐府)。
三 其他相似的例子
虽然《东山寓声乐府》是贺铸创造的独一无二的集名,“以词为乐府”的例子却并不只有贺铸的作品。朱孝臧指出:“‘寓声’之名,盖用旧调谱词,即摘取本词中语,易以新名,后来《东泽绮语债》略同兹例。”(《彊村丛书》本《东山词》卷末朱孝臧跋)南宋张辑《东泽绮语债》,今存一卷,有《彊村丛书》本和《全宋词》整理本。黄昇特别关注其整齐划一的命题方式,指出:“其词皆以篇末之语而立新名。”如《淮甸春》,标题摘取篇末一韵“旧游休问,柳花淮甸春冷”,题下注明:“寓《念奴娇》。”其后又有小序曰:“丙申岁游高沙,访淮海事迹。”取自篇末之语的标题,字数不一,如《比梅·寓如梦令》《疏帘淡月·寓桂枝香》《阑干万里心·寓忆王孙》。“寓”某某词调,即“寓声”之意。可见张辑《东泽绮语债》命题和寓声的体例出于贺铸《东山寓声乐府》。
稍有不同的是,《东泽绮语债》的标题不是统一的三字词语,不沿用乐府古题,也不效仿新乐府诗常见的以“引”“谣”“怨”“曲”等字命题的方式。不过,摘取篇中字词为题的方式,仍然是乐府的惯例。晚清张德瀛《词徵》卷一指出:“古乐府《长相思》《行路难》,摘曲中语为题。毛平珪词:‘何时解珮掩云屏,诉衷情。’即以‘诉衷情’名调。芦川词云:‘翻成别怨不胜悲。’即以‘别怨’名调。梅溪词云:‘换巢鸾凤教偕老。’即以‘换巢鸾凤’名调。词之上承乐府,观此益信。”张辑或许没有贺铸那样明确的文体观念,《东泽绮语债》的依从乐府惯例而拟造的标题为主而词调为宾的文献形态,也是一种“寓声乐府”,部分地表现出“以词为乐府”的观念。
《东山寓声乐府》与《东泽绮语债》二集,“以词为乐府”的文体观念主要体现在自立新题的方式、标题与词调之间的主宾关系等方面,并且在书籍版面上呈现出整齐统一的体例。这当然是两个极为特殊的例子,很难再找到这种体例的词集。然而,“以词为乐府”的观念并非仅见于这两个例子。以下举出宋以后的两个例子,表明这种观念并不算罕见。
元好问(1190—1257)的词集《遗山乐府》,或题作《遗山先生新乐府》,卷数不一。其中有七首在题序中提及乐府诗题。
《摸鱼儿》(恨人间情是何物)小序:“……予亦有《雁丘辞》……”
《摸鱼儿》(问莲根有丝多少)小序:“……此曲以乐府《双蕖怨》命篇……”
《贺新郎》(赴节金钗促)小序:“《箜篌曲》为良佐所新赋。”
《感皇恩》(金粉拂霓裳)小序:“洛西为刘景玄赋《秋莲曲》。”
《江梅引》(墙头红杏粉光匀)小序:“……故予作《金娘怨》……”
《鹧鸪天》(复幕重帘十二楼)标题:“《薄命妾辞》三首。”
《江城子》(吐尖绒缕湿胭脂)标题:“《绣香奁曲》。”
这些标题包含“辞”“怨”“曲”等字,属于新乐府诗中常见的题目。值得注意的是,元好问的小序记述作品的本事,在行文中是以新乐府诗题而非词调名来称引这些作品。后人引述这些作品,也是这样的方式。如卢文弨这样说:“至如《雁丘词》《双蕖怨》之类,亦得凌本始著其事。”其中《摸鱼儿》一首,小序更明言“此曲以乐府《双蕖怨》命篇”。“双蕖”二字本于小序所述“并蒂”“荷花”与篇中所写“双花”。由其命题和称引的方式看,其间蕴含的观念大概近于贺铸的“寓声乐府”。另外,这首《摸鱼儿·双蕖怨》抒写金泰和年间大名民家小儿女殉情的事件,正是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写作传统。对后世读者而言,这是一首以乐府诗题《双蕖怨》命题的《摸鱼儿》词;而对元好问而言,大概应该说,这是一首用《摸鱼儿》词调填写的《双蕖怨》乐府诗。
南明词人方惟馨《菩萨蛮》五首,记述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瑞金兵乱。这组词有一篇总序说:“兴之所感,吐为诗余。倘此邦之硕彦名流,读之而伤其志,庶几得与道州之咏并传矣。”明言写作旨趣出于唐人元结在安史之乱后出任道州刺史时所写的新乐府诗《舂陵行》。《菩萨蛮》五首各有一篇小序:
其一 伤流落也。劳劳末吏,不能造福残疆,徒啖雪瓜,真无辞于饕餮矣。
其二 痛焚烧也。城外屋宇,一望萧然,寇兵之祸至此。
其三 感田兵也。田兵激而生乱,以致合邑皆殃。安所得惟正之供?秋获届期,新租不入。奈何,奈何。
其四 悯驿站也。驿站之困极矣,而后辈骄横如此。殚丸疲瘠,其何以堪。
其五 愁檄羽也。杨兵肆逆,库藏如烟,而上台催饷甚迫。又田兵啸聚,不便开征。令君岂有点金之术耶?
小序的首句说明意旨,以下记叙事件,这样的体例出于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词的记事质径直切,以求读者易谕深诫,这也是沿承了白居易新乐府诗的精神。由其总序“诗余”的用语看,方惟馨当然是将这组作品看成词,不过,由其总序“道州之咏”的自我期许,小序的自述旨意和本事,词的记叙事件等方面看,《菩萨蛮》五首也不妨说是一组新乐府诗。
“以乐府为词”,还是“以词为乐府”,取决于审视的角度和论述的立场。问题不在于何者为是,何者为非,而在于是否承认视角转换的可能性。然而,现代学术史已经完全摒弃后者,拘执于词学研究的视野,从而忽视乐府的开放品格。对于词与乐府之联系的议题而言,这显然是狭隘而无益的学术理念。
四 词的起源问题
以上讨论贺铸《东山寓声乐府》蕴含的文体观念,兼及张辑《东泽绮语债》、元好问《摸鱼儿·双蕖怨》等作品与方惟馨《菩萨蛮》五首,藉此论证文学史上曾经存在“以词为乐府”的文体观念。提出这样的说法,并无意于否定长久以来这些作品作为词的文体归类,也无意于打破乐府与词之间的分界,这些作品仍然是词史研究的对象。揭出词史上隐现的“以词为乐府”的观念,用意还在于思考词源于乐府的词学命题。
词的起源是词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聚讼纷纭的学术公案,乐府、声诗、燕乐等作为词的起源,都已积累了丰厚的论述。此处不做全面的讨论,仅就诸种观点中的词源于乐府的说法,提出一点新的理解。
现代词学大抵都主张乐府与词分属于不同的音乐系统,倾向于词出于隋唐燕乐的观点。如叶嘉莹《论词之起源》提出:“词之起源却原只不过是隋唐以来配合新兴之乐曲而填写的一种歌词而已。”不过,在明清近代的词学文献中,词源于乐府的观点是比较流行的说法。这些说法在数百年间流行,想必有其可取之处,不必因为现代词学视野的转变而遽加否定。
据钱志熙考察,明清时期词源于乐府的观点,主要着眼于曲调的渊源、文体的递嬗与风格的继承三方面。这三方面的论述都有其若干史料的依据,这里不再赘述,而只关注其论述的立场。
胡寅《题酒边词》: 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
王灼《碧鸡漫志》卷一“歌词之变”: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
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者,乐府之变也。
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一《体制·诗余直接乐府》引徐巨源语:乐府变为吴趋越艳,杂以《捉溺》《企喻》《子夜》《读曲》之属,以下逮于词焉,而乐府亦衰。然《子夜》《懊侬》,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尚得其意,则诗余之作,不谓之直接乐府不可。
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一《旨趣·词别自为体》引沈大成语:词者,古乐府之遗,原本于诗,而别自为体。
陆蓥《问花楼词话·原始》:愚见词虽小道,滥觞乐府,具体齐梁,历三唐五季,至宋乃集其大成。
谭献《复堂词录序》:词为诗余,非徒诗之余,而乐府之余也。
沈祥龙《论词随笔》:词出于古乐府,得乐府遗意,则抑扬高下,自中乎节,缠绵沉郁,胥洽乎情。
在这些有关词与乐府之联系的论述中,其措辞用语,“变”“余”“遗”和“直接”“滥觞”,大都暗含特定的论述立场。无论是变化、遗(余)留,还是接续和滥觞,都包含词与乐府二者代兴的观念,以乐府的衰亡衔接词的兴起。在这些论述中,词都是独立于乐府之外的文体。循此思路而追溯词体源于乐府,就只能着眼于二者的相似相通之处,即前文所引述的曲调的渊源、文体的递嬗与风格的继承三方面。
胡寅的措辞稍有不同,所谓“末造”是末期、末世之意,也就是将词的出现看成是乐府诗史的最后一个时期。言下之意,词是乐府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于乐府之外的另一种文体。这就比较接近于贺铸的文体观念。贺铸《东山寓声乐府》是填入词调的乐府,在具备词调的体式上有别于乐府,然而仍然是乐府。由此文体观念而追溯词的起源,乐府就是词的母体,词孕育于其中,在曲调、文体、风格等方面得其滋养,而又受外部的新声变曲等因素的影响,终至于从中分化而出,独立成类,自成一体。
从乐府的开放性说,自汉魏以降,乐府作为歌诗,体式与时变化,可以“选词以配乐”,也可以“由乐以定词”,对于汉魏清乐与隋唐燕乐,应该都没有悖异之处。后来词史研究以清乐与燕乐的不同音乐系统,明确区分乐府与词,应该是与唐宋时代乐府自身的演变有关。关键的变化大概在于乐府的声与义的分离。南宋郑樵《通志·乐略》指出:“继三代之作者,乐府也。乐府之作,宛同风雅。今之行于世者,章句虽存,声乐无用。崔豹之徒,以义说名;吴兢之徒,以事解目。盖声失则义起,乐府之道,几乎熄矣。”汉魏六朝清乐背景下的乐府,由于声调亡佚而仅存事义。崔豹《古今注》、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等书以及唐代的新乐府运动,实际上重塑了乐府的传统,由此唐宋以后的古题乐府与新乐府诗大都专注于事义。民国间萧涤非研究汉魏六朝乐府,甚至提出“舍声求义”的说法,强调乐府在表现时代、批评时代方面的独特性质,并主张乐府与后出的唐声诗、宋词、元曲之间的差异:“是以宋之词、元之曲、唐之律绝,固尝入乐矣,然而吾人未许以与乐府相提并论者,岂心存畛域,亦以其性质面目不同故耳。”一方面是乐府自绝于声调并偏向于客观纪事,另一方面是词倚声歌唱并偏向于个人的抒情言志,乐府与词之间也就形成明晰的分界,由此,词也就从乐府的母体中脱胎而出,并且另开宗派,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