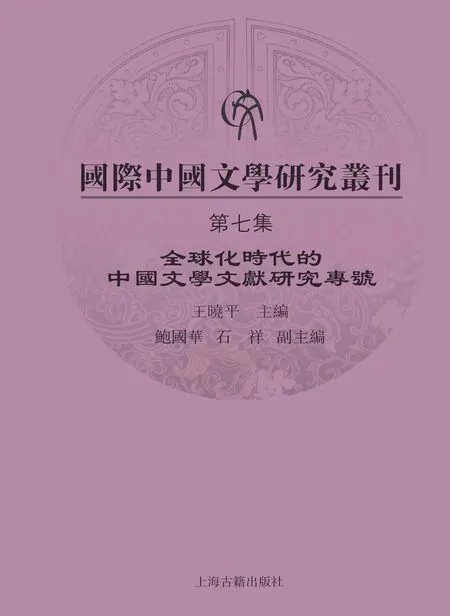改革開放助我走向世界
2019-11-12李逸津
李逸津
1966年我上高中一年級時趕上“文化大革命”,學業中斷。以後上山下鄉,直到1972年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被録取到當時的天津師院中文系進修班,一年後畢業,留校任教。當時那點淺薄的底子,教大學真是勉爲其難,只能拼命地自學、補課、進修。幸好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隨後大學和研究生招生恢復,我在1979年考入本校研究生,算是趕上了社會上所謂“新三届”的末班車,摘掉了“工農兵學員”帽子。但我是在中文系,中學時代學的那點兒俄語,早被蹉跎歲月磨光了。雖然80年代初已經有人出國留學,但大都是理工科或學外語的,中文系基本没有誰動那個心思。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鄧小平同志在1983年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學外語成爲那個時代青年的熱門。當時中央電視臺每天黄金時間播放英語教學節目“Follow Me”,書店熱銷《英語九百句》,小青年以手提一臺黑色板磚式日本松下便携録放音機爲時髦。我那時還真没有出國留學的奢望,只是想到以後評職稱要考外語,搞科研懂點外語也有好處,便重新拾起了荒廢多年的俄語,參加了本校爲青年教師晉升職稱舉辦的俄語培訓班。這樣從1985年斷斷續續利用業餘時間學俄語,基本上是有一搭無一搭的玩票兒式學習。不成想“無心插柳柳成蔭”,到1987年機會真的來了。當時蘇聯戈爾巴喬夫上臺,着手改善中蘇關係,提出兩國互派600名大學教師到對方國家進修。任務下達到學校,學校通知各系有意願、符合條件的教師報名,先在校内初選。那時很多中青年教師都没有思想準備,或家庭條件不允許,或對去蘇聯不感興趣,所以報名者寥寥。到學校請俄語教研室老師做評委進行考核初選時,記得當時只來了兩三個人,還有一位當場就退出了。經過簡單的筆試、口試,最後確定只有我一個人入選,被送到北京語言學院參加國家留學基金委組織的外語水準測試。1987年春天第一次考試没過,但瞭解了考試門路,到秋天再考,得了84分,超出非專業人員及格綫兩分,被批准參加國家教委委託上海外國語學院承辦的出國外語强化培訓班。這樣1988年上半年到上海培訓,考試合格,下半年就被派到蘇聯列寧格勒國立赫爾岑師範學院(現名俄羅斯國立赫爾岑師範大學)去做“訪問學者”(俄文名稱叫“進修生”——стажёр)。
第一次出國真是懵懵懂懂,兩眼一抹黑。與我同批到達赫爾岑師院的一共五個人,四男一女。三位年過50的老同志,有兩位是東北師大和西安外院的俄語教授,早年畢業于我黨最早建立的俄語高等學府——哈爾濱俄語專科學校。他們的俄語水準能達到跟俄國老太太開玩笑的程度,這次來俄國純粹是安慰學了一輩子俄語的老同志的情緒,讓他們到自己的精神故鄉實地體驗一下生活,根本没安排他們學什麽。另外那一男一女,來自北京外事機關和新聞媒體,也是俄語專業畢業,這次來蘇聯的任務是提高俄語實用交際能力,所以被安排在了對外俄語教學系(俄國名稱叫: 作爲外語的俄語系),上課地點就在我們住的赫爾岑師院招待所樓内。只有我一個人,憑著中學四年、研究生公共外語學了一年的半吊子俄語,還偏偏跑到專業性最强、語言水準要求最高的語文系,並且完全是靠我一個人應對各種事務,没有任何人幫我牽綫搭橋、幫我對話翻譯,其困難可想而知。
雖説當時到蘇聯對我來説困難重重,但那時我們算是中蘇關係全面解凍前的“破冰之旅”。50年代中蘇關係蜜月期在普通蘇聯人民心中留下的餘熱,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對正在醞釀改革的蘇聯社會各界的吸引力,使我們當時在蘇聯學校裏受到的尊重,享受的待遇,要遠遠要比當時雖與蘇聯官方關係密切,但却是伸手要錢的那些僕從國家,諸如越南、蒙古、蘇聯扶植的阿富汗等國的留學生要好得多。我就在所住招待所的前廳裏,親眼看過越南留學生排隊領取蘇聯政府發放的助學金時,蘇聯財會人員那副鄙夷不屑的表情。而我們當時享受的助學金是中國政府發的,按當時的外匯市場比價,可以在蘇聯過上很體面的生活,根本不需要看蘇聯官員的臉色行事,這就大大提高了我們的自豪感。
按照當時中蘇兩國教育部的協議,中國進修生一年享受兩次到蘇聯境内其他城市“學術出差”的機會。我們到蘇聯後不久的12月初,即申報去位於南方黑海之濱、比較暖和的烏克蘭城市敖德薩。不想回程時趕上大霧,登機後乾坐了兩個多小時,到夜間十點多機上才宣佈不能起飛,要推遲到第二天。按照當時蘇聯民航的規定,飛機滯飛期間由旅客自行解決食宿,航空公司没有任何補償。敖德薩當地人全回家去了,其他蘇聯國民都乖乖地在機場候機廳長椅上和衣而卧。我們這幾個中國人,兩位50多歲的老同志,在國内也是廳局級幹部和教授了,另一位是女同志,覺得讓我們這些“外賓”混在蘇聯百姓中間在機場椅子上睡覺,實在不像話,也不安全,便向隨行的學校外事處幹部(估計也是監視我們的克格勃人員)提出要求住賓館。那小幹部一開始態度很蠻橫,對我們説,兩國政府協議裏没有出差住賓館這一項,學校不能報銷。我們説,我們自己出錢,不用你報!雙方争吵半天,還是機場值班人員幫我們撥通了敖德薩國際旅行社的電話,旅行社派車把我們接到當地最好的涉外賓館。其實當時蘇聯物價很便宜,零點以後住賓館算半價,不過每人20盧布而已。而那個小幹部當時一個月工資才90盧布,怪不得他死活不肯住店呢!我們説,你不用付錢,我們請你了。這樣,他實際上沾了我們的光,享受了一宿高級賓館温暖的房間。我們這樣做,並不是我們多麽嬌氣,多麽不能吃苦,而是想到國家的尊嚴、中國人的尊嚴。當然,也是祖國的經濟實力給了我們這樣的底氣,使不少由於蘇聯多年對中國的負面宣傳,認爲中國還那麽貧窮寒酸的蘇聯人不得不對我們刮目相看。
祖國在改革開放中發展强大,這是海外學子最大的庇護和靠山。記得1989年新年前夕,我們住在赫爾岑師院賓館的幾個中國人主動在走廊裏出了一期壁報,由我執筆用俄文寫的大字標題是“中國在改革中前進”,再配上從國内畫報上剪下來的五彩繽紛的圖片,真是圖文並茂,滿目琳琅,令過往各國賓客驚歎不已。當時賓館裏住的主要是東歐及越南、蒙古等國來蘇聯短期進修的俄語教師,人家都是成群結隊集體活動,蘇聯方面負責人也從不過問我們幾個中國人的事。看了我們的壁報,培訓部主任主動找到我們,邀請我們參加他們組織的各國留學生新年聯歡會。就這樣,我們這支由五個人組成的當時賓館住客中人數最少的“小小代表團”(晚會主持人語),衣冠楚楚、落落大方地參加了赫爾岑師院外國留學生新年聯歡會,還表演了節目,贏得各國留學生的歡迎和好評。我即興表演的口琴獨奏——新疆民歌《美麗的姑娘》,竟引得一群匈牙利姑娘應聲合唱,甚至跳起舞來。一位蘇聯清潔女工私下裏對我説:“你們中國人畢竟是大國來的,有風度、有氣質,比那幫吃我們蘇聯的窮小子强多啦!”在社會上與普通市民接觸,一説是中國人,經常看到的也是驚贊、友好的表情。一次在公車上,一位俄國老太太聽説我是中國來的,馬上説:“中國改革好,你們的鄧小平和我們的戈爾巴喬夫都是好樣的!”當然,她當時不可能預見到戈爾巴喬夫最終葬送了蘇聯。但這説明,普通蘇聯人民也在盼望改革、擁護改革,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只是蘇聯後來走错了路,這是歷史的遺憾。
我在蘇聯的這一年,雖然兩國官方關係還没有正式恢復,但實際上已經享受到友好國家的待遇。不僅赫爾岑師院語文系的同行老師們,尤其我的導師、語文學博士卡斯丘辛教授對我十分親切友好,基本上做到有求必應。到其他單位辦事訪友,無論科研院所、圖書館,還是其他學校,甚至今天戒備森嚴、禁止外人入内的莫斯科大學,當年只要拿出中國護照,説出訪問目的或聯絡人,都能放行並受到很好的接待。當時我申報的進修課題是“蘇聯高等學校文藝理論教學評估”,但我自己在國内讀研時學的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任教的是“中國古代文論”。爲了儘量貼近自己的專業方向,我到蘇聯後,一方面旁聽文學理論課程,搜集當時蘇聯在文學理論研究方面的最新動態,同時征得導師同意,在他的幫助下寫成我平生第一篇俄文論文《什麽是“氣”——論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一個概念》(Что такое ЦИ?——Об одном из понятии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й те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這篇文章後來在我第二次到列寧格勒(此時已恢復舊名“聖彼得堡”)時,發表在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紀念文集上。這也算是我在中俄文學交流研究方面主動出擊,向世界傳播中國聲音的一次嘗試吧。
出於中文專業人員的職業習慣,我第一次到列寧格勒,除了完成預定的進修課題之外,還零零散散地搜集了一些俄譯中國文學方面的資料,拜訪了一些研究中國文學的知名漢學家,如著名漢語翻譯家、中國民俗文學研究專家尼古拉·斯别什涅夫(漢名司格林,1931—2011),著名中國古典文學和戲曲研究專家列夫·緬尼什科夫(漢名孟列夫,1926—2005),古漢語研究專家謝爾蓋·雅洪托夫(1926—)等,做了一些採訪筆記。當時也没想到要幹什麽,回國後有什麽用。不成想,我1989年8月底回國,本系王曉平老師找到我,説他和當時任中文系主任的夏康達教授領銜,申報了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世紀國外中國文學研究”,已經把我列入課題組成員名單。過不多久,他又找到我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周發祥先生約他申報的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古典文學在世界”也獲批准,但原定參加項目的社科院一位懂俄語的研究員因病退出,請我也參與這項工作。這樣,我一下子介入了兩個國家級社科基金項目的研究工作,壓力實在不小。自1990年春節過後,我基本上每年寒暑假都要用一周左右時間,到北京圖書館去查閲複印資料。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1998年我們第一部合作專著《國外中國古典文論研究》出版。
經過三年多奮鬥,我在1994年《天津師大學報》第2期上發表了我在俄蘇漢學—文學研究領域的第一篇論文《〈文心雕龍〉在俄羅斯》,同年9月在《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第2、3期合刊上,發表了《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在俄羅斯》,次年在《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1995年第3期上,發表了《俄羅斯漢學家對〈文賦〉的接受與闡釋》。這一年還在《河北師院學報》第1期上,發表了《前蘇聯中國新時期文學研究述評》。這幾篇文章的發表,使我得以晉升爲副教授,也從此奠定了我後半生學術生涯的基本走向。到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纂的《中國文學年鑒(1995—1996)》,全文收録了我撰寫的《中國古典文論在俄蘇》;我爲合作專著《國外中國古典文論研究》撰寫的《司空圖〈詩品〉研究舉要》一節,被俄羅斯著名漢學家李福清院士録入其爲2008年再版的B·M·阿列克謝耶夫《中國論詩人的長詩——司空圖〈詩品〉》一書編寫的《現代司空圖作品研究文獻目録》。進入21世紀,一些研究中俄文學交流的碩士、博士論文和專著中,也有人引用我當年對阿列克謝耶夫《詩品》研究所作的翻譯和評論,説明我對“海外漢學—文學研究”這門新興學術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當年的辛勞没有白費,這是我最爲欣慰的。
1999年,根據國家政策,出國訪學歸國不滿十年的學者,可以免試再度出國學習。這樣,我又一次獲批作爲國家公派訪問學者,再次來到已經恢復舊名聖彼得堡的列寧格勒,進入聖彼得堡國立大學語文系進修。這時的我,已經在國内與學界友人合作,出版了《國外中國古典文論研究》《國外中國古典戲曲研究》和《二十世紀國外中國文學研究》三本專著,有了一些可在俄羅斯漢學家面前自我展示和平等對話的資本了。
第二次到聖彼得堡訪學,我拜識了當時擔任東方系中國語文教研室主任的俄羅斯資深漢學家E·A·謝列布里亞科夫教授,又經謝教授介紹,認識了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研究員瑪麗娜·克拉夫左娃(漢名瑪麗),再以後陸續拜訪和結識了E·A·托爾奇諾夫(漢名陶奇夫)、譚傲霜、А·М·卡拉别契揚茨(漢名高辟天)、Г·А·特卡琴科等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知名漢學家,從他們那裏獲得了許多關於當代俄羅斯漢學—文學研究情况的最新資訊。這一年還與同住在瓦西里島謝甫琴科街25號聖彼得堡大學研究生和外國留學生宿舍樓的A·A·羅季奥諾夫(漢名羅流沙)及他的妻子О·П·羅季奥諾娃(漢名羅玉蘭)結下了“忘年交”。這是一對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懷有友好感情的小夫妻,當時還都在讀研究生。我們之間如俄國人所説的“互相幫助”(俄語помогать друг другу)的合作關係,一直持續到現在。他們對我後來在中俄文學關係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提供了很多幫助。
二訪聖彼得堡,我抱定的主要目的是考察研究當代俄羅斯漢學現狀,目標明確,動力十足,所以成果也最爲顯著。除了當面諮詢俄羅斯漢學家,尤其是青年一代漢學家之外,我還大量購買圖書和複印資料。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所在的大學河岸街11號樓一層半地下室的書店,以及大學主校區北面不遠的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分院圖書館,是我當時經常光顧的寶地。在我進修的那一年裏,幾乎書店裏所有新上架的中國文學翻譯和研究方面的著作,都被我盡收囊中。此外,位於涅瓦大街、鑄造廠大街和瓦西里島上的幾處舊書店,也是我淘書的好地方。我在這些地方淘到的一些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好書,如К·И·戈雷金娜的《太極: 中國1—13世紀文學與藝術中的世界圖畫》(Великий предел: китайская модель мира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культуре Ⅰ-ⅩⅢвв.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95年)、И·Г· 巴蘭諾夫的《中國人的信仰和習慣》(Верования и обычаи китайцев,莫斯科,螞蟻出版社,1999年)、B·A·魯賓的《古代中國的個性與政權》(Личность и власть в древнем китае,莫斯科,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學出版中心,1999年)、C·A·謝洛娃的《俄羅斯白銀時代戲劇文化與東方藝術傳統(中國、日本、印度)》(Театр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 серебрянного века в Росси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традиции Востока: Китай.Японния.Индия,莫斯科,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1999年)等等。尤其那本在舊書店裏淘到的《中國色情》(Китайский эрос,莫斯科,正方出版聯合體,1993年),回國後從中取材,助我寫成了好幾篇得以在核心期刊發表的重要文章。直到最近,《重慶三峽學院學報》發表我的一篇《俄譯中國古代豔情小説中的性民俗與性文化解讀》,許多材料還是取自那本《中國色情》。一年出國搜集的資料,我用了十多年,甚至國内某知名作家在舉辦中俄文化論壇展覽時,還借用過我收藏的俄譯漢籍作爲展品。直至我退休之後,仍有學界朋友邀我參與國家級重點科研項目,每年還能在國内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兩三篇論文。用我的一位當過出版社編輯的同事的話來説,這叫“抓住了活魚”,充分説明了在學術研究中佔有第一手資料的重要。
2000年秋天回國後,我申報並主持了天津市“十五”社科規劃項目“20世紀俄羅斯漢學—文學研究”,並承蒙天津師範大學和文學院領導的支持,成立了由我任所長的“天津師範大學當代俄羅斯漢學研究所”,組織本校學術力量,有計劃地開展對當代俄羅斯漢學的研究工作。以後我這個所又與王曉平教授主持的“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合併,于2009年成立了天津師範大學國際中國文學研究中心,承擔了國家級重大社科項目“20世紀中外文學學術交流史”的研究。有團隊的協作,有項目的規劃,使我的工作目標更明確,也更有動力。自2009年之後的8年時間裏,我在國内外學術刊物和學術討論會上累計發表了俄羅斯漢學—文學方面的研究論文70多篇,60余萬字,出版了兩部個人學術論文集: 《兩大鄰邦的心靈溝通——中俄文學交流百年回顧》(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和《文化承傳與交流互讀》(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這些零星瑣碎的成績,在方家耆宿或年富力强的學界新秀看來,可能微不足道,但畢竟是個人心血的結晶,難免“敝帚自珍”,聊以自慰。
回顧自1988年第一次出國至今整整30年的個人成長史和學術進步史,我深深感到改革開放不僅是國家的富强之路,也是個人成長的機遇之路、幸運之路。是改革開放,爲我們這一代人打開了面向世界的窗户,瞭解了當今世界學術發展的動向,見識了人類科技文明的最新水準,從而找到了學術創新的方向,也找到了個人事業發展的新的切入點。拿我近30年來所從事的俄羅斯漢學—文學研究來説,這門學術就是由最初幾個人在搞,發展到今天漸成氣候,有越來越多的俄語界以及中文、歷史學界年輕的學子加盟,成爲國内許多外語院校發展規劃列爲重點的方向。四十年歲月滄桑,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的對外開放、面向世界,也應提高到新的水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提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爲主、兼收並蓄。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這是黨對我們中外文學交流研究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我們今天的海外漢學研究,不僅要繼續介紹和引進國外最新學術動態,吸納借鑒他山之石,還應主動走出去,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我自己近年來在俄羅斯學術刊物或國際會議上發表的一些論文,如《俄羅斯翻譯闡釋〈文心雕龍〉的成績與不足》、《從俄羅斯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看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跨文化闡釋》《俄譯中國古典文獻譯名商榷》等,就是在海外漢學論壇上主動發出中國聲音,糾正海外漢學研究中對中國的種種誤解與曲解的一點微薄的努力。我衷心地希望,有更多年輕一代的同志加入我們的事業,進一步推動中外文學交流研究的健康發展。
謹以此文,紀念黨的改革開放戰略決策製定40周年。
2018年3月7日于華苑地華里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