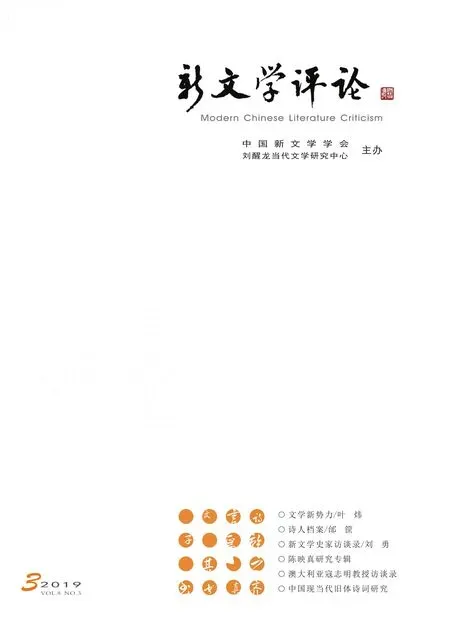人道与阶级的缠绕
——重读陈映真的《将军族》及其他
2019-11-12□赵牧
□ 赵 牧
《将军族》作为陈映真的代表作,在海峡两岸一向受到普遍地重视。众多评论几无例外地注意到它处理“省籍问题”时的独特视角,并对他在其中所表达的“人道主义”给予了充分的阐释。三角脸和小瘦丫头这两个无名无姓的底层人物,作为“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象征,他们“一个是落在异乡的异客,一个被家里像卖猪牛那样卖出去”的相似处境及其枯鱼之肆、相濡以沫的遭际,就被广泛解读为陈映真倾向于消弭台湾光复以来省籍矛盾的立场。但随着近年来后殖民主义影响的加深,却也有人从男女之间的宰治关系出发,认为小瘦丫头被出卖乃至为娼的经历隐喻了“被殖民的台湾”的命运,并对此表达出强烈的不满。于是,小说中一向为人所称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古典意蕴,也被别有用心地发掘出了性别霸权,似乎虽则沉沦底层但却来自大陆的三角脸,与败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某种比附关系。此外,就是对于三角脸和小瘦丫头一同赴死的结局感到疑惑或不满,以为陈映真是凭着知识分子的声口和观念,想当然地臆造了这么一出“殉情的闹剧”,所谓“败笔”之说几成定论,而沿着这样一种判定,不仅其人道主义观念遭遇质疑,而且其阶级观念遭到更进一步的漠视。人道主义与阶级观念并无根本分歧,它们都建基于对于弱小、卑微、无助者的关爱,但相关的解决之道、阶级观念却在人道主义所强调的互爱互助之外,更进一步发展了抵抗的政治。从人道主义角度解读《将军族》所触及的“省籍问题”并无不妥,但众多论述却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陈映真在这篇小说里所表达的阶级观念,而即便论及其中的阶级观念,则又在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殉情问题上,产生“抗争”与“幻灭”之间的认识分歧。为此,我们似乎有必要在层层累积的阐释的前提下,重回《将军族》及其周边的文本,尽可能剥除种种观念迷雾,探究这篇不无“密教”性质的小说背后陈映真所可能借以表达的真意。
一、 音乐的复调
《将军族》是以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意外重逢开始它的故事的。这样的安排给小说提供了一个回忆的视角,其间以三角脸这一外省老兵作为回忆的主体,他的文化教养虽则不足以让他抚今追昔,发出家国残破、久经丧乱的黍离之悲,但身世浮萍、沉沦底层的经历,却也足以让他悲欣交集。而事实上,就在三角脸和小瘦丫头意外重逢的那个冬日葬礼上,东洋风的《荒城之月》恰也烘托了这种感伤而又悦乐的气氛。陈映真在叙述中特别给这氛围做了一番解释,大意是“十二月里的好天气”,“使丧家的人们也蒙上一层隐秘的喜气了”。从表面上来看,所谓“丧家的人们”应该是指葬礼的主家,但在这里,却又显然别有象征。因为三角脸和小瘦丫头这一对姓名不为人所知的男女,从前就是在四处流浪的康乐班里认识的,他们一个是沉沦在社会最下层的外省退伍老兵,一个是被卖掉的本省贫困人家的女儿,都可称得上“丧家的人们”这一称谓的。而且因为他们曾经共同服务于康乐班的过往和如今分属两个替人送葬的礼乐队的现况,在葬礼上不期而遇也是恰如其分的安排:重逢的悦乐和丧家的感伤,就在这样的前提下并行不悖地出现在同一个时空。
然而问题是,《荒城之月》何以会被选择作为葬礼上的音乐呢?事实上,这首《荒城之月》的曲调悲凉、词意哀婉,倒也非常适合在葬礼上演奏,所以它被选中,很有可能是反映了台湾民间葬礼的实际,也就是陈映真在实录式的书写中,只不过是无意识地展现了台湾民间社会婚丧嫁娶等礼俗深受日本殖民文化影响的实际。我们知道,台湾曾长期处于日本殖民之下,而即便是1945年因为日本战败台湾得以光复之后,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仍广泛存在于台湾的日常生活之中,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就更容易超越国界和民族的界限而引起遥远的回响。这首泷廉太郎作曲、土井晚翠作词的《荒城之月》自问世以来,经过不同世代的人们的传唱,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而据郑鸿生的回忆,日据时期的台湾人,也就是他父执一代,也大多会哼唱的。陈文茜在一篇题为《给在天堂上的外婆》的文章中,提及外婆的冥诞仪式上不但特别找人演唱了《荒城之月》,而且利用现代电子技术模拟了日式贵妇装扮的外婆哼唱这首歌曲的情景。陈文茜的外婆出生并主要生活在台湾的日据时期,其丈夫何集璧作为台中的名门望族,早在1930年代就与著名小说家赖和一起积极倡导反抗日本“皇民化教育”的台湾文艺运动。尽管何集璧积极响应着“宁做潮流冲锋队,莫为时代落伍军”的口号,在日据时期做了抵抗殖民文化的前驱,但是,这却并不妨碍他的妻子模仿日式贵妇的生活,并哼唱着来自殖民宗主国的歌曲。而就在他们双双逝去几十年后,作为孙辈的陈文茜在缅怀先祖的仪式上抛却意识形态负担机械复制了这一昔日殖民地社会的日常景观,其中况味足以见证在“后殖民”的日常生活层面上摆脱强势的殖民文化记忆,的确仍是一件颇费周章的难题。
以一首来自日本的经典歌曲被选用在葬礼上的细节,暴露殖民地经验的阴魂不散或者并非陈映真的本意,但《荒城之月》的被选中,却也可能跟小说所要暗示的三角脸的身世遭际有关。众所周知,《荒城之月》这首包含着无尽的悲凉和哀伤的歌曲,是和日本历史上一段惨烈的战事联系在一起的。1901年东京音乐学校为编歌唱集,将泷廉太郎作曲的《荒城之月》交给当时已经颇有诗名的土井晚翠作词,土井晚翠因此想起他曾经游历过的福岛县会津岩松的鹤城以及家乡仙台的青叶城遗址,而有关鹤城,又让他联想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戊辰之役”:藩主松平容保拒绝归顺维新势力,据守鹤城同官兵展开了激烈交战。当时会津藩所有武士家十五岁到十七岁的少年们组成“白虎队”,手持武士刀或长矛与官军的近代大炮对抗。城池陷落,这些“白虎队”中的20名少年武士逃到饭盛山中切腹自杀,最后只有一位被抢救了回来。这一悲剧曾深深地触动了土井晚翠,而故乡青叶城的记忆又让他涌起了浓重的乡思,于是在《荒城之月》中,他通过往昔与今夜、战争与和平、华堂与废墟的多重对照,表现了“人世间的荣华与征戮,在时光的长河中终将一逝无存,永恒者只有这夜半的一轮明月”这等东洋式的无常观。从《荒城之月》在台湾的流行程度推测,陈映真应不难知道歌曲背后的典故,所以,除了在揭示日据时期的皇民教育仍无所不在的这一后殖民视角之外,我们或还可以在这里体会到他的别有寄托,比如古代日本维新派和地方藩主的征战与国共内战的影射关系,因为这其中新旧势力的争夺以及旧派地方藩主的失败,很可能在他这个有着左翼倾向的青年的“密教”式的创作中,跟国共内战以及国民党的败退台湾建立了联系,而作为国民党老兵的三角脸战乱之中的侥幸存活并四处离散的命运,也未必不能让他想到那位被救活过来的少年武士。

二、 阶级的隐喻
虽然在《将军族》中三角脸是《荒城之月》的演奏者,但其中明月高悬的音乐意象却未必能唤起他这等无知无识的基层退伍老兵的思乡之情,更遑论背后可能隐含的国共战争的影射了。不过假若让我们回到三角脸所忆及的五年前他和小瘦丫头海边谈话的场景,却的确是有一轮圆月正挂在半空中的。音乐中的月亮是隐而不彰的,其寓意恰如源代码一般,想要明白其中的隐曲,必然需要一番解码的工作。这其中还不免有强作解人的嫌疑。但我们眼中的月亮,却也并非物理学层面的,而是经由传统文化的熏染,它总是跟思乡怀旧关联在一起。所以,怅然地坐在海边沙地上的三角脸,显然是害了“怀乡病”的,小瘦丫头冷不防地叫他一声,他才“猛然地回过头来”。接下来他在小瘦丫头的纠缠下所讲的“被卖给马戏团的猴子”的故事,虽然小说并没有给予完整的复述,但是“被卖”与“思乡”这两个关键词,却是显而易见地指向了他作为流寓台湾、居无定所的国民党退伍老兵的悲惨处境。然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古典意境,在这里发生了耐人寻味的颠倒:讲故事的不再是白居易笔下的流浪歌女,而是换成了经历过战争、流浪、放纵而沉沦底层的单身男性退伍老兵三角脸。“正苦于怀乡”的他借着“被卖给马戏团的猴子”的故事给自己半生的遭际做了概括,没能料到的是,这故事竟然让小瘦丫头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原来她竟是被贫穷的父母卖掉的,因为不甘为娼,才逃难到这岛内四处流动劳军的康乐队。


这样的一种人道主义视角,当然是跟小说的主题相切合的,但若局限于此,却让我们很难理解五年后三角脸和小瘦丫头重逢的时候,她给他讲述第二次被卖的遭遇,何以特别强调那一个弄瞎她的“左眼”的大胖子与他有着相同的“口音”。显而易见,这里所谓“口音”相同,应该指的是大胖子和三角脸同样来自大陆(更进一步的,或者他们都是来自东北,然而作为一名台东乡下的小姑娘,小瘦丫头实在未必对于大陆各地的方言有着准确的区分,所以,她所谓的“我一听他的口音同你一样”,未必意味着这大胖子就是三角脸的乡党),而这样一来,刘绍铭所谓的“大陆人”这一泛称,就罔顾了他们内部的阶级分野。我们知道,“大陆人”(也常被称作“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矛盾中掺杂了太多政治操弄的因素,他们内部各自都有着相当巨大的分化,就“本省人”而言,他们中既有大地主,也有像小瘦丫头父母那样的贫贱的佃农,而他们所谓的“外省人”,也并非都是代表着特权的“军公教”,而即便是“军公教”,也彼此之间有着收入、教养、阶级的差别。这当然是常识了。但吊诡的是,族群的操弄却可以对此视而不见,并成功地塑造一种共同体的想象。小瘦丫头凭着“口音”而断定大胖子也应该像三角脸一样是个“好人”,这或是基于她为数不多的人生阅历,但陈映真之所以强调这个细节,却显然是别有寄托,其中之一可能是他对于方兴未艾的族群话语的不满,而舍此,则应是隐秘地提醒着在广泛流行于台湾社会的“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区分之外,还有着一种不可忽视但却成为禁忌的阶级视角。

三、 死亡的升华



从这样的经验中,我们发现陈映真更多地强调了“外省人”和“本省人”婚恋故事中的悲剧面向,他们即便是结合了,也难逃悲剧的收场。对此,我们当然可以有多个维度的解读,但综合他们与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相约赴死,更多的评论者发掘了其中的消极面向,而认为“陈映真的再三以死亡作为小说的收束,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取巧或方便的处理方式,因为基本上人生是不能化约成这般简单的形式,而死亡或疯狂也只是问题的搁置,而不是问题的解法。同时,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陈映真思想层次上,对‘人’本身的信仰已有某种程度的失落”。这里所谓“对‘人’本身的信仰”,大抵可以看作对人道主义的变通说法,由此,“冷酷地导引人物走向幻灭的末路”的陈映真,也就走向人道主义的反面,而沿着这样的思路,像张立本那样发出“陈映真关心弱小、受辱者吗?”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这样的解读,显而易见的是忽略了三角脸有关于“此生此世,仿佛有一股力量把我们推向悲惨、羞耻和破败”的激忿言辞。毫无疑问,这并非三角脸所可能有的声口而是陈映真所发出的控诉。这阶级内涵,当然不能像他在“解严”后所写的《后街》中那般直截了当,但若明了“有一股力量”的存在,我们就不难理解陈映真何以会令相约赴死的关键情节阙如,而不能在文本的世界中指向他想要的这两个受侮辱与受损害的人所可能走的反抗之路。
本文为河南省哲社项目“现代中国作家‘延安道路’及其创作研究”(2017BWX018)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中国博士后基金第十批博士后特别资助(2017T100528)的支持。
注释:
①白先勇:《〈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姹紫嫣红开遍》,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在文中白先勇先是引述了欧阳子的评点,“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佳作”,然后给出了自己的评价,认为陈映真的“人道主义在《将军族》中两个卑微的角色身上,发出了英雄式的光辉灿烂”。
②刘绍铭:《爱情的故事:论陈映真的短篇小说》,《陈映真论卷·爱情的故事》,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③宋冬阳(陈芳明):《缝合这一道伤口——论陈映真小说中的分离与结合》,《陈映真论卷·爱情的故事》,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页。
④陈映真:《将军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⑤郑鸿生:《台湾的大陆想象》,《亚洲的病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4页。
⑥陈文茜:《文茜的百年驿站》,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⑦金中:《土井晚翠的人生与艺术》,《诗歌三国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⑧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联经出版社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40页。
⑨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联经出版社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页。
⑩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联经出版社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