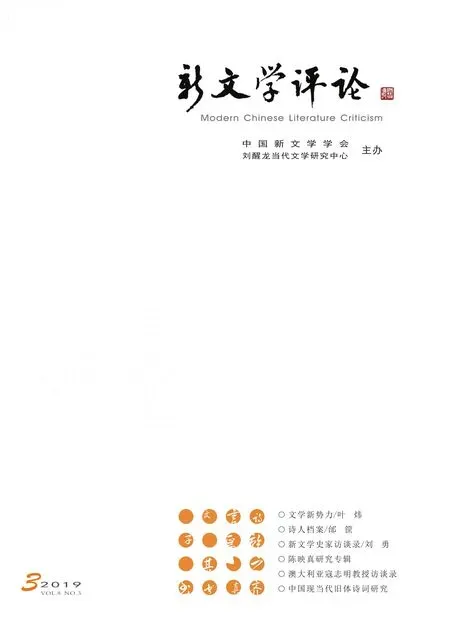如何重新表达人与土地的关系
——叶炜小说论
2019-11-20郝敬波
□ 郝敬波
人与土地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新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伴随着诸多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对这种主题话语的表达也呈现出不同的文学形态,从而构成中国乡土文学的整体貌相和历史流脉。198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的巨大变迁使得人与土地的关系更趋复杂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乡土文学的表现空间。丁帆在研究这一时期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在理论上进一步探讨了当代乡土文学的外延和内涵,指出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改变了城市文明的生产关系和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带来了乡土小说类型的某些改变。从创作实践来看,当代乡土小说家的创作应该说是富有成效的。贺仲明将20世纪乡土文学叙事类分为文化批判、政治功利、文明怀旧、乡村代言四种形态,打开乡土小说文本,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形态的乡土创作,其中当然包括70后、80后作家的创作。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阅读感受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面对人与土地关系日益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当下乡土小说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尚缺乏更有效的“及物性”,对正在变化中的乡土世界缺乏更为真切和更具现场感的书写。这种“力有不逮”的阅读感受也让我们对当下乡土文学创作充满更多的反思与期待,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及其发展道路极为复杂,新推行的土地流转制度使农村走进了市场经济时代的漩涡,许多问题变得急迫而严峻。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不少有良知的作家却陷入把握现实和表达现实的困惑之中。他们能走出困惑,写出大变革时代中国乡土的复杂性、写出中国农民的真实境遇、写出现代性挤压下的‘农村新人’的历史命运吗?这是作家和我们共同的焦虑。”
那么接下来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重新表达人与土地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思考中,叶炜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叶炜是70后小说家,近年来连续创作的《富矿》《后土》和《福地》并称“乡土中国三部曲”,以鲜明的创作个性获得了读者的好评,也引起了批评界的更多关注。走近叶炜,我们会发现他的勤奋和成果是让人惊讶的:已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集,5部文学研究专著。不仅进行文学创作,叶炜还一直从事高校教学和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因此汪政认为对叶炜的关注应该是多角度的:“叶炜在文学上的追求与工作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只看到一个创作的叶炜或小说家的叶炜,还应该看到学者的叶炜,评论家的叶炜,文学编辑的叶炜。”如果从叶炜的小说创作来看,乡土题材一直是其创作的重点。我们就从这里走进他的小说世界,探讨叶炜之于当下乡土书写的意义,反思重新表达人与土地关系的可能性。
一、 贴紧土地:乡土书写的一种姿势
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对于乡土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来说,这或许是一种挑战。当下的作家大多寓居城市,对于许多乡土小说家来说,原来在乡村生成的乡土情结仍然积淀在胸,而这种情结往往构成了乡土书写的动力。然而,已然渐行渐远的乡村却让他们的创作显得力不从心。不难看出,不少乡土小说很容易停留于一般意义上的乡愁和记忆书写,缺乏更有深度的乡土表达,更缺乏对人与土地关系变化的深度反思。应该说,这是当下乡土文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要写乡土,就要有勇气面对这个问题,有耐心去坚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乡土书写对于70后、80后小说家来说或许更是一种冒险。但叶炜这么做了,一直做到现在。多年来,叶炜始终把自己贴在土地上,匍匐在熟悉的乡村田野,并以此作为一种姿势或立场来进行乡土小说创作。
其实,叶炜的这种创作姿势从早期的练笔就初见端倪。叶炜的创作从短篇入手,在长篇小说之前,已有百万余字的中短篇创作的历练。叶炜的写作从大学校园开始,曾连续发表了许多反映校园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如《五月的爱情》《西公寓》《往日爱情》《新来的胡教授》《独自跳舞》《到远方去》《像鸟一样飞翔》《送你一束康乃馨》《反向运行》《我和诗人老马的物质生活》《眼睛》《在婚礼上跳舞的女孩》《爱情笔记》等。然而,叶炜对校园世界的书写一直都没有离开对乡村世界的关注,笔下的校园世界往往连接着乡村世界,小说人物也多来自乡村。可以说,此时的叶炜是从青春校园的视角去观察乡村变化的。同时,叶炜还创作了许多乡土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如《胡音声声碎》《母亲的天堂》《民间传说》《一九六九年的记忆》《小姨和大舅》《榆木弹弓》《丧》《午后》《种》《小李庄旧事》《种在阳台上的庄稼》等等,都是以对故土眷恋的情感方式关注着农民的生存状态,从略带迷茫的少年视角来呈现乡村的历史记忆和时代变化。其中,《胡音声声碎》《母亲的天堂》《民间传说》等小说尤其让读者印象深刻,初步显示了叶炜出色的文学悟性和文学能力,以及对于乡土世界的独特感受。这一阶段对叶炜来说是重要的,他不仅尝试和确立了适合自己的乡土创作姿势,而且也从先锋文学中汲取了艺术营养,在题材处理和叙事方式等方面摸索着自己的创作之路。可以说,没有这一时期的操练,就没有后来的“乡土中国三部曲”。
正是从“乡土中国三部曲”开始,叶炜相对固定了贴紧土地的书写姿势,对自己的“乡土”进行精耕细作。首先,叶炜的乡土小说定位于区域书写。与许多乡土小说家一样,叶炜的乡土创作致力于对某一地域的书写。一般来说,区域书写有其特定的创作指向和艺术内涵,是对一个特定地域的自然、风俗及风情进行全面观照和深度表达,在文化和审美上发掘区域经验,从而实现在某一方面对人类普遍意义特征进行表现的创作诉求。比如,沈从文、汪曾祺、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作家的乡土小说就属于这个意义上的区域书写。叶炜选择了鲁南(扩展到苏北)作为其区域书写的对象。鲁南地域是叶炜熟悉的,成长、读书和工作都在这个地方。从叶炜的经历我们可以知道,他常常往返于城乡,直到现在也没有远离乡村。这种经历使他获得了持续的乡村生活经验,并得以有效地观察和体验正在发生的人与土地的关系变化。正是对乡村的融入和谙熟,叶炜才得以真正贴在土地上进行乡土小说创作。其次,叶炜把乡土叙事聚焦于一个村落。叶炜的创作贴紧在大地上,叙事焦点只是一个村庄。《富矿》《后土》和《福地》都写了同一个村庄:麻庄。小说中的麻庄是鲁南平原的一个普通村落,叶炜显然熟悉它的一草一木,对它的呈现就像在述说自己的生活体验,并从这里开始构建小说的艺术世界和自己的乡土文学理想,这正像美国文学批评家布鲁克斯、沃伦在其名著《小说鉴赏》中对小说创作的描述:“小说是进行中的生活的生动体验——它是生活的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演出,而作为演出,它是我们自我生活的一种扩展。”在叶炜看来,一个小小的麻庄就是整个世界,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自己的亲身体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很难写出有价值的和被自己看好的作品的。我很欣赏福克纳的小说和他的写作方式,他的那种盯住自己的家乡那一小块土地那一个村镇的‘邮票式的写作’。福克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他用这种看似取材环境非常狭小的写作却反映了整个的社会风貌。”正因为如此,叶炜在“乡土中国三部曲”中聚焦一个村庄,专注于把这个村庄写得生动和丰富。最后,叶炜把对乡土的观照定位于独特的区域文化品格。正因为对鲁南地域如此熟稔,叶炜才不满足于仅描绘麻庄表层的生活貌相和变化形态,而是发掘以麻庄为代表的鲁南区域所发育和积淀的文化审美特质,而这种深度发掘也是以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为线索的。尽管叶炜对此充满信心,但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执着或许有一定的冒险性,也有学者在研究叶炜的乡土小说时指出:“进一步想,你选择的地域并不是一个易于成功的地方,而是带有一些难题。”但无疑值得肯定的是,在70后作家中,叶炜在乡土小说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耐心和坚守是值得重视的,他如此专注的乡土写作姿势是值得尊敬的。而从作家与世界的关系来看,这种创作姿态或许也是当下乡土文学创作实现突破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乡村迅猛变化的时代背景中,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作家的创作姿势,关注他们与乡土的距离,反思和审视他们小说中乡土世界的状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首先从这个角度来讨论叶炜,来探讨他以自己的创作方式带给我们的某种新的可能性。
二、 “乡土中国三部曲”:人与土地关系变迁中的民族心灵史
对叶炜来说,长篇系列“乡土中国三部曲”是其多年苦心创作的标志性作品。从整体上来说,紧贴土地,聚焦麻庄,从深度和广度上表现中国乡村的时代变迁,呈现乡村变化中的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是“乡土中国三部曲”的重要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主题的表达过程中,叶炜并不仅仅呈现乡村的生活原生态,也不单纯是拯救乡村的信仰危机或建构乡村的某种文化想象,而是在乡土的历史和现实的脉动中找寻一部心灵史。这部心灵史承载着人与土地关系变化中的苦难、疯狂、奋争、毁灭与希望,是民族心灵史的重要内涵。这一主题沉潜在叶炜小说叙事的表层之下,是其乡土小说创作的深层主题。在我看来,忽视了这一点,就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叶炜小说在当下乡土文学创作中的独特价值。对于心灵史的书写,叶炜的创作很“老实”,他没有从乡土世界中抽离出一个寓言故事来表达,也没有以后现代的方式来建构某种隐喻和象征,而是走近乡土进行全景式的观照,用“非道德”的视角去审视乡村,然后去感知和表达乡土的心灵脉动。
叶炜小说的心灵史书写,是建立在全景式观照和“非道德”视角审视的基础之上的。首先来看叶炜是如何对乡土世界进行全景式观照的。叶炜在小说中细密编织着自己熟悉的乡土世界,以全景式的叙事方式把一个乡村延展为广阔的社会平台,从而赋予其写作对象更为深远的时空纵深。《富矿》由麻庄的“黑雪”传说写起,以此交代了麻庄的“前世今生”,然后进入主人公麻姑和笨妮的生活世界。如果没有麻庄煤矿的开采,麻姑或许与心爱的六小结婚、生子,与她的前辈一样在乡村安静地生活。然而,煤矿改变了她的一切。通过麻姑的生活线索,小说展示了鲁南乡村的风俗画面,打猪草、磨豆腐、唱民谣、忙收割、婚丧嫁娶……小说的故事性并不强,故事叙述的同时努力拓展着人物的生活时空,关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乡土世界。在《后土》中,小说以刘青松、王远、曹东风、翠香等人物的活动为线索,以全景的方式书写了麻庄的乡村本相。刘青松、王远、曹东风是小说中极富性格魅力的人物形象,他们见证了麻庄的历史变迁,也承载了人们对于乡村世界的美好和丑恶、幸福和苦难的理解与想象。叶炜选择了一种朴素温情的话语基调,叙述了发生在他们身上一个个充满生命情态的故事,细致展示了乡土世界的生存方式和精神风貌。在故事推进的过程中,小说一次次将叙事重心转移到对乡村世界的整体描写上,从而使小说世界充满了一种广袤和鲜活的生活气息。在《福地》中,叶炜延伸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叙事时空,对麻庄进行了历史书写,从历史的视角呈现乡村世界的“前世今生”。小说以麻庄地主万仁义的人生经历为视点,以其四个子女不同的命运遭遇为叙事线索,书写了一个村落从辛亥革命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沧海桑田。小说最明显的叙事动力是万仁义家族的起伏变故,展现了一个家族的兴衰史,但叶炜让所有的线索都围绕着麻庄的变化展开,来表现麻庄是一个“福地”的精神符码,这也是小说名称的由来。因此,《福地》并不是惯常意义上的家族小说,而是通过家族的变迁来呈现“福地”麻庄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历史影像,从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乡村的历史画卷。接下来再来看叶炜小说的“非道德化”叙事。所谓“非道德化”的叙事,就是对传统道德叙事的一种反叛,作家力求在新的视角中观照当下复杂的精神世界,以解构传统道德伦理的叙事方式建立起来的一种叙事立场和叙事话语。《富矿》中的麻姑,是一个由乡村的纯洁姑娘“堕落”为煤矿上风流女子的形象。丈夫死后,麻姑接受了一个强奸自己的男人,“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结局。一个女人竟然原谅了强奸自己的男人并心甘情愿和他有了更亲密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还有些发自内心的喜欢”。刘青松是《后土》中的主要人物,主宰着麻庄未来的发展,但小说没有把他写成道德君子,相反却把他描绘成一个“非道德”的形象。刘青松任砖厂厂长时就与女工翠香发生了关系,随后让王傻子来砖厂做工,并极力促成了王傻子与翠香的婚姻,之后刘青松并没有结束与翠香的关系,最终使翠香为他产下孩子。在《福地》中,叶炜也没有从道德审视的视角来塑造地主万仁义,而是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有欲望的个体来处理,在历史变故中表现万仁义的精神世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叶炜往往通过欲望化的生活展示来实现小说的“非道德化”叙事。在叶炜看来,对欲望化生活的展示代表着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理解和认知,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那样:“这种欲望化的生活显然比那种‘道德化’的生活更为真实、更为感性。它以近乎本能的方式,完成了对于生活的意识形态性和抽象符号性的反动,还原了当下生活的人间烟火气,同时也完成了对于当下时代和人性的一种阐释。”
通过这种全景式、“非道德化”的乡土叙事,叶炜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投向乡土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广阔视角,并在这个视角里对人物的生存境况进行反思。在这个基础上,叶炜把小说叙事的重点指向了心灵史的叙写。或者说,全景式、“非道德化”的乡土叙事是一种基调,以此来铺陈丰富、浓郁的乡土气息,那么对心灵史的书写则是小说叙事的华彩乐章。而对这种心灵史的书写,又是在人与土地关系变化的视阈中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叶炜对于百年中国人与土地的关系进行了文化反思,并从这个路径上完成了民族心灵史的书写。具体来说,叶炜是在三个维度上完成了对心灵史的书写。第一,苦难的心灵书写。在“乡土中国三部曲”中,叶炜对于苦难心灵的书写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在《富矿》中,由于麻庄矿区的开发,人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随着这种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人们挥之不去的焦虑和痛苦:“矿上机器的轰鸣声越来越大,吵得整个麻庄的人都睡不着觉。男人们开始骂娘,女人们开始变得焦躁不安。老人们说这样下去,指不定要出事。他们想起记忆中的黑雪,对长辈们口口相传的那场大灾难的恐惧记忆,还残留在麻庄人的脑海中。”主人公麻姑和笨妮在这样的焦躁中走出了乡村,走进了由男人的痛苦、女人的辛酸,以及矿难、凶杀、死亡等组成的苦难世界。小说对心灵深处的世界进行了探寻,展现人们的贪欲和由此带来的痛苦,把煤矿世界和乡村世界混杂在一起,从而以苦难为底色表现了人们的一段心路历程。第二,奋争的心灵书写。“奋争”作为一个关键词,始终贯穿在叶炜小说的主题话语中,成为心灵史书写的重要元素。《后土》的叙事按照二十四节气的时序推进,叙述了麻庄近三十年的发展变化。小说以麻庄村委会的日常工作为叙事中心,塑造了王远、曹东风、刘青松等不同时期村干部的鲜活形象,叙写了麻庄人在社会变革中的倔强和挣扎。譬如,在刘青松的心灵世界中,如何在变化的土地上走出一条生存的新路子是其重要的精神追求。刘青松通过办砖厂等诸多行为去抗争命运,这种悲壮性的精神品格无疑成为心灵史的重要内容。第三,守望的心灵史书写。在人与土地不断变化的历史中,伴随着苦难与奋争,人们的心灵最终归于何处?叶炜把这个路径指向对于乡土的守望。《福地》在对麻庄的历史叙述中,始终在表现一种守望的心灵。在小说中,叶炜通过两个层面来构建守望的心灵世界。一是对“大槐树”意象的构建。大槐树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展开相对独立的叙述。这种叙事设置延宕了小说的叙事节奏,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时空。大槐树不仅作为麻庄历史的见证者,它的叙述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情感线索,其形象塑造具有了“象外之境”的艺术效果。在这种意境中,小说突显了大槐树“守望”的精神诉求:“这些年,我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守望着麻庄。我看着这个村庄一点点变老,看着这个孩子一点点变大,直至老去。”这种叙述逐步形成了大槐树“守望”的形象建构,并使之成为麻庄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是对老万精神世界的构建。《福地》尽管以“福禄寿喜”四人的人生经历来转换叙事时空,但他们总能回顾麻庄,并始终与麻庄的变迁缠绕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父亲老万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老万正是以其对麻庄深入骨髓的眷顾和至死不渝的守望,来形成家族的“麻庄情结”:“我本想让四个孩子和我一样,好好在麻庄守着,守护好祖辈开创的这份家业,守护好麻庄的天地人鬼神!”对老万精神世界的建构,极大地丰富了小说对于乡土变迁中人物心灵世界的书写。
在文本阅读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叶炜对于心灵史的书写不是在唱一曲乡村衰落的挽歌,不是在哀叹乡村文化的变迁,也不是试图坚守乡村的某种道德准则,而是在努力发掘和表达乡土中国的一种精神存在——犹如《福地》中大槐树和老万的灵魂一样。这种精神存在已融入乡土的历史,也显现在乡土中国的当代变迁中,它不会随着一个村庄的消失而消亡,因此它不需祭奠;它已成为我们精神的一部分,成为一个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我们要做的或许只是要感知它的深厚和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说,叶炜的乡土小说创作是成功的,也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三、 表达的方式:语言与乡土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通过语言与世界建立联系的,因此,可以说小说家对语言的态度和策略是其文学观念和文学审美的重要表征。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不会否认语言在作品中的价值和意义,但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一些作家往往重在对所谓的“经验”和“思想”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语言的忽视和弱化,正如有学者指出:“受市场之手的指挥,更多的作家重量轻质,很多人嘴上认同‘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但是实际上语言观念淡漠,压根儿就没有把语言当作一个‘问题’。一些实力派作家更多地沿袭旧的语言策略,在已有的语言习惯上滑行;而文学‘新秀’关注较多的是‘写什么’,而不是‘怎样写’,语言更不会受到特别的注意。”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发现叶炜一直在强化语言的个性自觉,始终在凸显语言的审美力量,如他自己所说:“首先是语言,语言要有味道,要有自己的特点,要有幽默感,让读者读到某处要产生会心的微笑。”在创作中叶炜始终在寻找从语言走近乡土的路径,以实现对乡土主题更为有效的表达。


保稳定,防汛抗旱减灾工作成效显著。成功战胜局部洪涝和严重干旱,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群众24万人,累计提供抗旱水源约41亿m3、浇灌面积3 298万亩次,挽回粮食损失41.5亿kg,保障了农业生产用水和群众饮水安全,保障了防洪和人民生命安全,保障了全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防汛抗旱减灾效益达187.1亿元,夺取了防汛抗旱工作的全面胜利。
更值得注意的是,叶炜对语言诗性的精致化追求可视为其乡土小说创作的一种语言策略。在乡村世界的书写过程中,叶炜并不过多地依靠方言、俚语来呈现乡村的生活状态,而是以诗性的语言来表现乡土世界的审美旨趣,从而在诗性语言与乡土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在阅读过程中,这种张力中更容易引导读者对乡土世界进行凝视与观照,更容易形成对人与土地关系变化的思考与审视。于是在这种观照与审视中,我们体味到了乡土世界中的喜悦、痛苦、无奈与哀愁。比如《富矿》中对乡村生活场景的描写:“三天五天以后,漫山遍野的金黄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或高或低的麦茬。不知哪个捣蛋鬼往地里扔了个烟头,干燥的麦茬瞬间便燃烧起来。临近还没有运完麦子的男人和女人嬉笑着大骂那个放火的家伙,着什么急,烧死人一样!边骂边加紧运麦子的速度。放火的被骂得不好意思,笑嘻嘻觍着脸过来帮忙,分享着收成的喜悦。” 比如《后土》中关于麻庄人对于死亡的感受:“在麻庄,一个人死去,就如同他出了趟远门,活着的人根本感觉不到他的离去。在麻庄,有许多死人还在被口口相传,仿佛他们还依然生活在自己身边一样。” 再比如《福地》中老万离世时的场景:“老万在半路上回头看了最后一眼麻庄,他看到在一片葱绿当中,掩映着一袭白色,那是众人在给他行‘路祭’。在万乐的帮助下,万达在老万的棺前摔碎了火盆。看着火盆落地,老万叹息了一声,走了。”这些简洁精致的语言,隐隐散发着一种凝重、哀婉的气息,与叶炜在小说中表现的反思与忧虑相得益彰。不难看出,叶炜不断在追求小说语言的变化和创新,以语言的力量来拓展小说的艺术世界。
四、 结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范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3BZW122),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参见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8页。
②参见贺仲明:《20 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形态及其新变》,《南京师大学报》2004 年第 3 期。
④汪政:《贴紧大地的书写——评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之〈福地〉》,《关东学刊》2016年第5期。
⑤鲁克斯、沃伦著,主万等译:《小说鉴赏》,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页。
⑥叶炜:《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种在阳台上的庄稼》(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页。
⑦李新宇:《如何面对这片乡土的前世今生——就“乡土中国三部曲”致叶炜》,《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5期。
⑧吴义勤:《自由与局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⑨张卫中:《当代文学应再造汉语诗性的辉煌》,《文艺报》2014年1月6日。
⑩叶炜:《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种在阳台上的庄稼》(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