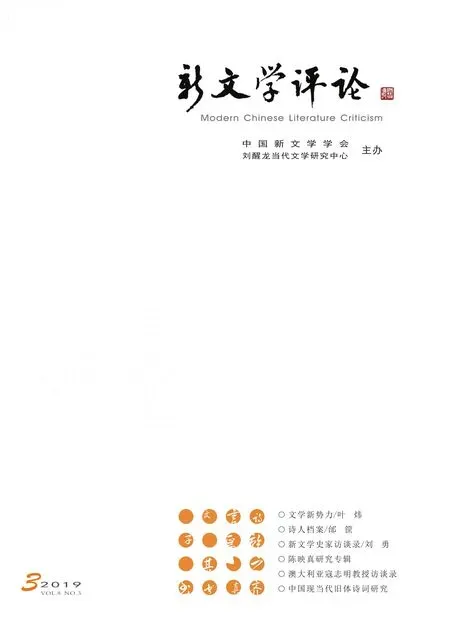叶炜“新乡土写作”在当下的重要意义
——以“乡土中国三部曲”为中心的考察
2019-11-12田振华
□ 田振华
新文学以来,乡土文学历经百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当代文学最为成熟和重要的文体形式之一。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文艺理论的大量引入,学界对“乡土文学”概念的界定、发展流变等的讨论愈演愈烈。至90年代,这一讨论似乎达到顶峰,并形成大致共识,即乡土文学已经发展成熟并基本定型。但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市场经济的持续推进、城乡格局的打破、人口流动的频繁等,乡土中国呈现前所未有的剧烈变迁。乡土文学在这一时期也呈现新的面貌,新乡土写作乘势而起。“新乡土写作”概念提及以来,对之的定义众说纷纭,但正如新乡土写作的实践者和理论的倡导者叶炜所言,新乡土写作必须具备新的文学视野、新的思想境界、新的写作手法。宋学清也认为,新乡土写作要具有世界性视野,要讲述中国故事,要表现中国乡村新问题、新现象与新农民。新世纪以来较为成熟的新乡土作家大多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具有“文革”经验的作家相比,70年代出生的作家大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而逐步成长起来的,童年或青年时代见证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的高速转型和变革。同时,这一时期的农村生活经验也给他们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穷的创作源泉和动力,乡村童年记忆也成为他们未来眷恋和怀念乡土的精神之“根”。中青年时代的他们开始走出乡村并进入城市甚至走出国门,在现代化的城市产生了对故土的深深怀念和留恋,在城乡对比中更为清晰地回望和书写中国乡土大地的转型、发展与变迁。可以说,新乡土作家是兼具乡土生活体验和世界视野,同时具备较高文学素养的一个群体。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叶炜就是这样一位持久关注并持续书写乡土中国的作家。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是21世纪以来他耗费15年左右时间呕心沥血创作的乡土文学力作。“乡土中国三部曲”以百年乡土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变迁为重点书写对象,也成为新世纪以来展现乡土中国变迁和乡土文学流变的重要文本。“乡土中国三部曲”不论是在创作的时代背景、乡土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乡土风貌、风俗信仰的书写和艺术手法的呈现等方面都与传统乡土文学有着较大差异,为新世纪乡土文学的书写和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可以说,叶炜已经成为新乡土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也充分展现了乡土文学“新”的特质。从他的成功创作所提供的经验来看,新乡土写作的未来也呈现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具备新的价值意义。
讲述具有时代经验的中国故事
与数千年的古老农业中国相比,虽然自新文学至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乡村也随着历史的车轮发生了细微变化,但是这一时期的乡土中国仍旧沿袭着旧有城乡格局的稳定状态。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在助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对乡土中国原有的城乡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和工业化、城市化的持续推进,更是直接改变了当下的乡村面貌。从外部来看,虽然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仍有着较大差距,但是中国农村已经打破了原有封闭的格局,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大,经济往来进一步加强。虽然土地仍旧是农村生存生活的重要收入来源,但是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和村办企业、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当下农村的收入来源途径更为多样,甚至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从内部来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在经受城市影响的同时,自身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新一轮的土地流转,从取消农业税到土地承包制度,从兴办村级、乡镇企业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生态农业等。这些变化都对农村和农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乡土中国正在朝着城乡中国甚至城市中国的方向发展,可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当然,中国的快速现代化进程在推动乡村变革、带动村民走向富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多不可遏制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谁也避免不了也不能抗拒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巨大车轮,但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从乡土到城市,而是从乡土到城乡。既然是从乡土到城乡,那就意味着‘乡与城’关系既有隔离、对立,更有交往、转型。”从对立或负面影响来看,既有市场经济下的物欲横流导致的利益至上和人性异化,又有过快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导致农村土地、人口的流失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等。按照马克思主义新旧事物交替原理,这些负面影响在转型期的中国也许难以避免,且在转型初期会较长时间存在,成为遏制乡村转型发展的一股邪恶力量。从这一角度而言,当下的新乡土写作面对的是新的时代背景和命题,即多元的、复杂的乡村变革洪流正在急剧上演。这为当下的新乡土写作提供了不竭的创作源泉。正是有了新的时代背景,才有了新的乡土风貌,进而才有了新的乡土文学。
叶炜的写作既关注到了改革洪流对中国乡村的正面影响,又更多地书写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乡村由外到内的冲击。《富矿》书写了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对话、融合和碰撞,工业文明既为农村带来了福利——提供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发展等,也对原有的乡村生态格局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人性堕落、土地塌陷和流失、环境污染等;《后土》则书写了麻庄四代村干部带领麻庄人在时代洪流下寻求致富道路的艰难历程,也写出了以王远、曹东风、刘青松为代表的乡村干部之间的权力博弈和纷争;《福地》则以现代性的视角切入麻庄历史,其目的同样是对当下的现代化进程给予历史的启示和借鉴。《福地》《富矿》《后土》共同构成了百年中国的沧桑巨变和乡土史诗。“乡土中国三部曲”紧紧抓住时代脉搏,写出了具有时代经验的当下中国故事。可以看出,与传统乡土写作相比,乡土中国面临的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使得新乡土作家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乡土书写现状。一方面,任何作家都不能摆脱这一时代而独立存在,这种变革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作家的创作中;另一方面,这一复杂的乡村变革现状又需要作家以更为敏锐的眼光抓住那些反映当下社会的真现实、真问题,以更为悲悯的情怀关切民生疾苦。与新时期一起成长的叶炜,在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后,一直在高校进行文学创作或接受文学理论的洗礼,能够以清醒的头脑、更高的视野审视乡土,在对乡土中国进行实际关切的同时,作品也呈现着一定的审美距离。这种审美距离的拿捏实则是对作家极为重要的考验,无则略显枯燥,过之则又显得凌空高蹈。综合来看,对新乡土作家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时代是乡土写作最好的时代,也是新乡土写作的黄金时代。
写出当下大变革时代农村人性的复杂
人们是历史车轮的核心推动者。当下乡村的大转型、大变革也是由千千万万个个体共同完成。这些个体有集思想智慧与谋略才干于一身的时代的先行者、弄潮儿、旗手,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庸普通的默默无闻的劳苦大众,也有为一己之利不择手段并阻碍社会前进的负面人物,还有无法跟上时代快速前进的步伐,甚至某种程度上说依旧是愚昧麻木的落后者形象。这形成了历史前进道路上的两股不同的势力,这两股势力在进行人与人、家族与家族、村庄与村庄等纷争的过程中,也无形中成为整个乡土中国前进的拉力和拖力。当然,人性是复杂的,任何人物其性格特征都不能用单一“好”或“坏”来形容,也不能用完全的“真善美”或“假丑恶”来呈现。当代乡土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新乡土写作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复杂的时代改革面前,人物形象呈现多面性,新乡土写作既塑造了正面人物形象,又有负面人物形象,但更多的是塑造了矛盾的、复杂的人物形象。这些复杂的人物形象既是时代的推动者,也是个人利益的获得者;既有集体主义倾向,也有个人主义倾向;既有土地的拯救者、留恋者形象,也有土地的破坏者、愤恨者形象;既有乡土的坚守者形象,又有城乡之间的游离者形象,还有完全背离乡土进入城市的形象。但是,叶炜在作品中所呈现的是:无论他们如何远离故土,家乡总在他们内心深处占有一席之地;无论他们走得多远,家乡总会成为他们精神的皈依。这些形象与传统的乡土人物有着截然的区别。新乡土作家们的主要任务是抓住这些新人物形象的时代和性格特征,写出人性的幽暗和深邃,捕捉新时代、新乡土背景下人物性格的暗流涌动和澎湃激荡。
叶炜《后土》中的王远和曹东风、《福地》中的万仁义等都是各自村庄中的核心人物,他们的言行举止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村庄的发展和前景。这些人物既是村庄历史的推动者,又曾为了个人利益而做出违背良心之事,甚至有些不择手段,程度令人发指。叶炜《后土》中的王远和曹东风是掌控麻庄的两代村干部形象。王远表面上看是个好干部,但实际上,他利用与镇上领导的关系在村里胡作非为,贪污腐败,与村里多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可以说是个道貌岸然、表里不一、奸诈而又恶毒的小人形象。曹东风虽然在担任村干部期间也曾为争夺权力而用尽心机,但他也为麻庄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发大水后积极帮村里困难户修房子,引导村民建砖厂、承包鱼塘、养绵羊等。《福地》中的老万是个旧时代麻庄的乡绅形象,虽然身上也有着不检点的行为,但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守护着麻庄的村民和土地,为麻庄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叶炜塑造的这些形象,既是赋有时代印记的鲜活人物,又具有着自我独特的个性特征。虽然这些人物形象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污点,但他们就是当下这个新的时代存在的新的人物形象。他们与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等形象截然不同,与柳青笔下的梁生宝、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也有所不同,甚至与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张炜《古船》中的隋抱朴等典型人物形象也不尽相同。叶炜笔下的这些人物是复杂的,他们的形象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或好或坏的变化。甚至在现代化的初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今天,他们这些掌握村庄权力甚至命脉的核心人物,在大是大非面前更多地或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叶炜深切地看到了这一点,也在“乡土中国三部曲”中对此重点表达和批判。除以上人物形象之外,《富矿》中的农民形象六小、矿工蒋飞通,《后土》中的刘青松、刘非平,《福地》中的万福、万禄、万寿、万喜等都是颇具特色的人物形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叶炜在“乡土中国三部曲”中着重塑造了一系列乡村女性人物形象。这些赋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女性人物形象既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暗示了她们力争在社会立足以及与男性争夺社会地位过程中的艰难。《富矿》中的麻姑、《后土》中的翠香等都是他重点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叶炜《富矿》中的麻姑在麻庄煤矿未被开发之前,过着中国传统女性一般的生活。自从煤矿建成和嫁给矿工蒋飞通后,麻姑一步步走向了堕落:从与青梅竹马的六小的私通到丈夫死后沦为矿上任人骑的“大洋马”。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产生冲击时,乡村原有的伦理结构也随之土崩瓦解。《后土》中的翠香早期为了孩子忍辱负重被道貌岸然的王远欺负,之后性情中人的她看上了有妇之夫刘青松,大女儿被乡村教师高翔强奸后抛尸井底,最终她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王傻子,命运无情而又残酷地捉弄着无力而又无奈的她。从以上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分析来看,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当代乡村女性有了较强的自我主体意识,在言行举止等社会行为上可与男性达到基本平等,但是在婚姻和两性关系上,女性往往仍旧处于弱势。她们或者沦为男人性的工具,或者成为男人生意场上的牺牲品,或者沦为风言风语的受害者。总之,在当下的乡村,女性与男性可以有基本的平等,但仍在某些方面受压制,乡村女性权利的维护仍旧有很远的道路要走。这是叶炜重点关注和呈现的。这些人物形象同样与传统乡村的女性形象有着较大的差异。究其原因:一方面,改革开放使得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女性较多施展空间,使得女性自我主体意识逐步增强;另一方面,在新的时代,女性也面临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自我保护的基础上得到社会特别是男性更多情感上的关注和心理上的认可。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新乡土写作对当下乡村女性已经给予重点关注,对其形象的塑造也有了新的突破。
风俗信仰的呈现和对现代化的反思
新时代造就新的乡土生活,产生新的乡土风貌。地域风貌、风俗信仰作为乡土小说重要的表达对象,成为展现地域文化独特性的重要标志。好的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地标和精神原乡,贾平凹的棣花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毕飞宇的兴化县等都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叶炜自然也不例外。叶炜的苏北鲁南也成为“乡土中国三部曲”中的文学地标。他从这一地标出发,展现故土的变迁,挖掘地域文化的深层内涵。具体而言,以叶炜为代表的新乡土作家对乡土风貌和风俗信仰两个方面的呈现给当下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乡土中国的地域风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到各地域虽有差别,但总体而言,都是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朝着乡镇化、城市化方向迈进。这一乡村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必然对原有的乡村布局、结构造成巨大的冲击。为节约土地,村民拆迁后集中居住;为发展工业而占据农田和居住地;为增加耕地,将原有废弃房屋夷为平地……由于粮食的附加值较低,在农民总收入中占据比例越来越少,与传统乡土中国比较而言,耕地在当下乡村的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而为实现现代化兴建的工厂、水泥地等越来越普及。可以说,土地在农民心目中的经济地位越来越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不论是情感关系,还是劳动关系与权利关系,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农民对土地的疏离、抛荒和农民土地权益的丧失等,是最突出的现象。”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化给当下乡村带来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土地越来越少造成农民归属感缺失,工厂大规模生产造成农村环境严重污染等。此外,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乡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乡村人口年龄结构极为不合理,留在乡村的更多的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乡村人口的外流也使得大量农村出现“空心村”现象,使得乡村风貌大为改观,也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当下的新乡土写作中,作家们对乡村风貌的呈现,不再仅仅关注农民如何致力于农业生产,作品中也很少看到农民能够仅仅依靠农业生产而发家致富,而是呈现出现代化进程导致的种种变化,这是新乡土写作与传统乡土写作在乡土物质和人文风貌的展现上的重要区别。在《富矿》中,随着麻庄矿的开发,原有的村庄风貌完全打破,种地已经不再是麻庄人唯一甚至主要的收入来源,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滥挖滥采,麻庄土地塌陷、环境恶化。在《后土》中,虽然麻庄村西有着一望无垠的大平原,村东有着苹果园,但作者重点论述的是以曹东风、刘青松为首的村干部为带领村民发家致富而创办砖厂、改建鱼塘、养绵羊的过程。进入新世纪,以刘非平为代表的麻庄第四代领导人开始在麻庄兴建小康楼,原有村民的居住格局也发生了显著甚至根本性的变化。
如果说作家对当下新的乡土地域风貌的书写是对乡村外在物质层面的呈现,那么对乡村风俗信仰的书写则是对乡村内在文化层面的挖掘。叶炜在“乡土中国三部曲”中重点书写了不同地域风俗信仰对村庄村民的或显或隐的影响。也就是说,他在对当下乡土外在物质层面关注的同时,还从文化的角度探索这种新乡土背景下人们对过往风俗的坚守和信仰的追寻,进而呈现当下乡土世界人们的天命观、历史观和世界观等。时代大变革虽然对乡土中国有着巨大的冲击,但在当下乡村仍有着对传统风俗、信仰的坚守和传承。当然,毋庸讳言,当下乡村中的有些风俗和信仰,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原理,甚至可能是封建迷信,违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但这就是变革时代当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新旧交织的、最真实的乡土现状。
(4)边坡开挖预裂孔残留孔率控制:①在开挖轮廓面上,残留孔痕迹应均匀分布;残留孔痕迹保存率,对完整的岩体,应达到85%以上;对较完整和较破碎的岩体,应达到60%以上;对破碎的岩体,应达到20%以上。
对风俗而言,叶炜在作品中呈现最多的就是与生活起居、婚丧嫁娶等有着密切相关的乡土风俗。在《富矿》中,有大量关于苏北鲁南风俗的描写:麻庄仍流行着说媒和相亲的传统;苏北鲁南农村有着约定俗成的“初一十五不出门”的传统;婚后第一年男方要给女方家送聘礼,聘礼为俗称“八个八”——八只鸡、八条鱼、八斤水果、八斤肉的传统;等等。苏北鲁南乡村的婚礼也很讲究,婚礼日期要请先生按照双方生辰八字计算,闺女出嫁宜早不宜晚,婚礼讲排场,往往需要集整个家族甚至全村人的力量。在《后土》中,麻庄村民依旧遵循着天地伦常,按照二十四节气来春耕秋收;地方柳琴戏《喝面叶》,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地方戏,深受苏北鲁南群众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叶炜在“乡土中国三部曲”中多次使用了颇具地方特色的民谣、歌谣、童谣等来记录和歌唱当地风俗,这些口语化的表达方式使得地方风俗显得更为通俗易懂和朗朗上口。对信仰而言,叶炜表达最多的就是对于土地以及由土地生发出的万物的信仰。在叶炜的《后土》中,有一个贯穿整部小说的民间信仰意象——土地庙。麻庄人对土地庙的信仰已经有着很久的历史,将土地庙视为守护家园和土地的对象。村民会定期到土地庙烧香叩拜,有问题找土地公、土地婆来请教或倾诉,家有老人去世要到土地庙集体跪拜,主人公刘青松则多次梦见与土地公的对话等。土地庙俨然成为麻庄人精神的皈依和信仰的归属。但归根结底,村民对土地庙的信仰是由对土地的信仰而来的,土地庙成为村民表达对土地敬意和崇拜的转化意象。
在现代化的时代,之所以作家们矢志不移地展现当下乡村仍旧存有的风俗信仰,除有个人情感或偏好之外,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对当下急剧变迁的现代化的反思。无论是对那些反映村民日常生活习俗的呈现,还是表达村民对信仰的坚守,都是日益现代化的当下所缺失的,也与今天人们普遍感觉缺乏信仰、无根性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以往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对传统采取的基本是全盘否定的态度,对那些封建迷信的、糟粕的存在予以成功剔除,但是也对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给以否定,导致现代人无法找寻自我的存在意义和生命的真实价值。叶炜《富矿》中麻姑一步步走向堕落,就展现了乡村的快速现代化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这是近年来新乡土写作的重要发现和突破。
新乡土写作艺术手法的创新与拓展
如果说以上的分析大都是关于新乡土小说“写什么”的问题,那么对于“怎么写”,新乡土作家依然提供了诸多新颖的、赋有借鉴意义的写作经验。具体到叶炜而言,从章节结构设置到叙事视角,再到语言使用,都彰显了他架构乡土小说的深厚功力和执着的艺术探索精神。
在章节结构设置上,叶炜的《富矿》选取的是由“0”到“71”再到“0”的结构形式,体现的是世间万物都是由“0”开始到“0”结束的轮回规律。“轮回”是佛教中的概念,而佛教在中国有着较长的历史,民间信徒众多,流传较广。《后土》采用的是“二十四节气”的形式,二十四节气恰好是一年,年复一年则显示的是二十四节气的周而复始。“从根本上说,二十四节气正是基于对太阳一年周期性变化的准确观测和把握。日月之行,四时皆有常法。”《福地》则采用的是“天干地支”的形式,从“辛亥”始,到“丙子”终,共60卷,即整一甲子,每卷又以时辰变化贯穿其中。“天干、地支分别指向两个祭祀系统,而这两个祭祀系统是古人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祭祀天日祈求庇佑,祭祀求子也是祭祀天日来庇佑子孙长全,是祭祀天日的所求之事。这使得天干、地支得以形成并反映古老的远古生活。”不论是“轮回”概念、二十四节气还是天干地支的使用,都无疑充分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这些传统文化具有时间的无限穿透性和空间的无限延展性,至今依旧深刻影响着中国乡村人们的劳动和生活起居,是古老中国人们集体智慧的结晶。此外,这些传统文化资源的选取恰到好处地符合了每部作品的写作主题,也为作家更好地表达思想情感助力不少。
在叙事视角上,叶炜的写作更有独特之处。最值得一提的是他通过独特叙事视角的选取而使作品达到了超现实的效果,呈现一种后现代叙事的意味。这给当下的乡土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写作经验。叶炜的《福地》最为明显地表现出这一效果。《福地》表面上看是以第一人称“我”作为主要叙事视角,但是这个“我”不是指任何一个人,而是生活在麻庄五百余年的老槐树。如果说第一人称“我”这一叙事视角有着一定的局限性,是限知视角,对他者过多的了解会让读者产生疑问,那么以老槐树这一带有神性意味的全知视角来展开叙事,就完全避开了这一弊端。老槐树这一主人公与作者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老槐树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数百年如一日地观照着麻庄的变迁,对麻庄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了然于胸。这一叙事视角的使用既给作者叙事带来极大的方便,也使作品产生了强烈的魔幻现实或超现实效果。可以说,作者对叙述视角的创新性使用所展现出的魔幻的、超现实主义的效果,既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方法的使用,又表现出当下中国乡村人们精神的神性和复杂性。
地域文化独特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语言,不同语言风格是不同地域文化长久积淀的结果。在现代化的今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和普通话的普及,民间方言土语似乎逐渐走向当代语言发展的边缘。除个别语言学家、民俗学家专门对此研究之外,普通大众已少有人关注。但是,新乡土小说家们不仅没有放弃对民间方言土语的使用,而且在不影响作品阅读的情况下有意增加对之的使用。新乡土作家既注重小说语言的发展规律,又能充分结合地域和时代背景,使用那些符合地域文化特色和人物性格的语言。在“乡土中国三部曲”中,叶炜能够结合时代和人物特征大量使用表现苏北鲁南地域文化特性的民间方言土语,让时代、地域、人物、语言四者相互印证,共同表达出新时代新乡土的本真面目。这成为读者深入了解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读者也可以借此领略一种独特的具有他乡民间气味的言说方式。在《富矿》中,手捏子、拉呱、熊妮子、歪脖子树、簸粮食等苏北鲁南方言土语的使用可以说随处可见。在《后土》中,表达苏北鲁南农村人物的语言贴切而到位,如当刘青松的老婆赵玉秀看到曹东风家的种猪跑到自家猪圈后,随口骂了句:“谁家的爹跑出来了也不管一管。”再如,当麻庄的第一位先人逃荒到麻庄后,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他忽然听到一声呻吟:“哎呦,你坐着我的头了。”不论是对民间方言土语的使用,还是书写贴切人物个性的语言,在叶炜的作品中都不少见。他没有盲目跟随现代化的步伐,而是通过地方语言特色而选取多样化的表达方式。不同语言策略的使用一方面考验的是作家的语言表达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作家有足够的耐心采集那些鲜活的民间语言样本,甚至按照人类学家的方式进行实地采访、调研,才能真正挖掘出那些符合地域文化特色的语用素材。叶炜有丰富的乡土生活体验,即使后来离开故土,也没有放弃对故乡的回望和关怀,而是以更加清晰的眼光和更为宽广的视野审视乡土。文学本就是丰富多样的,不同地域方言土语的使用在展现地域文化的同时,也增强了民族乃至世界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按照巴赫金的话语理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语言不仅反映着本民族杂语现象的大宇宙,而且反映着世界语言的大宇宙。
传播赋有当下价值的中国经验
新乡土写作发展到今天,虽然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解决,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新乡土写作已经具备了持续书写的新的时代背景,作家们也在艺术探索和美学追求上有了更为重要的突破。可以说,新乡土写作正在日益崛起并前景广阔。新时代,新乡土写作也具备了新的价值意义:一方面,新时代为新乡土写作提供创作源泉;另一方面,新乡土写作也为时代特别是乡土中国的发展提供文化意义上的反哺和精神上的食粮。新时代与新乡土文学形成互补、互鉴的良好格局。此外,新乡土作家在进行艺术探索的同时,也为整个当代文学的走向及未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果说新乡土写作基本是伴随着乡土中国大变革、大转型的步伐应运而生的,那么当下中国的这种持续快速而剧烈的变革,意味着新乡土写作的未来发展空间十分宽广。虽然说文学与时代并非完全同步和一致,但是任何文学都不能超越时代而独立存在。按照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步骤,未来数十年中国依旧会处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还会进一步发展。这一现代化进程必定会复杂而又艰难,而且不论时间长短,都会对当下乡村的发展产生不可磨灭甚至颠覆性的影响。小到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等,大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都会因之而发生或快或慢、或隐或显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必定是有好有坏、褒贬并存的。“正是因为这种分野,才导致了当下乡土文学发展的可能,也催生了乡土文学的新空间,也就是乡村空间、城乡交互空间、城中村、村中城等新的叙事空间,当然它的主题会变化,场域会变化,人物的精神构成会变化,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都会变化。”这就为未来的新乡土写作提供了充足而不竭的创作源泉。可以说,新乡土写作未来“写什么”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叶炜的小说创作已经对此作了足够的印证,也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大量引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迎来一次又一次新的潮流,先锋小说、新写实、新状态、底层写作等层出不穷。乡土文学也是其中的受惠者。但是,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对西方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的普及,这种小说中借鉴西方理论进行创作的潮流进入低潮或瓶颈期,甚至出现一些弊端。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我们对于西方文学和理论的过分崇拜和依赖使得中国文学正在逐步失去自我价值和传统,使得当代文学遍布着西方文学创作的影子。在那时,如果说哪一位作家不是跟随某些外国作家的步伐,好像不得在文坛立足。毋庸讳言,对西方文学的了解有助于开拓视野和激发创作,但是如果一味地亦步亦趋显然也不合理。另一方面,中国当下正发生着新的剧烈变迁,原有西方的文学和理论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下中国的发展现状,需要作家以新的视野、新的眼光进行新的阐释。正是在这时,在创作方式和理念上如何进行进一步的开掘,成为新世纪以来摆在作家们面前最主要和最棘手的难题。从叶炜新乡土写作的成功之处来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无疑成为一个至为重要的法宝和利器。或者说,未来的乡土写作要想取得新的突破,就要在借鉴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讲好真正的中国故事、传播赋有当下价值和意义的中国经验。叶炜已经在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相比较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来看,这些经验毕竟是冰山之一角。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对当下乡土有着深刻影响,对当下乡土人从言行举止到价值认同产生或深或浅、或隐或显的影响。这也需要并值得更多乡土作家对此进行深入、切实的挖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怎么写”的问题上,新乡土作家们完全可以在融合古今中外文化、理论等的基础上进行开掘和创新。当然,仅从叶炜的创作,我们便可以看到新乡土作家对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理论的努力。叶炜作品中的苏北鲁南地区位于孔孟的故乡——曲阜附近,以麻庄为代表的这一地域的乡村受到孔孟文化的影响较深,在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对乡土文明进行冲击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乡土文明的逐步瓦解,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传统乡村文明的反抗,这里的人们也更具有隐忍、中庸等性格。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并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结合中外特别是西方最新表达技巧予以呈现,如在叶炜的《富矿》中对老槐树的书写。一方面,中国乡村至今有着对古树的崇拜,这在许多作品里都有所呈现,也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相传;另一方面,他对古槐树的书写并没有停留在简单表达人们对它的崇拜上,而是将之上升到灵魂的高度。叶炜恰到好处地将古槐树和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相结合,当然,作家对传统文化资源借鉴的差异既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也与个人生命体验、知识结构等密切相关。
除此之外,新乡土作家还有一个可以挖掘的巨大宝库就是地域文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都有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在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信仰、价值观念甚至语言习惯等方面也都有着较大的差异,这些同样可以为作家提供无尽的创作空间。总而言之,不论是时代呈现的现实主义关切,还是艺术上无尽的探索,新乡土作家给当下乡土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提供了新鲜营养和最新价值。当然,如果说乡土中国变迁的道路漫长而又艰难,那么乡土文学的书写同样如此。新乡土写作在进一步探索书写空间、把握时代命脉的同时,需要更有担当、更有情怀的作家不畏艰难地向乡土文学书写的纵深处持续开掘。正如雷达先生所言:“我认为在现代性转向大背景下,如果发掘作家‘新’的视野、‘新’的观念,肯定作家发现、阐释、书写的有别于传统经验的新乡土,乡土文学仍大有可为。”如果从叶炜新乡土写作的创作实绩来看,我们还可以说,当下的新乡土写作正“风生水起”并“大有可为”。
注释:
①宋学清:《“新乡土写作”如何成为可能——以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为例》,《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
②张继红、雷达:《世纪转型: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雷达访谈录》,《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
③李兴阳:《“土地问题”与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的叙事想象——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土地叙事”研究》,《当代文坛》2015年第2期。
④刘晓峰:《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过程》,《文化遗产》2017年第2期。
⑤赵秀:《天干、地支本义与其对应的祭祀系统》,《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1期。
⑥叶炜:《后土》,青岛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⑦叶炜:《后土》,青岛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⑧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小说理论》,《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⑨张继红、雷达:《世纪转型: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雷达访谈录》,《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
⑩张继红、雷达:《世纪转型: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雷达访谈录》,《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