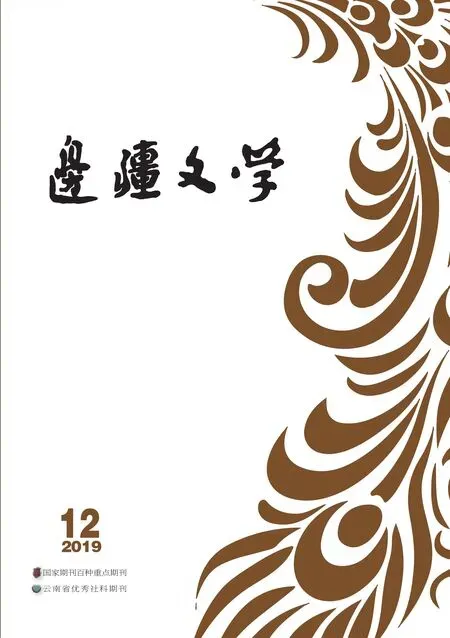小声说大河(二题)[散文]
2019-11-12马步升
马步升
涅瓦河的夜晚
童年时,我就知道世间有一条河叫涅瓦河,在苏联。那时候的苏联已经和我们翻脸了,我们叫它苏修。我们这些小孩子从此知道了,人有绰号,国家也有绰号,苏修就是苏联的绰号。有绰号的人一般都是不受待见的人,有绰号的国家当然也一样。我们的国家怎么没有绰号呢,因为是一个好国家嘛。我们的国家还有别的称呼,比如九州、神州、华夏等等,那都是敬称尊称,比现用国名还要尊贵的名字。这也和人一样,比如我们把医生和老师,都称为先生,有时在先生前面加上本人的姓,马先生高先生之类,有时姓都不加的,直接叫先生,好像天底下就这一个先生似的。
伙伴们放学后,隔三间二都要打一场群架。那是真打,所用武器都是应手的,在地头随手捡起土块砸,在河滩,弯腰捞起鹅卵石招呼,镰刀皮鞭之类,大约是正在给家中干活时,正好有架可打了,顺手充作武器的。孩子间并无什么深仇大恨,本村的孩子间大多都是本族兄弟姐妹,见天上学在一起,玩在一起,一个离不开一个,打起架来也毫不含糊。邻村的孩子大多都沾亲带故的,亲戚来往互为主客,礼仪不缺,除了在这种场合见面,再见面大抵都在打群架的战场上,打起架来也毫不手软。打完了,还是同学,还是伙伴。而且,打群架的双方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日内瓦协定”:打输了的,被打狠了的,决不许给家长和老师告状,谁要是犯了这种原则性错误,没人再跟你打架了。而且,永远会背上一个“玩不起”的恶名。
我们打群架的目的,不仅仅是顽童胡闹,也不仅仅是为了争强斗狠,我们是为了将来打仗,保家卫国,在几个假想敌里面,苏修排名第一。学校里,广播上,天天号召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打大仗,我们自以为都是打仗的行家里手了,敌人却迟迟不来。那个着急啊,那个沮丧啊,手脚那个痒啊!把这种种的情绪,只好暂且发挥到打群架的战场上。把苏修当成排名第一的假想敌,苏修却不能等同于苏联,因为苏联两个重要缔造者的画像还挂在教室里。我们打苏修是为了保卫祖国,也要保卫苏联。是没有被苏修修正过的那个苏联。乍听起来有些别扭,可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于是,就知道了涅瓦河。至于从哪个渠道知道的,电影?小说?还是别的?真的忘了。当然,长大后,读过涉及涅瓦河的俄苏作品很多,但不能把后来得到的见识穿越到童年去,不能像有些人,把多少年后人们才获得的某种理念,移植到自己先前的所思所想中,显示自己具有多么“先”的先见之明。
忽忽几十年,世事风云变幻,估计神仙也未必料得到,总之,在那年十月中旬,我来到了涅瓦河畔。在俄罗斯的十天时间里,我并没有调整手表上的时间,北京时间和莫斯科时间大约相差五个小时。我同时按照两地的时间作息。北京时间天亮时,莫斯科时间正是深夜,我按照北京时间起床,独自去大街上晃悠。北京时间的午饭时间,莫斯科时间该早餐上班了,我和团队一起做该做的事情,从未耽搁过任何工作。也就是说,我每天大约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涅瓦河是俄罗斯之行的最后一站,预计为三天。我要把这三天的时间全部利用起来。白天——莫斯科时间的白天——我与大家一起参加各种规定的活动。圣彼得堡的纬度已经跨在北极圈上了,这个季节白天很短,一晃,天就黑了。晚饭后,大约十点左右吧,大多数当地人也该休息了,而生活在北京时间的人正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酣睡正浓当口,却还没有到我平时习惯的上床时分。我平时一般是零点正式上床。回到宾馆,如果马上能入睡,则睡一会儿,不能入睡呢,我便按照北京时间起床了。我平时起床都是北京时间六时许。俄罗斯也许是因为劳动力缺乏,宾馆服务人员大多是中老年妇女,不像我们中国,宾馆服务人员大多是年轻女性,尤其前台服务员,无论大小宾馆,几乎没有不年轻漂亮的,而俄罗斯,无论前台还是楼层,都以中老年妇女为主。
俄罗斯的年轻女性都在干嘛呢,说真的,我知道的不多,更不全面。说一点观感吧,俄罗斯的女性本来就漂亮,尤其年轻女孩,走在大街上,举目移步都是年轻漂亮女性。是否可以说,俄罗斯年轻漂亮女性都在街上晃悠?我可没有这样说,也不敢妄语。天已经相当冷了,这些女性还光着两条小腿儿,穿着或长或短的靴子,在街上叮当叮当地走,同伴说,俄罗斯人的身体素质真好,看看那些姑娘,脚腕子上多有力量。我经过观察,她们腿脚上的力道固然是足的,但主要是经过形体训练,有些中老年妇女,体型已经相当臃肿了,走起路来,照样轻盈而动感十足。就这个问题请教俄罗斯人,他们的回答印证了我的观察所得。年轻姑娘们也很少戴口罩,不像我们的许多姑娘,包括许多小伙子,大夏天的都要捂一只大口罩,他们是怕别人沾了自己口香的光呢,还是怕别人的口臭污损了自己,不得而知。俄罗斯的姑娘也许知道自己的漂亮,便把漂亮尽情与他人分享,不戴口罩,便眉目有情,露着小腿,便让冷天多了些许暖意。
可惜我不懂俄语,夜晚独自出来,又不可能让翻译不休息。语言不通也自有妙处,调动一切这方面的知识积累,放飞想象,连蒙带猜,乐趣自在。我住在涅瓦河畔,离那座著名的大桥不远。深夜的河边人很少,也时有人在转悠,大多都是青年人,男性女性都有,也大多都成双成对。我顺着河边走,过桥,在河的那边走一走,又转回来,过桥,在河的这边转一会,再过桥,周而复始,大桥始终在视线内,这样便不会迷路。我看见码头工人在船只上装卸货物,我还看见过大桥从中间分开,放船只通行。我看见过河边无数的雕塑,有的雕塑已经残破了,可以从中窥见久远沧桑的历史风云,有的雕塑是簇新的,标示着这座城市也在变化。我所住宾馆的那个街区,据说是圣彼得堡最古老的街区之一,楼层都不高,很少看见五层以上的,而并排或对面的楼房,有的看起来很旧,有的看上去是新修的,但做旧了的。据知情人讲,二战时,这座城市遭受到严重破坏,战后,人们并没有借此将城市一律弄成新的,而是将破坏了部分,努力恢复成原样子。对于战争期间这座城市的遭遇,在几十年间,我陆续看过许多资料,还算熟悉,首次涉足,竟有些恍兮惚兮之感。所谓文化底蕴,这些旧建筑,或者修旧如旧的建筑里面,恐怕多少会储存一些吧。
在涅瓦河边的一座小码头上,停靠着一部轿车,无人,孤零零地。我感觉有些蹊跷,路过时,便有意离开几米远近。果然,轿车如飞驰在搓板路上,几乎要颠覆的那种情形。后排左侧玻璃开着一条缝儿,里面传来在特定情形下女性那种歇斯底里的叫喊声。走出很远了,这种叫声还尾随在身后,我回头试看,路过的行人和我一样,视若无睹,绕开轿车几米远,飒飒通过。而这时,在遥远的天际,出现了一抹绚烂的光彩。我知道,那是北极光。
在我童年时,这座城市名叫列宁格勒,涅瓦河仍然叫涅瓦河,现在,这座城市恢复了圣彼得堡这个老名字,而涅瓦河仍然叫涅瓦河。涅瓦河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不急不慢流淌着,向前不远,就是大海了。
住在黄河边
童年时,老家的村边挖出一具大象遗骸,放学后,每个午后,我们都像猴子一样挂在挖掘现场的悬崖上,来一波人,工作人员给讲一遍,来一波,再讲一遍,在那三个月时间里,来参观的人,每天从早到晚,一波又一波,从未断绝。可以肯定,这是我们村有史以来最热闹的时期,以后会不会在单位时间内有这么多人光顾,这个可真的不敢妄下断语。在此之前,谁又会料到,这个地方怎么会埋着这么一个稀罕的玩意儿呢,而当时,解说员肯定地多次对参观群众说过,埋葬黄河古象化石的山底下,还埋着一只黄牛那样大的老鼠呢。
四十年后,在一个博物馆看画展的时候,我邂逅了当年那位现场解说员。他不是专业解说员,他是考古队员,应群众的需要,临时客串了解说员。当然,不是我们互相认出了对方,一个朋友在给我介绍这位已经八十多岁的老者时,说他当年参与了“黄河古象”化石的发掘工作。我们的思绪就此共同穿透了岁月的迷尘。我把他当年解说时使用的核心语汇复述了一遍,他不禁感慨系之。二百五十万年前,目前世界发现最大、形体最完整、纬度最高的剑齿象化石。这就是他当年解说时所用过的核心语汇。全部挖掘出来后,化石总重量为八吨,被正式命名为“黄河剑齿象”化石,陈列于国家自然博物馆。我对老人说,您当年所有的介绍我都毫无疑义,因为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我是完全空白的。但对于您说这是黄河剑齿象,我心里大为不满,这明明是在马莲河边嘛。再说,我那时候已经看过不少地图了,知道不论从哪个方位走,出土现场距离黄河都在千里以上呢。当然,我以后才知道,马莲河只不过是黄河的一条三级支流,但是,叫成马莲河剑齿象化石,也没有问题吧。老人听后哈哈大笑,他说没想到,当年的一个小观众,还有这么大的心思。我问,您当年说还有黄牛那么大的一只老鼠呢,几十年了过去了,怎么不见有人前来挖掘,老人笑说,那只是推断嘛。
多年以后,我在见过许多大江大河后,定居于黄河边。站在黄河边,回望千里以外流过老家门前的马莲河,确实是一条毫不起眼的小河。可是,对于我,这条河却是我的生命之河,尽管,马莲河的水在注入泾河,泾河汇入渭河后,在三门峡附近,共同融入已经算是中下游的黄河了,而我现在居住于黄河上游。也就是说,我家门前的黄河里,并没有老家马莲河的水。不过,我宁愿假装在我的日常用水中,有那么一滴几滴,一定来自马莲河。河水固然不能倒流,但河水汇入大海后,海水形成云气,由季风送入大陆,形成降水,难道降在黄河上游的某一场雨水中,丝毫没有马莲河的贡献?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然而,真正在大河上下走过几回后,我突然醒悟到:黄河是地球上负担最重的大河。没有之一。雪山上的融水,自从以河流的姿势流淌在北部中国以后,黄河所流经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寸土地上的每一个生灵,无不依靠吸吮她的奶汁活命,而黄河所流经之地,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缺雨区或严重缺雨区。还有,超过补给量数倍的蒸发量,像扎在黄河上的无以计数的吸管,在向黄河榨取水分。还有,黄河所经之地,虽不时有支流注入,但每一条或大或小的支流,在汇入黄河时,无一例外都像一个个历经长途跋涉,到家门口已然气息奄奄的旅人,不是给家里带回了什么,而是亟需在家中补充损耗殆尽的体能。还有,黄河自从进入第二阶梯后,就到了传统农耕区,就到了人口稠密区,无数的灌溉工程在从黄河取水,而黄河上游中游,大型水库一座接一座,黄河被拦腰斩断达到十几处。我是查阅过历史上治黄资料的,这个曾在几千年典籍中被称为“害河”的民族母亲河,曾一度非但害不了谁,反被害死了。在下游,宽阔的河床里,只缓缓流淌着那么一溜窄窄的河水,干涸的河床里,自由奔跑着各种运载沙石的车辆。那一天,我面对黄河泪流满面,就像一个看着母亲咽气的儿子,而束手无策。
有一年春夏之交去延安参加一个活动,在间隙里,主办方组织大家去参观壶口瀑布。大家已经到了瀑布中心区,我还在询问瀑布在哪里,陪同的人指一指说,这不是吗。我定睛一看,一股涓流在面前像一条蛇在一道石缝里飞窜,我说这就是壶口瀑布啊?我感觉到,即便如我这种衰男,助跑几步,都是可以跳过去的。当证实这就是壶口瀑布后,像听到了对我的死刑判决书,我再也提不起精神了。此后,每接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参加某些活动的邀请函后,我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婉拒。其实,在我的心底是想去的,稍有空闲,便想沿着黄河走一走,看一看,但真的在行动时,又畏首畏尾,生怕看到什么令我心灰意冷的东西。
这种情形,在我居住城市的这一段黄河是不会有的,因为这是上游。本地有一首民歌唱到:早知道河里的水干了,还修那个桥做啥呢;早知道尕妹妹的心变了,还谈那个恋爱做啥呢。有人将歌词做了加工,变成:早知道黄河的水干了,还修那个铁桥做啥呢;早知道尕妹妹的心变了,还谈那个恋爱做啥呢。谁都知道,黄河上的铁桥在哪,歌词中原本一条不确定的河指向黄河,一座不确定的桥化身为黄河铁桥。于是,经常有人问我,兰州的黄河里没水了啊?我说哪能呢,兰州的黄河要是没水了,那北中国早崩溃了。看得出,有的人不怎么相信。对于缺少起码常识的人,是没有必要过多解释的。黄河上游的水量很大,消耗量很小,到了中游以下,补给量迅速减少,而消耗量迅速加大,加之泥沙含量急速增大,水量才渐渐不敷使用的。正是靠着上游的来水,在如此艰难的情形下,黄河才勉强撑过中下游,到达入海口的。为了不让黄河在中下游断流,上游做出过多么伟大的牺牲啊,为了水土保持,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大片耕地草地废弃,兰州以上的肥田沃土大多集中在黄河谷地,而一连五座大型水库,绵延数百公里,几乎淹没了所有河边平地。这样做,无非是发电,然后给中下游供电,还有蓄水,在枯水期,为中下游供水。
一条黄河,半个中国,黄河被尊为母亲河,母亲对儿女怎样,黄河对沿岸的人民便怎样。在定居黄河边以后,二十年间,我几乎每个傍晚,都要在黄河边步行二十里,看惯了水清水浊水涨水落,在很长时间里,每当我心中烦闷时,每当我产生无力感时,我便要来到黄河边,一眼看见不舍昼夜向东而去的河水,心中的某个结忽然自动开解了,所有的负面情绪都会被河水带走。我一直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但这一直作为一种事实,与我携手到现在。我深知,我是离不开河流了,童年少年时,在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岁月里,老家的马莲河带给了我绵绵不绝的人生动力,尽管那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河。人到中年以后,所幸有一条黄河陪伴,在艰难的生存中,沮丧过,失望过,但从未彻底绝望过。也许,因为黄河曾经泛滥过,也枯萎过,断流过,但从未彻底绝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