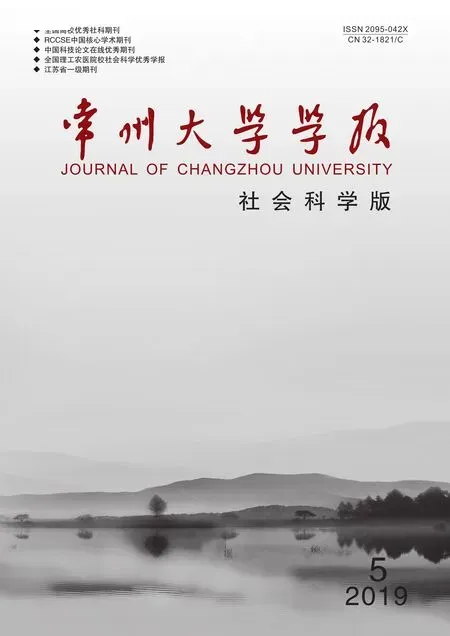蒋之奇潇湘摩崖石刻考释三题
2019-10-30陈安民
陈安民,周 欣
宋大学士蒋之奇(1031—1104),是活跃于北宋文人群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治平年间寓居潇湘,其仕宦经历有许多独特之处。《宋史》云:“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人。以伯父枢密直学士堂荫得官。擢进士第,中《春秋三传》科,至太常博士;又举贤良方正,试六论中选,及对策失书问目,报罢。英宗览而善之,擢监察御史。神宗立,转殿中侍御史,上谨始五事。”[1]10915蒋之奇历任福建转运判官,江西、河北、陕西副使,河北都转运使等职。为政期间,蒋之奇处事干练,多为百姓谋虑,治理漕运,修十贤祠,受到百姓普遍称赞。《蒋之奇天章阁待制知潭州敕》亦谓:“蒋之奇少以异材,辅之博学。艺于从政,敏而有功。使之治剧于一方,固当坐啸以终日。勿谓湖湘之远,在余庭户之间。务安斯民,以称朕意。”[2]所著有《孟子解》六卷、《荆溪前后集》八十九卷等百余卷,文集早佚。据《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记载,今存《蒋颖叔集》二卷、《三径集》一卷、《蒋之翰蒋之奇遗稿》一卷。
然则,关于蒋之奇的诸多史迹,充斥着诸多谜团,其生平亦有不少误判。本文以阳华岩、寒亭暖谷、九疑山等地存有的摩崖石刻真迹为线索,梳理蒋之奇的人生经历、社会交往,展现文人兴趣与时代思潮、政治身份与题咏刻石的双重互动关系,展现其在北宋文化史上的典范意义。
一、文人雅趣与蒋之奇阳华岩摩崖石刻
近日,笔者于湖湘区域江华瑶族自治县阳华岩搜访到蒋之奇摩崖石刻一则。由于岁月久远,泐损严重,且该题刻尚未引起学界关注,孤悬洞壁,倚斜疏散,能够清晰辨识的文字只有一部分,亦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经整理,兹录如下:
阳华岩,江华胜纪之地也。元结次山为之作铭,瞿令问书之,刻石在焉。自□□以还,不遇真赏者二百年于今矣。之奇自御史得罪,贬道州,是冬来游,爱而不忍去,遂铭于石间。
阳华岩位于湖南永州江华竹元寨乡回山。唐代元结两次出任道州刺使期间,曾在此作铭刻岩。《(道光)永州府志》载:“江华复岭重冈,地远而险,其山之秀异者,自古称阳华岩。”[3]220《(同治)江华县志》载:“阳华岩,在县东南十里。山势向阳,清迥高朗,中有石磬,下有寒泉。唐元结守道州时作铭,属邑合瞿令问书之,刻崖石,世称名迹,八景之一。”[4]元结任职之暇,以新奇的目光发现潇湘奇石泉壑之美,经常寻觅当地溪岩之胜。例如,他在《阳华岩》中,特别称赞道:“岩当阳端,故以阳华名之。吾游处山林几三十年,所见泉石如阳华殊异而可嘉者,未有也。”[3]220元结发挥其文学特长,通过“刻石铭记”的方式,打造了自己“独有”的山水文化烙印,相继作“十九铭一颂”[5],由此引发了后世文人墨客相继“跟帖”,抒发自己对潇湘山水之乐的体悟。
蒋之奇即是以文人怀仰圣贤的情怀,突出了阳华岩“爱而不忍去”之人文景象。而从石刻中“贬道州,是冬来游”来看,蒋之奇应该是刚来道州,事实上,这恰与《宋史》中“蒋之奇”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初,之奇为欧阳修所厚,制科既黜,乃诣修盛言濮议之善,以得御史。复惧不为众所容,因修妻弟恭薛良孺得罪怨修,诬修及妇吴氏事,遂劾修。神宗批付中书,问状无实,贬监道州酒税,仍榜朝堂。至州,上表哀谢,神宗怜其有母,改监宣州税。”[1]10915“濮议之善”即英宗生父濮安懿王尊号“皇伯”、“皇考”的争议。蒋之奇凭借在该事件中的良好表现,得到欧阳修的举荐,“以得御史”。又因宋神宗即位,“诬修及妇吴氏事”,即诬告欧阳修与长媳吴氏案,“问状无实”,遭到弹劾,被贬为“道州酒税”。
在遭遇“贬监道州酒税”的政治危机之后,蒋之奇似乎不再将人生目标聚焦于政治,更多的是在所管辖的区域,游山玩水,吟诗作赋,追寻元结遗轨。从形式上看,“元结次山为之作铭,瞿令问书之,刻石在焉”,因为元结作铭,瞿令问的山水之乐,阳华岩崭绝清奇的地貌特征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促成了他到阳华岩怀仰圣贤,涵泳性情,故刻石其间。但从实际内容上说,他通过描绘自然风光,书写远离尘嚣的宁静,借物言志,抒发情怀,“不遇真赏者二百年于今矣”,其实寓有对得不到“真赏者”任用的失落,以及被贬后的“愤懑”和对自身处境的“忧愁”。
饶有意味的是,与蒋之奇同时代的北宋文人,诸如周敦颐、沈绅等文人,也是如此。他们陶醉于自然山水,赋予景观以人文属性,蔚成风气。由此,“浴风舞雩”的精神气象被推向新的高潮,“自然之乐”演变为宋代儒家文人雅趣的一个特点。而“跟帖”元结亦成为纵贯唐宋知识阶层的公共话题,构成了潇湘独有的层累文化景观。这一线索,大规模地补辑了蒋之奇在潇湘的行迹。
二、《暖谷诗并序》的作者考辨
在距离阳华岩不远之处,有寒亭暖谷,元结以《寒亭记》“发帖”,称赞道:“今大暑登之,疑天时将寒。炎蒸之地,清凉可安,合命之曰寒亭。”蒋之奇紧随元结,“跟贴”作《暖谷铭并序》。然而,经考察,寒亭暖谷现存摩崖石刻不仅有蒋之奇《暖谷铭并序》,旁边还有一则蒋祺《暖谷诗并序》摩崖石刻。问题在于,《暖谷诗并序》是否为蒋之奇所作?蒋之奇是否因政治风波改名为“蒋祺”,蒋祺与蒋之奇是否系同一人?
对照方志史料,《暖谷诗并序》既刻之于石,也载之于籍,多可与传世史籍相互印证。因石刻模糊不可辨,现以《(道光)永州府志》为底本,迻录如下:
寒亭,本唐元结、瞿令问所构。宋治平中,成纪李伯英始得此大小二洞,蒋之奇为作铭,之奇从祖蒋祺,时为令,又纪以诗。
邑南山水秀且清,天地坏治陶精灵。有唐刺史昔行县,访得洞穴有寒亭。屈指于今几百载,磨崖字字何纵横。相随栈道倚空险,来者无不毛发惊。我来三载迷簿牍,有时一到泻余情。娱宾烹茶遽回首,孰知亭侧藏岩扃。成纪同僚到官始,居然心匠多经营。乃知物理会有数。天温桼谷原作□,天通寒因人成。鸠工畚筑忽累日,旷然疏达开光明。初疑二帝凿混沌,虚空之上罗日星。又若希夷擘华岳,暖谷之响轰雷霆。大岩既辟子岩出,岩中之景奇旦冥。门外春风刮人面,其中安若温如蒸。累垂石乳如刻削,周环峭壁无欹倾。旧梯既去小人险,新径知易君子平。临流地广又方丈,垒石经宇为轩楹。嗟吁土石仙山古,无情一旦逢时荣。方今出震成大器,鼎新基构清寰瀛。我愿天下无冻馁,有如此谷安生灵。不须吹律而后暖,千古宜以此为名。[3]222
“秀且清”、“陶精灵”、“倚空险”等词不仅生动描写了寒亭暖谷的奇异景象,对偶工整,辞采绚丽,而且由景到岩,由岩至人,记述“娱宾烹茶”、“多经营”的生活态度,最后归结到对“我愿天下无冻馁,有如此谷安生灵”的政治期望,联绵相连,脉络条贯,足以体现作者的独具匠心。
值得注意的是,《暖谷诗并序》在刻石与典籍之间,迥然异趣。笔者搜罗《湖南金石志》、《(同治)江华县志》、《八琼室金石补正》、石刻进行校考,排比异同,以求深化解读:
(1)《湖南金石志》作“延陵林咏书”、“太常博士知周事蒋祺”;石刻作“《暖谷诗并序》”、“太常博士知县事蒋祺”,未见“延陵林咏书”五字;《八琼室金石补正》作“太常博士知周事蒋祺”。

(3)“邑南山水秀且清”:石刻、《湖南金石志》、《江华县志》、《八琼室金石补正》“邑”作“县”。
(4)“天地坏治陶精灵”:《湖南金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作“天地坯冶陶精英”,《江华县志》作“天地胚胎陶精灵”。
(5)“访得洞穴有寒亭”:《湖南金石志》、《江华县志》“有寒亭”作“为寒亭”。
(6)“我来三载迷簿牍”: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来”作“此”、“簿牍”作“簿领”;《江华县志》作“我来二载迷簿牍”。
(7)“天温桼谷原作□”:《湖南金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无此句,《江华县志》作“天温桼谷因人成”。
(8)“天通寒因人成”:《湖南金石志》“天通”前有“繄”字,《八琼室金石补正》“寒”作“塞”。
(9)“又若希夷擘华岳”:石刻、《湖南金石志》、《江华县志》、《八琼室金石补正》“希夷”作“巨灵”。
(10)“暖谷之响轰雷霆”:《湖南金石志》、《江华县志》“暖谷”作“溪谷”。

(12)“临流地广又方丈”:《湖南金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作“临流又广□方丈”,《江华县志》作“临流又广地方丈”。
这四种说法并存,错综为文,颇有意味:首先,此题刻既未刻明具体年月,亦不署官位,且石刻未曾打磨,凸凹不平,隐约难辨,因此对首段序言部分进行了较大“瘦身”,体现出宋时湖湘学人对此摩崖石刻并不重视,也反映出该宋碑流行不广。其次,从字形方面来看,例如“我来三载迷簿牍”之“三载”误为“二载”,只是形近讹误或不谙生平。当然,除了容易发生文字讹误之外,还有篇章残缺不全的现象,如“天通寒因人成”等。再次,以时代风气来说,后世文士着意好奇,追求语式新奇,则涉及文学创作中字词句法的修辞问题,也涉及文学风格的转变等问题,诸如“县南”作“邑南”、“几百祀”作“几百载”、“巨灵”作“希夷”等,源于在收入文集时,对行文有所斟酌润色。
问题在于,蒋祺的生平系年据何考证?《(道光)永州府志》等记载:“之奇从祖蒋祺”,“祺族侄之奇”。从表面上看,蒋祺与蒋之奇姓名仅有一字之别,然辈分亦相差二代,“蒋祺”是否为蒋之奇因政治风波所更之名?此事攸关二人的身份,有待进一步考证。
简要回顾《暖谷诗并序》的各种版本,笔者发现,此碑在宋元时期不见文人提及,亦不见于金石学著作,来历不明。据《(隆庆)永州府志》载:“暖谷,在县东,寒亭之侧。宋治平守县尉李伯英、刘北得之,邑太守蒋祺命名,□文阁侍刺蒋之奇作铭。”[6]“又祺族侄之奇,有铭并序。永泰中,元次山为道州刺史,巡停江华,登县南之亭,爱其水石之胜,当暑而寒,遂命之。”[4]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载:“《暖谷题刻五段》,蒋祺诗,治平四年。蒋之奇铭,治平四年十月十七日。”[7]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蒋祺诗并序,正书,无年月,考在治平间。蒋之奇铭并序,正书,治平丁未十月十七日。以上二种,疑皆后人重刻。”[8]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暖谷题刻两段》,在湖南江华。蒋祺诗,林咏正书,丁未治平之孟春。蒋之奇铭,李宏正书,治平丁未十月十七日。”[9]
笔者综合蒋祺的传记资料,主要归纳出以下三点:第一,蒋之奇于治平四年(1067年)在潇湘境内多有刻石。联系“贬监道州酒税”的时代背景来看,其弹劾恩人欧阳修之举实属不当。迫于政治原因或出于某种心理顾忌,生活在道州的蒋之奇,内心无疑充满落魄失意之感。而且,治平四年前后,欧阳修反复请求罢免蒋之奇职位,先后上奏《再乞根究蒋之弹疏札子》、《又乞罢任根究蒋之奇言事札子》、《乞诘问蒋之奇言事札子》、《再乞诘问蒋之奇言事札子》、《封进批出蒋之奇文字札子》、《乞辩明蒋之奇言事札子》、《再乞辨明蒋之奇言事札子》等,势必在政治上将其置于死地,使蒋之奇的处境愈发艰难。蒋之奇既不能逃脱欧阳修的责难,也不能避免时人责其“小人”的讥讽,为尽力避免卷入斗争的漩涡,不得不时时警惕,小心翼翼,隐姓埋名,处于半蛰伏状态。此外,据杜维沫、陈新选注《欧阳修文选》载:“(治平四年)三月,降彭思永知黄州,蒋之奇监道州酒税”[10],“治平四年,转殿中侍御史、二月朔日劾欧阳修,贬监道州酒税”[11]。如果该选注的时间可信,那么欧阳修治平四年二月所奏《乞根究蒋之奇弹疏札子》:“臣近因误于布衣下服紫袄,为御史所弹。臣即时于私第待罪,蒙圣恩差中使传宣,召入中书供职。今窃闻蒋之奇再有文字,诬臣以家私事”[12],从字面意义理解“蒋之奇再有文字”之 “再”,即为多次,也就是说欧阳修上奏弹劾并不始于治平四年二月,而蒋之奇被贬道州应当在治平四年二月以前。
第二,蒋祺“治平二年(1065年)以太常博士知江华县”。关于蒋祺的传记资料,目前主要见于《全宋诗》、《唐宋人寓湘诗文集》等。《全宋诗》载:“蒋祺,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任江阴军签判(明嘉靖《江阴县志》卷一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以太常博士知江华县(《金石补正》卷一零三)。”[13]《全宋诗》收录了蒋祺《暖谷诗并序》、《又成五言律诗三首》等诗文,清代李瀚章编《(光绪)湖南通志》又据此收入二诗。近年湖湘文库编辑的《唐宋人寓湘诗文集》照录《全宋文》的四首诗文,其中蒋祺的生平介绍为:“蒋祺,生平不详,治平(1064—1067)年间任江华知县”[14]1027。
第三,蒋祺与蒋之奇署衔不符。蒋之奇为道州酒税,系监酒税官省称,为监当官;又,《宋史·职官四》:“博士,掌讲定五礼仪式,有改革则据经审议。凡于法应谥者,考其行状,撰定谥文。有祠事,则监视仪物,掌凡赞导之事”[1]3884,“监酒税官”与“太常博士知(江华)县事”不符。这是否意味着,蒋之奇在政坛遭遇排挤后,因族叔蒋祺知江华县事,故请求至江华道州一带为官。
以此而言,《暖谷诗并序》应为“蒋祺”所作。《湖南金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等有载:“《嘉庆通志》:‘琪,治平闲邑令。诗见《江华县(郑)志》。’按:蒋琪,疑即蒋之奇。《暖谷序》所谓县宰,吾族叔祖其人也。《金石补正》,廿四行,正书。祺,《省府志》误作琪。职官内亦同,无刻石年月,当在暖谷铭之前。《序》云:‘丁未治平之孟春。’《诗》云:‘我此三载迷簿领’,是蒋祺以治平二年之江华任也。《序》又云:‘邑尉□纪李君者,伯英也,而《官志》均以为邑令,恐误。岂后来迁转□□,其前之曾为尉耶?’”[14]5466源于“族叔”的亲属关系,触景生情,作诗以寄怀,在《暖谷诗并序》旁刻《暖谷铭并序》,并署名“蒋之奇颖叔”。
三、蒋之奇潇湘流域交游事迹举隅
又据《湖南金石志》[15]5456-5465载,蒋之奇在舜帝归葬之处的九疑山,存有四条题名:
(1)宋九疑山“无为洞”三字。《九疑山志》:“治平四年,沈绅、蒋之奇游此,取元次山‘无为洞天’四字,正其体,篆刻诸岩窦,而纪于石。”
(2)宋蒋之奇《碧虚岩铭》:“潇水之阳,九疑之□。清池涵镜,乱峰插□。庙临溪□,寺在山□。谁其爱之,义兴颖叔。”
《金石补正·永志》:“蒋之奇上多‘义兴’二字,石木所无铭,词前三行末石已缺损。《永志》,有‘谷笏麓’三字,当是据旧志补入。后款六行为郑安祖题刻磨去,《永志》遗之。首行尚存之,字六行存,治□□午字,盖即之奇所书时为治平甲午也。《志》别载有蒋之奇九疑山题名,疑即是刻。”
(3)宋蒋之奇“九疑山”题名。《九疑山志》:“在紫虚洞。”
(4)宋蒋之奇《赠黄冠何仲涓诗》。《九疑山志》:“在舜祠右石壁。”
无为洞原名碧虚岩,元结来游,作《无为洞口》诗:“无为洞口春水满,无为洞旁春云白。爱此踟蹰不能去,令人悔作衣冠客”。值得一提的是,“衣冠客”即是指为官者,表达了元结追慕自然山水,无心仕宦富贵的心态。
蒋之奇效仿元结,在九疑山题石作铭,表达了对无为洞自然景观的喜爱。其中,《碧虚岩铭》为四言韵文,自然清新,记录了碧虚岩及周边的人文景观。“庙临溪□,寺在山□”,无为洞旁的寺庙,暗示了蒋之奇有归隐山林的想法。有意思的是,蒋之奇在九疑山还作有《赠黄冠何仲涓诗》。《九疑山志》载:“何仲涓,宋郡人。游庐山,得炼丹之术,归隐何侯仙室。”[16]“何仲涓,别号黄冠师,宋时人。尝游庐山,得辟谷之法,归隐九疑何侯仙室,老而颜壮齿坚。熙宁时,蒋之奇赠之以诗,刻舜祠。”[17]虽该诗刻已佚,但何仲涓为仙释人物,蒋之奇寻僧访道,并为其题诗作跋,也反映出蒋氏对淡泊生活的向往。
《碧虚岩铭》下,有署款六行,可惜磨泐太重,仅存:“□之□奉□因□□登九疑□为□□无为洞□□□石室遂□□福寺憩□兹□勒铭□□治□□午。”如果说,《碧虚岩铭》的题刻时间为“治□□午”(《金石补正》考订为“治平丙午”,但经检索,治平年间无此纪年,疑为“甲午”,即治平三年),那么,这意味着蒋之奇初到永州的时间为治平甲午。与之同行的沈绅,“字公仪,会稽人。宝元元年进士,治平四年以尚书屯田郎中为荆湖南路转运判官”[18]。《全宋诗》收录了沈绅《和孔司封题蓬莱阁》一文,题目中的孔司封即孔文仲,孔氏反对王安石变法,曾撰有《(周敦颐)祭文》。在此,笔者无意于关注党争是非,但由此亦可说明沈绅的生活方式与周敦颐等人声气相通,以脱俗飘逸作为理想,在公务之余,寄情山水,留下诸多题咏。
与《碧虚岩铭》相唱和,沈绅作《无为洞铭》:“南行江华,出游九疑。恭欵有虞,乃登无为。庄严佛宫,清泠玉池。兹余盘桓,白云相随。□□沈绅,皇宋治平四年十月十七日,□□□□岩归时,蒋颖叔(下缺)。”[3]1149根据这篇铭文的语境,沈绅等人应当是前往阳华岩途中,在九疑山有短暂停留。这与蒋之奇《暖谷铭》“治平四年十月十七日”,在时间上刚好一致。可见,蒋之奇与沈绅具有喜爱山水的共同志趣,交游经历可基本重合。这似乎与蒋之奇被贬谪后,远离官场的烦恼与名利,沉迷“自然之乐”不无关系。例如,蒋之奇作《暖谷诗》、《暖谷铭》、《寒岩铭》,沈绅亦作《寒亭诗》,在寒亭暖谷相互酬唱,密切互动,还共同游历奇兽岩:
奇兽之岩,镶怪诡异。元公次山,昔所未至。我陪公仪,游息于此。斯岩之著,自我而始。勒铭石壁,将告来世。治平丁未同沈公仪游。[4]
奇兽岩又名狮子岩,与寒亭暖谷仅一山之隔,因洞口大石状似狻猊,故名之,徐霞客称“此景三湘绝有”。然奇兽岩诗刻为南宋邑令张壡于端平三年(1236年)重刻:“唯蒋颖叔,文高节奇。正名兹岩,作为铭诗。彼何人斯,大字覆之。来游来嗟,其孰与稽。端平丙申,邑令张壡,思永厥传。刻此崖际,俾冰壶孙,李焯古隶。凡百君子,爱而勿替。”[4]据石刻所载的“文高节奇”,我们可以大致推论当地人对蒋之奇的评价。
这类评价,在淡岩也有记载:“蒋之奇长歌最工”,“其游澹岩七古一首。又载:其游朝阳岩七古一首。王弇州称:其工书有苏黄法,则此题句百余字,亦足贵也”[3]1155。淡岩因修建厂房,填洞塞边,石刻大部分被毁。目前,笔者据《永州府志》补辑二则史料:一为熙宁元年(1068年)所作《题澹山岩》,云:“零陵水石天下闻,澹山之胜难具论”,尾署“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廿二日,蒋之奇字颖叔过此书。周甫、张吉刊”[3]1154。笔者据《金石文编》、《金石补正》等考证,得之:“此诗不见姓名,而《金石萃编》及《县志》皆属之蒋之奇”,“此诗作于元年,诸家皆误为九年,潜研独不误其书,故征信而可贵也。宗氏云:悉从拓本补正”[15]5316。
一为《澹山岩题名》,云:“澹山岩,零陵之绝境,盖非朝阳之比也。次山往来湘中为最熟,子厚居永十年为最久。二人者之于山水,未有闻而不观、观而不记者,而兹岩独无传焉,何也?岂当时隐而未发耶?……物之显晦固有时,何可知也?”[3]1155从“物之显晦固有时,固可知也”而言,这是否有着对蒋之奇仕途命运的暗示呢?实际上,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重用王安石,蒋之奇支持新政,与欧阳修等旧党纷争不断,整个政治态势发生了转变。此处“物之显晦”,与其说是对淡岩景观的描述,还不如说是对新旧二党政治风波,以及蒋之奇自身或显或晦人生经历的写照。尽管此方石刻未注明刻石年月,但时过境迁,蒋之奇此时的心态与其仕途遇挫、初至道州时的心态已是不同。当年,“之奇自御史得罪,贬道州,是冬来游,爱而不忍去,遂铭于石间”,希望远离世俗尘埃,游山玩水;而现在,蒋之奇从对阳华岩、九疑山等地自然景观的描述,转向元结、柳宗元“当时隐而未发”,指出元结等人并非不知澹岩风景“天下稀”,只是由于某些缘故没有题铭作跋罢了。蒋之奇借此含蓄表达自己的政治情感,即由于仕宦关系紧张,被贬谪至古来流寓之所的潇湘,不得不“隐而未发”,但“物之显晦固有时”,自己尚未对仕途心怀厌倦,即将重出江湖。由此,蒋之奇行事谨小慎微的特点,可见一斑。
事实上,蒋之奇追随元结、柳宗元等先贤踪迹,殆有深意。除阳华岩、寒亭暖谷、无为洞等刻石外,目前朝阳岩还留有蒋之奇等人游历的石刻:“鞠拯、项随、安瑜、巩固、李忠辅、蒋之奇,治平四年丁未秋九月,游朝阳岩。”[3]1146究其原因,一方面,从政之途的困挫,政治上岌岌可危的境地,促使他在政治领域之外,雅好山林风水,开拓生命理想,缓解精神压力,自然成为精神生命存在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道光)永州府志》所评,“蒋之奇、邢恕自外于君子,旦与常立钟传皆谪郡,属无善政可纪,又不合流寓之例,故第杂见《金石略》中”[3]891。另一方面,刻意追随元结等名流人士,借用刻石发“朋友圈”的形式以求得朝中奥援,能为他在吸引文人墨客的基础上发挥影响,以期引起官方关注,从而为自己的政治晋升蓄势。从宋代文人风气的角度而言,蒋之奇的刻石确实引起了后世文人的关注,例如,《蒋之奇寒岩铭》,即为南宋时江华县令虞从龙所重刻。“治平丁未十月,陪沈绅公仪游,蒋之奇颖叔作。右铭元刊于寒亭之上,年深字浅,几不可读。既新泉亭,得没字碑于岩左,意昔为斯铭设也,乃徙刻之,且以彰二公爱赏之志云。后治平一百二十有四载,邑尉西隆虞从龙、俾邑人李挺祖(下泐)……”[3]1148治平一百二十四年即绍熙元年(1190年)。而《蒋之奇朝阳岩西亭诗》,也为元祐四年(1089年)宋代张绶所重刻。这意味着,蒋之奇题名刻石,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吟诗作赋,相反的,他刻意追寻元结,这应与他所处的特殊环境有关,特别是元结在淡岩没有留下任何遗迹之事,却被他认为是“岂当时隐而未发耶?”。换言之,借由当地名流的政治力量,凝聚不同的“山水之乐”的体验,展示自己的翰墨之才,能吸引更多文人墨客不断书写、塑造、衍生。而在这种传颂的互动关系中,蒋之奇在学界与政界的影响也会与日俱增。很显然,蒋之奇题咏刻石之举,不无“彰名求进”的嫌疑,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
综上考述,蒋之奇在道州的贬谪生涯,虽时间不长,却留下了不少金石文字,这些记载,构成了追踪蒋之奇足迹、展现其“交友圈”的重要史料,亦成为后世文人群体“跟帖”潇湘人文景观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