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陈望道与中共的关系
2019-10-28钱益民
钱益民
陈望道是中共创始人之一,1923年退党后,他与中共是什么关系?他仍旧照他当年回答茅盾的话“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茅盾著:《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在党外为党默默工作。除了上世纪20年代他在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等为党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服务外,还有更多的案例可以说明他的政治身份吗?到了30年代中国的政治格局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后,陈望道的政治思想倾向有没有发生变化呢?中共对他的认识有什么变化呢?他在党外到底是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要回答上述问题,都需要扎实的一手资料才能说清楚,才能有说服力。
陈望道本色是一个学者,但是他关心政治。他不是一个脱离政治的学问家,但是他也不参与实际政治。倪海曙在长篇回忆文章《春风夏雨四十年——回忆陈望道先生》中说得最贴切,倪与陈望道相识四十年,但他四十年中“从未听见先生作过任何政治说教。他从1919年翻译《共产党宣言》以后,一直在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工作,可是从不炫耀自己的政治资历,也从不以什么‘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居”。倪海曙认为陈望道“从来不是一个脱离政治的学问家。抗日战争初期在上海,所有主要的日报他都订阅,我去看他,床上总是摊满了报纸。他搞学术研究,也时常考虑结合政治”。陈望道“耿直和质朴”的个性给倪海曙印象很深。“先生不是交际家,也不是演说家。他是个不会应酬、不会讲客气话、不会讨好别人的人,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特点。可是有时未免太直了一点,容易得罪人,或引起误会。先生对人其实是很厚道的。”这种个性的人去参与实际政治,大概不会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陈望道很早就明白自己的个性,给自己定好了位,选择了适合自己个性的文化教育事业,这是他成功之处。
那么脱党后的陈望道在党外到底处于什么角色呢?笔者在夏衍、冯雪峰的回忆录里找到几则材料,可以说明陈望道与中共的关系。
第一则,陈望道对解散“左联”的反应。
1935年8月11日关于解散“左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信,俗称萧三来信,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此事在夏衍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第192-201页有详细的记载。大致过程是,1935年11月中旬,“文委”开会时,周扬带来萧三从莫斯科寄给“左联”的一封长信,明确提出了要求“解散左联”。这封信是由史沫特莱转给鲁迅,再由鲁迅转给周扬的。这封信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左联”之目的,是为了“扩大文艺界的联合战线”,这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八一宣言》的宗旨是一致的。这封信写于8月11日,就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之后,也就是《八一宣言》发出后不久。萧三是“左联”驻苏代表。从这封信的內容和口气都可以看出,它是代表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左联”的指示。
这是一件大事,除了必须先征求党内外盟员的意见之外,还得广泛听取没有参加“左联”“社联”“剧联”等组织的文化界人士的意见。至于党外文化界人士,夏衍回忆中所述“我们”(具体指“左联”领导人,还是中共在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人群体?还有待考证)认为这一决策一定会得到他们同意的。事实上,萧三信中提到的“郑、陈、巴、王、叶”(指郑振铎、陈望道、巴金、王统照、叶圣陶),郑振铎和陈望道早在新“文委”组成之前,就和“我们”有过多次交谈。夏衍和周扬还将登在《救国报》上的《八一宣言》送给郑振铎看了,他不仅赞成,而且要夏衍把那份《救国报》留下,他要给朋友们看看。因此,夏衍认为,只要鲁迅、茅盾同意,那么通过茅盾向郑振铎、巴金、王统照、叶圣陶征求意见,他们是一定会同意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夏衍没有把陈望道包括在内。可见,在中共党内,没有把陈望道与巴金、王统照、叶圣陶并列,后三人与政治的关系更疏远些,与中共的关系更远些,知识分子的色彩更浓些。夏衍对陈望道与郑振铎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没有把陈、郑两人并列在一起说,而是分开说。对陈望道,夏衍显然是把他看成与中共立场一致,故而就没有通过茅盾向陈望道征求意见的必要了。
夏衍在回忆中接着说:“我们”把萧三来信给各联盟的党团成员看了,经过讨论,“一致同意解散原有的左翼组织,另行组织各自的广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之后,夏衍和陈望道、郑振铎谈话,告诉了他们萧三来信的内容,“并对解散‘左联和组织更广泛的文艺团体这个问题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同意”。夏衍还回忆道:“陈望道还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他说新组织的团体最好把戏剧、美术、音乐、电影等方面的人都包括在内,这样,新的组织可以叫做文艺家协会,而不单是作家协会,‘我们同意了这个意见。”这里,夏衍把郑振铎和陈望道并列,说明两人都同意了萧三来信的意见,尤其是陈望道,还提出了组织一个新的包容范围更大的“文艺家协会”的意见,被中共吸纳。
从解散“左联”一事来看,陈望道完全是赞同中共的主张。而且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心目中,陈望道是30年代早期“党外文化界人士”的重要代表人物,与郑振铎、巴金、王统照、叶圣陶并列。陈望道不仅赞同中共主张,而且还提出了更妥善的解决办法,并被中共接受。陈望道在党外文化界人士中,是有相当的话语权的。
第二则,陈望道与“著作者协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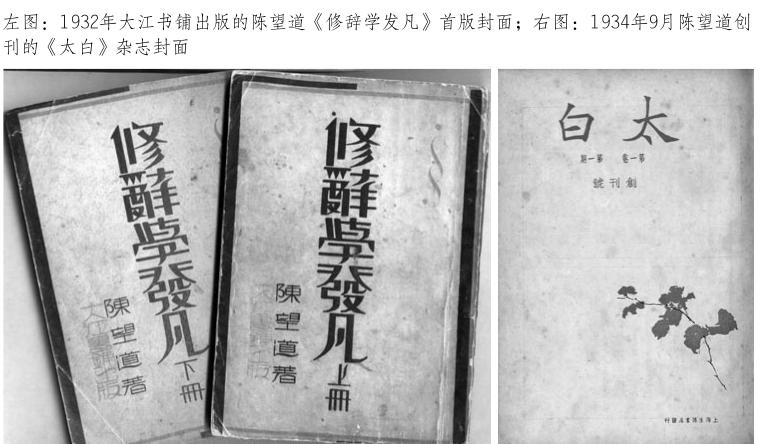
据冯雪峰1968年8月31日回忆,在1931年上半年,陈望道等人就曾经几次提起,“想发动著作人协会之类的广泛的组织,征求我们的意见。预期它是职业性的,带有职工会的性质,但也以吸收带有进步倾向的著作人为限,同时也负有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任务”。当时,“我们曾表示同意,并希望陈望道等人出面来进行”。不过后来又搁下来没有进行。到“九一八”以后,“陈望道等人又提出来,并且很积极,我们也表示支持,并且决定参加”。冯雪峰很清晰地记得这种组织带有统战性质,可以争取中间派。“当时我们认为通过这种组织,对于争取中间派人是能起些作用的,我记得这也在‘文委讨论过,并得到中宣部同意的。”陈望道于是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组织著作者协会的具体建议。1932年1月间,“中国著作者协会”在大世界旁边的青年会楼上举行谈话会,到会者有三四十人。关于参会代表,冯雪峰记得很清楚,“左翼方面到会的大概有十多个人(包括‘左联和‘社联),我也到会的;其他的人都是由陈望道等人提出经过我们同意的;其中有施复亮、梅龚彬、胡秋原、王礼锡、陆晶清等人,也是经过我们同意,并且经过中宣部同意的”。冯雪峰对这次会议的地点、出席人和开会情景都记得很清楚,回忆录里还说,这次谈话会是陈望道召集的,会开得相当久,关于组织的宗旨,什么人可以作为发起人,入会条件等问题,都有争论。争论中包括“我们同胡秋原、王礼锡等之间,大概在当天也有争论;记得好像他们曾提出托派的人——如严灵峰之类——也来参加发起人,而为我们反对掉”。冯雪峰还查阅了当时的出版物《文艺新闻》,补记了这个机构的筹备人名单,“‘左联方面是邓初民和我(冯雪峰),此外是陈望道、施复亮、孙师毅、胡秋原、王礼锡”。很清楚,“著作者协会”的筹备人考虑到了各方面的力量,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可供我们分析当时中共对上海文化界的统战策略。从陈望道提出的名单可以看出,他对“著作者协会”的构成持有包容的立场,把上海滩上政治立场迥异的著作人都吸收进来了。而且陈望道所做的一切,都与中共有协商,两者配合相当密切。
1968年10月8月,冯雪峰再次回忆“著作者协会”,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发生后出现的“上海著作者抗日会”,则是“由戈公振、陈望道、王礼锡、樊仲云等人发起,而我们(左翼文化界)也参加进去争取领导权并准备在内部对王礼锡、胡秋原等人进行揭露和斗争的一个团体”(《关于“上海著作者抗日会”》,《冯雪峰全集》(九),第191页)对成员构成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虽然冯雪峰的上述两条回忆都是在“文革”中形成,不免有夸大文化界著作人路线斗争之嫌,但是其中的事实不容否定。
第三则,陈望道与《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的签名。
冯雪峰还回忆了陈望道与“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一事。“一·二八”上海战事爆发后不到一星期,上海文化界发表过一个“告世界书”。签名的人更广泛,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领头,其中也有陈望道、任白涛等人,也有梅龚彬、胡秋原等人签名。宣言经中共中央宣传部看过,由谁起草,冯雪峰已经记不起来。作为一种策略,中共力求扩大签名范围,包括“要胡秋原之类的人签名”,这是“当时中宣部来直接领导的人(朱镜我)决定的”。宣言中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日帝屠杀中国民众、转帝国主义战争为世界革命的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保护中国革命等口号。(《有关“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和“著作者抗日会”的几点情况》,《冯雪峰全集》(九),第157页)在此,冯雪峰把上海文化界人士分成好几类,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是一类,陈望道与任白涛是另一类,第三类是梅龚彬和胡秋原等人。在这里,陈望道的角色是中派文化人。
从以上三则史料可见,在30年代初,陈望道是党外左派知识分子,不过身份微妙。有时候是左派知识分子里的中派。以这个身份出面,可以团结和推动右派知识分子,使其向中间靠拢,进而扩大左派的力量,增强党外知识分子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陈望道在党外为中共做工作,“也许比党内更方便”。
(作者单位为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