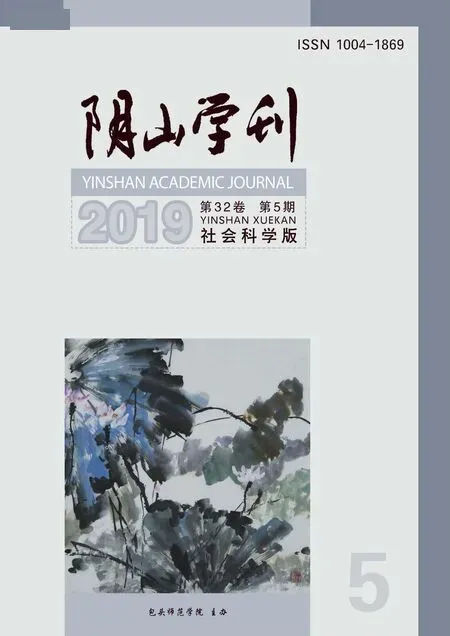阴山地区核心区域语言研究述评 *
2019-10-23李欣
李 欣
(包头师范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阴山地区区域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阴山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人物、风俗习惯的成果相对较多,但是还没有较综合、较全面的阴山地区语言研究(本文“阴山地区语言”是指“阴山核心区域语言,下同)成果面世。本文通过梳理阴山地区语言的研究情况及特点,阐述阴山地区语言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课题从整体上进行研究的意义。
本文中阴山地区语言主要涉及以下地区:呼和浩特市(下辖回民区、新城区、玉泉区、赛罕区、托克托县、武川县、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土默特左旗等)、包头市(下辖昆都仑区、青山区、东河区、九原区、石拐区、白云鄂博矿区、土默特右旗、固阳县、达尔罕茂明安联合等)、乌兰察布市(下辖四子王旗、察哈尔右翼前旗、察哈尔右翼中期、化德县、商都县、兴和县、卓资县、凉城县、集宁区等)、鄂尔多斯市(下辖伊金霍洛旗、乌审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杭锦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东胜区等)、巴彦淖尔市(下辖乌拉特前旗、乌拉特后旗、杭锦后旗、五原县、磴口县、临河区等)。
一、阴山地区语言研究现状
(一)阴山地区语言概况
阴山地区的语言主要包括蒙古语、汉语两种语言,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所使用的汉语。汉语大部分方言属于晋语区,归属不同的方言片,即:大包片(包头市、固阳县、武川县、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和林格尔县、托克托县、清水河县、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五原县、杭锦旗、乌审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四子王旗、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张呼片(呼和浩特市、卓资县、商都县、太仆寺旗、兴和县、化德县、察哈尔右翼前旗、察哈尔右翼中旗、集宁区、丰镇市)、五台片(临河区、杭锦后旗、磴口县)等。蒙古语主要是内蒙古方言,具体而言,有察哈尔土语(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商都县、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拉特特中旗、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固阳县)、鄂尔多斯土语(金霍洛旗、乌审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杭锦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东胜区、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五原县、磴口县)。回话,即回族所使用的汉语,主要分布在包头市东河区北梁新区和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等地。
最早有关阴山地区汉语音研究可以追溯到高本汉的《中国音韵研究》中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市)方言中大约1 700个例字,是目前见到有关阴山地区现代汉语方言语音最早的记录。最早将阴山地区主要区域的汉语命名为“内蒙古晋语”的是侯精一先生的《内蒙古晋语记略》,其中包括属于阴山区域内的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
20世纪50年代,全国方言普查后,该区域的语言研究成果渐渐丰富起来,表现在各种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语义以及语言之间相互借用等方面。具体如下:
(二)汉语
1.语音研究
阴山地区汉语语音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为研究范围的代表性成果;另一类是以阴山地区具体行政单位为研究范围的代表性成果。具体如下:

以阴山地区具体行政区域语音为研究对象的代表性成果有:(1)以包头市为研究范围的代表性成果:沈文玉《包头方言音系及同音字表》(1983)“认为包头方言的声母一共22个,其中包括零声母,韵母37个,声调5个,不包括轻声”[4];沈文玉《包头方言中的几个入声字词头》(1986)重点论述了圪、忽、日等词在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名词、量词、动词、形容词、语气词)的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和类型;沈文玉《包头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的比较研究》(2000)从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方面对包头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进行研究和说明并列出相关例字;沈文玉《包头方言中的儿化现象》(2001)列举了包头儿化规律,以及补充说明等。(2)以鄂尔多斯市为研究范围的代表性成果:宋秉章《鄂尔多斯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1987)以伊金霍洛旗方言点为基础,记录伊金霍洛旗周边六个旗县区方言系统;栗治国《伊盟方言的“分音词”》(1991)对伊克昭盟(今东胜区)的分音词进行研究和描写;辛玺娥《鄂尔多斯梁外地区方言的语音特色》(2002)从声、韵、调三个方面揭示鄂尔多斯梁外地区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等。(3)以呼和浩特市为研究范围的代表性成果:卢芸生《呼和浩特汉语方言本字考(一)》(1988)、《呼和浩特汉语方言本字考(二)》(1988)、《呼和浩特汉语方言本字续考》(1988)三篇文章对呼和浩特方言中的一些“本字”进行了研究;马丽娜《呼和浩特市城区方言字“e”“nia”的使用状况调查报告》(2013)“主要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言语社区、家庭、语言态度等方面入手,调查呼和浩特城区市民对方言字“e”“nia”的使用状况”[5];黄珂玮《呼和浩特方言声调特点》(2013)“对呼和浩特四个主要城区方言中的声调特点入手,通过与普通话声调进行比较,研究呼和浩特方言声调的变化规律”[6];蒋文华《呼和浩特方言韵母百年来的变化》(2014)“根据高本汉记录归化方言韵母跟当代呼和浩特方言韵母的比较,梳理一百年来的变化,同时,该文还论述了呼和浩特方言的分布情况”[7];霍伟丽《呼和浩特方言语气词“哇”的考察》(2015)“对呼和浩特方言中的‘哇’单独使用和其他语气词连用构成二合语气词的用法和意义进行研究”[8]。(4)以巴彦淖尔市为研究范围的代表性成果:雷雨的硕士论文《内蒙古晋语临河方言语音词汇研究》(2015)对临河方言进行了详尽的描写等。(5)以乌兰察布市为研究范围的代表性成果:王宇枫《从集宁方言普通话使用的三个阶段看普通话的推广》(2008)从集宁方言普通话使用的三个阶段研究该地区普通话的推广情况;妥彦平《内蒙古集宁方言语音研究》(2013)“通过对集宁方言和汉语普通话、中古音以及山西太原方言音读对比,得出一些相对可信的结论”[9]等。
2.词汇研究
阴山地区汉语词汇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一类是以“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为研究范围的代表性成果;另一类是以阴山地区具体行政单位为研究范围的代表性成果。具体如下:
以“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为研究范围的代表性成果:韩登庸《内蒙古西部地区何以能保留大量元杂剧中的方言俗语》(1991)讨论内蒙古西部地区方言中的词汇与元杂剧方言俗语地承接关系及其产生地原因;哈森《论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重叠式构词法》(1992)运用对比、说明等方法论述了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重叠式的类型及其特点;哈森《简论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单纯词》(1994)“通过介绍典型例词及其释义,讨论了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单纯词以及类型”[10];哈森《论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加缀式构词法》(1994)结合具体例词解释了加缀词在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的重要性;邢向东《内蒙古晋语的语气词“的”“呀”“么”》(1995)对西部汉语中的“的”“呀”“么”进行了具体的描写;邢向东《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祈使句的常用格式和语气词》(1995)描写了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句中的13种常见格式并讨论了几个格式和语气词的来源;李剑冲、郭丽君《论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词汇的几个特点》(1998)“从内蒙古西部汉语部分典型词描写出发,从六个方面对西部汉语方言进行了研究”[11]等。
以阴山地区具体行政区域词汇为研究范围的代表性成果有:(1)以包头市为研究范围:沈文玉《包头方言中若干虚词的用法》(1983)“对包头方言中既区别于普通话又区别于临近省区晋方言的同类词语进行解释”[12];胡云晖《包头方言探微》(2011)对包头方言词汇进行较为详尽的考察;吴燕《包头方言词汇研究》(2011)对包头方言720个词汇从构词、以及与普通话对比分析入手,论述了包头方言词汇的某些特点;胡云晖《“走西口”与颇具特色的包头方言》(2012)从“走西口”移民活动入手,对包头方言特点的形成、包头方言对山西方言研究意义以及相关问题进行论述;秦虹《包头方言分音词研究》(2012)以包头方言分音词为研究重点,主要从语音、语义、语法、语用几个方面对包头方言分音词进行分析;胡云晖《敕勒川地区汉语方言中的“风搅雪”现象》(2017)认为,“作为敕勒川地区的一种语言存在,“风搅雪”现象多鉴于传统二人台、山曲儿等演出中的道白与唱词以及蒙古语和蒙汉合璧的地名中,通过探究敕勒川地区汉语方言中的“风搅雪”的源流问题,对于深刻剖析敕勒川地区人文历史的发展变化,乃至社会变迁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3]。(2)以鄂尔多斯市为研究范围:栗治国《鄂尔多斯方言成语词典》,收词5 000余条,近50万字;此外,他的代表作还有《伊盟方言中的几个语气词初探》(1989)、《伊盟方言的“分音词”》(1991)、栗治国《河套地区民间婴幼儿语言训练探微》(1993)、《伊盟话的“露八分”》(1996);武燕《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A眉从C眼式四字格的特点》(2007)等。(3)以巴彦淖尔市为研究范围:李茹《巴彦淖尔地区熟语语言文化研究》(2015)“以巴彦淖尔地区方言熟语及其反映的文化立足点,通过对巴彦淖尔地区熟语的深入调查,搜集方言熟语的材料,并对其特点进行总结和分析”[14]等。(4)以呼和浩特市为研究范围:李作南、李树新《呼和浩特方言中常见的构词词缀》(1986)“主要讨论了呼和浩特方言中常见的构词词缀(包括前缀和后缀)以及由这些词缀都构成的词的一些语法特点”[15]等;李景泉《内蒙古清水河县方言中的古语词》(1992)“考证了保留在内蒙古清水河县方言中上古以及金元时代的一些古词语,并依据该县方言,对元杂剧中某些词语注释未详或未尽确切者,加以拾遗补阙,说明方言词对训诂的作用”[16];连漪《呼和浩特方言“的”字的研究》(2011)主要研究呼和浩特方言中“的”字的性质、呼和浩特方言中“的”字的比较研究以及呼和浩特方言中“的”字探源的三个方面;武彦赟《汉语呼和浩特方言特色词汇研究》(2013)“以汉语呼和浩特方言特色词汇为研究重点,从方言词汇的形成及特色词汇的来源、语义和语用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试图探究特色词所反映的民俗文化,揭示其使用的规律和特点”[17];王改平《呼和浩特方言中詈骂词的隐喻和转喻研究》(2015)“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分析呼和浩特方言中詈骂词词缀‘货’‘猴’‘鬼’的认知理据”[18]等。
3.语法研究
阴山地区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主要以“具体行政区域”为研究范围成果居多,(1)以包头市为研究范围:主要以吕世华的研究成果居多,如:《包头方言四字格的构成方式》(1991),着眼于包头方言四字格成语的构成方式与普通话四字格成语的差异,将包头方言四字格成语的结构方式分为五类,即:相加式、单一式、重叠式、交错式、附加式;《包头方言中几个特殊语法现象》(1991)“着眼于包头汉语方言中的词法特点,对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语气词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写”[19]。(2)以呼和浩特市为研究范围:李作南、辛尚奎《呼和浩特汉语方言一些词的语法特点》(1986)主要讨论了“习”和“一个”“个”“的”和“的了”“没”和“没有家”等词的语法特点;邢向东《呼和浩特方言中感叹句的常用句式》(1994)“对呼和浩特方言中的带“把”字的感叹句、用‘看’引导的感叹句、呼和浩特方言用来表达形状、程度达到极限的感叹句、由反问形式表达的感叹句、由‘一个’加上形容词、动词、名词(或词组)构成的感叹句、类似于北京话的感叹句等类型进行了总结与归纳”[20];高洁茹《内蒙古武川方言重叠式和附加式研究》(2016)“以武川方言中的重叠式和附加式为研究重点,讨论了武川方言在这两种语法形式上的特点,涉及到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21]等。
(三)蒙古语
蒙古语研究主要集中在蒙古语土语研究中,(1)以包头市为研究范围的代表性成果主要集中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土语研究中,同时,还有一些包头蒙古语使用情况研究的成果,如:包色音其其格《包头市蒙古族蒙古语使用现状研究》(2013)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包头蒙古族个人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与研究。(2)以鄂尔多斯市为研究范围的代表性成果:查娜《蒙古语鄂尔多斯土语第一音节短元音声学分析》(2000)“运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分析了蒙古语鄂尔多斯土语第一音节短元音的声学特征,并与察哈尔土语、巴林土语的第一音节短元音进行了比较分析”[22];苏米雅《关于鄂尔多斯土语中的汉语借词》(2009)“重点研究了蒙古语内蒙古方言鄂尔多斯土语中的汉语借词,同时也对鄂尔多斯土语固有词的保存使用情况进行了讨论与说明”[23];秀媛《语言接触引发的鄂尔多斯土语语言结构演变》(2009)主要运用语言接触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对语言接触所引发的鄂尔多斯土语语言结构变化进行了研究;雅茹《鄂尔多斯土语语言地理研究》(2011)对鄂尔多斯市6个旗39个方言点的语音及语法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格西格图《鄂尔多斯土语特词文化研究》(2016)运用文化语言学理论研究了鄂尔多斯土语中特殊词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与讨论等。(3)以巴彦淖尔市为研究范围的代表性成果:阿荣《巴彦淖尔市蒙古语土话方言地理研究》(2009)通过巴彦淖尔市蒙古语土语与蒙古语书面语的比较,解释巴彦淖尔市蒙古语土语语音、词汇、语法特点等。(4)以乌兰察布市为研究范围的代表性成果:乌仁图雅《乌兰察布市蒙古语的使用情况研究》(2017)分析了乌兰察布市蒙古语使用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鲁生《乌兰察布,包头市蒙古语土话方言地理研究》运用方言地理学的理论解释了乌兰察布市和包头市蒙古语土话的语音和语法的一些特点。(5)以呼和浩特市为研究范围的代表性成果主要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蒙古语使用情况研究居多。
二、阴山地区语言研究特点
(一)阴山地区语言研究的特点
就目前的成果而言,阴山地区语言研究的特点主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言本体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汉语方言研究主要立足于本体研究,大部分研究成果中在某一方言点的研究,由于阴山地区的大部分汉语方言属于晋语,但是又与山西等地的晋语有着一定的区别,因此,该区域的晋语研究不仅探讨内蒙古晋语与其他晋语的异同的,同时更加强调本地区晋语的独特性,《内蒙古汉语方言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蒙古语研究主要集中在内蒙古方言各土语本体研究,诸如鄂尔多斯土语、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土语等,与此同时有些学者从实验语音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角度对蒙古语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与研究。
第二,比较是阴山地区语言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比较不仅可以用于语音、词汇、语法系统等各个方面的共时研究,也可以用于诸如语音演化等方面的历时研究。阴山地区语言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方言与普通话的比较中,不仅研究与分析了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共性,而且较为准确地研究了它们之间的个性差异及其差异形成的原因一些研究成果将阴山地区晋语与山西等地晋语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对认识晋语的基本特征、分布以及使用晋语的地区区域文化的沟通和交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地方志中关于方言(或语言)的内容是阴山地区语言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所记载的内容包括该区域范围内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是体现区域文化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语言作为文化不可分割的载体,其内容的编写是地方志编纂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料,因为它能够使区域文化更加全面、更加系统。阴山地区目前出版的各级各类地方志中,大部分包括方言(或语言)部分,如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著《内蒙古自治区志·方言志》中的(汉语卷)、(蒙古语卷)对阴山地区的汉语方言、蒙古语方言的特点、分布等进行了深入的描写。包头市地方志编撰委员编纂的《包头市志》(卷五)第四十四篇方言部分,对包头汉语方言语音、词汇特点、语法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上述地方志中的有关方言(语言)内容都为日后考察和研究阴山地区语言情况保留了重要的语言材料及研究基础。
(二)阴山地区语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阴山地区语言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阴山地区语言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具体如下:
首先,语言接触研究中的历史层次研究相对薄弱。语言中的历史层次研究对区域语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阴山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一般只停留在词汇的相互借用、地名的考究上,但是有关探讨少数民族语言中汉语借词的历史层次、接触类型、接触等级等方面的研究数量不足;汉少(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研究程度不平衡,蒙汉语言接触研究相对较丰富一些,而回汉语言接触、满汉语言接触较少。
第二,缺乏综合的、科学的以区域语言为切入点系统的音系整理,换句话说,目前现代阴山地区语言没有共时层面的具体语音描写。而且由于各学者音系的研究角度描写方法不同,部分研究成果中即使涉及到具体某个方言的音系描写,但缺少一定的音系说明,如儿化、两字组连读变调规律等,也就是说,阴山地区语言研究某些方言音系描写的科学性、可靠性值得进一步商榷。同时,由于学者研究目的的不同(词汇研究、语法研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值得进一步推敲。
第三,词汇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但基本都以具体行政单位为研究范围,缺乏以地理、地域为范围的词汇横向之间异同的研究和论证,有些研究成果中语料来源的可靠程度比较低,即部分研究成果中的语料来源相似度较高,很难发现新的语言规律与特点。阴山地区各方言或者土语研究,缺乏系统的语法研究,汉语与蒙古语研究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缺乏以阴山地区为研究范围的语法研究论著。
第四,阴山地区回话(回族人说的汉语)研究实属起步阶段,回话做为内蒙自治区回族同胞所使用的主要语言,较之汉族人所使用的汉语,有其独特性,是阴山地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阴山地区语言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阴山地区回话的研究,鲜有成果问世,可以说很少见到明确的以“阴山地区回话”、“内蒙古西部地区回话”或阴山地区具体行政单位的回话为对象的研究成果。
三、阴山地区语言研究可以尝试突破的领域
首先,将语言地理学理论系统地引入到阴山地区语言研究中。语言地理学是在欧洲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兴起并建立的,它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利用同语线把方言(或语言)的特征绘出来,并将这些特征可以在方言地图上准确地呈现出来。它对于阴山地区语言研究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以阴山地区晋语词汇研究为切入点,绘制方言地图,做为阴山地区汉语方言传统研究的有效补充手段,可以进一步巩固和丰富地区语言的研究成果。2018年森格、高·那日格图主编《内蒙古蒙古语方言地图资料集》的出版,是阴山地区语言研究中系统运用语言地理学的重要标志。同时,以地理区域为研究视角,突破以行政区域为切入点的研究手段,通过对阴山地区主要核心区域各语言(汉语、回话)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有利于从整体掌握阴山地区语言的基本情况。
第二,阴山地区晋语、语言接触研究可以进一步尝试突破。众所周知,阴山地区的汉语方言主要是晋语,但分属不同的方言片,各个方言片的晋语研究缺乏横向的比较,因此,可以从各晋语方言片的区别与联系入手,来描写阴山地区晋语的整体特点及其成因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阴山地区汉少语言接触的类型与特点并解释其成因、历史层次,尝试对阴山地区的少汉语言接触之间进行比较,比较各地的汉少语言接触的差别,从而总结阴山地区语言接触的规律与特点,有利于更好地认识阴山地区语言整体的历时发展轨迹。
第三,多层次、多角度研究阴山地区回话及其演变规律是阴山地区语言研究的当务之急。回话作为汉语的民族变体,在不同地区又呈现出不同的地域变体,不同地区又会因为使用者的差异产生不同的社会变体。因此回话的研究对于以蒙古族为主要少数民族的阴山地区语言研究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回话与包头市北梁回话的比较、呼和浩特回话与汉话比较、北梁回话与东河话的比较研究等都可以作为阴山地区回话研究的突破点,从而进一步掌握阴山地区回话整体的演化过程以及回汉接触过程中的历史层次问题,同时有利于明确回话在阴山地区语言研究中特殊地位及作用,有效丰富和拓宽阴山地区语言研究的内容和范围。
四、阴山地区语言研究的意义
阴山地区语言资源极为丰富、复杂。无论是语言的类别,还是方言的种类,该地区的语言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因此,阴山地区语言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课题从整体上进行研究有其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
第一,阴山地区具体语言的研究,有助于语言习得、语言演变、语言发展、语言接触、语言融合、语言影响等语言学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通过对阴山地区具体语言情况的研究,进一步了解各种语言、方言的演变相互借用或吸收融合情况,为探讨阴山地区各种语言习得、语言发展轨迹等问题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从而可以深化对语言学特别是社会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对该地区回话进行比较研究,既可以了解阴山地区回话不同于其他地区回话的特殊性,又可以丰富阴山地区语言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及科学性。不仅如此,阴山地区语言研究对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语言接触是地区发展史与民族发展史的见证,是研究民族关系与地域文化发展的重要素材。不同语言之间如果有过语言接触现象,代表着历史上使用这两种语言的地域之间有过联系,有的是两者和平友好交往,有的是彼此征服,还有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与杂居往来等等。阴山地区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相互碰撞,产生大量的语言接触处现象。“随着蒙汉之间的杂居、通婚等,在语言上必然相互影响形成了西口地区的语言。特别是一些方言更能体现蒙汉融合的特点。”[24]因此,通过对阴山地区语言接触现象特别是历史层次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阴山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历史,而且还可以把握阴山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发展轨迹。
第三,目前,阴山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也比较集中。但目前还没有较全面较综合的阴山地区语言研究成果面世,因此,把阴山地区语言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课题从整体上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对阴山地区区域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研究阴山地区语言的研究,有助于梳理阴山地区各语言的发展脉络,同时可以预测该区域语言未来的发展趋势,展现阴山地区民族、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发展与相互融合,从而使阴山地区区域研究的基本内涵更加全面、更加完整。
综上所述,阴山地区的语言研究由来已久,并且成果显著,与几代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更注重其整体性的考究。阴山地区语言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因此,研究它,应紧密联系社会、历史、文化、地理等因素,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阴山地区语言整体发展轨迹及特征,促进阴山地区区域研究的全面发展。从某程度上也可以为其他区域语言研究提供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