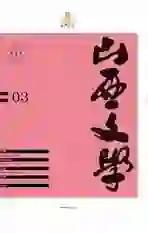试论刘亮程的语言观与人道主义思想
2019-10-08王春林
刘亮程在中国文坛的爆得大名,与他那部优秀的散文作品《一个人的村庄》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部作品的存在,刘亮程才一度赢得了所谓“乡村哲学家”的美誉。然而,就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刘亮程实际上却已经酝酿着由散文到小说的一种文体转型。或许,在刘亮程的心目中,他最理想的文学文体恐怕也还是小说创作。但刘亮程却又是那样一种下笔谨慎的写作者,即使他的写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小说这种文体上,他所写出的作品数量也极为有限。迄今为止,连同我们这里将要重点讨论的这部《捎话》(载《花城》杂志2018年第4期)在内,他所写出的也不过只有三部长篇小说。除了这部《捎话》外,还有《虚土》与《凿空》两部。事实上,早在多年前刚刚读完《凿空》的时候,我就曾经不无激动地表达过对于那部长篇小说的激赏之情。我认为,与其他那些同样以边地生活为表现对象的小说作品相比较,刘亮程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别一种”深度思索,“那么,与那些同样以边地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同类长篇小说相比较,刘亮程《凿空》的‘别一种意味究竟何在呢?就我个人一种直接的阅读感觉而言,虽然以上的诸多作品都具有现实主义的基本品格,都在努力地追求着对于边地生活的真实还原与表达,但是,相比较而言,如果说其他的那些小说更主要的是着眼于文化的层面上,多多少少都带有着某种文化猎奇或者说文化展览的意味的话,那么,刘亮程《凿空》的值得肯定之处,就在于,小说一方面固然也带有强烈的文化意味,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明显地突破了文化层面,更多地把自己的笔触探入到了边地的现实社会政治层面。对于当下时代的边地,具体到刘亮程这里也就是新疆的社会政治状况,进行了一种堪称是刻骨真实的思想艺术表现。或许正因为其他同类作品更多地着眼于文化层面的关注展示的缘故,在阅读的过程中,便总是感觉到有一种不无浪漫色彩的诗性弥漫于其间。然而,尽管说刘亮程早期那部曾经使他一下子爆得大名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确实也是以充溢其中的浪漫诗性而著称于世的,但是,到了他的这一部《凿空》中,那样一种多少带有一点刘亮程标志性色彩的浪漫诗性却已经了然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我以为,实际上正是长期生活于新疆地区的刘亮程对于新疆现实生活一种简直可以称得上冷峻而又内在深刻的观察与书写。”[1]对于自己多年前给《凿空》做出的如此一种判断,我至今都依然坚持。实际上,或许与自我的生存经验紧密相关,迄今为止刘亮程三部长篇小说的书写题材范围,的确没有逾出过“边地生活”的框限。只不过,如果说《虚土》与《凿空》关注表现着的是当下时代的边地生活的话,那么,到了这部新近完成的《捎话》中,刘亮程就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投射到了千年之前那个遥远的历史时代。出现在刘亮程笔端的,乃是那个遥远时代的古老宗教信仰,以及围绕这宗教信仰所发生的文化与人性冲突。
阅读刘亮程的这部《捎话》,首先給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刘亮程对小说语言的出色把握和运用。“从门缝看塔是扁的。塔后高耸的院墙是扁的。围坐塔下的昆门徒是扁的。香炉和烟是扁的。嗡嗡的诵经声响起来,声是扁的,像浮尘像雾,裹着昆塔一层层攀升,升到金灿灿的塔尖时,整个昆塔被诵经声包裹。那声音经过昆塔有了形,在塔尖上又塑起一层塔。一座声音的塔高高渺渺地立在裹金的昆塔之上。诵经声又上升,往声音的塔尖上再层层塑塔。越高处的塔就越扁,越飘渺。”小说开头处的这一段叙述话语,出色处在于对声音的比喻与拟人化表达。声音本来是只能够诉诸于人类听觉的无形事物,刘亮程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借助于特定叙述视角的设定而巧妙地赋予了声音以具体可视的形状和动作。那些昆门徒发出的诵经声,其形状不仅是“扁的”,“像浮尘像雾”一般可以被看见,而且还如同长上腿一般竟然可以在昆塔上一层又一层地向上“攀升”。更有甚者,这些本来抽象无形的诵经声,不仅可以像实在的昆塔一样在塔尖上又塑起一座“声音之塔”,而且这“声音之塔”的状态是越高便越“扁”越“飘渺”。与此同时,这一段叙述话语还给读者勾勒出了一幅由近及远、由低及高具有纵深感的形象画面。从昆塔,到塔后的院墙,再到香炉和烟,这是由近及远。从围塔而坐的昆门徒,到昆塔本身,再到塔尖上的那座“声音之塔”,一直到更高处那“越扁”“越飘渺”的同样依托于声音塑形的“塔”,这是由低及高。这其中,无论是动词,还是形容词,刘亮程的选择都不仅是精准的,而且也形成了某种“陌生化”的艺术效应。究其根本,这段叙述话语之所以能够成立,与那只被后来的主人命名为“谢”的小母驴的叙述视角的设定,存在着格外紧密的内在关联。一方面,只有驴这一物种才可以看见“声音的形”。另一方面,“谢”上述事物的观察,乃是在门后隔着一道裂开的门缝进行的。唯其因为如此,出现在这段话语中的一切事物才会是“扁的”。
然而,与对于小说语言出色的把握运用相比较,更重要的其实是渗透于叙事过程中刘亮程对语言功能的深度思考与认识。假如我们试图要从《捎话》中概括提炼若干理解小说的关键词,那么,语言肯定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捎话”,主要由于小说的主人公之一,精通多种语言的“库”的职业身份,就是一位依靠语言吃饭的翻译家。唯其因为他拥有这种可以识别多种语言的能力,所以在那个信息沟通特别困难的时代,他才成为了一位不可或缺的捎话人。事实上,也正是在成天和语言打交道的过程中,库对语言那样一种既可以使存在澄明却又可以遮蔽存在本相的矛盾功能方才生出了真切的体会。一方面,捎话人这一职业身份的存在,本就说明着语言所具有的交流与澄明功能。但在另一方面,其不自觉的歪曲以及遮蔽功能的存在却也是一种客观的事实。作为毗沙国中最重要的一座寺院,西昆寺里聚集了操持着多达几十种语言的译经师。在那里,“一部昆经被毗沙语、昆语、黑勒语、皇语、丘语等同时吟诵,每一种语言里有一个不一样的昆。”“昆经从这里被译成无数种语言。一部昆经由此变成无数部。”无论是“每一种语言里有一个不一样的昆”,还是“一部昆经由此而变成无数部昆经”,说明着的,正是语言歪曲与遮蔽功能的存在。实际上,也正因为真切地体会到了语言双刃剑一般的双重功能,所以库的师傅才会特别强调语言歪曲与遮蔽功能的存在:“‘你每学会一种语言,就多了一个黑夜。库的师傅深知语言带给人的黑暗。他老人家通晓世间所有的语言,在他看来,那些看似被不同语言照亮的地方,其实更黑暗。就像毗沙语说不出黑勒语的早晨。昆经想照亮世间的黑,可是,经文翻译成黑勒语、毗沙语、皇语和丘语时,都无一例外地被扔进这些语言的黑暗中。”在这里,库的师傅所特别强调的,其实是不同语言之间不可通约性:“所有语言里天亮这个词对于其他语言都是黑的。”这一点,与基督教《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寓意可以一脉相通。依照《圣经》中的说法,人类本来使用着同一种语言,但他们利用同一种语言建造巴别塔的行为却惊动了上帝。当上帝意识到巴别塔的建构,也即人类语言的统一,将会使得人类难以被统治的时候,他便设法变乱或者说分化了他们的语言,使得这座巴别塔最终由于人类语言的隔膜而无法建成。很大程度上,《圣经》借助于这个寓言故事,所揭示的,也正是刘亮程在《捎话》中所思考着的语言的双重功能问题。
请注意,关于语言的歪曲与遮蔽功能,刘亮程曾经借助于专事语言工作的翻译家库进行过尖锐而形象的揭示:“在这个说着十几种语言的混杂大军中,只有库能够把各种语言表达的意思准确地传递给可汗,再把汗王的指令和意图传递给各种语言的人。一个从黑勒语发出的指令,必须由黑勒语分别翻译给各语言,而不能先译成泰语,再由泰语译成丘语,这样一个指令就变成无数个,这无数个指令再翻译回来,就连汗王都不知道说的是啥了,其意思偏差之大就好像早晨赶出去一群羊,下午吆回来变成一群狗一样。”明明是同一个指令,在经过了数种语言的辗转翻译之后,竟然会酿成从“羊”到“狗”的巨大变化,语言一种歪曲或者遮蔽功能的存在,细细想来,端的是令人喟叹不已。
尽管语言在澄明某种事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备着遮蔽的功能,但迄今为止,除了语言之外,人类也还无法寻找到更为上佳的可以使事物与存在得以澄明的手段与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西哲海德格尔那句“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的说法,就是毫无疑义的。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语言甚至会关系到某个人的身家性命。这一点,身为翻译家的库,感受可以说最为突出:“在栏杆村,所有东西有毗沙语名字,被毗沙语称呼。明天翻过那个干河沟,被毗沙语称呼的所有东西都有了另外的名字和称呼,库也将在爬上那个深沟后,忘掉毗沙语,改说黑勒语或天语,那是最安全的语言。”就这样,由于国家政治严重制约影响的缘故,对于一种语言的使用与否,竟然关系到了生命的存在。在这个层面上,语言就不仅仅只是语言,而成为了与社会政治、与人类存在紧密相关的一种事物。很多时候,对某种语言的征服,也就意味着对一个国家,或者干脆说就是对一种生命存在的彻底征服:“黑勒人把听不懂的话都叫黑话,因为没人听懂他说话,所以没人要,卖不出去,才搭驴背上便宜卖。但师傅听懂了,这孩子说着一种已经死亡的遥远地方的语言,师傅好多年前在西昆寺接触过这个语言地区的昆门徒,后来便听说操这种语言的人已经被别的语言征服。但在师傅的脑子里他还活着,师傅便宜捡了一个能够跟他说一种死语言的孩子,高兴坏了。”事实上,也正因为一个地方的灭亡便意味着这个地方所流行的一种语言的彻底消亡,所以,到小说后半段,深谙此中道理的黑勒国可汗,面对着业已争斗长达百年之久的敌国毗沙,才会不无凶狠地强调,这次对毗沙国的战争必须以对毗沙语的彻底征服为根本目标:“汗王说,有黑勒语的天经就够了,我们征服毗沙后,跟我们对抗百年的毗沙语将不复存在,说毗沙语的舌头将全部腐烂成土。”“我要让说毗沙语的舌头全部腐烂成土。以后从所有毗沙人嘴里说出来的,都将是黑勒语。”可汗如此一种关于毗沙语的决断,对库的精神世界形成了极强烈的刺激:“库的舌根猛地一抽,仿佛说毗沙语的舌头一下被割掉,他下意识张着嘴,里面空空的没有话说出来,心里也空空的,在他有生之年,已经经历许多语言的死亡,包括他家乡的语言。”“库听到这句话时,舌根一阵生疼,仿佛他说毗沙语的舌头,又一次被割掉。”紧接着,“库大张着嘴,不知道要说什么,怎么说,仿佛他说所有语言的舌头都被割掉,只留下说黑勒语的舌头,他在嘴里找说黑勒语的舌头,怎么也找不着,他一着急,脖子一下伸直,嗓子里有一股倔强要喷发出来。”既然是以操持语言为业的翻译家,那库对于自己所熟练掌握的各种语言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本能维护。正是从这样一种真切的感受出发,库才会对可汗灭亡毗沙语的决断感到某种锥心刺骨的痛苦。实际上,在很多时候,仅仅是某个政权的被颠覆,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消亡。真正标志着某一国家彻底消亡的,往往是一种语言,或者说是以这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的覆灭。几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虽然一度四分五裂为无数个大小不等的邦国,但国家却最终没有消亡,一个根本的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以汉字或者说汉语为载体的文化一直是这些大小不一邦国的语言与文化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通常所谓历史悠久的中国,其实并不只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的中国,而更是孔孟老庄的中国,是李白杜甫的中國,是苏东坡曹雪芹的中国。无论如何,我们都很难想象,假若舍却了孔孟老庄,舍却了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我们通常所谓的中国是否还会获得相应的存在感。质言之,通常所谓的“亡国灭种”,只有在语言与文化的层面上,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解释。很大程度上,作家刘亮程正是因为洞悉了语言以及由语言而进一步衍生出的文化与生命存在之间紧密关系,所以他才会在《捎话》中以如此一种突出的方式强调凸显语言的重要性。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刘亮程是一位“乡村哲学家”,莫如说他是一位“语言的存在论”奥妙的观察与洞悉者。
关键的问题是,语言虽然对小说创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一部真正优秀的小说作品却绝不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上。在这部寄托着刘亮程深厚思想题旨的长篇小说中,借助于汉语言出神入化的使用,刘亮程更是将自己的关注视野鲜明不过地指向了千年之前围绕宗教信仰发生的堪称尖锐激烈的文化与人性冲突。实际上,尽管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捎话》的故事情节却实在称不上有多么复杂。作为小说最核心的一个情节,所谓“捎话”,就是指身为翻译家的主人公库,接受毗沙国西昆寺王大昆门的委托,要往另外一个名叫黑勒的邻国中桃花寺里的买生昆门捎一头小母驴。库以自己向来的原则是“只捎话,不捎驴”为由拒绝。王大昆门紧接着给出的理由是:“你就把驴当一句话,不用搁脑子里,她有腿,你骑也好牵也好,捎给买生大昆门就好。”库接受了王大昆门的委托后,不惜千辛万苦,最终如愿以偿地把这头小母驴如同“一句话”一样捎到了黑勒国,交给了买生大昆门。这里,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西昆寺的王大昆门究竟为什么非得如此这般煞费苦心地将一头小母驴千里迢迢地送到黑勒国去?却原来,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奇特的“捎话之旅”,与毗沙和黑勒这两个国家之间长达百年之久的战争紧密相关。毗沙和黑勒这两个西域国家,曾经是同样信仰着昆经的友好国家。然而,尽管黑勒国人有着长达千年的昆经信仰,但是,等到西昆寺为了阻挡日甚一日的驴叫而开始垒高墙,而且把墙竟然垒到驴再不敢发出叫声的地步的时候,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却莫名其妙地从此开始了。之所以断言这两个国家的战争莫名其妙,乃是因为战争的起因竟然与高墙有关:“墙垒好的当年秋天,毗沙国收到黑勒王朝的国书,内容是毗沙西昆寺的高墙挡住了黑勒城的太阳。”“这是毗沙国对黑勒王朝的严重挑衅,毗沙国必须在十日内把西昆寺高墙拆了。”从表面上来看,仅仅因为西昆寺的高墙挡住了黑勒城的太阳便引发了两个国家之间的百年战争,的确显得有些荒诞不经。只有在认真读过作品之后,我们方才可以搞明白,实际上,毗沙和黑勒两个国家之间所发生的,乃是一种与宗教信仰紧密相关的宗教战争。这一方面,一个显在的事实是,就在黑勒国放弃对昆经的宗教信仰之后不久,他们很快就开始信仰一种新的天经。一旦开始信仰天经,那些曾经的昆门徒也就自然而然地摇身一变成为了天门徒。就这样,一个国家信仰昆经,另一个国家信仰天经,两个国家之间发生的这一场前后绵延长达百年之久的战争,其实质也就只能是宗教战争了。
事实上,只要是战争,不管它是不是与宗教信仰有关,其根本的暴力性质都是无法改变的。战争的暴力,导致的一种直接结果,便是无数参战者的人头落地,是敌对双方平民百姓的生灵涂炭。这一点,在刘亮程的《捎话》中同样有着突出的体现。“一阵铁碰铁的尖利响声夹杂人的喊杀与惨叫。”“只一会儿工夫,战场平静了。库四处望,第一拨冲杀的士兵几乎全倒在地上。”如果说这样一种全景式的描写不仅概括,而且抽象的话,那么,另外一种关于具体个体死亡场景的描写所显示出的,便是如同电影慢镜头一般地“精雕细刻”了:“他从背后一刀砍下去,那人惨叫一声,扭头愣愣地看他,看落在地上的右臂,好像不相信是自己的,握着刀柄的一个指头还在动,指头不知道身体发生了什么,动一下,又动一下。他也愣住了,一只眼看地上的手臂,一只看那人扭过来的脸。那人也一只眼看自己落地的手臂,一只盯着他。他不知道自己也快死了,人死前才会两只眼睛分开各看各的。他被对面的那张脸完全罩住。那张命结束前的脸,恐惧、痛苦、惊愕,却很快安静下来,全身的动作停下来,座下的黑马停下来,周围一切跟他没关系了,脸上缓缓退却的惊恐也跟他没关系了,他感觉时间也停了,整个战场还在动,马在奔跑,人在冲杀,只有他和那个人停住。”请注意,这段叙述话语中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被看作是一幅静止的慢动作画面。将这些慢动作画面拼贴在一起,便是疆场上一名战士完整的死亡过程。这其中,尤其是类似于“指头不知道身体发生了什么,动一下,又动一下”的相关描写,更是不无荒诞地揭示出了死亡的残酷性质。但相比较来说,更具荒诞色彩的,恐怕却是人们在战争的过程中竟然会遗忘漫长战争的起因:“打了这么多年仗,许多人都忘了为啥打这场没完没了的仗。”“战争就这样打起来。第一仗是毗沙人攻打黑勒。因为黑勒人老喊叫着打毗沙,老不来打,毗沙人着急了,便主动攻打到黑勒城下,竟然破了黑勒城。”“打了第一仗,第二仗便免不了。因为死了许多人,国家要报国仇,家庭要报家仇。反正以后的战争跟高墙没关系了,谁也说不清为什么打仗。”既然说不清为什么要打仗,那这仗打来打去,其实早已成为一种似乎只是在为了打仗而打仗的惯性延续。尽管早已搞不明白为什么打仗,但对立双方的那些参战者却依然不管不顾地投入到战争之中。这其中,参战者那样一种群氓或者勒龐意义上乌合之众性质的存在,就是昭然若揭的一种事实。更进一步说,当我们把刘亮程笔端或抽象或具体的死亡场景与战争动机的被遗忘细节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作家一种诅咒否定暴力战争的现代反战思想就已经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与此同时,我们也须得注意到,当可汗率领十万大军攻克毗沙国的过程中,翻译家库曾经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拯救过不少毗沙人的生命:“旁边树上的人偏头看。库把刚才说的大声重复了一遍。库的话显然起了作用。多数人被他劝得归顺了,但还有硬头死不改宗,嘴里念着昆经,头伸过来让砍。”“本天门请示汗王带自己的军队去洗劫。汗王令屠杀全村,一条狗都不放过。库译给本天门的话是,屠杀全村有罪者,包括狗,天仁慈,原谅归顺者。”“结果半村人活下来”。面对着战争中生灵涂炭的残酷现实,翻译家库竭尽所能地利用自己既通晓毗沙语,也通晓黑勒语的语言优势,力求保全更多毗沙人生命的如此一种行为,更应该被看作是作家刘亮程精神世界中,建立在现代反战思想基础上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充分体现。
注释:
[1]王春林《边地现实的别一种思索与书写》,载《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1期。
王春林,1966年出生,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先后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当代文坛》《扬子江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万字。出版有多部批评专著与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