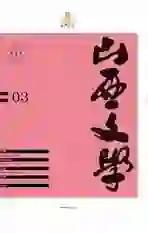拿希望劈成小柴生火
2019-10-08韩石山
从“末代诗人”到优秀诗人
原先定的讲题是《志摩与新诗》,没有变,还是谈志摩与新诗,现在这个题目,是为了发表文章(讲稿)用的。志摩与新诗,一听就知道会讲什么。这个题目太俏皮了,要解释一下,不解释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928年前后,徐志摩的名声已经很大了。住在上海,到了年根底下,会有报纸请他写新年贺词之类的文字,他人缘好,随和,叫写就写吧。这样到了1928年元旦这天,就有两家报纸登了他的新年贺词,一家是《申报》,一家是《新闻报》的元旦增刊。《申报》登的叫《年终便话》,《新闻报》登的叫《新年漫想》。本来该是欢喜的文章,鼓劲的文章,但这一年似乎流年不利,情绪不高,也就说不出什么慷慨激昂的活,可毕竟是徐志摩,对人性有深刻的体验,对生活从不会失望,情绪不好,反而让他说出一些更值得玩味的话。在《新年漫想》里,说“生活已皱缩到枯窘的边缘,想象脱尽了翱翔的健翮”。拿希望劈成小柴生火,是在《申报》的《年终便话》里说的,用在这里,是个短语,说全了是:“可是尽说这冷落丧气话也不公平,冷急了自然只能拿希望劈成小柴生火。”我非常喜欢徐志摩这种语言表达,俏皮,隽永,越咂摸越有味儿。希望,总是美好的,热的,而在这个让人沮丧的环境里,没办法了,只能将希望劈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小柴,聚拢起来点一堆小火,热热身子烤烤手,让我们的心不至于凉透了。
下面就要说到这个讲座的主题了。顺着这个话头说,就是看看我们的诗人,经历了什么事,思想上有了什么变化,怎样一个精神状态,这小小的柴堆,又能点起怎样的火焰。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空疏,所有的讲述,都能落到实处。还有一点要说的是,这个讲座,是首图和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合办的,是个新书推荐活动。着力推荐的是《远山》这本书。这样我的一切讲述,都将围绕着这本书展开。
书名《远山》,徐志摩的一本佚作集,商务印书馆出的,2018年3月印行。设计之典雅,印制之精美,近年我所见到的书里,都是数得着的。这是说包装,至于内容,也就是说所收的文章,是近二三十年来,徐志摩研究的一个大成果。有了这本佚作集,徐的著作更全了,这只是眼见的事实,重要的是,徐志摩的形象更丰满了,更端正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从改革开放,徐志摩的作品解禁以来,人们对徐志摩的看法,不外三个面目,或者说三个脸嘴。由高往低里说,一是优秀的诗人,诗好,人样好,风流倜傥,让人爱慕。二是诗还能说得过去,但人品太差,风流成性,爱了这个爱那个,不是一个好的文化人。三是思想反动,仇视革命,跟胡适混在一起,鲁迅狠狠地骂过。怎么个说,在不同的年代里,有不同的含义。这一点,我也是最近才悟出来的。
人老了,没事的时候,会回忆年轻时候的事。我这人,出身不好,大概人品也不怎么样,从上大学开始,只要有个运动,都会敲打敲打,“学习班”就住过三次。每次都是大会小会批评批判,踉踉跄跄,跌跌撞撞过了关。在这个过程中,对人的面目,就看得多些,也看得透些。过去对批评过我的人,是一概的反感,觉得都是些心地歹毒的家伙。现在不这么一概而论了。我发觉,当年那些批评我的人,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批评我骄傲自满的人,多半是想保护我。说我有剥削阶级思想,不过是送个反面的“顺水人情”,并无多大仇恨。只有那些说我思想反动,将污水往你身上泼的人,才是真正要置你于死地。从这点切身体会出发,我觉得,解放前,解放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说徐志摩堕落的人,极有可能是袒护他的。比如茅盾先生,三十年代初,写过一篇《徐志摩论》,说徐是“一步一步走入怀疑颓唐”的“末代诗人”。
茅盾的《徐志摩论》是1932年12月写的,距徐志摩罹难不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文章中,除了说徐是“末代诗人”外,还说徐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这一评价,几乎成了以后评价徐志摩的定谳。过去我总认为,茅盾是革命批评家,眼光又准又狠。现在我不这么看了,觉得茅盾这么说,极有可能是对徐志摩的一种保护,不是明里保护,是暗里的保护。为什么这么说呢,茅盾一直是革命队伍里的人,很早就是共产党员。1930年春天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要做什么事,他心里一清二楚,说白了,就是要跟胡适、徐志摩这一班人对着干。左联的首领是鲁迅,鲁迅跟徐志摩有过节,他是知道的。干胡适,他不能说什么,干徐志摩,还是有点不忍心,至少不愿意下狠手。可能有人对徐的定性毒了些,他便写了这么篇文章,说徐不过是中国布尔乔亚的开山祖师,顶多算个末代诗人,算不得反动分子,也就算不得革命的对象。说白了就是,革命还有大事,且放了这个颓废文人。
怎么想到的呢,也是最近的事。前不久,金庸死了,有人翻出我过去的一篇文章,放在微信上,我看到了。其中说到,金庸家跟茅盾家,是拐弯亲戚,金庸的父亲跟茅盾是表兄弟,又是大学同学,金庸小时候,还去茅盾家“走亲戚”。金庸家跟徐志摩家也是亲戚,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这样一来,茅盾家和徐志摩家不就是拐弯亲戚吗?还有一点,或许更重要,两人同岁,且有同学之谊。茅盾1896年生,属猴的,徐志摩是1897年1月生,也是属猴的。差下一年,是农历换算成阳历了。茅盾是1913年秋天考上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第一类相当于文科,学的是文史和法律。徐是1914年秋天考上的,也是第一类。第二年冬天,结婚后转到上海沪江大学念书。预科两年,也就是说两人同学了半年的时间。有这么两层关系,茅盾怎么会下狠手,将徐志摩推到敌人的位置上去呢?
当然,解放以后,徐志摩的脸面,是越抹越黑了。和胡适一样,由不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步一步升级为反动文人。胡适有个小脚夫人,引人同情,不会怎么堕落。志摩可就不同了,离过婚,爱女人,也为女人所爱,那就不光是反动文人,还是堕落文人了。现在又变了,不管喜欢他的,厌恶他的,都得说这是个优秀的诗人,著名的诗人。若以诗句流传之广而论,怕还得说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最大的一个诗人。
《远山》的亮点
说《远山》的亮点,是一种文学化的说法,应该说《远山》在徐志摩研究上的价值。书挺厚的,篇目不少,不能光看增加了多少篇作品,還要看这些作品的内容。两句话可以概括,一句是丰富了志摩的形象,一句是端正了我们的认识。如果以前在我们的印象里,他是瘦削而微瑕的,看了这本书,会觉得丰满而端正。爱他的人会越发的喜爱,当然,恨他的人会越发的恨他。
增加的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平事迹方面的,一类是思想境界方面的。两者我都喜欢,都欣赏,相比较而言,更喜欢思想境界方面的发现。这些内容,让我对徐志摩的认识,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先说生平事迹方面的。说增加,太虚泛,徐是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人,经过的事都是实际发生过的。只能说,有的我们知道,有的我们不知道,有的你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不知道。得要有个参照才行。我的参照,就是我写的《徐志摩传》。
我的徐传,有个重大失误。初版里,竟没有写徐志摩在沪江大学这段经历。写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能搜集到的资料不是很多。当时中国的出版界,正在陆续推出一套书,叫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其中《徐志摩研究资料目录》这本,是邵华强先生编的。可以说,当时发表的纪念文章,研究文章的目录,全收了,竟没有一篇说到志摩曾在沪江大学上过学。只有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里,有句话,说1915年秋肄业于沪江大学。我当时不知道,那个时候说肄业,就是上学的意思,心想,刚刚还在北大上预科,怎么冬天就从上海的沪江大学毕业了呢。因此初版上我就没写上过沪江大学这件事。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里,有沪江大学时的各科成绩单,又不能不理会。几乎在写传的同时,写了篇《徐志摩学历的疑点》,发表后又收在我的一个集子里。说到这个成绩单时,说了句,或许是为了送儿子出国留学,他父亲徐申如先生,走门子弄下的吧。这本书,台湾学者秦贤次先生看到了,在一篇发在《新文学史料》上的文章里,嘲讽我说,大陆学者韩石山不顾事实,以己度人,胡说什么徐父走门子开学科成绩单。我初看,还想反驳,后来一想,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跟个人声誉没有关系,错了承认错了就是,不存在丢人不丢人的问题。正好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印我的《徐志摩传》,前面要有个新序,说到修订事项时,就把这件事写上了,说感谢秦先生在台湾,就近查阅教育部迁台资料,敲定徐志摩上过沪江大学这件事。
沪江大学这地方,后来成了上海理工大学的校园,资料也归理工大学图书馆保管。这儿的学者在整理校史资料时,发现沪江大学校刊《天籁》上,发表过许多徐志摩的文章,整理之后,竟有十一篇之多。
生平事迹方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收入了志摩致英国学者奥格登的六封信。内容不是很多,联系的人事很丰富。这也是我过去有疑惑,而没有深入思考的地方。除了《徐志摩传》,我还写过一本《徐志摩图传》。说是图传,也有十几万字。书中特辟一章,名为《做一个汉密尔顿》,想从留学经历上探讨一下,什么人给了他精神力量,以之为榜样,才有回国后的一番作为。1931年8月,徐出了在世时的最后一本诗集,叫《猛虎集》,闻一多画的封面,一张虎皮,从书脊那儿折过来。志摩写了序,在他的集子里,大概是最长的,有点梳理一生的意思。谈到早年的志向,说他查过他家的家谱,从永乐以来他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二十四岁以前,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相对论和民约论的兴味,他父亲送他出洋留学。是要他将来进“金融界”的。可他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这个汉密尔顿,在美国历史上,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1755—1804年在世,早年就学于哥伦比亚大学,曾任炮兵上尉,参加过对英军的战斗。1789年华盛顿建立新的联邦政府,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说徐志摩回国后的作为,以汉密尔顿为榜样,显得太遥远了。现在好了,有了致奥格登的六封信,又知道奥格登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以谁为师的问题就解决了。没说的,办报纸办刊物,组织文学社团,学的就是奥格登。
亮点的第三个,是1928年回国后的几次演讲。他是11月回来的,梁启超病了,他来北平看望。轉年1月有两次演讲,一次是在清华,一次是在燕京大学。在清华的这次,有学生整理出来,叫《徐志摩漫谈》,在燕京大学的,也是学生整理出来,叫《现代中国文艺界》。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在上海的大夏大学也都讲过。不说内容了,光一次又一次的讲,就说明他已经从烦恼中解脱出来,要做事了,不多久就应胡适之邀,来北大教书。
亮点的第四个,是长篇论文《社会主义沿革以其影响》。我写传时知道有这么一篇文章,在北图,现在叫国图查资料时,想找没找见,或许就没有。现在陈建军找见了,编入书中。徐志摩研究相对论,我是知道的,他曾给林徽因说,任公,就是梁启超,知道相对论还是我徐志摩告诉的呢。有了这篇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文章,就知道徐志摩对前苏联反感,不是情绪上的,是有社会学的理论素养支撑的。
事实方面的亮点讲过了,该着说思想境界方面的亮点了。这个说法不怎么周全,一个人的思想境界,是体现在许多方面的。要总括,该依据各方面的材料,仅从《远山》里的文章归纳,是远远不够的。既然是讲《远山》,我们只能说由《远山》中的文章,引发了我们对徐的思想境界的重新认识。这个弯拐过来,下面的话就好说了。
过去我们谈徐志摩,很少谈人品,也不谈什么思想境界。似乎说诗好,已是高抬了,思想境界嘛,他也配!今天是专门谈他,还是应当宽容些。人品就不说了,要说也只说一句,你就是说他好,怕也没有达到他的那个好。还是说说思想境界吧。
这上头,志摩最可贵的,一是清醒的社会认识。前面说他与胡适,在对前苏联教育上的不同看法,就是一个显豁的证据。二是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组织社团,办刊物,不要看作是爱热闹,爱文学,不,他的心志比这要大得多。在这上头,他的顽强,也是可敬佩的。这不是说,没有烦恼,没有颓唐,就像长途跋涉的人,累了得歇息一样,歇好了,不累了,接着往前走。拿希望劈成小柴生火,看似希望的幻灭,实则是对希望的依赖,只有依偎在希望的小柴燃烧的火堆旁,就还有希望,就不会冻馁而亡。
第三个是他的反省精神。对一个优秀人物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的前行路线,不会是直直的一条线,直通目的地不打弯。左右的摇摆,前后的趔趄,甚至绕着圈儿的徘徊,都是会有的,靠什么走上正途呢,靠的是思辨的能力,反省的精神。志摩在家庭生活上,遭逢感情的幻灭,仍能振作起来,呵护爱妻,维系家庭,得力于他的反省。当初那么爱小曼,到了这个时候,就该拉上一起往前走。
志摩与新文化运动
过去说起徐志摩,不管他做过什么,印象中只是个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不会往高里抬。我觉得,该抬的时候,还是要抬的。事实上,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明确的倡导者,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
新文化运动这个词儿,要掂量掂量。我们总爱拿新旧说事,于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真像一首古诗说的,“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杜甫《佳人》)。透过新人的笑脸,看到的是一个个弃妇,悲苦的面容,凄惨的哽咽。该叫什么呢,该叫“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说,我们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文学艺术都有其精髓,衰落了,暗淡了,到了这个时候,要振作起来,复兴起来。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也是这样自命的。海外的研究者,也是这样定义的。
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里,说过这么个小故事,胡适的儿子思杜吧,在美国上学,语文考试不及格,唐德刚将这件事跟胡先生说起,胡笑着说:“哈,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儿子,语文考试竟然不及格!”我看过两本美国学者(多为华人)写的新文化运动史,用的英文词都是文艺复兴。也就是说,在国外的汉学界,中国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文化运动是一回事。既然已得到国际文化界的公认,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也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呢?接下来要探究的是,这个文艺复兴运动,是怎样发起的,由谁倡议,又由哪些人推波助澜,最后成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
一般的说法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发动且领导了这一运动。三人各有所司,蔡元培办学校,是作务人才,陈独秀办刊物,是鼓动舆论,也是提供阵地,胡适发表《白话文刍议》则是一声号令,天下影从。这个说法,太科学了,也太形象了,几十年添油加醋,越来越真实生动。再过上一两百年,就可以归到顾颉刚先生的“层累的古代史”系列里了。说不定会传成,蔡元培将他的新科进士的儒冠一摔,一手拉着陈独秀,一手拉着胡适之,到了一个酒馆,推杯换盏,喝得兴起,朗声言道:“仲甫(陈的字)你去办刊物,适之你去写篇文章,咱们来他一场新文化运动!”拆字先生甚至可从三人的名字上,看出他们各自的志向与作为。
实际上,我敢说,没有一个人在起事之初,会想出新文化运动这个词儿。但是,文艺复兴这个词儿,这个念头,有一个人却想到了,做到了,且有一番精心的布局。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戊戌变法的第二号人物,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先生。此中原委,起承转合,二十年前写《徐志摩传》时,我已写上了。原以为出版后,定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砍来,我挺枪迎战,写上几篇文章,就把这个历史的误会纠正过来了。没想到言重而人轻,喊破嗓子也无人理睬。今天在这里,只简略地谈谈,有兴趣的朋友,可找来《徐志摩传》看看。这段叙述,在第五章《回国之初》里,说在徐志摩回国前,梁启超率团,赴欧洲考察回来,有个大的振兴中国文化的计划,他们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迫切需要人才,正好徐志摩回来了,梁启超在松坡图书馆坐镇,便聘为英文秘书,倚为得力助手。好些文章里,谈到民国文人的逸事,常爱说一个典故,说梁启超写起文章来,大江长河,汪洋恣肆,一发而不可收。给某人写序,写出的序比人家那本书的字数还多,只好再写一短序,将那个长序当一本书印出来。给谁写的呢,给蒋百里写的,什么书呢,《欧洲文艺复兴史》。
蒋怎么想起写这么一本书呢,梁启超让他写的。原来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是战胜国,一时国威上扬,段祺瑞当政,研究系一班人吃香,梁启超当了财政部长,大概也没什么要紧事,便组织了个欧洲考察团去欧洲作了一次漫游,带的人员,可谓兵强马壮,都有学问专长。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蒋百里实为梁的助手,考察团的领队。欧洲之行,梁启超最感兴趣的,是文艺复兴,也想在中国造成一个文艺复兴,把中国的颓势,扳了回来,就让蒋百里写了这么一本书。不光是说一说,他们还有具体的布置。在北京建立了三個机构,一是读书俱乐部,后与松坡图书馆合并。二是设立共学社,收集经济、政治、军事、文艺多种书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丛书,三是与蔡元培、汪大燮三人,另一人是梁启超,共同发起讲学社,每年请一位著名学者来华演讲。这三个机构,均由蒋百里主持。徐志摩这个英文秘书,就是协助百里工作的。这样你就知道,徐志摩请泰戈尔来华,不过是讲学社的业务安排。成立新月社,也不过是业余的助兴。梁启超、蒋百里发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后来因为梁启超的猝死,蒋的他走,未成大气候。但这个职志,徐志摩自觉地承担起来。办 《新月》,是开辟阵地,在大学任教,是作务人才。前面说了的办第一届画展,也可说是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汉密尔顿的雄心,落到实处,便是奥格登的作为。
还有个说法,很是可笑。说志摩跟胡适关系好,胡适知道在文学创作上,提倡有功,实行无力,见徐志摩的诗写得好,为了壮大新文学的声势,就把徐志摩拉进这个阵营里。过去我也这么看,觉得是胡适这个帅才,成全了徐志摩这个将才。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我认为,在倡导与践行上,徐志摩一直就是自觉的,不是跟上谁才走上这条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志摩乃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历史总是将那些既有倡导之功,又有践行之绩的人物,镌刻在史册上。我甚至在想,过上一两百年,当一切都沉寂下来,暗淡下来,新文化运动的天空,熠熠闪光的,怕只有徐志摩这一颗星星了。
徐志摩对长篇小说的看法
时间还有,轻松些吧。
我看见下面有的人一边听讲,一边玩手机,要在过去,我就是嘴上不说,心里也是反感的。现在不了,能理解了。因为我也玩起手机了。三年前,我有个新手机,儿子要为我设定微信,刚设定上就有两个老朋友加上,我让我儿子赶紧取消了。当时我正在忙着写一部叫《边将》的长篇小说,怕分心,耽搁了思考与进展。去年吧,写完了,慢慢修改,就让儿子设了微信,不光看别人的,点赞,评论,自己也发朋友圈,希望别人点赞评论,很快就上了瘾。一醒来先看手机,晚上躺下了睡不着,嘟的响一下,赶紧拿起来看。我发朋友圈,最爱发的是我的信札,毛笔小行书,不衫不履,多半恰好六行,八行笺也是六行,八行就显得挤了。一说又远了,我要说的是,前几天在微信圈里,放了一封信札,是写给一个叫孙茜的女孩子的,是我们省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前两三年,小孙出过我两本书,一来二往就成了朋友。这几年,我在北京闲住,她在太原,闲了就写封信。跟一个女孩子,又不能说框外的话,只能是谈谈学问,谈谈读书的体会。这封札是这样写的:
经多年之研究思考,我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中文化之祸害,两项最大,一是毁灭了中国的诗歌,二是割断了中国长篇小说的传统。中国的长篇小说,多为名士逞才使性之作也。戊戌秋韩石山上(印)。
你不是谈徐志摩吗,怎么说起你的信了。是的,信上说的,是我的看法,这儿提起,道理还是刚才讲过的道理。就是我的看法,都是从徐先生那儿推衍出来的,生发出来的。我的判断,或许孟浪了些,却不能说没有来由。这来由,就是徐志摩说过的话。志摩回国后,写了许多文章,几乎可以说是手不释卷,笔不停挥。我们看重的,还是1928年从国外回来这三年,倦游归来,感慨良多。思想和感情,都到了成熟期,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关于诗歌,关于小说,都做了许多事,说了好多话——写了诸多文章。先说小说,后说诗歌。
民国时期,上海是中国的出版文化中心,书店之多,不可想像。我说的书店,不是光卖书,也出书,是书店与出版社的一体化经营,较之卖书,更注重出版,只有出了好书,才能卖出大价钱。有一家叫东亚图书馆的书店,很会经营,老板叫汪孟邹,安徽人,跟陈独秀,胡适都是好朋友。当年旧小说销路广,全是只有句读的老本子,汪老板就想,何不出个带标点的新本,于是便请人标点,又请胡适写序。胡适写了几个,《红楼梦》啊,《海上花列传》啊,都是他写的。还有一部《醒世姻缘》,也叫《醒世姻缘传》,亚东也要出,也该胡适写序,他不想写了,转给徐志摩。这时是1931年的7月,徐志摩来北大教书,住在胡适家里。起初让志摩看的是旧本子,拿在手上掉渣渣,后来给了个带标点的校样本,看起来就方便多了。志摩那一辈人,从小就看说部小说,留学后外国小说也不少看,他自己也写过小说,对小说的技巧与社会作用,早就熟烂于心。看完之后,没几天便写出一篇万字长文交差。这篇文章,在徐志摩的作品里,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可以看他的文学见识,二是可以看他对当时小说写作的具体看法。
见识就不说了,只说对当时小说的批评。徐志摩的话,颇有后世钱钟书的风格,就是时不时的,会带点色。他看这部《醒世姻缘》,一百回一百万字,而当时新小说的长篇,大都不长,比如巴金的《雾》,也就十一二万字。于是徐志摩说了:“当代的新小说越来越缩小,小得都不像个书样了,且不说芝麻绿豆大的短篇,就是号称长篇的也是寒碜得可怜!要不了顿饭的时光已露了底。是谁说的刻薄话,‘现在的文人,比如现代的丈夫一样,都还不曾开头已经完了的!”谁说的,我看就是徐志摩写到这儿来了这么个奇思妙想,又觉得笔下有碍,便趁势将恶名转赠给了别人,留下实利自家暗自欣喜。
这还只是就篇幅而论,内容呢,一样看不上眼。仍是跟《醒世姻缘》比,《醒》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写生,而现代最盛行的写实主义如何呢,可怜的新小说家,手里拿着纸本和全铅竺,想充分描写一个洋车夫的生活,结果洋车夫腿上的皮色,似乎比别的部分更焦黄,或是描写一个女人的结果,只说到她的奶子确乎比男人的夸大。看志摩的意思,是说作家的笔锋,沒有触到社会的肌肤,更不要说怎样的真实,怎样的深刻。
五四时代,写洋车夫,几乎成了一个时尚。鲁迅写过,郁达夫写过,老舍写过。志摩这话,是说谁呢?鲁迅的那篇太短,不会是,老舍写洋车夫,迟了好多年,也不会是,极有可能说的是郁达夫。正因为是好朋友,才会看,才会记得。达夫的那篇叫《薄奠》,早先看过,写没写到腿上的皮色,记不清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上一本看看。
中国的长篇小说,我们自己的传统,也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明清时代,叫说部,其作家,起初是整理充实说书人的本子,《金瓶梅》之后,就走向文人执笔创作的路子,可说是才子之书,特点是逞才使性,淫喻邪说。就我所知,许多当代的学者,都喜欢看这类小说。我山西大学上过学,毕业好多年了,有一年春节,和谢泳一起去山西大学看望几个老先生。到了姚青苗先生家,老先生都九十岁了,说起他最近的烦心事,竟是他听说山东某人手里有个金瓶梅的新本子,他要看,拿好多本书跟人家换,人家就是不同意。他烦心的是,他的书要比那个值钱得多,而竟不能如愿。有的大学者,说是在家里看书,不愿接待外面的人,我看他们的书里,不排除这类小说。据谢泳先生跟我说,陈寅恪就很爱看旧小说。
当代长篇小说的状况,我不想多说了,想说的只有一点,就是当今的作家,境界太低了,太不把写作当回事了。觉得写小说嘛,不就是编个故事,至于思想的深度,连想都不用想。你要再问下去,他会瞪了眼反问你:你要干什么!在他们看来,写小说,不过是用一个美好的,或是悲惨的故事,来诠释已经设定好的一个大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过去人们都知道,写小说是要有大才的,现在却成了,学习不好,升不了学,做不成别的什么,就去写小说。学习不好,去写小说,这大概是近几十年来最荒唐的事,最大的笑话。
最近在《文学自由谈》上看到一篇文章,冉隆中先生写的,《时间会记住哪些小说》,文末引用了一个日本作家池田正夫的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念给大家听听,池田正夫说:“好小说以细节形象以及隱藏其间的情感和思想,披露时代秘密。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民族的心灵史。”一个民族的心灵史,由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来写,不是笑话是什么?
徐志摩对新诗的看法
该着说诗了。我在这儿,用的是一种撂远了说的办法,就像写小说一样,笔搭得远远的,一步一步往近处走,直到走到眼前。说了徐志摩的职志,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再来说他在新诗上的努力,和对新诗运动的贡献,许多问题就看得清楚了。 徐志摩曾说过,他的祖上没有留下一首诗。好些书上说,他出身富商之家,好像是个没文化的大财主。我去过海宁,听人说他的伯父是当地有名的藏书家,现在的旧书铺里,偶尔还能看到徐家流出的古籍。徐志摩去英国留学时,曾送给狄更斯一套线装书,名叫《唐诗别裁集》,扉页上,或是书前的空白页上,写了一句话,说“书虽凋蠧,实我家藏,客居无以为赆,幸先生莞尔纳此,荣宠不尽。”可知家里是有正经藏书的。可能是带在身边自己看的,也可能是带出来专为结交朋友送礼的,这就不必深究了,书很旧,又是家藏,则是真的。再就是像徐志摩那一代人,上过私塾,一般都会作旧诗,写《徐志摩传》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会的,只是写起新诗,用力甚勤,顾不上写旧体诗。后来看到他给什么人们一封信,说他不懂韵律,故而不写旧体诗。新诗在国内没写过,在美国也没写过,初到英国也没怎么写,直到一九二一年才写起来,有人说是陷入与林徽因的恋情,感情郁积,不得宣泄才写诗的,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这样。再就是总得有这份才气,才会小叩即大鸣。
中国的新诗运动,从胡适1920年出版《尝试集》算起,差不多一百年了。怎么评价呢,各人的看法不同,我的看法可能比较极端些。我认为,基本上是失败的,唯一成全了的一个诗人,就是徐志摩。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诗人很多,能背一句两句的都是名诗人,而徐志摩的诗,朗诵,传唱,多少年经久不歇。就在前几天,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视频,是金星主持的一个娱乐节目,请台湾的明星费玉清唱歌,费要唱一首徐志摩的诗,金星主动说他来伴舞。诗叫《月下待杜鹃不来》,费玉清的声音,原本就有一种女性的娇媚柔情,唱这个歌,更是拿足了劲儿,沉浸其中,如醉如痴。金星呢,紧身暗红带花旗袍,高跟鞋,舞姿妙曼,让人惊叹。除了转身时,旗袍开衩处露出的小腿肚子,肌肉过分强健之外,堪称完美。一个声音,一个舞姿,还要加上徐志摩诗句的字词,所呈现出来的意境。下面就有字幕,可说还有字形之美。几个美加在一起,简直可以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仍不确,别人或许会几回闻,在我,只能是此生仅此一回闻,而有此一回,我也醉饱了,恹足了。由这首志摩诗谱成的曲子,我又加深了对志摩诗的理解,也更加肯定了我心里长期形成的一个看法。这就是,徐志摩其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最优秀的标志性人物,从“最”字上说,是唯一的。徐志摩的诗,代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在文学艺术上达到的最高水准,从“最”字上说,也是唯一的。
我编过《徐志摩全集》,也编过好几个选本,老实说,这首诗不知看过多少遍,并没有特别的感觉。顶多只是,这是徐志摩成长期的作品,还没有达到他自己的巅峰。感情的表达,很是细腻,字句上,仍受旧词的影响,痕迹明显了些,未能化为真正的新诗。听了费玉清和金星的演唱,一唱一演,我的看法变了。方才又翻了翻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的全集的第三卷即诗歌卷,头一次竟没有找见。为什么呢?翻书,很自然的会从左手大拇指卡住的地方打开。我卡住的地方是1926年,心想,这么好的诗,肯定是后期写的。从1926年往后,一页一页翻下去,全书翻完,竟未找到这首诗。还得说一句,我看视频,是老伴叫过去看的,她知道我喜欢费玉清的歌,也喜欢看金星的主持,一见是这两个宝贝的节目,叫我快过去看。我在书房,她在客厅,待我过去,已开始了,只听见金星说,徐志摩的诗啊,我来给你伴舞。费玉清唱了两遍,同一首歌,歌词重复。听得最新奇的是后面一句中的“风飕飕,柳飘飘,榆钱斗斗”,太美了,榆钱斗斗,跟荷叶田田,有同工之妙。我翻书找诗,就找这个“榆钱斗斗”,找见了就知道是哪首诗了。竟没有找见!莫非不是志摩的?不可能,那就从头开始,怕漏了,一页一页往过翻,果然见了这个“榆钱斗斗”,就是《月下待杜鹃不来》这首诗。我看了一遍,旧词痕迹明显,仍是一眼便可看出的特征,但这回整体的看法却变了。志摩作诗不过十年,连皮儿可说十一年,按往常看人的办法,总爱分个初始期、成长期、成熟期。错了,像志摩这样的天才,这样的路数根本框不住,框住也不灵,这个期那个期,全是胡扯,只有一个期,就是喷发期。早期有早期的特色,后期有后期的亮点,绝没有什么轩高轾低的感觉。
《月下待杜鹃不来》,作于1923年,属前期作品,不是我的舌头会打弯,过去认为旧词痕迹太重,恰是此诗的一大优长,典雅优美的词儿,达到的正是一种恍若仙境的效果。词儿是旧,搭配的方式,则是新鲜的,令人惊叹的,甚至可说是鬼斧神工的。我们可以想象,诗人在北京的某个公园里,夜晚,等着自己的情人来幽会,远处乡村的寺院,塔上的钟声,像梦里轻轻的波涛的声音,涌过来了又退了回去。心底里思念的潮水,一涨一歇,依稀像是浮在浪头的孤舟,踉踉跄跄,难以平稳。最有诗意,也最有情趣的还是第四节,即最末一节,听我念一下:
水粼粼,夜冥冥,思悠悠,
何处是我恋的多情友;
风飕飕,柳飘飘,榆钱斗斗,
令人长忆伤春的歌喉。
从最末一句看,又确实像是盼着,能在这样的春夜,等到再度来临的杜鹃。
说了志摩的诗所达的思想境界,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再来说,志摩留给我们在诗上的追求和告诫,也就可以推测出对他当下诗歌的看法。
《新月》是志摩创办的,时间在1928年3月。同年6月,这个事那个事,聚拢在一起,搅得他心烦,决心去美国走一趟,实际就脱离了《新月》这个群体。他是个随和的人,不能共事了,朋友还都是朋友。此后的《新月》,似乎背离了当初的宗旨,多刊发时论性的文章,文艺作品少之又少,诗歌几乎没有。一些年轻人急了,便推志摩挑头,办了个刊物,专发诗,就叫《诗刊》。到志摩去世,共出过三期,好像第三期发了稿,没出来志摩就死了。季刊吧,一季出一期。每期编起,都由志摩写个“卷首语”,名堂各有不同,第一期的叫《序语》,第二期的叫《前言》,第三期的叫《叙言》。我要说的志摩对新诗的遗训,全在这三篇文章里。
新诗问题,很难谈,又不能不谈。再不改,再不努力,中國的诗,甚至中国的文化,就不是沉沦,堕落,而是毁灭。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别人肯定不会这么看,可我就是这么看的。前几年,德国的汉学家顾彬,说中国的小说是垃圾,独独说诗歌还有好的。我一听就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小说是散文化叙述,结构、人物、情节,翻译过去,什么还是什么,优劣一眼就看得出来。诗歌就不同了,你拿上一首眼下的诗,让一个德国汉学家去翻译,你不说是诗,说是句子,他翻出来是一个样子,你说是诗,他翻译出来是另一个样子,一首德国诗样子的诗。因此可以说,凡汉语没有达到可以随意阅读汉语文学作品的人,经翻译看到的中国诗,都是不错的,至少是符合外语诗的规范的诗。
实际上,当下文学界,社会上,看到的诗是什么样子的呢?两个字,分行。汉语的字连起来,分行排列就是诗。这些年,文学界流传过许多关于诗的笑话,我看了,常常会想起鲁迅说过的一句话,是气坏了骂“四条汉子”的,说“我疑心他们为敌人所派遣”。我是“文革”过来的人,加上那时的词语,这个意思说全了就是,美帝苏修和国民党反动派,无法撼动我们的红色江山,红色文化,于是便训练了一批懂中文的人,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来,又通过各种手段混进我们的文化界,窃取高位,占据要津,然后卖力地提倡和书写这种只须分行便可称之为诗的文字垃圾,企图从诗上打开缺口,毁灭中国的文化,进而毁灭掉这个民族,至少也要让它退回到不知诗书礼仪的蛮荒时代。这是极而言之,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诗文古国,将要堕落到不知诗为何物的地步,这,还不可怕吗?
一个没有诗的国家,有什么文化可言!
谁来扭转这个趋势?
徐志摩,徐志摩,还是徐志摩。
他这个人,他的诗,他关于诗的遗训。 《诗刊》出了三期,各有卷首语,全是徐志摩写的,除了介绍本期组稿情况,还说一些对诗坛希望的话,也可说是,对中国新诗事业的期昐。前面两期不说了,只说第三期,这期叫《叙言》,先说了些印制和来稿的情况,接下来说,这一期诗很多,原本约定的散文,暂时不登。这里说的散文,是指非诗的文字,实际是指诗论文章。下一期,想让出一半或更多的地位,来给关于诗艺的论文。且说已约定下的,有孙大雨、胡适之、闻一多、梁实秋、梁宗岱、徐志摩等。也希望外地的朋友来稿。要是稿件多,且有相当的质量,也许会提议,另出一本诗论的专号,这要看情形而定。关于论文的题材,也就是论文涉及的方面,提出八点,其中第二点是:诗的格律与体裁的研究;第四点是“新诗”与“旧诗”,词,曲的关系的研究;第八点是:诗的节奏与散文的节奏。
我在写《徐志摩传》时,看过一些新月派诗人关于新诗探索的文章,对闻一多提出的新诗的三美,印象很深,这三美是建筑美、绘画美、音乐美。多年前,还买过一本《孙大雨诗文集》,看过里面收入的关于诗论的文章,说不定就是响应徐志摩的提议,为将要刊出的诗论专号写的。他的文章里,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音步”,就是诗的节奏。当时的感觉,这些留学回来的诗人,并不像胡适他们对待文言文那样,视之为女人的裹脚布,完全拋弃。这些诗人们,对中国的旧诗词同样的热爱,只是觉得旧诗词规范太多,不利于新思想、新理念的表达,因而要创建中国的新诗,说大了,就是要创建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不久前去南京参加一个传记文学会议,在车上与安徽师范大学的刘萍教授,谈起安徽诗人朱湘,她似乎正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我问她,可知朱湘对新诗看法,她说朱湘有这方面的文章。我让她回去,手机拍了给我看看。离开后没几天,就发来了,是朱湘的《评闻一多君的诗》里的话。对新诗的建设,他是这么说的:
新诗的工具,我们都知道的是白话。但是我们要知道,新诗的白话绝不是新文的白话,更不是一般人,如我如你,平常日用的白话。这是因为新诗的多方面的含义,绝不是用了日用的白话可以愉快地表现出来的。我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必得采取日常白话的长处作主体,并且兼着吸收旧文字的优点,融化进去,然后我们才能创造出一种完善的新诗的工具来,而我国的新诗才有发达的希望。
我把这几句话抄在这里,意思是想告诉不喜欢徐志摩的人,当时其他诗人,也是这样的看法。徐志摩、朱湘这些人,学过旧诗,也学过新诗,清楚诗是什么,什么是诗。一句话,诗是有规矩的。最起码,要有韵律,要有节奏,要有意境。意境太玄妙,难以把握,韵律与节奏,就成了诗的必须。在我的感觉上,他们几乎已达成了共识,再往前走两步,弟兄几个坐在一起拟定上几条,新诗的规范就立起来了。可惜,抗战来了,呐喊的诗起来了,抗战胜利了,内战起来了,内战完了,新的国建起来了,忙个不亦乐乎,这事儿就搁下,没人再提了。等到改革开放,文禁大开,人人都有了拿起笔写诗的冲动,这时的新诗,只留下一块遮羞布,分行。就是这么巴掌大的一块遮羞布,有人还嫌碍眼,扯了,写起什么散文诗。有时我见了散文诗,由不得就想,散文与诗,原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体,这种搭配可以,这世上还有什么文体的不同。 我有个不成熟,自认为是必须的想法,就是接续着徐志摩在《叙言》里的思路,走出下一步下两步。一是认定诗必须是有规范的,韵律应当有,节奏必须有。韵,不必讲究平仄,韵脚则必须有,节奏的字数不必固定,但节奏感必须分明。二是由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牵头,组织上十个八个全国著名的诗人和诗评家,如邵燕祥、謝冕、舒婷、潞潞诸人,开个会,定他十条八条,宣示天下,遵照执行。符合这几条的,是诗,不符合的,不得称诗,不得参与评奖,不得公开出版发行。先立起规矩来,再说怎么充实,怎么改进。眼下,只有这么一个办法,才可以挽中国诗歌这个狂澜于既倒。
谢谢大家,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
2018年12月29日写
2019年1月5日讲
韩石山,曾用名韩安远、韩富贵。1947年生,山西临猗县人。197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任中学教员多年。1984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曾任《山西文学》主编。2007年退休。有《徐志摩传》 《李健吾传》《张颌传》《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等著作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