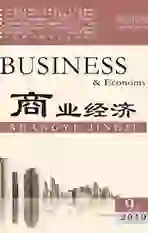债转股对于我国国企去杠杆的历史经验及理论研究
2019-10-08邵若马舒
邵若 马舒
[摘 要] 从当前国企去杠杆的背景入手,着重分析了我国目前主要的债务问题及债转股现状,并对比了当前与1999年债转股的核心区别,总结历史经验,探讨债转股对于国企改革的影响、难点、理论基础及对策。
[关键词] 债转股;去杠杆;国企改革
[中图分类号] F83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6043(2019)09-0167-02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background of deleveraging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emphatically analyzes the main debt problems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debt-to-equity swap in China, compares the co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urrent debt-to-equity swap and that in1999, summarize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ebt-to-equity swap o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related difficulti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debt-to-equity swap, deleverag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主要受到房地产泡沫及地方债务违约的挑战。化解债务风险,拆除债务杠杆,是管控当前风险的重中之重[1]。2016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同时附发《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债转股被作为“去杠杆”的举措而被提出,在两年多的实施过程中,国家有序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依法破产、发展股权融资,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期间,发改委、银监会、七部委分别发文,明确了债转股实施的相关法规。2017年8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当前要抓住央企效益转降回升的有利时机,把国企降杠杆作为去杠杆的重要任务。2018年6月,银保监会发布《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试行)》。而年底召开的全国市场化债转股政策宣讲和项目对接会,更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降低企业杠杆率及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工作的决心,以期助推我国经济稳步转型。
一、我国目前的债务问题
我国的债务问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企业债务,起源于实体经济需求扩张,投资加速,金融机构信用扩张推波助澜,最后可能由中央政府和央行买单;另一类则为政府债务,主要是由于投入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而形成的。据国家社会科学院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市场广泛采用债务与GDP之比)为249%。从结构上细分,居民部门杠杆率为39.9%,金融部门为21%,政府部门为56.9%,前三个部门数据并不算很高,但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高达131%,高于我国其他部门,也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其中突显了国企债务问题[2]。特别是2008—2016年企业部门的债务占GDP比率持续快速上升,反映了投入—产出效率的下降,更体现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并未完全实现。因此,国企降杠杆迫在眉睫。如何破解国有企业高杠杆困境,成为当下解决债务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1999年债转股的历史经验
债转股作为处置不良资产的一种手段,实质上相当于债务重组,并非新政。1999年,我国也曾启动过相似政策。除非国家另有规定,商业银行不得直接将债权转化股权,应通过向实施机构(比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转让债权,再由实施机构将债权转为企业股权。我国当时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它们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1.4万亿人民币的不良资产。
自1999年开始的债转股,伴随着2000—2003年的全球原物料价格暴涨,金属、炼油、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重现荣景。这类行业的企业利息与息税前利润之比在1998年曾高達40%,使得企业丧失投资动能。但随着1999年债转股的实施,股权上升,债务减少,资产负债率下降,利息费用下降,利润上升,亏损额下降,使得比值从40%降至4%,为企业带来了连续几年的投资热情。这些措施迅速活化了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改善了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实现了债转股企业转亏为盈,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
但是,一些债转股案例操作过程也不断暴露出了道德风险。第一,由于债务重组相当于就是在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进行的,并且银行在其中既不参与企业经营也没有按市场价格转换,这也让国家财政担负了相应的债务,遭受了相应的损失。同时又让债务人误认为债转股只是减轻债务负担,是一个不需回报的“免费午餐”,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并破环了市场规则[3]。第二,对于该破产的企业没有及时坚决地要求破产,而是“仁慈”地实施债转股,拖延了几年后还是不得不采取破产,使得国家资产遭受巨大损失。第三,原本有能力正常还本付息的企业,在看到参与债转股的企业被免除利息负担后,也故意拖欠利息,形成不良的“赖账文化”[4]。
三、此轮债转股的核心特征及难点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新的一年经济发展的五大关键任务“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其中的“三去”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其艰难程度不容小觑。如果企业不良贷款太多,不解放债务的话,就很可能影响到我国当前进行的“调结构”,甚至是“稳增长”。但如果去杠杆操作不当,有可能促使经济直接跌入“债务—通缩”陷阱。时隔17年后,面对企业经营不善,我国重启“债转股”的去杠杆化操作,即稳定、有效地拆除债务杠杆的基础上把债务资产转化为股权资产。在供给侧改革框架下,其目的主要有两方面:去掉过剩产能以及推动整个行业的转型升级。但与1999年政策不同,这次不再由国家注资或强势主导救助国企,而是“由市场主体自主协商确定”,并且严禁“僵尸企业”、失信企业、债权债务关系不明晰的企业和有可能助长产能过剩或扩张和增加库存的企业。
与股权合约相比,债务合约缺乏灵活性。债务合约在带来确定收益的同时也导致经济不稳定。它助长了过度的债务创造,这意味着债务积压将带来严重的通缩。另外,从原本的债权人摇身一变成为大股东,也许并非是债权人的初衷。因此在实践的过程中应“切实贯彻市场化原则,充分尊重债权人和投资人的自主意愿,切忌拉郎配和指标分配”。但市场上也担心政策执行力和落实效果,尽管强调“市场化”,但地方政府可能还是会偷偷担保,地方保护主义可能还会抬头。既要为暂时困难的企业纾困,又要特别避免“僵尸企业”占用资源却不产生效益,这是此政策目前与未来执行的难点。
另外,我国债券市场过去长期“刚性兑付”,尤其是央企和国企。投资者一直有一种错觉,即使流动资金周转不灵,也可以依靠政府补助等形式的“救命稻草”完成还本付息。债券市场如果想健康持续地发展,必须打破刚性兑付,发债企业应该多依靠自身盈利和资金周转去主动偿还债务,以构成一个良性的偿债模式[5],这应该成为共识。
四、债转股的诺奖理论基础及对策研究
201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霍姆斯特姆(Holmstrom)教授和哈佛大学的哈特(Hart)教授,以此表彰他们对于契约理论的贡献。前者的研究主要基于“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而Hart等人在不完全契约的框架下共同创立了产权理论,即由于诸多不确定性,现实中事前签订的是不完全契约。已投入专用性资本的当事人再谈判时可能会被敲竹杠,了解到这些风险的当事人会减少专用性投资,无法实现最优效率。应事前将剩余控制权分配给专用性投资相对更为重要的一方,提高其事后谈判的砝码,使其得到更多投资剩余,以此实现次优效率。多年前我国官员便相当于应用了Holmstrom等人的激励理论来推进承包制和放权让利等改革。但这种强激励在使国企效率短暂提升后,并未获得长期成功。此时,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国企效率无法持久的关键原因是企业的产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在Hart看来,当企业选择发行债券或股票等方式进行融资时,这实际上是一个缔约的过程。由于存在企业的收益流不能被证实等因素,因此缔结的是一个不完全契约。为了尽可能防止机会主义行为,例如企业经营者“盗取”资金,应该采取“硬”约束——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而当企业无法履约时,企业可能同时存在许多债权人,每个人在面临企业破产时都希望保证自己利益最大化,因而很可能会展开无效率竞争。这势必会导致企业的价值被低估,因此控制权不能直接交给债权人,而是应该把债权人变成股东,然后通过投票决定企业的未来,这就是“债转股”的理论基础。按照Hart的理论,最佳破产程序必须保证破产公司的资产应该用于能体现价值最大化的方面,并且伴随着原经营者权力的更替。当然,国企摆脱债务困境不能仅靠放开控股权或引入优质战略投资者。国企想要走出债务泥沼,应该首先靠自身的变革,应健全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特别完善企业经营者的监管,在“混改”引入民营资本的同时,将民营管理方法及民营创新精神进行重要引导及真正落实。
[参考文献]
[1]郑志军,李吉平.穿透中国债务:公共产品经济学逻辑[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2]李扬.去杠桿的路径与方法[N].经济日报,2016-07-21.
[3]吴晓灵.用市场化思维和手段去杠杆——兼谈对债转股手段的运用[J].清华金融评论,2016(5).
[4]李剑阁.债转股的历史经验和政策要点[J].清华金融评论,2016(5).
[5]李阳蓝.无刚性兑付情况下企业债券违约防范——以东北特钢债券违约为例[J].财会通讯,2017(14).
[责任编辑:赵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