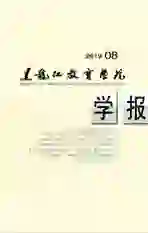男性的政治隐喻与丁玲的革命皈依
2019-09-12郝艺霞
郝艺霞
摘要: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之后,在当时的五四文坛影响颇为深刻,莎菲这个蜗居在北京公寓中的女性写作者与她本人当时所处的地位和人生经验似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近年来,研究者的视角纷纷集中在丁玲本人作为写作者与小说文本中刻画的女性人物之间所隐含的种种耦合性上。鉴于此,以丁玲创作的外部环境因素为突破口探寻丁玲小说创作的深层脉络。
关键词:革命政治;男性隐喻;女性出路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9)08-0106-03
一、文学启蒙导师
作为丁玲文学上的启蒙老师瞿秋白,在丁玲与好友王剑虹进入相对正规但受共产党主导的上海大学求学期间,他的双重身份在研究丁玲早期的文学作品方面至关重要。
起初两人是在南京认识瞿秋白,“瞿秋白讲苏联故事给我们听,这非常对我们的胃口。”[1]因此留下很好的印象。到上海以后瞿秋白经常拜访两位女学生并且帮助她们学习俄语,事实上瞿秋白经常以学习俄语为由向她们传递俄国的文学作品、宣扬俄国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瞿秋白渊博的文学知识与言谈风采给丁玲带来文学上的深刻启发;当丁玲迷失方向于茫茫人海中寻找自我出路时,瞿秋白坚定的文学信仰指引她走向她所崇尚的文学之路,在回忆中丁玲谈到她向瞿秋白请教将来怎么学等问题时,“他的话当时给了我无穷的信心,给我很大的力量。”[2]其次,瞿秋白的革命信念对丁玲影响深远,丁玲在湖南求学期间接触到的革命文化环境促使她崇拜和尊敬像秋瑾与向警予等这样为革命奋斗不畏牺牲的女战士,“虽然我对她们的活动没有多少了解,但她坚韧不倦的革命精神总是在感召着我!”[3]母亲从小对她灌输的思想虽然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发挥作用,丁玲的人格发展依然遵循着自由个性等几乎那时所有女性青年知识分子的特有情感脉络,但从之后《母亲》的创作内容安排上来看,早期的革命知识早已经作为一种潜在的、亟待开发的文学资源。青年时期的丁玲拒绝任何强加在她年轻、渴望自由的身体之上的约束,并且时时刻刻小心规避着这些束缚与条条框框。她认为,规则与章程对一个自由的女性来说实在是一种负担,政治的革命意识会制约她走向更为广阔的情感表达世界。这时的丁玲并没有遇到过大的值得她反思许久的挫折和困难,她更多的是倾吐着处于五四时代背景下青年女性内心的不平与感伤。
1927年丁玲亲眼目睹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眼看着无数革命志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戮,她开始反思自我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种种。革命这一套装置在她的大脑中开始慢慢发酵,瞿秋白等革命党人渐渐开始被丁玲理解与认识,她第一次以朋友的身份接触到从前看似非常遥远而高大的共产党形象。这些印记统统在胡也頻遇难,丁玲万分悲痛的心灵沉淀下浮出水面,从那以后丁玲的写作风格与内心机制发生反转,看似伟大缥缈的革命经验从此伴随她一生,直到丁玲20世纪80年代忍着腰痛伏案写作的时候,她的内心依旧以伟大的共产党领袖毛主席作为精神支柱,从中可以看出早期埋下的革命种子经过沉寂、发酵到最后的爆发,瞿秋白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对丁玲创作的深刻影响。
二、政治革命导师
1924年丁玲初识胡也频,如果说瞿秋白是丁玲文学萌芽时期的领路人,胡也频则是丁玲倒向革命文学创作的最大动力。胡也频从小的生活经历十分坎坷,两人在这方面似乎有很多相通之处,这种貌似平和安逸的北京生活为丁玲早期小说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开始启动早已沉淀多时的文学机制。丁玲的思考能力和鉴赏批评的灵敏度非常优秀,这与她早年所通读的古今中外书籍密不可分,同时也与胡也频等为她营造的文学环境密不可分。据沈从文回忆,丁玲并非以写短篇小说开启她的文学生涯,而且她丝毫没有要成就一番文学事业的野心,仅仅在看书无聊之际通过写信来打发时间,“她善写平常问询起居报告琐事的信,同样一句话,别人写来平平常常,由她写来似乎就动人些,得体些。”[4]这也就不难解释丁玲以书信体的形式建构笔下的人物,她用惯常的写作方式想象出一位涉世未深的文艺女青年面对当时社会形态所表现出的危机意识与焦灼感,以及五四时代女性在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悲凉,她想通过作品传达出时代新女性在走向革命道路过程中所承受的双重折磨。
1927—1930年间丁玲创作了很多作品,实际出版的作品后来集结成小说集《在黑暗中》。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中强调1929年这个海军学生的文学创作是最好的,三位知识青年早年在北京时期将办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杂志作为人生奋斗理想,一方面是可以在自己创办的杂志上发表他们的文学作品;不需要浪费无数精力为文章发表在哪里奔走辗转,这样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写作时间;那时候很多稿子投到某一杂志社久久不见回复,同时作家苦心创造出的作品由于各种原因被遗失,这种情况在当时中国文化环境时常发生,也是很多作家为之头痛遗憾的事情。这样的文学环境,用丁玲的话来说就是,好的环境影响了三位文学作家的创作数量与质量,在上海的文学创作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巅峰[5]。胡也频比丁玲和沈从文的政治革命经验丰富,他早已将人生方向转移到为革命与中共服务事业奋斗。其间杂志社被迫倒闭,无计可施的胡也频只能去山东济南当教师以便早日还清拖欠的债务。1930年,胡也频在济南教书期间整日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冯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6]。胡也频的革命意志力和精神斗争力在两年间迅速壮大,思想上他早已克服了五四时期小资产阶级的苦闷彷徨,并且创作了一批反映知识分子在革命转型时期的作品,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作家思想文化的浸染以及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结构的重组。这样的思想同样作用于丁玲的创作中,通过研究《在黑暗中》这部小说集就不难发现丁玲写作的强大爆发力,1929年的1月开始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部短篇小说诞生,到6月份杂志社被迫停刊时丁玲的创作思考都没有因此停滞,到1929年冬天丁玲完成了长篇小说《韦护》,这还不包括那些被丁玲撕掉的小说。一年的时间她完成多部小说,除去创办杂志为她人生带来的写作素材及创作灵感,胡也频作为丁玲的丈夫对她文学的革命宣扬及政治鼓舞影响颇大。
无政府主义思想一直保留在丁玲的信仰中,胡也频在这时早转向并且希望丁玲可以把她思想中那些虚无缥缈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转化为革命的斗争力量,并对她寄予厚望,但女作家始终无法放弃对反叛的知识女性的建构,她在自我创造的文学世界里享受着倾吐内心愤懑的快感。丁玲始终深深地尊敬胡也频的革命风范,1931年胡也频被捕入狱,虽然丁玲和沈从文经过多方努力到处打探,但胡也频还是被当局秘密杀害,现实的残酷已经不容女作家喘息和痛苦,她坚忍着失去丈夫的剧痛将幼子送回了常德家里,不断地编造谎言安慰并不知道实情的母亲。丁玲在面对丈夫、幼子、母亲三方面显示出了她超群的坚韧毅力。这件事给丁玲带来了沉重打击,由此她渐渐开始将视角转向现实。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一文中谈到,胡也频在福建的生活状况和他辗转南北的经历,革命的火种一直燃烧在他内心当中,只要社会给予他一个实践革命的平台,热血沸腾早已激情壮志的爱国青年是敢于挑战一切艰险的[7]。这些保留在胡也频性格基础上的精神风貌对丁玲的影响可谓深沉,使得她之后的文学写作总是出现一个雄心壮志具有男子气概的革命人物,虽然1931年之后的写作或多或少受到蒋光慈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的影响,但丁玲总是将更多的着眼点放到革命者敢于抛弃一切私心杂念,投身共产党事业中为党甘愿奉献一切这方面。胡也频牺牲之后,丁玲的创作环境与氛围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同时将笔调转向对现实社会的控诉,以此来倾泻她内心的悲痛。
纵观丁玲和胡也频短暂的情感发展历程,他对丁玲早期创作生活的政治引导最为深刻。相对最初开启丁玲文学机制的瞿秋白,胡也频对丁玲的影响与之前激发式的感受情态不同,那是一种缓慢式的浸入发展模式。这两种不同样态的外部影响力所反映出的最终接受力效果也不大相同,丁玲的文学写作方向已经完全发生了扭转,只需要一个适合的文学环境就可以将她皈依到革命的文学机制中来。
三、精神灵魂导师
1928年出现在丁玲与胡也频生命中的另一位中国共产党志士兼文学家冯雪峰成为丁玲革命文学机制中又一個重要人物。冯雪峰与丁玲交谈以政治性的内容为主,这方面也恰好成为两人交往的契合点,冯雪峰给予丁玲这种思想上的满足,却是丁玲从胡也频那里得不到的[8]。丁玲在《悼雪峰》中谈到了两人微妙的情感关心,“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9]两人经常谈论的主要是一些政治方面的内容:飞机、炸弹、金价、白人、黑人、资本主义与殖民地、屠杀、斗争、组织等等,这使得丁玲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现实情况,她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所处环境的险恶,作为经历大起大落的女性作家,她必须以顽强的意志与坚定的信念走到革命的队伍中,冯雪峰正因此为丁玲的“向左转”创造了有利的文化环境。
革命作为丁玲经过人生悲痛而找不到出路处于迷茫时刻的又一道光明,她已经不是十年前敢于反叛主张自我的文学青年,生活的积累与政治革命促使她将文学创作的中心转移到反映现实、大众的文学生活中来,并且与以往体现小资产积极知识分子苦闷彷徨的文学作品区别开来,冯雪峰是丁玲走到革命队伍中的实际操作者。他以帮助丁玲排遣忧虑为由将她吸纳到革命大众文艺范式中,同时中央宣传部决定要她留在上海创办并主编《北斗》,以此将丁玲的人生关注点转移到为中央服务的计划方面,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丁玲只能妥协。渐渐地她靠近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在组织活动中扮演着为党为人民服务的光荣角色。作为鲁迅思想浸染下的冯雪峰,他的眼光同鲁迅一样锐利而深邃,同时他利用与丁玲这样一种相对暧昧的角色完成了女作家的彻底蜕变。创办杂志之外的丁玲开始进行创作,她在编辑杂志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转变,笔锋跳转到反映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与革命者进行革命的艰难历程,同时更深刻地认识到组织文化工作对党和国家的重要性。
冯雪峰在丁玲的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引领她走向革命,深入中国社会来为人民服务,而且两人在文学上的关系十分微妙。《莎菲女士的日记》刚刚发表,冯雪峰就开始关注并且是最早对日记提出批评的人,他不希望丁玲沿着莎菲这条消沉的路一直走下去,他希望她能描写革命,投身斗争。冯雪峰始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关注女作家的创作,紧接着《水》的发表大受好评,关于《水》的第一篇评论依旧出自冯雪峰之手,在肯定小说成功的同时指出丁玲在小说创作中的局限性,她在文学方面受到冯雪峰的鼓励,创作的热情高涨,两人之间的通信交流频繁。作家在文学方面有知己的存在,不仅可以解决创作中的种种疑难杂症,还可以帮助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得到心理上的安慰,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对丁玲而言弥补了她内心的创伤,坚定了走向革命的方向。丁玲1931年5月在光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讲出了她内心的真实声音,首先,作为作家她以认真的态度面对每一部作品,并且时时刻刻都在自我反思与剖析;其次,她非常渴望有一个批判与被批评的文学交流环境,也就是每一个读者应当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以诚恳、真挚的态度来分析每一部作品;最后,她说出了让她彷徨与忧郁的文坛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作家在返过头来思考自己作品的同时发现很多的弊病,感觉错误非常之多,可是总无人对作品给予诚恳的批判,《我的自白》可以看作是丁玲站在相对客观的角度,也就是读者的角度与广大读者一起审视她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可谓是用心良苦。继《我的自白》之后的《一个人的诞生》自序中丁玲同样再一次提出了同样的忧虑,从这两篇作于同一年的小文章以及之后丁玲的一些书信中可以觉察到丁玲当时面临的困境。三年中丁玲在寂寞中从事写作并且为之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她几乎以一种恳求的姿态希望文字工作者和读者朋友给予一定的指正,丁玲如此渴望批判的文学态度,是作家对她所创作的作品极其负责任的表现。在这方面冯雪峰对丁玲作品的指正恰恰不会得罪她,反而会赢得信赖和尊重,因此冯雪峰成为了她人生中最崇拜同时也是遥不可及的一位导师,由此丁玲彻底完成思想的蜕变。
我们姑且将丁玲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称为丁玲内外转变的迷茫期,这一时期丁玲同时处在跨越“青年”与“中年”这两个时期的夹缝中,也就是向左转与向右转问题的十字路口。1933年闻一多在致饶孟侃的一封信中表达他的苦闷:“总括地讲,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自己的缺陷,一种根本的缺憾——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以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10]在革命文学机制的疯狂攻击下丁玲选择了“向左转”,之后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到达无数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革命圣地延安。丁玲历经时代变迁与各种挫折依旧坚持写作,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始终没有因为时代变迁而发生改变,之后的写作视点转移到当时被广泛宣扬的普罗文学上,丁玲的作品与革命文学机制达到了相辅相成的一种理想状态。由爱自由、爱幻想、反感规则束缚的青年女性转向要做党和群众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的革命工作者,新的革命的一整套装置随着时间的推移灌输到丁玲的思维体系中并且对她产生很大的效力。丁玲转变前后受到三位流淌着革命主义鲜血男性或多或少的影响,完成了她对革命的皈依与对文学的真实追求。
參考文献:
[1]丁玲.丁玲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丁玲.丁玲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3]丁玲.丁玲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4]涂绍钧.丁玲传[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5.
[5]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
[6]李向东,王增如.丁玲年谱长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7]沈从文.记丁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8]丁言昭.别了,莎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9]王中忱,尚侠.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10]张永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Male Political Metaphor and Ding Lings Revolutionary Conversion
HAO Yi-xia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133000, China)
Abstract: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Ding Lings Diary of Ms. Shaffy, she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May 4th literary arena at that time. Saffy, a female writer living in a Beijing apartment, seems to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er position at the time and her life experience.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rs have focused on the coupling between Ding Ling herself as a writer and the female characters depicted in the novel tex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eep vein of Ding Lings novel creation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factors of Ding Lings creation.
Key words:revolutionary politics; male metaphor; female outl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