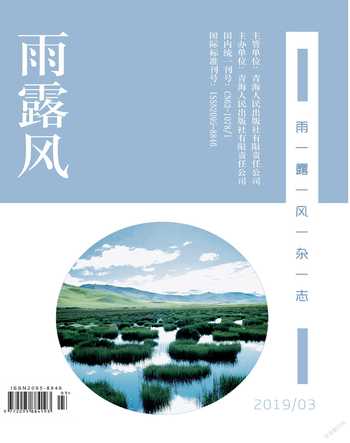陶渊明诗文中的儒道思想
2019-09-10谭田甜
谭田甜
摘要:陶渊明是中国的伟大诗人,纵观其一生,儒道思想对其影响深远。儒家思想使他具有济世之心,道家思想使他向往自由,两者在他眼中演化为仕与隐的矛盾。然而,他又可以将其调节,坦然面对一切,形成一种洒脱纯真的人生哲学。在这种矛盾和统一中,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儒道思想。
关键词:陶渊明;儒道思想;积极入世;崇尚自然
陶渊明的基本思想一直是有争议的,事实上,陶渊明的思想是多元而复杂的。他既有“大济于苍生”的儒家理想,也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种脱离世俗的道家思想。本文旨在从陶渊明的诗文创作中,探讨陶渊明的儒道統一思想。
一、陶诗中儒的思想
陶渊明从小就研究儒家经典。“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一)此外,陶渊明是官宦世家出身,深受曾祖陶侃和外祖孟嘉的影响,陶侃和孟嘉都是在朝廷当过大官,信奉儒家的出仕思想。虽然儒家思想相对薄弱,但统治者仍然祟尚儒家思想,重视儒家思想。因此,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一)积极人世,壮志难酬
陶渊明多次致力于实践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即使隐退仍心系朝廷、心系国家大事。陶渊明之所以出仕,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如他在《归去来兮辞》中提到的那样“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因为家贫而入仕。其次,儒家思想对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深刻地影响了陶渊明。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陶渊明诗中所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这种想要拔剑而出,荡平天下的精神,正是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体现。可见,陶渊明出仕之时,是想要在东晋这种混乱局面中,做出一番功绩来的。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旧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这些诗句表达其有志难伸,也可说明陶渊明原本有积极用世的心志。儒家思想的基本态度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当陶渊明年轻的时候,他充满野心,他的归隐,除了受到当时隐逸之风的影响以外,最主要乃是生不逢时,不得已的选择。陶渊明当时所处的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以陶渊明的背景,很难有发展的机会。尽管如此,经过几度的仕隐之后,终于决定从此归隐田园,不再复出。
在陶渊明的《屈贾》一首中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可见,读六经即是进德修业,而其目的在“将以及时”,即为世所用,建功立业。虽然这首诗是在歌咏屈、贾,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诗人自己远大的理想。陶渊明《杂诗八首》其五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他年轻的时候开朗乐观,意气昂扬。“猛志逸四海”,好男儿志在四方;“寒翮思远翥”,这是要展翅高飞,一飞冲天。这是何等的志怀和气魄。
陶渊明五次为官,十三年里他一直徘徊在进与退之间,他仍是人世心战胜出世心。可社会动荡,官场黑暗,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他力不从心。建功立业的热血可能冷却,但仍在他血管里流淌。随着岁月流逝,用世之心总有“有志不获骋”的感觉。然而,他反思自己,回忆起年轻时的英勇精神,并告诫后代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尔,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复何言”。(《子俨等疏》),诗中希望后辈子孙能尊崇效法《诗经》中的行为准则,并寓有自我鞭策、自我警惕的意味。
(二)固穷守节,安贫乐道
归隐后的陶渊明,选择自食其力,《移居》:“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这表明陶渊明当时不同于其他隐逸的人,即使生活贫穷到需要乞食,他却甘于这种生活。这种接受现实生活的态度和当时庄老之徒的绝尘避世迥然不同,在《劝农》:“舜既躬耕,禹亦稼稿……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论语·宪政》:“禹稠躬稼,而有天下。”陶渊明举舜、禹的例子,说明力耕的重要,然而不擅农事的他经常处于贫寒的处境,然“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陶渊明之所以能忍受饥饿和寒冷,是因为他“固穷守节”的节操。
陶渊明所谓的“道”着重于个人的道德品质,反映儒家思想。因为田园生活并不都是“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其一)》)虽然令人赏心悦目,但仍然充满了艰辛和无助。在陶渊明回到田野后的第三年,他的稻草屋突然被烧毁了,“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杂诗(其八)》)生活虽清苦,他却能够“不戚戚于富贵,不极极于贫贱”。(《五柳先生传》)“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不仅是儒家伦理,更是儒家“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的坚忍。
毕竟,在陶渊明的整个人生中,都坚持了孔子的“君子固穷”和与守道立善遗训。由于“固穷”,他能够“安贫乐道”,所以陶渊明可以舒适自足,在田园风光中回归“真我”。
二、陶诗中道的思想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南北分裂,战乱不息,社会动荡不安,当时知识分子顿时失落人生目标,经过恐惧、焦虑走向自我意识的觉醒,试图找回自己。道家提倡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道家思想成为当时文人主要的哲学基础,使人的心灵及行为得到自由和解放。而陶渊明淡泊名利,崇尚自然,生死豁达,热爱生命的思想也深深地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一)淡泊名利,崇尚自然
道教主张顺从自然,淡泊名利。官场的黑暗让陶渊明心灰意冷,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他在自然中寻找心灵的寄托。既然社会现实决定了他无法为国为民做出多大的贡献,至少他可以选择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好,“独善其身”。道教指出了名利与人生之间的矛盾,老子主张知足保和,庄子进一步透露:“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追求名利只会使自己成为名利的牺牲品,而“不与物交”才是“淡之至也”,才是“乃合天德”(《庄子·刻意》),才可以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
归隐以后的陶渊明并没有过多的物质需求,把目光转向田园,从自然山水中感受道家“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的淡泊。而且,他一直认为“人亦有言,称心易足”,所以他的精神已经从官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此,山水乡村生活成为诗人的新价值和精神寄托。他的《归去来兮辞》和《归田园居》里描写的那种静雅朴素的乡村生活,那种淳朴憨厚的农家风情,清新美丽的田园风光体现了他的灵魂,沉淀了他的灵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就像飞倦的鸟儿在巢中休息,就像离水的鱼儿又在故渊里自由自在地游着。看他的《移居二首》“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这在和谐欢悦的气氛中又增添了一层文雅气息。与这些心地单纯、不为富贵利禄动心的隐士在一起生活,农忙的时候各自归家下田,农闲的时候,相聚谈笑,饮酒作乐。这又是何等适意畅情!
“自然”指的是一种非人为的自然而然的状态。人们应该顺应“返璞归真”。崇尚自然也是陶渊明对生活更深刻的哲学思考。他希望返回自己本来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天真状态,所以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表明回归自然是一种快乐。陶渊明的“自然”不仅反映了对回归田园的向往,也体现了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的和谐状态。经常出現在陶诗中的松树、秋菊、孤云和飞鸟不再是简单的事物,而是与诗人的主观感受和体验相融合的特殊意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在东篱下采摘菊花,忘了自我。
(二)生死豁达,热爱生命
将人的生死置于自然背景之下,认为生与死是自然发生的事情,不必动摇情感。陶渊明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聊且凭嘟王,终返班生庐”,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人世的盛衰,一如季节的寒暑更替,就如人的生死亦是如此。陶渊明许多诗都纠缠在世俗的生死情节中,充满悲伤。亲人的离世曾使他压抑、痛苦,看着“寥寥空室,哀哀遗孤”,他不禁发出质问:“人逝焉如?”但他知道“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他总是把死亡视为生活的归宿,所以他微笑着轻松地谈论生死。
陶渊明委运顺化,崇尚自由,生死顺其自然的思想在他的诗歌中很常见:“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丝不如竹,竹不女口肉”答日:“渐进自然。”(《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人生如寄,憔悴有时”(《荣木》)、“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夜独雨》)、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他不相信仁者长寿,更不相信形尽神不灭。既然“有生必有死”(《拟挽歌辞三首》),为什么要对死亡感到不安?这种适应生死的态度使他能够平静地面对死亡。死亡只不过是将身体委托给山回归自然。但是,他和庄子不同,庄子通过超越生死达到了精神的自由,而陶渊明在顺应生死中寄托的是一种及时行乐的态度:“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诗序》)这种把握现在的人生态度不是人性的消极堕落,而是隐居时的自我鼓励和自我安慰。
他之所以视死亡如此豁达,是因为他了解生命的意义并理解死亡的基本含义,他摆脱了对死亡的恐惧,直面死亡,更多地体现了他对生命的热爱。
三、总结
综上所述,陶渊明既受儒家积极人世的影响,又向往道家的身心自由,在仕与隐的矛盾中进行内心的挣扎,然而又能用儒家的“固守穷节”和道家的“淡泊名利”、儒家的“独善其身”与道家的“归隐”来进行调和,使儒道思想达到了契合。从而使陶渊明进一步坚定自己归隐的信念,达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赠答诗》)的洒脱真率,活出了一个“真我”。
这种儒道思想的矛盾与统一、契合与协调在陶渊明的诗文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是济世之心、安贫乐道、崇尚自然、生死豁达。陶渊明诗文创作深受儒道思想的影响,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诗文创作风格。陶渊明自身品格及其诗文创作风格中都蕴含着儒道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寅洛.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02-205.
[2]方祖燊.陶潜诗笺注校证论评[M].北京:中华书局,1977:307.
[3]李文初.陶渊明论略[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4]刘宝楠.诸子集成本·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6:103-150.
[5]杨勇.陶渊明集校笺[M].台北:正文书局,1999.
[6]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