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霍巴利王》“脑洞大开”的背后真相
2019-09-10徐辉
徐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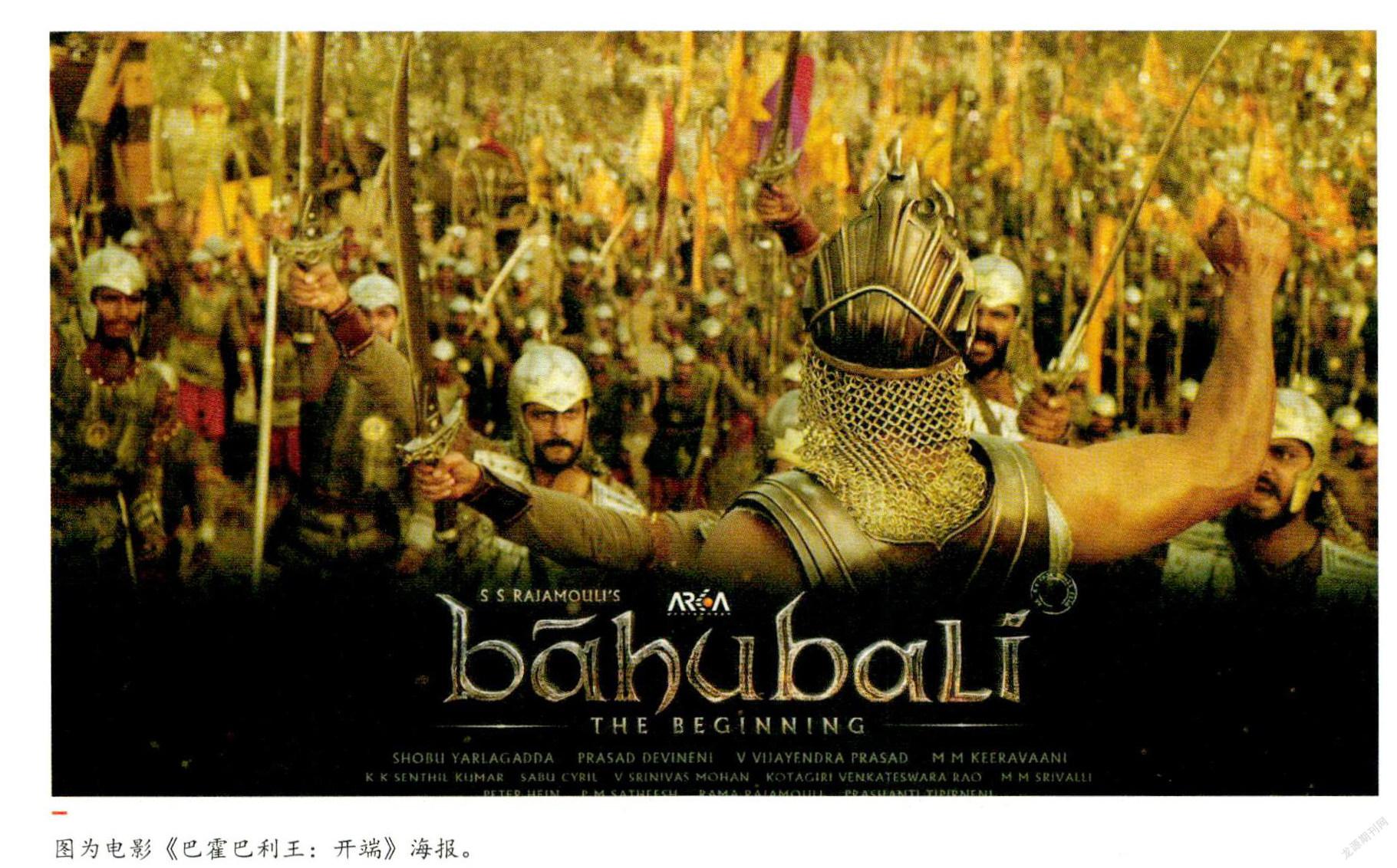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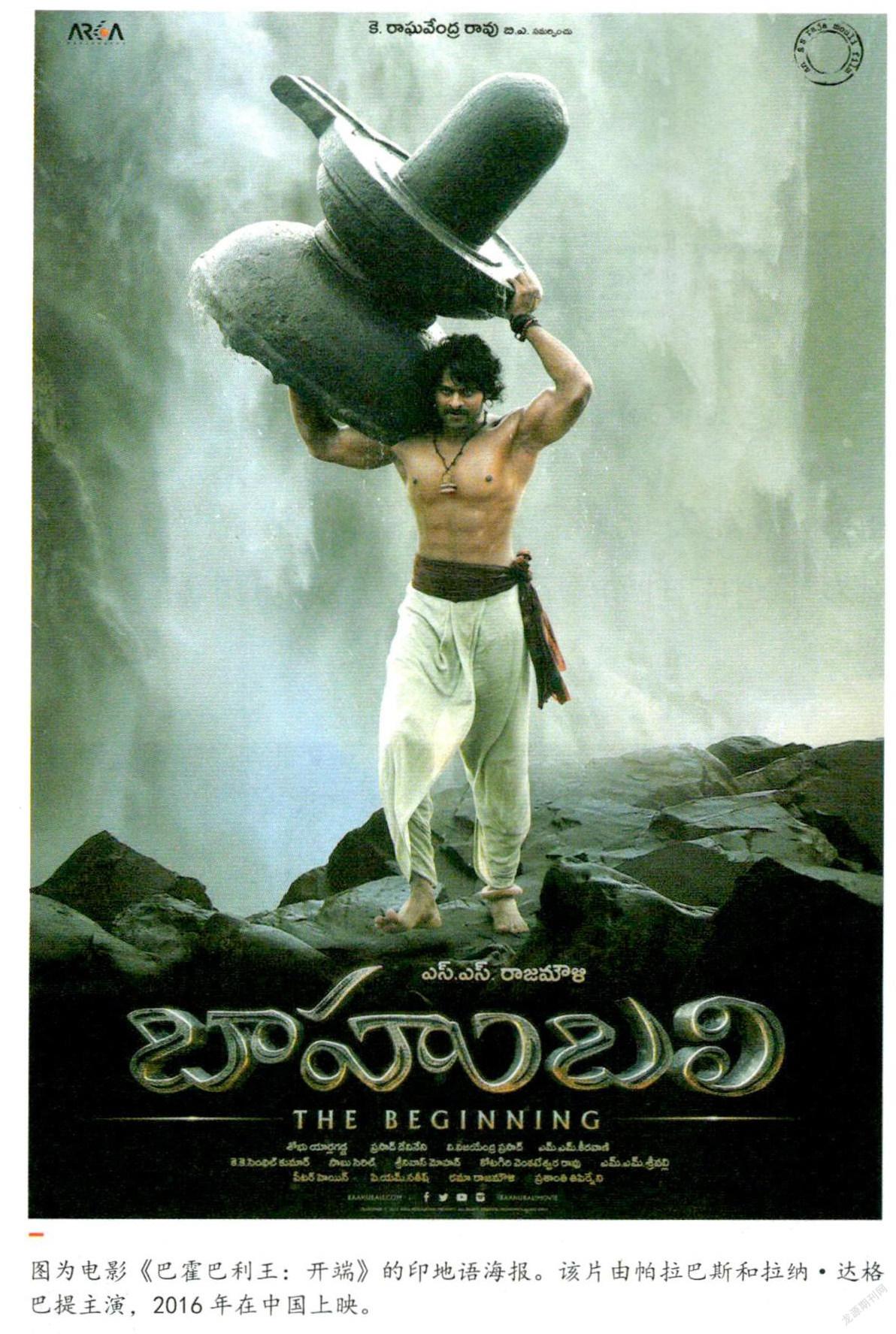
我们对于这部史诗片所承载的印度传统与文化知之甚少,卻习惯在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中或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来理解它。
在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我们对地球另一边欧美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毗邻而居的南亚邻国印度,这片南亚次大陆成了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对待印度电影,中国观众更乐于接受那些取材现实、聚焦当下,具有情感共通性的作品,而对于那些历史题材、史诗题材的作品,往往由于缺少相关的知识背景而产生理解上的偏差,甚至是误读。《摔跤吧!爸爸》以近13亿票房成为当之无愧的印度引进片票房冠军,然而在印度本土以及海外更多地区,打破多项纪录、口碑爆棚的作品则是《巴霍巴利王》系列,该系列的下部在印度本土上映时票房是《摔跤吧!爸爸》的近三倍。尽管如此当它雄心勃勃地进军中国市场时却折了戟,上下两部分别以700多万和7000多万票房收场。
从跨文化视角来看,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我们对于这部史诗片所承载的印度传统与文化知之甚少,却习惯在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中或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来理解它。《巴霍巴利王》系列通篇充满了各种神话和宗教隐喻,这些印度观众耳熟能详、了然于心的典故,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却像隔着两国的喜马拉雅山一样难以逾越。《巴霍巴利王》被中国观众诟病最多的便是“脑洞大开”的“开挂”和“歌舞”。那么,这些“脑洞大开”背后的深层缘由究竟是什么呢?
“化身”思想与偶像崇拜
在印度的宗教和习俗中,神灵往往具有多种化身。他们常常化身为各种形象拯救世界于危难之中,久而久之,印度就形成了非常浓厚的偶像崇拜情结,他们认为英雄都是神灵的化身。当人们崇拜某个英雄时,就不知不觉地赋予英雄某种神性,将其神格化,且对英雄的渲染无所谓过誉。
《巴霍巴利王》的故事框架脱胎于史诗著作《摩诃婆罗多》,书中描绘了婆罗多族的两支后裔班度五子和持国百子为争夺王位继承权而展开的一系列斗争。
电影的主人公大多能在史书中找到对应的人物原型。初代巴霍巴利的人物原型是班度五子,作为神之子,他们分别具有智慧、天生神力、正义、勇敢等品质和能力,巴霍巴利王身上也具有这些“神性”。“巴霍巴利”的梵语本意即是“大臂者”,他力大无穷、以一敌百,同时机敏过人、足智多谋,拥有“照亮夜空的智慧”。他为人亲厚、心胸阔达,受到百姓的尊敬和拥戴,他是一切至真至善至美的化身,是人亦是神。二代巴霍巴利可以看作湿婆的化身,他剧中的名字就是“Shiva”,即湿婆,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毁灭之神、舞蹈之神。林伽(男根)是湿婆最主要的象征,因而Shiva能够徒手举起巨大的林伽,会欢快地跳起坦达罗舞,还能在与叔叔决战中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伴着铿锵有力的坦达罗颂,以自己的血祭林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反败为胜。
勇敢且独立的提婆希那公主也是若干史诗里女中豪杰的集大成者:不屈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勇敢选择心仪之人时,她是“安巴公主”;忍辱负重、风餐露宿时,她是复仇女神“黑公主”;大仇得报之时,拎着敌人头颅,挺拔英姿又犹如“迦梨”女神附体,令敌人闻风丧胆、落荒而逃。从杀伐果决的希瓦伽米太后身上,我们又能看到“贞信”太后的影子,没有合适的王位继承人时,曾凭一己之力统治整个国家,国泰民安、富庶繁荣。除此以外,还有像“毗湿摩”一样忠心耿耿的卡塔帕,犹如“沙恭尼与难敌”附身的奸诈狡猾的巴拉父子,史诗人物的灵魂就这样鲜活地注入到电影角色当中。
歌舞段落的想象空间与叙事功能
《巴霍巴利王》上下两部在中国大陆上映时,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删减,尤其是歌舞段落。在中国观众眼里可有可无甚至略显尴尬的歌舞,却是印度电影中灵魂般的存在,是这个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国度得以紧密连接的文化认同载体。印度观众习惯在歌舞中互动、狂欢、尽情释放,获得被称为“Darshana”的宗教体验(可理解为观看者“信徒”与被观看者“神”之间的双向观看),因而歌舞也是印度人民寄托情感的重要载体。
印度的宗教与哲学倾向于将现实世界视为虚无,称作“摩耶(maya)”,中文译作“幻”,世界万物均为假象,唯有“梵”为真实存在,故而相比于注重写实,印度人民更加热爱且擅长幻想,艺术创作中也常常带有一定的魔幻风格。
《巴霍巴利王》下部中美轮美奂的天鹅船歌舞段落,应该会给中国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天鹅船腾空而起,船帆变作翅膀,在天际与云马共同驰骋时,我们为印度人民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感到惊叹的同时,也被不属于自身既有审美习惯与经验的陌生感所裹挟。
同样的情节给中印两国观众带来的观影体验大为不同。对于印度观众来说,天鹅船并非“脑洞大开”的产物,而是出自他们自幼耳熟能详的《罗摩衍那》。书中罗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战胜十首魔王罗波那救回妻子悉多,夫妻二人乘着财神俱毗罗的云车,回到了家乡阿约迪亚,而史诗中云车的造型就是能飞的天鹅,在诸多神话插图以及影视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云车的原型。罗摩和悉多被世人称为爱情的典范,而影片中也借此隐喻了王子与公主的结合像罗摩和悉多一样珠联璧合、佳偶天成。
除了拓宽想象空间,歌舞还在影片中承载了叙事功能。《巴霍巴利王》下部中被删减的一段歌舞,表面看起来是一首颂神之歌,实则是女主向男主表明心意,借“神”喻人。歌词里的克里希那是印度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之一。他的少年时代是在一个牧牛人的家里度过的,他和牧牛少女拉妲两小无猜、情投意合,给后人留下佳话。克里希那与拉妲的爱情超越了神与人的界限,是印度人心目中的“至上之爱”。
印度古典戏剧理论《舞论》中把艺术作品的“味”分为8种,首当其冲的便是“艳情味”,而“艳情味”对应的“常情”便是爱情,因而爱情是印度人格外钟爱的主题,是艺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提婆希那公主借歌词中拉妲对克里希那的爱慕之情,含情脉脉地表达了对心上人的一往情深,而王子也心领神会,遥寄相思。这首歌从情感到意境都对男女主角感情的递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删减后的版本呈现给中国观众的是公主对智勇双全、力挽狂澜拯救了自己国家的王子一见倾心,产生了突兀感,而完整版中这段歌舞做了很好的铺垫——原来公主从他还是那个“傻小子”时便已芳心暗许,从而令电影叙事节奏流畅、结构完整。
《巴霍巴利王》是印度神话史诗的现代传承,并且巧妙地融入了歌舞段落。在跨文化视角下,我们得以看清这部电影的“灵魂”。当整个世界变得更加扁平,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尤为重要,中国观众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平等的视角对待他国文化,客观看待文化多样性。加强多元文化之间的互联互通,不仅是减少文化折扣的有效手段,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