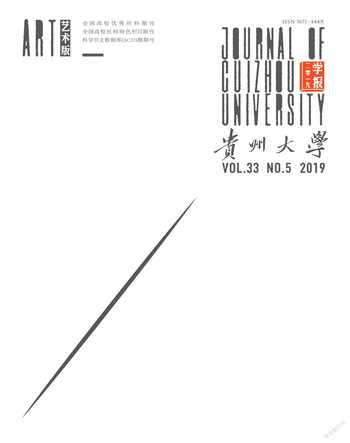台湾青春电影的散文叙事结构
2019-09-10杨欣茹
杨欣茹

摘 要:当前常用于说明台湾青春电影特征的“小清新”一词,仅能说明台湾青春电影的“视觉特征”,无法说明台湾青春电影的“叙事特征”。若试图确立台湾青春电影作为一种类型,不能仅依靠视觉一项特征,叙事结构的特征也需要有其模式。因此,文章通过分析自《蓝色大门》至《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之间多部具有代表性的台湾青春电影的叙事结构,提出台湾青春电影的典型叙事结构是“散文叙事”,而非经典的戏剧叙事结构。最后通过讨论台湾青春电影叙事的嬗变,认为台湾青春电影的叙事已发展出“前散文后戏剧”的叙事结构特征。
关键词:台湾青春电影;散文叙事;叙事结构;小清新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9)05-0018-07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9.05.004
Abstract:The current term “Xiao-Qing-Xin” (Little-fresh) is commonly used to describe the features of Taiwanese youth movies that can only illustrate their “visual features” instead of their "narrative features". If Taiwanese youth movies attempt to be defined as a genre, they should not only rely on the visual features, but also on those of narrative structure. Therefore, this essay proposes the typical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aiwanese youth movies is not the classical narrative structure of drama but “prose narrative” by analyzing several representative films, such as, Blue Gate Crossing and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Finally, it holds that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aiwanese youth movies has developed a narrative feature with “a prose style in the first half and a drama style in the second half” after discussing the evolutions of its narrative.
Key words:Taiwanese youth movie; prose narrative; narrative structure; “Xiao-Qing-Xin” (Little-fresh)
青春一直是台湾电影关注的主题之一。1980年代台湾新电影的几大代表作,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侯孝贤导演的青春成长三部曲—《风柜来的人》(1983) 、《童年往事》(1985)、《恋恋风尘》(1986),都以青少年为主角。到了1990年代,台湾电影市场趋向两极化:一边是以蔡明亮导演为代表的新新电影聚焦边缘青年走上艺术高塔,如《青少年哪咤》(1992), 另一边是以朱延平导演为首以商业为主诉求的青春偶像电影,如《七匹狼》(1989)。至此,台湾电影分裂成两边,一边是被视为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艺术电影,另一边是获得市场票房青睐,却被称为低俗肤浅的商业电影,两边泾渭分明。
进入新世纪之后,2002年导演易智言的《蓝色大门》开启了台湾青春电影的另一扇门,一扇兼容艺术与商业的大门。台湾影评人闻天祥认为《蓝色大门》为当时的台湾电影找回了与普罗观众沟通的管道。[1]《蓝色大门》从视觉风格到剧情内容都与1990年代台湾新新电影的晦涩大相径庭:《蓝色大门》在视觉风格上摆脱过去台湾电影的写实风格与浓郁色调,转而呈现唯美而明亮的暖色调、低彩度与浅景深的视觉风格;内容上以轻盈的个体为锚,书写青春期的自我成长,不论及宏大叙事。
《蓝色大门》的转向不仅被台湾观众认同喜爱,也获得艺术界的高度评价,入围全球十多个影展,一洗之前台湾电影或晦涩或低俗的两极评价分布,因而让《蓝色大门》成为一个标竿,后起之秀纷纷依循此模式企图获得市场与评价的双重青睐。此后如《蓝色大门》般的青春电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十七岁的天空》(2004) 、《盛夏光年》(2006)、《不能说的秘密》(2007)、《练习曲》(2007),2008年撼动台湾电影市场的《海角七号》,以及同年的《九降风》《渺渺》《花吃了那女孩》,2009 年《听说》《阳阳》《带我去远方》《乱青春》,2010 年《艋舺》《一页台北》《有一天》《第 36 个故事》,一部部一步步确立了《蓝色大门》以来的青春片模式。
直到2011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终于让由《蓝色大门》唤起的台湾青春电影,从小众成为大众;让《蓝色大门》那般清新唯美的画面风格以及平凡却动人的叙事,从电影边缘走向主流。
① 本文在行文中多处特意使用“新世纪以来的台湾青春电影”,而不直接使用“台湾青春电影”,是为了说明并强调本文所论的台湾青春电影的特征,都是在新世纪以后的特征,并不能简单地溯及过往的台湾青春电影的特征。也就是说,今天所谓“小清新”的台湾青春电影,实则是从《蓝色大门》开始,到《那些年》攀至巅峰。两者在视觉上或许都具备了小清新的特征,但是两者之间的叙事特征是否相近甚至相同?若不同,其嬗变又如何展开?据此,本文将分析自2002年《蓝色大门》至2011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之间的台湾青春电影,寻找新世纪之后台湾青春电影①的叙事特征。
一、“小清新”从音乐风格成为视觉特征
“小清新”已经成为台湾青春电影摘不下的标签,但是“小清新”不仅不能够等同于台湾青春电影,甚至不能概括台湾青春电影的大部分特征。“小清新”一词,仅能说明台湾青春电影的“视觉特征”。
許多研究论及“小清新”首先会论及其词源,将“小清新”指向“Indie Pop”,并认为这是一种“清新唯美、随意创作的音乐类型”[2],“之后逐渐扩散到文学、电影、摄影等各种文化艺术领域”[3]。
当前论述中,“小清新”已经成为一种惯用的词汇,它被用来描述多元的文化现象,其中之一是用来描述某一类型的电影——台湾青春电影以及像台湾青春电影的电影。然而,当“小清新”被用来表述这类电影的特征时,其实更多地偏向“视觉特征”。因为当我们试图辨识何为“小清新电影”的特征时,依旧指向“视觉特征”。这点我们可以从众多研究“小清新”电影特征的文章中发现:“小清新电影具备如下的特点 :视听语言上注重唯美造型,十分偏爱侧逆光和魔幻时间(Magic Hour)的使用,大量使用情绪性音乐”[4]。小清新电影“依照着固定的模式: 逆光、侧脸、背影、滤镜、过曝,传达着一种雾里看花的朦胧感”[5]。“‘小清新’电影的摄影风格通常‘清爽新鲜’,以天空、阳光、海等事物的色调为主”[6]。“台湾‘小清新’电影的故事背景大多设定在校园,自然唯美的影像风格和清新简单的叙事节奏,营造一种轻松、惆怅的带有梦幻色彩的青春记忆”[7]。
由上述引文可以发现,当“小清新”一词用来表述特定的电影特征时,其内涵高度统一:画面唯美是从他者次之、摄影重视光线使用、背景追求自然简朴。说明“小清新”作为一种形容电影的用法在视觉属性上具备共识。
因此,从“小清新”一词的渊源以及当下的用途,本文认为“小清新电影”更合适用来指向特定电影——如台湾青春电影——的“视觉特征”,而非“叙事特征”。小清新电影指向“视觉特征”,而非“叙事特征”的另一证据是不少被认为是“小清新电影”的文本其实在叙事结构上相去甚远,仅在视觉特征上相似。
二、“散文叙事”作为台湾青春电影的典型叙事结构“好不甘心喔,整个夏天都快过完了,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
“对啊,好像就只是跑来跑去,什么事都没有做。”
“没有赢过一场比赛,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做耶。”
“但是总是会留下一些什么吧,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蓝色大门》
《蓝色大门》的这段经典台词,似乎也正中《蓝色大门》一片的叙事核心:整部电影好像什么都没有说,就看到几个青少年在夏日里晃来晃去,但却又在每个观众心中留下了一些什么。这类不强调戏剧冲突,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腻呈现,堆叠出源于生活的体验,带出观众真切的情感,看似悠闲随性的叙事,属于“散文结构”的叙事结构。
电影叙事有六大结构:戏剧结构、诗性结构、散文结构、间离结构、套层结构及分段结构;其中戏剧结构是经典电影——剧情片最常使用的叙事结构,此结构着重戏剧冲突,讲究因果关系,包含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情节阶段。[8]305-313
然而,典型的台湾青春电影的叙事特色并不符合上述戏剧结构的描述。以《蓝色大门》为例,该片并无明确的高潮与戏剧性的冲突,而是许多琐碎的事件在生活的隙缝中断断续续、隐隐约约出现。故事从两个女主角与一个男主角的校园生活开始,结束在同一个夏天。电影中大多是平铺直叙地描绘两男一女在校园的互动,在校外的生活:两个女孩在校园上课散步聊天、放学后跟踪喜欢的男生,放假时到同学家嬉闹玩耍,让好朋友替自己送情书,情书被其他同学发现恶作剧,和喜欢的女生去海边听音乐会等等,一桩桩生活琐事的流动,完成了一部电影。
但是到了结局,真的什么都没有留下吗?骄傲的林月珍发现想要的不一定能得到;疑惑的孟克柔确定自己喜欢的是女生没有办法喜欢男生;单纯的张士豪体认到这个世界比他知道的复杂得多。这些发现、认识和体认都在闲散的叙事中娓娓道来。通过朴实无华、不强调戏剧性冲突的散文叙事结构,带给观众深深的体验与感动。
《电影学导论》一书对散文结构特征的归纳如下:
·采用呈现生活本相的多层结构,倾向于直接呈示生活的繁复流程
·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戏剧冲突,甚至没有一个始终贯穿的故事情节
·不再执着于故事的戏剧性冲突,更着意于对影片所表现的思绪的体验
·避开能够制造戏剧效果的关节点,以朴实无华的风格呈现自然的流程
·编导的主观意念显得淡而模糊,鲜明的价值判断被艺术感受所取代[8]308
综上而论,《蓝色大门》的叙事特征,符合散文结构的叙事特征:不强调戏剧冲突,甚至“避开能够制造戏剧效果的关节点”,例如易于制造高潮的闺蜜阋墙、同性出柜、异性告白、母女关系、师生暧昧等情节,导演都将之淡化处理;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戏剧冲突,而是由许多小事件累积而成;通过呈现三位主人公及周边人物的日常,缓慢地流出生活的质感、内心的成长;没有鲜明的视角,不对三位主人公的行为做出评价。
《蓝色大门》作为新世纪以来台湾青春电影的标竿,许多后来的台湾青春电影在叙事上及视觉上皆以它为模范——叙事多为“散文结构”,视觉偏好“清新”。本文试图分析与确立台湾青春电影的叙事特征为“散文结构”,因此以下论述《蓝色大门》之后的台湾青春电影是否也具备《电影学导论》一书中“散文结构”的叙事特征。
在《蓝色大门》于2002年下半年在台湾获得口碑与票房的双重青睐一年多后,出现了两部青春电影:《十七岁的天空》(2004)与《梦游夏威夷》(2004)。有趣的是《十七岁的天空》获得了当年台湾电影的最高票房,并且也引起舆论回响,但是今天讨论台湾青春电影时,很少会提到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即使具备了小清新的视觉元素:明亮的采光摄影、唯美的场景、湛蓝的泳池,但是并不具备台湾青春电影的叙事特征——散文结构。相反,这部电影恰恰是一部遵从戏剧结构的爱情喜剧。因此,它并不被视为典型的台湾青春电影。这也说明了仅仅具备清新的视觉特征无法被视为典型的台湾青春电影。
《梦游夏威夷》在气质上更接近典型的台湾青春电影。首先它在视觉上依旧毫无疑问地继承了《蓝色大门》以来的视觉特征:唯美画面、高光摄影,也进一步拓展视觉的清新感——更多的海边景色。而它在叙事上,则是偏向散文叙事的公路片结构。这部电影讲述两个年轻男孩在军中認识,而后被指派去追回一个逃兵。但是他们离开军营展开旅程后,却没有紧跟旅程的目标,反而闲散地游荡玩耍:去游乐园,去嫖妓被仙人跳,去找久未蒙面的小学同学,发现她因为联考压力太大进了精神病院,忍不下心只好把她带出来加入他们的旅程,继续去找逃兵。最后逃兵没抓成,他们都被送回了原本的地方。《梦游夏威夷》的叙事结构能够归属于公路片,但是在旅程期间主人公们闲散而漫无目的的活动,却某种程度符合了“散文叙事”的特征。
2006年,《盛夏光年》是接续《蓝色大门》后另一个台湾青春电影的代表作,它在票房上更是超越《蓝色大门》和《十七岁的天空》突破千万台币,这是新世纪之后台湾文艺片未曾出现的佳绩。《盛夏光年》是一部企图吸引年轻人的商业电影,而不是囿于自我表达的艺术电影,因为定位与立意明确,《盛夏光年》在叙事起伏上更为明确,引人入胜。然而整体而言,《盛夏光年》仍偏向散文叙事:它虽然是一个相对贯穿的故事,但在叙事过程中仍“采用呈现生活本相的多层结构,倾向于直接呈示生活的繁复流程” ;对于故事的戏剧性冲突点到为止,无论是两个男主角的情感纠结与床戏,或是三人一起回乡路上无法再粉饰太平终于开陈布公的情节,都没有陷入大撕特撕洒狗血的戏码,而是相当克制地呈现三人的状态与心境。最后的开放式结局更是把价值判断交给观众。
另一方面,《盛夏光年》被视为台湾青春电影代表作的同时,它的影像特征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小清新”的定义。“小清新”的视觉特征一是偏好高光摄影,以及暖色调和低彩度,塑造明亮而梦幻的氛围;二是较多自然场景与古老建筑,营造返朴归真的文艺气息。《盛夏光年》虽然也具备许多自然与复古场景,但是它的视觉却是冷色调与高色彩对比,然而它仍被视为是台湾青春电影的代表作之一。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典型台湾青春电影的标准,不仅在于是否具备清新的视觉特征,也在于是否具备“散文结构”的叙事特征。
2007年的《不能说的秘密》则是披着小清新的视觉,述说着一个奇幻爱情故事的经典剧情片。它有着严谨的戏剧结构,一路顺着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阶段展开,并且在高潮处(男女主角被迫分开时)进一步制造悬念,吊足观众胃口。
同年的《练习曲》(2007)无论视觉或是叙事,都具备典型台湾青春电影的特征。叙事上,《练习曲》讲述一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毅然决然背起行囊开始他的单车环岛之旅。根据题材内容可以将《练习曲》归类于公路片,故事开始于旅程,结束于旅程。但是在旅程的中间并没有明确的故事情节,没有冲突高潮,只有旅程中遇到的一个个凡人过客,一件件不大不小的故事。电影用旁观者的角度记录并呈现这七天六夜旅程的点点滴滴,也似乎让观众与主人公一起体验了这一趟洗涤心灵的旅程。叙事寡淡却余韵绕梁,符合散文结构的叙事特征。
到了2008年,撼动台湾电影市场的《海角七号》出现,同年还有《九降风》《渺渺》《花吃了那女孩》等青春电影。其中《海角七号》属于“戏剧结构”,《花吃了那女孩》属于“分段结构”。而《九降风》《渺渺》则是散文叙事结构,加上清新的影像风格,因此这两部电影被认为是标准的台湾青春电影。尤其《九降风》更是讨论台湾青春电影时不可不提的代表作之一。
《九降风》描述七个高中大男孩的学生生活,一如经典的台湾青春电影散文叙事,其中没有贯穿始终的戏剧冲突,而是由七个少年交错的误会、年少轻狂的冲动、爱情或友情的抉择、兄弟情义或自身未来的取舍交织而成。其中适合用来创造冲突的车祸桥段,也被导演平淡处理,没有激动的是非对峙,而是留下淡淡的哀愁让观众思考。
《海角七号》叙事结构则介于戏剧与散文结构之间,它具备一个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恒春海边的音乐祭要找一个当地的乐团暖场,但是它的冲突与戏剧性实则来自各个小角色的交叉互动,而非仅在于男女主角的感情线。为了能与市场观众沟通,《海角七号》加强商业电影的戏剧叙事,制造高潮,并且透露了导演的价值意念。这样的做法确实在商业上获得回响,成为台湾电影史上台片票房冠军。
2009 年开始有愈来愈多的青春电影出现在台湾电影市场上。《听说》《阳阳》《带我去远方》《乱青春》,在视觉上都具备小清新的元素。而在叙事特征上多在散文结构的基础上靠近戏剧结构,如《阳阳》《带我去远方》。《乱青春》属于诗性结构,《听说》则是在戏剧结构的爱情喜剧基础上增加散文叙事的使用,以提升《听说》一片的清新气息。
其中《阳阳》《带我去远方》偏向较典型的散文结构。《阳阳》讲述一位单亲且混血的少女迷惘的自我认同:她长着一张混血儿的脸但是她一句法语也不会说;她的继父同时是他的教练,畏惧、敬爱、嫉妒混杂;而她法律上的姐姐不仅是她田径场上的队友与对手,也在男女情感上视她为情敌;她不喜欢自己异于常人的长相,却开始做模特以此营生。她美丽的脸庞掩盖了她的灵魂,似乎没有人能认识皮囊之下的她,包括她自己。电影在一层层生活的迷惘中展开,没有一件特殊事件解决主人公的问题,冲突没有得到解决,电影就在主人公和观众交织的迷惘中结束了。由于这个故事本身就具备充分的冲突元素,因此整部影片仍然具有许多冲突节点,但是编导并没有强化冲突制造高潮。
《带我去远方》是一个小女孩和她表哥的成长故事。小女孩喜欢他的表哥,长大后才知道原来不能喜欢表哥,不只因为他们有血缘关系,更因为她察觉到表哥不喜欢女生。这一切都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慢慢流露,既然日常没有明显的冲突,就没有冲突能被解决。
总结上述对台湾青春电影的散文结构的定性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用定量的方法归纳结论(表1 ,○为显著,×为不显著,--为非特征):
从表1可知,从2002年到2009年8年的时间中,台湾青春电影的年出品量逐年增加,更重要的是,上映的15部电影中有8部属于散文结构,也就是超过半数都是散文结构的叙事,而且散文结构的比例逐年提高。
在电影的叙事惯例中,古典的戏剧结构一直都是主流的、大多数电影采用的叙事结构。因为戏剧结构不仅能够通过铺陈引人入胜,更能够运用惯例满足观众的预期快感,并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让观众获得正面的情绪。
但是从2002年到2009年,新世纪以来的台湾青春电影从开始发展到逐渐成熟的阶段,台湾青春电影的叙事结构竟以散文结构居多,颠覆了过往以戏剧结构为主的剧情片惯例,也就建立起了台湾青春电影的叙事特征——散文结构。虽然其中8/15的比例仅仅超过半数,但是其中一些采用戏剧结构的电影,也运用了散文叙事的手法,让电影呈现出来的叙事特性与典型的台湾青春电影更为相近,在制作层面,可以视为接近台湾青春电影的叙事典型,在消费层面,可以符合观众预期以提高观影快感。
综上分析,本文认为“散文结构”的叙事特征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类型惯例,成为新世纪之后台湾青春电影的叙事结构特征。
三、台湾青春电影典型叙事的嬗变:从散文叙事重回戏剧叙事的“前散文后戏剧”结构 当某些电影因为具备相近的特质,被归为一类成为类型之后,就会有从类型典型演变出来新的形式与发展的可能。“类型的成规提供了更持久的参考框架,但是它们也容纳变化。情节、人物塑造或者是每一個仿造场景的变化,都会通过引入新的因素或者越过旧的因素而改变观众对类型的期待。每一部新的类型电影由此加进了原有的类型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让制造者、放映者、买票观影者拓展了对成规原有的理解”[9]。
新世纪之后的台湾青春电影先是在《蓝色大门》的影响之下发展出“散文结构”的叙事特征,而后又在《海角七号》《艋舺》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等以观众快感为创作导向的标竿电影的影响下,展开了重回“戏剧结构”叙事的发展。
2010 年,《一页台北》《有一天》《第 36 个故事》《艋舺》相继上映。这四部电影除了《艋舺》之外,其主题都不再是以学生和校园生活为主,但是在视觉上都具备小清新的视觉特征惯例,叙事上也都非电影经典的戏剧结构,而偏向散文叙事。
由此可以发现,一方面,台湾青春电影典型的小清新视觉特征以及散文结构叙事已经扩散至非学生校园主题的电影;另一方面,学生校园主题的电影却也不再遵从小清新视觉特征以及散文结构叙事,台湾青春电影作为类型的典型特征开始嬗变。
《艋舺》一片是台湾电影市场继《海角七号》的奇迹之后,在市场上也相当成功的一部“异于”新世纪以来台湾青春电影特征的“标准青春片”。它的“标准”在于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群高中青少年的校园生活及日常生活的故事。但是它“异于”新世纪以来的台湾青春电影,在于它在视觉上并“不清新”,在叙事上也“不闲散”。《艋舺》完全是经典的戏剧结构叙事,每个情节环环相扣高潮迭起。以至于一方面根据它的类型特征很难将之列入新世纪以来“清新的”台湾青春电影之列,另一方面,它的主题内容却又是标准的关于青春的电影。
相对于《艋舺》的“异”,《海角七号》与《一页台北》《有一天》《第 36 个故事》则是另一种“异于”新世纪以来的台湾青春电影,却又时不时被纳入台湾青春电影范畴的电影。这些电影常因其美学特征——小清新视觉、散文结构叙事——而被视为台湾青春电影类型进行讨论。但是这些电影不仅题材渐渐脱离校园,更重要的是主人公都已经过青春期了,那他们能算“青春电影”吗?
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台湾青春电影作为一种类型开始出现的矛盾与问题:它究竟是根据美学特征——叙事的或视觉的,还是根据电影的题材内容而成立的类型?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而将《艋舺》《海角七号》等视为是新世纪以来台湾青春电影的类型嬗变的表现。
台湾青春电影作为一种新世纪以来的电影类型,已经开始不断地拓展其类型能涵盖的范围:首先,叙事上从散文结构的叙事特征,重回戏剧结构的古典叙事,如《艋舺》。其次,题材上从中学生的青春期,延伸到大学生甚至初出社会新鲜人的后青春期,如《海角七号》。而其中“小清新”的视觉特征则是大多数电影都持续沿用的特征,也因此使得“小清新”的视觉特征成为台湾青春电影最显著的特征。
2011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一部掀起台湾青春电影风潮的电影。如果说《海角七号》是一个凭空而降的奇迹,而《艋舺》是一个半路杀出的异数,那么《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成果。
因为在台湾青春电影的序列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不仅接续《蓝色大门》以来台湾青春电影的文本特征,更在观众接受层面上承袭《海角七号》和《艋舺》选择最大程度地面向大众。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叙事特征并非“纯散文结构”,也非“纯戏剧结构”,而是综合了两者,前半部使用散文叙事手法,后半部进入戏剧结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前半部分大量堆叠主人公们的校园生活、日常琐事、男女主角之间若有似无的暧昧与互动,散文结构的叙事手法像极了《蓝色大门》以来的校园青春电影。但是进入后半部,开始进入高潮冲突不断——两人甜蜜约会、而后却又彼此误解、第三者出现、兄弟阋墙等等,最后以成熟懂事的、好莱坞般的完美大结局收尾。
而这样“前散文后戏剧”的叙事结构也并非《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首创,这也是为什么本文认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成果”,因为可以从过去台湾青春电影发展的轨迹中找出相近的模式。如上文论及的《梦游夏威夷》《盛夏光年》《渺渺》《阳阳》等,都是在散文叙事结构中保留了戏剧的冲突,并没有特意“避开能够制造戏剧效果的关节点”,或者是具备“始终贯穿的故事情节”,虽然属于散文叙事,但并不完全符合散文结构叙事的所有特征。
《海角七号》开始使用“散文手法戏剧结构”,以求能以戏剧性吸引大众青睐,它也确实在台湾电影市场创下票房奇迹。但是《海角七号》由于在题材上并非是学生校园主题,主人公也已远离青春期,也就让它时不时面临“不是青春电影类型片”的质疑。
而一边具备小清新视觉特征、另一边使用“散文手法戏剧结构”的叙事特征,坐拥两大台湾青春电影特征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也就顺理成章地登上台湾青春电影类型的王位。
自2002年到2011年,10年的时间,一部部的青春电影,一步步确立了自《蓝色大门》以来到《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台湾青春电影作为类型的叙事特征——散文结构,与类型典型的嬗变—前散文后戏剧结构。
结 语
“台湾青春电影”常常被与“小清新”划上等号。但是,“台湾青春电影”就等于“小清新电影”吗?
当我们讨论“台湾青春电影”时,需要面对与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小清新”这个标签,是否能夠概括台湾青春电影?也就是说,当我们试图定义新世纪以来台湾青春电影的特征时,是否能以“小清新”一词涵盖这个类型的所有特征?
根据上文分析,本文认为2002年《蓝色大门》出现之后非常显著地影响了其后的台湾青春电影。而贴近《蓝色大门》特质的“小清新”一词虽然能够很好地形容新世纪以后的台湾青春电影,但仅能说明其“视觉特征”。新世纪以来台湾青春电影的叙事特征根据本文研究是从“散文结构”到“前散文后戏剧”的叙事结构。
“散文叙事”是台湾青春电影的典型叙事特征,且并不从属于“小清新”之下。因为并非所有具备“小清新”视觉风格的电影都同时具有“散文叙事”的特征,也就是说若一部电影被视为“小清新电影”,它并不一定包含“散文叙事”。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甚至是近期的《我的少女时代》(2015)。《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被视为是台湾小清新电影的代表作,但是若分析其文本的叙事结构,便能察觉其明显的“戏剧结构”。
综上所述,台湾青春电影作为一种类型,其特征可以分为三项:视觉特征——小清新;叙事特征——散文结构和嬗变后的“前散文后戏剧”结构;题材特征——青春生活。三者关系应为平行关系,而非从属关系。本文从视觉特征开始论述,进入叙事特征研究,未深入讨论题材特征。若要将“台湾青春电影”视为一种“电影类型”,对其题材特征的深度论述也是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议题。
参考文献:
[1] 闻天祥. 过影:1992-2011台湾电影总论[M]. 台北:书林出版,2012.
[2] 祝媛. 小清新电影的分类及特征分析[J]. 电影评介, 2014(03).
[3] 杜沛. 近期台湾青春片的主题与类型研究[J]. 当代电影, 2014(06).
[4] 王垚. 作为一种电影实践的“小清新”[J]. 当代电影, 2013(08).
[5] 蒋建国,化麦子. 网络“小清新”亚文化的展演与魅惑[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4(07).
[6] 汪徽. 可被设计的青春——泰国“小清新”电影研究[J]. 当代电影, 2013(08).
[7] 陈娟. 台湾新青春电影的文化身份与地域想象[J]. 当代电影, 2014(07).
[8] 陈晓云. 电影学导论[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
[9] 利萨·泰勒, 安德鲁·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M].吴靖,黄佩,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56.
(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