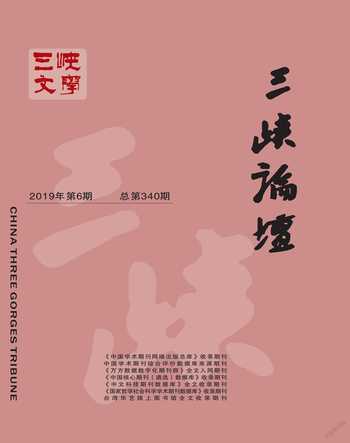塑造文化传统:华安高山族的舞蹈实践
2019-09-10董建辉林钰琼
董建辉 林钰琼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山族舞蹈逐渐被塑造为华安高山族的文化传统。其背后透露出华安高山族、文化权威及地方政府构成的权力关系,在政治经济脉络下,促使舞蹈成为一种社会记忆被标签化,也使高山族人对本民族文化呈现出多重认同感。
关键词:高山族;舞蹈;建构
中图分类号:J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6-0033-06
福建省华安县是大陆高山族的一个主要聚居地,高山族的人口数量与聚居程度在大陆高山族中均位居前列(据华安县民宗局2018年统计,全县高山族共99人)。而据《华安县少数民族族谱》记载,在华安定居的第一代高山族只有 9 位,他们多于20世纪50年代来此定居,定居原因主要有两种:从军及经商。因人口少、居住分散且多与汉族通婚,他们经历了一个在地化过程,所以其客观文化表征几乎消失殆尽,民族认同意识也随之变得薄弱。
1990 年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华安高山族中出现了明显的文化重构现象。其中,舞蹈是重构的主要对象,逐渐成为华安高山族独有的文化标签。这种文化标签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华安高山族塑造文化传统的过程中,舞蹈随着政府的介入、社会不同力量的参与,衍生出不同的意涵和变化。透过人群的交流往来、不同社会身份的个人或集体的互动,其意义在不同的情境下被生产、挪用、转达和叠加。那么,舞蹈被塑造为华安高山族的文化传统为何成为可能?尤其是,在客观文化表征几乎不存在的情境下,哪些因素在发生作用,其背后又有怎样的意涵?
一、高山族舞蹈在华安的形成
高山族舞蹈在华安县已被许多当地人认为是最有代表性的高山族文化。实际上,当地并没有这项传统。据几位年纪较大的高山族人讲述,最初移居到华安的几位一代高山族人每逢年节,都会相约到彼此家中串门,喝完酒后就开始手舞足蹈,边跳边唱。所跳的舞较为简单,只是手拉着手,和着曲调,左右踏步。至于所跳的舞有何意涵,他们却无法言清,大多觉得是节庆时的狂欢。因为他们没有参与其中,只是作为旁观者,既没有被传习舞蹈,也未被告知其中的含义。可见,第一代高山族人还保留着舞蹈习惯,但并没有延续至其后人的生活中。
不少高山族人均表示,现在所看到的由集体表演的高山族舞蹈,主要是高山族青年去外面学回来的。这里提及的“外面”,要追溯到1990年代初在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的经历。因华安县聚居有较多的高山族人口,该景区负责人于 1991 年底亲自到华安,招募了数十位高山族同胞,前往民俗村表演高山族舞蹈及其他技艺。因高山族青年从未习得舞蹈,景区所在公司专门请舞蹈老师培训他们,让他们学习老师创编的舞蹈。至于舞蹈是否真正来自台湾高山族的传统舞蹈,现已无人证实。培训结束后,他们开始在景区内为参观的游客表演。
及至1990年代中后期,華安地方政府为挖掘本地文化特色,了解到部分高山族人习得了舞蹈技能,且高山族其它客观文化表征几乎难以看到,于是便将舞蹈作为建构和发展的主要内容。当地政府召集那些跳过舞的高山族人,将他们与当地学校的一些音乐教师共同组建一支高山族舞蹈队,以便在当地官方举办的文化活动中表演。就这样,高山族青年沿用深圳民俗村高山族舞蹈表演的内容,形成了最早在当地表演的一支高山族舞蹈——《山地情歌》,意在表现高山族婚庆仪式,向观众展示高山族的文化。1998年,正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主办四年一度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漳州市需要组建一支高山族代表队参赛。因华安县高山族人数较多,居住较为集中,于是在政府的号召下,从深圳回乡的几位高山族青年被选拔到漳州市,与来自其他县的高山族人、部分艺校学生组建高山族代表队,赛前到市区艺校参加训练。
从1990年代开始,舞蹈与华安高山族人的关系变得密切。因时代不同,舞蹈不再是高山族人日常生活中的仪式行为,其内容也因新一代高山族人参加不同的活动得到拓展。虽然高山族青年也不知晓他们跳的舞蹈有何具体意涵,但在训练过程中与舞蹈老师互动,经过“身体”反复操练形成对舞蹈的记忆,扮演不同角色,逐步认识到舞蹈动作所表达的基本意象。高山族青年将习得的舞蹈及意象加以融合后,将其作为本民族的文化象征,并在地方文化活动中作为重要表演项目呈现。于是,原本是高山族人个人生活中与族人之间互动方式的舞蹈,逐转变为向他者展示本族文化的客观表征。其背后连结着人群的互动关系,也从族人之间向族外的他者进行延伸。随着展演活动的增多,高山族舞蹈的社会关注度增加的同时,其作为“高山族传统文化”的叙事呈现新的脉络。
二、塑造在地化传统:“一个民族需要特色文化”
霍布斯·鲍姆曾提到,“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 华安的案例无疑呼应了霍布斯·鲍姆的论断,在近20年的发展中,舞蹈经历了文化特质的选择、典范化展演、选取典型等不同阶段,逐渐被塑造为华安高山族的文化传统。
(一)文化特质的选择
到1990年代末,高山族舞蹈在当地演出引起不少关注,观众了解异文化的需求逐渐显现。再加上政府对挖掘高山族文化工作的推动,编创更多支高山族舞蹈成了那时的首要目标,目的是展现高山族文化特色。
于是,当地政府专门邀请富有经验的舞蹈教师(非高山族人)对舞蹈的曲目、动作、音乐等进行编排。据编舞老师回忆,由于会一些简单舞步的年长者都已去世,编舞老师只能通过多种途径获取高山族的舞蹈资源。因在大陆无法登陆台湾地区的网站,有关台湾高山族的详细讯息也无法获取,只能依靠大陆地区的搜索引擎查找资料,同时还得参考其他民族舞蹈的视频音像,查阅介绍有关高山族文化的文章,记录当下高山族人日常的生活习惯,将他们现有的生活技能转化为舞蹈动作。舞蹈表演中的音乐,则是结合之前高山族青年在外习得的一些舞蹈动作、采用的背景音乐,根据情境设计的不同,需从网络上寻找不同风格的音乐混剪,有的稍微改编在大陆知名的台湾少数民族歌手演唱的歌曲。
之后,编排者根据获取的有限资源,陆续创作出七八首舞蹈曲目,其中有《抛陀螺》、《竹竿舞》、《刺球舞》、《甩发舞》、《阿美迎宾曲》等,多是展现日常劳作的生产过程、节庆仪式及娱乐活动。以《刺球舞》为例,刺球舞系由台湾高山族社会中的猎头祭仪演变而来,以前存在于台湾高山族多个族群,如卑南人、排湾人、鲁凯人、平埔人等,有的纯用于祭祀活动;有的则具有较大的娱乐性;有的在丰年祭上举行此项活动;有的地方连妇女也参加,一边赤着脚一边唱着民谣,表现出一种轻松活泼的姿态和熟练的技巧。然而,华安高山族人从定居至今都没有举行过这种仪式,也不清楚仪式如何进行。但采借、重新编排这种源于台湾高山族生活中带有宗教性的猎头仪式,用竞争性内容以应“体育运动”的竞技主题。加上播放神秘感的音乐、穿着蛇纹服饰、头戴羽冠纹面,这些都成为区分他族风俗习惯的元素,进一步显示高山族的特色,丰富舞蹈内容的多样性。其他的舞蹈曲目在编创时也运用了相似的逻辑,运用效仿与采借的方式,拼接、杂糅不同的文化意涵,使得原本的仪式、竞技活动、生产劳作被简化成舞蹈元素搬到舞台上,作为民族文化的缩影,试图展现高山族过去的社会文化情境,强调与汉文化的差异,以此凸显本族文化的独特性。
(二)典范化的展演
舞台场域中的展演有更直观的“叙事”方式,与文本叙事不同,它涉及到舞蹈表演等多个要素。在参与观看演出中,观众可以获得不同的感官体验,感受舞蹈演出对民族文化的展示。
通常主持人会在每支舞蹈表演前简要解释舞蹈表达的意涵,让观众对该支舞蹈形成初步印象。例如,《抛陀螺》介绍词中提到:
高山族人民创造了许多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抛陀螺就是其中一项。抛陀螺在台湾俗称打干乐,是一种技巧项目,每逢丰年祭,男女青年聚集在一起,举行抛陀螺大赛,比赛场地由近及远,由低及高,难度不断加大。谁打得最准,打得最多,谁将成为高山族的英雄,族长为“最佳陀螺手”披红挂彩。大家围着篝火跳起了高山族传统舞蹈,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介绍词不乏呈现对异文化的主观描述和想象,以一段高山族的历史事实为核心,既融合了仪式、节庆、娱乐活动,又带有竞争、丰产、宗教等意涵,力图阐释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而当下高山族人透过表演舞蹈,获得了某种对历史、对文化的延续性。
文化的展示主要透过舞蹈者的身体来实现,包括高山族人在内的舞蹈者穿着民族服饰(台湾阿美人的传统服饰),女性头戴羽冠,穿着红色短袖上衣,红色围裙,腿上扎有黑色绑腿布。男性则穿红色背心,片式绑腿裤,头部用麻花状头绳装饰。结合道具的使用,表现生产生活的场景,如女性拿簸箕采茶、筛茶展现以茶叶为主的生计方式,男性用木杵向下敲击以示舂米,此外还有齐声呐喊、双手交叉排成一排左右来回踢脚、或围成圆圈一起舞蹈等。透过充满异文化色彩的情景,强化观众心中高山族的形象。此后,舞蹈者下台邀请观众一起共舞,观众可以一边模仿一边跟在舞蹈者后面试着跳过所有竹竿,其他圍观的人则拿起手机录下参与者们现学现卖的过程。短暂的互动能快速将观众带入异域的情境中,体验异文化带来的乐趣,在观众心理上造成民族意象的区分。
固定的解说方式、固定的舞蹈曲目和音乐、表演者与观众之间固定的互动,成为华安高山族舞蹈展演的模式。将高山族文化融入舞蹈中集中展示,规范了向他者输出高山族文化的具体内容,也促成了舞蹈的典范化。而主持人的简短描述,舞蹈者透过身体的展示,以及音乐的设定、服饰的穿着、营造的氛围等都不断反复呈现在观众眼前,成为一种被展示的社会记忆。
(三)典型的选取
在舞台展演的叙事脉络下,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呈现舞蹈,用最精彩的、最有特点的内容吸引观众,选取舞蹈中的“典型”变得十分重要。尤其在2008年,高山族拉手舞经当地政府申请,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高山族最具代表性的舞蹈。在之后的演出中,《拉手舞》更是作为压轴出场,并被强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特点,将其解释成高山族最为流行且象征团结的集体舞蹈。届时,台上的舞蹈者纷纷下台邀请观众,一起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圈,现场指导观众舞步。所有人跟随缓慢的节奏,变换手脚的动作,两手前后摆臂,两脚交叉移步,整个大圈顺势转动起来,将演出推向高潮。
拉手舞简单易学且参与感强烈,这种特点也使得观者将其作为文化符号,在脑海里形成固定的印象。不仅观众如此,许多媒体人也都奔着寻找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来,将其视为高山族最重要的文化象征,拍摄高山族人跳拉手舞的视频,通过网络、电视等多种渠道播出纪录片、新闻等,解说、诠释他们眼中的高山族文化,抓住社会大众对异文化的好奇心理,选择将典型又有差异的内容展现给大众,由他们的话语体系引导未能身临其境的人知晓高山族的特色舞蹈,加深对民族舞蹈的认知。
而在华安当地,一些文化教育者也有类似的作法。其中不乏有舞蹈编排者将其带进幼儿园中,作为幼儿教学的特色部分,并试图打造成该园的品牌和特色。当地县城的小学则与当地文化旅游部门联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更强调高山族舞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还专门开设高山族文化兴趣课程,邀请高山族人到学校为学生传授跳竹竿、抛陀螺的技能及拉手舞,让学生体验高山族文化。
舞蹈成为高山族文化传统,离不开多种力量的参与。在最初寻找素材时,舞蹈编排者不乏融入了对台湾高山族舞蹈的主观想象,选择一些特色元素编创舞蹈。为了吸引观者眼球,文化特质被再次具体化,从中抓取典型,制定固定的互动模式,挖掘民族文化的同时,更倾向于强调异文化带来的神秘性,与本土文化形成强烈的反差效果。观者凭借既有的标签和典型,“所见即文化”,能够快速进入到异域的、非自我文化的状态中,感受因差异带来的文化震撼。而舞蹈表演越来越频繁,舞蹈被更多当地人甚至外来者熟知时,这种文化就会被他们传播至其他场域,效仿、改编所观看的一些典型内容,并冠以高山族文化的名号,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他者对舞蹈的刻板印象。
三 舞蹈展演背后的“本相”
华安高山族人参与舞蹈表演、确定特定的舞蹈与观众互动,以及学习接受新的舞蹈内容等,这些塑造文化传统的过程是在社会中可见的,可以被大众或是表演者意识到的,就如王明珂所述的“社会表相、表征”,是具有社会性—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产生,被展示、展演在社会中,它们被社会大众感知而产生社会意义。但这些产生于背后的本相(社会现实),类似于布迪厄所讲的事实(reality),可能连结不同身份的个人及群体,从他们缔结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影响文化的发展走向,或是潜意识中对文化的认知等。
(一)舞蹈展演后面的权力结构
首先,产生这样的现象,主要牵涉到当地的权力结构与文化权威的状态。从1990年代末起,舞蹈作为呈现民族文化的形式,发展至当下被宣传为民族文化傳统,其中地方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政府依据国家制度和政策不断鼓励、支持高山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作为扶持少数民族发展项目的指标之一,向高山族提供较多资源,如召集组建舞蹈表演队,聘请舞蹈教师编排舞蹈,提供活动经费购买演出的服装道具,向参与舞蹈表演的人发放适量的酬劳补助等。这种发展策略在近年来逐渐往商品化方向发展。政府将民族文化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目标相结合,把高山族舞蹈包装成华安当地的特色文化以此转化为文化商品,吸引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从中找寻新的商机以获取区域性的经济效益。
为打造并不断丰富民族文化特色,政府在舞蹈上形成了不断“创新”的意见,并要求拓展舞蹈内容。实际上,高山族人并没有编创舞蹈的能力,只能依赖于当地文化权威。这些权威并非高山族人,他们主要受雇于政府,掌握编舞技能,能阐释舞蹈所表现的意涵。例如,当地政府会组织华安高山族人参与四年一届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作为高山族人在固定周期内参与的文化活动。因当地政府对荣誉的看重,为拿到理想的名次,舞蹈内容必须被不断创新。这也促使编舞者寻找新的资源进行创作,融入新内容于舞蹈中。但这些新的元素与内容由来自不同渠道获取的资源杂糅而成,并非全是高山族的传统,或是舞蹈原本的形态,可能会影响舞蹈变得更加异质化,展现多样意涵。
显然,地方政府集资源与权力于一身,一直在舞蹈展演甚至在高山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并连同编排者一起成为舞蹈实践中的诠释者。包括高山族人在内的舞蹈队员,只是用身体展演舞蹈。他们在舞台展演的资源获取上,不得不依赖于前两者。这三者之间形成了较为紧密的权力结构,地方政府与后两者则形成家长式的阶序关系,而这也决定了舞蹈及其代表的文化服务于政治经济的性质。即使随着政府重视高山族人传统文化的发展,而且文化权威的编创让他们有了内容可循,但高山族人并未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没有主动诠释舞蹈的意涵。依附于政府与权威的权力关系之下的高山族人,用身体展演舞蹈作为一种呈现民族文化的固定模式时,更容易传递社会记忆。
(二)社会记忆的形成
高山族最开始被社会大众熟知,应追溯到歌曲《高山青》被广为传唱的年代。这首歌后来作为大陆群众了解高山族的窗口,形成了对高山族较为固定的社会记忆。只要一提起高山族,阿里山的少男少女形象就会从大众心中被唤醒。如今,舞蹈是高山族传统文化最明显的客观表征,这一观念已经人们心中形成。而观念的产生与对社会记忆的塑造有关,尤其是当人们通过不同类型的媒介和身体行为表述的记忆在不同情境和目的下展现时。像舞台表演中主持人在表演前向观众介绍舞蹈的串讲词、演员用身体表述的舞蹈动作、舞蹈表演时播放的音乐,包括在媒体记者拍摄的影像、新闻,高山族人被采访时的言语及行为、教育者向大众普及高山族文化时所用的说辞等,这些具体的语言、文字、视频、人物形象、声音都围绕舞蹈这样一种单一固定的形式展开并被他者感知,形成他者感官上的经验记忆。
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展演,通过对“文化特质”的选择、安排、展出,来传递社会记忆。表演者将由采借、效仿而习得的舞蹈向大众展示时,大众就会将这些内容视为民族“原生态”的文化之所在,也就是“所见即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大众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最明显的,拉手舞在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后,高山族人甚至当地文化权威、政府部门,都将其标榜为高山族的文化传统,在对外宣传时更是被不断强调,久而久之成了高山族舞蹈的标签。除拉手舞之外,他如舞蹈曲目《竹竿舞》、《抛陀螺》也是如此。高山族人用身体践行特定的舞蹈、服饰、音乐、表演方式,也构成了人们了解高山族文化的模式,使得高山族人与他族的差异和独特性被不断放大。
实际上,塑造过程背后包含了一种社会现实本相,一种情境以及多层次的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往往会被社会表征掩盖。人们在追求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他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缺少认知的社会现实。即便不同身份的人,不管是展演者或观众、文化主体与客体、舞蹈的生产者与学习者,都存在一定程度对民族的想象。在此基础上,一些个体带有标签化的观念传播民族文化,使得更多人看到高山族舞蹈后,反而强化他们对舞蹈的刻板印象。在多数人的文化观念中,舞蹈表征展示了文化存在的必然性,民族作为人的集合体的存在,必然产生与之对应的文化。不管这个文化的内容为何,形式的展现是他者观看或获取信息时最直接的期望。
(三)文化主体的认同塑造
作为文化主体的高山族人,在舞蹈表演中以身体的叙述充当表演者角色。在不同情境下,表演舞蹈塑造着他们的多重认同感,使他们在建构高山族文化习性的同时,也以身体的展演被自身所记忆。正如保罗·康纳顿所言:习性记忆主要是指人们在集体纪念仪式和身体践行中展演的社会记忆。而布迪厄则指出,习性指的是一种具有持续性、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同时,习性是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生成的产物,按照历史产生的图式,产生个人的和集体的、因而是历史的实践活动。
显然,舞蹈经二十多年实践,已变成高山族历史的一部分。它联结过去的经验,确保既往经验的有效存在,这些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与各种形式规则和明确的规范相比,能更加可靠地保证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和它们历时而不变的特性。在具体的舞蹈展演中,高山族人通过身体感知舞蹈,产生舞蹈作为展演文化的思维,每个个体都获得了同样的行为图式,促进了他们保持对舞蹈同样的认同感。当高山族产生了习性后,便会指向一种实践、认识和再生产的行为,这种行为方式是无意识的、习惯性的,且能够激发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即便舞蹈内容由编排者建构,但他们通过不断练习舞蹈动作,并在展演過程中获得对舞蹈的熟练性,从而产生对舞蹈本身以及文化的习惯性。这种习惯性与实践密切相关,具有促进实践行为产生的结构功能。当然,高山族作为行为者也必须通过不断表演巩固自身的习性,促进实践行为的开展,通过具象的文化形式激发族人的文化认同,成为个体对民族精神的寄托。
近年来,高山族的文化认同感又在新的脉络中得到强化。随着海峡两岸互动日益频繁,两岸民族民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为华安高山族人习得舞蹈拓展了新渠道。2019年,当地民族宗教局更是直接邀请原住民艺术团到华安教授舞蹈。高山族人在与台湾原住民的互动教学时习得舞蹈,从中区分自身与他们之间的差异,据此来想象台湾原住民保有丰富的传统文化。于是,他们进一步向台湾原住民追溯文化传统,从地缘、族源出发连结“原生文化”,力图习得台湾原住民的舞蹈,努力寻求台湾原住民对他们的认同,来强化他们对舞蹈表演的自信,确保日后表演时传递本真的文化内涵。当然,舞蹈作为当下高山族文化内涵的重要部分,在华安高山族强调挖掘传统文化的情况下,台湾原住民的展示与教学为舞蹈重新提供了新的具象化内容。同时,如同许多歌舞所示,这是基于一种更为隐蔽的意图,即通过对实践活动的严格安排,对身体,特别是对情感的有规则支配来组织思想和启发情感。高山族人在学习台湾原住民的舞蹈内容中激发他们追求“原生文化”的精神力量,也结合个人生活经历以及对民族文化“原始、狂野”的综合想象,杂糅成自我对高山族文化的认知,并将其习得的内容作为自己的文化元素,逐渐显露民族性,以重新维系族内成员间的关系,尤其是参与舞蹈的高山族个体间的联系。
结语
1990年代末开始,舞蹈被逐渐塑造为华安高山族的文化传统。无论是地方政府运用政策支持和宣传高山族舞蹈的发展,还是地方文化精英以推广高山族文化之名强调高山族特色,或者高山族人本身参与到舞蹈表演中,以及观众透过观看舞蹈形成对高山族文化的印象与记忆,都推动着舞蹈作为高山族文化标签成为可能。若将塑造传统文化的过程放置于政治经济的脉络下,依赖舞蹈编排者与地方政府所掌握的权威和资源,将舞蹈逐渐塑造为高山族典型的文化传统,展现民族差异。但刻意标识文化上的差异,并不纯是高山族人的文化需求,更像是一种获取资源的途径,成为他们获得生存成本的关键。特别是近年来因当地发展旅游观光,舞蹈表演中包含的经济诉求被激发出来,舞蹈被展现为原始、新奇、异域的民族元素,成为观光旅游环节中的一个装饰品,不断累积经济与象征资本,却与他们的生活没有发生连结。虽然文化的价值通过货币的可取代性被转换,彰显了差异,更增加了认同的实质,但带来可能的影响是,文化主体会一直保持对政府资源的追逐和依赖。如果没有在塑造文化传统时自发地连结舞蹈之外的文化意涵,即召唤起民族甚至家庭、个人层面上的整合机制,又无法嵌入族人的日常生活,那么文化的挖掘就很容易沦为商品化过程的一个环节。日后无论舞蹈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存在还是作为族人生活习性,都可能面临不少挑战与矛盾。
注 释:
[1] 华安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华安县少数民族族谱》,2002年。
[2] 林钰琼、董建辉:《认同、想象与表达:华安高山族的文化重构》,《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7年第5期。
[3] [英]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
[4] 石奕龙:《别具一格的高山族传统体育活动——刺球》,《台声杂志》,1999年。
[5] 2019年6月田野调查期间由编舞老师提供。
[6]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
[7]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8]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
[9] 黄应贵:《族群、国家治理、与新秩序的建构:新自由主义下的族群性》,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
责任编辑:刘冰清
文字校对:向华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