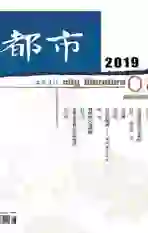原文:弟弟带刀出门
2019-09-10杨遥
杨遥
要想找到你认为美好的颜色,首先准备好纯净的白色底子。
———莱奥纳多·达·芬奇
一
弟弟第一次进货那天,家里人都早早醒了,大家蛰伏着不动,长短不均匀的呼吸声暴露了每个人都在装,大家还是装着,屋子里有一种格外的安静。一只老鼠出来悉悉索索啃东西,没有一个人呵斥。那种清醒地控制着自己装睡,比睡着难受多了。
四点半,闹钟一响,猛一下都坐了起来。彼此惊了一跳,有些尴尬。拉着灯后,屋子里由黑暗变得昏暗,像从黑夜返回到了黄昏。
弟弟匆匆吃了几口饭,急着便要走。
我看了看表,离五点还差三分钟。这时妈妈和爸爸一起说,别误了车。其实我们都知道,县里那辆去太原进货的车五点半才出发,到我们村口,最快也得用十分钟。可我心里也担心弟弟误了车。万一那辆车早早拉满人,提前出发呢?
弟弟拎起脚边的包,冲我们笑了笑说,把这个东西带上吧!说着他把一把裁纸刀放进包里。这把刀五寸左右长,刀背有牛角一样的弧度,刀刃已经磨得坑坑洼洼,黑乎乎的看不见一丝寒光。弟弟说话的时候,灯光暗黑的影子在他脸上移来移去,把他的恐惧照得一览无遗,本来为他这次出门就担忧的我更加担忧。爸爸妈妈也是满脸忧虑。在我们这里,谁没有听到过进货被抢或偷的故事?再说弟弟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太原是第一次。
临出门前,妈妈又叮嘱,钱带好了吧?弟弟摸了摸小腹下边。
出门后,我们不再提钱的事。都知道隔墙有耳。
那天有星星,我却感觉异常漆黑。平时熟悉的路变得到处都是坑坑洼洼。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拥簇着弟弟到了公路上,天仿佛更黑了,不知道是黎明前的黑暗,还是本来就更黑了。路上几乎没有车,风像一把大扫帚呼呼用劲划拉着公路,头顶上的电线呜呜叫着发出哀伤的声音。等了很久,脚麻得像两坨石头,那辆进货的车才来了。它突然就停在了我们的面前,里面的灯哗一下亮了。弟弟几乎来不及跟我们告别,就挤进了那个缓缓往开打的车门,仿佛那儿有一种神奇的吸力。车又轰鸣着发动起来往前跑去。车里的灯灭了,两个红色的尾灯也一眨眼就不见了。
我们不约而同打了个呵欠,往村子里走去。
妈妈说,弟弟从来就胆小。他小时候,我一听到有他这么大的娃娃哭,就以为弟弟被人欺负了。我眼前出现我和别人打架,弟弟躲在一边哇哇大哭的情景。爸爸说,那把刀子。唉!几只狗拼命大叫起来。
弟弟带回了如来佛、大肚弥勒佛、观音菩萨等几箱子佛像,最大的有二尺多高,最小的才五六寸。它们大多是瓷质的,有的纯白,有的象牙黄,有的白底上面点缀红色的璎珞和金色的衣服,还有一些是铜质的,沉甸甸的散发着庄严的光。除此之外,他还带回一箱子佛龛和香炉、烛签、香筒、莲花灯、木鱼等配用品,以及各式各样的香。
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后都非常惊讶。
小店卖什么东西此前我们商量过,当时主要在副食和衣服中间摇摆不定,没想到弟弟带回的是这样一批稀罕的玩意儿。当我们用征询的眼光望着弟弟时,弟弟的目光游移不定,他说,货卖独家,镇上那么多店铺还没有一家卖佛像供品的,一定賺钱。弟弟说完之后就借口累了,一头扎在炕上。我不明白为啥弟弟进回这样一批东西。爸爸说,进回些这东西,能卖了吗?妈妈盯了他一眼,朝炕那边点了点。爸爸叹了口气。
我们把佛像一件件摆上货架,惊讶地发现一种神圣的光从那些瓷质、铜质的佛像上散发出来,使这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庄严起来,不再那么窄逼、矮小。妈妈抽出一支香,对着最大的那尊观音菩萨,深深地拜了下去。
在箱子的最底部,有几本书。我拿起来翻了翻,都是经书。封面一律是黄色,开本有大有小,纸张优劣不一,字体的大小也不一样,一看就是些赠送品。然后发现了一包严严实实的东西,把包装一层一层撕开之后,是五把漂亮的刀子。它们插在精致的皮鞘里,不到一尺长,刀把上镶嵌着红色和绿色的宝石。我拿起一把,沉甸甸的。拔出刀子后,寒光闪烁,马上有一种力量从刀把上传到我手上,然后心里。摸了摸刀刃,没开刃却能感觉到锋利。我把它缓缓插回刀鞘,想起弟弟出门进货时带的那把裁纸刀,与这几把比起来,太垃圾了。
我在正面的货架上钉了一颗钉子,把其中一把刀子挂上去。看了看,觉得确实好看。
弟弟请人做了一个“佛香阁”的牌匾,与隔壁光明照相馆的牌子并排挂在一起,选了一个吉日,我们的小店开业了。
鞭炮响过之后,卫星的奶奶走了进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整张脸上,有一个突兀的大鼻子。她虔诚地双手合十,向最大的那尊观音拜了下去,然后向东边的,西边的。又有几个女人进来,差不多都四五十岁,看到这么多佛像,她们的眼睛放出光来,她们朴素灰暗的衣服随着她们眼中的光神奇地鲜亮了起来。几个提着篮子的年轻些的女人进来,瞧了一下走了。有个梳牛角辫的小女孩跑进来,问,有没有糖?又跑出去了。两个年轻人晃着膀子走进来,是卫星和“花生”,他们直奔挂着的刀子。
卫星。奶奶叫她。卫星张大嘴,有些夸张地说,是奶奶呀!顺手把刀子取了下来。多少钱?花生问。卫星你过来。奶奶说。卫星不情愿地把刀子递给花生,向奶奶走过去。奶奶把嘴凑到卫星耳朵上告诫,不要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她忘记自己耳背,声音奇怪地高而尖锐。屋子里的人都大笑起来。花生不自然地嘿嘿笑着,放下刀子,走出门去。卫星恼怒地瞪了一下奶奶,大步追去。
这个不省心的爷爷!都是叫那些勾魂鬼带坏的。卫星奶奶追着说了一句,对着最大的观音拜下去,祈祷保佑她的孙子。然后拿起一尊观音问,这尊多少钱?
到傍晚时分,请走了三尊观音菩萨,还卖了一套供器,外加十几块钱的香和纸。弟弟兴奋地算着一天的盈利。妈妈伸着细长的脖子,朝渐渐黑下来的街上张望。
两个人前后脚进了店,是看风水的“钟馗”,奶奶庙的跛子和尚。
钟馗打扮的与和尚差不多,短头发,灰色袍子,黄色的毡靴。
他与跛子两个对望了一眼,各自朝四壁的佛像望去。
看了一会儿,跛和尚朝弟弟笑笑,双手合十点点头说,阿弥陀佛。先走了。
钟馗开始说话。这是西方三圣。骑狮子的是文殊菩萨。骑白象的是普贤菩萨。这是……钟馗足足说了半个多小时,嘴角边都是白色的唾沫。
弟弟一句话也不说,认真听着。
第二天,弟弟看店时拿起了佛经。从那之后,弟弟几乎经不离手,只要店里没顾客,他就念念有词。有几次,我看见他拿着我的字典,查经书上的字。
二
小店的生意不理想。初一、十五这些日子稍好些,平时只能卖些香、纸、烛等消耗品,偶尔有人请走一尊佛像,我们都会在心里念阿弥陀佛。幸亏小店是自家的,要是别人的,可能连房租都不够。钟馗经常来,弟弟现趸现卖,与钟馗谈起佛教来,总是咳咳咳巴巴,有时说错一句话,被钟馗纠正,他脸马上就红了,双手搓来搓去,不知道搁哪儿好。
看刀子的人倒不少,除了卫星和花生,还有“大头鬼”“军长”这些家伙,他们烫着卷发或者剃着光头,没有一个和正常人一样的。每次钟馗一来,过一会儿这些家伙就来了,他们对钟馗非常客气,亲热地叫他钟馗师傅!钟馗对他们也非常客气。
钟馗看佛像,他们看刀子,两不相干。过一会儿,他们就会凑到钟馗跟前,指着一尊佛像问,这是哪位神仙?有一次花生指着文殊菩萨问,这是把孙猴子压在五行山下的如来爷爷吗?他真是威风,骑的都是狮子。弟弟忍住笑,不吭声。与这些流里流气的家伙讲话,他也磕磕巴巴老是紧张。他害怕讲错话挨打。
钟馗一走,弟弟就会很认真地拿出佛经,寻找他们刚才谈过的内容。弟弟看得很认真,半天才翻一页,有时刚翻过去,马上又折回来看,还经常在上面作记录。
那些人走后,店里会有一种奇怪的酸酸的味道,像橙子、猫尿等东西混合在一起。人们说那里面有些家伙吸毒,他们买刀子,大概为了防身。也有人说,大头鬼拿着刀子拦路抢人。弟弟听到这样的话,总是浑身不自然。把一束香点燃,插在各位佛像前的香炉里。钟馗说,众生平等,不可有妄念,妄自去猜测别人。
到一个月头上,佛像没有卖多少,刀子却卖完了。
弟弟再次去进货时,还是带了那把裁纸刀,看着这把黑乎乎的刀子,想起他卖完的那些精致的刀子,我叹了口气。
这次弟弟进回一箱子刀剑,有三尺多长的龙泉剑,一匝多长的弹簧刀,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刀、工艺刀。那时我们县里去太原进货的车都停在服装城的一个院子里,大家进上货把东西放在行李仓里,不用经过任何安全检查,换成现在,他这些刀剑大概就带不回来了。
弟弟在刀剑之外,还带回了一个小箱子,打开之后,上面放着厚厚两层书,除了有些和上次那些赠送的一样外,还有《禅灯梦影》《金刚经说什么》《中国佛教史》……我大吃一惊,想他读完这些书得花多长时间,万一他真的信佛了,怎么办?
有一天,弟弟突然宣布说他要吃素了。妈妈听到后怔了一下,问,上次咱们啥时吃的肉?十月初十,我回答。那是弟弟的生日。在我们家,一年吃肉的日子也就那么几天。过大年、七月十五、八月十五和家里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
弟弟宣布完的第二天,妈妈把菜盛好之后,弟弟端起碗来嗅了嗅,问,猪油?就重重地把碗推到一边。
又过了几天,弟弟把自己所有色彩鲜艳的衣服送了人,包括以前非常喜欢而舍不得穿的一件红色羽绒衣。
天气一天天冷下来之后,弟弟坐在门口硬椅子上阅佛经,不停地用僵硬的手指揩清鼻涕,表情肃穆。妈妈边给他缝棉衣边骂,活该!念佛机里传出“南无阿弥陀佛”的梵音,在寂寥的屋子里一遍遍庄严地回绕。
望着弟弟走火入魔的样子,我心里暗暗悲哀。觉得为了做生意没必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要是真正信,也不是非要吃素念经,像济公那样酒肉穿肠过不一样成佛?再说,弟弟的性子绵绵软软,连自己也保护不好,怎样度别人去呢?我一向瞧不起那些生活不如意就去信佛信耶稣信太上老君的人。真的,信什么,首先自己活个样子出来。
没想到,弟弟出息得很快。
有一次,看见他在店里和钟馗辩论,不高不低几句话,说得钟馗面红耳赤,浓黑的两道眉毛垂下来,要不是旁边有几个看刀子的家伙,钟馗可能撑不住马上就溜掉。还有几次,看见弟弟给卫星的大鼻子奶奶讲解她手里拿的佛经,那种认真劲儿,把我也马上吸引过去。弟弟没有因为我的加入受到丝毫干扰,他继续往下讲,卫星奶奶不时合掌点头,我心里也不由点头。慢慢地周围围了一群人,听弟弟讲。后来,庙里的跛子师傅也经常来向弟弟请教一些知识,这时弟弟眼睛里就会放出一种精锐的光,这种光只有在那种自信满满的成功人士眼中才可以看到,弟弟以前的眼神总是那么谦卑,一和人对视就躲躲闪闪。
钟馗没有把那次争论给他带来的难堪放在心上,他还经常来。经过那次争论,弟弟和他在一起小心了起来,他们都努力寻找共同的话题。钟馗一来,卫星、花生、大头鬼这些人前前后后就来了。钟馗师傅,他们说。他们有的人上次见过钟馗的尴尬,还是对他一样的尊敬。
慢慢地弟弟发现,只要钟馗在,那些买刀子的生意一般都能做成。钟馗不在,有时冒冒失失进来几个人,看看刀子,大多拔腿而走。弟弟产生一种感觉,觉得钟馗就像阎罗殿里真的钟馗一样,他一在,就把那些各种恶鬼镇压住了。钟馗还给弟弟带来另一种好处,人们找他看过风水,大多會谢土,钟馗就指点人们来店里请尊菩萨,或至少买些香烛。
一天天过去,小店的生意渐渐好了些。经常看见一些衣着和弟弟同样朴素的人呆在店里,大多是四十开外的女人,其中以老太太居多。弟弟和她们轻声慢语地交流,有时给她们朗读佛经。一群人安静围在弟弟周围,我不由想起徐悲鸿画的那幅《达摩讲经图》。这些人请的大多是观音,有的已经在店里看过几个来回,每次总要问一下自己心仪的那尊的价钱,然后选个日子请走。此后,她们会隔段时间请香,请烛,有些慢慢地会配齐香桶、烛签、香炉这些器物,有的还要莲花灯,佛龛。
也有些衣着光鲜,白脸涂着红唇的女人或戴着金项链的男人来请财神,他们大多是镇上的生意人。
我希望小店里出现一些年轻漂亮的姑娘,让弟弟感觉到生活的另一种美好。每次见到的却总是一些至少年近四十的老女人,还有那些混混。
三
逐渐地镇上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
信仰像呵欠那样传染,一有人信开,更多的人就会渐渐加入。这大概是人们怕别人信了自己没信会吃亏,万一佛爷灵验呢?就像人们看到有人在房子外边堆了一捆柴,或者在院子外面挖了一个厕所,马上其他人会跟着行动,他们认为这样的便宜不占白不占,于是我们看到很多村子的路边堆满了柴草、纸箱子、酒瓶子、烂砖头。许多村子人们的厕所在房子外边,还挂着把锁子。他们不管自家上厕所方便不方便,不管街上臭气熊天,还害怕别人随便用他们的厕所,占了他们的便宜。那些怕吃亏的人请了观音,觉得还不够,有余钱,又请如来、弥勒,害怕不够,又请财神、太上老君,他们觉得家里的神越多越好,这个不灵或许那个灵。请了神佛,他们又买香、纸、烛,害怕不供奉,神佛生气怪罪。
弟弟的生意越来越好,已能在维持开销之外,有一笔结余。他每个月进货的时候,不带那把黑乎乎的裁纸刀了。带什么,看不到。从他的神色上,知道他一定还带着刀子。那一定是一把特别小又特别锋利的刀子,它会在弟弟需要的时候,很容易地拿出来,锋利地切下对方的一根手指,或插进对方胸口中。
弟弟进的佛像越来越大,最大的一尊坐在那里几乎有我一半高,眼睛比我的都大。因为有些人买了小佛像,心里感觉不踏实,又来买大的,他们觉得大的比小的灵验些。与此相比,他进的刀子反而越来越小,有的小的像一尾鱼,握在手里根本看不到。以前用作招牌的那把刀子早已摘下了,所有的刀子摆在一个柜台里。买刀子的那些人越来越喜欢小刀子,他们喜欢把刀子握在手里、藏在口袋里,或随便掖在身上某个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一天早上,村里放羊的在村外的河滩上发现一具尸体。那具尸体紧趴在地上,几乎半个脑袋陷入满是盐碱的地里,身上的衣服七零八落,有几个刀痕。
弟弟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来找我。他说话的时候惊恐不安,嘴唇哆哆嗦嗦,一句话说得结结巴巴。他说,村外有人被杀了,凶器会不会是我卖的刀子呢?我吃了一惊,盼望杀人的刀子不是从弟弟这儿买的。为了放心,我和弟弟一起跑到河滩。那个人周围被拉起了一圈绳子,几个穿着警服的人在里面忙活。我们踮起脚尖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清那个人身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
我安慰弟弟说,你卖的刀子都是没有开刃的。
弟弟回答,万一他回去自己磨快呢?说着他手里一晃,出现一把闪亮的刀子。
我接过来打开,锋利的刀刃在阳光下闪着一团白光,像刀锋上有磁铁,把太阳吸引了过来。
你自己磨的?
嗯。
我说,首先凶手买的不一定是你的刀子,说不定还是用菜刀呢?再说,谁能证明他从你这儿买的刀子?
弟弟的脸一下变得苍白。他说,我卖刀子的时候钟馗一般都在场。他接着说,我马上去找钟馗。
弟弟匆匆忙忙走了,他灰色的影子尘埃一样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不知道万一凶手是从弟弟这儿买的刀子,弟弟会承担什么样的罪责?有些心神不安。
不知道钟馗怎样答应的弟弟?那段时间钟馗来了店里,弟弟对他好得有些过头。他坐着的话,一看见钟馗来了马上就站起来,还会用袖子把坐了半天的凳子擦一下,让给钟馗。无论钟馗说什么,他一律点头说是,还左一口、右一口钟馗大师附和。我看到弟弟的样子惊讶极了。弟弟说,第一次称呼钟馗为大师的时候,感觉脸红说不出口来,慢慢地就熟练了,像说个笑话一样。弟弟说这话时一脸轻松,看不出任何心理负担。
弟弟一人在店里时,不读佛经了。他买了一堆萝卜,用一把把刀子在萝卜上刺出各种各样的痕迹。他想判断尸体上的刀痕到底是不是自己这儿卖的刀子划的?他一天天这样徒劳地试着。那段时间,我们家吃的菜基本都是萝卜,腌萝卜、凉拌萝卜丝、炖萝卜、蒸萝卜条。弟弟不吃荤之后,我们的菜谱本来就更简单了,现在每天吃萝卜吃得反胃。
后来,案子破了没有?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亡者是个外地人,好久没有人来领尸体。反正慢慢没有人谈它了。
几年之后,镇上许多人家里有了观音。还有的作了佛堂,供奉更多的神佛。大多店铺里都供上了财神。
弟弟生意的好转引来了别人家的觊觎,有几家杂货店卖起了香烛,两家服装店里面也摆上了佛像,和性感的内裤、乳罩摆在一起,旁边是花花綠绿的衣裤、拖鞋。更有一个家伙,在破败的奶奶庙门前用床搭起了一个摊位,上面摆着各种佛像和土地、观音、太上老君,香烛黄纸,还有几把刀子,完全是照搬弟弟的店。只是他刚起步,本金薄,所有的东西都是小号的,摆在外面罩着土,看起来灰蒙蒙的。他留着鼻涕,搓着双手,脚冻得不住地跺来跺去,是弟弟的竞争对手。
弟弟的生意受到了一些影响,没有事先想的大。那些人不读书,枯燥的佛经哪里能看得进去?他们不能给顾客讲解各种神佛的职责,也讲不来佛经上那些拗口句子的意思。更没有钟馗来和他们切磋,给他们介绍生意。
那一段时期,小店里站满了神色肃穆的女人,总是以弟弟为圆心,扇子似的展开。如果弟弟点一下头,马上好几个人跟着他点头;弟弟皱眉,好几个人也跟着他皱眉。弟弟的目光带着温度一般,给这些风华不在的女人们镀上一层晚霞一样的光。
信仰方面的权威让弟弟有了一种神奇的力量。
甚至我们村那位年事已高的村长,在决定村里的几件大事前,来征求弟弟的意见。这种待遇,我们家以前从来没有享受过。
那些买刀子的人,对弟弟也仿佛像对钟馗那样尊敬了起来。他们进了店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大咧咧、咋咋呼呼,让弟弟取刀子时非常客气,有时居然用请这样的词。
有些人拿上刀子会马上离开,有些却翻来覆去挑好久。弟弟从来没有不耐烦,他把一把把刀子递上来,放下去,再拿上来。那些人挑好刀子,钟馗会代弟弟把他们送出门。这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达成的默契,弟弟帮助他们挑刀子,钟馗送他们走,仿佛里面大有深意。时间久了,弟弟发现,店里其他人多,这些人挑刀子就慢,慢到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他和钟馗。店里没有其他人,他们挑的就快,甚至随手指一把,拿上就付钱。
四
我们镇四周的山上忽然发现了铁矿。许多外地人一下涌了过来。半夜时分,经常听到载着音箱的摩托车唱着流行歌从街上驶过,间或有年轻女子的娇笑。有时听到喝醉了酒的外地人在街上大哭。他们的声音浑浊不堪,带着酒气,让整个镇子的夜发酵一样,不安,喧嚣。108国道上满是拉矿的大车。脸白肤嫩、走路一扭一摆的姑娘忽然就盛开在了路边的饭店里。
有一天,一位二十多年前被賣到我们村,孩子都在武汉上大学的四川女人忽然不见了。与她一起消失的,是住在她院里的一位技术工人。她这件事只被议论了几天,就过去了。他丈夫忽然雇了许多人,拆了以前的旧房子,起新房。村里许多人继续把自己多余的房子租给外边来的人,没有一个人引以她的事为戒。村里多了许多山南海北的人。
村子北边靠近集体坟场有块地,布满几道大沟,耕种不方便,几十年来只是一些梨树、杏树,任其开花落叶,春天秋天煞是好看。一位老板看中了那几道沟,包了下来。一座蓝色的厂房一下子从遥远的半山坡搬到了村子附近。从那之后,厂房不断从山上走下来。
村里的账务上一下出现了多年来没有见过的一大笔钱,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花,谁也想从中间得到点儿好处。于是每天开会。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党员会、村委会、支部会,一个会接另一个会。以往对村里的公共事务一点儿也不关心的人,现在也热衷于开会。甚至会议结束之后,他们还像那些吸在人身上的蚂蝗,不愿意离开,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
铁矿也给弟弟带来了好处,矿老板们喜欢大的关公、财神。弟弟把一尊尊磁的、铜的关公、财神装在纸板箱里,里面衬上泡沫塑料,外面用木架框住,运回来。它们站在店里,像一个个肃穆的真人。
忽然有一天,村边的公路陷了下去,出现一个长约七八米的大坑。在此之前,那些拉矿的大车已经把公路捣得坑坑洼洼,到处都是裂缝。这个大坑一下把那些拉矿粉的车拦住了。那天,那些被道路阻断的大车司机涌到了镇上,中午时分,每一个饭店里都挤满了人,划拳声、吵闹声震耳欲聋,吵得住在屋檐里的麻雀不敢回窝,在天空乱飞,像一片片灰色的网。整个镇子都被浓浓的酒气包围。
交通局、公路段的人都赶了过来,开会,做计划,报项目。弄好这个大坑,最少得需要半个月时间。
傍晚时分,几个老板找到了村长,把一摞钞票放在他面前,让他想办法在天亮之前把大坑填平。
村长在大喇叭里做动员,广大村民请注意,带上工具去公路上填坑,出一个劳力一晚上二百元,出一辆车……
村里许久没有见过的合作劳动的场面出现了。男人、女人都跑了出来。人们开上推土机、三轮车,推着小平车,拿着铁锹、箩筐,一起涌出来。我从来没有想到村子里有这么多的人。推土机直接开到路边地里,把青色玉米杆和土一起挖了出来,装到车上。有人抱着石头,有人从河床里装上沙子,一起往坑里填。
村长搞了一个录音机,里面不停地播放《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类的歌。村里的人尽管不是工人,听着这些歌还是很带劲。
半夜时分,村长安排人们送来了夜宵。热腾腾的面条,香喷喷的饺子。有人唱起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马上有人紧跟着唱“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
天亮时,那个巨大的坑被填满了。还在最上面铺了一层石头,里面灌了沙子、石灰、土组成的三合土,在缝隙里浇了些水泥糊糊。又把推土机、三轮车开上去压了一遍,全村的人排着队在上面踩了十来分钟。然后大家打着呵欠往家里走。
弟弟一个人落在人群后面,寻找哪里不结实。他担心大车走过来一下把路压塌,反反复复在这条新修好的路上走。
忽然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从车队的长龙里钻出来,她像在闭着眼睛走路,根本没有看见前面修好的路,顺着斜坡走向公路下边被挖得乱七八糟的庄稼地。弟弟以为自己累了一晚上,看花了眼。他继续机械地走着。猛地传来一声尖叫,弟弟醒了似的奔向发出声音的地方。女孩掉在一个大坑里,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脚,继续发出惊恐而疼痛的尖叫。这时,路上的大车发出一阵阵兴奋的喇叭声,车辆开始了流动。
弟弟趴在地上伸出手,女孩试着站了一下,又疼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弟弟没有犹豫,跳下坑里。女孩仰起头,弟弟看到一张苍白又漂亮的脸。他慌乱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伸出手想扶她起来,又不知道手往哪儿扶,赶紧缩回去。女孩呀地叫了一声!弟弟顾不得多想了,拉住她的胳膊。女孩脚一用力,又叫了起来。弟弟马上有了主意,他伏下身子,板凳一样蹲在女孩面前。女孩把双手搭在他肩膀上,女孩软软的胸脯时不时碰弟弟几下,弟弟如僵死一般不敢乱动,两个人慢慢站了起来。弟弟出了一身大汗。
仰头望,离地面还有一段距离。女孩的香气一阵阵地传到弟弟鼻子里,弟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香的女人。这种香味不同于弟弟常闻的那种点的香,它像小爪子一样把弟弟深藏在心底的欲念勾了出来。弟弟扶着女孩靠在墙上,狗一样开始拼命刨土、搬石头。很快弟弟建起了一道斜坡,他扶着女孩走上去,她的双臂能够着坑口了,弟弟用劲一托,女孩爬了上来。
这时,整个镇子陷入昏睡中。弟弟脱下外衣,站到公路中央,拼命挥舞,拦了一辆出租车,载着女孩去了县里的医院。
挂号,拍片子,女孩左脚骨折,需要住院。弟弟和女孩带的钱都不够。弟弟站在住院部门口,先是哀求医生让女孩先住院,他去取钱。被拒绝后,他开始破口大骂医院不讲人道。发觉没人理他时,他掏出了刀子,在收费处的玻璃上用劲划下去。玻璃发出刺耳的声音,里面的医生尖叫。保安过来拖走了弟弟。弟弟疯了似的,在县城的大街上疯狂地寻找熟人,人们看见他手里握着刀子,纷纷退让。后来,好不容易遇到我们村嫁到县里的一个女人,借了一千元钱。
就在女孩住进医院的第二天,村里80%的村民达成了一致意见,把村里账上的钱用来修奶奶庙。
决定好了之后,马上成立理事组。弟弟差点被选入,因年龄小,在最后一轮投票时比前面那位少了一票。
五
弟弟开始买排骨,买乌鸡,让妈妈炖成汤。每天傍晚,早早关了门,骑上摩托往医院赶。有时妈妈忙,他居然亲自动手熬汤。看着他把带着血丝的鸡块、排骨放进锅里,根本不会相信他是个不吃荤的人。为了保证味道好,他还每次舀上一勺,尝尝浓淡。
每天出发前,弟弟把脸洗干净,刷了牙,还在口袋里装一把小梳子。一天他从医院回来之后,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皮鞋。又过了一天,穿回一件黑色的立领皮夹克。他说女孩说他脖子长,穿上立领衣服好看。我们看到弟弟这样变化,暗自高兴。
白天在店里,弟弟不像以前那样总捧着一本佛经了,他经常拿着一本笑话书或讲鬼故事的书,因为女孩喜欢听笑话和鬼故事。
大约过了二十多天,弟弟忽然穿回一件红色的立领毛衣。他说女孩每天呆在医院没事干,为了感谢弟弟,给他织的。望着那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毛衣,我忽然觉得弟弟好幸福。
弟弟为了展现自己的幸福,在冷飕飕的店里故意把外边的夹克脱了,露出他的红毛衣。几个老太太看见,问弟弟,搞对象了?弟弟笑眯眯点头。
一个多月后,女孩的脚好了。她提了两瓶酒、一袋子水果,还有鲜奶、糕点到我们家里感谢弟弟。她穿着白T恤,白裤子,白风衣,说着一口漂亮的普通话,模样周正极了。我们都对她挺满意,觉得弟弟能娶上这样一个媳妇,是福气。
女孩和弟弟一起去了店里之后,妈妈开始包饺子、炸油糕,准备午饭。
到了饭点儿,迟迟不见弟弟回来。我跑去叫他。弟弟一个人气恼地用刀子消废纸板,地上已经乱七八糟一堆纸片,他手上还有一道带血的口子。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问,那个谁呢?
弟弟把刀子往地下一扔,说,我不饿。
那天,我劝了半天,弟弟也没有回家吃饭。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孩跟着弟弟去了店里,弟弟还开心地买了些瓜子、话梅、糖果。女孩帮弟弟把店里所有的东西都擦了一遍,最后抱着一尊雪白的瓷观音舍不得放下来。弟弟望着女孩说,你真像!
像啥?
观音菩萨。弟弟回答。
女孩重重地叹了口气,把观音放下。
这时,大头鬼和卫星来了。他们看见女孩,愣了一下。然后大头鬼鬼鬼祟祟捅了卫星一下,说,白牡丹!卫星走到女孩跟前,捏了捏她的屁股说,白牡丹,这段时间去哪儿逍遥快活去了?
女孩的脸一下变得刷白,白到嘴唇时那儿薄得像一层白纸,她额头上的一根青筋凸了起来,她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眼睛现出死灰色。拔腿跑出去。
弟弟趕忙追了出去,呼喊女孩。
女孩哭着说,你不要管我!
弟弟往前追着跑了几步,女孩继续往前跑,使劲大喊着别管我!她的声音像有魔力似的,路上的人们都停下来惊诧地望着弟弟。弟弟一下泄了气,抱着一根电线杆头抵在上面软软地滑了下去。
从此之后,弟弟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认真地读书念经照看小店了。他经常捧着书,半天也读不进一页,望着屋外发呆。一有女人走过来的声音,就紧张地站起来,看见不是那个女孩,就烦躁地在店里走来走去,然后去上厕所,有时连十分钟也不到,就上两趟厕所。
人们买东西时,他没有以前的那种耐心了,别人挑上几次他就不耐烦。要是人家讲价,他就生气。有一次,弟弟居然和一位顾客大吵起来。那位顾客请了一尊观音,回去之后发现底座上掉了一小块瓷片。她拿回来要求弟弟帮他换一个。以前碰上这种事,弟弟总是笑呵呵地说,没问题!那天却坚持不换,向顾客要证明,证明观音是在买以前磕的,不是买上回家路上或回了家之后磕的。那位请观音的是个烈性子的生意人,没想到弟弟会这样不讲情面。她举起观音赌誓说,谁把它磕了的谁不得好死!然后狠狠摔在地上。
那个女人回去之后,把自家店里以前卖的所有东西全部盘了出去,房屋装修一新。进回满满一屋子如来、观音、关公、财神等佛像。弟弟有的她都有,弟弟没有的她也有,包括藏传佛教里的欢喜佛、大黑天、绿度母等等。她进的货晚,都是最新的工艺,款式新颖、色彩鲜艳、釉色发亮。从她的铺子出来进了弟弟的里面,好像从现在的社会返回了以前的时代。弟弟店里也有新货,但几年下来,每次都有积压的旧货,旧货越来越多,那些新品种摆在旧货中,像春天嫩绿的树叶长在秋天的大树上,看起来非常不起眼。
女人这还不够,只要是和弟弟一样的货,她一律卖得价钱比弟弟的低。她不念佛、不读书,也不信佛教,生意却热热闹闹做了起来。
这时,奶奶庙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恢复,甚至远远超过了以前的规模。期间,理事会的人在镇上挨家挨户募捐了两次布施。人们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热情和慷慨,一百、五十、十元总要表示自己的意思。有三个矿老板,每人捐了十万。
与此同时,镇子周围到处在建天蓝色的选厂,天空像被撕成小块种植在地里。
弟弟手里总是捧着女孩喜欢的那尊观音,用一块棉布细细地擦她。那尊观音也许是被他抚摸的太多了,比其他观音更加晶莹剔透,泛着一层圣洁的光。
少了顾客的光顾,小店很快暗淡了下来。玻璃总是灰蒙蒙的,墙壁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苍蝇屎,那些货架上的佛像怎样擦洗,都散发出一种忧郁的色彩。只有钟馗还经常来,他一来,会有几个买刀子的来。弟弟的刀子越来越少,他却懒得去进货。
有一天,钟馗来了之后,卫星和大头鬼来了。这是那件事情之后,卫星和大头鬼第一次一起来店里。不知道他们是意识到了什么,还是这段时间各自有事?弟弟一看见他们,身子愤怒地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大头鬼要弟弟递一把刀子,弟弟埋下身子手伸进柜台,里面只剩下稀稀拉拉几把,弟弟却抖得不能够拿起大头鬼要的那把刀子。这时,卫星伸手去够一个木鱼,以往他对这些东西从来不感兴趣,这天不知道抽哪股筋?一不小心把弟弟放在柜台上的那尊白观音触到了地上。
弟弟听到声音,看见地上的碎瓷片,眼睛忽然红了。他猛地握住了那把刀子,直起身来,指着他们大声吼,滚!
卫星和大头鬼都愣住了!
钟馗听见吵闹走过来微笑着冲弟弟说,打碎什么东西让他们赔。
弟弟把刀子转向钟馗,大声冲他喊,我让你们滚,你们听不见?
钟馗的脸一下涨得紫红,拍了一下柜台就走了。
大头鬼的脸黑了。他一字一顿说,白—牡—丹—是—个—婊—子!
他说完,卫星又一字一顿重复说,白—牡—丹—是—个—婊—子!水—很—大!说完狠狠地朝弟弟竖了一个中指。
弟弟抱住头哇一下哭了。他边哭边用双手使劲扑拉那些碎瓷片,想把它们归拢在一起,他的手划破了,血抹的脸上也是。
第二天,弟弟把柜台里的那些刀子都收起来,装进一个黑塑料袋,扔在墙角。
六
弟弟的生意更加萧条了。他经常半上午就关了门,跑到公路上一家饭店挨着一家饭店问,你们见过白牡丹吗?
有的老板买过弟弟的财神,看见他问这个女子,十分奇怪。问,哪个白牡丹?
弟弟详细地把她的样子描述一遍,脸十分白,喜欢穿白衣服……
老板看着弟弟的脸色,小心翼翼地回答,好像几个月前见过这个漂亮姑娘,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弟弟于是满怀希望地问另一家,见过白牡丹吗?
哦,那个婊子,不知道跌哪儿去了?
这时弟弟就会痛苦地攥紧拳头,问下一家。
有时问到的是个年轻的服务员,她回话,白姐姐嘛,好久没见了。
弟弟把路上的三百多家饭店问遍,几乎大多数人知道白牡丹,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现在去了哪里?弟弟明白了白牡丹确如大头鬼他们说的那样,可是他不愿意相信,他想找到白牡丹让她亲口对他说,他们说的不是真的。
弟弟又一个一个问那些停在饭店门口的大车司机,你们见过白牡丹吗?
这次弟弟受到的侮辱比上一次更甚,有的司机直接就和弟弟描述与白牡丹在一起搞的细节,说的甚至流起了口水。
弟弟脸色苍白,但每次他都要坚持听完,然后又去找下一个人问。
人們这样说白牡丹,不仅丝毫没有打消弟弟对白牡丹的爱,还激发了他的一种强烈责任感。他想起她掉在坑里时那恐惧绝望的声音和苍白的脸,她在医院里一次次对他说,你老实,善良,和别的男人不一样。别的男人见了女人都动歪脑筋,你却。女孩握着他的手,一遍一遍回忆在那个大坑里,弟弟怎样想帮她,却一副窘相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敢扶她,不敢托她的屁股,狗一样去拼命刨土、挖石头。弟弟觉得自己就是命中拯救白牡丹的那个人。他想找到她,和她结婚。
弟弟费尽了辛苦,只听到白牡丹越来越多的风流事,却打听不到她去了哪里?他变得神情恍惚,眼睛血红,晚上整夜睡不着觉。有时半夜起来,在村外徘徊。当初白牡丹掉进的那个坑找不到了,村子外边到处都是天蓝色的厂房,连庄稼地也没了。有时他整夜在公路上奔走,试图拦住那些大车,问一下司机白牡丹在哪里?几乎没有一个司机停,都觉得他是神经病。弟弟经常在公路上走着忽然脚步就谨慎起来,他说感觉自己走在一张满是皱纹的老人的脸上,害怕把它踩出一个洞。
我们看到弟弟这样,很是担忧。
白牡丹消失之后,妈妈慢慢知道了她是个什么人,说啥也不同意弟弟和她来往。后来渐渐认了命,她现在愿意弟弟和白牡丹结婚,只要他变得正正常常的。她托人打听了许久,也没有那个女孩的半点消息。我们预感到,弟弟再也见不到白牡丹了,不知道拿他怎么办好?
有一天妈妈告诉弟弟,那家佛像店也卖刀子了。弟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半点反应,像根本没有听见。妈妈叹口气,跪在观音菩萨面前,默默流泪。
很快,钟馗出现在新开的那家佛像店了。卫星、花生、大头鬼他们这些流里流气的家伙也开始出现在那里。
几天之后,警察突然光临此店,抓了钟馗和正在交易毒品的卫星。那个店也被封了起来。
卫星的大鼻子奶奶跑到弟弟店里,劈头盖脸地骂起弟弟来。她骂弟弟是汉奸、叛徒、神经病、没头鬼。她把脸凑到弟弟面前,大鼻子几乎抵住弟弟的脸,吐沫星子喷得弟弟满脸都是。她忘了自己虔诚地信佛,弟弟曾经一字一句地给她讲解佛经。
弟弟脸色刷白,坐在那儿不停地摇头,一句话也不说。
人们传说是弟弟告的密,很久之前,钟馗就在弟弟店里卖毒品。
七八天后的一个晚上,弟弟的店里忽然冲出一阵火光。周围的邻居发现弟弟的小店着火了,赶忙打120、110。拍门喊弟弟,里面只有火噼里啪啦的声音,没有弟弟的半点动静。
人们围在外边,一桶一桶的水浇上去。上百年的老屋子,木材早已干透,那点水根本不管用。等消防车赶来时,房子只剩下一个空架子,高压水枪冲上去,轰隆一下倒下了。
弟弟回来时,消防车已经走了,废墟上冒着呛人的热气和香的味儿。妈妈一看见他,抱住就大哭起来,庆幸他不在里面,没被烧死。爸爸问他去哪儿了?弟弟没有回答,他红着眼睛冲进废墟,大声喊着,把它们弄走,把它们统统弄走!人们赶紧把他拉出来。
弟弟拼命地朝废墟摆手,仿佛想把什么东西甩掉似的,哭着大喊,我根本不想卖这些玩意儿!我第一次进货,一进铺子,后面就传来东西掉到地上的声音。那个人拿着刀子逼我买他的佛像,他拿着我的刀子啊!弟弟嚎啕大哭起来。他从来没有哭得这样憋屈,这样伤心,又这样痛快!
邻居们推来几辆平车,还有一位开来三轮车,一锹锹破瓷片被铲进车里。露出墙角的一堆东西,那是弟弟装在塑料袋里的刀子。它们融化成了一团,像正在交媾的蛇。
关于弟弟小店着火的原因,基本有两个说法,一种说弟弟发神经不想开这个店了,自己放了一把火;一种说弟弟告发了钟馗卖毒品,被吸毒的人报复了。
弟弟对这两种说法都不置可否。
事件过了一星期后,弟弟脸色苍白地出现在黑色的废墟上。他像柱子一样站在那儿,立了许久。两只麻雀飞过来,在废墟一角打闹。弟弟忽然像被惊醒了似的,猛地扑向那两只麻雀,赶走它们,自己疯狂地干了起来。他不知疲觉地干啊干啊,从早上干到中午也没有休息,叫他吃饭时,他不吃。我和爸爸去帮忙,他凶神恶煞般地朝我们喊,不用你们管!一直到天黑之后,他才踉踉跄跄地往家里走,累得仿佛随时要倒在地上。三天时间,他把一堆废墟处理干净了。然后,他处理烧焦的地面。天寒地冻,铁锹和洋镐落在地上只是一道不易觉察的痕迹,弟弟换一把凿子,像蚂蚁一样趴在上面啃着冰冷的大地。一点一点把所有烧焦的地面都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又从远处的山崖上弄来土,一点一点垫那些低下去的地方。人们不理解地问,春天来了不能干?弟弟不声不响,继续填土、夯实。
一直到了春天,一块崭新的地基出现在我们面前,谁也看不出这块地基上面的屋子被大火烧过,人们甚至已经淡忘了这块地基曾经被伤害过。弟弟请来一些工匠,在这块干净的像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地基上重建屋子。
在奶奶庙举行竣工剪彩的那天,弟弟的屋子也建好了。他请来工匠刷墙壁、割货架。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木板、刨木花、木屑的清香,弟弟发觉木头越是细小越香,它们穿过涂料那浓厚沉重的味道,清新而让人沉醉。
然后弟弟开始漆货架,他一个人仔细地漆,漆了好几天,货架都变成了纯白色。
几天之后,弟弟去进货,他穿着红毛衣、黑色皮夹克,在这已经曛暖的日子里,有些夸张,有些热。
弟弟带回一大堆东西,打开之后,全是白色的。白色的百合、菊花、牡丹、手袋、床单、珍珠、裙子、背心、袜子、瓷娃娃、白色封面的书籍、白色的茶杯、茶壶……
弟弟用白色的东西摆满了白色的货架,白色的屋子里一片雪白、银白、钛白。
弟弟把一块白色的木板挂在门楣上,上面写着“白色”两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