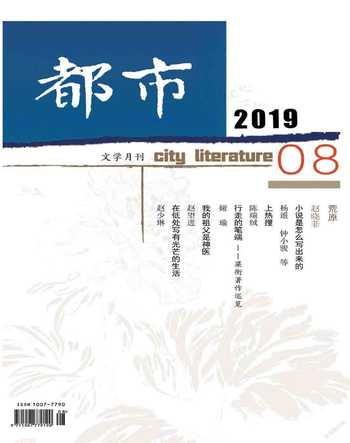对话:从核心发展出故事
2019-09-10杨遥浦歌钟小骏陈克海梁学敏
杨遥 浦歌 钟小骏 陈克海 梁学敏
浦歌:杨遥在写《弟弟带刀出门》前,跟咱们聊天时说过他设想的这个故事,后来写作过程中又有一些新的添加和设置。今天再看这篇小说,里面包含有非常好的情节设置,包括卖佛像的原因以及卖毒品两个隐蔽情节的后置使用,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和内涵。尤其是带刀出门这个意象与事实上的带刀起到的荒诞作用,像这样放在后面处理更有一些震撼的效果。
我想首先问一下,现实生活中你弟弟是个什么样的人?
杨遥:我弟弟很聪明,许多时候我觉得比我聪明。许多我搞不懂的地方问他,尤其是手工方面,他基本能解决。当年他从镇上的小学考到县里的重点初中,可惜上初中时生了一场病,病后回到学校,许多书本不见了,自己也跟不上了,读了职中,没有考上大学,在老家搞装潢,也种点儿地。他和村里人最大的不一样是特别爱看书,特别是兵器知识方面的,谈起国家国际形势滔滔不绝,但对自己的事情没有规划把握,随大流,也比较胆小,有几次机会能到北京发展,害怕失败,不敢去外边闯。
浦歌:小说里是不是可以加一些更明确的关于人物的细节特点,比如移植一些现实中弟弟的特点,这样是不是会更丰富一些?
杨遥:如果小说以塑造人物为重心,这方面加点儿笔墨,可以会更丰富些。但我写这篇小说时,主要是想讲人物内心如何战胜恐惧,慢慢成长,而且刚才讲了,我写小说更多愿意在幽微之处努力,所以没这样去考虑。
在北师大,老师讲原典阅读与研究,分析很多作家的文本,其中分析了一部小说叫《对面》。这是非常好的小说,我喜欢。里面有几个女人,一个特别喜欢吮吸大拇指,另一个喜欢吃零食,口袋里都装着零食,当时一读就记住了,但仔细分析,觉得通过这样的细节特点塑造人物,某种意义上降低了小说写作的难度。十九世纪那些现实主义大师,塑造的人物都是一笔一笔慢慢让他浮现出来的。但不得不承认,这样写效果很好,现在许多更年轻的作家,70后、80后也这样塑造人物,我以后可能会这样做,但不会每部小说的人物都这样去塑造。
浦歌:你說设定的故事核心是一个人战胜了他的恐惧,那你原先的设定里有没有一些更深的动机?
杨遥:没有,当时想的简单,只想写这样一部小说,其它的意义是写的过程中慢慢发现的。
钟小骏:你这个核心是一开始就想得很清楚的,还是在写作过程中受到已有内容影响逐渐清晰的呢?
杨遥:核心是一开始想清楚的,写作之初,就想到要表达这样的主题。但怎样能把它表达准确,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清晰的。
钟小骏:你是如何从这个核心引申出故事来的?你比如说我想写“绝望”,这是一个概念,我如何从“绝望”这个词变成故事?我很想知道那个跨过去的关键一步,你怎么就把成年人的恐惧和弟弟联系起来了?为什么就变成了这个故事?
杨遥:从核心引申出故事,得想办法让小说展开,当你清楚自己想要表达什么核心时,还需要一个核,就是故事展开的中心。心里隐隐约约有了这个核,奔着它去写,写着写着故事就出来了。因为好的核,它有扩散性。你想写“绝望”,也可以试着找个这样的核,比如什么使你绝望?自己印象中最绝望的事情是什么?找到核,去慢慢铺垫,挖掘,就形成了故事。
钟小骏:如果你刚开始是因为你父亲的那句话,想写后面这个故事,那么为什么会变成后来那个核心?那句话很有故事性,但和这个核心中间还是有跨越的。
杨遥:父亲这句话变成后来那个核心,这有个概括、归纳、推理的过程,跨过这个,有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认识。十五年前听了这句话,十五年后去写,我归纳到的就是这句话背后包含着成年人对世界的恐惧,而我作为成年人,也经常面对恐惧,便想写这样一个核心。
钟小骏:我想知道从日常生活怎么就得出了主题,我很少在写之前就有这么清晰的主题的。
杨遥:养成思考的习惯吧,事物触动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假如哪天突然感觉到某件事某个点有兴趣,就可能触动你了,必须要去想它,想背后可能隐含的东西,想着可能就会发现一个主题。
钟小骏:我现在给你五个词“毁灭、绝望、痛苦、遗憾、后悔”,理论上这五个词和“成年人的恐惧”是等价的,那你能不能把它变成小说呢?
杨遥:应该能,因为这五个词是我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每一个都有触动我的核。
钟小骏:这样的小说和你现在这篇小说区别在哪里呢?因为你这篇小说是从一句话开始的。
杨遥:触动点不一样。比如后悔,小时候孩子一哭闹,我喜欢把她抱到门外边,关上门说不要她了,孩子马上道歉,停止哭闹。当时觉得这样做很有效果,现在想起来,这样做容易造成孩子心理创伤,有些后悔。假如我以这个细节开头,写出来的小说就和《弟弟带刀出门》完全不一样。
钟小骏:这个作品你还记不记得修改过多少遍?你个人感觉你的第一段和后面一段是同一个水平吗?我感觉你的第一段比你的其他段要强好多,无论是你的语言,尤其是你的叙事节奏,一句废话都没有。
杨遥:这个小说修改不算多,我觉得第一段和后面是一致的。第一段你感觉比较好,因为每篇小说的第一段我都特别认真去写,有时一个开头想好久,所以感觉可能更好些。
钟小骏:我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改小说的,改小说会改什么?你刚才说现在回头看这个小说,有些地方你会改掉。你会压缩这个故事吗?你会改掉什么部分?那个和主人公对着干开店铺的那个女人,那个后来被举报的女人,如果你再修改,你还会给这个情节那么大比例吗?
因为就故事线条上说,我觉得白衣女子已经给了主人公足够的“改变”的能量了,为什么还要设计另外一条线,就是那条和顾客的冲突,又引入了那个开店铺的女人呢?为什么不让爆发的点就在原来那条线上?为什么不让主人公爆发在钟馗他们身上,去举报他们,为什么要弄出这个女人,举报这个女人呢?
杨遥:我改小说,一般会首先改掉小说中与整体不和谐的部分,使整部小说读起来更自然。接下来会打磨一些粗糙的地方,就好像打磨一根木头,先用六百目的砂布,再用三千目的,使它越来越光滑,呈现出事物原来有的样子,但看起来好像天然就是这样的,尽可能去除人工痕迹。
那个和主人公对着干开店铺的那个女人,在这篇小说中,是意外之笔,原先没想到,但她突然蹦出来,我很喜欢。小说出乎意料会给人带来更多惊喜。你觉得白衣女子已经给了主人公足够的“改变”的能量了,我觉得加上这个突出出来的女人更好,内因外因结合起来,更具有说服力。当然这和作者性格有关系,可能有的人不喜欢这个情节。
浦歌:《二弟的碉堡》和这个小说的情节设置有没有区别?
杨遥:区别蛮大的。《二弟的碉堡》中的人物“二弟”预先设置了一种性格,没有发展,它的情节相当于定点爆破,爆破点比较多。《弟弟带刀出门》中“弟弟”的性格是一直发展的,它的情节是集中爆炸,主要就一个点。
梁学敏:通常会有什么样的东西打动你?让你产生小说的想法。
杨遥:打动我的东西比较多,比如生活中一些异常的事情,和你关系很好的一位朋友,某一天突然不理你了;一位疯子,骑着自行车,双手大撒把,在路上大喊大叫;天气特别热等等。比如一本书。好多书读了会触动我,有的觉得有相关的经历,可以写一篇;有的觉得对方写得这么好,想模仿着写一篇;有的觉得这么好的素材,对方浪费了,自己想写出一篇更好的。比如看到某些东西,会有突兀的念头涌上来,2011年和同学去圆明园,在福海边看到那么一大片水,便想写一篇叫《在圆明园做渔夫》的小说;一次去云南参加《大家》的笔会,坐在大巴上,看到前排座位有个螺丝松了,便想写一个喜欢拧螺丝的人;在忻州的时候,看到飞机从天上飞过,觉得特别孤独,便写了《给飞机涂上颜色》。比如有些事心里过不去,便常常想把它写成小说,像借调、写材料等等。
梁学敏:你的“启动点”都有什么类型的?
杨遥:以描写场景的居多,觉得这样容易把读者带入进去。也有对话类型的,概括型的,没有总结过。
陈克海:我有两个困惑,想请教杨遥。一个就像刚刚小骏说过的那样,读开头几段,那种舒缓、自然、沉郁的情绪,节奏,非常棒。我读的时候,不免联想到赛珍珠的《大地》,哈金的《等待》。因为阅读时先入为主,带有这些参照,不免带来更多苛求,要不是刚刚听了杨遥的一番话,我还是无法带入更多的理解。一个是,写小镇信佛的整体迷狂。后面这样的叙述笔调,在余华、阎连科的某些小说中经常闪现。我想问的是,从开头的沉郁主题,突然进入笔锋一转的狂欢叙事,是提笔之前已经想好,有意设置,还是书写时的自然呈现?个人感觉,这种对众生信仰的描述,最容易简单化,少了些对他者遭遇的同情和理解,更多的好像是在反讽和鄙视。后面这样的情感,似乎与开头的纯粹旁逸。整个结构下来,就像一串珍珠,前后比例匀称,中间两颗突然变异了。
杨遥:小说有两种逻辑,一种是常情常理的逻辑,一种是反对常情常理下的另一种逻辑。我认为第一种逻辑是基础,第二种逻辑看似不符合常理,实际上更容易接近生活的真实。在这篇小说中,开始叙述是第一种逻辑,因为要把读者带入,所以舒缓、自然,进入中间部分,信仰佛教时狂欢叙事,是第二种逻辑,这种逻辑天生具有疯狂性,类似于弗洛伊德的自我和本我、超我的关系。
我还有一种看法,一篇小说像一条河流,出发时可能平缓,也可能急浚,看它中途遇到什么样的地貌。比如黄河,上游平缓,中游还有瀑布呢。这种对应是生活的真实,也可能有艺术的秘密。
对众生信仰描述的反讽和鄙视是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就如开篇对弟弟宽容的理解,其实是一样的,理解态度不同,表达方式不一样。
陈克海:再一个困惑是白牡丹的出现。在第三节,作家写到了身为哥哥的我,希望弟弟不要成天和一帮中老年妇女谈经论佛,能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出现,让弟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结果,白牡丹这样的风尘女子出现了。在作家笔下,小镇铁矿出现,自然就会有做皮肉生意的女人。只是让弟弟陡然陷入到对一个风尘女子的爱恋当中,这是不是传统小说才子佳人的套路?当然传统小说里,往往是公子落难,佳人拯救。甚至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某些小说里,也是妓女出现,主人公的灵魂得救。当然,杨遥在处理的时候,细节刻画得非常唯美,情绪铺排也合乎情理。我的困惑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究竟带给了弟弟怎样的人格成长。我想问这个白牡丹的形象,是不是这个形象有点太理想化了,好像太纯情了,如果换一种设置,比如让他和白牡丹结了婚,生活了段时间白牡丹走了,这个会不会更常情常理一些?
我在想我的局限,就像刚刚浦歌说的,读一篇小说,总是期待它会带给自己怎样的新鲜体验。是震惊,还是欣喜,这样的情绪也并不重要,就是读完了,能不能停下来,走走神,
再想一想。杨遥的这篇小说其实让我想了很多,那就是如果换作我写,该从哪里下笔,但我想了半天,也仍然毫无头绪。往抽象里说,杨遥生活的阳明堡就是一个巨大的象征和隐喻,他的众多小说似乎并不是要给人一个常情常理的理解,他在看似寻常的描述中,陡然变形。他在他打磨得像石头一样的文字中,建造了一座独属于他的城堡,凛然与他不屑为伍的现实对抗。
浦歌:刚才克海说到如果主人公他们结婚后会怎样,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在小说中,目前这个姑娘“白牡丹”更多是一个象征符号,她的离开仅仅在于卫星揭露她身份的一句话。而正是这一情节使得弟弟做出了重要改变,所以这是一个影响到整篇小说的重要细节,作为隐喻,它要牵连到整个故事的其他部分,现在这一细节感觉稍稍有点简单和单薄,因为它只涉及到最简单的道德表面。假如这里稍微再用点力,促使女孩离开的情节稍微再复杂一些,往深层稍微走一点,或再有力一点,但依然可以与“白色”隱喻相关的话,这篇小说的整体可能会更深一点。这是我的一点感受。
杨遥:白牡丹在这篇小说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她改变了故事的走向,也影响了弟弟的性格。这个人物是写作中间突然出现的,这样的人物其实在生活中很常见,或者说在我们那个小镇很常见,甚至很多人都爱穿白衣服。我经常觉得她们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员,因为生活,走上了这条路,我不敢鄙视她们,更多的是同情她们。写下这个人物时,我斟酌了很久,到底真实不真实?把自己带进去,觉得对于一个敏感的人,出卖皮肉,好不容易遇到一位真正喜欢的人,受到侮辱,出走应该是真实的。当然,如浦歌所言,白牡丹感觉稍稍有点简单和单薄,假如稍微再用点力,促使女孩离开的情节稍微再复杂一些,这篇小说的整体可能会更深一点。现在想来,确实可能,可以使白牡丹和弟弟在“我”的家人眼下多交往几次,把她性格写得再深入一些,离开的原因再复杂些,小说会更有意味。发表时没这样想,所以克海认为这个形象有些符号化,有点太理想化,太纯情了,确实是这样。假如再修改,会把这部分改一下,就像小骏刚才问的,修改什么,这也应该是修改的内容。
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局限,我也不例外,感谢朋友们提了这么多看法和意见。希望以后写出更好的阳明堡故事,也希望每位朋友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再次感谢大家!
嘉宾简介:
杨遥,2001年开始发表作品,有近200万字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等刊物,多篇作品被转载和年选收录。出版小说集《二弟的碉堡》《硬起来的刀子》《我们迅速老去》《流年》《村逝》《柔软的佛光》。曾获“山西文学优秀作品奖”“黄河优秀小说奖”“山西文学院优秀签约作家奖”“赵树理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上海文学奖”“纯小说年度金奖”等奖项。
浦歌,山西文学院第五批签约作家,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2011年起发表中短篇小说《某种回忆》《圣骡》《盲人摸象》《叔叔的河岸》《孤独是条狂叫的狗》《大鱼的模样》《狗皮》《麻雀王国》等,长篇小说《一嘴泥土》入选“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出版小说集《孤独是条狂叫的狗》。
钟小骏,作家,编剧,编辑。曾获赵树理文学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参与创作电视剧多部,电影微电影多部,广播剧舞台剧情景剧多部。偶有散文随笔评论发表。现于黄河杂志社任职。
陈克海,1982年生,湖北宣恩人。现供职于山西文学月刊社。出版有小说集《清白生活迎面扑来》《道德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