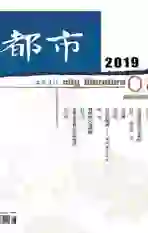我的祖父是神医
2019-09-10赵望进
赵望进
一
山西省西南部版图上,有一个临晋县。临晋县有个自然村潘家庄。潘家庄位于峨嵋嶺上,南距县城20里,西距黄河20里。这里居住着108户500多口人。在百余户居民中,没有一户姓潘。那么为何叫潘家庄?原来,500年前建村时,只有赵、畅两姓几十口人。赵姓来自距这里20多里路的赵村,提出村名叫“赵家庄”;而畅姓人口也不少,执意要以“畅家庄”为名。两姓争执不下,只好对簿公堂。
官司打到县里,潘姓县太爷听完诉讼,惊堂木一拍,只说了八个字:“就叫潘家庄吧!退堂!”就这样,村名沿用至今。至今村里仍没有一户姓潘的。
潘家庄村南有一个大池塘,下雨时全村南半部的积水都流入这里,平时供牲口饮水和妇女们洗衣服用。池边挺立着一棵四人才能合抱的大杨树,长相很怪,主干顶端有几个大而又大的树瘤,从树冠长出的分枝就插在它上面,向四面八方伸展开来。根部鼓起的树瘤更大,连成一个整体,直径两丈有余,春、夏、秋三季,人们总坐在上面乘凉聊天。杨树叶在风中哗哗作响,风大时像唱歌,风小时如私语,景色十分迷人。池东是多年堆积起来的垃圾山,以各家烧留的料炭为主,人们称这“琉璃疙瘩”为琉璃坡。
琉璃坡南部有两个神庙,一大一小。大的叫南池庙,小的叫大仙庙。
南池庙坐南向北,左边靠着池塘边,右边靠着大车路,与大仙庙相对。泥塑池神像三头六臂,高大威风,雕塑艺术相当高,特别是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好像盯着人看。谁看他,他就盯着谁。小孩子在调皮或哭闹时。大人常常这么说:“不要哭了!再哭,把你送到南池庙去!”听到这话,再哭闹的孩子也不敢吱声了。南池庙规模较大,前面连着个舞台。逢年过节常常在这里演出一些“家戏”。所谓“家戏”,就是不请剧团,由村里自乐班的人自己编导演出,有时最多请个教师(导演)来指点指点。每年春节期间,正月初三开锣,初五息鼓,总要热闹三天。我上初中时,就随着大人,登上台演过古装戏《折桂斧》、《二堂舍子》和现代戏《渔夫恨》。
大仙庙坐北向南,背靠琉璃坡,面积只有一间房大小,两层。上层供着大仙牌位,一片红布上写着一行黑字“大仙之神位”。上楼没有楼梯,要搭上木梯子才能爬上去。村里的老太太都是小脚,不敢爬梯子,只能在一层烧香叩头。这里香火很旺,许愿还愿的人川流不息,特别是九月初九大仙会那一天,人挤得满满的,想叩头都弯不下腰。
1952年夏秋之交,大仙庙发生了一件奇事,奇得怕人。连续两天,每到午夜时分,就有拳头大的一个火球从二楼出来朝南悠悠飘浮而去。越飘越远,而后裂变成三四个,慢慢消失。此情此景,第一天看到的人只有一两个。但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在全村传开了。第二天晚上,几十号人爬上琉璃坡和村里的制高处,等着奇观的出现。但直到半夜也没发现一丝丝光亮,大部分人都持着怀疑的态度各自回家睡觉了,只有十多个年轻人坚持守在那里要看个究竟。谁也没料到就在凌晨三点钟时,又出现了小火球飘悠南去。有人断言,这是大仙显灵了,说不定会给村里带来福气。也有人说,火向南飘,把福气带走了。一时间,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周围村里、乡里、县里。
县里有关部门认为这是搞迷信,很快就派人来村里了解情况。听了村民们反映,他们半信半疑,便请来了懂化学的中学老师现场考察,看有没有什么化学现象。那位南方籍的化学老师在村里住了两天,也没发现什么,从现场也找不出什么迹象,悄悄走了。
然而,在这以前的一段传言却引起了县里来调查人员的关注。
潘家庄后巷有位名叫赵森林的农民,是种瓜、务柿子的能手。他没上过几天学,大字也不识一箩筐。可是从五十多岁开始,他学会了中医针灸,治愈率和回头率颇高,特别是对小孩的常见病几乎治一个好一个。于是,在村里有人就传出了一段神话故事。说什么,一天,有位白胡子老者路过地头,吃瓜没要钱,老者从搭裢里取出三颗银针说,我是行医的,你既然不收钱,就收下我几颗针吧!以后也可用它行医治病。赵森林接过针,稀奇地捏在手里,细细端详着,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待抬起头时,那老者已无了踪影。他以后用此针给人治病,治一个好一个。
这段故事事出有因,但情节没这么离奇,连赵森林听了都感到有些玄乎。尽管他再三解释说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可是越传越神,有的人竟然说他亲眼看到的。还说,不信,你去看看,赵森林看病不就是神仙一把抓吗!
这故事已是几年前的热闹话题了。可大仙庙的奇观一出现,自然又有人把两者联系起来。土改时赵森林家定的是“富农”成份。工作组的同志一听,武断地做出结论,说什么“富农分子”赵森林在“装神弄鬼”。于是,一道命令就把赵森林传到县里,要他交代问题。
赵森林被安排住在县政府门口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民房里,每天上午被叫到卫生局问话。他脾气倔强,对“大仙显灵”的事一问三不知,并说“我根本不相信神啦鬼啦那一套,连给我先人都没有烧过几张纸。我除了种庄稼就是扎针治病救人!不信,你们到村里打听打听!”
前边赵森林被叫走,后边村农会干部和村民代表十几人就赶到县里。还有几位从荣河、万泉和永济来的病人代表也跟来了。大家围在县卫生局局长办公室,一面说明情况,一面要求放人,你一言我一语,说赵森林是“神医”,不是“神仙”,整天埋头给人看病,哪里还搞什么迷信!
局长从赵森林口里问不出什么线索,又有村干部、村民代表和病人代表赶来说情,再加上县里有的干部曾陪着家人去看过病,知道赵森林的针术,也说“不可能”。于是他果断作出决定:放人!他把赵森林叫来说,你回去仍可扎针行医,但不能在你家里,要搬到乡卫生院去。一听要去乡卫生院,赵森林急了,连连说,离开家我就不扎针了,我仍种我的庄稼。局长几次做工作,都说不服,便放他回家,由他去吧!
当天下午赵森林就回到村里,此时满院子站着来就医的病人。大家都围过来问长问短,村里人也都纷纷来家问安。他二话没说,又坐在土坑前的凳子上为病人把脉、扎针,真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二
赵森林就是我的爷爷。
我爷爷赵森林,公元1882年出生在潘家庄村。
当时,赵家的家业不算小。我老爷爷赵长喜生有三男二女,全家三代,人口最多时达到十八九口,一百多亩地,还有骡子和轿车。在兄弟姊妹五人中,我爷爷排行老大,名森林。也可能是我老爷爷喜欢树木,三个儿子的名字中就有九个“木”,而我爷爷独占五个。作为长子,他在家里干着最苦的活,扛着最重的担子。除每天干农活外,村东成行的柿子树,院房子后的一片果园,都是经他手作务起来的。尽管这样,在他父亲看来我爷爷总不顺眼,甚至被骂说“义子”,更不用说落下什么好了。俗话说“天下老偏的小”,在家里,我爷爷总是吃苦在先,而我爷爷的二弟,我的三爷总是享乐在前。
家大总得分哪,在分家时,我老爷爷的偏心眼就更加突出了。他把家业分成三份,不论人口多少每户一份。我爷爷年长,人口最多,大小八口,我三爷家只有三口人,同样是一份,而且都是好地。
如此不公平,我爷爷怒而不敢言。在以前,“严父”就是天啊!不过,我爷爷自小就有一股犟劲,有那么一种碰到南墙也不回头的坚韧精神。为了养家糊口,他在种好粮棉的同时,把很大精力投到种瓜和作务柿子树上。每年他都种二三亩瓜,是务瓜的一把好手。他经营改良的红砂瓢、“三白”等西瓜,“敬德访白袍”、“绿灯笼”等甜瓜,都是全村乃至邻村有名的。瓜熟了他装上车去卖,柿子熟了,他挑着担子去卖。日积月累,右肩膀上被压得由红变肿,由肿变青,最后竟磨出铁色老茧一层,担子压上去,不肿也不疼。记得儿时我不听话或发懒时,他总把我拉到他面前,把肩膀露出来,边让我看边拍着我屁股说:“你看看,你摸摸,这都是担子磨出来的,不受苦那能有甜,不吃苦哪能得到甜,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
三
我爷爷真是以“瓜”得福,从苦得甜,福从天降啊!
他的瓜地里搭有瓜庵———三堵一人高的土墙撑起一排短杆子,上面铺一层高粱秆,覆上一层泥巴,再盖上十几行瓦,就是一间避风挡雨的小屋子。小屋内下挖三尺,支起两片门扇作床板。粱上吊着一个钩子,挂起一个桑条编的篮子,里面放上蒸馍、咸菜和辣椒。小屋门外用蒿草和荆棘搭起一叶凉棚,棚下放一个自制的躺椅、几个小板凳和一个二尺高的小桌。桌下放一罐凉开水,桌上放一把切瓜的专用刀。这就是看瓜人的家。由于它小而且简陋,所以被称为瓜庵。
我爷爷种瓜入了迷。每年当小瓜坐胎时,他总先把瓜庵修整一番,做好了务瓜卖瓜的准备。瓜庵就是他的家。他在那里吃,在那里住,在那里奉献,在那里收获,在那里有惊天动地之举,在那里开始了他神奇的后半生。
有一年深秋,人们正在收谷子、掰玉茭。突然从高粱地窜出一只狼来,一下子把正在崖边割草的一个青年扑倒,咬着脖子拖上就要走。这个青年叫安运伙(小名伙儿),是从河南逃荒来的,在本村落了户,住在村西头。此时,看到的人们放开嗓子大喊:“狼吃人了,狼吃人了!”
我爷爷正好经过这里,听到喊声,拿起扁担一个箭步蹦上崖去。正好挡在了狼的对面。发威的狼见有人挡住去路,便红了眼,扬起尾巴想往前扑。血气方刚的我爷爷,毫不惧怕,举起扁担迎面向狼砍去。这扁担似有千钧之力,如大刀一般劈在狼的腰部。此时,饿狼又惊又怕,放下人撒腿就跑。幸好狼咬住伙儿的脖子后未来得及还口,若要还口,那人的命一定保不住了。看到伙儿的脖颈上鲜血直流,他把随身带的布巾撕开,一面包扎伤口,一面张罗人把伤者送往邻村的一位专治外科的中医大夫那里。伙儿得救了,被狼撕咬的脖子上留下一块大大的伤疤。他说我爷爷是他的救命恩人再生父母,跪在面前,一定要认做干儿子。我爷爷执意不应,拉起他说,不用了,只要你结结实实活着就好。
四
又是一个夏天,我爷爷正在瓜庵子凉棚下用桑条编箩筐,地头来了三个和尚,一位年龄较大,两位年轻。一位年轻的和尚拱手问道:“施主,买个瓜吧!”边说边向瓜庵子走来。此时赤日如火,热气蒸腾,来者满脸汗珠。我爷爷惊喜地立即站起身来迎上前去:“请,请,请各位都来凉棚下坐,这里凉快!”三位和尚来到凉棚下,他随手拉过小圈椅请年长和尚坐下,并递过一把蒲扇,随即从瓦罐里倒了一碗凉开水先递给老和尚,忙问:“各位想吃西瓜还是甜瓜?”年长者说:“就买个西瓜吧!”一个“买”字,我爷爷后来说他听起来怪刺耳,连忙说:“不用买不用买,遇见僧人吃几牙瓜,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哩,哪里还收钱!”话音还未落,他已走进瓜地,随手摘了一颗大“三白”西瓜。这“三白”西瓜,白皮、白瓤、白籽,既沙又甜,即可食用又可药用,既能切成一瓣一瓣吃又能用碗盛着一碗一碗邊吃边喝,颇受欢迎。所以我爷爷每每给它吃“偏饭”,从挖瓜窝子开始,就埋上了豆饼、豆渣或从大车轴上剥下来的残油。这样,不仅瓜秧子一出土就“与众不同”,长得旺,蔓子拉得长,瓜更长得特别大,一般都在二三十斤左右,可供四五个人吃。我爷爷抱着西瓜放在小桌子上,顺手从桌子底下拿出一柄长长的月牙形切瓜刀,“咔嚓”一声把瓜从中间切开。嚯!白瓤白籽格外引人眼球。年长和尚眼前一亮,抬起右手“阿弥陀佛!”两位小和尚也赶紧举起右手来。三位每人先吃了两三牙,而后又每人盛了一碗,连声说好。我爷爷在一旁问道:“各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位年长者说:“从陕西法门寺来,前往五台山,路过施主地头吃这么好的瓜。”临起身时年长者示意付钱,我爷爷执意不收,他说:“出家人四海为家,能吃我务作的三白瓜,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哩,钱,分文不取。饿了,我还管饭哩!”年长的和尚问:“施主贵姓?”“不敢贵姓,姓赵,就是百家姓头一个字!名字叫森林,五个木字。”年长的和尚点点头,连声道谢后又带着弟子徒步上路了。
第二年,大约还在这几天时间,三位和尚又路过地头,他们踏着瓜边的小道径直来到瓜庵前的凉棚下。我爷爷喜出望外,忙对在身旁的我叔叔赵存才说:“快跑回去给你妈说做饭!”
不一会,我叔叔提来了热好的大蒸馍、炒韭菜、辣椒、咸菜和一瓦罐萝卜丝汤。三位僧人好像在自家寺庙里,年长者边吃边说:“原本计划在北辛镇(距这里12华里)吃饭,你准备好了,就趁便吧!”他边吃边问这问那,家里几口人,几亩地,多大年纪等等。吃罢,又掏出钱来,瓜钱饭钱一块付。我爷爷忙用手挡住说:“这是咱们的缘分,钱买不到啊!”
说来真巧,第三年还是这几天,赤日炎炎,蝉声阵阵,这三位僧人又来到瓜地凉棚下。吃过午饭,年长的和尚意味深长地对我爷爷说:“施主,连续三年打扰你,你善心一片,实为感人!没什么东西谢你,就送你几苗针吧,以后有机会学学扎针治病!”说着把五苗针放在我爷爷的手心。一苗较长的是银针,丁字形状,四苗稍短一些的像普通妇女做活的针,只不过在针眼上缠绕了一些铜丝便于手拿。
说来也巧,那年秋天,从河南来了一位郎中。他辗转在我们乡一带的十里八村针灸行医,为孩子们种牛痘,走到哪吃到哪,晚上就住到哪。一天,来我们村给孩子们种完牛痘,天黑了就在我家吃饭,夜里就同我爷爷睡在槽头的土炕上。我爷爷热情好客,特别是对出门在外的下苦人多加关照。他同河南的郎中年龄相差不到十岁,两人一见如故,以兄长相待。晚上,他们相对聊天,只有微弱的豆油灯相伴。灯花拨了一遍又一遍,牲口的草料添了一茬又一茬,他们仍未入睡,直拉呱到深夜。
第二天晚上,河南郎中又投宿我家,仍然同我爷爷住在槽头的土炕上。一连住了好几天,即便就是在邻村行医,到晚上也赶过来,好像我家就是他家。一天晚上,那郎中摆弄他的针灸工具,给几苗针尾上缠细铜丝。我爷爷见状恍然大悟,忙说:“我也有几苗针!”郎中说:“拿出来我看看。”我爷爷拿出藏了几个月的针,述说了针的来历。郎中听后大为震惊!连连说:“兄弟,这是神人点化你,给你送福来了!”郎中仔细端详了那几苗针,对那丁字形的银针赞叹不已:“这针是银针,神针啊,是扎火针用的。”我小时候是常见这银针的,有大约三寸长,针尾为丁字状,看起来非常别致。“郎中是位热心肠人,拍着我爷爷的肩膀说:“兄弟,我教你,教你找穴位、扎针!”那郎中医道很广,特别给小孩诊治是手到病除。从此以后,他们晚上在槽头不是闲扯了,而是手把手地教授针灸,行针、起针,让他亲自体验针灸的神奇。也可能是天意和缘分吧,我爷爷竟通此道,很快就把穴位记清楚了,位置也找得很准。他常在自己身上用指甲寻压穴位,用做针线活的针在自己的棉衣棉裤上试扎。时间不长,就初步掌握了给小孩治病的医术。
我爷爷给小孩看病确实有些绝招。每有大人抱着小孩来,他先把孩子的大拇指和食指掰开,在自己右手大拇指舔点唾液,轻轻地在孩子虎口上擦一擦,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手上淡淡的青筋,从筋的发青程度便可看清孩子的病症———是伤风还是吃得不合适了,然后对症下针,扎得孩子哇哇直哭,据说这哭声也可减轻孩子的病情。他用针刺着不同的穴位,四五次就可见好了。每天都有三五个孩子来扎针治病,后来竟越来越多。先是本村的,再是邻村的,一传十,十传百,一年多以后,每天总有十多个孩子来就诊,往往看一个好一个。孩子是父母心头上的肉,孩子没病更是父母的福气。看到孩子病情很快好转,有人就惊叹:“真是神仙一把抓啊!”这样说当然是对我爷爷最高的赞誉,说得人多了,本村有些好事的人就把此话与瓜地里僧人赠针的事联系了起来,演绎出一段神奇的故事。
这件事添油加醋,越编越神,越传越远,来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我爷爷看病从不收一分钱,完全义务。这恐怕也是病人多的一个重要原因。说来也怪,慢慢的,日积月累,我爷爷的医术越来越高,竟然能给成人针灸了,而且每见成效。因他医病分文不取,病人来时或带五颗自家鸡下的蛋(这是多数),或带三个油酥火烧,或带两个自家蒸的大花馍,有讲究的人带一封南式点心或一小包水果糖。当然也有些人什么也不带的。每天桌子上堆得满满的,巷子里谁家的孩子哭闹,大人常说:“不要哭,去先生家给你取个好吃的!”说罢抱着孩子从我家桌上拿一个油酥火烧塞到孩子口里。
五
正当我爷爷医术开始“走红”之日,也是他开始遇到一生最麻烦之时。1947年,晋南一带开始土地改革,极“左”风盛行。前面曾提到,我爷爷的父亲在分家时一味“偏小”,我爷爷分到土地和房产等相对少得多。他的小弟分到的财产多得多,但却染上了吸大烟之恶习,毒瘾发作时,谁也挡不住,他不顾一切卖房卖地,连墙上挂物什的钉子都以废铁卖了。农民凭的爱的就是土地。看到自己曾精耕过的土地被亲弟弟一亩一亩地廉价卖了,我爷爷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当时,卖瓜卖柿子挣了几个钱,卖鸡蛋挣了几个钱,在陕西渭南熬“相公”的两个儿子挣了几个钱,这些钱加起来还是个不小的数字。我爷爷把这些钱集中起来,他弟弟賣一亩地,他就买一亩地,这样一卖一买,我三爷把地全卖光了,我爷爷把地置办了上百亩。
土地改革时,我父辈弟兄四人还没有分家。全家共十六口人,为全村家户人口最多的,也是全村唯一超过百亩土地的人家。
当时,村农会主席就是我爷爷从狼口里救下的安运伙。他感激我爷爷的救命之恩,没做成干儿子,但两家来往比普通亲戚还要密,更与我的父辈们以兄弟相称。
一天,安运伙找到我叔父赵存才说:“兄弟,土改工作员进村后,没有找到一户富农,咱赵家家大地多,先顶上一个富农吧。”我叔父当时血气方刚,好胜心强,根本不知道“富农”是干什么的,戴上这个帽子是好还是坏,便顺口答应了。
“富农分子”的帽子很自然的首先戴到我爷爷头上,因为他是户主。按说,富农必须有大量的土地和房屋,雇有长工,有放高利贷等剥削行为。可我家按本村当时每人平均六亩地计算,仅超出了十二亩。家里未雇过长工,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是我们家一远房亲戚遗留的孤儿,无依无靠,我爷爷收养下的,管吃管穿管一切。后来工作员就把这个孤儿算作长工。
当时,我年仅七岁,是小学一年级学生。一天下午,村里要开诉苦会,要求学生也得参加,地点就在学校里,一年级小娃娃坐在前排。在被批斗的地主富农分子中就有我爷爷。
主持诉苦的是驻村姓王的工作员,人称“王工作”。“王工作”高个子,长得很气派,坐在一张桌子旁,显得格外神气,给人以“鹤立鸡群”的感觉。他宣布:“把富农分子赵森林带上来!”我爷爷被两名农会干部带到正中间立定。他又放大嗓子说:“现在诉苦开始,先由长工尚存喜诉苦!”话音刚落,农会干部从人群中叫起一位青年,这位青年二十来岁,穿着白布上衣,黑色裤子和一双半新的布鞋,虽然均为粗布,但无一补丁,打扮得很是精干。这位就是我家抚养的远房亲戚的孤儿。小伙子迟迟不往前走,表现出满脸的无奈。主持人有点着急,大声说:“前面站,有什么苦,尽管控诉!”小伙子站在我爷爷面前,满脸涨红,半天蹦出几个字:“说实话,多亏我伯,没有我伯,我还不知道死到哪答了!”话音未落,就放声哭了起来。见状,“王工作”大失所望,大声叫到:“下去!”第二个诉苦的是我爷爷的亲弟弟,我的三爷赵生林。他个子低,身材胖,站在距我爷爷两三米远的地方,不往前走,也不发声。我爷爷一见他早就气不打一处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两人迎面对视,全场鸦雀无声。还是我爷爷先开口:“你诉呀,诉么!”我三爷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一步也不动。“王工作”催着说:“快说哇!快说!”我三爷在催督下,一边举右手一边竟说:“我真真想打你一耳巴!”我爷爷紧接住话茬说:“你来,打啊!”谁知他弟弟言不由衷,边说边后退了好几步!这时,全场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笑声中还夹杂着一些鄙视的眼神。在这种尴尬场面中,“王工作”立即收场,并大声嚷道:“把这个铁嘴老汉拉下去!”我爷爷被簇拥着出了会场。从此以后农会再也没有组织过穷人诉我家的苦,也没有找我爷爷参加什么批斗会。我爷爷仍每天以针行医,患者越来越多,“王工作”还介绍过不少病人呢。“王工作”包着我们村,一连四五年。我上三年级时,他竟天天跟着我写毛笔字,直到我大学毕业,他当了县城建局长,我们还打过几次交道。
六
我爷爷针灸大走红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那时,我上小学,除我伯父和我父亲在陕西外,在家里我三叔存才和我堂兄望虎扛着庄稼活,我母亲妯娌三人也似男劳力一样,农忙时下地,农闲时纺线织布、经营孩子,我的两个妹妹和几个堂妹年龄尚小,多数还在哺乳期或刚会跑,只有当家长的奶奶可以偶尔照料一下爷爷。
来家里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我爷爷埋头坐在一条长木板凳上,只知诊断扎针,往往都顾不上喝水。屋子里挤满了人,不时有人因先后而争吵。无人维护秩序,光线又暗,总得想个办法。我奶奶的外孙女、我的表姐侯飘洒长我一岁,又不曾上学,因姊妹太多,家境困难,常在外婆家居住。我奶奶就让她管理病人排队。她削了一把竹签,上面写上一、二、三……发给病人按号排队,秩序好得多了,一天可看四五十人。
我们家门口有一棵两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槐树,枝叶伸展出去,庇荫了大半个院子。树上有五六个喜鹊窝,从早晨到黄昏喜鹊叫个不停,来就医的人往往在槐荫下乘凉等候。人们说这是一棵神槐,它满身都是福气。
一天早晨,我爷爷刚开大门,门口站着一位干部模样的男子,两手不停比划,但说不出话来,急得弯腰就在地上用手指写划:“我说不出话。”后边跟着的家人忙说:“他开着会,半截就不会说话了。”我爷爷扶起那人说:“不用写了,你这是中风不语!”
原来,这位干部在猗氏县工作,开会发言中间突然不会说话了,在运城一家医院看了十来天,没有效果,才慕名而来的。他住在乡卫生院里,每天来我家扎针一次,连续七天,竟然叫出声来,会说话了。他激动地说,第七天上他感到有一块东西咽了下去,随之便叫出声来。他跪在我爷爷面前,要认做干儿子。我爷爷说:“会说话就好,不用认干儿子了。要认可多啦,咱不兴这。”这位干部要给钱,我爷爷分文不收,依然谢绝!实在过意不去,后来他扯了三丈蓝“洋布”送来表示感谢。
这消息不胫而走,传播很快。猗氏县一位副县长知道了。他的女儿已经六岁了还不会说话。他和夫人坐着马车带着女儿来到我家。我爷爷经过详细询问,简单检查,发现孩子耳朵实聋,舌头又短,全是胎带。他对副县长说:“她这哑巴是胎带的,天生的,无法看,也看不好。”
看好哑巴和看不了哑巴的事实都极具有说服力,既说明大夫针术确实高明,也说明他行医实事求是,不是胡吹乱骗人。这引起了乡卫生院的重视,他们也不断给介绍一些疑难病人。
大概是1953年的一天,乡卫生院副院长,当地有名的西医大夫侯吉昌,亲自领着一位病人上门。这位病人是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前线作战时,在巨响的大炮声中,震聋了耳朵,听不见了也说不出话了。经我爷爷多次针刺,能听见了,也可以低声说话了。
“志愿军会说话了”的消息再次不胫而走,引起震动。首先被震动的是卫生院,卫生院院长侯吉易激动地说一位没有行医证的“土大夫”竟能看好这么难的病,真不可理解。那位志愿军战士听说爷爷没有“行医证”,就亲自跑到县卫生局,说明情况,给爷爷办下了一纸《行医证》,并送到我爷爷手里。从此,有了合法手续,我爷爷更“红”了。
中医的针灸是非常神奇的。我爷爷用的针并非现在细长的专用针,也不像现在扎得那么深,而是像做针线活那样的针,只扎在表皮神经上。行针时不是单一的一根针一根针捻动,而常常一手按在穴位附近,一手活动患者的肢体,使一排针同时摆动。当时有很多医生对他的针法不解,好几位就装作患者套他的手法,但总疑惑迷茫,难得其法。
我爷爷不仅针灸好了哑巴,也治愈了不少疑难病和常见病。如癫痫、腰腿痛、腹泻、胃痉挛、气蒙眼、神经病,甚至保胎、治疗习惯性流产也可以一针见效。
来我家就诊的患者越来越多,不仅有本地临晋县的,而且有邻县荣河、万泉、永济、猗氏、河津的。一般情况下当天是不容易排上队的。于是我们家门口两旁的巷道里便搭起篷布摆起了小摊,有卖凉粉的,卖醪糟荷包鸡蛋的,还有炸油糕的;于是,村里有多余房子的人家也开起了简易旅馆,每晚每人收一毛钱;于是,村里还有人赶起了铁脚轿车,送走一车病人再接来一车病人,来回拉客,忙碌得很。毫不夸张地说,村里每天像赶会一样。我家里常常挤满了人,有的病人竟说什么在我家院子里走了一圈腿不疼了,还有的说吃了我家一块馍喝了我家一杯水,肚子不疼了。这些纯属妄言,纯粹胡说,可是却苦了我的堂兄赵望虎了。我们村处于峨嵋岭上,水井五十丈深处才能见水。每次绞水都要四五个人或七八个人联合行动,一个上午下来,每人才能分得两担,也就是说四桶。当地有个说法,宁让你吃块馍也不让你喝口水。确实滴水贵如油啊!就是我堂兄天天忙在井上也供不起那么多病人喝水,无奈只好将放水瓮的厨房上了锁。我们家有个规矩,就是家有满囤的小麦,每年秋后到一冬主食都必加粗粮,多是回茬谷子磨成面蒸的谷面窝窝,有白面也是与谷面分层蒸的二面花卷。我常常拿着谷面窝窝边走边吃。一次,有人细声说,那就是先生的孙子。话音刚落,就有一位病人跑过来夺走我手里的谷面窝窝,塞给我一个白面馍。我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拿在手里不敢吃也不敢扔。旁边有几位本村的长辈笑着对我说:“快吃去吧,他们是想治病哩!”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能遇到。母亲知道后训我说:“不能占人家的便宜,白面馍越吃越馋,越吃越懒!”从此后我再不敢拿着谷面窝窝边走边吃,就是有人把雪白的馍馍递在我嘴里也不敢乱吃了。
我虽然害怕扎针,但愿看爷爷给病人扎针。上小学时,每天下学后,站在爷爷的身后,看他如何把脉、问诊、扎针和行针,常常忘了上学。日久天长了也记住了我爷爷对几种病的疗法,略举几例:
癫痫病俗称羊羔疯。病人发作后会瞬间倒地,口吐白沫,浑身发抖,往往牙齿紧咬,发出吱吱响声。我爷爷治疗时,让病人脸朝上躺着,人中扎一针,十个指尖上各扎一针,然后,脱掉病人的鞋和袜子,亮出脚心,用病人的鞋底在他的脚心击打,不一会病人就清醒了过来。
淋巴结往往出现在脖项,手摸时滚动,我们那里人俗稱其为“耍核”,就是像滚动的杏核一样。我以为这就是医学上叫的“结节”。我爷爷在治疗时先用金戒指把“结节”套住,让一个人用手按紧,他在丁字形银针尖缠点棉花,蘸点灯油点燃,待银针尾端烫得手捏不住时,针尖上有点发红。说时迟那时快,他迅疾将针尖向“结节”中心刺去,这样两三次,“结节”就消失了。他说,用金戒指压住它就不会动了,用火针扎几次就把它“气死”了。
有的病人胳膊疼得动不了,我爷爷用十几支针从肩上的宣井穴扎起,每一寸一针,一直扎到手腕或手指处,而后不断行针,除一针一针轻捻外,他一手按患者肩头,一手捏着患者的手指慢慢摇动,扎在胳膊上的针随之一起同一方向摆动,然后让患者试着上举,一次举一点儿,一次比一次举得高。这样处置六七次,胳膊便慢慢举了起来。
我爷爷擅长医治的病症很多很多,我知道的却很少很少。上面举的只是我亲眼看到而且一直记在脑子里的几例。
我爷爷生活非常单调,早上起来吃两个荷包鸡蛋,一个馒头或二面花卷,菜非常简单,自家种的韭菜、萝卜和油泼辣子加面酱。大约九点多就开始治病,这一坐就到后半晌,大约是下午四点多了,停下来吃饭。农村一般只吃两餐,早九十点,下午三四点。两餐之间,我爷爷并不休息睡午觉,连续坐诊六七个小时,每吃完下午饭后,他累得直不起腰来,加之房子里光线很弱,能见度很差,只好停下来休息了。
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七旬之后,健康状况迅速下降。背驼了,腿肿了,最严重的是蹲不下去,大便时非常困难。那时没有坐便器,最好的办法是坐在板凳上,再加上便秘,每上一次茅房得半个多小时。尽管我奶奶扶着也难免常常跌倒。1957年正月的一天,他坐在木凳上大便,奶奶有事离开了一会,不料他向前扑倒了,怎么也站不起来。待人们扶起他时,他竟然迈不开步子,不会走路了。从此他躺在炕上,饭量大减,常常闭着眼睛,话语很少,也可能是多年的紧张工作让他积劳成疾,积重难返。家人根本没有料到,一个多月以后,他老人家竟在静静的睡眠中离开了人世。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没有来得及给儿女交代一字,留下的只是惊惧、遗憾和悔恨!
丧事办得非常简单,但送葬的人却非常多,除二三百名孝子外,自动前来跟在灵车后的人,本村的、外地的至少也有三四百人,从巷子东头排到西头,痛哭声汇成一支恸天的悲歌!
可惜!我爷爷的针技并没有传承下来。他没有专门教给儿孙医病的针技,哪怕是星星点点。耳濡目染中,我的四个姑姑中有两位只会给小孩医病,用扎针医一些常见小病。我父辈兄长中,只有我叔父赵存才一人学到一些针术,他不仅给小孩看,也开始给大人看一些简单的病,开始他也用粗针刺扎表皮,后来也改用通用的针灸针,结合上新的针灸技术。正当他开始起步时,不料心肌梗塞发作,年仅六十二岁就离开了人世。
关于我爷爷针灸行医之神,我曾给一些朋友讲过,不少人感到惊讶!曾经在我爷爷手中看过病与我同庚的高个子王广政感慨地说,他从小失去母亲,多病,他的命就是我爷爷给救的。至今,每年清明回家扫墓时,他都要念叨着给我爷爷烧几张纸。
为了永不忘我爷爷和门口那棵大槐树,从1980年开始,我取我爷爷的五个“木”,把“五槐斋”作为自己的斋号。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曾询问过本家的一些长辈和村里的老者。当然许多事实是我自己亲眼见,亲身经历的,还有好多事没有写出来。
在我爷爷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逝世六十周年之際,我写此文,一是纪念我神奇的爷爷,更是告诉赵家的子孙后代,祖上有这么一位伟大的人物,以针术治病救人,分文不取,无私奉献。
2017年夏于五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