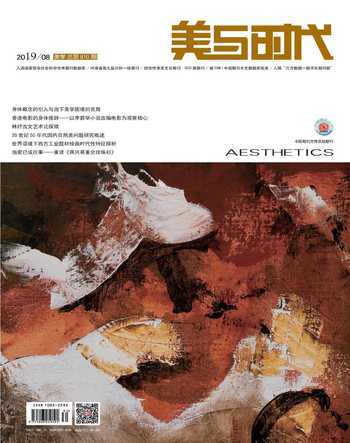多重语境下的知识分子话语
2019-09-10时雪丽
摘 要:新时期,知识分子反思题材的小说,深受苏联文学和“五四”文学传统的影响,但却没有把握其精髓。张贤亮是新时期的重要作家,有22年的劳动改造经历,小说多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重述他们在政治风暴前后的变化。作家在确认知识分子身份的同时,却失去了对历史的真实反思。这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从他的两部作品《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创作的话语环境中我们可以窥探一二。
关键词:知识分子;历史反思;张贤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从鲁迅开始,现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反思题材的小说。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反思的侧重点也发生了偏离。“文革”结束后出现的一系列的文学作品,或怀想青春岁月,或暴露伤痕,或反思过去,仍是我们记忆历史的一种方式。其中,一些“右派”复出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成为打压的对象,恢复政治身份后对历史发展充满信心,构成“坏事最终变成好事”[1]167的意义结构。张贤亮的知识分子改造小说《灵与肉》(1979)、《绿化树》(1984)、《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就是其中的重要作品,发表后曾引起很大的争议。作家对历史和知识分子的态度引起了不少评论家的质疑。这几部作品都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主人公的话语方式显然与现实的主客观条件是没办法分开的。
一、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话语环境
文学从来都是带着镣铐在跳舞,作家们的创作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人“试图记忆或忘却‘文革’的主要方式”[1]154不是通过史料而是作家作品对“文革”的叙述。“‘文革’以后的‘文革故事’,其实已是在重读‘文革’”,这些故事的叙述方式不仅反映着作家个人的思考也影响着国人的“文革集体记忆”。许子东总结的重读“文革”的四种方法,可以看到作家们在有意无意地循着一定的规则进行写作。这些“文革”叙述模式背后是一个时代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文化心理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们得到了平反。新时期,作家们渴望表达出这些年的压抑、痛苦,但是在长期的政治压制之后,他们汲取之前的经验教训,仍然小心翼翼地说话。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并不是完全豁然开朗的,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这也就可以理解“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小说《伤痕》(1978)为什么經历了许多周折、多次修改才被发表。卢新华本人说:“《伤痕》在发表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伤痕’,”之后书写“文革”的小说也都是在逐渐地冲破以往的思想禁锢。政治氛围的日渐宽松是作家们敢于吐露心声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它也没能提供最充分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文革”书写,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80)、《将军吟》(1980)和《芙蓉镇》(1981)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写作的主要目的是迅速疗伤,而不是反思历史和个体。从一些作家个人的创作轨迹中似乎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思想也在发生变化。在《灵与肉》中,张贤亮以一个资产阶级后代的身份被成功改造的“劳动者”形象拥抱苦尽甘来的伟大成果。几年后创作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章永璘对马缨花和黄久乡等劳动者感谢之后是诀别。这并不是说张贤亮对“文革”的认识更加深刻了,而是他开始表现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身份认同。显然,张贤亮创作思想的变化也仅限于对个体的反思,而不包括历史。
知识分子话语并没有得到完全解放,它依旧不同程度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除了要关注作品能否被发表,作家们还要考虑评奖制度以及是否会受到批判,或多或少会受到当时的文化与政治环境的约束。他们不自觉地将这些意识带入了自己的作品中,所以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思“文革”,遮蔽掉了很多真相不说,甚至会使人误读“文革”。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后引起了许多的社会争议,评论家王晓明、南帆、黄子平都对章永璘这一知识分子形象产生了质疑。张贤亮为表明政治立场将章永璘与“革命道德”衔接起来不免有些生硬,同时他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也与他要赞扬的革命力量发生了矛盾。总之,作家在这些因素的权衡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已经弃笔多年的作家们并不能确定读者们的阅读喜好,从传统文学中吸取经验是一个保守的选择。传统文学模式已经在读者群中扎下了根,很容易就能进入文本。知识分子历史反思题材小说嵌入好看故事的同时,也不忘与各方面的阅读群体达成和解。不止是张贤亮的作品,这一时期的反思小说如王蒙的《蝴蝶》(1980)、戴厚英的《人啊,人!》(1980)等,都在有意无意地遮蔽伤痛。这些知识分子主人公最终都在“苦尽甘来”的喜悦中迎接光明未来,渴望在新的时代一展身手。无论是主人公还是作家本人都在文本中维护了知识分子的颜面,避重就轻的叙述也能使读者从中获得一些宽慰。
可见,以上这些客观因素都影响了作家如何呈现“文革”。但是,作家在“文革”中的个人经历无法在他们的心中抹掉,在作品中也会时隐时现。所以,这些主客观条件会共同作用于作家作品,作家会不自觉地保持距离自己最近的身份介入文本。张贤亮多以知识分子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无疑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二、从诗人到小说家
张贤亮曾说:“我的人生就是一部厚厚的小说。”[2]1936年出生的张贤亮和所有同时代的人一样,见证了政治风暴带给人们的创伤,22年的劳改经历让他对这段历史更加刻骨铭心。“文革”结束后,张贤亮开始创作小说,成为当代著名作家,从贫瘠的宁夏镇北堡景观中汲取灵感,创办了镇北堡西部影视城。他既是文人,也是商人。在当代文学史上,张贤亮更多地是以一个反思历史的小说家的身份被大家熟知。从一个诗人到一个小说家、商人,这种身份的转换有作家不同的人生追求,也有历史的推波助澜。
他的小说其实是带有自传色彩的,落难知识分子的形象是他劳动改造经历的再现。张贤亮出生于南京的一个官宦世家,父母都是名门之后,父亲在“西安事变”后弃政从商,后来成为买办资本家。1954年,高中即将毕业的张贤亮,因历史问题,与母亲、妹妹来到了宁夏落户。在此之前,凭借少年时期受过的良好的教育及个人天赋,他已经发表了一些诗歌。1956年在毛泽东“双百方针”的指导下,文化形势一片大好,张贤亮被当地政府聘任为语文教员。“总之,我的确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来临’,于是我以全部的真诚唱出了这首《大风歌》。”[3]571957年7月,这首诗发表在了《延河》七月号中,在当时的“反右运动”中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随后他被押送农场劳动改造。这段经历散见于作家后来创作的作品之中。
1979年被“平反”后,张贤亮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灵与肉》,此后又创作了许多小说、散文、电影剧本等,但是再也不愿写诗。“人一‘务实’便无诗可言,我已失去了诗的境界和高度”[3]57,多年的“劳改”生活之后,张贤亮失去的不只是青春岁月,也失去了一个诗人的赤子之心。《大风歌》本是张贤亮对时代新发展的激情赞颂,却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诅咒,被扣上了“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帽子。作家认为不公正的对待与自己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有关系,这些质疑的声音在他后来的散文中表述得更为清楚。他在《中国文人的另一种风格》一书中感叹,仅因一张薄薄的漏洞百出的“雪莲纸”,自己就受了22年的苦。回望过去自由的21年和接受劳改的22年,张贤亮的写作显然无法回避刚刚过去的苦难。一个刚复出的“右派”作家,书写这段历史时已经失去了当年的自信和锐气,其中的妥协成分包裹了真实的委屈。
从诗人到小说家,中间的过渡身份是一个“劳改犯”,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压。随着身份变化的不只是作家的年龄,更有他的心态。在农村生活20多年,以“老右”的身份与乡民相处,似乎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灾荒之年忍受饥饿与寒冷,多次在死亡线上挣扎。面对过去的个人疼痛与历史疼痛,张贤亮的心情是复杂的。
三、知识分子历史反思的两面性
重新回到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之内,对于作家们而言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当代作家的“文革”叙述都表达了每一个自愿或是被迫下乡劳动改造的知识青年最终试图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被冠以“右派分子”“反党反革命坏分子”等罪名的知识分子,这种愿望则比普通人更强烈。所以,新时期的反思小说多少都会流露出对乡村的眷恋,即使他们曾经在那里吃了数不尽的苦头。在这一层面上,张贤亮的态度也是明确的。许灵均和章永璘对广阔的黄土高原、劳动人民有着热烈的感情,这片美丽又神奇、丑陋又邪恶的土地,吸干了他们的的汗水、泪水、爱情。他们逐渐适应了劳动,成为一个劳动能手,与这片土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灵与肉》中大段地描写高原上的美景,在平凡的劳动中许灵均的委屈和消沉渐渐变成了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许灵均在政治上是被批斗被劳改的“右派分子”、老放牧员、“郭蹁子”,秀芝这些农民把他当做好人。他最终放弃继承资本家父亲的巨额财产,选择了继续陪伴他的老乡们。同时,许灵均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为新时代贡献力量的决心与理想,也从侧面表现出张贤亮重获自由时的感激、喜悦之情。作品寫于作家离开农场不久,对于“劳改”当地的农村、农民的依恋是真挚的,毕竟他在那里度过了最年富力强的22年。
如果说许灵均是在以感谢苦难的姿态怀念过去,章永璘则开始跳脱出被改造的“劳动者”形象,以知识分子的身份重新审视自己和现实。章永璘在《绿化树》中对于马缨花、谢队长、海喜喜的善良依然抱有感激的态度,他认为是这些劳动者在严酷的环境中温暖着他。到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章永璘眼中对于历史以及其中的人们有了思考,“文革”期间为何创造了破世界记录的犯罪率,而这些阶级敌人到底是谁的敌人。他和大青马之间关于“自由”和“阉割”的对话是对历史发出的又一个追问。这些细节中,他都在以知识分子的眼光探索曾经失衡的历史关系。
但是,这种知识分子眼光并不是完全精准的,在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下发生了变形。章永璘对马缨花和黄久香的态度受到了许多评论家、女权主义者的批判。章永璘以和马缨花、黄久香的差距来粉饰自己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文革”结束后,知青与乡下姑娘的恋爱以结婚或诀别收场,的确是当时的现实情况。为了回到城市,知青们割断以往的联系重新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是常见的。章永璘们却以这些女性劳动者的深情为背景来衬托自己形象的高大。马缨花无条件地为章永璘提供当时最珍贵的粮食,只因恋着这个男人会“读书”。章永璘眼中的马缨花,尽管以前有“美国饭店”的不洁外号,现在却是一个只忠诚于自己、精明能干的农家女人。在他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开始思索爱情,认为“她虽美丽、善良、纯真,但终究还是一个未脱粗俗的女人”[4]。这里我们看到章永璘表现出的知识分子的虚伪性,在饥饿难耐时马缨花的落在馒头上的指纹都是性感的,一旦解决温饱就与之划清界限,他骨子里的清高、自恋可见一斑。
作品沉溺于个体伤痛的表达,对历史真相呈现和反思都浮于表面。作家沿用传统小说的“才子佳人”模式,多次制造落难知识分子被风尘女子拯救的桥段,获得现实利益之后又以两人的“差距”为借口诀别。章永璘因为新的政治运动和马缨花永远地失去了联系,他们的结局看似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不如说是章永璘或者张贤亮的真实想法。马缨花不过是普通的体力劳动者中的一员,她的出现似乎只是为了给男性知识分子落难时的物质和精神补给。章永璘受难之时马缨花是“女人”“女性”,重获辉煌时她是“劳动者”。章永璘获得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体面,也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决心。张贤亮的另一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直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另一半是政治。即使黄久香已经和章永璘结婚,维系他们的,“在根子上恰恰是情欲激起的需求,是肉与肉的接触”[5]。黄久香只是章永璘知识分子身份确认的一个工具而已。章永璘的“性无能”与知识分子使命之间的隐喻关系,作家强行将政治话语嵌入到了文本的叙事逻辑中。在抗洪救灾之后,章永璘恢复了一个男人的特征,作家无形之中又赞扬了革命力量的伟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章永璘对过去、未来的思考都没有谈及本质,从历史的苦难中走出,完成自己的身份确认才是他最渴望的。在身份和解的同时已经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意志。
四、结语
我们可以看到,张贤亮的散文比小说更加客观地反思了这段历史,除了文体本身的限制之外当然更多地是外部话语环境的制约。这些小说引起的社会争议和讨论,也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反思小说是在多种话语运作机制下发生的。保守的叙述方式不失为作家们保全自我的好方法,一举多得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可是这些亲历“文革”的作家,他们的叙述不仅影响着读者,也与我们整个民族的“文革集体记忆”密切相关。如果面对历史,知识分子的内心是如此脆弱,这就需要思考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性是否仍然存在?
参考文献:
[1]许子东.重读“文革”:许子东讲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张贤亮.我的人生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J].湖南文学,2009(1):23-26.
[3]张贤亮.今日再说《大风歌》[J].诗刊,2002(11):57.
[4]张贤亮.绿化树[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159.
[5]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164.
作者简介:时雪丽,郑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