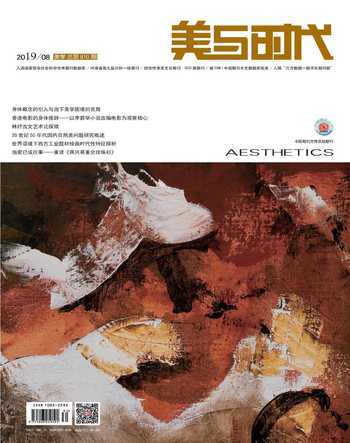《诗学》悲剧理论视域下的《原野》
2019-09-10刘婷
摘 要: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提出的悲剧理论,奠定了西方美学史上悲剧范畴的理论基础。以《诗学》中的悲剧理论为参照,探讨《原野》在创作上的结构安排、情节布局以及隐含在剧作中作者的人性理念,不仅可以更好地从理论上把握《原野》剧中所暗含的普遍悲剧创作理论与文章背后所传达的人生价值观,而且也可以了解西方美学悲剧理论对于中国现代戏剧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悲剧;《诗学》;《原野》;复仇正义性
亚里士多德《诗学》是西方最早一部具有系统美学理论的重要文献,书中的戏剧理论奠定了西方美学史上戏剧理论的基础,其中大部分篇章都在对悲剧进行探讨——悲剧的定义、性质、功用等方面。戏剧《原野》作为曹禺经典作品之一,单就剧中人物的经历和结局来看,是归属于悲剧的。以《诗学》中的悲剧理论为参照,探讨《原野》在创作上的结构安排、情节布局以及隐含在剧作中作者的人性理念,不仅可以更好地从理论上把握《原野》剧中所暗含的普遍悲剧创作理论与文章背后所传达的人生价值观,而且也可以了解西方美学悲剧理论对于中国现代戏剧产生的影响。
一、悲剧定义下《原野》的完整性
“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1]63亚里士多德十分强调悲剧作品的完整性,认为“因为有的事物虽然可能完整,但却没有足够的长度。一个完整的事物由起始、中段和结尾组成”[1]74。在现代戏剧的创作中这三者无疑是作品中最基础的概念与必备要素。起始不必继承它者,但要接受其他存在或后来者的出于自然承继的部分。在《原野》的序幕中,作者就借白傻子与仇虎的对话交代了主要人物的现状——仇虎从囚车出逃回原野,打算回老家找仇人焦阎王报仇,却发现仇人已死,心爱的女人(金子)嫁给了自己视如亲生兄弟的仇人的儿子(焦大星)。在焦母、焦大星与焦花氏的对话与举动之间便使观众知晓了存在于三者之间的矛盾。序幕的最后,作者又安排了仇虎和金子的碰面,这就为后面情节的发展与承继提供了条件。从一开始,作者就把复仇这一主题不加铺垫地直接推到观众面前,仇虎一出场就是来复仇的,其复仇的对象是自己的干妈、幼时的好友和还在襁褓中的孩子。这样的起始,简要交代了时间、地点、主要人物与其中所蕴含的矛盾关系,清晰明了,矛盾冲突明显,使文章后续的承继发展显得顺理成章。
而中段是承上启下的部分,随着序幕情节的发展,《原野》的中段部分主要集中在情节的具体展开部分(第一幕至第二幕)。承接了起始部分中所交代的各种矛盾关系,仇虎与焦大星、仇虎与焦母、焦母与金子、金子与焦大星之间的复杂矛盾通过人物之间复杂行动与意味深长的对话,情节逐步推进,最后仇虎狠心杀死了焦大星,带着金子逃窜至黑树林;焦母错杀自己的亲孙子,誓死都要杀了仇虎为自己的儿孙二人报仇。由此,各种情节承上启下,自然地引出了整个戏剧的最后部分:夜半时分,仇虎与金子在黑林子里迷路,焦母抱着死去的孙子,带着白傻子追至黑树林。再结合着作者有意安排的各种和现实不符的幻想和各种带有紧张氛围的环境,仇虎变得疯癫,强劝金子离开,自己选择自杀,焦母失足掉进水塘生死不明。这一悲剧性的结局就正好符合《诗学》中说的“结尾指本身自然地承继它者,但不再接受承继的部分,它的承继或是因为出于必须,或是因为符合多数的情况”[1]74。仇虎在带着金子疲惫地逃亡之中看到的各种幻像引发了他内心深处对于人性的思考,他不但意识到了他复仇的绝路,而且意识到了作为肉身自我的极度的困境和绝望,承继着他复仇之路所犯下的各种罪孽,面对侦缉大队的追捕,他选择了自杀。而焦家也承继着之前对仇虎一家所犯下的罪孽,落得个断子绝孙的下场。整个戏剧从起始矛盾鲜明、人物关系复杂到中段承继各种矛盾作精彩具体的深化发展,再到最后结尾矛盾在人物的行动与曲折的情节之下逐一化解,各个人物都得到了自己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结局。
“一部悲剧由结和解组成。所谓‘结’,始于最初的部分,止于人物即将转入顺境或逆境的前一刻;所谓‘解’,始于变化的开始,止于剧终。”[1]13悲剧就是表现人物命运的变化,“结”与“解”是由起始转向结局的情势安排。“结”是矛盾的出现及其承继的展开,“解”是剧情发展的必然结果。“结”经“解” 转变,改变了顺或逆的走向,矛盾继续发展,最终矛盾推至高潮,達到必然性的结局。《原野》的“结”就是由戏剧的起始部分作者制造的仇虎与焦家的杀父辱妹、霸占家产的矛盾与焦母与金子二人婆媳之间的矛盾开始发展至戏剧的中段部分,焦大星被怀疑金子在家与外人偷情的焦母从铁路上的岗位召回家为止。而戏剧中的“解”便由此开始,焦大星回家后在与焦母的对话之中得知金子与人偷情,婆媳矛盾与夫妻矛盾进一步激化,焦家母子由此发现仇虎的存在。整部戏剧就在伴随着仇虎与焦家母子的碰面之下,形势由起初的焦家母子占主导地位的顺势转向了焦母害怕仇虎逃狱回来复仇、处处被仇虎牵制、陷入被动局面的逆势。最后,焦家与仇虎之间的矛盾被推至高潮,仇虎痛心杀害了焦大星,焦母在处心积虑的谋划后却阴差阳错地错杀了自己的亲孙子——小黑子。戏剧便在仇虎带着金子慌乱逃窜、焦母因自己儿孙的死陷入癫狂、誓死都要跟着仇虎为其报仇之处进入了戏剧的结尾部分,最终达到了所有主要人物相继死去,金子不知去向的这一必然性的悲剧结局。《原野》中的“结”与“解”密切契合,使得整个戏剧对于观众来说,达到了对于整部戏剧必然性悲剧结局的理解和对于复仇道义的正义性的体会。
二、 《原野》情节的突转与发现
(一)情节的“突转”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情节是对行动的摹仿。“情节”是指事件的组合,它是悲剧的目的、根本、灵魂,一部好的戏剧应该是“复杂的行动”。“复杂的行动指其中的变化有发现或突转、或有此二者伴随的行动。这些应出自情节本身的构合,如此方能表明它们是前事的必然或可然的结果。”[1]88“突转”和“发现”是情节的两个成分,它们对于一部戏剧中情节的变化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突转”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这种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而《原野》是存在着符合可然或必然原则的“突转”的。在仇虎还未与焦家母子碰面之前,虽然焦家存在着婆媳矛盾,焦大星介于婆媳之间两面为难,但总的来说,焦母在焦家仍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焦家的生活状态还算美满。可是这一切都在仇虎与金子相遇、二人偷情之事被焦大星验证之后发生了转变。焦大星在与仇虎叙旧的饭桌上听闻仇虎叙述自己的父亲不顾两家人多年的情谊,杀死仇虎的父亲,将仇虎的妹妹卖至妓院导致其被折磨致死,仇虎被自己的父亲以莫须有的罪名冤入大狱之后,在醉酒的状态之下被仇虎用一把匕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个拥有自己美好生活轨迹的人就在这突转的情节之下发生了转变。在仇虎看来,焦大星的死是父债子偿,合情合理,而焦大星自身懦弱的性格也使得这一情节的突转符合必然原则。在之后的情节之中,焦母还未知晓自己的儿子已被仇虎杀害,打算在深夜趁仇虎熟睡之时用拐杖打死仇虎,却不料因自己眼盲,计谋被仇虎识破,阴差阳错打死了自己的亲孙子。这里,情节随着焦大星的死发生突转之后,紧接着又以孙子小黑子的死再次发生突转,剧情的发展被推向了高潮。此时小黑子的死对于剧中人物来说是太过偶然的,但是对于剧外观众来说,又可以理解为是偶然中的必然。焦母从仇虎在她面前现身开始,就没想过要让仇虎活着离开,仇虎也心怀复仇,抱着打算让焦家断子绝孙的这一目的。因此在二人如此激烈的矛盾之下,无辜的焦大星与小黑子就必然会成为这一矛盾进一步演化的牺牲品,这一点也使剧外的观众产生共鸣,感受到因为焦母与仇虎二人人性的泯灭与扭曲,焦大星与小黑子二人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悲剧命运。
(二)情节的“发现”
“发现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中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最佳的发现与突转同时出现。”[1]89“发现”的类型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一方身份明确,发现是另一方的事。就如《原野》中对于金子来说,与她私会的男人是仇虎的这一身份是明确的,但这一身份就要顺着情节的设置、线索的铺垫,等着焦母与焦大星去发现,继而焦家母子发现了仇虎的归来,使得后面的情节发生突转。另一种“发现”是双方需互相发现。但这一种情况在《原野》的创作中没有涉及。在小黑子被焦母错杀这一情节处,仇虎之前早就料到焦母会对他痛下杀手,就将计就计,明知躺在床上的只是一个无辜的小孩,却因为是焦家的后代,理应为焦家犯下的罪孽赎罪,放任小黑子惨死在焦母的拐杖之下。对于床上死者的身份,仇虎与金子是知道的,只是等着焦母去发现。而当双目失明的焦母发现时,情节也被推向了高潮。正是在这一情节处,整部戏剧发生了强烈的突转,发现与突转同时发生,二者产生关联,共同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与矛盾的激化,在戏剧所设置的各种偶然巧合之下使戏外的观众知晓了焦家必然的悲剧命运。因此,这一发现,算是《原野》之中最佳的发现。
三、《原野》中的怜悯与恐惧
(一)情节构合方面
亚里士多德规定悲剧摹仿的不仅是一个完整的行动,而是能引发恐惧和悲悯的事件。悲剧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于人的行动,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悲剧的功效就是通过能使人惊异的剧情引起读者或者观众怜悯和恐惧并使他们在体验这些情感中得快感。”[1]71“通过源于自我的情感体验,使压抑在内心的不利于身心健康的情感通过合适的渠道(如悲剧)进行宣泄,将这些不利的情感排逐出去,从而达到净化心灵的功效。”[2]可以看出,这与观众是有着紧密联系的。因为“怜悯”对象是遭受了不该遭受之不幸的“别人”,而“恐惧”的产生是由于遭受不幸的这个“别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由此,能够引发怜悯与恐惧的事件与观众发生联系,观众感同身受地被痛苦的情节所打动,从而产生相同的情感。而在《原野》的创作之中,作者也巧妙地看到了文本与观众这一密切关系,在情节设置上,精心编排了能够引发观众怜悯与恐惧的事件。例如,焦大星与小黑子的死,只是因为上一代人犯下的错误就要遭受到本不应该降临在自己身上的祸事,在情节的“突转”与“发现”结合之下,打动了观众,使观众在戏外观赏的过程中产生怜悯之情,为二人悲惨的身世感到惋惜。同时,观众也会因为作者对于情节精彩的描述,将自己带入到剧情的发展之中,感受到当时紧张的气氛,在自己的内心产生惊异感与恐惧。在《原野》最后一幕的设计上,作者选择了不同于之前作品的传统写实手法,而是采用了与尤金·奥尼尔《琼斯皇》相类似的表现主义手法,设计了各种伴随着鼓声浮现在仇虎面前的各种脱离现实的离奇诡异的的幻像,将仇虎带回到自己父亲、妹妹被洪老、焦阎王残忍活埋害死的场景之中,带回到自己当时被焦阎王陷害入狱在坐狱时被狱长残害的场景,带入到具有神秘及神话色彩的自己的父亲与妹妹在牛头马面的押送下被真正的阎王爷在地狱审问的场景之中。作者所设置的这些幻像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惊异感,使观众将自己的注意力都转向了作者所设置的情节之中,跟随着主人公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来回穿梭,感人物所感。在这些幻境之中,仇虎不得不再次面对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痛苦场面,看到即便是到了最公正、能够还人公道的阎王爷的面前,自己的父亲与妹妹的冤情也被巧舌如簧的仇人给辩驳敷衍过去的场景。这所有痛苦的场景与最后得到的不公的审判结果都使得仇虎内心痛苦不堪,这让他觉得自己为了复仇,不惜违背自己的良心,杀死自己的兄弟和对一个无辜的婴儿见死不救的这一切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此时仇虎内心情感的变化已经从一开始的复仇后的喜悦转变成了对于自我极致的绝望,最终仇虎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来摆脱现实对于他所带上的“镣铐”。就戏外的观众而言,观众在作者刻意设置的这些带有虚幻神秘色彩的情节里见证了仇虎这一明显变化,由此也会相继产生对于仇虎悲剧命运的怜悯之感和对于现实冰冷残酷之实的恐惧之感。这些被引起的怜悯与恐惧之感继而使观众内心不利于身心健康的情感得以疏泄,“堵着”的内心由此得到了净化,达到了平和的状态。
(二)戏景方面
《诗学》中提到恐惧和怜悯除了可以出自情节本身的构合之外,还可以出自戏景。但亚里士多德认为,戏景虽能够吸引人,却最缺少艺术性,是相对次要的部分。与之相反,现代戏剧的创作对于戏景(环境)的营造却是十分重视的,并且认为好的戏景的创造对于情节的发展会起到深化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在《原野》之中,戏景的描述在整部戏剧的创作比例上占了较大比重。作者在每一幕的开头都会描绘一些代表阴郁孤寂一类的景象来渲染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苍茫的原野上,没有村落,没有人烟,只有野风的呼啸和野塘里青蛙的叫声、树上的蝉声,以及火车的鸣叫声。”[3]在作者描绘的戏景之中,充满着原始气息,使观众强烈地感受到在这里,只有仇虎的仇恨,再无其他。因为他内心的复仇已将周遭的一切“燃烧殆尽”。观众能够从描绘的戏景中间接地感受到人物内心的痛苦挣扎,继而产生怜悯与恐惧之情。作者描绘夜半后阴森森的原野和恐怖的黑树林,使观众联想到了现实世界的黑暗和残酷,明白了正是因为当时社会的冷漠与不公才会导致原本生性纯良的主人公的人性发生扭曲,产生一心只想要复仇、与整个世界抗争的这样一种怪异的性格。在仇虎的认知层面,复仇是充满正义性的。并且通过作者一层层对于幻境的描绘剖析,观众仿佛如同主人公一般看到了他内心痛苦的挣扎:屡遭挫败,饱受苦难,不公对待,强权压制,这使仇虎慢慢变成了一个仇恨的化身。大星、小黑子的死使他内疚,仇虎内心深处的善良在与他的仇恨发生博弈,而剧中多次伴随着幻境出现的鼓声(后改成木鱼声),更进一步渲染了紧张神秘的气氛,从而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仇虎内心的矛盾。曹禺通过表现主义的手法来描写戏景,创造出一种神秘诡异的美,使观众在作者设计的戏景之中去感受仇虎所经历的痛苦与苦难,从而在自己的观赏与审美之中产生怜悯与恐惧,体会到复杂扭曲而又令人惊异的人性力量以及作者对于复仇这一行为正义性的理解——尽管以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仇虎从一开始就已然从白傻子的口中得知自己的仇人焦阎王已死,但仍然选择复仇是可笑而又错误的,但作者的创作意图显然已经跳过了这一层面,而是想要为复仇者找到一种突破自己内心由复仇所编织起来的“枷锁”的方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脱。
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理论来解析曹禺的经典戏剧《原野》,不仅可以加深对于其理论的理解,找到二者的共通点即承继戏剧创作之中经典化的部分,而且可以在具體的理解分析中找到现代戏剧在戏剧创作上所做的新突破、新尝试。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李恒.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理论综述[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4):80-82.
[3]吕晓明.论《原野》中人物形象的塑造[J].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9(3):73-74.
作者简介:刘婷,西南大学文学院美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