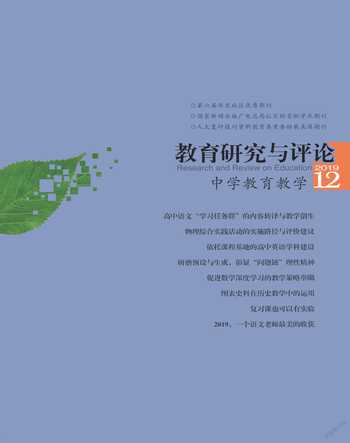教师可以写什么
2019-09-10谢嗣极
教师可以写什么谢嗣极教师总要写一些和教学有关的文章,无论是自觉的还是功利的。下笔前想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写什么。这个问题不必急于求成,要相信水到渠成。关注热点,但不蹭热点。“热的”往往是“新的”,“新的”就需要实践、思考、再实践,然后才能成文,故要关注热点。一个热点问题出来,有的教师立马有长篇大论,信手拈来,那是因为积累丰厚,经验丰富,这也正说明我们需要长期积累,独立思考。如果每节课,从备课到上課都能独立思考,“写什么”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教材、教法等都有话题可写。
先说教材。别以为经过这么多年、这么多教师的咀嚼,就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以名家名篇为例,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写“铁屋子”的那一段非常经典。我见到的分析,都说这是用了比喻(有的说是比喻论证)的方法。原先我也是这么教的,但教着教着,我产生了疑问,这是比喻(比喻论证)吗?对照比喻的定义,发现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再如,苏轼的《石钟山记》的观点,毫无疑问是成立的,也是有价值的。但是,文中所引郦道元的话,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郦道元的本意是说石钟山得名的原因,还是说石钟山发声的原因,抑或因其发声故而得名?要弄清这一点就得去查郦道元的原著。这些都是可以做文章的。
再说教法。近几年听课,看上课录像比较多。我发现许多教师的授课方法,几无本质差别。比如,说明文,讲说明的方法和语言的准确性;议论文,讲论点、论据、论证方法;小说,着重讲小说的三要素;文言文,则字字落实地翻译,讲文言语法特点。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讲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哪里?是否需要改进?我们在确定教学重点、选择教学方法的时候,不妨想一想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觉得大家如此、从来如此,我便如此。那么即便如此,也明白了如此的理由;若不再如此,且有自己的反思、完善与实践,那么,“写什么”的问题就不会是问题。
还想说说文章的语言。语言不仅要没有语病,还要通畅。有的文章疙疙瘩瘩,晦涩难懂,原因有二。其一,长句泛滥,似乎不用长句就不足以显其严密。长句不是不能用,但我以为能用短句,尽量用短句,因为文章是要让别人看的,要考虑读者的感受。其二,术语成堆,似乎不用术语就不能显其高深。金克木先生说:“当代有些论文中术语繁多,被人比作森林。森林不是丛莽,不用大刀阔斧就有路可走。丛莽才需要披荆斩棘。”可见术语只要不成为语言的“丛莽”,用也无妨。但是,“把术语当成打牌的‘听用’‘百搭’随意支使,那是丛莽,不是森林。森林是有规律的”。而事实上,不少论文中的术语已经成了“丛莽”,这样的文章只能拒人于千里之外。看老一辈学者,如陈鹤琴、叶圣陶、张中行、启功等的学术专著,也写得如大白话。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