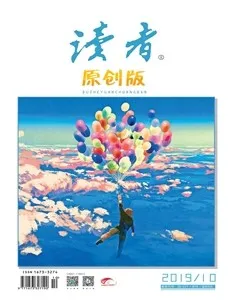莲阴
2019-09-10许冬林
许冬林
一
初夏之夜,窗外在下雨,听见蛙鸣。并不稠密的蛙呜,从楼下的小河边传来,耳朵里就有了清凉的湿气,觉得这样的夜晚在蛙鸣里真像宋人的小令,三句两句,唱唱停停。
合上书本,闭上眼睛,恍惚看见蛙鸣里层层叠叠浮起了团团绿云,那是莲阴。
不记得是在哪里看过一幅画,画里翠盖微斜,雨珠弹跳,一只绿色的小青蛙懵懂憨厚,呆呆地坐在一茎莲叶下。那只小青蛙坐在莲阴下看什么呢?看池塘青草?看白雨跳珠乱入船?看岸上匆忙赶路的行人?看与它无关的纷纷扰扰、辛辛苦苦的红尘……
还记得,那个少年的我就那样被一幅画给迷住了,我多想做那样一只小青蛙呀,可以野在外面不回家,可以蹲在一枝硕大的、在雨里起伏的莲叶下。
我记得,似乎在哪里见过一幅小孩在莲阴下避雨的画。一个小男孩,趴在草地上,趴在莲阴下,手托腮,肉乎乎的脚翘在莲叶后面,胖藕似的。我喜欢那样的画,他就像我懵懂的小弟弟,那幅画就像我们曾经在乡下度过的那些童年光阴。
在乡下,在童年,我们喜欢刮风下雨,然后赤着脚,冒着雨跑。明明应该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可是偏不。我们举着笨重的大雨伞,或者举着大人的草帽,一路奔跑,到树荫下,到草垛下,到荒僻的老屋檐下……
我们喜欢跟大人们隔着一场雨。而我们,也在避雨。
唐诗的插图里常常有牧童。春天,那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夏天,那牧童还骑在牛背上,只是,牧童头上常常顶着一片莲叶。我们这个江北平原上也有养牛的人家。童年时,邻村的那户养牛的人家雇了个放牛仔,从山里来的,据说家里穷,十五六岁的样子,算不得牧童了,可是在夏天,他依旧是唐诗里的牧童打扮——头顶一片莲叶。我那时同情他不能上学到别人家放牛谋生,却又在心里悄悄羡慕他日日头顶莲叶放牛归来。我想象着,他放牛时,牛在江堤上吃草,他在柳荫下睡觉,脸上罩着一枝新采的莲叶,清香袅袅。也许,他头下枕的也是莲叶,肚子上盖的也是莲叶;也许,他不睡觉,他下了莲塘,干脆藏身在莲叶下避阳,然后脚踩到一根嫩藕,拽出来吃也不一定……
似乎是因了那些画,因了童年的那些想象,此后每路过一片莲塘,我总忍不住停一停,总忍不住伸手掐一枝莲叶,举在耳畔,举到头顶。我在莲叶下,多像我一直梦想要做的青蛙;我在那阴凉里,心里微风荡起,清凉安妥。烈日不在了,风雨不在了,一枝莲叶像一座屋宇,可佑护二十四个节气相牵连的长长光阴。
宋人毛滂有一阕词《醉花阴》:檀板一声莺起速。山影穿疏木。人在翠阴中,欲觅残春,春在屏风曲。劝君对客杯须覆。灯照瀛洲绿。西去玉堂深,魄冷魂清,独引金莲烛。
我喜欢这阕词,只是因为喜欢词里这一句“人在翠阴中”。虽然千万回梦想要做一只蹲于莲阴下的青蛙,但终究不能,终究要长大。长大了,能有一团翠阴将自己暂时淹没一下,也是人间一大自在。
朋友家里养有一盆莲,夏天,莲叶茂盛成荫。一日,她女儿放学回家,看了那莲,竟说:“妈妈,我真想睡在莲叶下乘凉!”
朋友跟我说时,我忍不住莞尔。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可不就像当年的我,明明个头已经赶上妈妈了,可是,看到那团团莲叶,竟就忘记了自己的身高体格,竟就以为自己是一只青蛙或一只蚱蜢,可以弛然卧在莲叶下,享受一片叶子覆下的清凉。
二
汉乐府里有《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在多水多莲的江南,一边采莲,一边看鱼戏莲叶间。诗歌写到第三句“鱼戏莲叶间”似乎就可以了,可是作者不休,通过方位的变换来不断渲染鱼戏莲叶间的情形。有专家解释那后面四句其实是唱和,通过东西南北的方位变换来和前面的“鱼戏莲叶间”。这一说,似乎在荷风的清香里听到汉朝田野上的歌声了。
這首诗美,美在莲叶田田的葱茏茂盛、生机蓬勃,美在“鱼戏莲叶间”的活泼轻灵,更美在一静一动的相互映衬。动的是鱼,静的,就是那一塘叶叶相叠搭起来的巨大莲阴啊。
南朝乐府民歌里有一首《西洲曲》,也极美。多年之前,我混迹于“榕树下”文学网站,也像“鱼戏莲叶间”一般欢喜自在。那时论坛里有一个作者,网名“西洲”,文字典雅,人也静寂。我喜欢他的文字,似乎更喜欢他的网名,想来还是因为《西洲曲》这诗就爱屋及乌了。《西洲曲》里句句皆美,但是,美中挑美,相比“栏杆十二曲,垂首明如玉”和“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这些,我还是始终如一地最喜欢“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这一句。确实,这一句里的画面感不是一般的美。你想,有莲花,自然有莲叶,绿的叶和红的、白的莲花相互映衬的美已是令人陶醉。还有“莲花过人头”里,莲花、莲叶在高处,在明处;采莲的小舟和舟上人在低处,在莲花、莲叶遮蔽的朦胧幽暗处——这些由明暗、远近、高低构成的层次之美,已足够人品味。再想想,那人和花交相辉映的青春之美,更是令人怦然心动。我喜欢“莲花过人头”,还因为,这里有莲阴——莲花过人头了,莲叶也一定过人头,莲花和莲叶交叠形成的花阴莲阴,可消多少暑气,可静多少尘心啊。
想象在南朝那样古老的年代,一个面容姣好、怀抱相思的女子,在莲阴之下摇动小桨,采莲,剥莲,将清凉的莲子放进袖子里,就觉得千百年来的莲阴都多情起来了。
水生植物多有一种独立世外的仙气,如芦苇,如菖蒲。在水生植物里,莲的仙气不同他物,那玉盘似的硕大的叶子,静时如庙宇,如长亭,可荫庇那么多卑微的、活泼的、流浪的生物。莲阴的仙气里,不止自洁自守,还有荫庇他人的清凉与慈悲。它是生于凡尘,高于凡尘。它是生于污泥,又清洁独立于周遭的污秽之外。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这是李商隐的一首诗。有时想,读唐诗读到晚唐,如果没有李商隐,会多么枯寂空落啊,就像没有爱情滋润岁月的荒荒中年。记得第一回读到这首诗,是少年时在一本钢笔字帖上。相思迢递,枯荷秋雨,从此我知道,在江堤脚下的那片莲塘里,那莲阴不仅可以遮阳,可以挡雨,还可以用来听雨打残荷点点滴滴的幽怨之声。
在那一片葱茏的莲阴下,我不仅可以做一只歇凉观雨的青蛙,不仅可以做一个举莲遮阳的牧童,不仅可以做一个采莲怀远的女子,还可以做一个忧伤听雨的诗人。
翻过盛唐这座山顶,“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些雄奇繁丽的风景一一阅过,然后,在清流缓缓的山脚转弯处,在月色朦胧、薄雾清扬的晚唐,读李商隐,像读晚香弥散的碧水上一片莲阴。李商隐一身青衫,缓缓行走在晚唐的风里,他把自己走成了一纸清凉。“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这些诗句太美妙,以至读着读着,全忘了字句里透出的微苦,却只欢喜玩味着诗人微凉的叹息。
他是晚唐的一枝荷,时间的雨落了千年,我们在听。忧伤时在听,内心不平时在听,长路行走怅惘时在听……
因为我们在路上,因为我们长作不归人。
我有一位画家朋友,喜画墨牡丹和墨荷。在暑热的长夏,我喜欢潜进他的博客里乘凉,看他晒画,晒墨荷。从官场从容隐退下来的朋友志在丹青,生活安定悠然,他笔下的墨荷仪态万方,生气蓬勃,莲阴深处仿佛有清甜的晚唱悠扬飘荡。
八大山人也有许多画莲的水墨画,他似乎是取了仰视的角度来画莲,让画者和观者低成一粒尘埃——莲柄疏朗高挺,仿佛热带雨林里的乔木;莲叶硕大,仿佛能覆盖整个红尘。看八大山人的莲常常会感动,会生出羽化的轻盈感。那些莲叶亭亭高举,浓淡虚实中,仿佛已经高高接上了天宫瑶池的莲花。莲下有清风,有空阔的水域,有一个广大无边的慈悲世界——可栖息,可独自沉吟,可嘯歌,可彼此凝望。
他有一幅莲图,画里一片墨色莲叶占去了画面一小半,一片莲阴大过一栋屋宇,一只孤独的水乌单足立于水面之上的一截枯茎,此画看了令人悲欣交集——悲,因为孤独,因为尘世立足之难;欣,因为还能暂得这一片安宁与阴凉。
案头置“扬州八怪”之一金农的几本画册,我向来爱读他画里的题诗题跋,古拙方整的隶楷体,像有青铜锈要染了指尖。他的一篇题画跋里有一句“茫茫宇宙,何处投入”,我读到,心里凛然一惊。感觉金农像是站在时空之巅俯视红尘,忍不住发出这难解的千年一问。在浩渺无垠的时空里,究竟哪里有一方净土和乐土,可以安置这肉身和灵魂?
大约还是一片清凉境吧。像莲阴一样的清凉境。
金农有一幅莲图,或者说是画人物的画。画中,竹林萧萧,林边是莲塘,莲塘之上,悬空架起一座六角凉亭,香茆覆顶,亭下横放一几,几上—人酣睡。微风拂过,莲花点点,莲叶团团交叠,在风里摇摇荡荡。画里他题“风来四面卧当中”,他睡在一池莲阴之上,四面荷香萦绕,真是清凉自在啊。不知画中人是梦是醒,若是梦中,想来也是不梦长安公卿,而梦浮萍池上客。
曾经发出“茫茫宇宙,何处投人,’的金农,有一日,终于明白了这人生如寄的“客”的身份,便终于释然,酣然而卧,来享受这世界的无上清凉了。
在画里,虽然是人卧莲阴之上,可是我分明觉得有一枝更大更恒久的莲阴,荫庇在酣卧之人的头顶。是圆如莲叶的茆顶凉亭吗?是画梅画竹画莲画芭蕉画幽冷清静之物的一管羊毫吗?是独行于世已然宁定的一颗慧心吗?
四
我慢慢知道,有一天,我们长大,青蛙也离开了莲叶下,青草池塘在秋霜里荒芜,无归之时,还有一处莲阴,在笔尖种下,在心头种下。
心安了,莲阴不败,清凉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