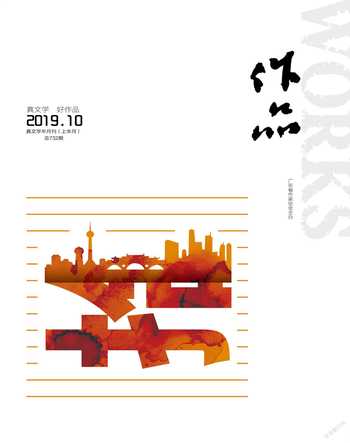成长的现实画卷(评论)
2019-09-10洪艳熊焕颖阿探李涛石凌
洪艳 熊焕颖 阿探 李涛 石凌
成长小说的人间况味
广东湛江 洪艳
在文学书写的众多主题中,成长主题与爱的主题一样长盛不衰。读罢周岂衣的《十八岁》,我自然而然地将其归类于成长小说的主题行列之中。所以也就能理解在一些叙事背后,有些稚嫩的笔法和文本中鲜明的难以跳脱感伤、细密的青春抒情式的语言特质,以及埋藏着的无处安放的青春迷惘与独特的成长创伤。但我一直相信成长小说应有一种浓厚的社会启蒙价值,当然,周岂衣的《十八岁》也值得我们从这个视角去挖掘它的此般价值。
以成长为主题的小说,在叙事上有着程式化的套路可以寻迹,因为它的叙事结构一定跳脱不出“幼稚—受挫—释怀—长大成人”这样的逻辑框架。周岂衣把《十八岁》中的众多成长人物,用平行叙述的手法加以展现,但在塑造过程中,他们彼此之间却是交织联系着的,起到了人物在成长中互促和互证的效果。比如山上画室“状元班”里的“周岂衣”、马永泉、王琳琳、林一川、李嘉诚、胡生、朱雪莲等诸多的同学,甚至室友冯小小都有着各自成长的轨迹,但又在彼此的成长轨迹中照见自己的成长。值得一提的是,周岂衣将这些人物的成长圈囿在首尾接续式的结构中,即马永泉的死讯既为开端又为终结点画出的圆圈内。可以说这样的结构组合,打破了成长小说单一僵化的套路;也让这部小说与当下冠“青春”之名的浅薄言情文本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我相信这个距离,得益于《十八岁》呈现出的现代性和多元化特质。
所谓的“现代性”是《十八岁》所具备的启蒙特质:它将现行应试机制下青少年成长之殇做了呈现,在揭露人性恶面的同时,却又使人物在青春怅惘、迷途中努力生长出一种不屈的成长姿态,比如历经人间炼狱的冯小小在考前的归来,马永泉在零分后与我们共赴考场的淡定……凡此种种使得“现代性”在各色人物不断成长中,展现出了哈贝马斯所说的“一种未完成的构想”的可能。至少,作为读者而言,这种“未完成的构想”足以使我们在阅毕《十八岁》后仍会有一份审美延留存在心中,也能使我们在忆青春中继续生长,洞见生活表象之下潜藏的社会问题,思考人性背后的社会现状与变革的可能性。
而所谓的“多元化”特质,一是周岂衣将成长小说的叙事结构“幼稚—受挫—释怀—长大成人”的结局做了“成长夭折”与“成长希望”的处理。尤其是“成长夭折”,除了马永泉这样以死亡作为结局的夭折,也做了如冯小小这种右手腕粉碎性骨折致使梦想破灭的夭折,还有如李嘉诚这般生长不出责任感的精神夭折。二是成长小说因特殊的角色定位需要承担“教育”的重责。《十八岁》和其他成长小说一样,不可避免地使用了第一人称铺展成长时空,甚至作者在文本中用上了自己的本名以拉近真实。但《十八岁》一定不是一个封闭的话语场域,否则《作品》不可能将其冠以“虚构”文本之名刊出。所以我以为正是它的“多元化”的教育思考视角,使得《十八岁》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的故事,不似成人作家写成长小说一般要把回忆线拉长。《十八岁》的回忆光影是很切近的,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还原了未成年人为本位的原生态书写。它自然剔除了成人话语的哲理性批判规则,但却是将成长小说的教育性融合在塑造的各色人物血肉之中,全文本只是呈现。而文本单纯呈现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带出多元化解读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伴随着阅读视角和阅读层次的不断扩大,会显现出多样化的读解可能。而可赞的是,區别于冷峻客观的呈现或鲜明的成长小说说教的重责,周岂衣并未用《孔乙己》里那个店小二的“我”冷漠视角作画,而始终是用一种人间暖色做底,“我”在母爱温情中长大,也使得“我”必定带着善意和温暖去帮助所有同路人,祈愿他们在跨越一道又一道沟壑的时候获得成长的希望。
悖谬世界中的自我迷失
广西桂林 熊焕颖
周岂衣的《十八岁》与其说是一部高考题材的小说,不如说是一出关于成长、关于逐梦、关于自我价值追寻的悲剧。在这出悲剧中,学子们遭遇的不仅是孤独、黑暗、压抑、焦虑……最可怕的是遭遇自我迷失而不自知。在这个意义上,《十八岁》试图以个体的日常经验还原高考如何使莘莘学子迷失在一个悖谬的世界之中。
小说中的“山上画室”虽然是一所民办的艺考培训学校,但却具有强大的身体规训作用。它与全国任何一所高中一样,通过反复训练、时间管控、身体控制、激励机制、心理暗示等方式进行规训,规训的目的就是考上艺术类重点大学国美。从这组关系中,我们不难发现身体越是能服从就越是能考上重点大学,反之亦然。其中复读四年的马永泉便是迷信这组关系的极端例子。问题是,每个个体生命都是鲜活的、独特的存在,这才构成了丰富多元的大千世界。小说中存在两个明显对立的世界:一个是枯燥单调的学习世界,另一个是丰富多彩的恋爱世界。相比之下,我们会发现小说中描述的恋爱方式是趣味多元的,甚至不乏同性恋。在这个层面上,高考意味着追求个性与压抑个性之间的悖论,实现自我理想与泯灭自我价值之间的悖论,建构主体性与毁灭主体性之间的悖论。在这个悖论的世界中,那些挣扎奋进的学子或遍体鳞伤或心有余悸,他们该如何面对未来?
小说不仅力图呈现高考作为一个开放式的规训场域的复杂性和悖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在规训过程中主体性建构的彻底失败。
小说的标题“十八岁”不仅仅是一个年龄标志,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它代表个体的成年和壮大,象征着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最重要的是象征着主体性建构的达成。但主体性建构要有一个来源,有一个成长过程,也就是说到底是谁在塑造主体,如何塑造。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来看,主体性建构的达成是在自我技术与权力话语之间的一场博弈,即个体想按照自己的意志活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但这个意志并不是主体自行产生的,而是主体自身与外在的各种权力话语形式之间达成某种妥协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小说中的高考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形式或者规训机制,太过于强大,导致很多十八岁的鲜活个体还未完成主体建构,就已经迷失自我了。小说结尾描写了迷失自我价值、丧失存在意义的荒诞大学生活。这不是狗尾续貂,而是对高考神话的一种批判。
小说中的高考学子无一例外,都想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未来。也就是说,他们都把高考当作实现自我价值和完成主体建构的唯一途径,试图通过暂时压抑自我来实现更大自我的个性和自由。而在这一点上作者是绝望的。小说所揭示的恰恰是主体性在高考这场盛大的规训仪式之后丧失了建构的功能。换言之,这个文本是关于人的主体性建构彻底失败的悼亡词。
炙烤中失航的青春
陕西西安 阿探
《十八岁》不是青春的诗行,不是花季的盛放,而是纯情年代的告别与挽歌。不堪重负的青春动影,铸就了对背离教育本质规律的产业化荒诞世相陈列与犀利批判——高考已无关理想与艺术,只是心灵炙烤中的青春失航。小说批判无痕,隐藏艺术浑然天成。
高考过后一片荒凉,同窗作鸟兽散,散场的同学群沉入静寂。一条刺眼惊心的讣告,勾起十八岁青春被虐的记忆。对《十八岁》的追溯,是一种艰难的成长历程,是理想坠入坚硬大地碎裂的过程,更是社会对青春残酷冰冷地冲撞。青春以感性碎片的形式被素描,被定格,亦是一种束之高阁的行为语言,更是一种泣血的祭礼,从此藏匿本真走向理性与成熟。
小说简笔聚焦了一群艺考生,亦勾勒出了社会整体性概貌。被生活宠溺者的肆意妄为,生活优越者情感纠结的游弋,良善者被欺辱,底层者卑微、虚荣的追逐以及肉体与空花幻影的交换,贫困者脆弱崩溃的神经,艺术的真谛与虚构的生活,等等,高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抵达彼岸的一次跨越,然而真正的跨越者寥寥无几。所不同的是,高考对于更多的底层者意味着未来与一切。虽然几乎所有的人在做着同样的努力,但是努力的结果远远不同,对于有些人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对于更多的人则是命运的翻转,而这种翻转的几概几乎可忽略不计。马永泉的第四次艺考再次铩羽而归,看似只不过一连串偶然事件的反应,冯小小关键时刻的跌跤骨折似乎亦是意外,然而这只不过是高考影子下社会残酷法则正常不过的演绎。即便重演千次,或许结果依然如故。
周岂衣的过人之处在于将社会运行的残酷性了无痕迹地融入了青春叙事,强力凸显了此时代高考承载命运的分量,更是强化了十八岁青春成长过载的重量。这是一个羞于谈人生与理想的时代,所有经济通则驱逐罢黜了人生的非物质意义,高考不再是为理想而战,而沦为一场青春的撕裂。小说叙事专注,语言平淡而彰显力道,结构自然而然地不失大一统思维优越,重大主题以轻盈之态实现腾升。
更重要的是,周岂衣把人生常态上升为哲思,把具象升华为抽象的表达与起底式总结,最终完成了文本从不堪一击的感性横陈到坦然无惊理性凝铸的惊艳华丽转身,小说艺术性及完成度抵达预设目标。“而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是我们无法成为的人。有多少个我们,欺骗了多少个自己?有谁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总是有它既定的悲伤与离合。此时此刻我明白,一个人最可怕的,并不是焦虑、紧张和艰苦,而是,一睁开眼的迷茫和浩瀚无边的无所事事。”这既是一种青春的归结,又是小说余音的强化延宕。
青春的猛虎与蔷薇
四川达州 李涛
周岂衣的《十八岁》在青春文学中的存在,绝对是真实而又虚幻的。她的小说不是纯自然主义,而是带着厚重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让人无助、迷茫,同时又充满希望。她把对青春的关注、生命的純真、社会的本质跃然于纸上,也跃然于读者的脑海里。
青春题材的小说,无非是写关于年轻人的一些事。周岂衣也不例外,但是她超脱了青春本态,以既是参与者又是旁观者的身份,用纯真的语言还原纯真的青春。“纯真”这一形式,是她以全面的视角去诠释青春的深度,以及青春的走向和脉络。青春的深度就是这一批年轻人对过去、现在的反思和批判,对未来的迷茫、不知所措但也充满梦想而一往无前的精神矛盾。周岂衣表达出来的青春深度是犹豫的,也是羞涩的,同时充满忧郁和快乐。这源于她对青春本真的探源。
《十八岁》并不是固定的十八岁的年纪,它代指成年前后那个年纪,《十八岁》的青春,是这个时代必然的产物,它缔结于这个时代的走向和深度。《十八岁》的青春是冰与火、寒与热的交替物。周岂衣以参与者的身份用火去写十八岁的热,以旁观者的身份用冰去写十八岁的寒。《十八岁》正是年轻人在“那一时段”的镜像。“那一时段”,是属于无忧无虑的,也是属于奋勇向前的。而《十八岁》表现出来的“那一时段”,像是一场梦,在梦中经历了生死,也经历了“五味杂陈”,这种经历,让人眼里充满忧郁和坚定。梦醒时分,生命存在的痛感依然强烈,那种痛感使人精神麻木,在现实中时刻警醒。梦中和梦醒的通感,是连接虚幻与现实的纽带,只有刻骨,才能铭心。
小说的时间节点是中国高考前的三个月,这一时期正是中国高考前最具代表性的时间段。山上画室是除了学校以外另一个高考集中营。这个集中营的成员是一群十八岁左右的年轻人,而管理者是一群成年人。本该发生在成年人身上的生命的疼痛,被一群尚且纯真的人经受了,使之在这样的环境下,青春变得有骨有肉。周岂衣在小说中构建了层次性的生命场域,她辩证的看待了矛盾的产生和激化。
山上画室是一个小社会,作者在里面亲身经历了“十八岁”,同时她又超脱于小说,搭建了读者和小说的联系,使小说纹理清晰,情感外漏。小说的痛感来源于生命之间的联系。复读生老马,在理想的道路上高歌前进,最后堕入黑暗;饱经沧桑的冯小小,多次经受痛苦的折磨,依然奋勇斗争;单相思的马小淘,天真单纯,傻得让人可怜。这些生命构建的根基都来源于痛苦,而痛苦来源于社会本质,它是促使生命联系的诱因,使生命联系具有“酸甜苦辣”,所以周岂衣才会在这种痛苦的基础上,升华为青春的痛感。相对应的是,在写青春的痛感时,也写了青春的美感:排练春节晚会时的默契、一起偷偷喝酒的放松、互相关心时的温暖。青春的痛感和美感是同时存在的,这也是青春的矛盾,也正是这一矛盾,让整个青春完整具体,以至于周岂衣在写它时,是犹豫和羞涩的,也让小说带有沉重的现实感。
灯渐次熄灭,路依然漫长
甘肃平凉 石凌
十八岁的青春本应是生命中最激越最壮丽的歌,周岂衣的长篇小说《十八岁》却为青春谱写了一支祭歌,一群高中生朝着理想飞奔,路上的灯一盏接一盏地灭了。周岂衣采用回溯手法,带着读者逆流而上,为十八岁演奏了一曲激烈、跌宕的青春之歌。在私人化写作盛行的时代,《十八岁》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作品。
出身卑微的马永泉是求学路上的殉道者,他连考四届,孤注一掷搏命换来的是理想的破灭,伴随着理想塔的坍塌,他对人生的憧憬徹底幻灭,走投无路之下,他决绝地走上不归路。与马永泉出身相似,遭遇更加凄惨的冯小小像一根柔韧而顽强的藤,任凭生活的大风大浪一次次地袭击,她都选择了活下去。活着才有可能逆袭!小说通过冯小小把当代底层女青年可能遭遇的种种问题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母亲早逝,父亲消沉,冯小小在没有阳光照耀没有雨露滋润的石头缝隙中顽强地活着。考上大学改变命运是她人生最重的一根稻草,为此,她不惜牺牲贞洁与尊严,委身于两个有钱男人,她的行为没有得到父亲的理解,反而遭到父亲残忍的家暴与强奸。命运一次次把她投入炼狱,她都奇迹般活了下来,因为她有梦——考上大学是支撑她忍辱含垢活下去的明灯。然而,命运在最关键的时候再次把她狠狠地掷到地上——她竟然在考前摔断了手腕。在高考这场硝烟弥漫、节奏紧张的战场上,马永泉与冯小小像两匹跛脚马,尽管他们使出了十二分的努力,依然败在与努力无关的因素上。周岂衣剥葱一般,层层剥开生活真相,露出铁面獠牙的一面。
与马永泉、冯小小相比,其他同学的苦难似乎不能算作苦难。陷入单相思无力自拔的马小淘即使把自己低到尘埃里,也没有换来心上人的眷顾;长相一般、谦卑怯懦的王琳琳错把渣男的引诱当成爱情,失去贞操换来的竟然是人格侮辱。心高气傲的朱雪莲先是被一个所谓的导演欺骗、玩弄后抛弃,后又为一个没心没肺的渣男堕胎,十八岁的身体被现实一次次撕裂才换来她的成熟与冷静。林一川艺术天分极高,却一次次坠入同性恋中无法自拔。李嘉诚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处处留情却无情,是典型的渣男形象。胡生外表粗犷但内心细腻,责任感强,是作品中唯一的暖男形象……人物是长篇小说的灵魂,周岂衣用沉稳、凝重的笔调,直面青春期的矛盾与困惑,立体而深刻地反映了当代青年学生的精神状态,为当代文学画廊增添了一批崭新的人物形象。
稍感遗憾的是,作者对马永泉与冯小小结局的处理。他们都来自底层,都奋力与命运赛跑,却跌倒在高考的临界点上。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因素固然有出身原因,但对于底层青年而言,高考也许是他们逆袭的唯一出路。冯小小能在沼泽地里活下去就是奇迹,她完全可以通过高考摆脱命运的枷锁,但小说结尾却为她安排了一次意外,让她与梦想失之交臂,为十八岁的青春画上一个残缺的句号。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