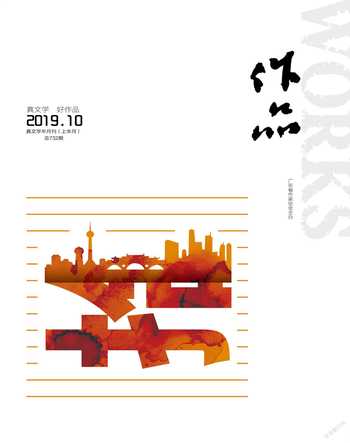从洞穴到地下室(随笔)
2019-09-10杨无锐
杨无锐
那晚,填完一堆表格,正喝闷酒,老友电话响起。每次都是这样,没有半点寒暄,劈头一句:“我咋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像柏拉图。”我放下酒,把表格推到一边:“这个话题好玩,愿闻其详。”
老友说:“陀老在《少年》里提到三种坏蛋,第一、第三两种是丧失罪感的人,这很像柏拉图的不可治愈的愚人。”
我说:“《罪与罚》里拉斯科尼柯夫们说的那些有权杀人的最新理论,《高尔吉亚篇》的卡利克勒、《理想国》的塞拉西马柯早就说过了。”
老友说:“柏拉图说当代雅典心灵的处境,是身处洞穴而仇恨光。陀老说当代俄罗斯心灵的处境是身处地下室而仇恨空气。洞穴和地下室,多有意味。”
我说:“此语甚有机锋,挂电话吧,这就去找你。”
那晚,我先填了一堆表格,然后跑去跟老友聊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至深夜,不亦乐乎。
下面的内容,是对夜谈的追忆。本想写成柏拉图对话录的样子。写了几行,我决定删掉“老友说”“我说”之类的废话,因为,这一点也不重要。
一、洞穴与地下室
写苏格拉底对话的柏拉图、写《地下室手记》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为灵魂分类的大师。现代人也热衷于分类。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的“白痴”梅什金公爵说:“只是由于懒惰,人们才从表面上把人加以分类。”(《白痴》)他和柏拉图关心的,不是这些外在事物,而是人的灵魂。他们辨别灵魂等级的尺度,是灵魂与光的关系,或者直接说,灵魂与光的距离。
《理想国》里,柏拉图把哲人定义为热爱光(智慧)、看见光的人。城邦里的多数人,则生活在洞穴里。洞穴里的人,未必不需要光,却惧怕光,渐渐忘记光,恼恨那些带来光之消息的人。《理想国》第8卷、第9卷,柏拉图写了一部政治的败坏史:从贵族制到寡头制,到民主制,再到僭主制。现代读者往往忽视,这部政治败坏史,同时也是灵魂沉降史。依照柏拉图,每种政体类型都对应一种灵魂类型。僭主政体当然是由僭主心灵缔造的。但僭主城邦里不只有一个僭主心灵。一个僭主城邦,会把城中所有臣民塑造成潜在的僭主。而在柏拉图那里,所谓僭主心灵,无非是欲望对灵魂实施独裁。僭主自己就是这样,他也需要把所有的臣民扭曲成这样。僭主心灵、僭主城邦,是洞穴人向洞穴深处沉降的最后绝境。洞穴人从依稀记得光,沉降成恨光之人。
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地下室手记》。陀老的这位“地下室人”,是现代版的洞穴人——恨光者。柏拉图笔下的僭主心灵,已被欲望接管,因而与光隔绝。尽管如此,他们仍有强悍的行动力、行动欲。柏拉图强调他们的盲目和狂暴。陀老的“地下室人”则连行动欲都已丧失。他高喊“地下室万岁”,却不热爱地下室。他只是害怕光,害怕人,害怕行动,因而除了地下室无处安身。跟柏拉图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用人与光的距离辨识灵魂的沉降。所谓害怕光,是对正义、爱欲、美善失去基本的反应能力。比如,“地下室人”反复思考复仇的问题。他说,对于过去的人而言,受辱、复仇,是本能一样自然的事。而在地下室,他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找到各种时髦理论,把受辱解释成公式般的必然,把复仇稀释成可笑的冲动。这个“地下室人”,从不缺少理论。他的理论太多了。以至于,从前的人们凭借德性、血性做出的任何事,在他这里都变得不可能。那些把他包裹起来的理论,个个不同,个个相似。每一个理论,都想要把世界简化成一个公式,或一张表格。而人,则只是一个代表必然性的统计数字、逻辑符号。当一个人被这样的理论俘获,他就仇恨自己身上的血性、德性,仇恨日光下的爱与正义。爱是累赘,正义是谎言。当然,这个“地下室人”仍旧喜欢“美”“崇高”之类的字眼。他如何喜欢呢?40岁那年,他在地下室斟上一杯酒,又往酒里滴几滴眼泪,“然后再为一切美与崇高的事物把酒喝干”。从此,他成了美与崇高的爱好者,“会在最丑恶、最无可怀疑的肮脏之中”找到它们,并且随时准备为它们哭泣,随时“眼泪汪汪,像块海绵”。他并不为此自豪,他只是无可奈何。他早已被公式表格、科学规律、历史逻辑驯化了。他知道在这些之外还有光、空气、生活,还有关于人的神秘。但他已是地下室的土著居民,公式表格、科学规律、历史逻辑是地下室的精神食粮。离开这些,他根本活不下去。他想出各种比喻,用以贬损自己:“没有个性的人”“耗子”“蒸馏瓶人”“没有意志的琴键”“不是活生生的父亲所生”……在贬损自己这件事上,他真诚极了,坦荡极了。只可惜,他仍然只能是他:在地下室呆了40年,并且将一直呆下去。
1864年很重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地下室人”。1866 年,他发表《罪与罚》。1868 年,《白痴》。1871年,《群魔》。1875年,《少年》。1880年,《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杰作里,“地下室人”的身影贯穿始终。拉斯科尼柯夫“不习惯人群”,“一个月以来,天天躲在角落里”,他的转租的小屋,像个衣柜(《罪与罚》);斯维德里盖洛夫对拉斯科尼柯夫说,地狱未必是什么庞然大物,可能只是“一间小房子,像乡下被熏得漆黑的澡堂,屋里个个角落都爬满蜘蛛”,直到永远(《罪与罚》);肺痨少年伊波利特寄居斗室,撰写对人类的控诉词,他也在梦里看见了满屋子蜘蛛(《白痴》);工程师基里洛夫坚信,唯有自杀才能证明人就是上帝,他在空荡荡的小屋里彻夜喝茶沉思,等待那一刻的到来(《群魔》);基里洛夫、沙托夫有个共同的导师——斯塔罗夫金,他在空气清新的瑞士买了一幢“小小的房子”,一场人间闹剧之后,他回到小小的房间,把自己吊死(《群魔》);大学生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在自己的斗室里撰写宗教大法官判处上帝死刑的诗剧,也是在这里,与夜访的魔鬼相互谩骂(《卡拉马佐夫兄弟》);而伊凡的追随者和代理人斯梅尔佳科夫,杀人之后,在另一间斗室把自己吊死在一个钉子上(《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在逼仄的空间里绝望着的人,是陀氏小说最阴郁最毛骨悚然的部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正主题,不是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绝望,而是信、望、爱。但陀老之所以是陀老,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要想在现代世界谈论信、望、爱,必须先研究这种毛骨悚然的绝望;戳穿地下室,才能把人从地下室里拉出来,让他们重新记起光。
二、上行与下行
别林斯基只喜欢《穷人》。纪德则说《地下室手记》是陀老小说的穹顶。
只写《穷人》的陀老,不是陀老。《穷人》干净、慈悲,却尚未降至灵魂深处,因而未曾触碰现代心灵之苦况。只写《地下室手记》的陀老,也不是陀老。《地下室手记》锋利、残酷,降得够深,绝望至极。但陀老并非那种热衷于摆弄绝望的存在主义作家。他把灵魂推到绝望的边缘,是要为救赎廓清道路。正如柏拉图,不是要用僭主统治诅咒雅典人,而是要用僭主绝境提醒雅典人:生活不应如此。
《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引导着朋友们,开启一次先上行再下行的心灵之旅。上行之旅,朋友们见识了城邦和灵魂应有的样子。然后,大家带着对美善事物的见识下行,渐次辨别灵魂的败坏。必须见识过好,才能识别坏;对好见多识广的人,才能对坏辨析幽微。这是柏拉图的重要洞见。所以,他筆下的心灵之旅,必须先上行,再下行。最终,朋友们见识了好,也识别了坏。旅行结束,生活开始。带着这些见识,朋友们得以重审自身之处境,并对自己的灵魂状况施以诊疗:那是生活的上行。
陀老的小说,也有类似的上行、下行结构。他要用《穷人》写出人的美与善,也要用《地下室手记》写出人的罪与愚。《罪与罚》之后的每一部杰作,陀老都用一群“上行人物”照亮一群“下行人物”。他的意图,是让“下行人物”认出自己。在他笔下,所有灵魂沉降的“下行人物”都喜欢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但他们全都无力认识自己。唯有通过“上行人物”的引导、映衬、照亮,他们才能认识罪,接受罚,重启“活生生的生活”。没有苏格拉底的引导,卡利克勒和塞拉西马柯会永远陶醉于权力即正义的梦话(《高尔吉亚篇》《理想国》)。没有拉祖米欣和索尼娅的爱,拉斯科尼柯夫会永远相信自己是偶然失手的拿破仑(《罪与罚》)。没有梅什金公爵白痴般的慈悲,罗戈任、娜斯塔霞的疯癫爱欲就得不到宽恕和洁净(《白痴》)。没有朝圣者马卡尔的爽朗笑声,少年阿尔卡季有可能成长为另一个拉斯科尼柯夫(《少年》)。没有阿廖沙的墓畔赠言,伊凡的“宗教大法官”可能被误会成终极真理。没有那些“上行人物”,“下行人物”会陷入自我崇拜,自以为发现了真理,自以为可以用“真理”捏造出某种全新生活。直至某个神秘时刻,他们忽然发现,自己所谓的真理和生活,只是地下室里的虚构。而“活生生的生活”,就在大地之上。每当写到这里,陀老都会说:“那将是另一个故事了。”他笔下所有的明净故事、阴暗故事,都是为了引人眺望、开启那“另一个故事”。
柏拉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灵魂分类大师。他们各自上穷碧落下黄泉,探索灵魂的光谱。《理想国》里,柏拉图谈论了五种心灵。《斐德罗篇》里,灵魂等级扩充为九种。要把握陀老笔下的灵魂光谱,最方便的参照,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老三阿廖沙,是那种怀抱信、望、爱的“上行的人”。老大米佳,代表活在“玛利亚和索多玛”之间的,“大地上的人”。老二伊凡,是那种憎恨信、望、爱的“下行人物”,或者说,“地下室人”。
三、上行的人
《白痴》的梅什金公爵、《群魔》的吉洪(见通行本“附录”)、《少年》的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佐西马长老和阿廖沙,他们是陀老笔下的“上行的人”。
“上行的人”是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们在心灵的上行之旅渐至顶点时,才能见识到的灵魂。这样的灵魂,柏拉图称为“哲学家”“爱智者”。他们的主要特征,不是良善、纯洁,而是灵魂向世界的神性本源敞开。套用柏拉图的譬喻,他们是热爱光、见过光的人,是在洞穴人中间徒劳叮咛,想要帮人们记起光的人。这样的人,在洞穴人眼里,是笨拙、啰唆的废物,是对洞穴生存技术一无所知的白痴。故而,洞穴人总要羞辱他们、赶走他们、除掉他们,以求清静。而柏拉图却坚称,只有这样的人才配成为城邦的王和法官。柏拉图的“哲人王”常常遭到现代读者的误解和指控。那不过是因为,现代读者太过熟悉僭主心灵,根本不相信灵魂还有别的可能。对他们而言,“哲人王”只能意味着满口谎言的僭主。其实提到“哲人王”时,柏拉图强调的并非王的无限权力,而是哲人的有序灵魂。哲人的灵魂,向神性本源敞开,受神性本源整饬,因而完整有序。哲人既知道欲望的苦乐,也知道理智的价值,更知道智慧的神圣。哲人是对灵魂里的一切事务深有体验的人。他见识过好的,因而能认出坏的,还能识别各种伪装成好的坏。
这就是柏拉图的心理学:知道什么是完整,才能理解破碎;体尝过有序,才能懂得无序;向上眺望过的眼睛,才能凝视深渊。人对人的理解,只能自上而下,反之则荒唐。柏拉图说:“那些没有经历智慧和美德,始终热衷于吃喝的人会下降,终其一生就在中间和下面变动,绝无可能超越这个范围。他们不会向上仰望真正的上界,或向上攀援进入这个区域……他们的眼睛只会向下看……永远那么贪婪。”(《理想国》第9卷)一个永远向下看的人,永远不会明白向上看的人在说些什么,甚至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是在向下看,除非,他因机缘巧合,把一个完整有序的灵魂当成自己的镜子。
陀老笔下的“上行的人”,很难让人想起“哲人王”,因为他们身上无不带着浓厚的斯拉夫、东正教情调。但恰恰在最重要的一点上,陀老和柏拉图相通:唯有圣徒,才拥有最广博最深刻的理解力;唯有圣徒才能洞悉发生在灵魂里的那些事——苦、爱、恨、罪、愚。柏拉图并未赋予“哲人王”真实的肉身,也未让“哲人王”实施现实的建国和统治。他的“哲人王”更像折射日光的镜子,用以帮人识别伪装成哲人的僭主。陀老的现代圣徒们,也都不是积极的行动者。陀老让他们穿行于人群之中,唯有透过他们,陀老才能说清那些发生于现代灵魂里的惊悚故事。
白痴梅什金公爵,是陀老创造的第一位“上行的人”。他自幼为癫痫所苦,寄养在瑞士深山,对人间事务缺乏基本的知识。经过一番人间的情欲闹剧,他又回到瑞士深山,彻底丧失意识,成为名副其实的白痴。这位白痴,匆匆闯进人间,又匆匆离去,没有改变任何事,没有挽救任何人。但正是这位白痴,让一幕乏味的情欲闹剧,变成一部可以理解的灵魂悲剧。小说一开篇,陀老就把最为惊人的心理洞察力赋予白痴。他津津有味地谈论狱中的囚徒、断头台前的濒死者。他从这些濒死者的心里发现重生的渴望。他能理解罪人,也能理解孩子。在瑞士山里,他能很快让孩子们敞开心扉。他能理解短暂人间之旅遇见的每一个人。只有他知道,被侮辱被损害的娜斯塔霞为何渴望自毁;只有他看出,被情欲、嫉妒折磨的罗戈任,竟是一位挣扎在罪与信之间的斗士;只有他明白,那个一边忏悔一边骗钱的无赖,也能在虚假的忏悔里说出一些高尚的实情。无赖这样评价白痴:
您那样忠厚老实,那样天真无邪,即使在黄金时代也闻所未闻,与此同时,您突然用无比深刻的心理观察,像利剑一样把人都看穿了(《白痴》第424 页)。
肺痨少年伊波利特,在自己的世界里怨恨人类,却又不知拿尚未消失的对人的爱意如何是好。只有在白痴面前,他才发表那番绝望的独白。他对白痴说:“您什么也不要说;您站好……我想要看看您的眼睛……您就这样站着,让我看。我要跟一个大写的人告别。”(《白痴》第556 页)
梅什金公爵既是白痴,又是无比深刻的心理学家,既是无足轻重的外乡人,又是闯入故乡的大写的人。他诚然未曾改变任何事,但他把爱给了渴望自毁的娜斯塔霞,他与行凶者罗戈任成了兄弟,替他安魂,他倾听了每一个愤怒者、绝望者。他也曾感到疲惫,想要逃离:“他突然想撇下這里的一切,回到他来的地方去,到更远的地方,到穷乡僻壤去,而且马上就走。”但是没过十分钟,他就意识到逃跑是不行的:“在他面前摆着一些难题,他甚至没有任何权利不去解决它们,或者至少也应尽全力去解决。他这样想着,回到了家。”等到爱了、宽恕了、倾听了,他才再次回到来的地方。这位“上行的人”,为一大事因缘进入人间,因缘已尽,又离开人间,归于寂灭。他的身上,有耶稣和佛陀的光影。
《白痴》之后的“上行的人”,也都被赋予深邃的心理洞察力。《群魔》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物,是斯塔罗夫金。斯塔罗夫金最坦诚的自白,发表于谒见吉洪长老的时刻。斯塔罗夫金不停地说,吉洪只是听。他在不经意间说了一句“我爱您”,又在不经意间告诉斯塔罗夫金,他离耶稣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远。这时,斯塔罗夫金生气了。这个人几乎从来不生气,这次不同寻常,他觉得好像被人看穿了:
听我说,我不喜欢密探和心理学家,至少是那些探测我的心灵的人。我不呼唤任何人进入到我的心灵里来,我不需要任何人,我自己能够对付(《群魔》第846 页)。
这是整部小说里,魔鬼斯塔罗夫金最虚张声势的时刻。《少年》里的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佐西马长老,共享很多信念和言论。陀老可能有意借助他们表达自己对某些最重要问题的看法,比如,对俄罗斯命运的看法、对东正教使命的看法、对现代的科学主义的看法、对虔敬生活的看法。
马卡尔给少年讲了很多罪人和无神论者的故事。让少年惊异的是,这个几乎不识字的乡下人,对现代科学家的生活相当熟悉,更对现代那些博学的无神论者的心灵状况洞若观火。作为现代心灵战争主要论题的“科学与信仰之争”,在马卡尔那里,竟然轻易化解了。他告诉少年,科学家的显微镜很好:“这是伟大的了不起的事,是上帝赐予人的本领。上帝不是白白地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的:‘活着,去认识一切吧。’”与显微镜无关的秘密同样很好。马卡尔说,他见过的最博学的人,也解决不了他们自己这个大秘密。只不过,有的人因秘密而快活,有的人因秘密而愁眉苦脸,瞎忙。马卡尔不认为那些愁眉苦脸的无神论者是上帝的敌人,只是同情他们的瞎忙。
佐西马是卡拉马佐夫三兄弟的导师。他给老三阿廖沙的建议之一,是走入人间,让信仰经受淬炼,尤其是经受种种现代偶像崇拜的淬炼。他给阿廖沙的另一个建议,是在这场悲剧落幕之前,尽可能去陪伴父亲和兄长,听他们说话。阿廖沙的这个使命,很像梅什金公爵进入人间的使命——充当镜子。那些陷进苦难和仇恨的人需要这面镜子。没有这面镜子,他们会把自己想得太好(不信),或把自己想得太坏(不望),骨肉相连却骨肉相残(不爱)。
陪伴父兄,是阿廖沙走入人间的第一桩试炼。老卡拉马佐夫为情欲所苦。老大米佳的情欲里还包含着嫉妒、羞愧、愤怒。老二伊凡为思想所困。他跟着自己的思想沉降到心灵至暗之地,他对世界的愤怒,远比米佳贫血,远比米佳冷酷。三人各自受苦,彼此羞辱。他们绝不相信可以彼此理解,甚至不相信可以弄明白自己。但他们都向阿廖沙袒露心迹。倘若世间还有人可以明白这些沉降灵魂的苦,那只能是阿廖沙这样的人。
梅什金公爵的人间之行草草结束。马卡尔和佐西马分别指导了一个少年,然后离开。阿廖沙则属于未来。在《作者的话》里,陀老说他“尚未定型,难以捉摸”,而且因为“明净如水”,肯定被这个时代视为“怪物”。但是,陀老说,像这样的“怪物”,说不定在某个时候成为社会的中心,而现在,只是因为某种奇怪的风潮,大家暂时远离他而已。这可能就是陀老对“上行的人”的期待:生活需要他们,他们本该成为生活的中心;但他们往往被需要他们的人视为异类;但他们毕竟是人间的镜子,也是人间的种子。这不就是柏拉图“哲人王”的命运吗?
《卡拉马佐夫兄弟》没有写完。据说,陀老打算让阿廖沙投身革命,然后死去。陀老留给未来的革命,肯定不是《群魔》里的那种革命。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里隐约看见的城邦,不是处死苏格拉底的雅典。这部未完成之作,结束于阿廖沙的墓畔谈话。阿廖沙在一群孩子的环绕中讲述爱与记忆。这是陀老小说里最明净的、献给未来的段落——恰到好处的未完成。
四、大地上的人
《卡拉马佐夫》开篇不久,米佳和伊凡分别找阿廖沙长谈。伊凡的谈话,就包括那篇著名的《宗教大法官》。哲学家和评论家们太看重伊凡的沉思了。其实,唯有把伊凡的看似深刻的沉思跟米佳的醉话连在一起,它才是可以理解的。
《宗教大法官》说:为了如今的卑微生灵,必须把奥秘从大地上割除;那带着奥秘重回大地的人,必须放逐或杀死;卑微的生灵担不起赐给他们的自由,所以只配活在一个强者的自由的奴役之下。从开篇的《宗教大法官》到结尾的《魔鬼夜访伊凡》,伊凡的所有煎熬,都围绕着这个“秘密”。他想凭理智破解这个秘密。当他带着这个雄心沉降的灵魂的至暗之地,活在仇恨秘密、否定秘密,又渴望秘密的撕裂之中。
陀老的小说,几乎都有一个常见于报纸的刑侦故事外壳。参照这个外壳,伊凡是查无实证的弑父者,米佳则是最像凶手的蒙冤者。杀人与未曾杀人,根本不是米佳和伊凡的真正区别。他们的真正区别是:一个仇恨秘密,一个承认秘密。
见到阿廖沙时,米佳喝了不少酒。他絮絮叨叨讲述自己的情欲经历,忽然就背起普希金和席勒来。他说,每当沉湎于最最无耻的荒淫之中,就背诵席勒。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掉进深渊,但他还想亲吻上帝的裙摆。他感到怨愤、耻辱,但他也时常感到爱和快乐。单单从他自己身上,他就知道,人,是一个很大的谜。人,不是玛利亚,也不是索多玛,而是从玛利亚到索多玛之间的广阔疆域。单单从他自己身上,他就知道,这片疆域何其广大,不可捉摸:
糟就糟在这里,因为一切在世界上都是一个谜!……有许多神秘莫测的东西!人世间,有许许多多哑谜压在我们头上……有的人,甚至心灵高尚、智力超群的人,也是从圣母的理想开始,以索多玛的理想告终。更可怕的是有人心里已经抱着索多玛的理想,但是他又不否认圣母的理想,而且他的心还在因此而燃烧,真的,真的在燃烧,就像天真无邪的少年时代那样。不,人是博大的,甚至太博大了,我恨不得他能够偏狭些。鬼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卡拉马佐夫兄弟》 第161 页)。
一些人爱着、恨着、受苦、犯罪,但他们始终承认世界是个谜。特别是当他们对自己感到无能为力时,他们感到自己就是最难解的谜。既然是谜,就可以堕落得很深很深,也可能在奇迹中重生。米佳是个大老粗,但陀老让他用酒话道出了人之真相。
人之真相,即,人是秘密。博学善辩的伊凡,则耗尽心智否定这个真相。他用才智建造碉堡,把真相挡在外面。米佳希望人能变得偏狭些,因为那样人就会活得轻松。比如,如果偏狭成昆虫,人就可以轻松自在享受情欲。可是米佳知道,那不可能。伊凡在斗室里思考出一种偏狭的人,偏狭如虱子或蜘蛛的人。然后,他觉得自己有权力蔑视这样的人、碾死这样的人。当然,他并未因此感到轻松。他病得比米佳深,罪得比米佳深。米佳是大地上的人,伊凡凭借才智沉降為地下室人。
讲述大地上的人的故事,陀老堪称大师。几乎所有伟大的俄罗斯小说家,都是这方面的大师。陀老的惊人之处是,不只写出人之复杂,更写出人之广阔。他的确在玛利亚和索多玛这个无比广阔的领域里观察人。《穷人》《白夜》都是感人肺腑的大地上的人的故事。那是水一般明净温柔的大地上的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写受辱者的愤恨、宽恕、在爱中救赎,也写那种以行凶为美的属灵的罪。《死屋手记》写那些被社会弃绝的罪人,在他们身上发现美、善,也发现无法由司法审判割除的恶。西伯利亚的那座囚堡,似乎是陀老后来所有小说的隐喻:一群罪人生活在一起,谁又不是罪人呢;人的使命,是在罪人中认识罪,也在罪人中发现美和善。
《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之后那些更伟大的长篇里,陀老写了无数个“大地上的人”。他们大多数属于次要角色。但他们每一个都在玛利亚和索多玛之间挣扎浮沉,身上有黑暗,也有光。而他们的复杂光影,只有在“上行的人”的观照之下,才显得完整。
《白痴》里的列别捷夫,是社会意义上的平庸狡猾之辈,陀老借着梅什金公爵的眼睛,在他身上发现对家人的爱、对时代的悲愤;罗戈任是刑事意义的凶徒,梅什金公爵在他身上发现一个挣扎在情欲和信仰之间的斗士。《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革职的步兵上尉斯涅吉廖夫怯懦卑微,他的儿子伊柳莎暴躁无礼,只有阿廖沙,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对尊严和爱的渴欲。《少年》里那个叫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的地主,依照大地上所有标准,都是不可原谅的恶人。可是朝圣者马卡尔从容不迫地讲述了他的一生:行凶、恐惧、悔改、救赎。马卡尔讲述这个故事,是想让少年知道,对于人这个谜,要给予多大的耐心和敬畏。
“上行的人”看得见这个谜,带着谜上路。“大地上的人”,在谜里挣扎,忍耐,盼望。“地下室人”,不相信这个谜。不相信这个谜的人,也就不再相信罪与救赎,反过来,他们崇拜自己的才智和权力。陀老的那些“大地上的人”,没有一个傲慢至此。酒鬼马拉美多夫磕磕巴巴地对看热闹的人讲《路加福音》:
等把所有人所有的人审判完毕,他就会对我们说:“你们也过来吧!过来吧,酒鬼们,过来吧,懦弱无力的人们,过来吧,不知羞耻的人们。”那时我们就一点儿不羞愧地站过去。他会说:“你们是一群猪!是牲口的模样,有着牲口的记号;不过,你们也来吧。”于是大智大会和精通事理的人们说:“主啊,为什么接纳这些人哪?”他会说:“……我之所以接纳他们,是因为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认为自己对此是受之无愧的。”(《罪与罚》第29 页)
为何不会觉得受之无愧?因为对于“大地上的人”,生活和天国,永远是个谜。米佳的坏脾气,跟伊凡的傲慢,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米佳的坏脾气,是大地上的坏脾气。伊凡的傲慢,是地下室的傲慢。
五、地下室人
《少年》里,少年阿尔卡沙为了炫耀聪明,说出了三种坏蛋的理论:
一种是无知的坏蛋,就是说,他们自信干的坏事绝顶高尚;第二种人是知道羞耻的坏蛋,就是说,他们对自己干的坏事感到羞愧,但由于决心已定,还是继续干到底;最后一种是地道的坏蛋,真正的坏蛋……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当穷人孩子快饿死的时候,他用面包和肉去喂狗(《少年》第72 页)。
那些有羞耻感的坏蛋,正是陀老笔下无数个“大地上的人”,不会觉得进天国受之无愧的人。地道的以作恶为乐的坏蛋,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里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是《死屋手记》里的 A——夫,或者,《少年》里的兰伯特。这样的人,陀老称之为“精神上的夸西莫多”(《死屋手记》第98页)。他写了这样的人,但似乎不愿多写。他要着意研究的,是所谓的“无知的坏蛋”。这里的“无知”与“受教育程度”毫无关系,甚至与识文断字毫无关系。在柏拉图那里,根本的“无知”,是对正义的扭曲、对美善的麻木。少年阿尔卡沙的表述,无意间接通了这个古老传统。
纯粹的坏蛋,不可治愈。无知的坏蛋,难以治愈。不可治愈,因为毫无罪感。难以治愈,因为他们的罪感被他们的“无知”扭曲了。这种“无知”,自古有之。陀老发现,在现代世界,“无知”常常表现为博学。正是各种畸形的博学,让人把罪恶扭曲成崇高。“无知的坏蛋”的另一种表述是,“地下室人”(《少年》“前言稿”)。
《地下室手记》里,陀老的“地下室人”处于生活的瘫痪状态。这种瘫痪,是一种“理性的瘫痪”。地下室人是由各种现代理论喂养长大的。这些理论无不声称可以破解世界之谜、人之谜。破解之道,就是把世界压缩成规律、逻辑、统计表格,把人贬低成规律的注脚、逻辑的常量、表格的数字。于是,世界和人没有神秘可言,只剩下“理性”和“必然”。然而,根据“理性”和“必然”,人可以做什么呢?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无须做。一个崇拜“必然”的人会告诉自己: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都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因此必须接受、忍受、享受;一切对规律的质疑、对逻辑的抗拒、对表格的厌恶,都是不理性的、徒劳的、蠢的。“地下室人”就被锁在“理性”“必然”编造的牢笼里,无所事事。他可以忍受一切,但不是基督徒出于自由意志的忍辱。他忍受,只是看不到世界有任何自由可言。
紧接着《地下室手记》,是《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这几部大书。陀老把“地下室人”扩展成一个序列:《罪与罚》的拉斯科尼柯夫,《白痴》的伊波利特,《群魔》的群魔们,《少年》的韦尔西洛夫父子,《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伊凡……这是一组“地下室人”群像。陀老告诉读者,“地下室人”的病,不只有“理性的瘫痪”,还有“理性的疯癫”。
在柏拉图那里,“理性”指灵魂对神圣本源的爱欲和探究。在陀老的 19 世纪,“理性”仅仅指合乎算术的心智模式。从18世纪到19世纪,这种算术心智成为人类最新的偶像崇拜。人们相信,它是真正的救世主。想要过上好生活,除了“理性”,不需要别的了。“地下室人”发现,对这种“理性”的崇拜,榨干了自己身上的血性、德性,因此生活瘫痪了。假若他想挣脱这种瘫痪状态,唯一的办法是,更加疯狂地崇拜“理性”,按“理性”的指引大胆行事。“理性”的算術显示,需要杀人,那么就去杀人;“理性”的算术显示,需要自杀,那么就去自杀。要么陷入瘫痪无所事事,要么疯狂行事:“地下室人”就在这两端徘徊。
《罪与罚》。大学生拉斯科尼柯夫根据“理性”推算,断言人只有两种:拿破仑和虱子。拿破仑是世界的主宰,虱子只不过是世界的材料。拿破仑当然可以碾死虱子,只要觉得必要。他穷困潦倒,把自己关在一间像是衣柜的小屋里,怕见女房东,怕见任何人。他就在屋子里推算拿破仑对虱子的权力。除此之外,无所事事。7月初的一天,他出门,杀了放高利贷的老女人和她的妹妹。
《群魔》。革命理论家希加廖夫根据“理性”推算,为人类规划了一条通往自由之路:把人类分成不相等的两个部分。十分之一的人享有自由和支配其余十分之九的人的无限权力。这十分之九的人应当丧失他们的个性,变成类似牲畜的群体。在无限权力和无限服从中,人类恢复原始人的淳朴,重回伊甸园。希加廖夫说,这就是人类的必然规律:从无限的自由出发,以无限的专制结束。革命小组的另一位理论家说,为了更快地改造世界,应该先砍掉一亿个脑袋。革命小组的头头韦尔霍文斯基说,这些理论仍然只是空想,远水不解近渴。当务之急,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制造混乱,砸碎旧世界。制造混乱的前提,是保证组织团结。保证组织团结的办法,是在谈论砍掉一亿个脑袋的空话之前切实杀掉一个人。于是,革命小组集体行动,杀了一个人。
《群魔》。美丽的魔鬼斯塔罗夫金,出于无聊,推演出两套理论。一套是说,在没有上帝的时候,要把民族提升到上帝的地位。另一套是说,在没有上帝的时候,人要把自己提升到上帝的地位。前一套理论,征服了大学生沙托夫。于是,沙托夫参加旨在破坏的“小组”,又被“小组”杀掉,成为保持“团结”的祭品。后一套理论,征服了工程师基里洛夫。于是,基里洛夫把自杀当成头等大事。因为,没有上帝的时候,人是自己的绝对主宰。如何证明人对自己的主宰权呢?杀掉自己。基里洛夫根据这个理论杀了自己。
《少年》。性情宽和的年轻人克拉夫特对俄罗斯做了两年研究,根据生理学推导出数据坚实的结论:俄罗斯民族是世界上的二等民族,它的使命仅仅是给更卓越的民族充当材料。克拉夫特对自己的推理深信不疑,把自己这个二等民族的成员杀掉了。
《卡拉马佐夫兄弟》。对神学颇有研究的伊凡,在斗室里写了一部雄伟的诗剧。这部诗剧的主要理论是:上帝给人自由意志,要人用自由意志去信、望、爱。而人,根本不配拥有自由意志,承受不了自由之重负。唯一的办法,是由强者接管所有人的自由,背负起自由之重负。配不上自由的人,只能在强者的照管下,过他们配过的生活。这是他们最好的出路。为了帮这些弱者解除自由的重负,必须杀死重回人间的上帝。伊凡在笔记本里写下杀死上帝的诗剧,然后告诉自己的兄弟:如果没有上帝,什么事都可以做,包括杀人。同父异母的弟弟斯梅尔佳科夫听了这些话,就杀掉了老卡拉马佐夫,又杀了自己。
“地下室人”,或者依照理性瘫痪,或者依照理性疯狂。无论无所事事还是杀人自杀,他们都被某种“理性”裹挟着。他们崇拜自己的“理性”,以至于丧失了对世界和生活的直觉。仅凭直觉,米佳就知道人是个谜,就想要亲吻大地母亲和上帝的裙摆。拉斯科尼柯夫和伊凡却感觉不到,因此,他们只能效忠于“理性”,为“理性”杀人、自杀。当他们这样做时,甚至会从心底生出英雄气概:我是唯一有勇气接受冷冰冰的“理性”的人;我是唯一有能力推动“理性”早日降临于大地的人;我不曾犯罪,我是英雄。
伊凡远比米佳有学问,但伊凡才是“无知的坏蛋”。他的学问和“理性”,是地下室里的学问和“理性”。或者说,这种学问和“理性”,就是心灵的地下室。正是这样的学问和“理性”,让他成了“无知的坏蛋”。
六、地下室人编年史
从“大地上的人”到“地下室人”,是灵魂的沉降。从《群魔》起,陀老不只关心“地下室人”这种灵魂现象,似乎还想梳理出一部“地下室人”的灵魂沉降史。《群魔》写了两代人,《少年》写了两代人,《卡拉马佐夫兄弟》也写了两代人。其中的“地下室人”之间,不仅有生理、社会上的代际关系,还有心灵上的代际关系。现代世界的形成,不只是苹果手机和原子弹的发明史,还是一部“地下室人”的编年史。
《群魔》的第一代,是自由主义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少年》的第一代,是自由主义者韦尔西洛夫。陀老是在俄罗斯语境里使用“自由主义”这个词的。他们是把欧洲时髦词语、话题带回俄罗斯的人,他们相信,有了这些词语和话题,人们可以不必再去操心上帝。
《群魔》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开篇,也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结束。陀老为他画了一幅细腻的漫画。这幅漫画的主要特征,不是思想,不是行动,而是慵懒和闲谈。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身边,聚集了一批“高级自由主义者”。这些人的每日工作,就是打牌和闲谈。老自由主义者时常无所事事,侧身而卧。他和牌友们一边打牌一边谴责:“打牌!我坐下来跟你们玩叶拉拉什牌!难道这相称吗?谁应对此负责?谁使我的事业归于毁灭而变成一场叶拉拉?唉,让俄国完蛋吧!”于是他气派十足地打出一张红桃五(《群魔》 第13页)。这个妙语如珠的老名士,谈论俄国,也谈论上帝。他的本领是把一切都变成闲话。对于俄罗斯,这位接受女地主供养的清客早已隔膜。对于上帝,他已多年不读《福音书》,脱口而出的一点儿教义谈资,都是从敌基督者的书里看来的。小说快要结束时,他觉得被时代和恩主抛弃了。为了捍卫尊严,他发表了一篇演讲,然后离家出走。演讲时,他告诉听众,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美,美在人类一切追求里是最高的,也是最终的。离家出走时,他对邂逅的女人编造往昔罗曼史,想要和这女人发生新的罗曼史。
《少年》的韦尔西洛夫似乎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改写。陀老去掉了加在斯捷潘身上的漫画成分。韦尔西洛夫自称俄罗斯的“一千个自由主义者”之一。他爱俄罗斯,也爱欧洲。他对欧洲的历史和思想了若指掌,甚至比法国人、德国人更能在欧洲找到故乡之感。他对现代欧洲和俄罗斯的情况甚为忧心。他知道,丧失信仰、敬畏、礼法之后,世界可能走向疯狂。但若有人问他此刻应该做些什么,他说:“最好什么都不干,至少能因为什么都没有参与过而感到心安。”(《少年》第281页)他属于没落贵族,还保有对贵族风度的记忆和爱好。他知道应该爱人。但他说,他只有闭上眼睛、捂住鼻子才能不讨厌人。他知道应该担负责任。仅仅为了这个“应该”,他才在几番抛弃之后,善待不合法的妻子。“他心里装着黄金时代,知道无神论的未来景象”,这是儿子对他的概括。他的确是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但这些“知道”只是抽象的道理,从这些“知道”里,长不出生活的力量和秩序。小说结尾,韦尔西洛夫分裂成“两个我”,一个是“知道”黄金时代的我,一个是为“情欲”所苦的我。“两个我”合力,卷入一场情欲闹剧。恰恰是在这里,读者隐约认出,他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兄弟。
陀老把韦尔西洛夫们叫作“退场者”(《少年》“结尾”)。他们身上还有往昔时代的余晖。他们有理想,看重尊严,关心世界,颇有学问,还带着老派人物的高贵。但也正是他们,为新的时代制造了真空。生活上,他们自己就是失序者,因此无力为下一代提供秩序。思想上,他们是把旧日信仰、域外思想变成谈资的人。他们谈论一切,但也仅仅是谈论。他们所谈的,没有一样能在自己身上扎根,更没有什么能成为下一代人的根。充其量,他们只能让自己守住所剩不多的体面和激情。守住体面,是依靠对美的残存信念;守住激情,则只能靠自己也收拾不住的情欲。这些“退场者”,以可怜可笑有时可悲的方式终结了往昔时代。
陀老的意图很明显:正是这些“退场者”,担当了现代世界的教育者;可这些“退场者”,偏偏无力承担教育;他们留给未来的,不是遗产,而是真空。信仰的真空、思想的真空、生活秩序的真空。有真空的地方,就有填补真空的渴望。那些接受“退场者”教育的人,其实算是精神的失怙者。他们会带着复仇般的怨愤,把自己的精神真空填满,少年阿尔卡沙就是这样的人。他是韦尔西洛夫的私生子。开始,他想要抓住某种可靠的“思想”。审视了众多流俗“思想”之后,他决定发明一套自己的“思想”。这套“思想”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相信只要抓住它,就可以摆脱虚无,超越世俗。很快他就发现,“思想”本身就飘忽不定:“思想”可以为他所做的坏事开脱,同时,“思想”又从未坚定到压制他行善的渴望。既然如此,所谓“思想”就对生活起不了什么作用。少年求助于韦尔西洛夫,想从他的那些抽象谈话里获得生活指南。可是,他先是发现韦尔西洛夫只能谈论抽象的东西,继而亲历韦尔西洛夫的“分裂”和情欲闹剧。他能从父亲身上得到的启示,不像想象中那般坚实。直至遇到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这个“上行人物”,少年才意识到“人品”比“思想”重要。少年所说的“人品”,可以理解为精神和生活的秩序。马卡尔让他见识到活在秩序里的样子。
《少年》是一个精神失怙的孩子谋求对自己的教育和拯救的故事。当一个人的心灵处于真空之时,很容易抓住某个“思想”,复仇般地崇拜它。少年阿尔卡沙启灵于自己编造的“思想”,很快又摆脱了。那些无力摆脱的人,便可能沉降为“地下室人”。《白痴》里的少年伊波利特,很像是不那么幸运的阿尔卡沙。
拉斯科尼柯夫、斯塔罗夫金、伊凡,都是自以为抓住“思想”其实是被“思想”抓住的人。陀老在很多地方都暗示,他们跟第一代的“退场者”有微妙的联系。伊凡处死上帝的想法并非什么独创,早在韦尔西洛夫的梦里就出现过了。而斯塔罗夫金则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学生。他看不起老师和老师的那些闲谈,但师生之间却在一个重要的地方保持一致:贫瘠到只剩下美感。老师崇拜的美,还包含对崇高精神的渴望。到了学生这里,美感则成了行动的唯一尺度。斯塔罗夫金坦白承认,自己对善恶毫无感觉。对善恶无感的人,可以什么都不做,也可以什么都做。斯塔罗夫金就是这样,他可以只为了美感和快感而行善,也可以只为了美感和快感而作恶。他也曾希望能从作恶中感到恐惧、羞耻、罪,但一无所获。除去为了美感和快感去行凶,他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让他证明自己是个活着的人。那个抓住拉斯科尼柯夫的“思想”,也把善恶之类的精神原则剔除净尽,贫瘠得只剩下美感。拉斯科尼柯夫说自己是“有审美感的虱子”。他坚信自己有权杀死另一只虱子,用斧子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女人,没什么不对,只是形式上欠妥而已。杀死上帝,留下美感,这就是“退场者”和“地下室人”之间的精神纽带。
像斯塔罗夫金、伊凡这样的人,在行动上仍是慵懒的。正如典型的“地下室人”,并不特别感到要做什么。可是,他们有学问、有魅力,他们的“思想”能够死死抓住那些更贫瘠的心灵。当他们成了新一代的教育者,就会培养出疯狂的行动者。
斯梅尔佳科夫是伊凡的弟弟,也是伊凡的学生。老师杀死上帝的“思想”,创造了这个杀死父亲的学生。斯塔罗夫金有三个学生。基里洛夫笃信一种“思想”而自杀。沙托夫笃信另一种“思想”而遭到谋杀。韦尔霍文斯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儿子)根本不在乎什么“思想”,他着迷的,是破坏一切的行动。对于这种行动,他有惊人的实践智慧。但他知道,除了权术和煽动,行动还需要有一个新的神、新的导师。能够玩弄“思想”、含笑行凶的斯塔罗夫金,是最合适的人选。《群魔》快要结束的地方,陀老告诉读者,韦尔霍文斯基也有了自己的学生。“小傻瓜”埃尔克利,是韦尔霍文斯基的崇拜者。他理解不了复杂的思想,只是真诚相信老师的革命宣言。他认真执行老师组织的谋杀和破坏。当老师仓皇逃跑时,他觉得怅然若失。
从无所事事的“退场者”,到被“思想”囚禁的“地下室人”,再到地上的自杀与暴行,人先沉降到一无可信,继而,一无可信催生出全新的狂信。这是陀老留给世界的现代启示录。
那晚,我先填了一堆表格,然后跑去跟老友聊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至深夜,不亦樂乎。当我们谈论那些博学的“地下室人”的时候,好像是在谈论自己,以及那些精神上的父亲。我们知道,陀老那些阴郁故事的底色,是明媚的生活。他为所有“地下室人”留着通往生活的门。他们可以走出“地下室”,也应该走出“地下室”。但那属于另一个故事,也属于另一个晚上。
注:本文引文,全部依据河北教育出版社《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