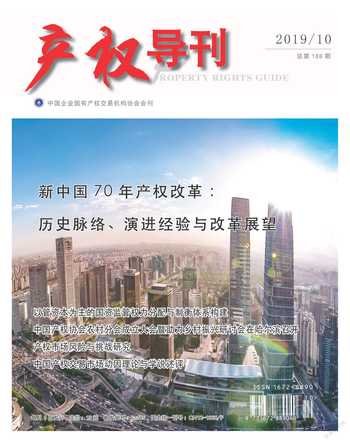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权力分配 与制衡体系构建
2019-09-10李红娟
李红娟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我国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进入了新一轮的改革和战略方向调整。2019年4月国务院印发《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提出到2022年基本建成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出资人代表机构与国家出资企业的权责边界界定清晰,授权放权机制运行有效。当前,我国国资监管主体之间权责不清,监管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仍有发生,有效的国资监管权力分配与制衡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以管资本为主,厘清政府、出资人代表机构、企业的权责边界,才能把国资监管有力、运行有效真正落到实处,实现其公共利益目标的根本性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资监管新的体制模式。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模式,从实质上看,是通过进一步理顺国有资本出资、投资、运营、监督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为中心,使国有资本的所有权、经营权、监督管理权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实现分权。按照改革的顶层设计要求,在新型的监管体制下,国资监管的重点应当在于资本布局的优化、资本运作的规范和有效、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资本安全维护等层面。当前,我国的国资监管权力主要集中在政府出资部门、国有企业集团公司、运营控股公司、投资公司等主体层面。法律规章制度对国有资产所有权、占有使用权和监管权主体职能、权责归属等方面界定较为模糊,对国有资产监管主体之间监管权责尚未进行明确划分,责任约束机制缺乏、国有资产的所有权条块分割,各所有权主体可以依据自身所有权能行使权力。这不仅不利于监管过程中部门的协调和衔接,更不利于全面监管体系的形成。需要从监管模式入手,改革和完善国资监管权力分配体系,构建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有效监管模式,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
1 关于国有资产监管的对象和内容
在每一组法律关系中,都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形成与之对应的法律关系。国有资产监管法律关系的调整对象是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以国有资产为标的物,形成了国家、企业和全民所有的企业产权关系。国有资产监管对象,既包括国有资产也包括进行监督、管理、经营和使用的自然人。我国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归属于国家,经营权归属于企业,这种权能分离状态体现了国有资产本质上是政府行使其财产所有者权力的体现和延伸。在市场化经济运作环境和产权流动交易规则下,基于效率的需要,国家行使资产所有权须通过私法化的形式予以实现。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运作除了需要考虑效率,还需要兼顾社会责任等目标需求,所以,监管模式的构建是一个各主体权益不断平衡的过程。
从广义上看,国有资产监管的客体自然包括被监管的所有资产监管机构、国家经济管理机关、企业经营者和企业职工的个人行为;但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它主要是指国有资产经营者的行为。国有资产监管的客体是一种对于“行为”的监管,具有非常广泛的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行为都是国有资产监管的客体,对哪些行为该列为监管的客体需要依法而定。就监管对象而言,虽然地方上已经建立了国有资产国资委监管的模式,但是,具体的监管和职能权责划分在体制和政策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从我国国资监管主体和国有监管客体的关系上看,国有资产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的责任不明确,国有资产出资人不到位、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的国有资产经营主体处于权力失衡状态,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权、委托权、决策权和自由裁决权等权力层面较大,而人大、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监管权范围较为有限。现阶段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和控制上,监管的内容主要是基于事前审批等初级层面上的监管,而对企业管理所需要的成本审核、成本控制、消费者保护等内容的监管相对较弱。
2 关于国有资产监管权力的制衡
法律制度的本质在于对权力和权利的确认以及分配。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有资产监管权力的内容主要有立项权、人事权、财产权、经营指导权、政策法规制定权等六方面。[1]这些监管权力的主体和内容往往存在交叉重叠现象,对实践中监管权力的履行和监管部门职能性质界定造成了困惑。完整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不仅需要以产权和契约为基础,还需要一个健全的产权交易流转的制度保障体系。一直以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具有重保值增值、轻监管的特征,在国家、政府、企业之间的权利分配和制约上没有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造成国有资产所有人权利虚置,国有资本运营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制度歪曲、制度失效等现象。近年来屡见不鲜的国有企业腐败大案、要案的发生,对国有企业自身和国家经济效益以及外部形象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对于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力分配是否科学合理,关系到权力自身运行的通畅和良性健康发展。监管机构权责不明确,权利和义务不对称等必然会导致权力滥用、监管失效等问题出现。权力自身所固有的属性决定了权力不可避免的有自我扩张倾向,这就涉及到了权力的制衡。
权力的地位决定了其自身需要制衡,实现国有资产监管权力制衡,需要建立国资监管有效的体制机制保障。我国国资的权力分配在横向上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条块管理,在纵向上表现为以专业划分的行业管理。这种资产管理的权力分配方式,特別是行业管理方式严重阻碍了国有产权在市场上的横向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需要在加强企业权利保护的同时,注重加强国家行政监管的力度,用严格的约束机制和有效的监管模式,以此提高国资资本运营的效率。制衡的本质是行政监管主体之间和国有企业内部权力结构主体之间的合理分工,相互平衡、相互牵制,防止任何一个权力超出其规定的权限,并且通过一套有效的规则促使其他主体权力对其进行约束和限制,在这种状态下,权力构成部分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
3 统一监管下的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模式适用
我国当前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是依据不同行业或不同企业特征进行监管权力的分配,各监管职能部门不但没有明确界限,同时也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协调统筹性差,政策冲突累积较多,影响了国有资产监管的效率和水平。权力制衡机制本身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过分强调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比如,会出现权力主体之间扯皮推诿、无谓的遏制,降低权力设置目的的效率等问题。权力的制衡是需要以一定的条件为基础,即一方面需要明确不同的权力主体的权限处于相互平衡状态,另外一方面是处于权力平衡状态下的权力主体中任何一方权力享有超出其它主体权能范围的特权。
为了防止多头监管而导致的监管无效或者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国资监督无力现象,根据我国国资监管现状和改革需求,建议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的模式采用统一监管下权力集中与分权相结合的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模式分两个层次,其一是监管部门和机构的相对统一,其二是资产出资人、产权转让人、产权监管人权力的集中与分散。
第一,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应独立而公正地行使国资运营监管职能。建立统一、以管资本为主的、各司其职又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形成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独立于国有资产出资人、产权转让人、受让人等资产利益相关人的监管体系。统一的监管模式,将有利于提高监管的效率和效益,这与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不谋而合。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独立行使监管职能,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制度,对国有资产的运营全过程实行统一的监管,防控国有资产流失。
第二,行政监管主体之间的监管权力相对集中与分权。国有资产监管主体的外部独立性与监管主体之间职能的分离性。在具有监督管理权力的主体之间,对监管的决策权、执行权和裁决权进行分置,由不同的行政部门进行行使,各自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以实现权力制衡。
第三,行政监管主体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监管权力集中与分权,国有企业内部的权力集中与分权。按照国有资本授权机制,在授权范围内,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市场主体经营活动自主权。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章程对国资内部的监管作用。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公司决策主体、执行主体和监督主体之间的权力分配方案、权力制衡的方法,使各种主体的权力运作都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在股东和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形成权力制约关系、监事会与董事会之间形成权力制约关系以及形成董事会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制约关系。
4 有效国有资产监管权力结构框架构建
国有资产监管权力需要在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之间进行分权,没有分权就谈不上制衡。对于权力的制约机制,通常被归纳为“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三种途径。对权力的约束,不仅要通过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制衡,而且需要最大化的借助社会力量的广泛监督。强化权力平衡机制,形成权力制衡链条。积极主动的形成权力制衡链条,在整个权力链条中,合理分工与协作,相互制约、互不兼容、交叉控制。
一是立法主体与监管主体分离。当立法权和执行权集中在同一主体控制下,法律所代表的公正与公平将难以实现。目前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暂行条例》以及《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国务院国资委是一个既负有对国有资产增值保值义务,同时又承担监管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义务的机构,导致国资监管部门对自己权力监督的局面出现。我国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为了更好地实现国有资产的监管和实现权力制衡目的,须对国有资产监管权力的立法主体与国有资产监管的执行主体进行分离。
二是,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范围进行调整和重设。构建将其监控功能从管理职能中相分离,分别实现管理和监督功能。不仅是国资委立法权与执行权的分离,在整个国有资产监管体系中,立法权与执行权的分离,还可以避免立法主体为了部门利益而产生的立法条块分割现象以及法律之间的相互冲突。不仅如此,还要充分发挥全国人大立法和监督权力,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问责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监管权力的程序机制和主要负责人的问责机制约束和督促监管权责的统一的国有资产监管主体外部审计制度、国有资产信息公开制度,确保立法权与执行权的有效行使。
三是行政监督与社会监督权力分离,中央与地方统一政策下分级监管。准确定位政府监管的角色,在国有资产监管体系中,强化社会主体监管的能力与责任。重新划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监管权力范围,建立统一的监管制度和监管政策。理顺中央和地方对国有资产监管权力的主体关系,使其各得其所、各有其权、各司其职,实现政府对国有资产监管的职能由管理转向服务,由侧重计划和控制转向以市场主导为模式宏观调整。在集中、准确、全面准确掌握全国资产的数量、基本情况、组织结构等数据的基础上,进而合理分析和研究,判断和制定国有资产监管的总体策略。强化国资委的基础监督权力,对中央与地方产权关系进行准确定位,改革国资委对国有资产所有和社会公共管理的双重职能身份。
四是实行中央和地方对国资监管的分级管理。理想的国资监管体系,应当是国资监管部门和政府部门、中央和地方监管部门、政府与企业之间,上下贯通、横向对接、依法监管、部门协调联动的大监管格局。面对新的监管体制改革要求,需要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对国资的监管关系及监管权限,明确各自对国有资产监管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监管权力的明确分工,落實各自的责任。在国有企业内部建立科学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建立各级国企更加规范和有效实现资本的高效运作。
(作者为国家发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企业的投资、划拨、资产调配和收益的支配权等;四是稽核权,包括对国有企业财务状况的预算权、审核、业绩考核等;五是经营指导权,包括对国有企业的发展政策、规划战略、经营方向的指导权等。六是政策法规制定权,包括国有资本存量管理、动态调整规划、收益收缴和支出管理、财务管理及防范内部人控制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