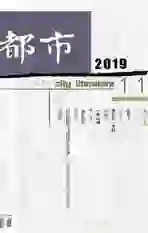耳畔再萦北风吹
2019-09-10刘小云
刘小云
解释不清楚,五十年前的人,五十年前的事,我為什么如此牵挂?2019年4月19日起,临汾纺织厂1969年版《白毛女》剧组组织了一次跨越半个世纪的为期三天的大聚会,参加人都是剧组成员。我不在其中,自然未参加。但我天天关注微信群,看动态,看照片,数念着每一个角色,时不时还与某一个角色或某几位角色有点语音或是文字往来。他们流泪,我眼潮;他们激动,我兴奋,恨不得我也去红地毯上亮亮相。
更有意思的是,这几天,耳畔萦绕、嘴上哼哼的,是挥之不去的白毛女主题曲《北风吹》。
我和他们一样,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一群容易激荡感情的人,临纺情结是埋在心中的。
一
临汾纺织厂,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站。
出临汾城,一条大道直往东走,一座新型的锯齿形厂房就会呈现在眼前。1969年,投产不久的临汾纺织厂从太原、临汾、中条山等地招来近千名学徒工。厂房和机器都是崭新的,清一色的花季学生怀揣美丽的梦想,在纺纱车间,在织布车间,在纱云布海中,编织着自己甜美的梦。
进工厂不久,我就被调到机关,手中的笔专门书写跟我一起进厂的少男少女。同在一个办公室的马天瑞老师是位小提琴手,他那时大概也就三十岁左右,他拉小提琴的动作非常倜傥。常在办公室听他讲,在哪个车间,他又发现了哪些有音乐舞蹈天赋的人;也听他说,工厂又招工了,他在过筛子般挑人,有文艺表演经历的,会什么乐器的,他都要问到,收到自己麾下。更有甚者,还有被他从火车站直接“劫持”到乔里排练基地的。他们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车间、到部队演出。我记得他们演出的有《亚非拉人民齐战斗》《纺织儿女心向党》之类的小歌舞。很快,宣传队开始排练整场芭蕾舞剧《白毛女》。真没想到,非专业的剧组居然排练出了专业水平,轰动的何止是本厂,晋南地区,谁人不知临汾纺织厂的《白毛女》?立起脚尖跳芭蕾,太惊艳了。那个年代,好像各个工厂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起码临纺周围的临钢、建筑公司等大一些的单位都有宣传队,可是,唯独临纺的宣传队出大名了。我这个不会唱不会跳的人,也有一分自豪感。挂在嘴边的,就是随处炫耀他们在临汾大礼堂公演那一个月,天天座无虚席!海报上的光鲜组照,吸引了多少过往行人!几乎所有的驻晋南的部队和大型厂矿企业、国家机关都请他们去演出过。
有一次在三楼会议室开会,白毛女的扮演者宋庆云就坐在我身边,只见她在一张小纸上,三下五除二,就出神入化地绘出各个角色的动作,胳膊腿的位置和角度,好神啊!一个场次的剧本居然像连环画一样跃然于这张小纸上,我看她的眼神,不亚于发现新大陆。专业剧团的导演也是这样的吗?她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呀!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独创的表演动作简笔速写,她说,这个图,只有她能看得懂,她以此来规范每一位演员的动作。
我与《白毛女》剧组的缘分就来自于这些看似肤浅的点滴记忆。
二
我在临纺只待了四年,就调回太原,银行工作与纺织厂丝毫不搭界,但是,五十年来,我总觉得我还是临纺人。2009年,步入社会四十年的那天,我与剧组饰演二婶的曲雅贤、主唱赵丽珠有了一次重返第二故乡临汾的机会。
这一次,我对剧组的了解由浅入深了。
到临汾火车站接我们的是在剧中先饰演黄家狗腿子,继而又饰演八路军战士的陈勇强,还有饰演杨白劳的樊太林。勇强一个电话,在不足一天的时间里,将临汾的剧组原班人马全部召集到位。四十年过去,面孔大都生疏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向我介绍,哪个是大春,哪个是赵大叔,哪个是黄家的打手,哪个是窗花舞和大红枣儿的舞者……当然宋庆云是我一眼就看出来的,她饰演白毛女的造型,早已深深印在我脑海里了。他们对我也不陌生,怎么说,我也是临纺人。他们说,我的到来会使他们远未逝去的美丽变成文字,让他们在字里行间尽情地回味。
马天瑞老师来了,之后,我们又到他家里叙谈,再之后,我们一起去临纺旧址。工厂不复存在,我和马老师来回漫步在落叶铺地的厂区深处,由他向我娓娓道来。
那也是他的青春记忆啊,那是一段美妙和谐的音符,在他心里余音缭绕。那时,八个样板戏风靡全国,纺织厂最大的优势是女工集中,为何不搞芭蕾舞剧?芭蕾舞是高雅艺术,业余剧团跳芭蕾,这是一次高难度的挑战。他愿意为此一搏。
恰巧他有一位朋友叫李凤山,他是陕西省歌舞团的。陕西省歌舞团有个任务,为全国各厂矿培训芭蕾舞剧《白毛女》,李凤山给他来信,机遇给了他这个有准备的人。
虽然朋友与他是直接联系,但他没有亲自带队到西安,是陈导演带着剧中主要角色19人去西安学习的,马老师得留在家里购买乐器,培训乐队,搞舞美设计等。
陈导,名陈世华。我不熟悉,演员们带我来到陈导家。陈导家就在临纺宿舍,熟悉的大院,自然有很多记忆,偶然遇到一位熟人,看到相随于我的人,就知道我是为何而来的。可见《白毛女》芭蕾舞剧是深入到临纺每一个人骨子里的。
陈导有病,言语已经不利索,但他看到当年与他朝夕相处的演员们到来,异常高兴。这些已入花甲的演员们视陈导为父,用自己的脸去贴贴陈导的脸,然后,蹲在陈导膝前,双手抚着陈导的双膝与他笑语。他们说,当年陈导就如同慈父,给他们讲剧情,讲内涵,引导他们进入角色,几个春秋啊,从无厉色。而今,他们只能从陈导不多的言语和神态中重新感受那种特殊的感情。
大家回忆,陈导带着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孩子们来到陕西省歌舞团。他们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排练大厅,四面通体大镜子,光洁的地板和锃亮的练功杠。芭蕾梦开始植入他们的心田。
陈导没有贪大,毕竟是业余宣传队,如果一口气学下整场,难度似乎太大。还是先试着排第一、第四和第七场,但是,天资聪颖、自幼练过体操、接受能力颇强,且会画画的宋庆云,居然在半个月内,将整场的舞蹈全部学会,还做了场记。她用各种符号和图形、线条,标出了出场顺序,男女演员位置、舞姿、队形队列和舞台背景。奇才呀,厚厚一个本子,完完整整交给陈导,陈导欣喜的表情是可想而知的。
庆云为剧组之魂是必然的。
在陜歌学习期间,还有一个大忙人,就是乐队的曹国宝。在没有打印机、没有电脑的年代,要将所有的曲谱复制回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陕歌的老师,帮着将交响曲谱翻译成简谱,曹国宝就一曲曲抄下来,一个音符都错不得呀,抄着抄着,免不了眼花而错行,曹国宝就定定神,看清了再接着抄。回来后,他也像庆云一样,交给马老师一个厚厚的本子,这就是马老师挥动指挥棒的乐谱总图。
接下来就是三个月的封闭排练,地址在临汾乔里村棉麻厂的仓库。空旷的仓库里,四周安上了厂里用钢管做的练功杠。演员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艰苦的排练。排练从立脚尖开始。谁能踮起脚尖走路呢?何况她们是立着脚尖舞蹈啊!五指并拢,两脚后跟对齐,两只脚成一字型,脚尖立起来。一切按照专业要求,一次立三分钟。她们的训练强度是每次三十分钟,立起来,放下去;再立起来,放下去,从晨钟到暮鼓,不停地练,疼得她们龇牙咧嘴,但是,没有人退却,流着眼泪,淌着汗水练。脚脖子肿了,大腿根肿了,怎么能举到练功杠上呢?必须按要求来,你帮我,我帮你,双手把腿抬上去,还要不停地压,近乎残酷。那时,临汾没有卖芭蕾舞鞋的,她们就到长治去买,买回的鞋,硬邦邦的,很快就把脚指甲盖顶掉了,她们就用棉布缠绕住脚趾,继续练。晚上脱袜子时,连肉带血一起往下撕。还有人从此没了脚指甲盖,那就是代价,那就是记忆!
马老师将自己融化在音乐之中,乐队的合成耗费了他全部的心血。顾名思义,交响乐就得各种乐器相得益彰。大部分队员刚进来时,还都是乐盲,不要说吹拉弹奏,就连这些七七八八的乐器都没见过。这样的基础,愣是让马老师手把手夯实了。他们先是抄出自己的分谱,然后,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朝练暮收,单个练,合成练,田野里练,墙壁前练。而且必须单独对着马老师弹奏,少不了马老师的“呵斥”,含着泪也要练。到底都是有灵气的姑娘小伙儿,眼里盯着马老师的指挥棒,慢慢地沉浸在乐曲的悲喜之中。乐池里,马老师指挥演奏的那张照片,实在是太经典了,产生幻觉时,我会将他视为小泽征尔,好有风度!他要通过自己的手,将音乐的感觉传达给乐队,乐队再传达给演员和观众。整台剧能否演下来,或者能否演出成功,马老师的作用至关重要。他调动了自己对音乐的积累,对着总谱,一目数十行,既要顾及各个方位的乐手,还得环视舞台上的演员,舒缓激昂悲愤欢快,都流淌在音乐之中。每当马老师的指挥棒一亮,音乐即起,演员们就登场了。那时,既无录音机,也无留声机,陈导的“开始”“停”,激活了所有的人。所有的舞蹈动作都随着乐队和主唱赵丽珠的歌声起动、停歇,周而复始。三个月,整场《白毛女》在苦练中速成。
临汾大礼堂公演第一场,谢幕后,厂里领导在后台与他们握手,有些演员竟然呜呜大哭,陈导还用临汾话对他们说:瓞子娃,哭啥呢?
演出多了,他们已经能将感情升华甚至真的流泪。有一次到28军演出,饰演喜儿的南爱民脚指甲盖掉下来,生疼,上场前,打封闭针。演出中,有一个情节,黄母要拿簪子戳喜儿的脸,二婶想方设法带喜儿逃出虎狼窝。饰演二婶的雅贤真的哭了,为南爱民的坚强哭,也为喜儿的命运哭,哭得眼泪混着妆容变成黑色的。不到20岁的雅贤,最怕化妆时陈导给她脸上画皱纹,这下倒好,陈导说,你可不能再哭了,那黑脸可是你自己画上去的。
我问马老师,你们大概演出过多少场?马老师说,怎么也在百场以上。有的打电话,有的亲自上厂里预约,还有的就直接找厂领导,厂领导有计划地给他们安排。这实在是临纺的一大骄傲。
临纺厂的《白毛女》历经几代了,我最钟情的还是原版。这其中,有创业的因素。各种才智碰撞,乃至汇合所产生的奇迹,就在他们身上见证了。
三
回并的火车上,马老师给我打电话了。显然,马老师对我这次造访动感情了。我说,马老师,您造就了一代人。电话那端,我感觉出来了,马老师在哽咽。
不但是因为有了出演《白毛女》芭蕾舞这段经历,剧组的姑娘小伙子跟艺术结上了缘分,他们的自身潜质得到挖掘,而且他们结成了半世纪的友谊,一个团体的几十号人,始终如亲人般亲近。
临汾之行,我见到了大春的饰演者许真,七十岁的人了,依然板直而俊朗。当年,大春解救喜儿的那张剧照,很多很多人都以为是专业演员,真有英雄气概。见到大春,还想见见黄世仁的饰演者袁战胜,但是,看到的是挂在大家脸颊上的悲泪。他们说,那几天,他们本来是要聚会的,袁战胜在聚会的前夜,穿上崭新的衣服,静等着天亮,也许是想得太重了,也许是不想让大家看到他生活的窘迫,居然在那一夜心梗永远地走了。大家说,他饰演的是剧中最坏的人,而他却是生活中最好的人。看到他坟头上那随风不去的纸花在不停地旋转徘徊,那就是他不愿离去的灵魂。
跟马老师联系上了,就会有电话叙谈,可是,有一天,他来太原了,住进了山大一院。我去看他,他不知道自己的病情,状态倒还不错,还在跟我唠嗑。他所叨念的无一不是剧组的人,北京的,上海的,武汉的,石家庄的,南京的,济南的,太原的,临汾的,他实在想念,泪水根本就控制不住。
他回到临汾不久就去世了。在他走前二十二天,陈世华导演先他而去。再之后曹国宝老师也走了。这三位同时从霍县文工团转业到临纺,都为《白毛女》舞剧呕心沥血的老朋友又聚到泉下,他们又会分工合作再筹备一台新舞剧。庆云对我说,你多写写走了的人,无论他们在天上在地下,都能听到人世间对他们的思念之声。
马老师对大家说,四十年聚了,五十年还要聚。要记住,我不走,谁也不准走。可是,他没有等到五十年,他的儿子马树德代表他来参加跨越半世纪的盛典了。
四
这些少男少女的艺术潜质是通过芭蕾舞剧《白毛女》发现的,之后,有几位在艺术道路上有了瞩目的成就,比如,宋庆云、李京武等。庆云的头衔和荣誉太多了,是名副其实的舞蹈家,最让我佩服的是在1990年9月22日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上,她叱咤风云般指挥了四百人的“威风锣鼓”,那惊心动魄的声响,舒展挺拔的舞姿,顺畅连贯的队形,所向披靡的阵势,震撼了会场内外,数万名观众掌声雷动。这是她深入临汾各县挑出来的精兵强将———一色的壮年农民。她对从远古至今流传于民间的“威风锣鼓”之精华采集、创新、编排,国庆四十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崭露头角后,又精心编导出《亚运曲牌》。亚运会要求“威风锣鼓”在三分半的时间里,既要频繁变换队形,又要击鼓震天,扬钹飞镲。于是,庆云就选择了农闲的四月和八月,起早搭黑冒黄沙顶骄阳地排练。一个“女教头”啊,在全世界都瞩目的亚运会上,指挥四百条汉子,十一次巧妙地牵动着看台上数万名观众的眼球,纷呈异彩,将开幕式表演推向高潮,并由此名声大震。乃至于张继钢、张艺谋都请她参与更为重要的艺术片的编导。
2009年,我回到临汾那天,庆云给我送来三本书,是她的著作:《威风锣鼓》《威风锣鼓民俗及符号谱译解》《翼城锣鼓》,好专业啊,既有探史的,还有技艺的,文字和插图都让我惊叹。庆云喜欢画画,而这几本书中的插图全是她的妹妹宋汾云画的,汾云也是临纺《白毛女》剧组的,和姐姐有一样的才华和风采!
庆云是从临汾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接着,她又开辟了新的园地,组织了一个“老来俏”艺术团,培养了后几代《白毛女》演员,也推出了不少精品。今天,喜儿的饰演者南爱民还给我发来一个搞笑的抖音小视频:喜儿依然是南爱民饰演,杨白劳则由宋庆云饰演。有模有样,好像他们当年就是父女搭档。
李京武远在南京,我是用电话采访的,对方很健谈,一口气将他的艺术生涯倒给我。他是唱着“漫天风雪”应征解放军前线歌舞团的。进入专业后,他经常下部队演出,保留节目便是《白毛女》。他说,他一生钟爱的事业是在临纺起步的,生命长河的源头就在《白毛女》剧组。当年,他与剧组的19位同道在陕西省歌舞团学习时,懂得了什么叫舞美设计,如何才能达到审美效果。他将剧中的每一道布景都做了详细的测量,对每一个道具都仔细剖析其结构,对灯光的运用心领神会,回到临汾,临纺巧匠制作时,都以他的测量为依据。他告诉我,整场《白毛女》,就是一门综合艺术,他自己不但能唱会跳,而且能用唱歌的练声法演出话剧。有了这样的基础,到了专业团队后,他适应非常快,甚至能在演出前后装台、卸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彻底改行做摄影,九十年代专业搞电视剧拍摄,他拍摄的电视剧有我们熟悉的《秋白之死》《小城之恋》《红蜻蜓》《石评梅》《豫东之战》《秦淮八艳》《七战七捷》等。
跨越五十年大聚会接近尾声时,杨各庄的庄主陈勇强拿出了手机,与远在南京的李京武视频。在场的每一位演员,依次与京武对话,清晰的屏幕上,可以看到京武的泪水已经布在脸面上了。
以《白毛女》起步,走上艺术之路的还有不少。可以肯定地说,剧组所有人无论在什么行业上,都发挥了他们的艺术才能。
我曾撰文《远未逝去的美丽》,长长的文章占据了《太原日报》大大的版面。
我的博客上,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阶段内,我几乎是一一答复所有点评和留言。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演职人员,给我提供了许多影响他们一生的动人故事,我成了剧组的編外,成了他们的朋友。
五
人生易老天难老,当年的姑娘小伙儿,转眼间,成了爷爷奶奶辈,加入靠回忆打发日子的老人群。
想见面,想叙旧,还想有个舞台展示青春风采,这绝不是异想天开。时不我待,说干就干。相约在2019之始,他们要来一场“春天的芭蕾”,剧组所有人都寄希望于杨各庄的庄主陈勇强和剧组的灵魂人物宋庆云。
准备期一年。
他们的相聚是盛典。
雅贤、慧云、爱民、艳春都跟我有微信交流。她们的绘声绘色,给我勾勒出壮观的画面。
4月20日上午,距离临纺原址不远的地方有家鑫金龙大酒店,从外边看,有大拱门和红地毯,像是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喜气而华贵!
拱门上明显写着“原临纺宣传队《白毛女》剧组50年联谊会”,好奇者驻足,欲看明白。老临纺人明白,几分向往,多看几眼,也有对逝去年华的追念。
来参加这场盛典的七十多位嘉宾,都按捺不住那颗兴奋、虔诚的心。男士们穿着节日才穿的盛装,女士们穿着汾云专门准备的唐装汉服演出服,男男女女都披上了长长的红纱巾,从踏上红地毯的第一步,就将自己想象成正在走向奥斯卡颁奖台,要有那般惊艳亮相之效果,人生大概只此一次!踩着《迎宾曲》的乐点,两人一对,三人结伴,款款徐步,在签名墙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走向大家早已翘首的老照片墙。
这堵墙高3米,长15米,展有122张老照片。这些老照片是1969年至1990年期间临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剧照与合影。其中,《白毛女》剧照31张。此外,没有上墙的还有1990年至2008年,临纺职工业余文工团的彩照80余幅。如果将这80幅作品也上墙,那恐怕还得有一块同样大小的老照片墙了。想一想,容易吗?这122加上80,200幅老照片都是陈勇强从演职人员手中收集并扫描的,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
在筹备的日子里,他将这些老照片放大洗印,又根据心里的谱,一张一张非常艺术地张贴上去。
勇强,真是有心人。这场盛大聚会,处处能体现他的匠心。
踏上红地毯的顺序,也是勇强和庆云安排的,白毛女,大春,喜儿,杨白劳,张二婶……七十多位,依次闪亮登场!
签名,到老照片墙上寻找自己,眯着老眼,再三定神,找到了,找到了,我在这儿,这样的舞姿!然后,兴奋地指点给同伴:你看,你看,这是我,那是你。是我们吗?好年轻啊!不对呀,我还有这样的好时光?说时迟那时快,分秒之内,有人抢拍了一张照片,堪称经典:马天瑞老师的儿子马树德与专程从北京回来的张兆宗相泣而拥。树德身上有父亲的基因,自幼也拉小提琴,还有好嗓音。他参加工作进临纺,在清花车间,与北京知青张兆宗同开一部车,俩人还都在宣传队,朝朝暮暮,感情能不深?张兆宗是从插队的临汾贾德村被分配到临纺的,当时还不足20岁。自他调回北京后,再无联系。大聚会带来机会,俩人相见,无论如何也转换不过今与昔,脑海里分明都还是小伙子,怎么就成白发人?大男人,涕泪滂沱,甚至哭出声来,真是情到深处。
当年饰演大春的许真大哥八十岁了,他是与饰演白毛女的宋庆云一起走过红地毯的。多少年了,他们俩在深山相认的那个经典造型早已成为剧组甚至是临纺的标志。面对这么多陌生又熟悉的面孔,他们应呼声重现了那个造型,庆云问,我这么胖了,你还能托起我吗?许真大哥憨厚一笑,动作跟了上来,太完美了,完全没有一丁点龙钟老态,掌声经久不息,俩人心潮澎湃!
就在这时,曲雅贤脑子里闪现出50年前,他们在乔里村排练,大家都将许真当大哥哥。那年,饰演二婶的雅贤17岁,许真30岁。雅贤当年有个纠结:我小小年纪,为啥让我演二婶。这个纠结直到几十年后见到陈导,才明白。陈导说,你演二婶有条件啊!有条件,这本是看重她,她却不明白。跳完一段,累了,到大哥哥旁边坐下,大哥哥就会从口袋里取出一把大红枣奖给她。如今大哥哥老了,还这样范儿,雅贤一激动,上前与大哥哥合张影,接着,好多人都与大哥哥合影。每个人对大哥哥的崇敬都是由衷的。
要全体合影了,浩浩几十号人,如何安排座次?勇强心中有数:七十岁以上的入座;不够七十岁的,主角也入座。但是,我看发过来的照片,杨白劳、喜儿、白毛、灰毛、二婶等主角都站在二排,他们自己虽然奔七或已突破七十,但也想心里“年轻”一把。
每个人都张着嘴,许是跟着摄影师,在喊“茄子”或是“美”吧。靓丽的影像,留下了永恒。
六
尽管盼望已久,尽管事先做足了功课,但是,《白毛女》专场开始之前,准备上场重温红色经典的这些演职人员,还是有点忐忑的。
节目单是事先制定好的,舞蹈有《北风吹》《窗花舞》《大春送面》、《漫天风雪》《扎红头绳》《冲出虎狼窝》《盼东方厨红日》《红旗插到杨各庄》,诗朗诵有《献给情深似海的临汾(白毛女)剧组》《携乐同行》,还有山东快书《表表咱们的大聚会》、弦乐演奏《大红枣》、口琴独奏《小战士舞曲》,最后,还有歌剧、京剧联唱《白毛女选曲》。
主持人是陈勇强和从石家庄回来的张慧云。
我没有到现场,感觉到应该是备有投影设备的,因为,布景的图像始终能与现场的演出相匹配。
慧云是跳《大红枣》的舞蹈演员。我与慧云从未谋面,但她的声音我是非常熟悉的,我俩之间,靠了电话交往。她是个率真的人,言语干脆爽快,音色非常美,是甜润甜润的那种美。勇强和慧云做主持,是最好的搭档。他们熟悉所有的来宾,甚至掌握很多含有细微情节的故事,他们能调动起气氛,台上台下自然呼应。
由乐队管弦乐演奏《白毛女》序曲开场,当年的小提琴手董小林指挥。那种范儿如同当年的马老师,甚至比马老师还酷。在舒缓的音乐声中,慧云朗诵了自己创作的《半个世纪的聚会》,用她那带磁场的声音将人们带回到五十年前的青葱岁月,台下静悄悄。
她说,每每回忆,都有热血沸腾的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我们,吃那么多苦图什么,受那么多累又为了什么?而我们要自豪地说,什么年代造就什么样的人,什么年代就有什么样的精神,把青春献给那个年代,我们无怨无悔,因为我们生在那个年代,跟那个年代有着割不断的缘分。
台下掌声四起。
我将关注点放在“原配”上场,一是杨白勞和喜儿,二是二婶和喜儿。饰演杨白劳的樊太林,71岁,饰演二婶的曲雅贤67岁,饰演喜儿的南爱民也是67岁。
与樊太林交往不多,在群里试探着问他,能不能简单与我语音一下,哪知道,不善用手机交流的他,竟然用一张小纸条,一笔一画写下了他恢复练功的过程,同时,太林还发来一段由他的孙子给他拍的练功视频。在一间未曾装修的房间里,太林在音乐的伴奏下,一丝不苟地练着他的那段戏,可以看出,那是在重温《漫天风雪》,仿佛在舞台上,声情也能随着那一招一式而表现。他说,这段时间,老伴不让他做家务,让他专心练习,千万不能让大家失望。如果腿疼,就是打封闭针也得上。
太林简单朴实的几句话,不但写出了他,实际上剧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心情。
他写道,2017年6月份南爱民从外地回到临汾,在临汾的剧组成员为喜儿归乡而高兴,那时,他们就有了五十年相聚的念头。太林从心里泛出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与爱民一起排练,重现《漫天风雪》和《红头绳》。
爱民回来,是剧组的一件大事,喜事。她回来,不但能跟太林复活这两场,而且还能与不同的角色复活更多的经典场次。
虽然演出的只是《白毛女》舞剧的片段,但是,在他们的心里早已贯通全场,一幕接一幕,到宋庆云的独舞《盼东方出红日》,再到群舞《红旗插到杨各庄》,台上台下欢腾起来了。
这些节目先后上场,其中由主持人进行访谈,采访对象就是上一个节目的表演者。因为都是切身体会,因此,当主持人采访他们时,都能简单流畅而且在意义上升华。曲雅贤演出二婶救喜儿逃出虎狼窝,未上场前,她有顾虑,生怕有一点闪失,但是,一上场,一入境,所有的动作都娴熟,与背景墙上再现当年照片完全吻合。
主持人慧云等音乐落下来,就问台下,对她俩的表演满意吗?自然台下以掌声回应。有人说,雅贤这次是真的“二婶”,当年17岁,脸上太嫩,现在是有经验有胆识的智慧二婶!
慧云的主持,既顾及台上的演员,也随时能发现台下的闪光点。有一位当年在剧中先饰演黄家家丁,后饰演八路军小战士,同时还兼管灯光道具的演员叫郑福怀。当年剧中有一个情节,喜儿在二婶的帮助下,逃出虎狼窝,这个家丁用肢体语言告诉穆仁智,喜儿逃跑了。这个动作的难度大,在空中旋转360度,落下来又是一个不好做的造型。他的柔韧度非常好,每一步都做得稳稳的。慧云问他,你现在还跳舞吗?他说,年纪大了,老胳膊老腿,跳不动了。老了,转向雕刻。
郑福怀,非常内秀而低调的老人,雕刻也是一门技艺啊!
一个下午,到场的老演员几乎都登台了,即使没有自己的表演,也还有主持人的访谈,我熟悉的有主唱赵丽珠、剧中黄母的饰演者邢玉珍、灰毛的饰演者田军等。环顾全场,每个人都沉浸,每个人都欢腾。未能前来参加盛典的李玲大姐和牛秀梅也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献给情深似海的临纺》,由宋汾云朗诵。
专场最后的环节是才艺展示,几位队友向组委会赠送自己的书画作品。
意犹未尽,久久难以从《白毛女》舞剧中拔出来。他们没有歇息,调整状态,晚间,他们还要登上一个新的舞台,以当下的年龄,表现当下的才能。
又是歌又是舞,欢天喜地,阳光路上。哪里能想到,这些跟共和国风雨同舟的所谓老年人,能有如此爆发力!太原去的13位剧组成员,既有舞者、歌者,还有弹奏者,女生小合唱《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和《含苞欲放的花》,更是将她们的精神风貌展现得淋漓尽致。
整整一天的联谊即将结束,赵丽珠领唱,《难忘今宵》回响大厅。
五十年聚会圆满成功,大家期待六十年再现风华!
七
大聚会结束了,回到各地的演员们又掀起了一轮的热闹,他们的心似乎还在平阳古城,还在“杨各庄”里,只是平台转移到手机的微信群了。
大聚会之后,必然有思考。
我就想,为什么这些白发人有如此的爆发力,为什么在舞台上看不出他们的年龄?为什么上年纪的爷爷奶奶还能轻盈地舞起来唱起来?为什么全程自费,而且心甘情愿主动付出资金、物质和精力,激情来自何方?合力是怎样形成的。
毕竟我们是同一代人,我身上也有激情澎湃的因素。
我们从小就知道崇尚英雄,知道集体的利益高于自我,知道展现自己也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的。
《白毛女》剧中饰演喜儿的南爱民,我只有一面之交。那是2017年6月份,她从山东回来,与太原的剧组姐妹聚会。她们也是久别重逢,相拥而泣的场面让我的眼也热起来了。本来我跟剧组的姐妹就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在一起拍照,她们的服饰和舞姿,都那么文艺,唯有我,站在她们中间,像一根棍,呆板僵硬,手脚不知道该怎么摆弄。
两三天后,她和雅贤一起回临汾。我看她们发来很多照片,杨各庄的兄弟姐妹又在一起蹦跶起来了,原来爱民的舞姿这么美!不行,我的好奇心战胜了不好意思,盯着她,我得让她给我讲讲她的舞蹈人生。
我问她,当初陈导为什么选中她饰演喜儿?答曰:至今无答案。她说,到陕歌学习,她学习的是集体舞,有《窗花舞》《大红枣》等,回到临汾,曹国宝老师推荐她跳喜儿,为什么给她分配这个角色,她真的不知道。但既然给她这个角色,她就得尽最大努力。她那时才17岁,花季,但要吃大苦。苦是什么?她说了四件事,我听着心酸。第一件是大拇指脚指甲盖脱落,十指连心,何况是生生剥离呢!跳芭蕾,最基本的动作就是立脚尖,大拇指二拇指和中指一起立起来,显然重力分散均衡了。但她偏偏是大拇指长,那两个指头根本就不挨地。每天都在排练中,哪管你脚指甲疼?脱落前淤黑发紫再发青,疼,慢慢地供应不上血,指甲盖就能被她撕下来了。那几年,指趾盖根本就长不上,快长起来了,就又开始练,就又淤青发紫发青,又掉。疼得她龇牙咧嘴,但是,要上舞台了,她就得打封闭,在舞台上,和着音乐,她表现得轻松自在,甚至要表现出丰富的情感。真难为她,17岁的孩子,就这样跳了百余场。第二件事,是在某一次演出中,黄家的两个狗腿子去抢喜儿,将她高高地举起处,不知道哪一下没有协调好,竟然将她重重地摔在地上。没有一点犹豫,她就爬了起來去演第二场,连疼都顾不上。第二天,摔到的地方,乌黑发青,但她绝不在别人面前流露一点痛苦。接着,剧中有个情节,黄世仁调戏喜儿,拽她,她向后退,没站稳,脚脖子又崴了,陈导马上让人骑自行车把她带到厂里医院,晚上回到家,妈妈给她按摩,擦虎骨酒。实在躺不住,几出要紧的戏都在等着她往下排练呢,那些天,爸爸妈妈和哥哥都骑车送过她。还有一次,在大礼堂演出,扎红头绳那场,杨白劳拿出红头绳,她高兴地去抢,一下子滑倒了。这一跤,摔得好响亮,两只手展展地甩到地上。可是音乐还在响,分秒之内,她还是站起来,笑着去抢回红头绳。
爱民回忆起来,眼泪又流出来了,仗着年轻,无论多少次外伤,她都坚强地忍过来。这是她说的第三件事。
还有一件事,对她来说,有难度。17岁啊,对剧中地主压榨贫苦农民全然不知,如何能在表情上表现出地主的仇恨,这确实是难以做到的。陈导总在提示她,眉头皱起来,她怎么也表现不出来。五十年后,再演出,大家说,爱民比以前演得更好了,有内涵了,有恨了。是啊,经过五十年的风雨磨炼,她将对生活的体验,表现到角色中,是很自然的了。
爱民庆幸她有饰演喜儿的经历,有接触并献身芭蕾的经历。
退休后,她在山东报了老年大学,系统学习了几年芭蕾舞、古典舞、民族舞,从理论到动作,她更成熟了。她回到故乡临汾,加入庆云的老来俏艺术团,又开启了艺术人生第二春。
从临汾起步,到回归故乡,她始终保持追梦状态。
从爱民的成功,我又想到马天瑞老师创建起来的乐队,乐队的乐手,也都是六七十岁的长者了,也分散在各地。
乐队的指挥叫董小林,我也不熟识。微信采访,他一字字敲出他的情怀。
董小林出生于音乐世家,父母亲都在省歌舞团,父亲教他二胡和小提琴。高中时,他就是校乐队队长,后来插队到农村,辅导大队的文艺宣传,两年后,面临工厂招工,父亲与马天瑞老师是故交,让他去投奔马老师。于是,他就成了《白毛女》舞剧的小提琴手。
马老师对乐队的训练是正规而严格的,参加五十年大聚会的乐手,都是马老师训导出来的,基本功和团队精神也就是那时候形成的。
小林此生视小提琴为自己的生命,从临纺调到山西铝厂学校担任音乐教师,更是给了他尽情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是运城市小提琴学会副会长,带领着学生到处演出并参加各种比赛。昨天从微信群里,我看到他的家庭音乐会,敢情他的家族成员都是小提琴手,艺术之家,生活的氛围该是多么诱人!
一年前,“杨各庄”庄主陈勇强给他打电话,交代给董小林这个任务,将老乐队组织起来,再上舞台,再现当年风采。人都有怀旧情结,真要是老班子同奏一支曲子,那真是求之不得的,22位老乐手,他来当这个指挥。他拿出自己的计划,按六到七分钟来设计,演奏《白毛女序曲》和序幕中的两个主题音乐。
整台舞剧,乐队能不能打响第一炮,至关重要。习惯了马老师指挥的乐手们,马上就熟悉了小林老师的指挥风格,盯着他的一招一式,开始排练。仅仅一个下午啊,分别五十年的老乐手们,就将各种乐器顺利合成了,非常有把握地跃跃欲试,等待着开场。
在小林老师指挥棒的挥动下,由圆号领奏,再由小号转调领奏,管弦齐鸣,拉开了整首序曲,小林老师和他的团队深情奉献出了他们对《白毛女》舞剧的老年之恋。
我在想,临纺当年该有多少人才?我们身临其中时,没有多少感觉,离开了,临纺没了,但临纺情结却更浓烈。三天的芳华再现,更说明临纺的人才没有被埋没,人脉在延伸,分散在社会各个层面的老临纺人,还愿意在临纺的旗帜下,以临纺的《白毛女》为自己的品牌,继续发扬我们那一代人对事业的热爱,吃苦和奉献精神,这应该是社会的最积极的层面吧。
这就是,我这个非《白毛女》剧组的人,为什么要倾情写出他们不老风华的主观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