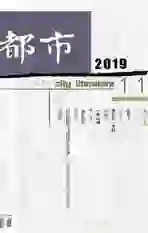夏日微风
2019-09-10刘晖
刘晖
我拿了成绩报告单和作为珠算比赛奖品的两支“中华牌”铅笔回到家里,开始过暑假。那时我十岁多一点,长得比同龄孩子高,瘦,不爱说话,经常咳嗽。我的头发又多又黑,编两条过肩的麻花辫,辫梢上扎着红绸结。辫子是我自己扎的,有点毛糙。
我家住在校园的西北角。家里没人。父亲因为恃才傲物被领导发配到乡下,母亲还没有下班。我打开煤球炉的炉门,拿一根筷子插进锅里淘好的米中,按照母亲预先画好的记号放上水,开始煮饭。锅里的水煮开了,白米的清香淡淡地逸出来。我把锅盖打开一点,斜放在锅上,让水气蒸发掉一些。然后,我关上炉门,盖好锅盖,把锅斜放在火上焖饭,隔五分钟将锅换一个方向。
米饭的香味暖暖地扑向我的脸。饭煮好了,母亲还没有回来。母亲是五年级的班主任,还要负责学校里的文艺宣传队,忙得顾不到家。我心里和胃里都空空的,但我已经习惯了等待和饥饿。我把心里和胃里的不舒服当成常态,带着孩子特有的温柔和顺,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看爸爸给我买的连环画《小兽医》和《银花朵朵开》。这两本书我不知看过多少遍了,都能将文字背出来。
母亲回来了。由于炎热和疲劳,她脸色泛黄,神情烦躁。豇豆在锅里焖的时候,她拿起我的成绩报告单看。语文100,数学99,体育55。她脸色阴沉得可怕。我知道那个红笔写的体育成绩让她很不满意。她在师范学校时酷爱文体活动,不能接受一个安静得有点古怪的女儿。她开始按照我们班主任写在成绩报告单上的评语来教育我,至少她自己认为是在教育我。她的声音平板、严厉、生硬,与在课堂上训学生别无二致,列数我的种种缺点:不合群,不参加文体活动,有骄傲自满倾向等等。
我低着头。我又羞愧又烦闷,却无法躲开羞愧和烦闷,正像我无法躲开母亲。如果这算是教育,那么我要说受教育真是世界上最让孩子们感到痛苦的事。我说不出希望母亲怎样对我,但我意识到我需要的不是这种已在教室里受够了的冷若冰霜的指责。我想提醒这个正在不停地教训我的陈老师:“我是您的女儿小慧,您忘了吗?”
但我什么也没说。我是一个木讷的孩子,而且从此以后更加木讷。
暑假生活中唯一可盼望的,是父亲会送我到乡下爷爷奶奶家去住一两个星期。一小时汽车,再走五里路,看到一方清清的池塘时,就到爷爷家了。青砖黑瓦的房子,有着乡村人家统一的格局:进门是客堂,夯实的泥地阴凉舒适,放着香案和八仙桌,角落里放着一小堆西瓜和几箩筐新麦。右边是厨房,放着大灶、水缸、食橱、柴堆等,左边是卧房,放着雕刻繁琐的红漆花板床,房顶上有一块玻璃明瓦。姑妈一家住在爷爷家北面,相距不到一里路。姑妈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嫁到镇里去了,儿子胡明在村里的抛光厂上班。
爷爷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他笑着打量我,不停地叫着:“慧慧,慧慧。”他脸上弯弯的笑纹让我看也看不够。我笑笑,跑到房子东侧的水塘边去玩。我抓住河边柳树的枝条,走到水深没膝的地方。水波温柔得让我晕眩。
爷爷在清凉的早晨带我翻过草香弥漫的小坡到瓜田里去。浓绿的色彩在仲夏的田野里铺展。路上碰见人,爷爷就对那人夸我成绩好,又懂事。我马上红了脸,叫声伯伯或爷爷,就不再说话。“你孙女真文静啊。”人们都这样说。我却觉得心虚,因为我不相信我是文静的。我几乎时时处于不安之中,总是在等待和盼望,却不知到底等待和盼望什么。
爷爷在田里干活。我坐在用毛竹和稻草搭成的瓜棚里,玩爷爷的草帽。草帽很旧了,散发着植物和人混合而成的香气,很特别,很好闻。帽沿周围用蓝土布滚了边,是我奶奶的手工。
黄昏,奶奶穿着洗旧了的斜襟蓝布大褂走在田埂上唤鸭子回家:“伊———呱呱呱呱,伊———呱呱呱呱。”声音在暮色中像河水一样波动。
在洒了水的院子里吃完晚饭后,爷爷奶奶继续坐在小竹椅上闲话家常。我关上吱吱作响的木板门,脱掉花布圆领衫和短裤,跨进大圆木盆里洗澡。吸饱了温水的毛巾碰到肩膀时,我哆嗦了一下,全身肌肉都紧张起来。我撩了水轻轻拍拍前胸。“拍拍胸,不伤风。”母亲撩起水拍在我的胸前背后,一边说着这奇妙的韵文口诀。那是我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事。现在,母亲碰都不碰我了。
我忽然哭起来。我想变小,让妈妈抱在怀里。“拍拍背,早点睡。”妈妈小声说。这声音是从我自己的身体里面发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不会再听到这样的声音了。
我才十岁多一点,可我的皮肤饥渴已久。我极其笨拙地抚摸自己的身体。我的皮肤因羞怯而充满张力,排斥着我的手。然后,我摸到了左耳的伤疤。我一生的记忆就是由这道伤疤开启的,那时我两岁半———
电压不足的白炽灯光线昏黄,看上去没有温度。电灯正下方的八仙桌旁,母亲抱着我看书,不时同父亲说一两句话。奶奶在一边做针线。我喜欢这种气氛,不想离开它,害怕失去它。可是母亲让我去睡觉。我扭动身体表示反抗。母亲大声喝斥我,然后把我猛地一推。在我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只聽见奶奶大叫:“不好了呀,耳朵破掉了呀!”我不认为这声惊叫同我有什么关系。可是大人们都围了过来,手忙脚乱地抱着我往外跑。
我被脸朝下摁在医院的床上。我感到了针从我耳廓的软骨中一次次穿过的锐痛。我的哭叫声比我的身体要大上无数倍。大人们紧紧地按住我,不停地说:“还有一针了!还有一针了!”可是我耳朵的感觉知道他们是在骗我。疼痛和被骗,让我哭得很绝望。我的世界像一把破伞,还没有撑开就已经崩塌了。
父亲把我从医院抱回家后,我哭不动了,安静下来。父亲轻轻地把我放在床上,蹲在床边看着我。我知道他眼里的神色叫做沉痛。我觉得我应该安慰他,便说:“爸爸,我朝这边睡,耳朵就不痛了。”这句话将父亲的眼泪引出来了。我看到父亲流泪,自己又想哭了。
这时,母亲在哪里?她为什么不来看看我?
母亲弄伤我,母亲不来看我,一定是因为我做了坏事,做了极大的坏事。一个对母亲做了坏事的孩子是不可饶恕的,我自己都不应该饶恕自己。
在远离母亲的乡村,我仍然是一个古怪的女孩,时时感到紧张不安。
邻村的爱兰姑娘经常来找我的表哥胡明。胡明大概有二十岁,和我父系家族中所有的人一样身材高大挺拔,穿着白的确良衬衫,看上去英俊和善。他说:“慧慧,今天到我们家吃饭吧?”他笑嘻嘻的,洁白整齐的牙齿闪闪发光。胡明青春焕发的样子让我觉得不安,以至于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只能扭过头去不理他。其实我很喜欢这位表哥,有时甚至想他要是我的亲哥哥就好了。我扭过头不看他,但我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通过空气感知到他的一举一动。
胡明跟爱兰说笑。这两个近在眼前的人,两个好看的年轻人,他们就像大门前的守卫一样,守着一个我无法进入的世界。孤独像荨麻的刺,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让我刺痒难忍。
他们在房间里坐着说话,我就在客厅里看墙上贴的破旧的《红灯记》剧照。画面上浓烈的色彩极不真实,更加映衬出乡村生活中蕴含的无边无际的静默和我无法理解的忧伤。
姑妈坐在门口看小鸡在场院里走来走去,不住地叹气。我偶尔听到一句半句:
“我们胡家穷是穷点,可是我家胡明有模有样,哪里比别人差了?”
我在心里同意姑妈的话。我喜欢看胡明和爱兰在一起,胡明干干净净的样子同眉清目秀的爱兰很谐调。他们像是美丽而陌生的花卉,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真正属于这个村庄,是否某一天会突然消失。
有时,爱兰挎着竹篮,带我去田边割猪草。羽状叶片的猪草长得极茂盛,肥厚多汁,发出腻滞的刺激人的气味。我的手臂纤细无力,好长时间才割下一小把猪草,爱兰的篮子很快就装满了。她坐在田埂上休息,顺手采来一种被称为“麻果”的果实,中间用狗尾巴草一穿,旁边每个小齿上都插上蓝色勿忘我花,就成了一只花篮。她还会采两根长长的狗尾巴草,在茸毛部分打个结,各自的细茎往对方的结子里一穿,可以拉来拉去。爱兰说,这是胡琴。
傍晚,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在河里游泳。村里的男孩们全都又黑又瘦,灵活得像泥鳅。双喜大概十五岁,他和弟弟如意都穿着肥大的短裤。有几个小点的男孩不穿裤子。我不敢朝他们看,但又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戏闹声伴着水声没完没了地在我耳边响着,但我认定自己走不进他们的世界。
我想起四五岁时我在这里过夏天,每天看到戏水的孩子光着身子跑来跑去,看到他们身上突出的与我不同的东西。我想我也有的,只是我年纪小,它还没有长大。几个月之后,冬天的晚上,我发现自己两腿间还是没有长出东西来,终于忍不住问父亲母亲:“我的小鸡鸡怎么还没有长大啊?”笑声从他们口中爆发出来,刺耳极了。我羞愧难当,就此过早地结束了我的天真岁月。我接受自己是女孩这一现实的一开始就是被嘲弄的,自认欠缺的,低人一等的。
我不跟爱兰说话是因为我觉得她太美,就像我不跟胡明说话是因为他太英俊。我很少说话是因为我在世上太弱小太孤单。我的心理模式在十岁甚至更早的时候就确定了,那就是我越向往什么就越是避之惟恐不及。
两个星期后我回到县城家里,看见门前空地上马齿苋长得更密集更肥厚,那强大的生命力把人类的空间和气势逼得后退。
母亲把箱子拿到空地上晒。平时密闭的箱盖此时开得大大的,让人感到偷窥的紧张和愉悦。我围着箱子转来转去,想细看里面的东西。我知道母亲上师范时用的那只箱子里有很多奖状、奖章和照片。
母亲坐在门口走廊上拆毛衣,右脚搁在左膝上,以此为支撑将毛线一圈圈绕起来。她有些发胖,姿态懒懒的,却又随时会暴躁发怒。我在她的视线内不敢随意行动。
母亲大概是对转来转去的我感到不耐烦了,说:“小慧,四(1)班教室现在成了夏令营的图书室,你去看书吧。”
我喜欢看书是因为没有其他东西可喜欢。我去四(1)班找书看。参加夏令营的同学拿着阅览卡,给坐在门口的方老师看过之后才可以进去。我没有卡片,站在走廊上不敢上前,直到方老师看到我。
方老师说:“韩小慧,你是不是来看书的?”
我点点头,觉得手没地方放,肩膀上不知压着什么东西,挺不起来。我小声说:“我妈妈叫我来的。我没有卡。”
方老师笑起来。我本能地眯起眼睛。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明亮的笑容,连胡明哥哥的笑也没有这么亮。他说:“快进来吧,教师子女还要什么卡呀!”
我从方老师面前经过时,和坐在小板凳上的他差不多高。我顿时觉得自己穿着短裙的腿长得令人尴尬。方老师仍然处于一种觉得挺有趣的心情中,对我笑着,拍拍我的大腿,说:“你真是老实得可爱。”
从来没有人拍过我的大腿。这是一种全新的、特别的感觉。我并没有觉得不适,也不害怕,而是莫名其妙地轻快起来。
我把方老师给我的特别的感觉藏在心里,终于不堪重负。在闷热的白纱布蚊帐里,我半夜惊醒,发现自己在流鼻血。
幽暗的夜色中,血是黑的,又腥又甜,粘得无法摆脱。恐惧使我纯净得一无所思,像祭物静静地躺在祭坛上,即将被神悦纳。我带着受伤野兽般的谨慎,到水缸边舀一杯水,到院子里清洗鼻子。然后,我采几片菊花脑叶子,揉碎了塞在鼻孔里。
菊花腦叶可以止鼻血,这是方老师在体育课上教我们的。我一时想不起方老师的样子,只觉得他突然变得无边无际,充溢了我的内心,覆盖了我的整个生活。
隔壁母亲房间里静悄悄的。她怕热,所以夏天睡觉时总是把房门敞着。我溜回床上时看见母亲床上的蚊帐被风掀起一角。我惊讶地发现床上没有人,继而发现床前也没有鞋。母亲不在床上,她去了哪里?我全身发麻,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第二天早上,母亲招呼我吃早饭。泡饭加萝卜干是世界上最让我厌恶的食物。母亲几乎不看我,但她的面色比平常柔和一些。我想问她昨晚到哪里去了,但我不敢问。如果她问我为什么在半夜起来,我怎样回答呢?说我想方老师了吗?
不管怎样,母亲脸上那一点柔和的神情使我稍稍轻快起来。我大口吞咽着无味的泡饭。
胡明哥哥带着爱兰来县城玩的时候,父亲还在乡下。母亲对他们很冷淡。胡明给我看他在照相馆里刚拍的照片:三七开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神情俨然,是个很俏的并且知道自己很俏的青年。他拿着照片左看右看,我却不敢多看他顾影自怜的样子。
七八天之后,姑妈托人捎信来,说胡明死了。
父亲到乡下处理丧事。我也想去,可是父亲不让我去。“你一个小姑娘,不知道害怕吗?死人也是好看的?”他训斥我。我真的不觉得死人有什么好怕的,况且他不是别人,是我的胡明哥哥。他那么干净,爱俏,脸白白的,笑嘻嘻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会死,他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三天后父亲回来了。他把身上的六十块钱留给了姑妈,这让母亲勃然大怒。疲倦和忧伤使父亲特别温和,他不说话,慢条斯理地吃饭。母亲骂了一阵,觉得无趣,一摔门出去了。
我慢慢移到父亲身边,小声问:“爸爸,死是什么?”
父亲看着我的目光充满爱怜,又严肃郑重,像面对一个大人。他说:“死就是一个人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再也不回来了。”父亲伸手拢我的鬓发时,我很想倚到他身上,但我端立不动。
“可是爸爸,我没有忘记胡明哥哥,也不会忘记他,那么对我来说,胡明哥哥不就是没有离去吗?这样也算死了吗?”
父亲说:“小慧,你不要多想。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但有时想得太多了,所以你不快乐。”
我固执地问:“胡明哥哥为什么会死?”
父亲站起来,不耐烦地说:“我叫你别问了。”
晚上,我听见父亲母亲在房间里的低语,知道胡明哥哥是自杀身亡,因为爱兰家里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胡明和爱兰,他们是那么美的两朵花,美得让人不安,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属于这个世界。爱恋与忧伤,美丽与死亡,它们在我脑中不住地纠缠,也把我和世界焊接在一起。
父亲又到乡下上班去了。学校里的夏令营还没有结束。
母亲晚饭后出去,直到我睡觉的时候还没有回来。不知什么时候,我被母亲叫醒:“小慧,小慧,你睡着了吗?”
我睁开眼睛,看到母亲的头从蚊帐外面伸进来,好像悬挂在那里一样,让我感到陌生和害怕。我说还没睡着。她说:“你愿意和我一起睡大床吗?”
我鼻子一酸。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盼着能和母亲睡在一起,后来看看没指望,也就忘了去盼。今天母亲一提这事,我便明白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一盼望。
“小慧,你不愿意的话就算了。”
我急忙说:“我愿意的,妈妈。”
母亲的蚊帐里充满白兰花和清凉油的味道。黑暗中母亲的眼睛亮闪闪的。我从没见过她像今天这样美,也从没像此时一样觉得她陌生。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如愿以偿躺在她身边时会有这种陌生和不适的感觉。我的身体和我的心都保留着她给我洗澡时的印象:她撩起热水拍到我的胸口,说:拍拍胸,不伤风。在哄我睡觉时,她会拍着我的后背说:拍拍背,早点睡。
我闭上眼睛,想躲进耳朵破损之前的婴儿时期的记忆中。那时的记忆如此稀薄,缥缈如雾。母亲突然说:“小慧,你觉得妈妈好吗?”
我无法回答。我知道我的沉默和迟疑会让她失望,可我就是无法回答。
“妈妈近来脾气不好,是有原因的。你才十岁,不会明白一个女人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你爸爸被贬到乡下,你又这么小,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是很苦的。”
我真心真意地说:“妈妈,你让方老师跟你说话吧。”
妈妈一怔,随即说:“小慧,方老师很喜欢你,是吧?”
“是。”
“那么,你不要在别人面前提方老师,好吗?”
“好的。”
我不懂母亲的意思,但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
方老师到我家来,请我母亲和他一起给夏令营的孩子们排练舞蹈。他说我也可以到夏令营里去玩。
方老师给同学们测弹跳力。每个同学拿一支粉笔,站在地上伸直手臂,在黑板上画一个点,然后原地跳起时再画一个点,方老师量出两点间的距离,让我把他量出的厘米数记下来。
我为自己能帮老师做事而觉得骄傲。有时记错了,他就站在我身后,抓住我握筆的手改正过来。他几乎是从后面抱住我。这时,我想象是父亲抱着我,但是胡明笑嘻嘻的脸却又突然飘浮在我眼前。幸好,这样怪异的时刻只是一瞬间。
清新明丽的上午,母亲和方老师一起给孩子们排练舞蹈。音乐教室里,八个男孩和八个女孩在练习跳舞。母亲弹琴,方老师教动作。我熟悉那支歌曲,是《万紫千红》。方老师穿着红色的背心式球衣,手臂举起时看得见腋窝里浓密的汗毛。
休息时,方老师倚在风琴旁边,母亲随手弹着《康定情歌》。方老师和着乐声唱起来。他的声音高亢明亮,好像整个八月的阳光一时间都洒落到教室里了。
中午的校园很亮很静,蝉声不绝于耳。家家的大人小孩都在午睡,我却没有午睡的习惯。一般情况下我自己洗洗脸,洗洗胳膊,在肘弯里涂上海鸥牌痱子粉,躺在床上望着蚊帐顶,望着窗外绿叶婆娑的刺槐树,头脑越来越活跃,自己给自己编一些离奇的、远远超出我十岁半生活经验的故事。午睡时间就是我自言自语的时间,我像那些槐蚕一样通过纤细的丝把自己吊在半空,随风摇摆。
不知多少次了,这个片段又突然出现在我的意识中———
村子里的男孩子们从我身边呼啸而过。他们赤裸着上身,又黑又瘦,举止灵活。他们盯着我,很默契地手拉着手横在路上,挡住我。我往左边走,他们横着跳到左边;我往右边走,他们又跳到右边。我恐惧而迷惑,站在路中央。我无法突破这些男孩子织成的网,无助地哭起来。
在正午的明亮中,在积了灰的白纱布蚊帐顶部,这个情节清晰地显现,但我一直不知道是确有其事还是出于我的幻想。每一次,我的心都会往下沉。我本来就不是活泼的孩子,这样的情节就更让我缩回内心。这一情节预示了我对男性世界的态度:崇拜,恐惧,无法进入,无力突破。
我的狂乱活跃的午睡时间是我一个人的秘密,母亲是不知道的。这一天的中午,我在恍惚中听见母亲走出家门。我悄悄起身,远远跟着她。我看见她走进了音乐教室。
我想琴声就要响起来了。在这炎热安静的中午,琴声的出现将会是某种仪式的高潮。我站在厕所旁边的冬青树下等。没有琴声,一直没有。
我绕到音乐教室后面,趴在窗台上往里面看。母亲坐在风琴前翻一册《战地新歌》,弯曲的脖子又白又美。我看到靠墙的长凳上躺着一个人,那个人是方老师。
“小方,你也该成家了。听说下学期会分来几个师范生,你自己留意一点,总会有姑娘适合你的。”
方老师不说话。母亲的侧影凝然不动。
“小方,我不能这样偷偷摸摸的。老韩他不得志,心里窝火,不理睬我也是暂时的。我虽然苦闷,却不能对不起他。”
方老师说:“我原来以为你很特别,敢爱敢恨,敢想敢做,现在发现你和别人一样,和这个小县城里所有的庸人一样。你不了解我,而且,你也不了解你自己。”
“你要我怎样了解你?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有好感,那个女人恰好也需要他,仅此而已。”
方老师坐起来,盯着我母亲,眉宇间英气逼人。他说:“雅芬,我喜欢你不仅仅因为你是一个女人。我喜欢你身上的味道,这让我想起我妈妈。她死的时候我刚两岁,我还没被她抱够……”
母亲扭头望着方老师。慢慢地,她站起来,走到方老师面前,把他的头抱在胸前。方老师的双臂紧紧搂住我母亲的腰。母亲的手轻轻地、无意识地、有节奏地拍他的后背,像拍一个婴儿。
我立刻觉得天昏地暗,我在这个中午失去了两个我爱的人:我的母亲和方老师。他们互相拥抱,而我只能偷偷地看着。我失魂落魄地走回家,一路上喃喃叫着:爸爸呀,爸爸呀。
整个校园仍然沉浸在午睡时分的安静和荒凉之中。这个世界昏过去了。这个世界代替我昏过去了。我宁愿昏过去的是我。为什么我没有昏过去?为什么我在手术台上缝耳朵受痛受骗时没有昏过去?我想把自己丢到太阳底下曝晒,晒成一根干树枝。我不想要这个孤单的我,因为孤单让我又敏感又脆弱,没有人保护我,没有人遮挡我。我的孤单比裸体更令人羞耻。
开学了。
父亲的才华终于得到一位要人的赏识,于是他被调回县城。
家人团聚,父亲的心情好起来。母亲的脸色也柔和了,显得更加漂亮。她在家里喜欢哼唱苏联歌曲,走路时脚步富有弹性。对我这样一个不声不響、从早到晚心事重重的女儿,她打量着,困惑着,然后扭头走开,不再理会。我用沉默呼唤母亲到我身边。母亲听不见我的呼唤。那么,我的呼唤是谁听去了呢?如果世上没有听见,就不会有呼唤。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把种种复杂难解的感受藏在心灵的角落里,专心学习。后来我上大学,工作,结婚,有了一个成天对着我笑的女儿雪儿。
休产假时我住在母亲家里。父亲母亲都退休了,对着外孙女笑得合不拢嘴。我看见母亲有一颗牙掉了。那个黑洞很刺眼,令人伤感。
母亲给雪儿洗澡时,撩起温水轻轻拍在她的胸口。雪儿咯咯地笑起来。母亲说:“宝宝乖呀!拍拍胸,不伤风……”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曾经以稚嫩的心灵承受着生活中的种种困惑,现在终于明白我是幸福的。除了认真地、谦恭地接受生活给我的种种安排,我不需要做更多的事。
我的女儿在我母亲的抚弄之下笑声不断。母亲,这个孩子是我身上开出来的花,我通过她那花瓣一样晶莹娇嫩的皮肤感觉到你的爱抚,我生下她来就是为了重新认识和再次感受你对我的爱。我和你,我们彼此相爱,从来,一直,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