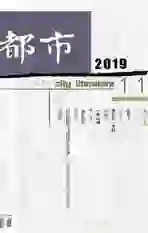一束玫瑰
2019-09-10李弗
我曾试图欺骗自己,我曾试图掩耳盗铃,但这都无济于事。睡眠质量越来越差,精神状况日渐不佳,幸好有位朋友做心理咨询,她建议我把这件事公之于众,用文字的方式。也许这些字没几个人看,但对你来说,却是种解脱,她最后语音是这么说的。为表示感谢,我回她一束玫瑰,但显示发送失败。显然,她把我拉黑了。
三十岁时,我已在广州打拼五年,刚升任副部长,事业顺风顺水,但相处五年的女友突然离我而去,因为她家人的反对。一个月后,她赌气和家里介绍的男友结婚,而我一气之下辞职回到老家。
回到平城,我先后在两家小单位待过,但时间都不长。头一个领导喜欢开会,每天开到晚上十一二点。他喜欢坐着,倚在皮沙发上,端着康熙青花茶杯,一边喝茶,一边给我们讲他的创业历程。那段日子每天下班后,小食堂吃完饭,我们便关上典当行卷闸,一排人站好,聆听他嚼烂了的历史。他笑,我们陪他笑;他感慨,我们摇头感慨。作为办公室主任,我偶尔小跑给他添茶,其他人只能定在原地三四个小时。最敬业的员工已经站了十五年,而我站了六个月,腰疼得受不了,就去了第二家单位。
这是家没在工商局注册的相册厂。单位除了我和门口的老黄狗,其余都是老总的亲戚。之前工人按天算工资,我去了后宣布改革,作为总经理,我规定每周放假一天。起初他们欢迎,后来他们认为请假还扣工资极不合理(以前全年无休,偶尔请假不扣钱),他们开始背后说我坏话,说我每天坐办公室,啥也弄不成。时间长了,老总也看我啥也弄不成。一天下午四点多,老板睡饱后灌了一缸凉白开,把我叫到办公室。我抢在他之前提出离职。他笑着挽留我,小李,干得好好的,干啥走呢?我拿上打过折扣的工资,坐上公交回了家———六十平的出租屋,堆满了书。
我也说不清什么时候爱上了写作,起先我写诗,但诗人太多,里面门派也多,口语、非口语、下半身、元诗歌、撒娇派、90后等等,有的互打口水仗,像古诗和现代诗一样军阀割据,自成一派,搞得人心惶惶,不说也罢。
我的第一首诗诞生在六年级。数学课堂上,我读完打油诗,周围同学放声大笑。写板书的老师回过头,让我站了一堂课,课后还要我叫家长。我怕我爸把我打死,就哭了。老师念我初犯,就没再追究。我要感谢老师,否则我就没了。我没了,你们就看不到我这篇废话啦。当然,我还是希望我爹揍我一顿,可惜没机会了。一次矿难把他带走啦。我高考后,母亲一人搬到了乡下。
高一我写了第一首现代诗,来自语文老师的作业。当时刚学完海子的《面朝大海》还是舒婷的《致橡树》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那首诗的大意:我们要好好学习,否则走上社会,越没文化起得越早。这个规律是我上学路上悟出的。我发现最早起床的是环卫工,而有钱人几乎不用起床,每天猪一样躺在被窝里就把钱挣了。
記录这首诗的日记本高三时归了西。因电热毯连电,小平房烧光,日记本也就没了。屋子烧了三个多小时。晚上十二点半,火吃饱木头,黑灯瞎火睡了。随后我和母亲躺到炕上,头枕繁星也睡了。烟味勾引我梦到大草原,在篝火旁,我和父母围坐一团,开怀畅谈。父亲不时摇动烤全羊,我频咽口水,却始终没吃到肉。
回到那首诗,我还记得老师的评语:人无贵贱之分,读书关键在于做人;人有聪明迟钝,关键在于持之以恒。我要感谢老师,他纠正了我的价值观。从此我加倍努力,不过因为脑子笨,差一点上二本。想到家里条件,我没复读,选了大专。
毕业后,我找了份工作,在一家大企业。一年内,我自考完本科(工资按本科算)。在南方,我过得很好。但回来后,学历开始失灵。去好单位要托关系。考公务员要本科,还要全日制。这就是现实,虽然我以前干得很出色,但这里没有工作适合我,或者说我不适合在这里工作,直到我做了一个决定———写短篇小说。
当然我写过长篇,毕业后,在第一家单位我就发誓要写一个长篇。我用一年写了十五万字,修改十多次,哭过三四回,但出版的事最终不了了之。
搞文字的人大多清贫,这是王老师说的。当时我读高二,他在朋友的一家书店遇到我,见我喜欢读书,就说想借书随时借,全部免费。接着我成了他的私人学生。他每周给我上一节免费作文指导课。他家在学校东的一个村里。当然现在这个村已变成市区,村里人每家每户都拥有三四套楼,真正过上了小康生活(除了个别因赌博毒品败了家),但这里没有王老师,当初他租的房,是只有八九平的小房。
至于王老师讲过什么,我早已忘却,只记得那个冬天,炉火正旺,照着他满地的稿纸(最高有一米多)。他刚讲完课,突然叹了口气,像在对我说,又像是在对他自己说,搞文字就要耐得住清贫。他左手抚摸稿纸,身子倚上去,像靠在爱人身上。
后来我知道,他那时刚离婚。之前他是初中语文班主任,离婚后就不干了。有人说老师就是他老婆帮讨的,所以没脸继续干了。如今想想当时的他,没钱没工作,正如现在的我。或许我还赶不上他,毕竟他结过婚,而我还没有。
说来你别笑话,我上次拉女孩的手还要追溯到六年级。打油诗事件后,女同桌可能看上了我的才华,爱屋及乌,她又看上了我写诗的那根钢笔。我写纸条说,想要吗?她点点头。钢笔金光闪闪,像金子做的。那你给我什么?纸条替我问。她画了一朵玫瑰,用红圆珠笔。小李弗摇摇头,想了想,在纸上写下,可以摸摸你的手吗?
于是,原始交易出现了。钢笔像个小奴隶,被我推到课桌中央,又被她关进铁笼。她盖紧文具盒,把一支铅笔碰到地上。声音刚响起,她便蹲下,在安静的自习课上,一只手落到我裸露的膝盖上。
我头冒虚汗,双臂交叉桌前,假装看课本,实则一只手在下面反复抚摸另一只手。她的手很绵,像肥皂般打滑,我怎么也抓不住,直到蛇一般溜走,回到她身体。她捡铅笔坐起,挺胸抬头,认真写作业,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胳膊偶尔碰在一起,我红着脸望她,她依旧认真写字,偶尔拿出那支笔用一下,像用自己的钢笔一样。
那之后,我再没摸过女孩,更别说亲了。所以我是个处男,虽说这对三十多的男人来说有些耻辱,但我还是要不知羞耻地说出来。也许有人会问,你不是说交过一个五年的女友吗?
对!在我们交往的瓶颈期,她约我来到一家教堂,颇为严肃地说,李弗,我有洁癖,而且家教很严,可是为了我们的将来,接下来我说什么,你都能答应吗?我鸡吃米似的点头。随后,在主面前,我把双手按在圣经上,对着她展开的小抄念道:我李弗今天发誓,在结婚前,我绝不碰女朋友一下,否则天打五雷轰,阿门。
总之,在相处的五年里,我们只能用眼神交流。一次,我在电影院和她看鬼片,偌大的影厅被四五对情侣瓜分,其他女孩都依偎在男孩身旁。他们心思不在电影上,恐怖情节是他们感情的润滑剂。就在镜头一晃,一颗血头颅出现时,我面对屏幕,手悄悄伸向她。
最终,我爪子没碰到她,碰到一瓶她手握的可乐。可乐让我乐不起来。她愤怒地看着我,像对待流氓一样,用可乐瓶做教鞭,用力砸向我的鸡爪———我长长“啊”了一声。其他人好奇地看向我,有几个女孩还在抿嘴笑。这件事的后遗症是我的手肿了三周。
此后,我再也没敢碰她,包括碰她的想法,都被我彻底囚禁。我们像圣人谈恋爱,直到五年后,她打电话向我哭诉。她说她爸给她介绍了个老乡。我问什么时候的事。她说不到五年。我陷入沉默。
李弗,你快说,我该怎么办?他昨天把我领到酒店那个了。她开始下雨,像梅雨季没完没了。半小时后,雨声小了。我问她怎么办?她叹了口气,在电话那头自语,看来只能和他结婚了。就这样,我一气之下回到平城。我曾计划孤老终身,直到遇见了另一个她。
万事开头难,短篇写到第三年,终于发了一篇。一千多稿费让我高兴了一整天。当天吃了碗刀削面,加了鸡蛋、丸子和一块豆腐干。另外我从饭店顺了三瓣蒜,方便回家吃泡面。以前上班时攒了些钱,写诗也有一点稿费,但这些钱要维持长久的温饱还是远远不够。
我尝试做兼职,在网上发信息:本人男,身体健康,本科学历(自考),可帮人跑腿、排队、解决各种疑难杂症(只要不违法即可)。名额有限,快来联系我吧。
消息发出半年,才有人联系我,在御河生态园门口,他戴墨镜扶银色金属栏杆说,任务很简单,就是帮我给一个女孩送花,每天一束玫瑰,连送三个月。除去花儿的钱,报酬两千,怎样?
任务没难度,我当场点头。别说两千,五百也干,毕竟我无所事事(用小区人的话说),快要吃土了。另外,往高尚靠拢,给人送玫瑰相当于为月老跑腿。也许月老在天有灵,见我为他(她)分担工作,说不准哪天一高兴,就许我一段好姻缘呢。
闲言少叙,我随他走进公园,左拐右拐,在假山旁停下。他从屁兜掏出单筒望远镜递给我,你瞧,就那女孩。透过朦胧的眼镜和斑驳的绿叶,一群人在广场上跳舞。我对他的审美感到惊讶。我对任务的信心跌到谷底。你说年纪轻轻一人,长得也不算難看,怎么会喜欢上老太太?莫非对方是富婆?我在心里合计。
把眼镜架脑袋上,我下蹲,闭右眼,举起望远镜,调整焦距:镜头划过一个又一个老太太。过了一会儿,我放下镜筒,脖子绕圈响了几声后仰头问他,到底是哪个老太太?
他笑到咳嗽,顿了顿说,哥,难怪你戴眼镜,不是老太太,是那个领舞女孩,站在最前头的。我放下眼镜瞅了瞅,好像是有个领舞女孩。我以树丛为半径,以女孩为圆心,逆时针转了至少九十度,直到我再次蹲下,一眼瞧见了她。
广场舞喇叭不那么刺耳了,当我看见镜头里的女孩儿,突然发现我厌恶的不是广场舞,而是广场舞上的大妈。我眼球像附了魔的司南,即便没了望远镜,它依旧不自觉地朝女孩转。
我把身份证递给他。他用手机拍照后,交我五百定金。从明天起,你开始任务!我要和她说什么吗?我问。除了打招呼,啥也不要说,她会懂的。那她偏要问呢?你按我说的做就行了!小伙消失后,我穿着老北京布鞋,走了过去。在音响后面,我找了块石头坐下。默默注视着她。
我看过许多文章,说一个人美到无法用语言形容。每读到这些,我就觉得作者在扯淡。怎么可能?明明因为自己词穷不能形容,还冠冕堂皇地给自己找梯子下。如今,坐在公园,清风拂柳,看着舞动的她,我只能说,她美到无法用语言形容。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扯淡,说我词穷。可有一天,遇到你心所属,你定会瞠目结舌,和我有同样的想法。
接下来看看她身后的这些人吧,和她有同样的舞姿,但完全是女娲加班疲惫后丢出的不合格产品。二排左手这男人,跳得完全不合拍,有眼无珠,僵尸一样摆动手臂,偶尔还自顾自地原地转个圈儿,活宝一样,看着就让人发笑;右边大妈一脸怒气,像谁把她得罪了,机械地模仿舞步,没半点情感律动;再看后面这二十几位,广场舞对他们而言,就像上班一样磨洋工。
既然不快乐,为什么来跳舞呢?如果跳舞都不能带来快乐,还有什么能带来快乐呢?我去过几个国家,也接触过一些老外,他们工作的时候,总感觉他们是在享受。而我们的笑容去哪儿了?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用十八世纪浪漫主义抒情的笔调发问,我们的笑容哪儿去了呢?
关于小说,我以前学过不少技巧。比如写一个人,直接描述就很低端。如果用语言行动来展现人物的性格,那样的技巧必然更为高超。就像要表达曹操多疑,当他听到主人家有磨刀声,他不会去调查,直接杀光全部人。当然我也可以这么写,但如今的我还怕什么?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有十几篇稿子像精子一样迷失在网络,找不到投胎圣土。所以对这篇小说而言,我打算放弃那些技巧。过去的作品大多源于想象,而她太过逼真,频频在我眼前舞动,仿若触手可及,又远在天边。那么来看看她吧,来看看她吧,跟随我笔触的眼来看看她吧:
舞动中她的腹部像鱼儿打挺。丰满的唇一张一合,仿佛歌声就是从她嘴里流出。她面带笑容,酒窝似沙坑让任何看过她的人都深陷其中。她牙齿雪白,眼睛大大,黑皮筋儿扎的辫子上下舞动。白T恤布满亮片,像鱼鳞在舞动。白浪一波未落,一波又起。牛仔短裤黄金分割点上,一颗铜扣瞩目耀眼。舞动中她的T恤偶尔卡在裤边,鱼肚白一闪而过。她的舞姿如此优雅,让我忘了她是否有穿鞋。她四周围着一群人,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给她添柴加火。她在持续燃烧。
我想就此搁笔,不再描述。当然不是我文笔有问题,她可以写三天三夜,三天三夜也只能描绘她的一只眼,描绘她一只眼的一个瞬间。我不敢描述,我会深陷其中。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如果描述太过逼真,那会令人窒息的。你想,如果艺术品比生活还要逼真,如果机器人比人还有人性,那世界就乱了,真的乱了。当然,这些话可能自相矛盾也难以理解,如果你不能理解,直接跳过就好。
第二天她跳完舞,我便走上前去。她在收拾音响。我把玫瑰藏在身后,对她说你好。她愣了一下,面带疑惑点了点头,轻声问,你是?把玫瑰交给她,在单筒望远镜的注视下,我对她说,你舞跳得真好,是我见过跳得最好的。她吐露微笑,像一杯牛奶,一杯温牛奶,加少许蔗糖。我还有点事儿,今天就这样吧,再见!在她的注视下,我匆忙而羞愧地冲她摆了摆手。她手举得不高,也冲我挥了挥。
不久,年轻人追上我,问她说了些什么。我说我什么都没告诉她,就按你说的,我什么都没告诉她。年轻人说,我看你和她好像说了很多。我摇摇头说,只是普通的寒暄。年轻人笑了,他拍拍我肩膀,说干得好。这让我想起以前的新加坡老板,每当我做完一件事,他就会拍拍我肩膀,对我说Well Done!
光阴似箭,每天我都早早起床,买上玫瑰送她。晚上她也有广场舞。每到夜晚,我会躲在暗处观察她。在月光下,她如水中百合,散发出迷人气息,让人不能自已。
整整一个月,我都没写一个字。过去我每月会写一两个短篇,最近我一个字都没写,我的心完全静不下来。唯一和以前一样的是,我还保持着读书的习惯,这个月读了八本:《高窗》《曼布克奖短篇集》《阅微草堂笔记》《巴卡卡伊大街》《二十一个故事》,还有几本杂书。
每天依旧泡面,以前吃两块五的康师傅,一天三袋。后来改成一块一袋的,这些面的名字不固定。我每次给小卖部十块,阿姨就会给我装十一袋,超大面饼,非常适合我。方便面吃腻了,偶尔我也会买几个馒头,就着咸菜吃。
从前我眼里只有小说,似乎我已没有亲人,小说是唯一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如今我重新焕发活力,每天刷牙洗脸刮胡子叠被子,偶尔还会给我妈打个电话,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我感觉生活充满了希望,我会对陌生人微笑,偶尔陌生人也会对我微笑;我会偶尔给乞丐一枚硬币;我会把垃圾放进垃圾桶;我会站在斑马线前耐心等待红灯(哪怕其他人全部闯红灯);我会对别人的冷言冷语报以微笑。
我没问她名字,她也没问我的。每天把花交她手里,她都会冲我笑,那是我一天的点睛之笔,是我灵魂出窍的时刻。偶尔她也有烦恼,当她的笑显得犹豫不定,那一天我也会难过。她就是我头顶的天空,我随着天气改变自己的心情。当然,拿望远镜的人依旧每天蹲在那里。
对了,我可不是那种人,那种不道德的人。我不会破坏他们的感情。社会教育我不能做第三者,哪怕遇到心上人。我只会把这份爱藏在心底。日子过得巧克力般絲滑,直到有一晚,年轻人把我叫去。
当时我还在公园,趴在假山旁看她跳舞。手机响了。我手机半年多没响。半年前给我来电的是一个95开头的骚扰电话,对方问我对股票有没有兴趣,我认为这是对我赤裸裸的挑衅,我直接挂断电话,把它拉入黑名单。之后便没人骚扰我。我像一只山羊,即将死亡的瘦山羊,体内没有多少血肉,饥饿的猛兽撞见我都会转身离去,包括嗜血的蚊虫,这些飞舞的先知,都对我丧失了兴趣。
我是第一次来平城的夜店。以前在广州时我去过两次,在平城还是头一次。大厅浮着白雾,像涌动的海面,人头上下漂浮,双手似桨前后摇摆。这些丢失身体的双手想要抓住什么?这些七零八落的头颅在呐喊什么?
划过舞动的人群,我在角落找到了他。他让我喝酒。我知道他请客,一口喝下半瓶啤酒。我好像突然醒了,周围浓雾笼罩,却又如此清晰,舞动女孩的身材个个完美,男孩子们个个富有朝气,我觉得自己是里面最丑的一个,穿着规矩,没有品位,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喝下三瓶酒,他开始说话,兄弟,人啊,麻烦。我没回答,继续喝。音乐一震一震,我就着花生米,放眼舞池中央:一个女孩穿着暴露,冲台下蹦蹦跳跳,她高举双手喊一声,人群高举双手喊一声。不久,我眼神开始迷离。她不过是一颗星,一颗流星,而她是太阳。
他说他本来不想活了,直到看见广场上的她。你们不认识?我恍然大悟。他点点头,抬起眼皮,布满血丝的眼望着我说,虽然她还没见过我,但我很喜欢她,真的很喜欢她。我点头附和。他继续说,我希望可以嫁给他,三两秒后,他露出尴尬的笑,不,我想把她娶回家。他面露苦色,摇头感慨,但我不敢表白,可能我受过刺激,你能帮我吗?
我脑子有些昏沉。他脸朝舞池,好像不是在对我说,你知道吗?我没什么正经工作,我怕她拒绝我。你干什么的?我问。他挠头说,我本科生物工程,但刚开了个起名算卦店。你也知道,我们这里没什么对口职业。起名算卦?我有些好奇。你知道吗,最近起名比较火,各地整治崇洋媚外楼盘名什么的,我感觉是个商机,所以打算试试。
又聊了一会,他突然说,我想明天向她表白,你……可以帮我吗?我说你不是要送三个月的花吗?他低头说,我现在心都在她那里,我活得难受,一刻得不到她,我心里就不踏实,我怕别人把她抢走了。他抬起头说,你不用担心,钱全给你,一毛不少,我都给你,只要你明天完成任务。他把一枚戒指交给我。钻戒闪闪发光,似乎价值不菲。我拿在手里,掂量掂量说,你不怕我把它拿走吗?他笑着把钻戒收回说,明天早上见。
晚上我彻夜无眠。原来他们不认识。他和我一样,只是见到她后喜欢上了她,仅此而已。第二天跳完舞,她像往日一样收拾音响。我叫了一身嗨。她停下手,转身站起,冲我笑了笑。看我手里没花,她半开玩笑说,今天怎么没带玫瑰,忘了吗?我表面微笑着,单膝下跪,绅士一样,从衣兜掏出钻戒盒,用力拉开弹簧,把钻戒呈给她。她高兴极了,至少有那么一刻她是开心的。当她快要碰到钻戒时,在一群人的围观下,我告诉了她实情。
手缩了回去,脸变得苍白,她转身回去,收拾音箱。为了钱,我跟了过去。她没抬头说,你告诉他,我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我。而且,我的家庭他不一定能接受。她声音低下来,我的家庭没几个人能接受。你的家庭?可以说说吗?我知道这对她来说有些残忍。我家有个病人,卧床多年,我要照顾他一辈子,你懂吗?她嘴微张,呼出一口气,摇摇头说,对不起,我忘了,我们还不认识。她转头走了,拎起小音箱。
我知道此刻望远镜注视着我。他看到的和我看到的一样,女孩点点头,又摇摇头,最终没有接受钻戒。为什么?女孩不应该拒绝钻戒啊,在林边他问我。我把女孩的话转述一遍。他瞬间眼神下垂,摇摇头说,真可惜啊,真可惜。花还送吗?我问他。他摇摇头说,我要回去问问。他把剩下的钱交给我,让我等他消息。
当晚他又找我,还是在酒吧,他说他是独生子,家里有车有房,无奈年龄大了,家里催得紧。我说你们要结婚吗?他摇摇头说,我妈不同意。我点点头说可以理解。喝了几瓶,我还是忍不住问,你不爱她了吗?他看着舞台上的女孩说,你知道吗?我以前给自己算了一卦,我们没戏。你看,果真没戏。
喝到晚上十二点,他终于醉了,而且还哭了。他拉着我的手,喊我小美,还不停要我原谅他。我结过婚,他酒醒了一些,放下我的手说,结了一年半,今年过完年,我们离了。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他鼻涕拉出一头长,我递给他几张纸巾。
他说过年有一天喝多了,他回家就打了她。他说当时是不受控制,可能因为事业不顺,他和朋友合伙开店,朋友卷款跑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我打了她,他苦笑着说,我当时打算跳御河,阴差阳错,在广场遇到了她。可惜,他摇头感慨,可惜,可惜她的家庭,要她家人都没毛病就好了。
我们关系越来越好。她很体贴,在电影院依偎着我,像普通情侣那样。也许你没有想到我们会在一起,毕竟如果她的话属实,在当今社会,没几个人会为了所谓的爱情而一辈子多个累赘,而且还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当然,我也不是圣人,能和她走到一起,我只是比普通人多了个心眼。说实话,你别骂我,我这样做可能有些不道德,但在爱情面前,哪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呢,是吧。
也许你猜得到,也许你猜不到,她拒绝他第二天,我尾随进入她小区,在十三号楼二单元门前凉亭旁停下。请原谅我的无耻与好奇,我就这样守着,直到一辆电动三轮停在门口。车栏放下,一位大叔穿蓝大褂走进楼道。一会他背着四箱饮料出来,放在车上垒好。不久她出现了(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叫白雪),她也穿着蓝大褂,背着三箱饮料,放在车上垒好。
就这样,我天天在她家门口蹲守。一天早上,她出去跳舞,我走进楼道。一楼左门虚掩着,我拉开门,这是一家超市,货物堆满整个房间。瘦阿姨问我要什么。我往里走,左右看了看。左面是方便面房,右面是卧室。卧室门开着,没见有人卧床。
在路上我心里乐开了花,看来这是白雪的计谋,可能追她的人太多,她只能用家有病人来考验对方。事情弄清第二天,我带着一束玫瑰找她。開始她没接受。我说这束玫瑰是我的,不是他的。
她之后曾问我爱不爱她。我说爱。非常爱。她问我当初为什么不自己表白,非要替别人那个。我说人要讲信誉,我不能夺人所爱。她掐了我一下,非常用力地,在我胳膊上留下一条爱的痕迹。
后来她向我吐露,高中毕业后就没继续读书。因为小时学过舞蹈,就在北京待了几年。现在一边照顾家里,一边在舞蹈班或什么地方兼职。她还说家里以前做批发生意,租了个门店,后来门店拆除,就在御河小区买了房,住房又当库房,她笑着说,平时我爸给小卖部送货,我妈接电话什么的,这就是我家的大概情况。在等待咖啡馆,她胳膊抱拳支在胸前,闭眼许下了生日愿望。
那天夜里,我们坐上最后一班公交车。在二层最前排,面对夕阳,我轻触她的手,她轻碰我的手。我们目视前方,最终两手握在一起,像两块磁铁,久久不能分开。我的大拇指抚摸着她的肌肤,大脑一片空白。夕阳无限好,我送她回到家,在单元门口,她第一次邀请我进她家。
正因为此,我们的爱情草草收场了。在她家拥挤的卧室,我找地方站下。她母亲端来水,我客气地点着头,目光始终盯着床上。不知该如何表达,他躺着,光头,面部没什么肌肉,像外星人。她很熟练地跨步上床,把一盆水放在一旁,掀起男孩身上的被单。这是一具男孩的裸体,一米六左右,全身没肉,表皮松软似蜡滴从骨骼垂下。她洗毛巾,给他擦拭……
看来她没有撒谎。她后来说,她弟本来很健康,也很聪明,但一次疫苗出了问题,从此就瘫痪在床。我问她为什么那天没看见弟弟。她说父亲经常打听哪里有神医。那天应该是拉她弟大早去了个大夫家。听说那大夫听了她弟的事,说可以免费治疗,但看了看他的身体,还是摇了摇头。
就这样,知道实情后,我逐渐疏远她。其间,送玫瑰那小子问过我她的微信。她也问过我为什么不再和她交往。我没回复她。因为母亲把她的情况告诉过她的亲戚,她的同学,她的邻里,他们一致反对我们在一起,说我们不会幸福的,如果有那个弟弟。
后来有近三个月,我没在公园见过她。我向人打听,一位大妈说,她结婚了。我有些惊愕。直到昨天,我在公园又遇见了她。我蹲在树丛,偷偷看她。她似乎还和以前一样。
正当我恍惚时,有人拍我后背。我回头看见了他———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笑呵呵的。他让我过去看,我摇摇头。他说,我们结婚了,你知道吗?我摇摇头。我们还要感谢你呢。我尴尬地笑着,嘴里吐出几句祝福的话。
他说上次和我要白雪微信时,他家刚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因为什么我没问,但他笑着回答了,你看,我腿被打断了,因为算卦的事。他拍拍腿,爽朗地笑着说,可我娶了白雪,真是因祸得福啊。
我推着他来到广场,一起看白雪跳舞。我隐约见白雪胳膊底有淤青,当然也可能是我眼花。广场舞结束,我打算离开。他拉住我,说要一起吃个饭。我摇摇头说,我还有事。他说那你和白雪打个招呼吧。我点点头走了过去。你还好吗?我问她。她没抬头,边收拾音箱,边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