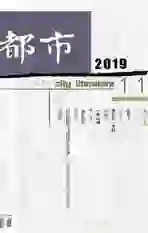遥远的父亲
2019-09-10刘焕兰
刘焕兰
我的父亲刘仁昆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每當想起他,我的眼泪就会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可我小时候却怨过他、恨过他。
小时候,从我刚学会说话,稍有懂事,就知道我妈亲我,我爹不喜欢我。每当别人逗我,让我学我爹怎么叫我,我就拉下脸来,恶狠狠凶巴巴地喊:“焕兰!焕兰!”又问我妈妈怎么叫我,我就学着妈妈的样子,笑眯眯地亲切地喊:“焕兰兰,焕兰兰”。逗得大人们笑得前仰后合。这时,我总看见妈妈和外婆并没有像别人一样笑着,而是偷偷地抹眼泪,外婆一边哭一边摸着我的头说:“恓惶的我孩,这么小就遭上后老子,没人亲。”
是啊,那不是我亲爹,而是“后老子”。稍微大一点,我就问妈妈为什么我爹是后老子不亲我?妈妈哭着告诉我:“你亲爹叫刘仁昆,十四五岁就当兵,一直跟部队打仗,我们结了婚也很少回家。后来跟王震的部队去了新疆,留在新疆工作,你两岁时你爸回来要和我离婚,嫌我没文化,我也不想到新疆去,就答应离婚了。原来他们不想让我带你,可是我舍不得你,我提的唯一条件是,要让我离婚,孩子必须跟我,否则我不离婚。就这样我什么都没要,就带上你,谁知道找的后老子不亲你,尽让你受罪。”
听说我小时候特别爱哭,妈妈在继父家生的第一个女儿,没活几天就死了,我就接着吃上奶,继父看见就生气地骂我:“哭、哭,硬把小的哭死,真是个扫把星。”
那些年闹饥荒,没吃的,继父常嫌我能吃。特别是妈妈后来又生了两个弟弟后,继父更嫌弃我了。每当我端起饭碗,他总拿白眼瞅我。妈妈一边抹眼泪,一边塞给我个窝头,让我到院子里吃去。因为经常吃野菜,吃了以后又特别容易拉肚子,因此,我的身体从小就弱,冬天,经常又因为吃糠太多,拉不下屎,特别受罪。村里人看见我的状况经常说:“不寻你当官的老子去,在这里受这些罪。”每当这时,我就会怨恨我的亲爹刘仁昆,是他抛弃我们,让我遭受这么多苦难。
一九五三年,我虚岁八岁,看到其他小朋友报名上学,我很羡慕,就央求我妈给我报名,妈妈说:“咱们家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供你上学,你后老子也不会同意。”眼看其他小朋友都能上学,而我却不能,我很伤心。
一天,姑姑来继父家找我,说我亲爹从新疆回来了,叫我回去。妈妈高兴地一边给我洗脸、梳头,一边叮咛我说:“是你亲爹回来了,快回去,嘴要甜一点,要叫爹,这下你就可以念书了。”
跟姑姑一进奶奶家,见门边凳子上坐着一个男人,穿一身不同于一般农民穿的干部服,姑姑对着那个男人说:“哥,给你把女儿领回来了。”那个男人一下把我抱在怀里,由于对生父有些怨恨又很生疏,我就把头扭在另一边。只听奶奶、婶子、大娘们说:“仁昆,你闺女长得真像你。”那个男人高兴地说:“是吗?我看看。”他抱着我在镜子前照来照去,然后高兴地说:“像,像。”一边问我:“你叫我什么?”我已猜到这个男人就是我的生父刘仁昆,于是怯生生地说:“叫爹(dia)”。只见他高兴地到柜子跟前,打开柜子,给我抓了几把葡萄干和糖,见我手里放不下,就装在我口袋里。看见我吃得香,爹高兴地说:“吃完还有呢。”
第二天,我爹就带到学校报名,爹告诉我说:“这次回来就是为你上学。”每天婶子、大娘请爹吃饭,爹总是拉着我的手一同去吃。我吃剩的,婶子、大娘们要吃,爹总是说:“我的女儿吃剩的我吃,哪能让你们吃呢。”为此,奶奶曾逗爹说:“你经常说我不讲卫生,这个不干净,那个不干净,你女儿吃剩的你就不嫌不干净,我剩下的饭你肯定不吃。”爹笑笑承认。爹还专门带我进城买了好多衣服,学习用具。我穿上新衣服,爹高兴地说:看我女儿穿上新衣服更加漂亮了。爹问我高兴吗?我说高兴。爹说:叫我一声“爸爸”,我低着头叫了一声“爸爸”。爸爸高兴地边答应边抱起我亲了亲。
爸爸由于工作忙,一共在家住了四五天。在这四五天里我真正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父爱的温暖。爸爸临走时问我愿不愿意跟他走,我真舍不得离开爸爸,就说:“愿意。”不过要离开为我吃苦受累的妈妈,我更不舍,于是就对爸爸说:“我还是不去了。”爸爸尊重我的意见,爸爸还嘱咐我好好学习,一定会寄钱供我上学的。
1959年冬天,爸爸在北京开完会又抽时间回临县看我。虽然由于工作忙只住了四五天,但爸爸对我爱护和关照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爸爸见了面抱了抱已经十三四岁的我,问我冷不冷?一边给我搓手,一边问我的学习情况。之后又给我买了几身衣服和一双浅绿色的非常漂亮的雨鞋。记得姑姑说:农村的孩子没人穿这么贵的雨鞋。爸爸说:“女孩子大了,下雨在雨水里蹚不好”。回了家,爸爸把买的新衣服放在我面前让我叠,我不会,爸爸笑着说:“笨丫头,来我教你。”爸爸一边教我叠衣服,一边告我要讲卫生,一个星期洗一次澡,换一次内衣,洗脸时要把脖子、耳朵都洗干净。爸爸带我到亲戚家吃饭时,村里的人见了会说:“仁昆,快四十了吧,才记得还是小伙子呢!”爸一边摸着我的头一边说:“丫头都这么大了,我还能是小伙子吗?”时间虽然短,但爸对我的生活询问得很仔细,问我继父对我好吗?我实话实说:“不好,老嫌我能吃,一次蒸过年的糕,让我捏糕,我肚子饿,边捏边吃了一个还没炸好的素糕,继父看见了就说我偷吃。”爸听了很难受,第二天就专门到继父家和继父谈话。只记得爸爸对继父说:“焕兰是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对她好点,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三四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依依不舍告别了爸爸,但深深感到爸爸还是爱我的,他并没有抛弃我。
一晃我中师毕业,参加工作后结婚、生子,中间整整二十年爸爸没有回来过。虽然爸爸也来信教育我好好学习,要求进步,长大做好人民的勤务员,但1960年,在我刚考入初中那年,妈妈在继父家生的两个弟弟突然被烟闷死,妈妈忍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也跳井身亡了。我从此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爸爸并没有回来接我,只是来信说,灾难也能锻炼人。1963年初中毕业,虽然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当时国家困难,招生极少,我害怕我考不上学校,要求去新疆找爸爸,继母来信说:“你奶奶、姑姑一家、叔叔都在这儿,现在生活已十分困难,你来会更困难。”我怨恨爸爸不接我去,但又没有勇气直接反抗他们,只是去信借着埋怨妈妈没有把我抚养成人就弃我而死表达自己的不满。我还在信中写道:“我是冬天的寒风,夏天的烈日,疾病的传染者,大海航行的暗礁。”总之是人人都不待见的东西。爸爸来信说:小小年纪不懂事,怨天怨地太不像话。
虽然后来我考上了师范,有了落脚的地方,沒有必要必须到新疆找爸爸了,但二十年多不见,总觉得爸爸对我没有对他后来生的孩子们亲。当别人问我有没有爸爸时,我说:有和没有一个样,我的爸爸像在天上一样,够不着。我想去,一方面由于身体不允许,另一方面听说继母不想让人知道找了个老公家里还有孩子。这样我的心就慢慢凉了,也没有想去的念头了。我想,你们愿意承认就承认,不愿意就算了,与我无关,反正世界上有个我。
1979年,爸爸在北京开完会说要回来看我,我很麻木,我不相信他会真的回来。因此,他回来的那天,我没有去接他。爸爸就直接走到伯伯刘崇德家。当堂弟成生通知我爸爸回来后,我的心突突乱跳,不知是想笑还是想哭。到了伯伯家,我绷着脸说:“爸爸,你终于回来了,我以为你这辈子都想不起我来了。”虽然看见我不高兴,爸爸还是笑着说:“回来了。”在和伯伯、大娘们聊天中,爸爸说:“焕兰是个苦命的孩子。”我说:“我的命苦都是你害的。”爸爸说:“看这个丫头现在还恨我。”在伯伯家吃完晚饭,我提着爸爸的行李对爸爸说:“走吧。”伯伯、大娘说:“要不今晚就住这儿吧。”我不容商量像命令似的对爸说:“走吧。”爸爸向伯伯和大娘笑笑说:“我还是跟着女儿去吧。”伯伯说:“这一次你们父女俩终于有时间好好团聚团聚了。”一路上我虽然话不多,但确定这一次爸爸是真的回来了,而不是做梦,心里还是非常高兴和激动的。回了家,从未见过面的孩子们高兴地围着爸爸叫爷爷,儿子当时在院墙外面玩,看见我和爸爸回来更是迫不及待从两米多高的墙上跳下来,一边跑一边喊,我亲毑(jie)回来了。爸爸也高兴地抱着孩子们亲了又亲,闻了又闻,爸爸一边闻儿子满头是汗的头,一边笑着说:“一股狗骚味。”看到爸爸和孩子们亲热地闹着、玩着,我心里对爸爸的怨恨早就无影无踪,有的只是幸福和满足。
这是我成年后第一次和爸爸相聚,在这相聚的几天里,通过沟通,我知道了爸爸的不易。爸爸十四岁临县高小毕业后,经临县地下党的领导人高闻天介绍,到兴县参加了八路军。期间他还在临县赵家石崖一边教书一边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筹粮筹款支援前方。1949年他跟王震的部队去了新疆,留在和田地区担任洛浦县委书记,后又调到和田专署计委工作。刚到新疆土匪很多,他身上经常得带枪。总之,工作繁忙,而且有生命危险。“文革”开始后,爸爸又被夺权,失去了自由,唯一的儿子小晋也被武斗队打死。爸爸的心里藏了多少苦和累,能熬过来,并能回来看我,是我的福气。
亲情真是一种奇妙的感情,不会因时间和距离而隔断。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里,我想着法儿孝敬他,给爸爸缝了新被褥,孩子们每天晚上轮着给爷爷打洗脚水,爱人又买了最好的烟、酒、茶,叫上爸爸当年最好的朋友、同学来家里,做上最好的饭菜大家一同享用。总之,爸爸住得特别开心。不知不觉一个星期就过去了,我舍不得爸爸走,哭得很伤心,爸爸一边替我擦眼泪一边安慰我说:“傻丫头,别哭,我刚恢复工作,还要发挥余热好好干几年,等退休后还会回来的。”爸爸在“文革”中受了许多的委屈和伤害,但他信仰未变,总是教导我们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对当时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总是满怀信心地说:“不用担心,共产党有的是办法。”
1984年和1991年,爸爸又回来过两次,这时他已退休,但他不顾年老体弱,不远万里,不顾一路上多次换车颠簸,从新疆回来看我,这两次是我们父女一生相聚最长的一段时间,共两个多月。爸爸看我胃不好,特别消瘦,心里很是难过,他像检讨似的说:“唉,都是小时候没人好好照看落下的毛病。”于是爸爸到处打问医生,还找到他的老朋友当时的卫生局局长说:“你是卫生局局长,请一定找最好的医生把我女儿的病看好。”并亲自买鸡买鱼给我熬汤补身体。
爸爸虽已是古稀老人,但依然保持着革命军人的风度,走路呼呼生风,办事雷厉风行。每天早晨出去散步前都要用手摸摸还在睡觉的三个外孙,平时给孩子们讲他从小参加革命的许多故事,教育孩子们好好做人。爸爸还风趣幽默地和外孙们上街,也和孩子一样打闹,甚至和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孩子们特别开心。每当看到爸爸和孩子们玩耍的场面,我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满足,爸爸用深厚的父爱解除了我心中对爸爸的误解。
1998年,爸爸在珠海妹妹家中突发心脏病去世,我和老伴去时,爸爸已放在了殡仪馆冷冻。抱着爸爸冰冷僵硬的身体,我悲痛欲绝。亲爱的爸爸,你不是说今年秋天还要回山西看我和你的两个小重孙吗?为什么就这样狠心地匆匆走了呢?
爸爸的战友和上级部门为爸爸办了隆重的追悼会,《新疆日报》做了专题报道。爸爸的骨灰安葬在乌鲁木齐革命公墓,公墓里安葬着爸爸的许多战友,还有革命烈士,如毛泽民、陈潭秋等。我曾问爸爸,百年之后如想回老家,我负责。爸爸说:“从小参加革命,将来还是和战友们在一起,都是中国的土地,在哪都一样。”爸爸,您是真正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2014年,我和老伴带着孙子、孙女到新疆乌鲁木齐给爸爸扫墓。跪在爸爸坟前,我对爸爸说:“爸爸,女儿女婿带着您的两个重孙子看您来了,如您所愿,女儿的身体也有了好转,孩子们虽平凡,但都正直、善良、积极向上,我现在和继母、妹妹们相处融洽。爸爸安息吧,我们一定继承您的遗志,让您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发扬光大,愿爸爸在天堂一切安好!来生我还愿做爸爸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