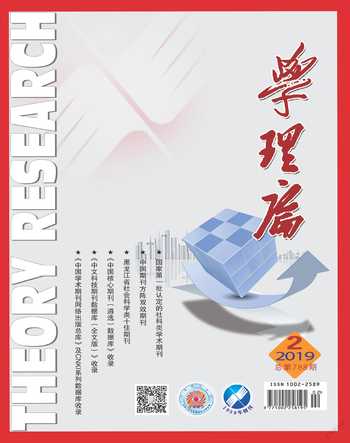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效力
2019-09-10陈姝元
陈姝元
摘要:《立法法》既规定我国的法律解释权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又赋予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解释的权力,但沒有明确司法解释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效力地位,使得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游离于整个法律体系之外。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这种效力不明确引发了大量问题,不仅无法完全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更是引发了法律规范适用的严重冲突。立法机关应规定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释在我国立法体系中的地位,对司法解释的效力加以明确,实现法律解释形式的规范化。
关键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法律效力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2-0110-02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法律解释分为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两类,其中司法解释即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做的解释。司法解释又包括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两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在性质上属于审判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通过发布专门的司法解释文件对法律进行解释,在形式上与立法一样表现为抽象的法律条文,承担着弥补法律漏洞、填补法律空白,和使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的功能。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的历史在我国由来已久,究其本源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伊始,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在立法缺位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承担起以解释创设法律、以解释细化法律的功能。乃至发展到今天,每一部法律出台后,通常都会有相应的司法解释与之配套。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可以被裁判引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我国的“法律渊源”,对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秩序和法治建设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的效力定位,其二是司法解释与其他法律解释发生冲突时如何确定效力位阶。探索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有助于规范我国法律体系,促进司法机关通过审判活动推动法律的完善与法治建设。
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类型与内容
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该决议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做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这是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
2007年4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发[2007]12号《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开始施行,1997年7月1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同时废止,进一步明确了司法解释的性质、效力、分类和程序。该文件第6条规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对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解释”的形式。根据立法精神对审判工作中需要制定的规范、意见等司法解释,采用“规定”的形式。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批复”的形式。修改或者废止司法解释,采用“决定”的形式。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主要的内容大致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直接对颁布的某部法律进行全面系统的细则性解释,如《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类是对某一类型的案件做出解释,如《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三类对某一类问题的系统解释,如《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类是人民法院内部有关司法程序操作的规定,如《关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类是对日常工作中高级法院就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的请示做出的解释,这一类解释占了已有司法解释的大多数。
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效力定位
前文已经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是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由此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具有进行司法解释的权力,但其发布的司法解释究竟具有何种效力,是否能够将其理解为司法解释具有与法律同样的效力,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做出规定。
我国目前关于司法解释效力的学说,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类型化说”,认为对司法解释的效力可以采用类型化的方法来认定。对具体法律条文进行解释的司法解释,其效力等同于法律。为法院内部审判工作需要而制定的司法解释,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部门规章”。第二种是认为司法解释效力低于法律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司法解释的效力低于宪法和法律,但根据上位法制定的司法解释的效力是否低于下位法,持这种观点学者还未就这个问题给出答案。第三种学说则认为司法解释的效力等同于行政法规。第三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有一个大的前提相同,即都认为司法解释的效力低于法律。不同的是,行政法规说将他们的结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将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纳入我国现行的立法体系当中。
在笔者看来,“类型化说”中的“对具体法律条文进行解释的司法解释,其效力等同于法律”这一观点更具合理性。笔者认为,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应当与其解释的具体法律条文具有同一效力。如果被解释的条文属于上位法,则解释该条文的司法解释就应当按照该上位法确定效力,下位法不得与该解释相抵触。如果新法律条文的司法解释与旧法律条文相抵触,应该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适用。同时,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除解释具体法律条文这一部分之外的内容,亦即关于某一类型案件、司法程序操作、具体法律问题适用等方面的司法解释,可以将其效力等同于“行政法规”。既明确了这类解释的效力低于法律,又使其处于我国现行立法体系中较高的位阶,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更有效的应用。
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效力位阶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效力位阶问题,主要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检察解释、行政解释之间的位阶问题。司法解释权是法律解释权的一种,是法律解释权分配于司法机关形成的权力。不同主体做出的法律解释效力高低,与不同主体权力层级高低有关,也与解释主体在诉讼中的地位有关。
立法解释位阶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这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关系决定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而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予修改或者废止的,可以提出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废止的议案,或者提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法律解释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由此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合法性进行审查,有权要求其修改或废止,也可以以做出法律解释的形式解决司法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问题,这就说明了立法解释的效力是高于司法解释的。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解释的位阶应该是同级的。司法解释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审判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的检察解释,《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这个规定表明了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之间没有位阶高低之分。当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解释对同一问题的规定不同时,具体适用哪种解释目前没有定论。笔者认为,当检察院处理案件的时候,如果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解释,自然应当适用。但当该案件进入审判流程时,则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行政解释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各自发生效力的领域不同。《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对行政解释的对象做出了规定,包括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而司法解释的对象仅限于法律,二者存在重合。审判机关、行政机关的解释,只能对各自的下级机关有约束力,不约束其他机关。
应当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具体案件审判依据是某一司法解释而非相对应的法律条文的情况,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下级法院具有普遍约束力,这实际上变相地在审判实践中推动了司法解释朝着“立法化”的方向发展,导致实践中低于法律与立法解释的应用价值反而低于低位阶的司法解释。
四、结语
长久以来,我国立法工作中对于一些具体的事项,往往都不进行规定。这种“立法宜粗不宜细”的整体原则是邓小平确立的,我国司法实践中逐渐演变成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来填补具体规则层面法律的空白。从实践经验角度来看,司法机关由于具体承担了适用制定法裁判案件的职能,这使得司法机关对于制定法的漏洞与不足最为敏感也最有深切体会,为司法机关通过审判活动推动法律的完善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司法机关能够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为审判活动规定具体的操作细则。然而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效力的不明确,越来越多的问题也暴露在人民视野中。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从源头的效力问题人手。站在立法角度来说,立法机关应当以立法形式对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效力地位及其位阶做出规定,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纳入我国立法体系之中。而从最高人民法院自身的角度来说,最高法院应当对自身进行司法解释的权力做出规范限制,应当仅就具体条文的应用进行解释,并须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如此,也更能契合十九大厉行法治的精神。
(责任编辑: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