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游与逃跑主义:何工访谈
2019-09-10孟尧何工
孟尧 何工

孟堯:《声音考古学》和去年你参加广安田野双年展的那件作品都是用喇叭做的装置,应该是同一时期的方案。这两件作品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
何工:不同之处是有的,广安田野双年展有两个要
素,一是改革开放40年,二是在邓小平故乡举办,
这就意味着浓厚的社会变革底色。中国改革开放始
于土地,那件名为《原野——肖申克留声机》的
装置在户外日夜播放有强大叙事力的古典音乐以隐
喻土地的自身讲述,混合了悲伤、苦难、期待与重
生,因此它仿佛有自己的主体性,是第一人称象征
物。而《声音考古学》是专为《画刊》45周年创作
的更多围绕信息传播史与时代演进展开思考,时间
因素使得优秀的媒体成为历史的镜子和纪念碑,成
为预言未来的标识,至少这是《画刊》杂志带给我
的启发。
孟尧:你的很多画,画得很厚、很重、很满。装置也重视体量和规模,来谈谈你的“表现主义”。
何工:我相信“新表现主义”对我们这一代艺术人有或多或少的心灵撞击和语言启发。1994-1995年我在荷兰驻留创作了半年多时间,乘火车漫游了一些欧洲国家,那里的几乎所有火车站都是古典主义工业风格,在我眼中就像历史剧场,回放着一幕又一幕流亡与重返的历史悲喜剧。后来几年里,我创作了几十幅名为《欧洲车站》的大尺幅厚重油画,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表现主义宏大呈现。仿佛我把青少年时代在中国的沉重经历链接到更有人类共同经验的场景中,进行一次关于灾难和命运的考古追问。
孟尧:我上次在你工作室里看到好几块画好的茶砖,印象挺深的。以前你也用牦牛粪砖画画,为什么选这类东西做媒材?
何工:过去10年我用藏牦牛粪砖块做过几件装置作品,比如2009年的《向路易威登致敬》和2011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5000米到0海拔——拯救威尼斯》等,之后又在粪砖上画过一些世界史人物的丙烯画。一度为收集牛粪,我常去藏区,在藏民家里,我第一次见到茶砖,材质和形状都很适合我的选择,也更容易获得,于是就尝试在茶砖上画画了。我的工作室没有暖气,晚上画大画比较寒冷,所以茶砖和粪块上的画都是冬夜在我睡觉的小阁楼里完成的,题材是些我感兴趣的历史图景,如美国嬉皮运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类轻松的东西。最近我的大学同学、雕塑家叶宗明先生研制了超大号茶砖和茶墨汁,我用它们画了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波士顿倾茶运动”,效果挺好。
孟尧:创作中最糟心的事情是什么?
何工:糟心的主要是技术问题,比如为了一件装置作品,我从藏区购买了100多张牦牛皮,由于技术处理不当,它们发出很浓的味道。类似的问题很多,技术问题背后实际是经济能力问题。
孟尧:你说:当我的思考走投无路,出现困难时,我的办法是逃跑,在逃跑中思考,把思考表达在作品里。我想问:怎么样的情况,属于思考走投无路?
何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是个天生的边缘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反主流,不合作,无集体认同,无家国意识,无乡愁,格格不入,逃离中心,自我放逐,怀疑自己。《在路上》式的办法好像过于颓废,难以向人交代,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加拿大读到了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以后才给自己的存在找到了解释。反西方中心,崇尚多元主义,对权力对体制持不可调和的批判立场,从萨义德那里我获得了我存在的理由。后来我又到了美国,消解话语霸权,抗拒既成法规,每年的报税、保险和一系列汽车违章都是我反感的,因此一直欣赏和梦想无政府社会,思想方面对社会规训的不顺从和经济能力的低下,使一切变得不容易。而“9.11”事件的爆发改变了美国和每一个个体。许多过去左倾的高校知识分子产生了动摇,新的站队出现了,靠向保守主义的人越来越多,下意识里能感到种族身份压力。我开始认真申请固定的教书工作,也得到了一些积极的回应。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面谈毁于我和两位面试者对待萨义德的不同看法上,他们告诉我,除了基础课教学之外(基础教学其实是我最不擅长和最不喜欢的),还得负责每年一到两位校外驻留艺术家的推选,问我有什么样的思考。我脱口而出建立多元文化工作室,邀请萨义德做讲座,气氛立即降温,结果可想而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教席(U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仿佛志在必得,数百位申请人中挑选了十位到那年在费城召开的CAA上面试,又从十位中挑选两位到学校讲座面谈,我就是那二分之一。特别想好好表现得到这份工作与我欣赏的芬伯格(Jonathan David Fineberg,Art Since 1940的作者)成为同事,但最终事与愿违,严重受挫。后来到华盛顿参加反战大游行,再后来就漫无目的地开车顺着美国边境绕了一圈。路经亚利桑那州水晶镇(Quartzsite)时到嬉皮公社残部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一段时间的绘画黑暗厚重,表达了对一些事情的警觉和忧虑。2004年我把这些画运回国,在北京做了个展,还出了一本薄薄的画册,你提问里的话好像就是我写在画册上的。

孟尧:“爆炸头”是你的重要标志,什么时候开始尝试这个发型的?对它满意吗?
何工:后来我回国到四川大学教书了,狂热的物质主义浪潮滚滚而来,人们在赚钱的焦虑和消费的亢奋中不知所以,令我这个赤贫的海归陷入尴尬。我决定在切·格瓦拉摩托之旅60年之后的2011年重走其路,以另类的行为反击享乐,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满足自己根本停不下来的放逐欲望。为此我改装了汽车和摩托车(因各国车辆管理太严苛而未能使用自带车),也改变了发型,好歹和切·格瓦拉弄得像模像样一点。旅途中(特别在秘鲁)的确多次被当地土著以为我是他们的同族,因此我对新发型是满意的。
孟尧:谈一谈你重走切·格瓦拉之路的经歷吧。
何工:起因还是萨特那句话,他认为切·格瓦拉不仅是个知识分子,而且是那个时代最善良的人。萨特说此话的年代是五月风暴和学运的年代,是列侬高唱让war over的年代,是西方知识分子集体左倾、里应外合反美的年代。2009年有一天,我在四川大学地摊上淘了一张《摩托日记》影碟,看完影碟就有了打算,觉得以“重走”之名周游南美是件挺酷的事情,不断邀约文艺圈的朋友与我同道,热血沸腾蠢蠢欲动者众多,但是到了出发时只剩我自己。如果把切·格瓦拉分解成几个时期,那么他的青年时代是单纯的,值得欣赏的。但是我的重走就没有那么单纯,也没有严格按照他当年的路线行进,多去了好些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去找寻博尔赫斯的旧居、去巴塔哥尼亚会面加乌乔牧人与他们共饮马黛茶、去乌斯华雅眺望南极、去沃索尔诺看火山、去聂鲁达故居朝拜、去亚马孙丛林邂逅雅华土著,以上都是当年切·格瓦拉没去的。当然他们游历的所有地点我也一个没拉下,阿塔卡玛沙漠、邱吉卡玛塔铜矿、提提卡卡湖、马丘比丘遗址、圣·帕巴罗麻风病区等等。我短暂而谈不上深入地目睹了当前南美各国的社会现状,对国民性和国体的关系有了更复杂的体会。从成都出发又回到成都一共102天,是一次很过瘾的浪游。

孟尧:为什么称长途旅行为浪游?
何工:浪游(wandering)、逃离(escape)、放逐(exile)是普遍的人的天性,不管主动还是被迫,这些行为都一直伴随人类。作为人类之一员,我在10岁那年读了《鲁滨逊漂流记》之后就盼望逃离家园流放天涯。特别当个人遭遇使你失去对家园认同感之后,你会暗示自己哪来故乡异乡,所有生命不过是小小寰球短暂过客而已,不然就没有了哥伦布、麦哲伦和“五月花”号。这种并非为了现实目的游离故土古已有之,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之后就更频繁了。比较影响我的是一战前后美国文艺青年游历巴黎的那些故事,失落的一代就是浪游的产物,南美诗人作家那时也加入了浪游的行列,不然也没有博尔赫斯。迈克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曾经感动过我,2015年我的个展也是以他的书名为展览标题的。
孟尧:你刚才提到了《鲁滨逊漂流记》,顺带分享一些对你有重要影响的书吧。
何工:我这样的人出生和成长于物质与知识双重饥荒的年代,求生欲远远重于求知欲,少年时代并不算丰富的阅读完全是以逃避严酷现实为目的。其中《鲁滨逊漂流记》为我播下了流浪的种子,当知青时读过的一本无头无尾繁体字关于杰克·伦敦传记的书保住了我心中希望的火苗,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让十八九岁的我深知生命的沉重,也刺激了荷尔蒙和青春幻想。而立之年在堪萨斯一所教会学校里读到的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On the Road)对我心头最后的顾虑起到了颠覆性的摧毁作用,以致几十年来我对“垮掉的一代”深怀敬意。我的不惑之年是十分困惑的,一个后来与我成为至交的西班牙雕塑家送给我一本克里希那穆提的英文小书《你就是世界》(You Are the World)安抚过我许多年,一本新书那些年被我翻得破旧不堪,但今天看来它就是一支麻醉剂和一碗鸡汤。自进大学以来所读的专业的、文艺研究的、史论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书籍杂多,它们不外乎给我提供了思考方法、表述策略和不同场合的谈资,还真不想对此多说。但是萨义德的书对我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全面地激发、纵容了我的批判、尖刻、反主流、不合作。但从根本上讲,我又是个逃跑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这真是个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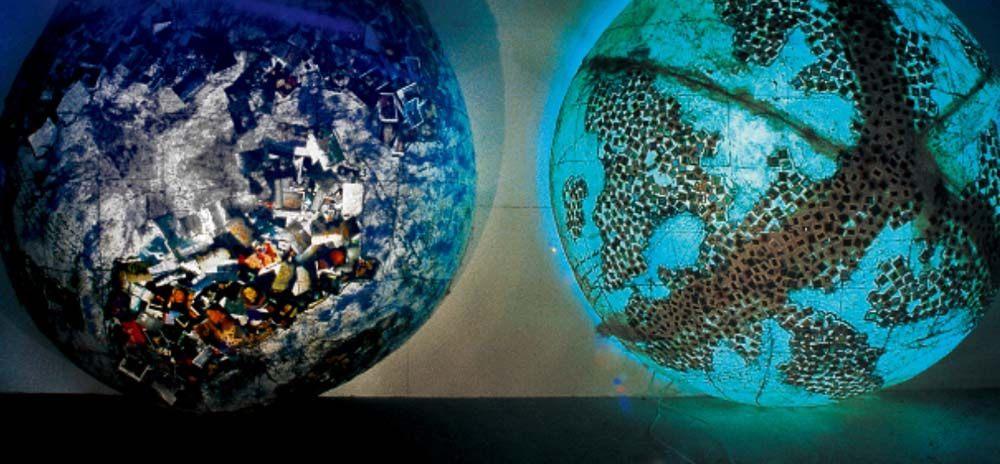
孟尧:对今天的艺术媒体(无论网媒还是纸媒),你是否还关注?你怎么看今天的艺术媒体?
何工:我不时怀念传书递信的慢时代,当年不仅没有手机,中国人还没有家庭电话,一封信至少半月才从堪萨斯寄达重庆。我在美国看美术馆的见闻和心得成为那群留校的哥们儿集体阅读和讨论的材料,舒群从北方群体给我寄到重庆西南师大的信经由同事转寄到我手里,时间已过去半年之久。那时的世界很大,未知的东西也很多,一册《国家地理》激活万千向往。今天大爆炸般的信息量和完全没有时差的传递速度使人们的感知系统疲惫,反而厌倦信息和渴望“无知”。我在电脑能力上的挫败感一直存在,长期依靠学生搜索必要的资讯,因此在教与学方面,我和他们的角色常常是颠倒的。这样也好,有限的脑空间较少被八卦占位。纸媒在今天虽然大受冲击,但其存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至少对我个人而言,纸本(或实体书)阅读能使节奏缓慢下来。艺术类杂志首选就是《画刊》,长期以来的新知、先锋和探索决定了杂志与未来同在生命力;《艺术当代》的学术性也受到我的长期关注;几本明星化、资本化和权力化的杂志因不合我的趣味越来越少阅读;还有少许杂志,在上面发表作品即可提拔职称,但出于保护眼睛的原因,我从来不看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