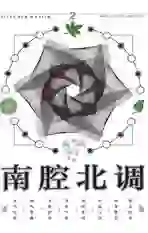从欧化特征明显到表达方式中国化
2019-09-10宋宁刚
宋宁刚

摘要:在新诗发展百年之际,检讨中国具有标志性的诗人的创作及其资源,非常必要且具有特别意义。其中,艾青在“朦胧诗”之前的诗人中,尤其具有代表性。艾青近70年的创作,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界,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借重西方诗歌和语言资源尤多,其欧化的特征也较为明显,无论是从语言格调、还是从表现方法来衡量,都是如此。不过,他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到40年代达到创作高峰期间,他的诗歌语言欧化的特征逐渐淡出,语言格调和表现方式愈来愈中国化。这种特点在中国新诗的百年发展中具有普遍性。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诗,在学习西方乃至化西为中的过程中,表达的欧化特征,是一种必然现象,通过学习、借鉴欧化的格调与表达方式,最终扩展了现代汉诗乃至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
关键词:艾青 欧化 中国化 语言的成熟
在新诗发展百年之际,检讨中国具有标志性的诗人的创作特点与成绩,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中,诗人艾青以近70年的创作,见证了20世纪的历史变化和白话文学的发展,在“朦胧诗”诞生之前的老一辈诗人中,尤其具有代表性。
一.艾青的“前期”
诗人艾青(1910—1996)自23岁(1933年)在狱中写下《大堰河——我的保姆》而轰动全国,直至86岁去世,活跃在诗坛60余年。实际上,艾青的创作生涯还可以再往前延伸。他的《当黎明穿上白衣》写于1932年;不少艾青的诗歌选集(比如2006年人民文学版的《艾青》一书),则将他写于1927年的《游痕(二首)》作为他诗歌创作的起点。如此算来,他的诗歌生涯有将近70年。
细察艾青跨越60多年的创作经历,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从他诗歌创作之初,到诗集《大堰河》的出版为限,在这期间,他的诗作与自己的个体性的生命经验结合较多,受欧化影响较重。
中期从1936年至1942年期间,出版有诗集《北方》《他死在第二次》《旷野》《向太阳》《火把》等。这一时期,他还出版了《诗论》。此外,诗集《献给乡村的诗》和《黎明的通知》,虽然出版于1942年之后,但其写作时间却基本上都在1942年以前。这一时期的创作,由于抗战爆发,诗人越来越深地被卷入时代的洪流,进而愈加深切地投入到中国现实中,其在诗歌创作上,无论题材还是写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诗歌语言方式也更加中国化。
晚期从1943年至诗人去世,又可分两段。第一段从1943年到1956年,第二阶段,从1957年到诗人去世。之所以这么划分,是因为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艾青在写作上更要求自己与工农兵的结合,在此创作理念的指导下,创作了长诗《吴满有》和《黑鳗》,并出版了《欢呼集》和《艾青诗选》等。其间创作相比1942年以前,又大不相同。第二段起于1957年,艾青被错打成“右派”,先后流亡北大荒和新疆,直至“文革”结束,重新复出,写下了《光的赞歌》等诗作,结集为《归来的歌》。这期间的诗风相比之前,又有所变化。
从以上划分来看,将艾青横跨半个世纪的后半生作为其创作的“晚期”,在时间跨度上似乎与早期和中期不尽协调,但是从其创作实际来看,却有其道理。一方面,无论从创作的数量还是质量来看,这一时期以1957年为界的前后两段都不足以成为单独的一个时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虽然漫长,但从其创作上看,与前述的早期和中期相比,艾青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其取向是服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转变在诗人的整个晚期创作中又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正因此,我们将其统一地看作“晚期”。实际上,包括艾青在内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于这一转变都是有确切的理由和真实的情感基础的。“文革”结束后,在诗歌创作上,艾青延续着自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形成的“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创作路向。因此,仍然有理由把以1957年为界的前后两段视作同一个时期。
早、中、晚期的划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把握艾青的创作历程,但是用来考察艾青诗歌创作中的欧化特征,似乎不很能说明问题,因为他在创作上的欧化特征,从早期一直延续和渗透到了中期,虽然这一影响的痕迹在减弱。直到1942年以后的创作,可以说他才摆脱了欧化特征,以简短有力的铿锵句式进行创作——稍早一些时候,具体说是1941至1942年,他也为“街头诗”写过创刊词,也对田间的战斗诗表示过肯定,从其文章来看,似乎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应景之作,相反,有理由相信他是真誠的。基于此,笔者认为,不妨以1942年为界,将上述的早期和中期合称为艾青诗歌创作的“前期”,而将其晚期的创作视为“后期”,以此两相对比,似乎更能说明艾青诗歌创作上的欧化特征之浓与淡、重与轻,乃至存在与拒绝。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路径也正是新诗中国化的普遍路径。
二.语言格调的欧化
何为欧化?用艾青的话来说:“欧化主要表现在语言格调上、表现方法上。”因此,“写外国的东西,如果采用我们民族理解的表现方法”,就不叫欧化。他还说,对于欧化,也要具体分析,电扇,皮鞋,西式衬衣,都是外来的,说欧化也可以,“但实际上与我们的民族发生了很久的关系”,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算不上是欧化。因此,这里说的欧化,就需要一个时间参照——在此便是以艾青前期的创作期(1927—1942),来考察他的“语言格调”和“表现方法”,在当时已然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抑或仍然是新的元素?进而,这些新的元素对当时乃至今天仍然具有价值和意义?
先从语言格调来看。艾青的早期诗作《当黎明穿上了白衣》,自注的写作时间和地点是“1932年1月25日由巴黎到马赛的路上”。全诗如下:“紫蓝的林子与林子之间/由青灰的山坡到青灰的山坡,绿的草原,/绿的草原,草原上流着/——新鲜的乳液似的烟……//啊,当黎明穿上了白衣的时候,/田野是多么新鲜!/看,/微黄的灯光,/正在电杆上颤栗它的最后的时间。/看!”这首诗,从语词的运用(“乳液似的烟”、“微黄的灯光,/正在电杆上颤栗它的最后的时间”),到断行方式(尤其第二节的“看,/微黄的灯光,/正在电杆上颤栗它的最后的时间/看!”),都有浓厚的“拿来”色彩。类似的还有《透明的夜》:“透明的夜。//……阔笑从田堤上煽起……/一群酒徒,望/沉睡的村,哗然地走去……/村,/狗的吠声,叫颤了/漫天的流星。//村,/沉睡的街//沉睡的广场,冲进了/醒的酒坊。/……”这种奏鸣曲一般节奏极强的诗,其语言格调,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无可借鉴,它只能来自对西方诗歌的学习,包括通过翻译来学习。
从艾青诗中强烈的色彩感(如“紫蓝的林子”“青灰的山坡”“绿的草原”“新鲜的乳液似的烟”“微黄的灯光”“透明的夜”)来看,欧化的特征就更是鲜明。仅就对色彩的敏感和强调来说,中国传统的绘画从没有像西方绘画(尤其油画)那樣注重色彩差异和光影的变化。当青年艾青写下这首诗时,他正在法国学习绘画,他对色彩天然的敏感,以及他从所受的专业训练中领悟到的对色彩感的敏锐和自觉,都强化了他在观照事物时对色彩的注重。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有时/我伸出一只赤裸的臂平放在壁上/让一篇白垩的颜色/衬出那赭黄的健康//青色的河流鼓动在土地里/蓝色的静脉鼓动在我的臂膀里//五个手指是五支鲜艳的红色/里面旋流着/土地耕植者的血液(《生命》,1937)
黄昏的林子是黑色而柔和的/林子里的池沼是闪着白光的(《黄昏》,1938)
你们的帆像阴天一样灰暗,/你们的篙篷像土地一样枯黄,/你们的船身像你们的脸/褐色而刻满了皱纹,/你们的眼睛和你们的船舱/老是阴郁地凝视着空茫(《船夫和船》,1940)上述诗中,无论“白垩的颜色”“赭黄的健康”“青色的河流”“蓝色的静脉”“鲜艳的红色”“耕植者的血液”,还是“阴天一样灰暗”“篙篷像土地一样枯黄”“船身像你们的脸”“ 褐色而刻满了皱纹”“ 阴郁地凝视着空茫”,都体现了受西方油画影响的艾青,以画家的眼睛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甚至在他回国数年之后,仍然如此。
1932年初,留学法国学画3年的艾青归国。未曾料,回国不到半年,他就因为所参加的“春地美术研究所”,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是“左翼美术联盟之机关”而遭逮捕,并因此招来3年的牢狱之灾。然而,也正是这个不幸的遭遇,造就了作为诗人的艾青——因为在狱中无法画画,拿起纸笔写诗却是可以实现的。在监狱里,艾青读到了亲人和朋友送来的《圣经》《兰波诗选》;也是在监狱里,他写下了《芦笛——纪念故诗人阿波里内尔》《ORANGE》《巴黎》《马赛》,以及著名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26首诗作——它们后来都被收入1936年出版的诗集《大堰河》。在这一时期里写下的诗作中,还有著名的《铁窗里》:
只能通过这唯一的窗,/我才能——/看见熔铁般红热的奔流着的朝霞;/看见潮退后星散在平沙上的贝壳般的云朵;/看见如浓墨倾泻在素绢上的阴霾;/看见如披挂在贵妇人裸体上的绯色薄纱的霓彩;/看见去拜访我底故乡的南流的云;/看见法兰西绘画里的塞纳河上晴空般的天;/看见微风款步过海面时掀起鱼鳞样银浪般的天;/看见狂热的夏的天,抑郁的春的天,飘逸而/又凄凉的秋的天;/看见寂寞的残阳爬上/延颈歌唱在屋脊上的鸠底肩背;/看见温煦的朝日在翩跹的鸽群底白羽上闪光;/看见夜游的蝙蝠回旋在沉重的暮气里……
这首诗引人注目,不仅在于它鲜明的色彩感(“熔铁般红热的奔流着的朝霞”“贝壳般的云朵”“如浓墨倾泻在素绢上的阴霾”“微风款步过海面时掀起鱼鳞样银浪般的天”……),其语词构成上的新意,强烈而鲜明的造型感(“如披挂在贵妇人裸体上的绯色薄纱的霓彩”“法兰西绘画里的塞纳河上晴空般的天”),其浓墨重彩式的准排比句式,浪涛般汹涌激荡的铺排及其气势,都是典型的欧化(排比句远非中国传统诗歌的产物)。对比一下艾青在狱中所翻译的凡尔哈伦的《原野》《城市》等九首诗,尤其诗中形式宽松的排比,不难看出他的诗歌的来源。读者从中甚至能够听到惠特曼的回声(虽然艾青不见得直接受过惠特曼的影响),也不难看到,后来者如金斯堡如何将这种排比句式“玩”到“癫狂”的程度。
三.表现方式的欧化
在前引《铁窗里》准排比句式的铺叙中,从单个的句式内部来看,属于语言的构成。它既是语言格调上的,也可看作是表现方式上的特征。从其众多的诗行所构成的准排比句式来看,虽然也表现出了语言格调上的特点,但更多的其实是表现方式的特出之处。这种铺排的表现方式,在我们所熟悉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地掐死之后,/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大堰河,为了生活,/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她就开始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她含着笑,切着冰屑窸索的萝卜,/她含着笑,用手掏着猪吃的麦糟,/她含着笑,扇着炖肉的炉子的火,/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大堰河,为了生活,/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她就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如前所论,这里大量的铺排是欧化的;倒装的句式也是欧化的(“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大堰河,为了生活,/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她就开始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虽然中国语言传统中也有倒装句,但是这里的句式结构方式,显然来自于西方诗歌,与西方语言复合句中的从句形式有关;在一节诗的首尾以重复的方式来增强语势,打动人心,更是欧化的复沓,对于讲求简洁的中国诗歌,绝不是主流。
除了上述方式,我们还会发现,在强烈的铺排中,诗人还有许多入微的细节刻画。人物和细节的刻画,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倒是不鲜见,在诗歌中,却是稀有。这不仅与中国诗歌重抒情轻叙述、尤其与轻描写的特点有关,更与中国诗歌的形式和语言有关——传统中国诗歌的形式和语言容纳不下如此详尽细致的描述,比如“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地掐死之后”这样的句式,且不说“在……之后”的句式。中国古典诗歌就是描述事实本身,用传统诗歌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李白《赠韦秘书子春》:“披云睹青天,扪虱话良图。”苏轼《和王族二首之一》:“闻道骑鲸游汗漫,忆尝扪虱话悲辛。”),其意味也就截然不同了。因为诗歌的情绪和感兴力量,与其表达方式息息相关。

也因此,由于借用了欧化句式,诗歌才有了详尽刻画的可能。正如艾青在《古宅的造访》里,对大他几岁的法国女教师的刻画:“你开始以微温的呼吸/嘘动你大波形的/单薄的胸间衣皱;/停滞在思索里的/幽默的蓝眼/在揣想我幽默的心怀;/你金黄的鬈鬈长发/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个/幻想的多波涛的海……/沉浸在淡紫的宇宙里,/你安详地摆动着你/丰满的圆润的胸脯/——那使我遥遥地想起/拉飞尔的/充满妩媚的日子……”。如此散文化的细节和不厌其详,既是传统中国诗人不屑为之的,也是中国传统语言难能为之的。再如《旷野》中对“农人”的描写:“农人从雾里/挑着篾箩走来,/篾箩里只有几束葱和蒜;/他的毡帽已破烂不堪了,/他的脸像他的衣服一样污秽,/他的冻裂了皮肤的手/插在腰束里,/他的赤着的脚/踏着凝霜的道路,/他无声地/带着扁担所发出的微响,/慢慢地/在蒙着雾的前面消失……”。这般借重散文化的叙述来达成的细致刻画,在传统诗歌中更是不可想象。而这,也正是艾青从欧罗巴借来而贡献给中国诗坛的音色绝异而美妙的“芦笛”之一。同样地,也正是它们伸展了中国白话文的表达,也拓宽了现代新诗的表意可能。
四.难以“杜绝”的欧化
艾青的研究者和传记作者周红兴先生曾考证说,艾青将自己1937年以来的《太阳》《春》《生命》《黎明》《煤的对话》《浪》《笑》《春雨》《马槽》《老人》《常州》《卖艺者》等诗作汇集成一本名为《春》的诗集交给上海某出版社出版,但因战事紧张而告吹。1940年6月,艾青在重庆编成诗集《旷野》,将上面的12首诗作以《马槽集》为名,均收入新诗集《旷野》中。周兴红指出:“这些诗歌,杜绝了早期诗作中存在的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和某些欧化的、诘屈聱牙的句子,而是以凝练、顺畅的语言,舒卷自如地抒发内心的情感”,并以艾青“1937年5月2日”写于“吴淞炮台湾”的《浪》作为例证:
你也爱白浪么——/它会啮啃岩石/更会残忍地折断船橹/撕碎布帆//没有一刻停止/它自满地谈述着/从古以来的/航行者悲惨的故事//或许是无理性的/但它是美丽的//而我却爱那白浪/——当它的泡沫溅到我的身上时/我曾起了被爱者的感激

对于以這首诗为例的艾青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我们能够接受周先生所说的,诗人在此能够“以凝练的、顺畅的语言,舒卷自如地抒发内心的情感”,但是却难以赞同他所指认的,艾青在此“杜绝”了欧化的影响。仅就《浪》这首诗来说,第一节和最后一节的倒装补充句式,就是欧化的——虽然它也可以被认为诗歌惯用的特殊言说方式。如果放眼艾青这一时期的创作,就更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不能说此一时期的《煤的对话》《春》《黎明》《浪》等诗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实际上,即使只考察其作为象征手法的运用,这一影响也是存在的,此后的重要诗作《手推车》《北方》《桥》《树》等更是如此。需要承认的是,艾青此一时期的创作的确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的。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将中国沉重、惨烈和悲怆的现实转化为诗行时,艾青曾学习过的西方经验在此产生了潜在的催化作用。因此,与其说艾青杜绝了欧化的影响,不如说艾青在欧化地学习中国化、本土化的努力中,做得愈来愈出色。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艾青以短句所写的诗里,他的欧化句式的痕迹就显得隐曲、淡薄一些,也少一些,而只要他怀着回荡、繁复的激情,以长句驱遣诗行时,他的欧化句式就显露无疑,空前突出。
在与《浪》写于同一个月的《黎明》(艾青自注日期为:1937年5月23日晨”)中,艾青曾这样写道:“当我在那些苦难的日子,/悠长的黑夜/把我抛弃在世面的卧榻上时,/我只会可怜地凝视着东方,/用手按住温热的胸膛里的急迫的心跳/等待着你——/……//而当我看见了你/披着火焰的外衣,/从天边来到阴暗的窗口时啊——/我像久已饥渴哭泣得疲乏了的婴孩,/看见母亲为他解开裹住乳房的衣襟/泪眼迸出微笑,/……”从其中的长句“用手按住温热的胸膛里的急迫的心跳”“我像久已饥渴哭泣得疲乏了的婴孩,/看见母亲为他解开裹住乳房的衣襟/泪眼迸出微笑”,我们不仅看得到欧化句式的痕迹,甚至能看到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因为现代汉语尚在发展的途中而显露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语言的特征。而在写于1939年的《低洼地》里,诗人运用语词时似乎更圆熟、更中国化了,但是其语言格调却仍然有明显的“现代性”和“拿来”痕迹:“岩石砌上岩石砌上岩石砌成山/山下是杂色的树杂色的树排列成树林/林间是长长的长长的石板铺的路/石板铺的路通过石桥一直伸引到乡间……//……马在嘶鸣着人在劳动着铁与木的声音在响着/稀少的行人在石板铺的路上走着又走着/阳光在照着雾在蒸化着香气在喷发着/我在沉思着感激着终于深情地唱出了土地之歌……”这些不打标点的长句所造成的特殊的音乐效果,其直接的源头也更像是现代西方的。
不过,总体来看,从上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艾青的诗,无论其意象,还是其语言方式,越来越中国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妨看一看艾青40年代初的诗歌中长句:
开车的钟还没有响,那年老的士兵/从破了的制服的胸前的小袋里/掏出了一张五分的纸票买了一个烧饼,/他寂寞地扯啃着,两眼/没有离开那小贩篮子里的鸡蛋;/那些番号都肮脏得看不清名字了;/那些灰的帽子遮着的土黄的脸额/都有一片一样的阴影……(《兵车》,1940)
没有一个人的痛苦会比我更甚的——/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不甘心地,像一个被俘虏的囚徒/在押送到刑场之前沉默着/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抒发我的激情于我的狂暴的呼喊/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它从我的内体直到我的灵魂/我在它的前面显得如此卑檄/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它的脚像马路一样踩过我的胸膛……(《时代》,1941年12月)
这些诗歌以及1942年的《我的职业》等,再与约10年前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铁窗里》对比一下,其语言方式的确越来越中国化了。但是欧化的痕迹并非全然消失和“杜绝”了。从上述诗歌中,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艾青的诗歌在句式的组织和具体的表达上,其欧化的痕迹并没有杜绝,而只是淡化了。结果是,其诗的整体表达显得更畅达、更中国化,也更成熟了。这种成熟,与现代汉语本身的成熟是差不多同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解放区的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发生了重大变化,等到1949年之后,全国的文学语言都随之一变,越来越中国化了。这其中,有语言自身成熟的因素,也有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因素,只是这些都是后话,也是另一个话题了。回头来看艾青,不同于其长句中欧化痕迹的明显,他的短诗中欧化的痕迹更显淡,以至于几乎看不到。其原因大约在于,中国式的表达更适合短句。一如王力先生所言,与西方语言化零为整不同,汉语的特点是化整为零的。
五.陌生化效果与启示
通过以上对艾青前期诗歌创作中的欧化特征的考察,我们不难感受到,带有欧化痕迹的诗歌,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会觉得兴味盎然。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这些诗作的思想意蕴和社会历史价值?还是因为它们所呈现出来的特殊的表达方式?似乎都有。仅从语言的陌生化这个角度来看,都是值得我们再三玩味的。回顾其长诗中表达的曲折汹涌,辗转回荡,无论是氣势,还是表达方式的新奇,抑或长句中丰富的涵纳能力,都造成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令当时的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哪怕时隔近一个世纪,我们也不觉得陈旧,更不用说俗套。
无需讳言,中国现代以来的新诗,其直接来源在西方诗歌。在学习西方,乃至化西为中的过程中,诗歌表达的欧化特征,既是必然现象,也是一件功不可没、得大于失的事。诗人通过学习、借鉴,不自觉、抑或不得已(比如李金发)地以欧化的表达方式,在语言格调和表现方式上显得欧化的特征,说起来是有意无意的“食洋不化”的结果,其结果却是扩展了现代汉诗、乃至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这些,对于身处汉语世界的我们,永远都是有益的滋养。
诚然,当西为中用进展成为化西为中时,西方的也就成为中国的了。如艾青所言,什么是欧化,什么是中化,就需要进一步讨论。不过,即便如此,欧化的表达特征,只要它还没有成为普遍的表达方式,成为我们习焉不察的表达常态,就不算真正的化西为中,也算不上真正的中化。也因此,我们讨论欧化,就还是有意义的。在新诗诞生百年之后的今天,更是如此。更不用说,以上借助艾青对新诗欧化特征的讨论,乃由于欧化的特征还很容易在“汉语的表达方式”这面镜子前映现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仍然走在学西和希望做到化西为中的路上。
参考文献:
[1]周红兴.艾青的跋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2]邢晓飞.延安文坛宗派之争现象考[J].随笔,2016(5).
[3]艾青.艾青论创作[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4]艾青等:漫忆四十年前的诗歌运动[J].诗刊,1982(5).
[5]艾青.艾青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6]牛汉,郭宝臣.艾青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7]艾青.中国当代名诗人选集·艾青[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8]艾青.艾青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