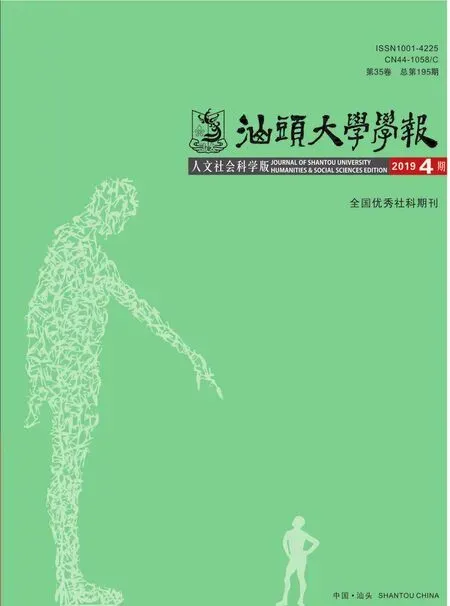从原始仪式看中日艺术中的“神”
2019-08-31奚皓晖
奚皓晖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0)
信仰、巫术、宗教三位一体是世界原始文化的共同特征,原始文化积淀了古人如何定义自己和宇宙关系的智慧。仪式囊括了信仰、巫术、宗教三大特征,是原始文化的核心,是集中体现人类和宇宙交流的方式。最原始巫术形态的仪式从图腾崇拜开始,集中表现为对“神”的信仰。从而,对“神”的信仰和艺术的起源产生出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说仪式是原始文化的精髓,那么掌握仪式中的“神”就掌握了开启艺术起源的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理解了中日文化仪式之“神”的特点,就能对中日艺术的起源和性质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中日皆属东亚汉字文化圈,仪式之“神”的观念在中国距今两千年前的先秦典籍中得到书面化的定型。而712 年大和朝廷以《春秋》编年体编纂的《古事记》,用天照大神以来一脉相承的“神代”当作统一王朝的“创世纪”,是对中华文明吸收创造的结果。由此日本文献中的“神”与中国文化的“神”因文化的交融产生密切的互动。日本文化在阐释神道的同时渗透着其中的汉文化思维。比如,「神ながらの道」(惟神之为道)一度被平田笃胤当成是日语古语,认为是“从神代传来的、神之本意、不加任何人为因素的日本故有之道”[1]。为避免概念上的混淆,有必要对“神”的语义加以分殊,进而从“神”反映的美学观念去理解其各自艺术的本质。
一、立中仪式的“神”
神的右边是“申”。“申”,在古文字中,就是“S”型,可以说是闪电,天的具体体现之一。闪电以其出现又消失体现了中国宇宙的显隐关系,是中国人体会神的一种较好的形式。[3]如果说前面的“示”表示仪式的形式,这里的“申”就象征仪式的目的。就巫术的信仰而言,仪式的心灵需要通过一定的目的才能变成合乎“礼”的文化。那么,什么才是仪式的目的呢?在上古文化中,龙因为变化多端、合乎天意而成为“申”。“S”型象征的就是蟠龙的形状。龙的一个来源是蛇,中国人的始祖女娲是人首蛇身,“补天”,就是祈求天意的改变。女娲炼石补天,就是像上下纵横的龙一样与天互动。正如龙形有九似,天意也是时刻变化的,人申合一既是一种通天的手段,也是企图在交往中去征服天。四面脸的黄帝是龙,三代的夏启自己乘龙,所以帝王都是真龙天子。龙在仪式中象征人与宇宙神秘力量(天意)的合一。所以,人王要乘着龙,金殿里绘着龙,龙椅上雕着龙,龙袍上绣着龙。总之,龙就是奉天承运,有了龙就有了天命,有了龙“王”就可以称“帝”。中国有个成语叫“天意难测”,有句诗叫“天意从来高难问”,就是用来形容龙的威力。闪电是来无影去无踪又破坏力极大的天候,与龙有着某种内在的共通性。划过天空的闪电象征着不可预知的天。看见的形式是“有”,看不见的本质是“无”。“有”并不是本质性的东西。那看不见的“无”才是神意的体现。闪电和龙的关键之处在于,实在的形式对应的是后面虚灵的本质。正如“有”后面的是“无”,实体的形式和虚灵的天道是一种有无相生的关系。故《中庸》曰:“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毛诗》亦称:“言其上下察也”。[4]鲤鱼跳龙门,鱼龙本是一体,鲲鹏互变,是气候变化的预兆,视线的上下变化对应事物由显至隐的转化,通过“观其会通”彰显出“天道”这一有无相生的显隐结构。所以,到了先秦时期,孔子论《易经》曰:立天之道曰阴曰阳,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不测谓之神。韩康伯注“阴阳不测之谓神”曰: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5]“申”是“阴阳不测”“变化之极”,也就是指认识天地万物虚实相生的变化规律。《说卦传》又把“申”和“妙”联系起来:“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明“神”既是万物变化的规律也是玄妙的道。《老子》讲道:“玄之有玄,众妙之门。”正因为天道是这样一个虚实相生的众妙之门,在伏羲的仰观俯察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智慧总结,才能使中国之道“天长地久”。“申”有如天安门前的华表,既是昔日的中杆,又有蟠龙居焉。“申”与“示”相呼应,既有“立中”显出的居天下之中容纳万有的气魄,又有“蟠龙”显出的阴阳不测、无体无方的变化万方,正可谓是一正一变,一虚一实。在中华文明由“示”而“申”,向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乃至整个东亚弥漫的同时,中国人也呈现出一种胸怀天下、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大一统精神。这大一统精神在统一周围少数民族的过程中既体现为移风易俗的直接统一,又体现为四方典属的间接统一,还体现为册封朝贡的域外之统。如果说华夏在笼罩四夷的过程中突出的是“神”背后“化成天下”的文化观,那么“神”背后的这一人文思想,则更深地浓缩了一种通变的艺术观。所谓通变,就是通过“化”来表现艺术的法则。龙作为一种高级的神兽就是对一切动物的同化。龙与凤、龙与虎、龙与蛇,龙与猪,皆可以相互转化。女娲在《说文解字》里被解释成“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化”是身体的“消化”,“化”是佛祖的“点化”,“化”是庄子的“物化”。“化”是看不见的“变”,“化”的过程不是西方的质量互变定律从实体到实体的“变”,而是虚实相生的“变”。“化”不是实体性的质变,而是虚实相生的通变。《管子 内业》云:“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化不易气,变不易智。”“化”就是“通变”,通变就是“有无相生”这一天道的根本规律。其实,物的规律不在物本身,而是以它与什么相关而决定。“通变”就是从四通八达的天道中去通达宇宙万物的规律。如果说在先秦理性当中“气”的观念是“变动不居,周游六虚”活的因素,那么“通变”就是这活的因素的根本统一。正如“通变”是在“气化万物”的天道中进行的,“化”出的不是具体事物的规律,而是“通天下一气”宇宙时空的规律。“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看一个人“神”不“神”,就看他能不能站在“通变”的立场从静态的“物”中去悟动态的“事”,从外在的“实”去悟内在的“虚”,从眉睫之前的“形”去悟视通万里的“象”。“通变”就是要在这虚实相生的天道中通达出活的规律。《孟子·尽心下》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大而化之之谓圣”,赵岐注“神”为:“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6]“神”在“天道”之中不断从有限向无限去“大而化之”,当“化”由显至隐以至不可知就成为艺术的终极奥义。
二、“通变”与中国艺术的诗、文、画
《孟子》曰:“夫君子所存者神,所过者化。”传统社会里面君子是有文化的人,不仅要会做官,也要会写诗。诗是一个人知人论世最好的写照,因此“诗”是最讲“通变”的。一方面,“诗者,天地之心”,另一方面,“不学诗,无以言”。学“诗”学得好,既要“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要把这些道理和现实的为人处世一一对应。孔子曰:“诵诗三百,不能专对,亦奚以为?”诗是虚和实,有和无,可表达和不可表达的统一。中国文化讲究“以人合天,而不强天而从人”的天人合一,一方面是人心与天道的贯通,但更重要的是人心与天道的通而能对,对而能通。东郭子问道于庄周:“所谓道恶乎在?”庄周说:“无所不在”。“道”是无所不在,四通八达的。有个成语叫“分道扬镳”,还有句俗话叫“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一方面,黑有黑道,白有白道,“道”无巨细,“道”无本末。另一方面,“道”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通过衣食住行,一点一滴的实践中去经验、去直觉,去体悟。程颐说:“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道可道,非常道,可道的一面是道通为一,不可道的一面是通道必简,“道”是普遍和特殊的统一,而“在”(to be)是西方人几何学定义的方式,所以东郭子问得不对。庄周回答“无所不在”等于是说“在又不在”,是以“不对”对“不对”。正如“无所不在”的“道”,“诗”不是像西方的抒情诗、叙事诗、史诗那样固守一种成心(立场)去表达,而是要用方方面面都相通的“道”去开启智性之“对”。这智性的表达,就是诗的“神”。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讲“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7]“诗”既是书本知识,又超越书本知识。诗品如人品,贵悟不贵解。《老子》讲“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条条大路通罗马,道既有可理解的一面,道又有不可理解的一面。写诗就是论道,关键看会不会通变。通变是要有灵性的,所以科举考试要考试帖诗,就是看有没有灵性。唐代科举考试前要去找关系,叫“行卷”。白居易找关系找到顾况,顾况用其名开玩笑,说京城之居很不易,京城的米很贵哟。白居易就把自己写的《赋得古草原送别》一诗献上:“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一看,马上说:“诗写得这么好,你在京城居住确是很容易的啦。”[8]“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用清浅的语言形象地道出了盛衰皆自然的道理,在草木的荣枯中蕴含着对天道的信念。正如道是可以言说的,但又不是一般的言说。言他人所不能言,道他人所不能道,这就是诗的“神”。
中国文化诗画一体,诗之通变亦如画之通变。顾恺之论画,“悟对之通神”是五字真言。“通”既是“对”,“通”也是“变中之对”,是千变万化的“达画之变”。《世说新语 巧艺》云:“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9]谢鲲是“江左八达”之一,是赤身裸体、披头散发在屋子里饮酒作乐的放达之辈。顾恺之将他画在岩石里,恰说明他是“对”的人,换了别人,就不对了。隐士配丘壑,宝刀赠英雄方可“传神”。只有在特殊情境中的“悟对”,才算得上是以形写神。《论画》有云:“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10]中国文化中的人体并非西方文化实体性的人体,是一个形神一体、虚实相生的人体。《淮南子 原道训》曰:“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也。”[11]“形”是生命的形体,气是充实生命的要素,神是生命的主宰,经脉血气通于五脏,是“心神”统一的结果。所以“气”不“精”则无“神”,无“神”则“精”不能“一”,“精”不能“一”则“形”不固,“形”不固则“神”不存。如果说中医的五脏合参,望闻问切是对人体之“通”,那么对症下药、妙手回春就是应人体之“变”。绘画中表现人体,同样要和中医一样望闻问切,从有入无。与中国的形神一体观相比,西方的神是与身体绝缘的神,身体是客观可分的身体。西方对身体进行分节促进了分析性的解剖学,从而人体的艺术形象应符合解剖学的科学规律。但是按中国风水学的说法,身体并非仅是科学的外观形象,而是可以从中发现某种命运的表征。比如说你印堂发黑,那就是命不久矣的征兆。所以中国画想画好一个人,要运用虚实相生的想象力,让人体与整个生存环境相“悟对”。顾恺之说:“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手挥五弦”弹得再潇洒,也不过是“一像之明昧”的有形之人,只有用不受时空限制的眼神来打破绘画空间的限制,使视线向远方的归鸿聚集时,画面中的人像才能超越有限的时空限定,与自由且不受时空羁绊的归鸿相“悟对”,从而创造出虚实相生的无形之趣。绘画的通变,就是从人体外在的形去“悟对”内在的神。
《周易·系辞上》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12]作文之通变,更甚诗画之通变。南北朝时期,骈文既是朝廷奉召应对的官样文章,又是才子佳人怀抱宇宙的方式。骈文一方面讲用事,谁用的事多谁拥有的天地就广;另一方面讲对偶,“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古人看一个人的才情,不是看他考试考多少分,而是考他“对对子”。所谓言对为易,事对为难,正对为劣,反对为优。“对对子”正如四通八达的道,是特殊和普遍的统一。中国文化的智慧,就隐藏在这非常简单又非常巧妙的窍门里头。骈文以四六句为主,容易属对,用事越多,对偶也越多。如果说用事是学,对偶是才,那么骈文就是才学相济,所以“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13]“文章千古事,得失存心知。”作文既有学自外成“通”的一面,又有才自内发“变”的一面。因此骈文把中国士人的心智和宇宙的无限一道贯通起来了。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把骈文的作文之理归纳成“情”和“采”两方面。情采是作文之中才性、风骨、章句、丽辞、事类、练字的体现。既体现规律性的文法,又体现不受规律束缚的个人,既有外在的显的一面,又有内在的隐的一面。对作文而言,规律性的东西是外在的纹饰,是形式的丽显,而不规律的东西是内在的体悟,是文章之美的本质,这两个东西是合二为一的。《文心雕龙·隐秀》曰:“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隐是文含多义之处,秀是文有卓绝之处,二者的生成都与个人的机缘有关,“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课”。作文之妙裁,皆通向一种“文已尽而意有余”的显隐之道。所以刘勰把情和采在具体时代具体之人的统一称作附会,把情和采在不同时代不同个人的演变称作通变。通变,就是“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作文的通变,是普遍之通与个体之变在时空中的统一。
三、咒术仪式中的「かみ」
日本多神信仰的形成和原始村落长期处于隔绝状态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古事记》号称高天原上有八百万神居住,表明从京畿到地方,神是彼此分散开来的。山有山神,村落也有村落的神。因此,神并不是指天皇这类人格化的对象,而是指自然之物的「霊」(たま)。从「神」(かみ)这个词本身看,这一词语的语根是mi,ka 是加上去的接头语,mi 是指某种拥有灵力的精灵和灵物。[1]16对蒙昧时期的土著民来说,mi 作为自然的神秘力量,兼具破坏性和保护性。一方面是人感受到威胁的灵,另一方面是不得不仰仗的神。mi 既可以是使人亲近的幸福的神灵(在村落周围的山头保佑自己),mi 也可以是使人畏惧的恐怖的恶灵(在咒术中加以清除的对象)。正是因为mi 的双重意义使「神」成为带来幸福的神灵和拥有危险咒力的恶灵。既然“mi”是自然万“物”(もの)背后的主宰,人们就要借“ka”这一咒语预卜“物”的凶吉来显“灵”。
“物”在日语中分「もの」和「こと」,前者表示实在的事物,实在的“物”是受不定的“mi”控制的,所以「もの」是令人不安的存在。以「もの」为词根构成的「もののけ」指妖怪,「ものに凭かれた」指鬼魂附体,「もの」后接形容词往往表示不安的情绪,如「物思い」(担心)、「もの恐ろしい」(可怕)、「物忧い」(忧虑)、「物怖じ」(恐怖)都是以「もの」(物)作为词根的。因此,正如文学史家西乡信纲所指;“「もの」在上代往往是无秩序的源头——恶灵的象征。”[14]《日本书纪》讲土人祭祀埋葬在纪伊有马村的“伊邪那美命”就是用“ka”消除mi(死灵)恐怖的祭祀。到了《古事记》当中,每每以吉凶显灵的「もの」就渐渐转化成凶神和吉神。
“神”这个词的接头语是ka。如前所述,“ka”应当是指针对物背后的灵的咒语。既然「もの」由令人不安的灵主宰,那么“ka”就是用咒语去操控这不安的灵。「もの」这个词除去表示物,同样也有“语言”的意思,“语言”和“物”是彼此相通的义项。语言是观念的符号系统,人类学家弗雷泽说:“未开化民族(指原始部落)对于语言和事物不能明确区分,常以为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人或事物之间不仅是人的思想概念上的联系,而且是实在的物质的联系。”[15]在土人的咒术仪式中间,神秘的ka(咒术)语言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灵媒。土人认为语言是显灵的事物,事物是咒语的灵验,语言(こと)的记号内容和物(もの)的客观呈现是一致的。如果说物背后的灵是对无法掌握的原始自然事物所抱的不安,那么为了消除事物的不安就必须用ka(咒术)去影响它背后的灵,所以ka 本身就是有灵魂的语言。《万叶集》「大和の国は皇神の厳しき国言霊の幸はふ国」[16]的意思是说,大和之国是受言灵恩泽的国度,是皇祖神(天照大神)的威严所系。「言霊」咒术就是用咒语去影响物的意志,仪式的操控过程就是巫祝通过“言灵”与物之灵融通的过程。一年一度熊野的送熊仪式中,人们在享用熊肉前用含有灵力的语言大声表达歉意,这样熊会觉得人类很好,明年就会再来,可见「言霊」遵循的是事物与语言彼此感应的心灵逻辑。高桥亨教授认为,在古代日本,人们普遍认为,作为记号表现的「言(こと)」和作为记号内容的「事(こと)」是一致的。”[17]所以日本人把言语称作「物言い」(way to speaking),强调言说的事物(こと)和言说的方式(もの)对“我”而言是彼此关联的整体。《四月一日灵异事件簿》里面说:“名字是很重要的!名字是有力量的!不管是生物还是非生物,只要冠上那个名字的话,就能和叫做那个名字的东西拥有相同的力量!”[18]9姓名崇拜其实是从“言灵”当中分化出来的信仰,它证明通过言说和事物的合体,语言背后的心灵与体现自然意志的神灵就能在咒术仪式中合一。与土人的咒术仪式相近的是大和朝廷的神前唱祓仪式,称为愿祷祝词。上代人根据“言灵”的心灵逻辑,相信善言会有善报,怨言会有怨报,「言祝ぎ」就是用美、善、吉言使神灵降福的咒术。如果用恶言恶语招惹了物背后的神灵,就称之为「言扬」(放声宣扬)。「言扬」会触怒神灵而大祸临头。《古事记》里讲倭建命东征,曾狂妄地扬言要杀死山神化身的白猪,结果天上突然下降奇妙的大冰雨,不得已英雄只好返回大和。这说明善意或恶意的咒语与神意的善恶是相互对应的,言必有报突出了“言灵”这一咒术信仰的威力。为避免触怒神灵,宫廷的「物忌み」(禁忌)就是通过祓(はらえ)、禊(みそぎ)等净化仪式来表明内心不敢有任何欺骗神灵的心意。
如上所述,如果说ka-mi 是一种借言语操控物灵的仪式,那么在仪式中不加虚假地用语言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就叫「诚」(まこと)。「诚」与「伪り」相对,「诚」就是真,是内外如一的真心。《古事记》讲“须佐之男命”去高天原时,天照大神问他:“怎样才能知道你心地纯洁呢?”女神想知道自己的兄弟是诚心,还是别有用心,须佐之男命回答说:“因为我的心地洁白,所以我生的孩子是柔和的女子。”[19]男神用“生女孩”强调了自己内外如一的真心。按照“言灵”言必有报的逻辑,没有篡位野心的言说是因,真的生下女孩是果。言说的方式和事物的体现是一致的整体。这说明在上代文学当中,咒术的“言灵”信仰已经渗入神话编纂者的意识之中。因而“言灵”对日本人信仰天皇和对艺术观念的萌芽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如果说「かみ」(神)的本意是用言灵咒术影响天地万物的灵,那么「もの」(事物)所包含的“物”与“言”的心灵锁链就构成言灵咒术的本质。正如《少年阴阳师》里的召唤祝词:“谨奉归命与诸佛,除灾的心宿!东方降三世夜叉明王!西方大威德夜叉明王!南方军荼利夜叉明王!北方金刚夜叉明王!压服吧!净化吧!压破吧!粉碎诅咒的束缚!出来吧!高龙神!”[18]5在「言霊」信仰的支配下,巫祝通过意念的观想和心灵的移入,就可以实现仪式之人与仪式之神的统一。咒术仪式在中世发展成真言密宗。它将土人的咒术和复杂的手印相结合。手印不仅是手的姿态,也是心的显现,心手合一加上咒语就构成仪式的三位一体。“人体如收音机,手印如天线,结一种手印,相当于调到一个电台,身与外物的对接于此开始。手结印契的同时,是口诵真言。密宗的真言,犹如一种专门的声波,与外物发生感应。意,就是对外物作意念上的观想和心灵上的移入。身到(手结印)、口到(诵真言)、意到(观想移入),是一个整体,相互关联又相互带动。”[20]可见,在求福避祸的汉文化心态驱动下,根据“意念”观想和“心灵”移入的咒术法门,通过连接“言”与“物”的心灵锁链就可以达成仪式之“神”。
四、“言灵”与日本艺术的和歌、俳谐、物语
咒术仪式的“言灵”信仰之所以在土人咒术、朝廷祝词、密宗法门等方面影响日本文化,是因为其植根于上代文学的深层意识。从朝廷的「宣命」到首部敕撰和歌集《万叶集》的成立,「明き、清き、直き、诚」始终构成“和歌”之美的本质。“诚”就是坚信心灵的语言可以获得神灵的意志,从而通向事物的本质和艺术的真谛。与中国的“诗”相比,和歌之“歌”是与之对立的艺术。“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志”的本义是停止在心上,进而产生记忆、记录、怀抱的意思。[21]“咏”是拉长声音而咏。“志”有待完善为书写工具的语言,“咏”是共同体生活口耳相传的口语。诗言其志,歌咏其声,志和咏构成汉诗与和歌形态上的差异。“歌”的题材、用语、形象比“诗”更朴素。每一首歌就是凝聚每一缕心情,不经思致的过滤就从心灵中迸射出来。“诗”并非不能“咏”,“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诗”和“和歌”同样追求“寓目入咏”的表现方式。但是中国文化是时间空间化的历史时空,不主张胶柱鼓瑟地将视线凝定在局所的物象上。而是追求“揽碎古今巨细,入其兴会”的虚实相生之美,使意象的大跨度跳跃膨胀至意境的广度。所以“杜诗句意,大抵皆远,一句在天,一句在地”“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诗的情绪焦点并非停留在此时此刻的青冢,而是要跳出此时此刻去追求突古往今来的宇宙。作者在近景(青冢)和远景(朔漠)之间构筑广阔的心理联系,目的是要让人们去反思王昭君的命运与王朝兴衰荣辱的历史,使之通向言不尽意的象外之致。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汉语是孤立语,日语是黏着语。孤立语倾向于语言单位的自我完结性,有助体现思维的有序和广阔。而黏着语突出语言单位的连续性,适合展心灵意识的细微构造。可见和歌的表现力在抒情而非言志。尽管和歌的表现力在抒情,但它又不同于欧洲的抒情诗。和歌是心灵高度纯化的抒情诗,往往只抒发苦、乐、哀、愁的幽情单绪,从不追求情感的深刻和凝练。在表现方法上是即兴式的,主题也只是春、夏、秋、冬、恋、羁旅、等仪式性的程序。说明和歌的兴趣并不在于抒情自我的表现,它的目的是力图用语言外化出人们对现实的真实感情。尽管真正的抒情诗永远表达人心的真实,但是和歌的抒情缺乏使抒情的主体淹没到对象的同时开放自己的企图,它只通过自我面对事物作心灵移入的观想来达成抒情。因此和歌是再现而非表现式的抒情,一方面心灵移入对象的实体,在对象的实体中投射出心灵;另一方面心灵又为对象所淹没,从而无法透视自己的心灵。黑格尔指出,东方抒情诗往往采取一种客观的语调,诗人不是把外在事物和情况表现为他所想的那个样子,而是表现为它们本身原来的样子。[22]这并不符合汉诗,却符合和歌的抒情方式。和歌的抒情主体一方面绝对诚实于自己的心灵,另一方面语言的表达方式又要追求与「もの」(物)结合的心灵逻辑,心灵胶着事物的同时便失去了使自我对象化的能力。所以,和歌与欧洲抒情诗最大的一点不同是,和歌绽放的是纯真心情之花,而不注重在吟咏过程中收敛、浓缩、深化特定的情感,它抒发的是人类最普遍最内在的现实心情,而非艺术化的诗的心情。因此和歌的抒情特点是再现而非表现。
这样看来,和歌既不能像汉诗的咏怀那样,致力于造型力的宏伟广阔,也无法像欧洲抒情诗那样,在统一内心世界的同时达到表现的深刻。既然如此,和歌的抒情特质如何体现呢?我们需要把它放到共同体仪式的方面进行考虑。上代在祈祷丰收的农业祭典结束后,人们会在山上、海边举行欢聚飨宴的「歌垣」。男女双方如果心心相印,就用和歌与心仪的对象赠答,在成婚过程中和歌一直是男女双方亲密交往的信物,是高度仪式化生活化的艺术。与酬酢奉召相对严谨的汉诗不同,和歌遵循的是语言和事物相融通的心灵逻辑。歌学大师藤原定家就认为,和歌十体之中“有心体”胜过一切样式,只有心的“朦气”消失,心自正且美,才能言之有物。事物的形象(姿)一旦与心分离,就会在语言上出现重“实”轻“花”或者重“花”轻“实”的结果。因此,“不应只着眼于句之姿及言辞的优美,清心寡欲,人间色欲要淡,在万事万物中深悟人世无常。不忘世间人情,对他人之恩,要以命相报,歌句方可能从内心深处涌出。而心地虚伪之辈,其和歌之词虽漂亮,在真诚者仍会听出虚伪,因为其和歌之心不够清纯之故。”[23]所以咏歌之要义,在定心神止妄念。“心”与“物”的融通在和歌中永远是相互连锁的整体。今道友信指出,「もの」(物)和“事”不同,是在与我的关系上被把握的总体状况。“物”不是具体的实在之物,“物”是与自己秘密关系的结合之“物”。[24]和歌就是用简洁明快的方式(31 音)表白自己最贴近心灵的语言,是心灵的明亮透明对天地万物的投射。因此《古今和歌集·真名序》开宗明义:“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花于词林者也。”[25]证明和歌是再现心灵的抒情艺术。其抒情方式之一是通过具体的直观截取印象的断片,凝聚美的瞬间形象。「秋の田の穂のへに雾らふ朝霞いずへの方にわが恋やまむ」[26]作者用疑问的语气揭示恋爱的不安心情,并非表现式的咏怀,而是通过秋天晨雾濡湿的稻穗沉甸甸地低垂所暗示出来的。恋爱的迷茫本来是难以言喻的心情,但是通过物象实态的正确把握,透亮地映射出内心迷茫的象征。稻穗的露珠与秋天的早晨组成一幅雾蒙蒙的画面,这是作者内心不安的真实剪影。「ひさあたの光のどけき春の日に静心なく花の散るらむ」[27]33舒缓的节奏透出春日的悠闲,此时此刻连心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吧。可是眼前飘落的樱花花瓣唤醒了作者的遐思,推量的语气「らむ」表现出春去夏来的怅惘心情。这首和歌的妙处在于没有使用任何技巧,以淡雅之景写之悠闲之心,似有情似无情,所以让人感觉既含蓄又优雅。和歌的再现法之二是不以客观的物象,而以主体的情绪为主导,通过音调的组织串联起心灵的节奏。「花の色はうつりにけりないたずらにわが身よにふるながめせしまに」[27]9心的移情化作雨中洒落的樱花,樱花飘洒的姿态照应忧虑的心情。“色”是「挂词」,既是花瓣的残败之色,又是容色的残败之色。「うつり」(变)既是花色之变,又是容色之变。「ふる」是雨过又是时过,「ながめ」是远眺又是雨长,通过词义不同的搭配造成不同的意味。物之性与人之情的密切互动,使言外之意的沉淀显出更复杂的韵味。加上ナマラ这一咏叹效果的押韵声调,传递出岁月与时光共老的无尽叹息。
藤原公任在《新撰髓脑》里讲:“凡歌心深姿清,应以心有奇处者为优。”“心”是审美的主体意识,是与物态的“姿清”相对的明澈的心灵,它借助创造性的观想,使心移入到事物之中并借以表白作者自己。俳谐(17 音)是和歌(31 音)的缩小版,除去语言的俗化以外,俳谐的风格是以轻盈凝练的句法、用新奇的物象来反映潇洒自在的心情。但是就吟咏方式而言,俳谐使心灵的感受通过物象再现的方法与和歌并无本质上的不同。首先,“新鲜是俳谐之花”,俳谐的创作好比是切西瓜,看准位置一刀切两半,要在瞬息之间捕捉感动的形象。“闲寂古池旁,青蛙跳进水中央,扑通一声响。”这“一瞬”是“花落”,是“蛙跳”的一瞬,这一瞬也是心象与物象之姿融合的一瞬。在“心”和“物”的融通中,环境的“寂”由于青蛙的跳而打破了,回音又使人意识到环境的“寂”,现实的断片通过物象和心灵的融通得以发现。其次,只有心灵体会物之“本情”,才能实现心与物的融通。“本情”是指物性本身的趣味。为了使心灵移入物体的实相,咏松的时候要向松学习,咏梅的时候要向梅学习,只有体会符合事物之为事物的“本情”,心与物契方成浑然一体。第三,俳谐的完成是以心灵外化出美的语言为定型的,俳谐语言彻底贯彻了“言灵”信仰。心灵的波纹反映出事物的真实样态,事物的真实样态还原为言语罗列的结晶。俳谐的吸引人之处就在其擅长通过新奇的语言表现出事物的新鲜感。比如“镰仓出产的,活蹦乱跳的鲷鱼。”它的妙处不是凭宿构写成的“手帐之句”,而是使集市上新鲜的野趣成为“即目入咏”的素材。正如大西克礼所言:“多听,多看,从中捕捉令作者感动的情景,这就是俳谐之诚。”[28]在这里,“言”与“物”的心灵锁链构成俳谐美的本质。因此,俳谐本身不表达任何思想,它只用再现去反映直觉,不使用修辞,它是最初直观的直接反映,是直观本身的清澈透明。
日本叙事文学的代表是「物语り」,更突出地反映出其源自原始的咒术言灵。正如前面所说,「もの」(物)不是静态且呈实体的thing,而是在我与事物关系之中把握的信念整体。“每当有所见所闻,心即有所动。看到,听到那些稀罕的事物、奇怪的事物、有趣的事物、可怕的事物、悲痛的事物、可哀的事物,不止是心有所动,还想与别人交流共享。对所见所闻,感慨之、悲叹之,就是心有所动。”[29]31-32对事物的“心有所动”,就是本居宣长说的“知事之心”和“知物之心”,有了“知物之心”,才会有诉诸心灵的语言。「语り」就是要使语言的叙述贴近人们对事物的真实感情。所以“物语”要求作者对事物的喜怒哀乐都诚实不加欺骗地用语言表达出来。人生在世,失恋的悲哀是任何人都眷恋的情感。爱联系着恋人最切实的灵魂,“爱”又是易遭受不幸的意识,物语的主题就是通过“爱”的语言去诉说“爱”的不幸,其表现为「物の哀れ」(物哀)。所谓“物哀”,就是抒发人心最隐秘最深切的悲哀以达到抚慰人心的作用。《源氏物语·萤卷》讲玉鬘读《住吉物语》,沉浸在住吉姬内心的忧愁里,连头发散乱也不顾,只是埋头写写画画,这便是陷入“物哀”时痴狂的表现。本来“恋爱”就是直觉到对象感觉的意识,是没有主动也没有被动的感情,是心灵和对象完全融通的互体意识。通过诉说“恋爱”与“失恋”的“物语”,读者的心灵就融入到物语主人公所处的恋爱情境,从而通过这种辗转反侧的爱的诉说不断去重温与对象融通的心情。本居宣长说:“道原本不是靠做学问来获得的,而人与生俱来的“真心”才是“道”,所谓“真心”,就是无论善恶都是人与生俱来之心。”[29]302其实宣长用不着用“道”来论证“真心”,因为“真心”本来就不是“道”,而是物语的“言灵”信仰。这不知之知的真心就是指不学而能的物のあわれ(知物哀)。所以“物哀”的心灵不必过问任何现实的理性,只需要不断诉诸心灵本身,不断纯化心灵本身,表面上犹如孟子的“反身而诚”以回归本性。但中国人回到本性的目的是为了知天合天,虚一而静的“心斋”是“返虚入浑”,使心灵重新向宇宙开放。“诚”关乎的是天人关系应该合,怎样合的问题。但是从魂灵净化到唱祓仪式再到密宗手印,日本文化的“诚”突出的是人与对象合一的心灵逻辑,是宗教式的意念观想和心灵移入。如果说中国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以天合天的主动合一,那么日本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心与物冥的静默感应。如果说中国文化的理想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大一统,那么日本文化的理想就是一切由现人神支配的统一自治。如果说中国艺术突出的是广度和动态的心灵,那么日本艺术则趋向细腻且敏锐的心灵。二者对“诚”的理解差异,在艺术风格上表现为“雄浑”的积极之美与“幽玄”的消极之美。幽玄之美不同于“尺寸之波尽沧溟之势”的庙堂园林,也不同于“墨气所射,四表无穷”“咫尺有万里之势”的全景山水,而是在31 音的和歌中寄托瞬间感兴,彰显出人生的片断之美。“幽玄”之美向往有如“和静清寂”的茶道之优雅,有如显露心灵一角的俳句之含蓄,有如人生无常的和歌之感动。因此“幽玄”表现的是心灵敏锐的境界,是以被动的态度让心去沉潜,是至虚至淡的心象之充盈。无论是和歌还是俳谐,无论是31 音还是17 音,日本艺术都贯穿了言灵信仰的心灵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