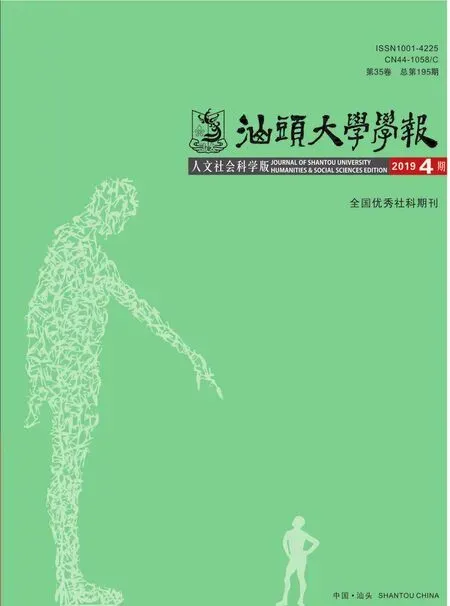学术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统一
——读王富仁先生的《语文教学与文学》
2019-02-11廖四平
廖四平,郑 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24)
王富仁先生的《语文教学与文学》一书是由王先生和郑国民先生共同主持的《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丛书》中的第一部,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11 工程”二期成果。与王先生此前的其他学术著作以及同类其他著作相比,《语文教学与文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点。
一、别具一格的结构形态
在《语文教学与文学》中,王先生围绕着“语文教学与文学”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颖别致”的观点——教育是“人”的培养而非仅仅是“人才”的培养,“人”的培养的“指标”是人的“‘幸福’感”而非人的“‘地位’感”,情感的培养是“人”的培养的一个主要方面,培养“人”的情感的任务应该主要由语文课来承担,语文课本应该以文学作品为主,语文教学首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要使学生对读书产生兴趣就得不拘泥于他们对“书”“求甚解”,“中学语文教学的最高目标是建立起学生感受、理解、运用、创造民族语言的乐趣和能力”[1]52在语文教学中必须同时坚持“文本作者的创作主体性、授课教师的教学主体性、学生的学习主体性”[1]34……这些观点大致涵盖了教育的目的、内容、途径、手段、发展规律、应该规避的问题等方面的内容,包含了教育的一些基本“要素”,涉及到教育的一些主要“环节”,且大多标新立异;同时,彼此关联,且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从而形成一个完整而又严密的教育思想体系。
一般来说,建构了完整而又严密的思想体系的著作总是以完整而又严密的结构形态出现的,如康德的“三大批判”、黑格尔的《美学》和《小逻辑》、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然而,建构了完整而又严密的思想体系的《语文教学与文学》一书却并非如此——全书除《总序》之外,一共包括三个部分:“语文教学改革”“读书与教书”“名篇赏析”,各部分均由一组彼此独立的文章组成。从外在形态来看,三部分彼此没有必然的关联,各部分的文章彼此也没有必然的关联。这种结构形态不仅与《小逻辑》《资本论》等著作的结构形态迥然不同,就是与王先生自己此前的学术著作如《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古老的回声——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等著作的结构形态相比,也可谓别具一格。这种结构形态一方面使王先生得以“放开手脚”、纵横捭阖地论述自己基于教育现状的观点,并在这种“不经意”的论述中建立起一个独标一格的教育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又使王先生得以摆脱为追求建构体系而不得不苦心孤诣或削足适履式的“布局谋篇”,从而获得了符合自己言说心性的方法论的自由。
二、宏阔深邃的学术造诣
如果仅仅从表面上看,《语文教学与文学》似乎只是一本关于语文教学或“教改”的书,所谈的无非是一些有关语文教学的问题,至多也就稍及一下“文学”而已,但如果静心屏息地阅读完全书,就会发现其实“大谬不然”。
首先,该书有宏阔的学术视野。
该书虽然篇幅较小——不足20 万字,格局也不大——主体就只有似断似连的三个部分,但所表现出的视野却相当宏阔——该书不但如前所述提出并论述一系列教育观点,建构一个完整而又严密的教育思想体系,而且还紧扣“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这一“丛书”题目阐释一系列文艺理论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解析一系列经典语文课文。该书除了在各篇中均散杂着一些相关的文艺理论外,还在《小说的阅读与欣赏》《散文的阅读与欣赏》《诗歌的阅读与欣赏》《戏剧作品的阅读与欣赏》等文中集中系统地阐释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作品的特点以及如何“阅读与欣赏”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作品等问题,同时,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又旁征博引、广泛地涉及古今中外经典名篇,并在《从音、形、义话杜甫诗〈白帝〉》《自然·社会·教育·人——鲁迅回忆散文〈从百草园到三维书屋〉赏析》《怎样感受人?怎样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说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等一系列文中详细地解读古今中外的一些经典名篇,在解读的过程中又运用文学批评和文艺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如在《从音、形、义话杜甫诗〈白帝〉》《独特的组接方式独特的美学效果——李贺诗〈李凭箜篌引〉赏析》等文中运用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理论,在《〈秋思〉发微》《触摸语言——徐志摩〈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等文中运用视觉心理学的相关理论。
其次,该书有深邃的学术识见。
该书基本上是每一篇都相应地重点论述一个方面的问题。在具体地展开论述时,除了旁征博引外,还穷“形”尽“义”、发微释疑,说前人之所未说,见前人之所未见,表现出深邃的学术见识,如以上所列举的围绕着“语文教学与文学”的问题所提出一系列“新颖别致”的观点,此外,还有虽不成系列但颇为“闪光”的观点,如《谈“好读书,不求甚解”》一文的“理解一个好的文学作品,依靠的是读者本人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的不断丰富化,在现有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的基础上硬要理解作品更深刻的意义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往往伴随着对作品的曲解”[1]98,因此,读者没有必要总要对书“求甚解”;《呼唤儿童文学》一文的“在知识技能的世界里,任何时代的成年人都优越于儿童,正因为这样,少年儿童需要成年人的教育,需要成年人灌输给他们在社会上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但在精神境界上,任何时代的少年儿童都优越于成年人。我们不是不需要儿童的世界,而是极其需要儿童的世界;我们不是不需要儿童的梦想,而是极其需要儿童的梦想。儿童的梦想在整个人类的发展中都是有着巨大的历史作用的。哪一个时代的人淡漠了儿童的梦想,哪个时代的人就会堕落,会丧失自己的精神的家园;哪个时代的人更多地保留着儿童的梦想,哪个时代的人就是更为崇高的,真诚的,纯洁的,即使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也能充满生命的活力和生活的情趣。”[1]137“中国现当代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教育味太浓”,“把儿童文学当成了教育的辅助手段,把儿童文学当成了班主任教育学生的形象化教材”,从而,“严重丧失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吸引力”[1]139;《谈科幻小说》一文中的“正像一个民族的童年没有充分发展的神话会影响一个民族的整个历史发展一样,没有丰富幻想的童年将使一个人的一生缺少蓬勃的追求意识和健全的理性精神。”[1]148《〈秋思〉发微》一文中的游子之所以“不归故里,是因为在故乡时发生了使他肝肠寸断的伤心的事情”[1]172;《触摸语言——徐志摩〈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一文中的《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这首诗的本身就是这个日本女郎的形象。它小而美,构成的也正是这个日本女郎娇小而美丽的身体的形象”[1]211等观点即如此,而且,像这类的见解深邃独到的观点在该书中还有很多,甚至可以说触目即是。
第三,该书有纯正的学术品位。
该书纯正的学术品位具体表现为学理性强。其一,它有很强的思辨色彩——无论是王富仁教育观点的提出还是其教育思想的最终形成都不是他凭感觉、想当然或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他基于中国教育的现实充分运用逻辑推导而进行理论思考的结果,如其教育是“人”的培养而非仅仅是“人才”的培养、“人”的培养的“指标”应该是人的“‘幸福’感”而非人的“‘地位’感”等观点实际上是他基于中国现代教育尤其是1949年以来的应试教育这一现实、通过对教育的本质和目的及“人”本身的逻辑推导性的思考的结果;与之相关的其他观点及其整个思想体系也大抵是如此产生的,正因为如此,它具有相当的“穿透力”和理论“宽厚度”——透过“现实”触及其“本质”,同时,又引人深思且让人“回味无穷”。其二,它有与“内容”相应的专有术语——从教育学科史来看,“社会化教育”“国家主义教育”“大语文”“小语文”“文本作者的创作主体性”“授课教师的教学主体性”“学生学习主体性”等基本上都是王富仁在表述其教育思想时撰构的专有术语,而且每一术语基本上都有明确的界定,被赋予了独特内涵,恰到好处地表达王富仁特有的观点。
三、深入浅出的风格
一般来说,学理性强的思想表述总是用语典雅、文字“艰涩”甚至“晦涩”,如康德的“三大批判”。但具有强烈学理性的王富仁教育思想表述并非如此——通观王富仁所有有关教育的著述,可以看出,不仅几乎没有一处“佶屈聱牙”、没有一语晦涩难懂,而且总的来说,用语通俗、文字浅显、文从句顺、语意流畅,甚至还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和感染力,如“教参重要起来了,教材反而变得极不重要了。这就像到商店里买东西,只把商品的产地、厂家、规格、用途、价格记下来,却没有把商品拿回家一样。这就把我们的语文教学抽空了,语文教学提高的不是学生实际运用民族语言的能力,而是给语言文学作品插标签的能力。”[1]49“文本是作者和读者的中介……教师和学生都是读者,他们都必须直接阅读和欣赏作品文本,通过文本的语言感受和理解它的思想或感情。这就像一男一女谈恋爱,得两个人直接谈。各自对对方的印象如何,就从他们各自的亲身感受中总结出来,不需要当中再加个媒婆。教参就像夹在恋爱双方的一个媒婆,并且这个媒婆的权力好像无限大。人家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并不重要,她的看法才是唯一正确的。人家自己不能拿主意,非要按照他的意见办(不可)。”[1]50“中学语文教学的最高目标是建立起学生感受、理解、运用、创造民族语言的乐趣和能力,而不是他们在中学语文课堂上学到了多少课文,背诵了多少篇诗文,记住了多少具体的语文知识。现在的中学语文课,通共加起来才有多少课时?即使一个课时也不耽误,才能讲多少课文?才能让学生背多少篇诗文?你能和古代私塾的语文教育比?你能和古代的秀才、举人比?即使你中学语文教师,你编写教材的专家教授,就敢说一定比古代知识分子背得多、记得多?为什么一定要让学生和他们比?”[1]52等文字即如此;诸如此类的文字使王富仁的教育思想显得虽“阳春白雪”,但也颇为“下里巴人”,具有“专家学者”和普通民众“皆宜”的通俗性。
四、“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从全书来看,《语文教学与文学》的“语文教学改革”和“读书与教书”两个部分是“理论”——它们所承载的是王先生有关教育和文学的思想,“名篇赏析”部分是“实践”——它们是王先生有关教育和文学思想的具体运用;也就是说,全书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理论”与“实践”彼此关联、有机统一。从篇章之间的关系来看,《小说的阅读与欣赏》是“理论”,《精神“故乡”的失落——鲁迅〈故乡〉赏析》《怎样感受人?怎样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说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等是与之对应的“实践”;《散文的阅读与欣赏》是“理论”,《自然·社会·教育·人——鲁迅回忆散文〈从百草园到三维书屋〉赏析》等是与之对应的“实践”;《诗歌的阅读与欣赏》是“理论”,《从音、形、义话杜甫诗〈白帝〉》《〈秋思〉发微》《触摸语言——徐志摩〈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独特的组接方式独特的美学效果——李贺诗〈李凭箜篌引〉赏析》等是与之对应的“实践”,也就是说,在这里“理论”与“实践”是一一对应、相互支撑、彼此搭配的。从具体的篇章来看,每一篇文章都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理论”部分的文章在阐述观点时都列举了例子,“实践”部分的文章都有“理论”的运用,也就是说,“理论”与“实践”是共生共存的一个统一体。由此可见,该书不论从整体来看还是从局部来看,“理论”与“实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以上特点组合在一起使该书呈现出学术性与文学性完美统一的总体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