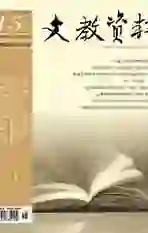浅论冯梦龙“情教”观
2019-08-24陈若仪
陈若仪

摘 要: 在作品中,冯梦龙的“情教”观作为方法论,其实现的必要手段是引起读者的共情。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他以因果报应观的认知为主导达到表层共情,以人物行为的情感缘由达到深层共情,最终起到教化作用。通过对文中王三巧、蒋兴哥行为与命运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冯梦龙的“情教”内容是围绕情不断波动、具有弹性的道德,是情化之理。
关键词: 冯梦龙 “情教”观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冯梦龙在《情史·序》中說:“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1]这是他“情教”观的宣言。“情教”即是冯梦龙的“教化”论,他认为“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1],将“情”看作本体,体现在文学上,“情教”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核心思想,是对通俗文学创作目的的界定,也是一种方法论。在《警世通言·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痛,导情情出[2]。
显然,这是对“情教”的形象说明。心理学家麦独孤的动原主义认为“行为的原动力是本能和情绪而不是理智”[3],听众的行为来源于与《三国志》故事的共情,而后将故事中的“情”投射到自己身上,随之发出相应的行为,因而读者要与故事达到共情,才能起到“教”的作用。因此,作品能否引起人们的共情是“情教”能否真正实施的关键,冯梦龙结合话本小说的特点,充分发挥共情的作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作为整部“三言”的首篇,是“情教”的典型代表。
一、表层共情:因果报应
“共情是一种人格特质或者一般性的能力,是一种了解他人的内部感受、感受他人情绪的能力和倾向”[4],对于话本小说,读者面对的有两类人:一是宏观上带有一定价值取向的叙述者,二是具体至小说中的人物。表层共情是读者直观地从叙述者的宏观角度,抽象化、符号化故事情节,达到了解感受叙述者主导的价值观的过程。“心理学家Gladstein认为,共情既包括认知又包括情感成分”[5],因果报应作为阴间正道,对人间不平进行拨乱反正,是古代小说劝善惩恶的惯用手段。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贯穿全篇的因果报应观以认知为主导,引导读者与叙述者达到价值观上的表层共情。
比较直白的形式是叙述者以全知视角直接发语,篇首“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6]告诫人们该放手时须放手,莫要贪图一时便宜,否则就会陷入“烦恼与事非”[6],已然初步显露“报应”观念。特别是在入话写道:“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6]强调恶人必有恶报,并且影射文中的陈商,生心设计勾引了三巧儿,最后妻子平氏作了蒋兴哥的妻子,“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们做个榜样”[6]。篇尾“恩爱夫妻虽到头,妻还作妾亦堪羞。殃祥果报无虚谬,咫尺青天莫远求”以回顾的方式强化了善恶有报的观念,同样是在劝诫人们“人在做,天在看”[6],一报还一报,莫求侥幸。
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是呈线型的人物命运,文中六位主要人物不论出场先后、身份地位,都因其行为获得了相应的报应,由下表可见:
东晋僧人慧远《三报论》记载:“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7]显然,相比其他两种报应,现世现报更能引起人的共情,文中的六位现报不仅来得快,还在数量和程度上达到善恶报的平衡状态,这是冯梦龙追求和谐同一思想的外现。
二、深层共情:人之本性
如果说因果报应是以认知达到的价值观上的共情的话,那么以王三巧、蒋兴哥为代表的人物具体形象的描绘就是从人的本性出发,透过人物的行为语言窥视背后的情感缘由,使读者站在人物立场理解、宽容,从人性根本上达到深层共情。
饱受争议的王三巧是一个复杂而立体的人物。首先,美貌自不必谈,不足以说明人物性格,但倘若加上温柔、深情就足以动人了。面对蒋兴哥私自安排远行经商,王三巧深明无能阻碍,与蒋兴哥指树为约,再三嘱咐“好歹一年便回”[6],如此柔情美貌又深情的女子,怎能不令读者动心。丈夫走后,王三巧谨记丈夫的嘱咐,“足不下楼,甚是贞节”[6],一心等待蒋兴哥归来。尽管丈夫逾期未归,当薛婆挑拨“官人出外好多时了,还不回,亏他撇得大娘下”[6],但她只是回答:“便是,说过一年就转,不知怎地耽搁了?”[6]丝毫没有埋怨之意。薛婆再三提及自己女婿在外纳妾映射兴哥与王三巧时,王三巧断然回答:“我家官人倒不是这样的人。”[6]显然,王三巧虽然悲伤但依然十分信任、深爱蒋兴哥的。在被休后,王三巧悔恨交加,企图自杀。蒋兴哥遇难时,即刻“两眼噙泪,苦苦哀求”[6],舍身相求丈夫吴知县,与蒋兴哥相见后“紧紧的你我相抱,放声大哭”[6],王三巧内心深处对蒋兴哥的爱未曾改变,这种爱可以说是平衡王三巧失节之过占比最大的因素。
其次,王三巧独守空房的凄冷孤寂更是惹人爱怜。当别人家“闹轰轰的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欢耍子”[6]时,王三巧触景伤情,必然会忆起新婚时二人恩爱的场景,思念丈夫,以至于她将希望寄托在问卜上,问卜的结果正是造成王三巧认错陈商的直接原因,二人相遇的因归在了蒋兴哥未按期归来,留王三巧一人空盼夫归、饱受煎熬,令人怜悯。
最关键的使读者深入王三巧内心的是对她失节过程的描写,这是整篇小说所占篇幅最大的部分,意在强调“被骗”这一过程,塑造王三巧天真善良、涉世未深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王三巧因涉世未深而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当薛婆进蒋门时,买首饰不仅不讲价,还说可以先只收半价,又借口有急事将珠宝首饰放于蒋家,多次交往时表明自己与三巧的知遇之情,显然是有目的地接近三巧。但天真善良的三巧丝毫未起疑心,还满心欢喜以为遇到知己,与薛婆同吃同住起来。如此,冯梦龙将王三巧刻画成一个用情至深、天真善良但孤苦难挨、渴求人情的闺中少妇形象,达到了让读者从人性上与王三巧共情、理解其失节缘由的目的。
按照儒家礼教传统,在夫妻关系上,夫为妻纲,妻子一切依从丈夫,须从一而终、保持贞洁,男子则可以三妻四妾、借故休妻。蒋兴哥这一形象大不同于传统封建男子的夫权思想,在情感上将王三巧看作与自己地位同等。在得知三巧与陈商的私情后,蒋兴哥先是又气又恼,但待回到家乡后,“不觉堕下泪来”[6],想的是:“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6]可见蒋兴哥有着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将三巧的失节看作自己的主要责任,归家后不但未责怪三巧,而是做了以下两件事:一是休妻。与其说休妻是因为不能容纳妻子的背叛,不如说是因为蒋兴哥认为妻子对自己不再有情。并且休书上未明晰修其原因,当王公问起时,蒋兴哥也不明说,只让去问三巧,为三巧留下颜面。二是在三巧再嫁时将十六箱妆奁原封送回。这是蒋兴哥对三巧再嫁给予的祝福。显然,他对三巧的爱未有改变,对其失节也是采取同情、理解与宽容的态度,他因情而起的谅解给予读者更深刻的情感共鸣,是读者理解王三巧更深层的原因。
三、共情所教:情化之理
所谓“情教”,“情”是手段,“教”是目的,冯梦龙以共情为手段,达到教化目的。他在《情史》中对“情教”内容有明确表述:“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1]“教”的内容是冯梦龙真正想要传达的“理”,它既不完全是传统的儒家伦理,又不是人情至上的世界观,而是围绕人情不断波动、具有弹性的道德,冯梦龙试图以此反抗僵化的儒家思想,最终实现挽救世风的目标。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以宋明理学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王三巧与陈商的通奸之罪万死难辞,而一个重病而死,一个仅是由妻变妾,显然陈商的恶报比王三巧要重得多,原因在于陈商是纯粹的“欲”,王三巧的“欲”出于“情”。冯梦龙反对纯粹的欲,所以给予王三巧恶报;但出于对人性的肯定,减轻了恶报的程度,本文“教”的重点在于后者,“理”的标准因“情”而变了。蒋兴哥的做法是对儒家尊卑等级中夫权的反抗,在传统夫权之下,蒋兴哥完全不必隐瞒三巧失节事实,不必归还妆奁,更不必再接受三嫁的三巧为妾,但他都做了,并且是心甘情愿所为,而他能够获得幸福的结局,正是冯梦龙对夫妻之间情等而序不等的反抗,初步显现出男女平等的价值取向。还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既然有情,蒋兴哥为什么要休妻?正如上文所提,冯梦龙对并不肯定人情至上,蒋兴哥不休妻就变成了纯粹的“情”,休妻行为就体现了冯梦龙对“理”的界定,如此蒋兴哥就是“情”与“理”真正和谐的统一体。在“三言”中,还有其他看似充满“情”与“理”矛盾的情况,如《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的韩夫人、《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的田氏,与三巧一样,都是丢失贞洁的女子,但她们的报应却各不相同[8]。再有《滕大尹鬼断家私》中的滕大尹与《桂员外途穷忏悔》中的桂迁二人都爱财,但冯梦龙的评价及二人的结局也不尽相同,这都是冯梦龙试图在作品中平衡“情”与“理”的表现。
晚明时期,中国由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冯梦龙处在新兴市民阶层活跃的时期,又难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思想趋向复杂。他一方面受李贽等人影响,“笑那孔子这老头儿,你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9],反叛儒家经典。另一方面似乎以通俗文学传达封建伦理,唤醒世人,认为“而通俗演義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2]。实则不然,朱光潜在《谈情与理》中说:“问理的道德迫于外力,问心的道德给予衷情,问理而不问心的道德只能给人类以束缚而不能给人以幸福。”[3]冯梦龙的“情教”就是追求“问心的道德”,不忠于其他任何传统观念,他在作品中宣扬的忠孝节义并非封建的愚孝、愚忠,而是“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1],在冯梦龙的笔下,它们既是理,同时又是情,二者的统一即是心甘情愿、由衷而为,即“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妇其最近者也,无情之夫,必不能为义夫无情之妇,必不能为节妇”[1]。可见冯梦龙的“情”真正要“教”的是:拒绝纯粹极端的情和理,二者的平衡与和谐,即情化之理,才是稳定、有利于世风的真正的道德。
参考文献:
[1][明]冯梦龙,评辑.周方,胡慧斌,校点.情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2][明]冯梦龙.警世通言[M].济南:齐鲁书社,1995.
[3]朱光潜.朱光潜谈美[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4]黄翯青,苏彦捷.共情中的认知调节和情绪分享过程及其关系[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6(06):13-19.
[5]郑日昌,李占宏.共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04):277-279.
[6][明]冯梦龙.喻世明言[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7]吴光正.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76-102.
[8]王和勋.浅析“三言”中因果报应故事的类型与思想成因[D].北京:中国海洋大学,2009.
[9][明]冯梦龙,著.尔弓,校点.广笑府·序[M].沙县:荆楚书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