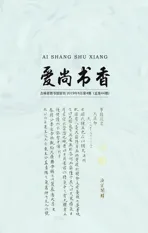新书故人
——读唐吟方《新月故人》
2019-08-23侯君明
侯君明
一套古色古香的《开卷书坊》第七辑买回来摆上书架,我不禁犯了踌躇:几位作者都是鼎鼎有名的实力派学者,书的题目也都是我感兴趣的话题,先看哪本好呢?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先看《新月故人》,理由是我和作者唐吟方先生熟悉,也算是故人吧。
书不算很厚,不到三百页,五十来篇短文,原本打算花个半天时间就读完,没想到却读得很慢,每读一篇就停下来细细咀嚼回味半天,遥想一下前辈学者艺人的风范,这样每天读两三篇,用了半个多月才读完全书。但我并不嫌自己读得慢,像书中人物这样有古风的人越来越少,读完了又到哪里去寻找呢?
作者着意在文化精神的传承。无论是记人述事还是状物,这一条主线都贯穿全书。在作者笔下,“敬希免赐修改”的孙机,自信可“颉颃汉人”的徐生翁,期以“文章相传”的吴战垒和沈左尧,“佛魔同体”的章祖安,无意于佳的朱家溍,平易而又执着的史树青,虽然各有专攻,各有个性,但无一不是传统的捍卫者。作者记述与蒋维崧的见面,蒋先生一开始一言未发,只在受到有关文化没落的话题触动时才说了一句:“现在什么都成了商品,都在‘卖’了。”读到这里,相信每个人都会思考:商品经济社会,是不是所有东西都应该成为商品?是不是应该坚守些什么?想到这一层,就不难理解章汝奭为什么甘愿做潮流的“退守”者了。
作者注重为学治艺方法的记述。他给吴小如写信,向吴先生了解青年时学书的经历,其本意即是在了解民国时期士绅阶层用于少儿书法教育的方法,对今天是不是有用;再就是因为吴小如在高校任职,其父亲又是大书法家吴玉如,作者希望吴小如的书法学习体会能对求艺者帮助。作者对吴先生的回信做了认真的解读,实际上也回答了好几个书学命题,比如孙过庭说过的“虽在父兄不能移子弟”,比如“家学渊源”、兴趣和信心对书法学习的作用哪个更大,比如语文教育和书法教育的关系,等等。作者描述魏启后写字,“中间蘸过两回墨,接笔的地方都在字的中间,墨干,但纸好,落在纸上水墨清润完全没有火气”;写魏先生盖章,“特意拣出上海印人韩天衡刻的姓名印,质量上乘的朱砂印泥,捺在纸上饱满而厚实。怕印色污及纸面,又找出牙粉刷上。”读时如身临其境,让人见识到一个洒脱而又认真的艺术家,而且对每位读者的艺术创作也会有所裨益。
作者长于艺术史料的钩沉和考证。他花了很大力气,去考证一些比较冷门的掌故,比如郑逸梅曾使用过的梅笺,在京派印人中风行一时的房山石,齐白石父子的看家本领“工虫”,钱锺书的三方自用印,沈从文写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幅章草,许明农对陶印的开发,不但可以补艺术史之阙,且读来令人兴味盎然,感到发现了一片新天地。
更难得的是,作者不为贤者讳,甚至不为自己讳。这种秉笔直书的史家风范,使他最大限度地为我们保留了一些独特的艺林掌故。他写去拜访嘉兴老辈学人吴藕汀,“看着吴先生会客室兼画室靠墙一排书架,架上摆满了书,妻子问吴先生:‘那些书您全读过吗?’吴先生脸通红,细声细气地回答:‘常有人来看我,要是会客室连书都没有,不像样,书架上的书是给别人看的,我没有读过。’”读完以后,一个坦诚可爱的老人好像就立在我们面前。据说文章发表后吴先生及其身边人有些不满,但我觉得,这样写丝毫无损于吴先生的形象,正如作者所说:“买书不读,难道不是一种快乐的境界?”他写去拜访章祖安,因为打不上出租车,于是边找车边给章先生打电话说明情况,没想到话音未落,电话那头就传来:“你不用来了。”一般作者可能会有意不谈这种略显丢面子的事儿,但唐先生却不避讳,于是我们不但见识了章先生的直截了当、不留情面,也看到了作者的真诚和大方。
作者的文笔有口皆碑,每篇文章读后都让人口齿生香,击节叹赏。他的旧作《雀巢语屑》,我已经借给即将小升初的女儿看,作为她学文言文的台阶,这本《新月故人》,我也准备送给她当美文读。
说完新书,再说故人。
说是故人,其实是我给自己脸上贴金,应该说我是唐先生的读者更合适。在二十多年前,我就在书法类报纸上读到过他的文章,写得轻松幽默,又言之有物,和报上其他的文章都不一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篇文章,就是收入《新月故人》中的《印印》。后来又在报纸上零零散散地读过《雀巢语屑》的一些篇章,但是因为当时工作调动频繁,报纸收不全,颇以未窥全豹为憾。后来在书店买到《雀巢语屑》单行本,当时真是欣喜若狂,连读了好几遍,结果发现了几个错别字和误用的标点,我认为这是校对的失责,就把这些白璧之瑕记了下来,找到唐先生当时供职的文物杂志社的地址,寄给他以供再版时修订。这种带点儿显摆带点儿不客气的行为估计一般人都不会欢迎,所以我寄出后也就没当回事儿,没指望能收到回信。但仅仅过了一周,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中承认书中确实有错别字,也有其他朋友指出过,这完全是自己的责任,不能怪到手民头上,感谢我指出错误,并希望经常联系。随信还附了一张名片。以后通过电话和短信联系了一段时间,我提出想去雀巢拜访他,他马上就跟我约了时间,说了他的住址,原来他离我很近。到了他家,看到满屋子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书,于是我们就先围绕着书的话题谈了起来,他读书之博、思考之深都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后来谈到收藏,他随手拿出一册珍藏的当代学者手札让我翻看,记得里面有一张王力请客的便条,他说:“有财力应该收些学者的字,多看能养气。”后来我请他在我带去的《雀巢语屑》上签名,他拿出一枝油笔签了。我最怕拿这种笔写字,在纸上停不住,写出来的字轻飘飘的,但他随手写来,毫不费力,每个字都力透纸背。当时光欣赏他写字的动作了,没有细看,回家后才发现,他把我的名字写成了“明君”,我发短信跟他开玩笑说:“齐白石为钱君匋题签,误写成‘君缶印存’,钱君匋遂刻一印‘白石老人称我为君缶’,我以后也可以刻一方‘雀巢先生称我为明君’。”他的回答很幽默,也很意味深长:“可惜我非白石你非君匋,为此印计,我二人均须努力。”
认识以后,唐先生对我颇为照顾,每有新作,必慨然相赠,我在欣喜之余,每生惭愧:读了这么多书,什么时候也能写出一本呢?我时常向他请教书艺,他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对章草感兴趣,有意学章草,他收藏有上百封被誉为“浙北章草第一人”的江蔚云先生的手札,毫不吝啬地拿出来给我观摩。有时我求他赐字赐印拓,他也爽快答应,觉得不满意的,还多写一两张让我挑。我搬到新家后,唐先生赠我一幅墨竹补壁,友人秦纪明自海南寄来一诗相贺,中间有两句“但使居有竹,宁可食无肉”,有了这幅画,“居有竹”才算没落到空处。有一次,我请他为一个手卷题签,签题好了,他通知我去拿,见面后,他告诉我,本来可以寄给我的,但因为我没告诉他手卷的尺寸,他是估摸着写的,装裱时需要处理一下,然后当面告诉了我处理的方法,我听了非常感动。这时候,快到中午了,他又请我吃饭,地点就在他家附近的“红辣子”(他曾在《五道口的餐馆和书店》一文中写到这家饭店),虽然没吃到招牌菜芷江鸭,也没见到常在此出没的北大清华名教授,但那顿饭还是给我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回忆。
以上是唐先生真诚、热情、随和的一面,他也有不苟且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他在一起吃饭,席间谈起书画,在座的一位朋友和他意见不太一致,起了争执,这位朋友喝得稍有些多,说话时近似吵架,唐先生总是静静地等他说完,然后不卑不亢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我当时想,和一个喝多的人争什么呢?顺着他说不就得了?但唐先生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毫不退缩。还有一次,我想出一本小册子,想请他写一点文字,其实是有拉大旗做虎皮的意思,但给他发了短信后,他一直没回,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提此事,他说实在忙写不出,后来我再看自己的作品,哪有出的必要啊,他要写了那才是砸自己的牌子呢。
在生活中,唐先生的装束打扮一向是普通不过,真看不出来他像艺术家,但和他略有交往,就会发现他的骨子里都能透出来艺术家的气息。我每天看他发的朋友圈,无一则不和艺术有关,无一则不见文心艺心,曾想以《唐吟方的朋友圈》为题写一篇文章,但因事迁延未就,后来有时间想写,发现他的朋友已经设成“朋友三天可见”,想看更多有趣的内容也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