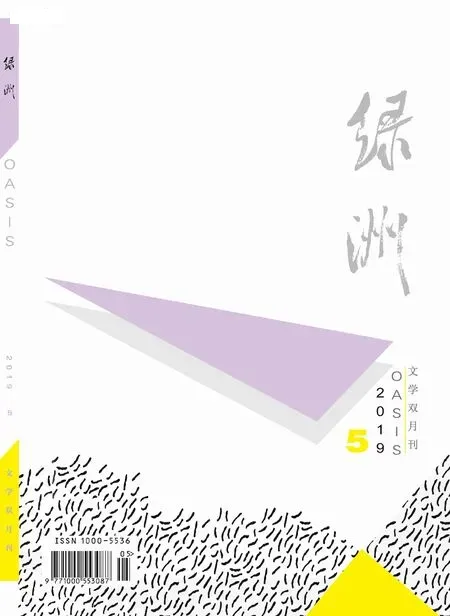茴香
2019-08-20綦水源
綦水源

庙前搭起了一个舞台,解放军的文工团正在演歌剧《白毛女》以及歌舞《谁养活谁》,为即将在农村开展具有划時代意义的減租反霸、土地改革运动作宣传。歌剧演到高潮的时候,忽然有个乡亲来报告:“土匪从山上下来了,你们赶快停锣吧!”于是乎,罗乡长爬到台口上,双手在空中忽闪忽闪着,嚷道:“户儿家们,土匪下山了,各回各的家呀!”
演员们没来得及卸妆,在罗乡长的带领下,登上一个寨子。这个寨子一面是高坡,三面是围牆,易守难攻。解放军文工团下乡演出,都帶有武器,他们很快就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只要土匪靠近寨子,就一齐开火。
土匪们一看,解放军居高临下,从坡上冲上去,肯定是送死,所以他们朝天放了几声空枪就跑掉了。
新疆刚解放不久,乌斯满土匪与国民党残余部队以及地方反动头目勾结在一起,他们出沒于崇山峻嶺,時不時地下山抢劫民财,破坏土改运动,妄图推翻人民政权,配合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陸。
巡回演出结束之后,文工团分成若干个工作组,深入到每个村,组织动员农民实行減租反霸,土地改革。小队长俞德带着季泉泉几个队员来到山口村。
这个村坐落在山口上,山洪常从这里咆哮而出,野狼,野猪也常从这里窜出来损坏庄稼,伤害家禽,加上地主的残酷剥削压迫,这个村多灾多难,格外贫穷。村长马福录,嘴上留着三羊胡子,是个地地道道在农村里喝涝坝水长大的农民,他张口就对工作组说:“解放军同志来得好呀,咱这个村的户儿家都苦扎咧,日子难行得很吆!大家种的都是地主白神仙的地,放的也是他的羊,白神仙放个屁你都得说是香的,他一只手能遮住半拉天。村头山坡上有个寡妇,模样儿长得俊,都让他霸占了,可谁也不敢言传。”听村长这么一说,就知道这个村的封建势力很強大,減租反霸运动在这个村里一定会展开激烈的斗争。工作组在访贫问苦中,去的第一家就是村头山坡上的那个寡妇。
这是一个独居的院子,房后有一个用柳树枝围成的羊圈,圈边有一堆隔年剩下已经发黄了的苜蓿草。两间土房,外间有个烧火做饭的灶,里间有个睡觉的炕,灶与炕是相通的,为的是通点热气。炕上舖了块烂毡,放了个沒有油漆的矮桌,房里沒有凳子、椅子,只有几个木墩儿。炕是多用的,客人来了,便招呼着坐在炕上,吃饭的時候,也是围着矮桌坐在炕上吃,到晚上,把矮桌搬下来,将破旧的被褥铺开,就成了全家人睡觉的地方。
俞徳帯着季泉泉来到寡妇家,进门后看到一个衣着褴褛但体态丰满,皮肤嫩白,眉清目秀的中年妇女。她一脸的郁闷和忧伤,身后站着一个璞玉般的小姑娘,她站在娘的身后伸出头来张望解放军,却是一脸的天真与欢笑。工作组长俞徳问:“大嫂你贵姓?”
中年妇女说:“我们户儿家命里注定是做牛做马,所以咱就姓马。”
俞德又问:“哦,马大嫂,你家有几口人?”
马大嫂凄惨地说:“我活得孽障,男人给白老爷放羊,在后山上让狼咬死了,这扎只剩下我和闺女了,她叫茴香。”
俞徳问:“白老爷是不是大地主白神仙呀?”
马大嫂回答说:“就是,这哒的户儿家,全都靠着他呢,这哒的地,都是他的地,这哒的水,都是他的水,这哒的山,都是他的山,沒有他的地和水,我们种啥呢?沒有他的山,我们哪哒去放羊呢?沒有白老爷,我们户儿家两只空手能挖抓个啥?能吃啥喝啥,不早就零干了。”
季泉泉急着说:“马大娘,你全说反了,沒有你们户儿家,他白神仙才会饿死哩!”
那个天真浪漫的茴香姑娘,听了季泉泉的话,竟然嘻嘻地笑起来,笑得是那样活泼灿烂。
俞徳又问:“马大嫂,你觉得白神仙这个人,对你们怎么样?”
“好着的,好着的,好着的。”马大嫂一连说了几个“好着的”。
工作组从马大嫂家里出来,俞徳说:“看来马大嫂还不明白是谁养活谁?吃了一辈子苦也不知道苦是哪来的,她不认为白神仙是坏人,反倒说‘好着的’,要改变她的认识,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难度很大。”
访贫问苦结束以后,工作组要选择几个典型,培养几个苦主,为召开诉苦大会、激发贫下中农的阶级仇恨作好准备。俞徳就对季泉泉说:“马大嫂这位苦主我们选定了,一定要提高她的阶级觉悟,改变她的认识,让她把一肚子苦水倒出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取得她的信任,要让她感到我们解放军是她的亲人,我们要做到以心换心,慢慢地感化她。干脆这样吧,你搬到马大嫂家里去住,给她当儿子,让她感到你就是她的亲人,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你懂这个意思吗?”
季泉泉回答说:“组长,我懂,住到他家里,和她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她家的一员,亲亲热热的,是这个意思吧?”
“对了。用你的一颗心,去暖她的一颗心,她认了你这个儿子以后,就会什么话都给你说,什么事都告诉你,一肚子苦水也会倒出来。”
俞德请村长先去与马大嫂商量,问她有个小解放军住到她家里愿不愿意,村长回来说她满口答应了。为了不给马大嫂増加开支和负担,俞德还托村长买了一袋白面,一壶胡麻油,半麻袋土豆,连同季泉泉的被包一起装在毛驴车上。临走前,俞德给了季泉泉一支左轮手枪,里面装了六发子弹,以防万一。
马村长赶着毛驴车,将季泉泉送到马大嫂家里去,快到马家時,村长喊了声:“马寿家,﹙马寿是她死去的丈夫的名字,村长依然这么叫着﹚解放军同志来了。”
马大嫂还沒出来,茴香倒笑嘻嘻地先跑出来了。一出来就忙着搬车上的东西,一对亮晶晶的眼睛盯住看季泉泉,目光里饱含着友好的情意。
马大嫂出来后说:“村长呐,小解放军圪蹴到咱这个穷人家里,你就不怕他受罪吗?”
村长说:“解放军和咱们穷人是一家人,你只会欢迎他,决不会亏待他。”
季泉泉说:“大娘,我叫季泉泉,住到你家里,给你添麻烦,我有哪点做得不好,你就批评,有什么要做的事,就吩咐我去做。”
马大嫂说:“你到咱家来,就好好地歇着,要做的活有茴香呢。”
村长在炕上坐了一会儿,给马大嫂交代几句就走了。
马大嫂除了两间土屋以外,还有几只红冠鸡,一年四季,都把心血和汗水撒在白神仙租给她的五亩山地上,女儿茴香也把豆蔻年华放在为白神仙放牧二十只绵羊上。
因为穷,马大嫂一天只吃两顿饭,早晨出工前吃一顿,傍晚收工回来再吃一顿。季泉泉到她家吃的笫一顿饭是马大嫂用白面蒸成的又软又暄的刀把子,﹙一条长形馍,用刀切开,所以叫刀把子。﹚一盆炒鸡蛋,一盆切成细得像粉丝一样的土豆丝,还有一盆从腌菜缸里捞出来的仍然保持着嫩绿的咸韭菜,上面还泼了一层胡麻油花。这是马大嫂倾尽全力为他精心做的一顿最为丰盛的饭菜。吃饭的時候,马大嫂让季泉泉吃刀把子,而她和茴香吃包谷馍。于是季泉泉放下碗筷,说:“我不吃了。”
马大嫂忙问:“我挖抓的饭菜,不香,难吃,是吧?”
季泉泉说:“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吃两样饭,我吃白面刀把子,你们吃包谷馍?”
马大嫂解释说:“面是村长送来的,村长说了,白面是给解放军吃的。”
季泉泉说:“我们组长给村长也说了,我住到你们家里,要同吃同住同劳动,你们要不吃刀把子,只吃包谷馍,那我也就不住了,我走!”
茴香一把拉住季泉泉的手,急得脸都红了,说:“你别走,你千万別走。”又喊了声“娘!”显然是求娘把季泉泉留下来。
马大嫂赶紧说:“你可不能走,你走了我怎么架跟村长交代呢,那好吧,茴香,你也吃刀把子。”说完,她自已手里依然拿着包谷馍。
季泉泉拿起一个刀把子,递给马大嫂,说:“大娘,你要不吃刀把子,那我还得要走。”
马大嫂说:“好,我吃,我吃,你千万不能走!”马大嫂终于放下了包谷馍,拿起了刀把子。
茴香笑嘻嘻地吃着饭,嘴里说:“娘,今天像过年。”
这一顿饭,是在茴香满面春风,笑声朗朗中吃完的。到晚上,茴香问道:“娘,解放军睡哪哒?”
那时候农村人没有木床,一家人睡一个炕。马大嫂说:“娘睡左边,解放军睡右边,你睡中间。”
茴香乐滋滋地一蹦子窜到炕上,把矮饭桌搬下来,又一蹦子窜上去,用笤帚把毡上的尘土扫干净,然后将季泉泉的被包放到炕上,打开,铺好。炕不大,除了放木箱和被褥,剩下的地方也只能睡三个人。
马大嫂住在山坡上,吃水用水很不方便。村里有个大涝坝,夏天的洪水,开春后融化的雪水,都储存到涝坝里,全村人吃的用的都是涝坝里的水。每天傍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马大嫂便和茴香拿一根木棒,提一个鉄皮桶,到涝坝里去打水,然后两人一高一低把水抬回来。季泉泉对马大嫂说:“大娘,以后抬水的亊情就归我和茴香了。”
经过几天的相处,马大嫂觉得季泉泉这个小解放军是个不娇贵、能干活、和得来的人,与户儿家的娃沒什么两样,于是也就不客气地说:“那好吧,就归你们两个了。”
从此,每当日落西山的时候,季泉泉与茴香就一起到涝坝里去抬水。茴香虽然比季泉泉小一岁,但个头长得与季泉泉一般高,抬起水来,不高不低,走路的快慢,也都一致,因而既平衡又和谐,那鉄桶里的水,从未撒出来过。抬水的时候,茴香坚持着要让泉泉走前面,她走后面,泉泉依着她,但走着走着,泉泉觉得肩上的负重越来越轻了,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茴香把水桶往她那头移过去许多,泉泉说:“茴香呀,你真鬼!让我抬轻头!”
茴香嘻嘻地笑着,打出村长的旗号说:“村长说了,要关心解放军,热愛解放军。”
泉泉说:“我们组长也说了,要军民团结一家亲,下回抬水,你走前头,我走后头。”
茴香又说:“你可不能搞鬼!”他俩就这么说着笑着把水抬了回来。
村里人做饭烧炕,用的都是山上的柴火。天刚亮,马大嫂便对茴香说:“今天你别去放羊了,我把羊拦到地边去,你去山上砍柴,明天就沒烧的了。”
茴香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说:“娘,我起来就去。”
季泉泉接着说:“我也去。”
茴香说:“你不能去,山上有老虎!”
季泉泉说:“有老虎你怎么敢上山砍柴呀?!”
茴香说:“我有碧柳庙里山神娘娘保护着,老虎不敢吃我。”
季泉泉说:“你怎么相信山神娘娘呀?那是迷信。真要有老虎出来了,我才可以保护你哩,我有枪,我能把它打死,还是我和你一起去吧。”他一面说,一面掏出左轮手枪给她看。
茴香一双水灵的眼睛望着娘,说:“娘,你说哩?”
马大嫂说:“解放军有枪,他能保护你,你们就一搭儿去吧”
茴香立马高兴得笑起来,其实她心里可愿意和季泉泉上山砍柴了,她快手快脚地穿好衣服,下了炕,她不刷牙,用葫芦瓢在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口,把剩下的水倒在手心里,抺了一把脸,拿了两根麻绳,掂起一把斧头,就和季泉泉上山砍柴去了。
出门就是山,只见满山的雪松,葱茏葳蕤,郁郁苍苍。松鼠在松枝上窜来窜去,啄木鸟把雪松啄得当当响;黃羊站在悬崖上,昂起头呼唤着太阳;瓜拉鸡,五更鹚满地乱跑,旱獭时不时地从洞里鉆出来,蹲在洞边竖起两个耳朵,一双眼睛盯着这一对少男少女。
爬上山以后,茴香就说:“别急,山上柴火有的是,把倒下的枯木树枝砍巴几下就是一大捆,坐下咱俩喧一喧。”
于是,他俩便在水桶粗的枯树干上坐了下来。
茴香问道:“哎,解放军,你是哪哒人?”
泉泉回答说:“我是湖南人。”
茴香又问:“湖南在哪哒?”
泉泉说:“湖南在洞庭湖边上。”
茴香又问:“洞庭湖在哪哒?”
“洞庭湖在湖南的边上。”季泉泉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只好又这么倒过来说。
茴香笑嘻嘻地说:“噢,我明白了薩,湖南在洞庭湖边上,洞庭湖在湖南边上,都在边边上。”她说她明白了,其实她还是个不明不白。
茴香又用眼睛盯住泉泉问:“你有哥有妺吗?”
泉泉回答说:“我沒有哥,也沒有妺。”茴香高兴起来,说:“呆好,你沒有妺妺,我给你当妺妹,行不?”她说得十分动情,十分纯洁,十分自然。
泉泉说:“行,不过,我有个条件。”
茴香问:“啥条件?”
“妺妹要听哥哥的话。”
“我听你的,啥都听你的。”茴香说得很认真,一点不虚假。
泉泉说:“以后你早晨起来要刷牙。”
茴香:“行。”
泉泉:“再不许喝生水。”
茴香:“好。”
泉泉:“还要学文化。”
茴香:“怎么架学文化?”
泉泉:“我教你识字。”
茴香:“呆好。”
二人说了一阵之后,就干起活来,茴香高高兴兴地举起斧头,噼噼啪啪地砍着倒在地上的枯树枝,泉泉又从她手里把斧头接过来,也噼噼啪啪地砍着。就在他们轮流着砍树枝的時候,茴香突然将斧头一摔,火急火燎地跑到一棵大树的背后,抹下裤子,蹲了下去。
泉泉急着问:“你干嘛跑到树后边去了?”
茴香回答说:“军哥,我拉肚肚了!”从此,她不再叫他解放军,而叫军哥了。”
过了一会,茴香又说:“军哥,快给我撅几根柴棍棍。”
泉泉问:“你要柴棍棍干什么?”
茴香答道:“擦沟蛋子。”〔屁股〕
泉泉一面给她撅棍棍,一面心里在说:山里妺子真不讲卫生。
茴香说:“快给我送过来,闭住眼睛!”
泉泉问:“要我闭住眼睛,我怎么走路,又怎么能把棍棍送到你手里?”
茴香说:“那你就睁开眼睛送过来,不许看我的沟蛋子!”
真是难为了季泉泉,他把眼光移到大树上,朝着大树走过去,走到茴香的身边,把几根柴棍棍递到她手里。
茴香与季泉泉,一人背了一大捆干柴,下了山,回到土屋里,马大嫂见了就说:“呆呀!呆呀!够咱们烧三五天的了。”
马大嫂租种了地主白神仙五亩山坡地,有两亩地种的是苜蓿。是到割苜蓿草的时候了,马大嫂和茴香一人拿了一把钐镰,下地割苜蓿。钐镰是新疆独有的农具,镰刀上安着一根长长的木把,农民不是弯腰用它割庄稼,而是直着腰左右来回钐动地割苜蓿,会使钐镰的人,一钐一大片。季泉泉从未见过钐镰,更不会使用,于是他就力所能及地把她割倒摊在地上的苜蓿草拢成堆,然后捆成捆,好往家里搬运。茴香用钐镰在前面割苜蓿,泉泉紧跟在后面将苜蓿拢成堆。茴香手中的钐镰挥动的速度太快,面积太大,一下钐到泉泉的腿上了。锋利的镰刀不但撕开了季泉泉的裤子,而且拉破了腿上的肉皮,鲜血直流。茴香一见吓呆了,措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大哭起来,哭得好伤心,好难过。马大嫂过来问:“香,大白天你哭什么?”
茴香哭着说:“娘,我的钐镰钐到军哥的腿上了,军哥裤子破了,血都流出来了,怎么架办呀!”她用双手狠劲地捶打着自己,又说:“该死!该死!我真该死!”
马大嫂连忙撕下衣上一块布,包扎好季泉泉的腿。
季泉泉忍着痛,脸上还露出笑容。茴香一面擦眼泪一面对泉泉说:“你快圪蹴下来。”
于是,季泉泉就坐在地上,茴香也坐了下来,她用双手将季泉泉的那条伤腿托起来,放到自己的腿上,低下头来,鼓起腮巴,对着伤处一口一口地吹,边吹边问:“军哥,还痛不?”
季泉泉嘿嘿一笑,说:“香,我早就不痛了。”
茴香还是眼泪巴巴地说:“我不信,怎么架也把你痛死了。”
季泉泉从地上站起来,故意地在地里走了几大步。说:“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划破点皮,没啥要紧。”
茴香看他能走路,这才止住了哭,还伸手在泉泉的脸上抹了一把。
马大嫂望着泉泉与香香那种亲热的样子,自己也会心地笑了,她对季泉泉说:“你就坐在田埂上歇着,我和香香捆苜蓿,赶明天就把它背回圈边去,一冬天也就不愁绵羊没草吃了。”
笫二天,马大嫂领着香香和泉泉,把地里的苜蓿草揹了回来。茴香放下最后一捆苜蓿草,已经是汗流满面,干渴不已,她抓起葫芦瓢,往水缸里舀水喝。季泉泉一把抓住她的手,声色俱厉地说:“你怎么又要喝涝坝里的生水!”
茴香说:“哎呀!军哥,我都渴零干了,快让我喝几口吧!:”
季泉泉坚决不松手,说:“一口也不许喝,涝坝里的生水不卫生,喝了会得病!”
茴香说:“村里人都是喝涝坝水长大的,沒事。”
季泉泉说:“什么沒事?那天上山砍柴,你为什么拉肚子?还不是喝涝坝水喝的?”
茴香说:“不是,是我晚上沒盖好被子,肚肚着凉了”她仍坚持着要喝。
季泉泉说:“你怎么就忘了,要听哥的话。”
茴香立马放下水瓢,说:“不喝了,听哥的。”
季泉泉又说:“以后必须喝烧开的水,我要你永远不喝生水,更不许你偷偷地喝!”
茴香认真地回答说:“我要再喝涝坝里的生水,你怎么架用柳条子抽我都行。”
地里的活都做完了,马大嫂说:“泉泉,香香,今天我没亊了,就把羊赶到地里去吃剩下的苜蓿,你俩在家里歇着。”
马大嫂拿起羊鞭,吩咐道:“我放羊去了,你们自己热饭吃。”
茴香吟吟地一笑,说:“娘,你就放心去吧,我绝不会让军哥饿着。”
马大嫂走后,茴香高兴得啍起歌儿来。
泉泉问:“香,你还会唱歌?”
香香答道:“会呀,我会唱山歌。”
“你是怎样学会唱山歌的?”
“到山上砍柴的,捡蘑菇的,放羊的,都会唱山歌,他们一唱,我就用耳朵听,听上两三回,我也就会唱了。”
“那好,香,唱个山歌给我听。”
泉泉叫她唱,她立马就唱:
碧柳河上柳树多,
柳树叶叶往下落
叶叶落在柳树下,
根根扎在妺心窝。
东山拉雾西山开,
天山头上雨下来,
阿妺不怕下大雨
雨里等着阿哥来。”
香香唱罢,泉泉听后大加赞扬:“哎呀!你唱得真好听,比我们文工团的独唱演员唱得还好。”
香香嘻嘻地笑着,说:“你说我唱得好听,那我就天天唱给你听。哎,军哥,你会唱歌吗?”
泉泉回答说:“我是文工团的,当然会唱歌。”
“那你也唱一个给我听。”香香要求他。
泉泉说:“好,我唱个《谁养活谁》的歌儿给你听。”
泉泉唱道:
老乡,老乡,亲爱的老乡,
谁养活谁呀,咱们来想一想,
地主不劳动,住高楼,穿绸缎,粮食堆满仓;
农民做牛马,吃不饱,穿不暖,天天饿肚肠。
老乡,老乡,亲爱的老乡,
谁养活谁呀,咱们来想一想,
地主靠剝削,收地租,纳捐税,还放阎王账;
农民靠双手,春天种,秋天收,流尽血和汗。
老乡,老乡,亲爱的老乡,
世道不平呀,咱们要推翻,
扛起大红旗,拿镰刀,拿斧头,咱们拿起枪;
推翻旧制度,不信命,不信天,起来干一场。
泉泉唱完后,还给她一句一句地解释歌词的意义。香香说:“这个歌真好,说的有道理,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泉泉说:“香香,你觉得这个歌好,我就教你唱。”
香香:“呆好。”
泉泉又说:“你学会了,咱俩就一起唱给你娘听。”
香香:“行。”
于是,泉泉就一句一句地教她唱这首歌。香香有唱歌的天赋,没教几遍,她也就学会了。
唱完歌以后,香香问道:“军哥,你会打髀矢吗?”
泉泉说:“不会,啥叫打髀矢?”
香香说:“打髀矢可好玩了,不会我教你。”她从炕头上拿出一个小布袋,又说:“打髀矢要到门外打。”于是,两人出了门。茴香将布袋里二十个羊骨头倒在地上,然后分成两堆,一堆十个,香香说:“喏,这堆是你的,这堆是我的,都一般多。我把我的羊骨头放在这扎,你站在五步以外的地方用你的羊骨头来打,你要打中了,就把我的羊骨头捡走,还可以在我的脸上亲一口,要是我把你的羊骨头打中了,我就把你的羊骨头捡走,也得让我在你的脸上亲一口。说话要算数,不准耍赖。”
泉泉说:“好,我决不耍赖。”
于是,泉泉和香香就在门前打起髀矢来。季泉泉是湖南人,从小只玩过捉迷藏,丟手绢,打髀矢见都没见过,因此,他很不熟练,沒有准头。而茴香一打一个准,十个羊骨头让香香捡去了九个,还让香香在他脸上亲了九口。泉泉只剩下最后一个羊骨头了,还真邪乎,就这最后的一个羊骨头,偏偏让他把香香的羊骨头打中了。于是,他捡了香香的羊骨头,而香香很自然地把脸伸了过来,说:“你亲吧!”
于是,泉泉就在香香脸上亲了一口。
工作队要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安排下一阶段的任务,因而季泉泉到乡里开会去了。泉泉这么一走,香香像丢了魂似的,心情很不安,她想了很多很多:他会不会不回来,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要不回来,我到哪哒去找他?他又想起了他教她唱的那首歌,于是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来,娘听了就问:“香,你唱的什么歌?我以前咋就没听你唱过。”
茴香回答说:“娘,我唱的是新歌,军哥教的,名叫《谁养活谁》,娘,好听不?”
娘说:“好听,给娘再唱一遍。”
茴香唱完后,也像季泉泉一样给娘讲了歌词的内容,还问道:“娘,你说这歌里说的有没有道理?”
娘说:“仔细想想,是这么个理儿,我咋以前就不明白呢?”
茴香又说:“娘,你过去说是白老爷养活了我们,其实是我们养活了白老爷,你都倒巴朗了。”﹙弄反了﹚
娘说:“哎咦!是娘糊涂呗!”
季泉泉到乡里开完会,顺便到乡合作社门市部买了些生活用品,快到家時,老远就看到茴香站在家门前那个土包上,季泉泉问道:“你站在土包上干什么?”
茴香笑吟吟地从土包上跳下来,扑到他跟前,一双手热烈地在他身上摸摸打打,然后说:“我每天下午都站在土包上,看你回来沒有。”
“我说过开完会就回来,你沒有必要天天站在土包上去望啊!”
“哎呀!人家想你了嘛!”茴香说得那么纯洁,那么天真,那么自然。
季泉泉进了屋,茴香递过来一碗水,还特别说明:“这可是烧开了的水,你就放心喝吧!”
季泉泉高兴地说:“你进步了,知道不喝涝坝里的生水了。”他几口就把一碗水喝了进去,然后从挎包里拿出一件新外衣,对马大嫂说:“大娘,这是给你买的,你不要嫌它不好看。”
马大嫂不接衣服,说:“哎哟!我怎么能叫你破费,叫你给我买衣服,万万使不得!”
“大娘,上回你撕下自已衣服上一块布给我包脚,那衣服也不能穿了,我得赔你一件。”季泉泉说完,就把衣服递给马大嫂。
马大嫂还是不肯接。
季泉泉又说:“大娘,我们解放军有规定,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你一定要收下这件衣服。”
马大嫂还是不肯收。季泉泉说:“你要不收这件衣服,那我就回去了,再也不来了。”说完,提腿就往门外走。
这一下吓坏了茴香,她赶紧过去拉住季泉泉,嘴里急出了白沫,说:“你可不能走!”又对娘说:“娘,你就收下吧,别亏枉了军哥一片好心。”
马大嫂终于收下了那件新衣。接着,季泉泉又从挎包里拿出一瓶牙膏,一把牙刷,一个识字本,对茴香说:“这是给你的,从今以后,每天早晨起来,都得用它刷牙。”
茴香将牙刷捏在手里,看了又看,说:“这东西毛叉叉的,还不会把我刷痛了?”
“绝对不会,只要你刷习惯了,一点不痛。还有这个识字本,以后你要早点起来,我教你学文化,每天识五个字,能行吗?”
“行,我就怕今天认识了,明天又忘了。”
季泉泉最后从挎包里拿出一包草纸,递给茴香说:“以后解大便,不许用柴棍棍擦沟蛋子,用纸擦。”
“哎呀!军哥,我擦沟蛋子你也管?!”茴香反问道。
这時候,马大嫂说话了:“军哥管得对,管得好,以后你啥都得听军哥的。”
茴香反问道:“娘,我听军哥的,你听谁的呀?”
娘说:“我也听解放军的。”
季泉泉趁机又说:“娘,香,以后不要信命,不要信天,也不要信碧柳庙里的山神娘娘,只信共产党和解放军。我们劳苦大众为什么受穷,都是白神仙那些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穷的。他们不是你们的恩人,是你们的仇人。”
茴香立马又问:“娘,军哥说得对不?”马大嫂说:“你军哥说的对,是我们的仇人。这哒的户儿家活得孽障,都是因为有个白神仙。”
马大嫂穿上了那件粉红色的新衣,家里沒有穿衣镜,只好问女儿:“香,你看这件衣服合身不?”
茴香认真地看了一眼,说:“娘,不大不小,正合适。娘,你穿上这件漂亮衣服,准能给我再找回来一个大。﹙父亲﹚”
马大嫂生气地说:“该死的丫头,你怎么说出这样难听的话,寡妇改嫁,那还不会笑掉大牙!”
季泉泉接上话说:“大娘,现在都是新社会了,时代不同了,寡妇改嫁完全是应该的,你有你的自由,你有你的权利,想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不会笑话。”
马大嫂只是微笑着,不愿把心里话说出来。
这天晚上,一轮明月高挂在天空,满天的星星,向着大地微笑,山风送来了凉爽,夹帯着薰衣草的清香,飘进家家户户,夜静得能听到归巢的鸟儿从房顶上飞过。
茴香扫完了炕,舖好了被子,一家人在愉快和谐的气氛中很快就睡熟了。睡到半夜,季泉泉感到身边好像有一团火,热乎乎的,是这团火把他热醒了。他睁眼一看,原来是茴香不知道什么時候钻进了他的被窝,竟然紧挨着他睡在了一起,一条腿还搭在他的身上,季泉泉顿時心慌得咚咚直跳,冒出一身冷汗,不知如何是好。他赶紧把她推醒,埋怨地问:“你,你怎么睡到我的被窝里了?”
茴香一面揉眼睛一面说:“啊!睡到你的被窝里了,我咋不知道。”
季泉泉又急不可待地说:“快!快睡到你的被窝里去!”
茴香用脚在他身上蹬了一下,表示不满,但她还是睡到自己的被窝里了。
笫二天早晨,茴香果然起来得早,用泥碗舀了一碗水,拿起牙刷与牙膏,蹲在门前刷牙,一溜白沫顺着嘴角流下来,她好不奇怪,怎么还有甜味儿。
季泉泉也起了床,刷了牙,洗了脸,拿起那个识字本,在初升的阳光下,教茴香认字。他用手指头点着识字本上的字,说:“这个念你,这个念我,这个念她。”茴香也跟着念“你,我,她。”
季泉泉又解释说:“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她就是你娘。”
茴香跟着说:“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她就是你娘。”
“哎呀,错了,错了!”季泉泉说。
“哪哒错了?”
“她就是你娘,说的是你的娘,而不是我的娘,你明白吧?”
“我明白了,你说的那个她,指的是我的娘。”
吃完早饭,茴香拿起羊鞭,打开羊圈,吹起口哨,赶着羊群上山去放,季泉泉跟在她的后面。茴香再也不讲客气,好像军哥上山和她一起去放羊,是完全应该的,份内的事。
青山如洗,一片黛绿,山坡上长着酥油草、苦豆子、马莲、牛蒡。野薔薇和金蓬花开得绚丽多彩,耀人眼目。瓜拉鸡,五更鹚在草丛中穿行,羊群在山坡上漫游,雪山林立,青松滴翠。茴香将几朵金蓬花插在自己的头上,问道:“军哥,好看不?”
季泉泉回答道:“好看,像个仙女。”
茴香听后非常满足,特别高兴,嘻嘻地笑起来。
天有不测的风云,羊群突然骚动起来,拥向茴香的身边,寻求主人的保护。茴香一看,立马就说:“军哥,狼来了!”
山里的孩子不怕狼,茴香捡起地上的石头,向狼猛击过去。季泉泉一看,来的不是一只狼,而是三四只,而且狼也不怕茴香击过来的石头,竟然张开露着獠牙的大嘴,向茴香扑来。就在野狼快要咬住茴香的时候,季泉泉举起左轮手枪,将野狼打倒在地,另几只狼见势不妙,掉头就跑。
茴香没有恐惧和害怕的样子,还笑吟吟地说:“军哥,你日能得很,一枪就把狼掉倒了。”
季泉泉回答说:“我的这点枪法,还是小队长俞德教的。”
茴香听后,又笑嘻嘻地说:“军哥,这回你救了羊,又救了我。叫我怎么感谢你呀?”
季泉泉说:“我不要你感谢,只要你听我的话就行了。”
茴香:“以后我句句都听你的。”
茴香与季泉泉,二人赶着羊群,抬着一只打死的狼,下了山。这天晚上,马大嫂炖了一锅野狼肉,一家人吃了个满嘴流油。
一个阴沉沉的天,太阳被乌云遮沒了,山里拉起了大雾,松林成了黑乎乎一片。远处传来几声枪响,还有马的嘶叫,户儿家的狗也狂叫起来,村里人心惶惶,一片混乱。马村长喘着粗气跑进马大嫂的家,惊慌地说:“土匪趁着山上拉雾看不见,窜到村里来了!这回他们不是来抢粮食,是对着土改工作队来的,他们要把工作队抓到山里去。季泉泉同志你赶快走吧!”
村长的话音刚落,土匪的马蹄声已响到门前了,季泉泉要走是走不出去了,他拔出左轮手枪要抵抗,村长说:“人家一大群,你一个人能抵抗得了吗,还是躲起来吧!”
茴香心里一激灵,拉起季泉泉从后门走了出来,指着羊圈边那一大堆苜蓿草说,“快,你快钻进去!”
季泉泉拨开苜蓿草使劲往里钻,茴香又把拨开的苜蓿草恢复成原样。一个穿国民党军官衣服的人,领着几个乌斯满土匪来到房前,伪军官对站在门前的马村长与马大嫂说:“你们这些泥腿子,拿羊鞭的我们都不抓,只抓土改工作队。”
马大嫂说:“什么工作队,我们一满沒见过。”
伪军官说:“哄,你想迷糊我,捜!”
匪兵在炕房里,灶房里,羊圈里捜了个遍,什么也沒找到。本想要走,那个伪军官的一对牛眼盯住了那堆苜蓿草,说:“嘿嘿,工作队肯定是藏在牧草堆里,给我上刺力,使劲往里戳!”
于是,几个匪兵就用白哗哗的刺刀,像对着草人练兵那样,一下又一下地往里戳。马大嫂瞪起眼睛,望着那白哗哗的刺刀戳进去,她的筋在暴跳,血在奔流,土匪每戳一下,她牙咬一下,心跳一下,恨不能上去与土匪搏斗。
这时候,茴香在房后将一个铁皮水桶使劲往地上一摔,发出哐当的响声,伪军官带着几个匪兵赶了过来,问道:“小丫头,看到土改工作队的人吗?”
茴香说:“看到了。”
伪军官又问:“看到他往哪儿跑了?”
茴香用手指着说:“那不是,往后山上跑了。”
伪军官看到有一个身影正往山里跑,他对匪兵吼道:“快,给我追。”
其实那个身影不是季泉泉,而是马村长。
伪军官带着匪兵走了以后,茴香拨开苜蓿草,将季泉泉拉了出来,她把他从头到脚,身前身后,摸了一遍,问道:“军哥,伤着你了没有?”
季泉泉说:“没呀,你不看我还是好好的嘛!”
马大嫂说:“匪兵用刺刀往苜宿堆里戳,都把我吓灵干了。”
季泉泉说:“他要真戳到我的身上,我就开枪把他毙了。”
茴香又笑着说:“还是军哥命大,就没戳到他的身子上。”
工作队经过访贫问苦,培养苦主等一系列工作,终于在全村召开了诉苦大会上,马大嫂带头诉出了她的覆盆之冤,受压迫受剝削的穷苦人,都把深仇大恨诉了出来,像火山喷发,是那样炽热,那样浓烈,那样的不可抗拒。
诉苦大会结束之后,户儿家们像是出了一口挤压在胸头几十年的怨气,下地干活也增加了几分劲头,走在路上相互都用笑脸打着招呼,茴香更是高兴得哼着那首山歌:“东山拉雾西山开,天山头上雨下来,阿妹不怕下大雨,雨中等着阿哥来。”
早晨起来,茴香已经养成了刷牙洗脸的习惯,她像对自家人一样地说:“军哥,上山放羊去。”
季泉泉也把放羊看成是自己份内的事,爽快地答应着:“走吧。”
于是,他们打开羊圈,茴香吹着口哨在前面给羊群领路,季泉泉在后面驱赶着掉队的羊。他们把羊群赶到深山一处水草丰茂的地方,任羊群自由地吃草,他俩在一块青石上坐了下来,高山挡住了太阳,他们坐在阴凉处好不爽快。
正当他俩四处观望的时候,一个大白兔长着一身丰满的肉,从洞內鉆了出来,竖起两个耳朵,凝望着这一对心心相印,亲如兄妹的少年。
季泉泉高兴地拔出左轮手枪,对准那个野兔说:“送到嘴边的肉,我把它打死,捡回去让你娘炖着给我们吃。”她抠动扳机,“嘣”的一声,兔子应声倒地,茴香高兴地把它捡了回来,说:“军哥,你日能得很,一枪就把兔子撂翻了。”
就是这一声枪响招来了大祸,一支土匪闻声赶了过来。
茴香说:“哎呀!军哥,土匪过来了,咱们赶快跑吧!”
季泉泉拉起茴香的手,朝树林跑去。土匪骑的是马,四条腿比两条腿跑得快,他俩终于被土匪包围了。伪军官指挥着几个土匪,说:“给我把这个小共军捆起来,戴上头套,带走!”
于是,几个土匪用牛毛绳将他捆住,戴上头套,推着拉着把季泉泉带走了。
土匪将季泉泉抓走之后,茴香一屁股坐在草地上,痛哭起来。她以泪洗脸,声音嘶裂,两条腿在草地上乱蹬着,一双手抠起地上的泥土,一把一把地撒向空中。
她哭得无比的伤心,声声都是撕心裂肺,她一直痛哭着,直到哭哑了嗓子,哭不出声音,才勉強地站起身来,四肢无力,搖搖晃晃,脚步沉重地赶着羊群向家里走去。
茴香将羊群关进圈里,一进门就倒在娘的怀里,又是痛哭起来。马大嫂问她:“香,你哭什么?快给娘说!”茴香还是只哭不说话,娘又问:“香,你不能只哭不说呀!你要把娘急死不是?”
茴香终于哽咽地、一字一句地说:“土匪在山上把军哥抓走了!”马大嫂听后,长长地“啊”了一声,惊呆了好长时间。她一口气跑着去报告了马村长,马村长立马又告诉了小队长俞德,俞德直奔剿匪指挥部。
这一夜茴香躺在炕上,闭上眼睛就出现季泉泉和她在地里割苜蓿;砍柴时用柴棍棍给她擦沟蛋子,打髀矢时,互相在脸上亲一口。这一夜她想了很多很多,翻来复去睡不着,她的一颗心,一直拴在军哥的身上,天刚亮的时候,她就从炕上爬起来,也没给娘打一声招呼,就操起那把砍柴的斧头,进山去寻找军哥,她要和土匪拚了,她要把军哥救出来,就是死,也要和军哥死在一起。茴香就这么憨憨地但又无畏地走进了深山,钻树林,爬悬崖,找了一条山沟又一条山沟,进了一个山洞又一个山洞,就连草窝她也要拨开看看,然而,连季泉泉的影子都没发现。她站在山头上高喊:“军哥,军哥,你快答应,你在哪里?!”她每喊一句,大山回应一句,于是,整个山河大地,都回响起了“军哥,军哥……”的声音。
就在她绝望的时候,发现天上有几只老鹰在盘旋,在向下俯冲,山里的孩子明白,老鹰盘旋俯冲的下面,一定有它能吃的东西。于是,她向那边跑去,终于在一块巨石上发现了季泉泉,她拚命地扑了过去。原来是:土匪事先強行给季泉泉灌满一肚子水,灌得肚子鼓了起来,然后脱光他的衣服,用牛毛绳捆住手脚,给嘴里塞满羊毛,再用细麻绳捆住生殖器的龟头,使他无法排尿。然后放在石头上暴晒,直到肚子爆裂而死去,让老鹰和野狼来吃水肉。这是当地土匪所用的特种刑法,比用刀子割肉还要痛苦得多。
茴香赶紧掏出季泉泉嘴里的羊毛,解开捆住他手脚的牛毛绳,喊道:“军哥,你醒醒,你快说话!”
季泉泉微微地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香,香,我还活着,我要撒尿,我一肚子水,胀得好难受,都快要爆了。”
“你快尿呀!”
季泉泉用手指了指下边,说:“我尿不出来。”
茴香一看,原来是龟头被捆住了,她毫不犹豫地用手来解龟头上的麻绳。然而,龟头越触动越硬,越硬就越大,越大越难解开麻绳。茴香急出了一身汗,骂道,“这个坏东西,怎么硬成铁棒棒了?”她心里一激灵,用指甲在他生殖器上使劲一掐,掐出了鲜血,生殖器立刻就软了,小了。茴香很快解开了麻绳,一股尿便冲向了天空。
尿出来以后,没多久,季泉泉便站了起来,对茴香说:“走,赶快离开这里。”
茴香扶着季泉泉,在那弯弯曲曲,沟沟坎坎的山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最终走出了深山,回到了自己的家。
剿匪部队开进了深山,把土匪打得死的死,逃的逃,活的活捉。山口村在土改工作队的组织领导下,召开了批斗大会,斗倒了恶覇地主白神仙。批斗大会结朿之后,贫下中农扬眉吐气,一个个欢心笑语,茴香更是高兴得拉起季泉泉的手,唱起了那首山歌:
碧柳河上柳树多,
柳树叶叶往下落,
叶叶落在柳树下,
根根扎在妹心窝。
东山拉雾西山开,
天山头上雨下来,
阿妹不怕下大雨,
雨里等着阿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