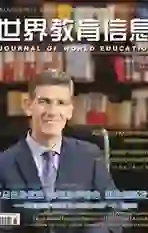《达喀尔行动纲领》发布以来的国际教育援助投入研究
2019-08-10姜少杰
姜少杰
摘 要:自《达喀尔行动纲领》发布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各援助方的努力下,国际教育援助投入获得了更多的关注,援助投入量得以显著提升,并向基础教育倾斜。但不能忽视,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力度仍旧不足,难以支持全球教育治理目标的全面实现,同时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仍存留有关援助投入分配和有效性的问题。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已被提上日程,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势必在投入量、投入分配和投入有效性方面面临挑战。此外,对国际教育援助投入的研究对我国实施对外教育援助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国际教育援助;援助投入;全民教育目标;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际教育援助产生自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国际援助,其后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各国对外援助部门和开发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DAC)的成立,以及联合国开发署、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IDA)等国际组织多边教育援助的出现,国际教育援助逐渐从起步阶段迈入快速发展阶段,并一直在全球教育开发和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2000年的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上,论坛委员会基于1990年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起草了《达喀尔行动纲领》。该纲领重申每个人的教育权和学习需要,回顾了过往全球基础教育治理取得的成就与不足,评估了现存的全球教育问题,并提出六项全民教育目标。《达喀尔行动纲领》指出,“任何对实现全民教育做了严肃承诺的国家都不得因资金不足而贻误这一目标的实现”[1]。《达喀尔行动纲领》的出台使得世界范围内再次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及现存教育问题的严峻性,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可行性的全球教育治理途径,并鼓舞各方达成治理目标。此外,《达喀尔行动纲领》多次提及“预算”“资金”“筹资”“减贫”“援助”等词汇,让各方代表意识到了国际教育援助投入的重要性。总之,《达喀尔行动纲领》为各教育援助方设立了艰巨的教育援助投入挑战。目前,全民教育目标已经收官,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首倡导的新一轮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迈入起步阶段。
本文通过总结和分析《达喀尔行动纲领》颁布以来的国际教育援助投入的主要进展与问题,预测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在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并对我国的对外教育援助工作提供启示。
一、国际教育援助投入的主要进展
(一)国际教育援助投入获得更多关注
在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提出六项全民教育目标后,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于联合国纽约总部召开。参会各国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并确定了必须在2015年前达成的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其中,第二项目标是“普及初等教育(Universal Primary Education,UPE),使世界上所有儿童都能够完成初等教育,并平等地接受各级教育”。两次会议都强调了更多的、更有效的援助投入是实现全民教育及教育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2002年3月,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于蒙特雷举行,会议上达成的《蒙特雷共识》要求“增加官方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投入、实施有效援助、發展筹资伙伴关系”[2]。同年4月,世界银行开发委员会提出快车道倡议(Fast Track Initiative,FTI),聚焦于增加国际教育援助投入以帮助受援方应对到2015年实现UPE的挑战。2005年3月,100多个援助方及受援方共同签署了《巴黎援助有效性宣言》,旨在通过国际协作加强援助的有效性,以助力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同年在八国集团格伦伊格尔斯峰会、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五周年”领导人大会和欧盟首脑峰会上,各援助方承诺加大援助投入力度。2008年多哈发展筹资问题会议、2009年伦敦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以及拉奎拉八国集团峰会全部重申了国际援助投入的目标。在2008年阿克拉第三届援助有效性高层论坛以及2011年釜山第四届援助有效性高层论坛的推动下,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国际教育援助投入的有效性。在各类宣言、倡议及会议的推动下,国际教育援助投入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二)国际教育援助投入量取得显著提升
洛克菲勒基金会报告显示,投入到正规教育中的补助金及贷款总额从1970年的147.1万美元增至1975年的276.5万美元;世界银行报告显示,教育援助投入总额从1975年的20.18亿美元增至1980年的44.96亿美元。但是,由于缺少当时关于教育援助投入的详细报告、不同国家和组织对教育的定义不同、通货膨胀以及投入资金与接受资金间存在差距等因素的限制,只能大致上说20世纪70年代的教育援助投入小幅上涨[3][4]。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增长量较小,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反而整体走低,平均每年的教育援助投入约42亿美元[5][6]。20世纪90年代的教育援助协定投入如图1所示,1990年世界全民教育大会的召开使教育援助协定投入在1990-1991年维持着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但随后在1991年末冷战结束、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等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全球经济与政策的变动使得国际教育援助协定投入出现下滑。到2000年,国际教育援助协定投入降至90年代最低值。
与2000年相比,2001年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在ODA投入总额中占比下降2%,双边和多边教育援助投入都呈小幅下降,2002年的国际教育援助投入水平与2001年相当[8][9]。同时,由图2可以看出,2003-2014年间的国际教育援助支出总额整体上相对于2002年的支出水平有了显著提升,约为年均120亿美元。此外,相关国际倡议和行动推动了援助方对投入的重视程度,在2002-2010年间,除了在2008年下降了约2亿美元,国际教育援助投入整体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可以说自《达喀尔行动纲领》颁布以来,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得到了显著提升。
(三)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向基础教育倾斜
自《达喀尔行动纲领》发布以来,国际教育援助投入更多地向基础教育②倾斜。20世纪90年代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出于满足社会快速发展和对精英及技术人才的急迫需求,以及基础教育分布过广、需要持续大量投入等原因,相比于中等后教育及职业技术教育,基础教育在教育援助中的优先性一直较低。例如,在1981-1986年,初等教育援助投入为平均每年1.813亿美元,仅占年均教育援助投入额的4.3%,约2/3来自多边机构,且整体上逐年下降,其中32%被分配到低收入国家(生均0.87美元),57%被分配到中低等收入国家(生均0.99美元)[11]。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专注于中等后及职业教育的援助取得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反而陷入“失去的十年”,许多发展中国家暴露出了适龄儿童受教育比例低、成人文盲率高等一系列教育问题。此后,国际上开始认识到基础教育的重要性。1990年3月,在泰国宗滴恩举行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全民教育思想,旨在使每个人都能获得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随后,20世纪90年代的基础教育援助投入出现些许增长。双边教育援助中的基础教育援助占比从1993-1996年的约19%增至1997-2000年的约21%。多边援助方面,世界银行教育援助投入中的基础教育援助占比从1990-1993年的约24%增至1994-1997年的约34%,但在1998-2001年间降低到32%。③[12]
自《达喀尔行动纲领》发布以来,基础教育援助投入的发展是较为乐观的。由图2可知,2002-2014年间基础教育援助支出占比大体稳定在40%~44%,年平均占比约为41.8%。此外,2001年的基础教育援助投入水平相对2000年有着小幅增加,2002年的基础教育援助投入水平与2001年相当[13][14]。2003-2014年的基础教育援助年均支出额约为50亿美元,较之2002年的29亿美元有大幅提升。由此也可以看出这种投入倾向使得基础教育援助投入量显著上升。全球范围内的基础教育援助致力于确保人人获得教育,同时有研究表明“对于低收入国家,初等教育援助可以促进其经济增长,而中高等教育援助对其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15]。显然,国际社会在21世纪肯定了基础教育对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提高了基础教育援助在实践中的优先性。
二、国际教育援助投入的主要问题
虽然国际教育援助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我们仍不能忽视:预估2015年有45%的国家(数据可查)的学前教育毛入学率较低或非常低[16];仍有5700万初等教育适龄儿童失学;仍有1.03亿青年文盲[17]。若不认清并及时解决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存在的主要问题,则难以促进上述问题的解决。
(一)国际教育援助投入量的问题
虽然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及基础教育援助投入在2000年后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援助投入量仍不足以帮助全球摆脱教育危机和实现预期的教育标。
其一,国际教育援助投入量整体不足。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教育援助投入水平虽不是很高,但年均投入额占援助总额的9.2%[18]。相比之下,虽然自《达喀尔行动纲领》发布以来的国际教育援助投入显著提升,但教育援助协定投入在整个社会部门援助中所占比例在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前后几乎没有变化,同时教育援助在援助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在2000-2010年间从未超过10%[19]。由此看来,国际教育援助投入似乎只是随着ODA总额的增加而增加,国际社会并未从根本上认识到教育援助的重要性,教育援助投入量也并未取得根本性增长。这一问题也使我们注意到,自《达喀尔行动纲领》发布以来,鲜有援助方能够按时按量地严格拨付他们承诺的教育援助投入。
其二,基础教育援助投入量不足。《达喀尔行动纲领》估计,实现全民教育目标每年大约需要80亿美元[20];《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保守估计,2005-2015年在所有国家实现UPE每年至少需要90亿美元,若要同时实现全民教育的其他目标则每年至少需要110亿美元(2003年价格)[21]。虽然自《达喀尔行动纲领》发布以来的基础教育援助支出额有所增加,但与上述估值相比仍有很大的资金缺口,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则可以说是相差甚远。
其三,从国际教育援助投入量的走势上来看,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以来的教育援助和基础教育援助投入大体呈上升趋势,但2010年后出于全球经济衰退与援助疲劳等原因,两者都整体走低。在实现全球UPE的冲刺阶段,这一正需要大量援助投入的时间段,国际教育援助的表现无法让各方满意。虽然增加援助投入并不能与教育成功直接关联在一起,但长期的供资不足无益于教育取得成功[22]。因此,在教育援助投入缺乏以及国际上接连制定理想化的全球教育治理目标的背景下,国际教育援助很难顺利地完成它的使命。
(二)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分配的问题
在援助分配方面,《达喀尔行动纲领》提出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资助,优先考虑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最不发达国家,同时必须向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和危机后的国家提供支持等倡议。但就国际教育援助投入的發展历程来看,援助投入分配中仍存在诸多问题。
在国际层面上,一是各级教育分配中的问题。由图2可以看出,虽然2002-2014年间的基础教育援助在教育援助总支出中的占比一直处于主要位置,但实际上这些投入几乎全部流向初等教育(如2010年为92%),以致于基础教育的其他领域未能获得充足的资金。此外,多数援助方依旧更为关注中等后教育,而只有少数援助方较为重视中等教育,这直接导致两者在援助投入上的差距。2002-2010年间的中等后教育援助支出为每年平均45.2亿美元,而中等教育仅为16.2亿美元(2010年不变价格)。二是各类教育分配中的问题。援助方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了正规教育上,而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特殊儿童教育等极少能够获得国际教育援助的大额资助[23][24]。三是分配地区的问题。世界上的大部分失学儿童生活在最贫穷与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但划拨给这些地区的援助投入量并不理想。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统计可以最直接地反映这一问题,虽然世界一半以上的失学儿童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但2002-2012年间投入到这一地区的基础教育援助投入平均占比仅为31%,年增长率也仅为1%。此外,教育援助在人道主义援助中也仍未受到足够关注,2000-2013年间教育援助在人道主义援助中的平均占比仅为2.2%。[25][26]
在国家层面上,一是投入分配问题。虽然全民教育高级小组建议各国每年将4%~6%的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投入到教育,即政府预算的15%~20%,但2012年低收入国家中教育投入在GNP中占比的中位数为4%,2012年教育在公共支出中占比的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3.7%。二是各级教育分配中的问题。国际层面的倾向反映在了国家层面中,2012年学前教育在公共教育支出占比的世界水平只达到了4.9%,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则仅占0.3%,大部分公共教育支出被分配到了初等和中等后教育。同时,公共教育支出中的大部分被用于教师工资,以致教育部门的其他领域只能获得有限资金,如在2012年37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数据可查)中,教师工资在初等教育支出中平均占82%,而在2012年36个国家(数据可查)中教科书及其他教育材料的投入在初等教育预算中的平均占比不到2%[27]。可以看出,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分配到国家层面后仍存在分配上的问题。
(三)国际教育援助投入有效性的问题
有效性一直是国际教育援助的重要议题。《达喀尔行动纲领》明确提出国际社会应开展全球性活动,制定有效战略,以增加教育援助投入,确保援助投入可预见性,加强援助方有效协调等倡议。在国际教育援助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提升援助投入有效性(或增加有效教育援助投入)被看作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实际上,针对援助有效性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在国际层面上,一是全球协作框架中的问题。虽然国际范围内都认识到如果各援助方能够基于一个有效的协作框架行动,那么简化的教育援助程序以及一致的教育援助目标等优势将会使援助投入更有效地应对教育危机并取得成果。但从2000年以来多边援助投入减少的趋势来看,国际教育援助仍缺少一个稳定有效的协作框架[28][29]。二是教育伙伴关系中的问题。虽然在2002年基于FTI建立的全球教育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GPE)给受援方带来了大量有针对性的教育援助投入。但由于GPE主要由世界银行严格监管以及FTI最初主要重视UPE等原因,GPE在实施过程中显露出了对受援方来说支付率低,对援助方来说参与困难、援助投入分配单一等问题[30]。三是援助目标中的问题。多数援助方依旧将自身的援助目标置于受援方目标之前,并时常不能与其优先发展目标或国家整体发展规划相一致。同时,基于援助方目标的教育援助更多地关注援助投入所取得的最终成果,而较少能够真正关注到援助投入是否能使学生受益。[31][32]
在国家层面上,低收入国家中,腐败仍旧是影响教育援助投入在国家层面有效应用的重要问题。同时腐败问题不仅影响着实际的公共教育支出,而且影响着国际上众多援助方的热情与信任。另一个问题是教育援助投入的可预见性低,当受援方不能及时预见实际投入与投入预算之间的差距、资金拨放时效等问题时,便不能及时对预定计划进行调整,进而降低公共教育支出的有效性。此外,国际层面基于成果的援助在国家层面上也显露出问题。某些受援方为达成援助方的目标而获得充足教育援助投入和持续资助,在教育成果上易倾向急于求成或数据造假。如此一来,当教育援助投入下放到各地区和学校层面时,学生也往往未能受益。[33][34][35]
三、国际教育援助投入面临的挑战
2014年5月,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的全球全民教育会议上确立了2015年后教育议程,同时提出“确保到2030年实现公平、全纳的优质教育及全民终身学习”和七项具体目标,会上通过的《马斯喀特共识》强调“完全实现2015年后教育议程需要一个来自政府和援助方的强大承诺来为教育分配足够的、平等的和有效的资金”[36]。同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教育全球会议上出台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全球行动计划的路线图》,该计划明确了未来10年内全球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努力方向,并在资源配置上“鼓励利益相关者通过利用有关教育及可持续发展的现有筹资机制及机会,为他们的倡議寻找筹资机会”[37]。在2015年后教育议程及可持续发展教育全球行动计划的铺垫下,在全民教育及千年发展目标的收官年,国际社会开始着手部署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4,SDG4)。2015年5月,在韩国仁川举办的世界教育论坛上颁布了《仁川宣言》,明确了至2030年的全球教育发展目标,并声明国际社会将继续为未完成的全民教育目标努力。此外宣言中强调“如果在资金投入上没有显著且具有针对性的增长,SDG4的愿景将无法实现,尤其是在那些各层次都远未实现优质教育的国家中”[38]。在同年7月举办的奥斯陆全球教育发展峰会和亚的斯亚贝巴国际发展筹资问题会议上,与会代表们强调为达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应优先增加教育投入。9月,联合国峰会正式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确立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教育作为第四项目标位列其中。基于这些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后,于11月通过了“教育2030行动框架”,进一步明确了“确保到2030年实现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并促进全民获得终身学习机会”的目标及基本行动框架。
教育2030议程(Education 2030 Agenda)总结了全民教育目标和千年教育发展目标的成就与经验,并将未竟的事业纳入其中继续努力。新一轮SDG4的实现无疑成为今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各类国际会议及倡议也强调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在未来全球教育行动中的重要性。回望过去,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仍存在一定问题。展望未来,全球教育治理持续加速并怀揣更高的理想,国际教育援助投入也将面临众多的挑战。
(一)国际教育援助投入量需更显著地提升
同全民教育目标及千年教育发展目标相比,SDG4站在可持续发展观和终身教育理念基础之上将“全纳、公平和优质”的教育目标覆盖到了更多的教育层次,教育将帮助更广泛的群体并承担更多责任。一方面,国际社会向着可持续发展的全民终身教育目标的跨越是全球教育治理理念与实践进步的表现,同时将教育列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也说明了国际上肯定了教育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SDG4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受教育人群和教育层次,这一目标中无疑涵盖了各级各类教育的基础设施、教育质量、教学环境及用具、教师培养及发展等多方面的综合发展。因此,SDG4对国际援助投入的需求量也将远高于过去。对于全球范围内的援助方来说,这必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此外,在援助方探索满足愿景中需求的教育援助投入量的途径时,如何确保在经济波动、援助疲劳等因素的影响下能够稳定、持续地向受援方拨款和严格拨付协定投入也是将要面临的一个挑战。
(二)国际教育援助投入需更合理地分配
首先,基于SDG4的特征,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在进行分配时,各援助方不能再只着重考虑基础教育对援助投入的紧迫需求。在分配投入时,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终身教育等都将被加以审思和规划。因此,更合理地将教育援助投入分配到各级各类教育必须经过各方的深思熟虑,这将是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分配面临的一个首要挑战。其次,从教育援助投入的发展历程来看,大部分的援助投入往往没有被划拨到相对更加迫切需要国际资助的国家、地区和群体之中。因此,援助方在未来如何抛开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因素来根据全球教育发展版图规划援助投入分配,以及如何建立和实施国际互联的教育援助投入分配协调机制来促进全球教育可持续发展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最后,一个最基础的挑战是,援助方与受援方必须重视监管和调控国际教育援助投入下放到国家层面时的分配、教育预算与实际教育支出是否有出入、教育支出是否被分配到使学生最受惠的方面。
(三)国际教育援助投入需更有效地使用
自《蒙特雷共识》和《巴黎援助有效性宣言》达成和签署以来,“有效援助”历经了数届援助有效性论坛及会议的讨论和完善,一直是国际援助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所必须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实现SDG4所需的教育援助投入量无疑是巨大的,以往单是全民教育目标的需求,国际社会都未能完全满足,因此完全满足SDG4需求的援助投入未免是不现实的。有限的資源是驱动人们关注援助有效性的重要因素[39],增加有效的教育援助投入将成为最主要的问题解决方式之一,这也是国际教育援助投入不可避免的挑战。援助有效性在实践层面涉及有效地开展援助及有效地达成援助目标[40]。各援助方亟需建立稳定有效的全球教育协作框架并改善GPE,同时加强和发展与受援方的联系,以进一步改善援助方之间及援助方与受援方之间的协作关系。受援方也需做好迎接面向SDG4的援助投入的准备,巩固国家组织规划、财政、反腐等系统。此外,援助方与受援方需加强对援助目标及有效性的认识、构建灵活的评价机制、明确责任分配。这些都是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在迎接有效性挑战时必须面对和积极着手解决的复杂工作。
四、对我国实施对外教育援助的启示
我国历来重视对外援助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发展也逐步增速,并在近年来与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国一同被称为“新兴援助国家”[41],国际社会也对中国等新兴援助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中的表现满怀期望。而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SDG4具有很高的优先性,并对其他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起到促进作用,正如《21世纪议程》中所言“教育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能力的关键”[42]。因此,在未来的国际教育援助工作中,我国需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发挥更大的教育治理作用。回顾国际教育援助投入的主要进展与问题,以及预测其今后在教育2030议程中的挑战,给我国对外教育援助工作参与全球教育2030议程带来几点启示。
首先,我国需全面把握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发展态势,着力发挥我国对外教育援助投入实力。从国际教育援助投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社会在投入层面的努力一直难以满足全球教育治理与开发的需求。许多地区的援助投入资金持续处于短缺状态,尤其是当全球出现较大经济波动时,某些援助方都屡次出现财政赤字。而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较强的抗经济风险能力以及稳固的经济发展体系,因此我国可以着力发挥经济优势以合理地增加对外教育援助投入。尤其是在实现SDG4的进程中,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受援方需要更广泛和实质性增长的教育援助投入的情况之下,我国更需在全面把握国际教育援助投入态势的基础上,在一定范围内增加对外教育援助投入,以更好地融入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努力之中。借此,一方面,可以促进更多贫困国家的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实实在在地助力更多人走出贫困和边缘;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提升我国在国际教育援助领域的地位、展示我国经济实力、建立积极的对外援助形象及立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其次,我国需厘清全球教育治理版图,合理分配我国对外教育援助投入。从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分配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教育援助往往很难切实帮助到最需要教育资助的国家、地区、部门、群体等。因此,我国需要更为关注全球教育发展大数据以及全球教育发展动态,同时也要着重注意全球范围内的典型教育危机,以准确地把握全球教育治理的重难点。在完成满足国家利益的对外教育援助投入分配的基础上,预算内的其他对外教育援助投入应基于全球教育治理版图更合理地分配。而在实现SDG4的进程中,国际教育援助投入分配无疑将面临复杂的挑战。我国需与受援方建立国家层面分配教育援助投入所需的监管机制,确保教育援助投入顺利、准确的分配。同时我国也需主动与各援助方建立国际层面援助投入分配协调机制,避免对外教育援助投入分配重复或遗漏,推进全球教育协调发展。
最后,我国需主动参与国际教育援助协作,综合提升我国对外教育援助投入有效性。从国际教育援助投入有效性的发展历程来看,援助方与援助方之间及援助方与受援方之间的协作水平影响着国际教育援助投入的有效性。而我国作为新兴援助国,受援方数量有限,同时我国的教育对外援助方式与投入并未与国际充分接轨,以致国际层面难以对我国对外教育援助工作准确统计或有效统一协作。因此,我国需主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积极参与有关教育援助协作的沟通与商榷。同时,我国需基于以往在援非进程中建立合作关系的经验,与更广泛的受援方建立教育援助协作关系。此外,国际教育援助有效性未能得以迅速取得全面成功,与援助方中从事相关研究和实践的人员较少、水平及专业能力参差不齐有一定关系。因此,我国亟需加强国际援助及国际教育援助领域的研究,从本质上提升我国外援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水平。一方面,我国可以与其他援助方更为顺利地通力协作,更有效地制定援助投入预算、援助实施方案等;另一方面,教育援助研究水平的提升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发现和理解援助有效性问题,并获得解决方案。
注釋:
①IDA及IBRD(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是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多边援助的主要机构。
②文中“基础教育”采用DAC做出的定义,包括:儿童早期教育、初等教育、青年和成人的基本生活技能教育。
③这里没有给出具体的投入数值,是由于当时各国家、地区及组织对“基础教育”的定义不同,教育援助很多是跨子部门的,关于教育援助的详细分配报告稀缺等,导致有关基础教育援助的信息较难获得。
参考文献:
[1]王晓辉.全球教育治理——国际教育改革文献汇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36-40.
[2]United Nations. Monterrey Consensus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Z].Monterrey: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2002.
[3]菲利普·库姆斯.世界教育危机[M].赵宝恒,李环,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97-328.
[4]World Bank. Priorities and Strategies for Education:A World Bank Review[R].Washington D.C.:World Bank,1995.
[5]赵玉池.国际教育援助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J].外国教育研究,2013,40(5):80-84.
[6][11][18]Marlaine E. Lockheed,Adriaan M. Verspoor,et al. Improving Primary Education in Development Counties[R].Washington D.C.:World Bank,1991.
[7][12]UNESCO.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2-Education for All: Is the World on Track?[R].Paris:UNESCO,2002.
[8][13]UNESCO. 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3/4-Gender and Education for All:The Leap to Equality[R].Paris:UNESCO,2003.
[9][14]UNESCO. 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5-Education for All-The Quality Imperative[R].Paris:UNESCO,2004.
[10]UNESCO.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6-Education for People and Planet:Creating Sustainable Futures for All[R].Paris: UNESCO,2016.
[15]Elizabeth Asiedu,Boaz Nandwa. On the Impact of Foreign Aid in Education on Growth:How Relevant Is the Heterogeneity of Aid Flows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Aid Recipients?[J].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07,143(4):646.
[16][25][27][28][30][31][33]UNESCO. 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5-Education for All 2000-2015: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R].Paris:UNESCO,2015.
[17]United Nations.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R].New York:United Nations,2015.
[19]OECD-DAC.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atistics:Creditor Reporting System[R]. Pari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4.
[20]UNESCO. The Dakar Framework for Action-Education for All:Meeting our Collective Commitments[Z].Dakar:World Education Forum,2000.
[21]UNESCO. 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7-Strong Foundations: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R].Paris:UNESCO,2006.
[22]UNESCO. 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1-The Hidden Crisis:Armed Conflict and Education[R].Paris:UNESCO,2011.
[23][32][34]UNESCO. 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2-Youth and Skills:Putting Education to Work[R].Paris:UNESCO,2012.
[24]亚伦·贝纳沃特,等.全民教育(2000-2015年):全球干预和援助对全民教育成就的影响[J].张惠,译.比较教育研究,2016(4):57.
[26][29][35]UNESCO. 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0-Reaching the Marginalized[R].Paris:UNESCO,2010.
[36]UNESCO. 2014 GEM Final Statement:The Muscat Agreement[Z].Oman:Global Education for All Meeting,2014.
[37]UNESCO. Roadmap for Implementing the Global Action Programme o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Z].Paris:UNESCO,2014.
[38]UNESCO. Education 2030:Incheon Declaration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4-Ensure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Quality Education and Promote Lifelo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Z].Paris:The 38th Session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UNESCO,2015.
[39]Desmond Bermingham,Olav Rex Christensen,Timo Casjen Mahn. Aid Effectiveness in Education:Why It Matters[J].Prospects:Quarterly Review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2009,39(2):133.
[40]胡小嬌.国际教育援助及其效果的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8.
[41]刘鸿武,黄梅波,等.中国对外援助与国际责任的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05-206.
[42]United Nations. Agenda 21[Z].Rio: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1992.
编辑 朱婷婷 校对 王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