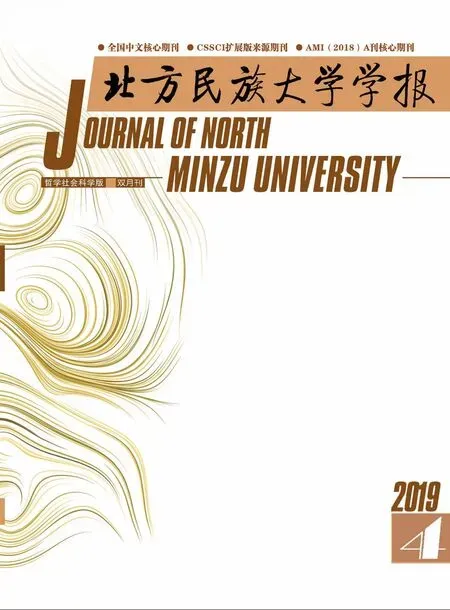东乡族历史研究现状综论
2019-08-08陈文祥
陈文祥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
学术界对我国东乡族的研究主要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开始的,以此为起点,东乡族各方面的学术研究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东乡族研究从早期较为单一的语言、族源和宗教研究,扩展到了人口、教育、经济、文化、健康、基因和体质等众多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时至今日,有关东乡族的学术研究整体上已具备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但是,综观当前东乡族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医学和遗传学、文化、教育、经济等现代社会问题研究面向上,而东乡族历史领域的研究尚属薄弱环节,笔者在中国知网及其他各类数据库中检索1957年至2018年间发表的题名或主题中包含关键词“东乡族”的学术论文,得到相关度较高的文章610篇,其研究领域整体分布比例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到,在东乡族相关学术研究论文中,前三项研究领域贡献了超过一半的研究论文,而涉及东乡族历史的文章(包括族源、人物、宗教等领域内的历史类文章)综合比例不到10%,且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东乡族历史相关研究成果中,高质量的研究性成果更属凤毛麟角。此外,这些论文多发表于2008年之前,这意味着有关东乡族历史的研究2008~2018年来已步入学术研究低迷期[注]此前,马虎成(《东乡族族源研究综述》,《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马自祥(《东乡族史研究纵述》,《民族研究动态》1994年第3期)、马亚萍(《20年来东乡族研究述评》,《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陈文祥(《东乡族研究现状及其前景展望》,《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4期)、杨文笔(《近十年(2005~2015)东乡族研究回顾》,《民族艺林》2016年第1期)以及安守春(《东乡族研究现状概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等人对东乡族历史研究状况做过一些梳理,但马虎成、马自祥等人的综述已略显陈旧,难以反映当前状况,而其他几篇研究综述着眼于东乡族研究的整体状况,其中对东乡族历史研究的梳理不够全面和深入。。故推进和强化作为东乡族研究之瓶颈和薄弱环节的历史领域的研究,已成为当前东乡族研究各领域均衡发展、并取得长足进步的必然要求和可以预见的趋势。当然,后续研究必须立足于现有基础之上,故对东乡族历史研究现状做全面梳理就凸显其必要性。

图1:东乡族研究领域整体分布比例图
一、东乡族历史研究的肇始与奠基
历史上,东乡族多强调宗教认同,而民族意识比较淡薄,故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自认为和被认为属于“回回”(甚至回族)而非一个少数民族,而有关东乡族的历史史料亦因此多混同在回族史料中,难以区分。比较明确的关于东乡族的文献资料极少,往往只能通过文献中“东乡回”“东乡土人”等具有明确指向性的称谓加以辨识,故与东乡族历史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一直少有人涉及。
国内外学术界对东乡族历史的考察,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1906~1908年受俄国总参谋部指派,马达汉对中国西部地区进行了军事考察,在此期间,他接触了东乡族,并对其历史有所认识,他认为东乡族属于从中亚迁徙过来的部族,是古代回纥的后裔[1](149)。民国十九年(1930年)勘定的《和政县志》对东乡族来源的解释是“即畏吾尔之裔或系蒙古之奉回教者”[2](443)。而美国传教士毕敬士也是较早对外介绍东乡族的人,1933年,他在东乡族地区做伊斯兰教调查及传教过程中接触到了东乡族,并留下了一些有关东乡族的珍贵照片,他认为东乡族是蒙古人的后裔[3]。此后,一些国内学者在西北地区进行游历考察时,亦惊异地发现河州东乡族地区生活着一个具有鲜明文化异质性特征的人群,即后来认定的东乡族。他们通过访问和考察,对东乡族的来源及宗教信仰问题做了初步了解,仍多认为东乡族源于蒙古人,只是信仰了伊斯兰教[注]如黎小苏(《青海之民族状况》,《新亚细亚》1934年第2期)、马鹤天(《赴藏日记》,《新亚细亚》1936年12卷2期)、李安宅(《论回教非即回族》,《新西北月刊》1939年2卷1期)、白云(《西北回教问题》,《西北论坛》1940年8卷23期)、吴景敖(《清代河湟诸役纪要》,《新中华》1943年(复刊)1卷5期)、黄文弼(其观点被引用于《西北通讯》1946年2卷8期)、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西北通讯》1947年1卷1期)、幼轩(《甘肃民国日报》1947年8月28)、马兹廓(《穆斯林在临夏》,《西北通讯》1948年3卷1期)等。。尽管以上这些学者对东乡族的描述和说明多一笔带过,观点亦多停留在问题表层而未深入,且缺乏后续研究,但仍不失为东乡族历史考察之肇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为了理清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了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起,又进行了少数民族语言和社会历史调查。在这几次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起开始组织专家编写“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直到1991年才基本完成。其中,除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专论民族语言外,其他四种丛书都涉及各民族的历史问题,成为研究各民族历史最为宝贵的基础材料。东乡族历史的研究也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为初步了解东乡族历史,1953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委派部分学者到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开展了第一次东乡族社会历史调查。在此基础上,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甘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成立,其中就有东乡族社会历史调查小组。该小组通过对东乡族自治县、临夏、和政等东乡族主要分布区域的全面调查,结合各类历史文献及档案资料,完成了一份《东乡族调查资料汇集》和一本《东乡族简史简志(合编)》,前者主要包括《东乡族经济发展简况》《清代以来东乡社会经济的发展》《民国时期东乡经济情况调查报告》《元明以来东乡政治情况》《东乡人民的反清斗争》《东乡族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东乡族语言情况调查报告》《伊斯兰教在东乡的一般情况》《东乡族生活习俗》等内容;后者则包括东乡族概况、历史简述,以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乡族政治、经济发展情况的介绍[4](545~546)。这两份研究资料是对东乡族社会历史首次展开全面调查的初步成果,大致确立了东乡族历史研究的基本脉络,影响深远。此后整理出版的《东乡族社会历史调查》(收于《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社会历史调查》)和《东乡族简史》就是在这两份研究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学者们的进一步完善而成的,而这两部公开出版的著作更为此后东乡族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注]尽管《东乡族简史》《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社会历史调查》正式出版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但由于其主要内容都完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故本文仍将其视为东乡族历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其中,《东乡族简史》是全面论述东乡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第一部专著,它从历史学角度对东乡族的族源展开了全面的梳理和论证,并对明清以来东乡族的社会经济、反抗斗争、重要人物、宗教状况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还对东乡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民俗文化、民间文学和文教卫生做了介绍。《东乡族简史》影响极为深远,多年来,有关东乡族的介绍、宣传内容多出自此书,相关的学术研究更绕不开它,但囿于史料和时代背景,《东乡族简史》的内容过于简略,缺乏深入的学术探索和讨论,尽管2008年出版的修订本更新了很多观点,补充了一些新内容,但因其“基本保持原貌”的修订原则及其固有的“简史”特征,而未能完全弥补此缺憾。
《东乡族社会历史调查》主要由三部分调查报告构成,其中前两部分资料来自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调查:第一部分资料是1953年中央民族学院甘青地区民族调查组在东乡族地区进行调查后所写的调查报告;第二份资料是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的甘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东乡族分组所写的调查报告[5](115)。这一调查资料成为我们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东乡族社会经济、政治概貌、宗教信仰、文化礼俗、教育状况等方面内容的最为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尤其是社会经济方面的调查资料数据最为丰富,目前,学术界对这些资料的利用和研究还很不足。当然,受当时政治形势、历史条件限制,此调查资料中也存在部分资料不准确、不全面的不足。
总而言之,东乡族历史的研究之门微启于民国时期,让人们对东乡族有了一定的认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的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明确了东乡族作为我国的一个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正式开启了东乡族历史研究的大门;而此后完成的东乡族社会历史调查成果《东乡族调查资料汇集》和《东乡族简史简志(合编)》,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版的《东乡族简史》和《东乡族社会历史调查》作为东乡族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定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
二、东乡族历史研究的勃兴与突破
改革开放后,随着各领域学术研究的复兴,之前受政治运动影响而一直被搁置的“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的编写工作再次被提上议程,东乡族历史的研究亦趁此东风开始高涨起来,并首先在族源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突破,继而在其他诸多历史研究领域也有开创性的成果问世。
(一)东乡族族源研究的勃兴与突破
1980年7月,甘肃省民委为编写《东乡族简史》而组织学者及部分干部召开了一次讨论会,此次会议的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东乡族族源问题上。此时,部分东乡族学者和干部对本民族的族源已经有了新的思考和判断,他们对此前在学术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东乡族族源“蒙古人为主说”提出了质疑和批判。经过激烈的讨论及多方沟通,《东乡族简史》的最终文本在省委主管部门领导批示的“尊重本民族意愿”的基本原则下,放弃了原文中主张的东乡族族源“蒙古人为主说”,而采用了较为折中的表述,“东乡族是……回回人、蒙古人、汉人以及藏族人共同融合而成的。在他的形成过程中,使用蒙古语的那部分回回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那部分蒙古人起着主导的作用”[6](26),强调了回回色目人在东乡族形成中的重要影响。
但这次关于东乡族族源的讨论并未因《东乡族简史》的观点而盖棺论定。讨论会后,马通先生率先在《甘肃民族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浅谈东乡族族源与伊斯兰教》一文,强调东乡族族源中“有中亚人居多数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蒙、回、汉等族的成分”[7]。此后,曾参与过东乡族族源大讨论的马国忠先生和马自祥先生亦联名发表了《关于东乡族族源问题》一文,进一步论证东乡族的主要来源是“成吉思汗或其后人西征时俘获或征集的中亚西亚一带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工匠”,现在的东乡族是他们后来“逐渐融合了当地汉族、回族、藏族而形成的”[8]。几乎同时,持东乡族族源“蒙古人为主说”的杨建新先生也发表了《关于东乡族的族源和形成》一文,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他认可东乡族是由居于东乡族地区的多种民族成分逐渐融合而成的,但坚持认为在其中“占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的,首先是蒙古人”[9]。在这两种观点的交锋中,最初“蒙古人为主说”占据上风,在其影响下,国内的一些重要辞书、科普性读物、民族介绍作品等都采纳了这种观点,甚至费孝通先生在其作品中也持东乡族族源“蒙古人为主说”[10](178~179),足见其影响之大,但随着此后东乡族学者们提出的东乡族族源“撒尔塔说”的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这一学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仍坚持“蒙古人为主说”的学者已经不多了。
东乡族族源“撒尔塔说”的提出是东乡族历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这是东乡族学者在本民族族源研究中的第一次正式发声。最早将“撒尔塔”概念引入东乡族族源研究的是东乡族学者马国忠和马自祥的《关于东乡族族源问题》一文,但该文引入这个词是为辅助说明东乡族族源的“回回色目人说”,而不是用以证明它同东乡族族源的直接关系。很快,马志勇在其长文《“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中正式提出这一观点,主张“撒尔塔人是东乡民族形成的主要因素”[11],此后,他在《撒尔塔考辨》一文中又对“撒尔塔”一词做了进一步考证,补充说明了“撒尔塔人在东乡族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具有合理性[12]。但马志勇的观点在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和关注,故未产生大的社会影响。这一观点沉寂近十年后,马虎成旧论重提,在马志勇这两篇论文的基础上,先以“撒尔塔说”为观点撰写了《甘肃民族源流》一书中的东乡族族源部分[13],紧接着发表了《撒尔塔:一个曾经被忽略的民族名称——也谈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一文。马虎成的文章运用历史学、语言学、地理学、遗传基因学等多学科知识对东乡族族源“撒尔塔说”做了更加全面和翔实的论证[14],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甚至荣获甘肃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此后,学术界渐渐认识和接受了这一观点。2004年,马志勇将与东乡族族源“撒尔塔说”相关的数篇论文整合为《东乡族源》一书出版,该书是对多年来东乡族族源研究的一次大总结,全书编排虽略显粗糙,文字错讹也比较多,但瑕不掩瑜,全面论证和构建了东乡族族源之“撒尔塔说”[15]。目前,这一观点已经成为东乡族族源学说的主流观点。当然,也有研究者对东乡族族源“撒尔塔说”的论证过程提出质疑,认为其赖以立论的三个核心论点均存在论证不足的问题,而且指出其所使用的现代遗传学资料也存在问题,认为“撒尔塔说”尚需更加严密、科学的论证,否则难以让人服膺,学者们此前提出的东乡族族源“回回色目人说”更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16]。
在这一阶段,还有很多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东乡族族源的相关问题,例如,何锁南普的族属及其同东乡族的关系问题、从群体遗传的DNA线索考察东乡族族源、东乡族族源研究中跨学科方法应用的误区、东乡族族源中的藏族成分等[注]如,舍力甫《何锁南普的族属与东乡族族源问题》(《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马志勇《河州土司何锁南》(《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马效融《河州东乡族源流》(《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94年),马兆熙、唐世明《东乡族马姓渊源》(《甘肃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陈文祥、何生海《少数民族族源研究中跨学科方法应用误区初探——以东乡族研究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陈其斌《东乡族族源中藏族成分的历史考察》(《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王慧婷、赵海军《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东乡唐汪川唐姓群体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这些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对东乡族族源研究提供了思路。但笔者认为对弄清东乡族族源最具启发性的研究是马兆熙先生的《东乡哈木则宗族形成与发展的考察研究》一文,这篇文章跳出传统族源考证的窠臼,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对哈木则宗族的来龙去脉、发展变迁做了详细的挖掘[17],为我们探索东乡族族源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可能路径。因为东乡族整体上是由十多个较大和数十个较小的宗族构成,弄清了这些宗族的来源,东乡族的族源自然拨云见日,如果我们循着这样的研究思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调查研究,对弄清楚东乡族的族源和发展历程会很有意义。
(二)东乡族历史研究其他领域的突破
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东乡族历史的研究并未局限在族源研究上,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新的发展和突破,甚至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
第一,东乡族历史人物研究的发展。在东乡族历史人物中,备受学术界关注的是中国伊斯兰教伊赫瓦尼派的开创者马万福,先后有马通、马克勋、奥斯曼、马自祥、晓夫、马文选、马全龙、马文学、樊前锋、马晓旭、张嵘等众多研究者撰文介绍这一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东乡族人物[注]马自祥《马万福》(《西北民族历史人物选介》,1983年);晓夫《果园哈智——马万福》(《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9年);其他人的研究成果都被收入海默汇编的《果园哈志与伊赫瓦尼研究论集》(内部交流,蓝月出版社,2015年),不再赘列。。在这些文章中,马克勋的论文资料最为翔实,他通过访问马万福的亲属及一些知情人,获取了大量有关马万福生平经历的珍贵口述资料,颇有学术价值;而马晓旭的《马万福宗教思想探析》作为第一篇专论马万福思想的硕士学位论文,也具有一定价值,可资参考。
在东乡族其他历史人物的研究中,马志勇先生用力最勤、成果最丰,他史海钩沉,使很多原不为人们所知的东乡族历史人物被挖掘出来,他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史话》《东乡族史话》等作品中较全面地介绍了几十位东乡族历史人物,还对其中的一些人物做了深入研究,如他不仅证实了妥明(妥得璘)的东乡族身份,还指出他在反对外来侵略和维护国家统一方面的重要贡献[注]马志勇《反压迫反侵略的东乡族英雄妥得璘》(《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吴万善此前也曾发表过《论妥得璘》(《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一文,且亦着眼于平反学术界对妥得璘的负面评价,马志勇的观点同此文基本一致,但吴万善在该文中认为妥得璘是回族历史人物。。目前,学术界引述的有关东乡族历史人物的文本,大都出自马志勇先生手笔。
整体来看,当前东乡族历史人物研究的参与者太少,成果显得极其不足,除马万福较受关注、相关成果较多外,专论妥明(妥得璘)的研究性文章仅有两篇,专论马悟真、闵殿臣等人的研究性文章各仅有一篇[注]马志勇《反压迫反侵略的东乡族英雄妥得璘》(《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吴万善《论妥得璘》(《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马志勇《闵殿臣传》(《甘肃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马自祥《马悟真》(《西北民族历史人物选介》,内部资料,1983年)。,其他专论东乡族历史人物的文章多引述以上成果,缺乏原创性,或者仅仅是简单的介绍性文字。此外,在有关东乡族的方志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的著作中也都会涉及一些重要的东乡族历史人物,如《东乡族自治县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中国伊斯兰教史》等著作都对东乡族历史人物有较为翔实的介绍,是研究东乡族历史人物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总而言之,东乡族历史人物的研究尽管已经开展起来,但当前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太少,相关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还很不够。
第二,东乡族宗教发展史研究的深化。东乡族的形成和发展与伊斯兰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东乡族的宗教状况在其历史研究的肇始和奠基阶段就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改革开放后,相关研究得到了极大深化。这一领域研究中着手最早、贡献最巨者为马通先生,他在1981年率先发表《浅谈东乡族族源与伊斯兰教》一文,简要介绍了东乡族的宗教状况,此后,他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两书对起源于东乡族的伊赫瓦尼派、北庄门宦、胡门门宦、张门门宦等派系的演变发展、道统世系都做了极为详尽的研究[18],还原了其真实的历史发展脉络,此后有关东乡族教派、门宦制度的研究成果多以此张本。杨建新先生也是较早关注东乡族宗教信仰的学者,其《东乡族与伊斯兰教》一文是最早对东乡族伊斯兰教状况及其演变发展趋势做全面、深入分析的学术论文[19]。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有关东乡族宗教发展史的成果不断涌现。马世英《中国伊斯兰教库布忍耶门宦谱系》一书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他在马通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详尽地研究了东乡族库布忍耶(张门)门宦的发展历程及传承谱系[20];高占福、胡青对伊斯兰教在东乡族中的传播、分化及各派系的特点做了全面解析[21];马有禄、汪文明则第一次关注了东乡族经堂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组织特征,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22];马桂芬、赵国军利用大量民间文献和访谈资料对胡门门宦的历史发展做了深入探索,是对马通先生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23];此外,《东乡族自治县志》对东乡族宗教发展历史也有一定的介绍和分析,但略显简略;汪文明、马志勇、杨光荣、陈国光等人也发表了与东乡族伊斯兰教发展相关的研究成果[注]汪文明、马志勇《东乡族的宗教信仰》(《中国东乡族》,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杨光荣《玉门市小金湾东乡族宗教生活调查》(《甘肃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陈国光《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宗教信仰述略》(《新疆社会经济》,2000年第3期)。。总体来说,这一阶段对东乡族宗教发展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整体数量仍然偏少,且存在高质量、有创新性成果不多的问题。
第三,新疆东乡族社会历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新疆是仅次于甘肃的东乡族第二大聚居区,但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新疆东乡族的认知和研究是空白的。1984年,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率先对生活在新疆的东乡族做了一次全面调查,开创了东乡族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这次调查的主要成果是三篇学术论文[注]曾和平《东乡族移民迁移新疆情况调查》(《民族理论研究通讯》,1985年第2期);苗剑新《新疆伊犁地区东乡族的婚姻家庭问题》(《西北人口》,1985年第4期);赵同起《新疆东乡族人口结构状况》(《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分别从东乡族向新疆的整体迁移情况、婚姻家庭问题和人口结构三方面做了研究,这三篇开创性的论文后来均被收入《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此后十年,学术界再无关于新疆东乡族的研究成果问世,直到2005年,笔者发表了《1950年后东乡族移居新疆原因探析》一文,对1950年后甘肃东乡族迁往新疆的历史原因做了深入的探讨[24],接着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东乡族移居新疆的特点和影响做了阐释[25],后又发文对新疆东乡族的语言使用历史变迁状况做了全面调研分析[26],而马秀萍亦对东乡族移居新疆的原因及趋势做了进一步的研究[27]。
第四,东乡族宗族发展史研究的深入。宗族制度在东乡族发展中影响重大,是研究东乡族历史的重要突破口,马克勋较早对东乡族“赤斯拉务”家族的发展历史做了初步探索[28],此后,马兆熙先后对东乡唐氏宗族和哈木则宗族的来龙去脉及其发展历史做了深入考察[29][30],刘夏蓓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和访谈,完成了第一部专论东乡族宗族发展史的著作,对东乡族北庄家族的发展历史做了全面的研究[31],而廖杨从宏观上对东乡族宗法制度的特点及形成的历史原因做了分析[32]。但遗憾的是,这一重要历史领域的研究此后再无成果问世。
第五,东乡族婚姻家庭制度历史考察的尝试。部分学者对历史上东乡族婚姻家庭制度较有兴趣,如马文贤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东乡族四种主要的婚姻形态[33],刘夏蓓分析了历史上影响东乡族婚姻家庭观念的五大因素[34]。但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是昙花一现,缺乏研究的延续性。
此外,这一时期在东乡族其他研究领域的部分成果也涉及东乡族历史,如有关东乡族文学、人口、经济、文化及伦理道德等领域的研究,但多浅尝辄止,未做深入探讨,故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陈其斌的《东乡社会研究》虽着眼于研究当代东乡族的社会发展,但其作品中涉及东乡族历史的内容也颇有见地[35],而马自祥先生在开展东乡族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东乡族历史亦多有深入见解和贡献,他整理的东乡族古籍、碑铭资料尤为珍贵,对东乡族历史研究大有裨益[36]。
总体来说,这一阶段是东乡族历史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不仅在传统历史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还开创了一些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并且出版了诸如《东乡族自治县概况》《东乡族自治县志》《东乡五十年》等综合性志书。当然,这一阶段学术研究中存在明显的问题,如学术研究的延续性不强,高水平研究成果过少,参与东乡族历史研究的学者尤其是本民族研究者严重不足等。
三、东乡族历史研究的低迷与蓄势
2008~2018年间是东乡族历史研究新老交替的一个过渡时期,一方面,部分长期关注、研究东乡族历史的学者开始淡出学术研究领域,从而使东乡族历史研究蓬勃发展之势顿缓,进而导致东乡族历史研究逐渐步入低迷期——学术研究成果产出量大为缩减,十年里仅有十余篇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问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十余篇论文的作者均为年轻学者,且普遍拥有硕士、博士学位,尤为重要的是,这十余篇论文大多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体现了对学术理论前沿的关注。
近年来,备受学术界关注的认同理论是很多研究者研究东乡族历史的重要切入点,如这十余篇论文中,就有四篇论文接续前一阶段的研究,继续关注了东乡族唐汪川唐氏宗族的认同问题。其中,王慧婷和赵海军梳理了东乡族唐姓家族群体认同的主要表现形式,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分析了唐汪镇唐姓群体认同产生的原因[37],此后,他又对唐汪人的民族认同及变更民族成分问题做了理论反思,尽管论述较为简略,但对我们认识唐汪人独特的认同意识具有很好的学术启发性[38];崔明的博士论文也是以唐汪人“一个家族,多个民族”的独特群体特征为视角,深入考察了唐汪人在历史记忆、文化差异及利益寻求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是一份比较有深度和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39]。
杨德亮则从田野中的“历史记忆”切入,对历史上东乡哈木则宗族成员内部的互动与宗族的裂变做了翔实的考察,认为哈木则宗族具有同东乡唐氏宗族完全不同的宗族内部关系模式,说明东乡社会宗族的互动与裂变形式具有多样化和情境性特点[40]。阿布都哈德和马琳娜的论文也涉及“历史记忆”,他们认为流传在临夏回族和东乡族之间相互戏谑的民间笑话是族际互动情境下维护和保持各自族群边界的手段[41]。在当前历史研究“碎片化”现象越来越凸显的背景下,整体史观的价值和意义在学术研究中再次受到人们的重视,笔者也以西北回族、东乡族、保安族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为个案,指出这几个民族的历史研究须在整体史观的观照下,摆脱民族中心主义思维,以民族关系史研究为媒介,实现其民族史的综合研究[42]。樊莹通过考察《东乡族简史》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认为其变化体现了从“他者”到“自我”的话语权的转移,是国家与地方、“他者”与“自我”合力作用下的东乡族的自我确证[43]。
这一阶段对新疆东乡族展开研究的学术成果主要是笔者的专著《分化、调适与整合——新疆多民族杂居区东乡族移民文化变迁研究》,本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乡族向新疆的迁移及其文化变迁的历史做了全面的阐释和分析[44]。
生活在宁夏的东乡族一直以来被学术界忽略,杨文笔等人率先对这一群体进行了考察,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从田野中追寻历史——海原县东乡族族群的迁徙历程》一文从历史学角度对海原县东乡族的来源及迁徙历史做了探讨[45]。
学术界对东乡族宗教信仰相关主题的研究始终未中断,马全龙的硕士学位论文《东乡族伊斯兰教历史人物研究:以马伏海、马葆真和马万福为例》是多年来以东乡族宗教历史人物为主题的唯一一篇学位论文[46],尽管论文创新性略显不足,但仍不失为一个好的开始;笔者也对东乡族的形成、发展与伊斯兰教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探讨[47];马秀萍对新疆东乡族经堂教育的发展历史做了简要评介[48]。
此外,刘江荣的硕士学位论文对东乡族自古至今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为今天东乡族经济的发展寻求历史的民族精神依托,当然,该论文将历史上生活在东乡地区的羌人作为东乡族族源之一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49];李百龙的硕士学位论文对东乡族历史研究的现状、成就及史观构建做了一些总结,但整体上缺乏研究深度和学术创新性[50];科敏对东乡族的民族识别过程做了回顾,通过田野调查整理保存了大量有关东乡族民族识别过程的访谈资料,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51]。
2008~2018年间,东乡族历史研究的成果尽管在数量上并不尽如人意,但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体现了相关研究蓄势待发之势:第一,参与研究者均为青年学者,年富力强,即将步入学术产出高峰期;第二,参与研究者多拥有较高的学历,接受过较为严格的学术训练,具备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学术基础;第三,学位论文撰写中,选择东乡族历史研究课题者越来越多。有此三者,足可预见东乡族历史研究在今后必将迎来新的繁荣。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4月,东乡族文化研究会成立,并定期召开学术讨论会,出版学术刊物《中国东乡族》,这必将为中国东乡族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历史机遇。
四、结 语
尽管我国东乡族研究自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这些成就与其人口基数相比,仍然显得极为薄弱,尤其东乡族历史研究的不足和缺陷就更为明显:旧史料重复使用率高,新史料挖掘利用不足;成果产出数量少,高质量成果凤毛麟角;综合论述多,深入精到的专题研究少;零散研究多,系统研究少;参与研究学者寥寥,其中本民族学者更为稀少;等等。
东乡族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它同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因为东乡族历史研究是我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相较学术界对其他各民族历史研究的成就,东乡族历史研究不仅缺乏深厚的前期学术积累,也缺乏充足的研究后劲,甚至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已成为影响和阻碍我国民族史研究全面深入的短板。加强对东乡族历史研究领域的探索,使作为中国民族史重要组成部分的东乡族历史研究深入下去,对促进东乡族历史研究乃至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我们也应看到,如今东乡族已经不是完全被动的“被书写者”,东乡族学术精英们已经开始尝试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获得了学术界的回应和认可。而东乡族文化研究会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东乡族学者的凝聚力,并形成研究合力,让东乡族历史研究能够有规划地开展和深入下去,尽快走出研究低迷期,进入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收获期。
要在东乡族历史研究领域达成这一目标,笔者认为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重视新史料的挖掘和利用。尽管东乡族历史相关的史料数量非常少,但并非没有,更多的可能是我们对东乡族历史史料挖掘不够。其二,再次全面开展东乡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东乡族民间尚有很多未被发掘整理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实物史料、小经文字史料和口传史料,这些都是亟须搜集和整理的。其三,进一步夯实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乘的学术研究作品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就是史料,所以,全面搜集、整理并出版东乡族历史史料集势在必行。其四,提携和培养东乡族历史研究的学术新秀。青年研究者是东乡族历史研究的未来,但在他们的成长中尚有很多不成熟之处,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地提携和培养他们,以使东乡族历史研究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