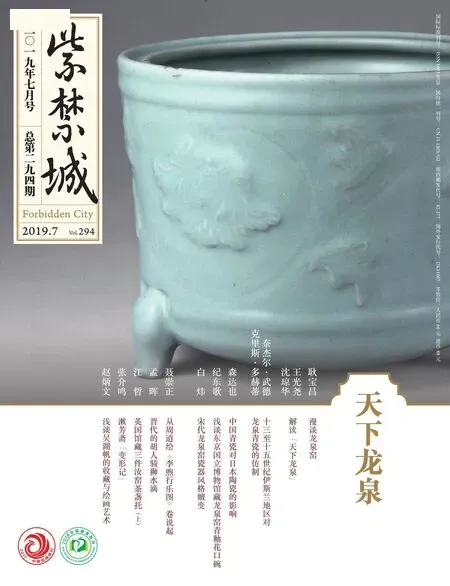晋代的胡人骑狮水滴特稿
2019-08-03孟晖
孟 晖
自由撰稿人。著有长篇小说《盂兰变》,随笔集《维纳斯的明镜》、《潘金莲的发型》、《花间十六声》、《贵妃的红汗》、《画堂香事》等
早在西汉时期的酒会上,就出现了一种器物,它代替舀酒勺,通过一汲一放制造魔术效果,引发在场人的惊奇与开心,其实是利用了压强差的科学原理。
相同的原理应用在文房器用—— 水滴上,精致的构造与艺术化的外形相结合,成为古时案头的日常物件,受到一代代文人的欢迎,存续上千年,堪称设计史中的奇迹。
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的一件「胡人骑狮水滴」,在文物图册中被误会其用途,解释成「胡人骑狮铜烛台」,是个小小的疏忽。
这件青铜制品采用人骑狮子的造型,狮子背上的人物双臂分别向两侧伸展,一手翻掌向天,呈托举状,另一手持着一只短短的空管。器体内部中空,骑狮人的头部形成一节圆形管口,开口在顶部。在这个开口中,插有一支精巧的青铜长管,顶端做成花形纽,其正中为一小孔,由之向下,管腔一通到底。从这支铜管,就不难猜出整件器物的用途,是研墨时向砚台上滴水的专器。
戴念祖《文物与物理》(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中《砚盒中的物态变化》一文介绍了这种传统文房用具的工作原理:将长管插入水内,用手指压住花纽中心的小孔,然后将管子提起。由于手指把长管上端的通气孔塞住,管内水面上的大气压强与管外的大气压强变得不同,形成压强差,管内的水便不会泄落。将其移到砚台上方,松开手指,此际,管内外的压强恢复一致,管内的水才会落下,即可就水磨墨。(不过,书中对细管进水方式的理解似乎有误:「用手指头压住铜水滴的上端,使其另一端进入水中,在大气压的作用下,水进入竹管或铜管。」实际上,如果采用这一方法,留在管内的空气反而会阻碍水进入。相反,应是在顶口敞露的情况下插管入水,根据连通器原理,水会进入管腔)传统的书写方式中,研墨时需要控制水量,防止加水过多,于是,古人发明了这种特殊的工具,利用科学原理,让清水一点一点地滴落到砚台上,所谓「虚管溉满,捻上悬之,水固不泄」(【唐】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即如铜水滴,捻其窍则水不滴,放之则滴」。(【宋】俞琰《席上腐谈》)子顶微大,正盖脑心,俨一席帽」。文中描述的这件太元年间的「水滴」,与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的青铜胡人骑狮器极为相像!由此可以推知,洗砚池晋墓骑狮胡人的右手当初大约也是架着一只鹰,只不过此鹰已经残失。更重要的是,陶宗仪以及元代文人都清楚此件器物是水滴,属于文房用品,用途为向砚台滴水,而胡人头中所插的细管是「吸子」。显然,因为这种细管能吸住水,把水转移到砚台处,所以在元人那里也被叫作「吸子」。书中接着说,鲜于枢曾经有一只形制大同小异的水滴,作为传世物,一代代沿袭的叫法为「蛮人狮子」。他非常喜欢这件古董文具,然而,当寓居西湖断桥的时候,却不小心把吸子掉进了湖水里,三年后,又神奇地在原地找到了它。鲜于枢特别开心,把铜水滴改名为「神人狮子」,还写了篇长文叙述这段因缘,并请当朝、在野的各路文人加以题咏,最终形成一幅长卷。《南村辍耕录》的这则文字非常重要,实际上已经为洗砚池晋墓胡人骑狮器的定名与用途作了清楚的阐释。从唐人王冰、宋人俞琰的讨论可知,吸子作为文房用具的一种,历代都为人们熟悉,大
从考古发掘来看,「铜水滴」一般都与青铜水丞配套制作,典型如安徽马鞍山三国朱然墓出土的「青铜水注」,即是水丞与水滴的组合:水丞为扁圆形,由三个矮蹄足撑起,另外,腹部附有三个短圆管,实际上是笔插,可以将毛笔安插其中。同时配套制作了一支圆管,像塞子一样插入水丞顶面正中的圆口内,管内上下贯穿,直通端头花形纽内的圆孔。
不难看出,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的胡人骑狮器,在构造上与朱然墓青铜水注完全一致,只是被赋予了更具艺术化的外形。人与狮形成的小容器用于贮水,而从其头顶插入的带花纽长管则是「水滴」,使用时,按住顶端,封死孔口,然后把管子从器内拔出,移到砚面上方,再松手滴水。
关于这件器物的实际功能,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神人狮子」一条早已谈得非常清楚。这一则记载曲折有致,很吸引人。其中说,松江的横云山有很多古冢,当地人世代相传是晋代陆氏的家族墓,墓中有很多当年陆家人的宝物。结果有个盗墓贼在至正甲辰这一年的春天盗掘了其中一座墓,墓砖有「太元二年造」的铭刻。墓中挖出了二百多件铜器,「内一水滴,作狮子昂首轩尾走跃状,而一人,面部方大,髭须飘萧,骑狮子背,左手握无底圆桶,右手臂鹰。人之脑心为窍,以安吸子。吸家知道如何使用它,把它看作日常物件。南宋佚名画家所绘的《槐荫消夏图》(现藏故宫博物院),中景的书案上有一件鱼形器,鱼身下有四条支足,鱼背上凸起一只圆鼓,一根细管由鼓中心竖起。与朱然墓出土实物进行对比,可以推测出,这里表现的是一只鱼形水丞与一支吸子的标准组合。在它旁边,则是一座插有两支毛笔的笔架、一台晋唐流行款式的辟雍砚,构成了一整套案头文房。画家能这样表现,也可见吸子露面的机会不少,宋代上层社会不陌生。正是因为水丞配吸子的形制一直沿用下来,经常在书案上占据小小的位置,元代文人对其再熟悉不过,见到前代的同类出土文物便能够立刻认出它的职能,而且很顺手地援为己用。
妙的是,明人高濂《遵生八笺》「水注」提到,「有江铸眠牛,以牧童骑跨作注管」。晋代出现的胡人骑狮水滴,竟然一直沿用到明代,只是随着时代趣味的改变,发生了形象的变化,牛取代了狮子,牧童取代了胡人,但总体造型并未改变,仍然是人骑动物,而以动物背上之人物作为安插吸子的管座—— 「注管」。这样一种既实用又美观的文房款式,一经创造出来,受到一代代欢迎,存续上千年,堪称设计史中的奇迹了。
清楚了历史上曾经流行这种吸子加水丞的组合,一些相关表述才好理解。如宋人赵希鹄《洞天清录》中说,铜制水丞损笔毫,同时「又滴上有孔,受尘,水所以不清」,如果改用玉或玻璃水丞,「若当中作滴子,则尘必入」。看了出土实物,就不难明白赵希鹄的意思,滴水管—— 古人所说的水滴、滴子或吸子,作为长塞插入水丞内,中空的管腔会漏灰,导致容器内部不洁。所以他想出了替代方案,在小水盂上加盖,盖的一侧开个小豁口,插入一柄小勺,以勺取代滴子为砚台加水。从明清文物看,后世文人大多喜欢这一替代方案。
阅读链接
《南村辍耕录》中的 “神人狮子”
—
◎ 松江之横云山,古冢累累然,世传以为多晋陆氏所藏。山人封生业盗冢,至正甲辰春,发一冢,冢砖上有“太元二年造”五字。(按:太元、东晋武帝时也)逆数而上,计九百一十余年矣。或者谓,冢有志石,但恐事泄,秘弗示人。冢中得古铜罍、勺、壶、洗、尊、鼎、杂器物二百余件。内一水滴,作狮子昂首轩尾走跃状,而一人,面部方大,髭须飘萧,骑狮子背,左手握无底圆桶,右手臂鹰,人之脑心为窍,以安吸子。吸子顶微大,正盖脑心,俨一席帽。胡人衣褶及狮鹰羽毛,种种具备。通身青绿,吸子浑若碧玉。论其制作肤理,则非晋人所能,乃汉器无疑,必其平生宝惜,而以徇葬。约长五寸,高四寸许,诚奇物也。至秋,夏士安偶过生,生出以售,捐钱五十缗买之归。剔凿沙土,饰泽蜡石,神气百倍于昔,韫椟保藏,时以示博古好雅者。一日,为有势力时贵夺去。昔鲜于困学公尝畜一水滴,正与士安者大同小异。相承曰蛮人狮子,爱之未尝去手。寓杭州断桥日,临湖有水阁,倚阑把玩,偶坠吸子于湖水中,百计求之不可见,悒怏慨叹,形神为之凋枯。既他往,逾三年,复来杭,仍居昔所寓舍,追怀故物,注视湖波,适当霜降水净之时,吸子俨在土内,亟命仆下取,欣然如获至珍。即易号曰神人狮子。遂序述颠末,求馆阁诸老与夫骚人雅士,歌咏以张之,寝成巨轴。公殁,子孙不能世守,水滴与诗卷皆归婺州陶氏。陶亦不能久有,又将求善贾而沽诸。今不知所在。自我朝百余年来,仅闻公得其一于先,而士安得其一于今,非若他古铜器比,可以屈指数也。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之十九“神人狮子”,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
然而,二〇一一年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王陵出土了一件「错金银嵌宝石鸟柄鎏金汲酒器」,却是用吸子代替酒勺。它的形制十分奇特,底部为一只扁圆罐,罐底面的正中开了一个小孔。罐体之上竖起一根长管,这一长管的顶端铸有一只禽鸟,鸟儿内部为空腔,而在背部正中有一个圆孔,与内部的空腔相通。整件酒器以铜打造,罐、管、鸟无缝接合,浑然一体,但彼此贯通,只有上下两个穿孔,足以让空气在中空的器腔里流动。两千多年前,它作为随葬品入葬时,被置于一张大漆案上,周围放有众多酒器,这一状态一直保持到古墓重开之时。由此可知,这件器物是用于饮酒。具体使用,则是把圆罐部分沉入盛有酒的容器内,让罐与管都尽可能浸到酒液当中,由于连通器原理,酒液会通过罐底穿孔涌入罐腔,甚至上升到长管内,而器腔里的空气则通过鸟背的开孔溢出。对古人来说,神奇之处发生在下一步:一旦用手指严密堵住鸟背上的小孔,把器体从酒盆中提起,借助压强差,便足可令酒液无法从罐底面的孔中流下。也就是说,只要手指紧按鸟背的孔口,不令透气,就可以把器体连同其内所贮之酒提着四处移动,不会有酒泄露。然后的一步,也能产生意外效果:把罐底的小孔对准酒杯,按住鸟背穿孔的手指松开,那么,器内酒面上的压强恢复,酒液就会落下,灌入杯子。
据研究,这座王陵的主人是汉景帝之子、第一代江都王刘非。这就说明,至晚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已经发现了气压差造成的效果,掌握了利用这一原理的技术,聪明的巧匠使用这样的技术制造出了趣味性的取酒器。在酒会上,它代替舀酒勺,通过一汲一放制造魔术效果,引发在场人的惊奇与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