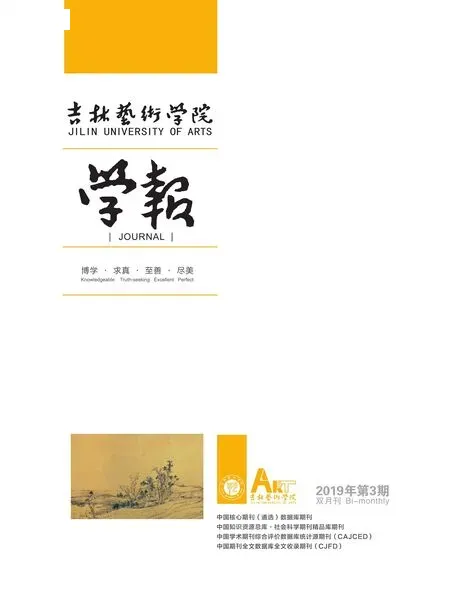“戏”而生艺
——中国杂技艺术纵横观
2019-07-27张月
张月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27)
历史悠久、多姿多彩的中国杂技是一类以身体技巧为核心,辅以桌椅竿梯、刀剑球环、碗盘碟坛、瓶罐缸绳、高跷车轿等器械道具,可与音乐、舞蹈、戏曲、武术、科技等有机结合的综合性传统艺术。它突出展现人体在柔韧、力量、速度、准确、平衡等方面不同寻常的特异技能,具有驭物为灵、动中求静、以奇制胜、以险惊人等审美特点。它凭借超越时空和本能束缚的精神力量,追求在自然界自由畅快的生命境界,展现人对自然万物超凡的驾驭能力和人体文化的生命意蕴。数千年以来,中华杂技艺术以智慧的创造、精湛的技艺、绚丽的形象、多彩的表演和鲜明的民族风格让世界为之赞叹,赢得了“第一杂技大国”“东方人体文化中的活化石”等美誉。
一、杂技艺术的发生
“杂技”,顾名思义涵盖了多种多样的技艺技法。杂技之“杂”表现在该类艺术来源广泛且表演内容丰富多样,杂技之“技”说明这是一种以技术为核心的艺术。技与艺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是否以审美为目的。丰富多样的实用性技术如何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杂技艺术?这便需要对各种技术进行艺术化的加工与升华。
艺术的发生往往离不开生产劳动,原始人类的生存本能、技能和手段是产生杂技艺术的源头。原始文化以人体文化为主流,反映出中国杂技艺术的悠久历史,被誉为“东方人体文化中的活化石”,体现了杂技艺术在人体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作为人体文化中以展现身体技巧为目的的传统艺术门类,杂技中蕴藏着人体发展的原始密码。劳动目的发生转变是杂技产生的重要源泉之一,人们对渔猎农耕等劳动技能进行提炼并加以艺术化的提升,于是出现了例如投掷、上树、走索、攀岩、跳涧、渔猎等杂技的原始形态。
中国杂技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杂技“飞去来器”源于捕猎活动,原始部落的猎手投掷十字形的猎具打击猎物,借助风力作用,猎具能够回旋去来。较之石块、木棒等原始工具,“飞去来器”的使用多了一份技术的意味。这一技术经杂技演员的艺术加工,十字猎器如流星飞燕般往返于观众与演员之间,飞去来器便从实用工具转变为艺术道具,其表演形式就成为具有一定互动性的杂技节目。
杂技的另一种起源是游戏。人们在游戏中不断创造新“玩法”、新技能,逐步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空竹、转碟、顶缸、高翘、回跳丸等手技艺术都源发于游戏。与音乐、舞蹈、戏曲等能够反映丰富情感的艺术门类不同的是,杂技带给人们的往往是新奇、谐趣、兴奋与欢乐,较少传达悲伤、哀怨的消极情绪。这一特征便与杂技的游戏意义密切相关。
模仿也是杂技产生的一种途径。生活中,人们通过再现活动场景,在模仿中开拓创新、打破常规,从而促成特殊技艺的产生。例如飞刀是一种古老的征战武技,以击中猎物为目的。当飞刀以杂技艺术的身份展现在观众面前,技术要求同样是精准巧妙,但表演目的则转变为恰好不击中目标演员。
从劳动生产、游戏模仿到杂技艺术的诞生,这一过程体现了人与一般动物的本质区别。但单纯的劳动、游戏或模仿等方式都难以创造如此丰富的杂技艺术。作为艺术的一种,不论表演技术还是辅助道具,较之其他表演类姊妹艺术,杂技更为贴近生活的同时又更加强调违反常规。与其他艺术门类不同,杂技不仅符合“艺术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这个普遍规律,并且更具典型意义,往往追求在“高于生活”的基础上还要有所突破。在这一艺术精神的促动下,杂技不断超越普通人体的极限。艺术家们通过杂技表演向观众传达并分享着人类超越自我、挑战自然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功与喜悦。
二、杂技艺术的发展与类分
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杂技艺术的发展水平同样与人类社会文明程度、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与把握状况以及人的思维发展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人类智慧同期开发进化,杂技艺术也不断完善创新。原始艺术是多元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杂技何时独立为门类艺术,目前尚无准确考证。研究者大多认为杂技起源于原始社会,成型于春秋战国,汉唐间兴于宫廷,宋元以降江湖盛行,清末民初流传海外,近现代享誉世界。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活跃,各路诸侯豢养武士成风,武士们的特技异能成为杂技节目的先现。思想与技能的碰撞为杂技发展带来了生机。这一时期杂技艺术由简至繁,从朴素的力量游戏向技巧技艺发展,已具备技巧、造型、节奏、组合等基本要素,更加鲜明地体现出人类思维具象与抽象的结合。
秦代,始皇下令收缴兵器并将六国艺人聚集咸阳。在此社会环境下,杂技向形体艺术方向发展,角抵戏正式登台。同期各类技艺相互切磋融合,为百戏诞生创造了条件。汉代,国力强盛、思想成熟、社会安定等有利条件促进了杂技艺术的发展。艺人们充分发挥其综合创造力,使精美绝伦的百戏大展华彩(图1),杂技中音乐、服装、道具等配置也有了显著突破。

图1 山东济南出土的汉代百戏陶俑图片来源:济南市博物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杂技艺术注入了更丰富的民族元素,而长久的南北分治则使杂技风格出现地域分化。北方杂技在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下偏向惊险、健伟;南方杂技则更多继承汉族儒家风范,逐渐细腻秀美而注重意境的塑造。
隋代天下一统,京都汇集的各类杂技名目达七十余种,杂技艺术逐渐步入全盛时代。隋唐年间,由于部分杂技的文化内涵不符合礼教思想,曾遭禁演。但帝王的喜爱终又将其推向历史的高潮,在编制规模、专业水平、艺术造诣、创新融合、中外交流等方面达到新的高度。
宋元以降,市民文化兴盛,民间杂技表演多以户为单位,市场竞演促使民间杂技不拘一格地开拓创新,专业化、体系化程度大大提高,使杂技达到空前繁荣。其中腰腿顶功、手彩技艺等尤为突出,杂技与杂戏结合继而促进了杂剧的诞生(图2)。

图2 《杂技戏孩图》苏汉臣 宋代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
明清之际,宫廷杂技日渐衰落,江湖杂技蔚然成风。走马卖解、撂地摊等是常见的杂技表演形式,社火、走会等民俗礼仪也为杂技艺人提供了一展身手的机会(图3)。杂技与戏剧进一步结合,这不仅促进了人体杂技的提高,还推动杂技向舞台艺术转化的进程。

图3 明清之际行香走会杂技表演《豫园把戏图》图片来源:雅昌艺术网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近现代中华杂技既继承传统艺术精华,又擅长吸收西洋魔术、电光幻术等先进技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杂技艺术迎来了新的篇章,其审美品位、文化内涵、技术技巧、节目品种、理论建树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不仅在国际文化交流和比赛中为我国摘得多项荣誉,还连续举办了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中国武汉杂技艺术节、中国上海国际魔术比赛等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杂技活动。自1981年参加摩纳哥世界杂技大赛至今,中国杂技已十数次获得“杂技奥斯卡”的“金小丑”奖等荣誉。获奖节目有武汉杂技团的《顶碗》、山东省杂技团的《女子车技》、沈阳军区前进杂技团的《钻台圈》、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的《双顶碗》、山东省杂技团的《女子车技》、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的《女子大跳板》、上海马戏学校的《跳板蹬人》、上海杂技团的《大跳板》和《男子艺术造型》等。
从生活技能、游戏到业余表演再到专业从业,从地摊大篷到厅堂剧院,从技术到艺术再到文化内涵介入,杂技的发展历程饱含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民间与官方的多维结合。杂技之“杂”反映了杂技是千姿百态、包罗万象、丰富混合,甚至是与各艺术门类盘根错节的。这一本质属性注定了杂技类分将有多种方式。
杂技理论界曾从风格特点、表现形式、技能技巧、功能作用、社会属性、审美特征、表演空间等多角度试图对杂技艺术类归,但终难形成一致公认而又恰当全面、尽善尽美的分类方式。例如“二分法”是根据作用和目的将杂技分为生活杂技和艺术杂技,按照表演空间分为地面表演和空中表演。“四分法”是根据表演特征,有的将杂技分为人体技巧、魔术、驯兽和滑稽,有的分为滑稽、马戏、技艺以及文活,其中技艺由形体、耍弄、高空、力技组成,文活包括魔术、口技;根据艺术形态,结合中国古语又分为把戏、幻戏、优戏和马戏。“五分法”同样注重表演特征,有的分为形体动作技艺、魔术、象形象声、驯兽及滑稽,有的分为形体表演、奇妙变化、象形象兽、驯练和驾驭兽畜、滑稽小丑艺术等。“六分法”按技术类别分为投掷技、力技、射技、攀缘技、口技、驯兽技等。此外,还有复合型分类法,例如将魔术、滑稽、马戏以外的杂技按空中、地面分类,将杂技分为力技、形体技巧、耍弄技巧、高空技巧、幻术、马戏、滑稽七大门类等。[1]-[4]
对事物进行类分,通常遵循物以类聚、同级并列、全体涵盖无缺漏、同级类分间无重叠交织等原则。综合比较上述各种类分方式,“四分法”中将杂技分为幻戏(魔术)、优戏(滑稽)、马戏(驯兽)、把戏(人体技巧)基本符合这些原则,且与杂技变(变魔术)、戏(滑稽戏)、驯(驯兽畜)、耍(耍器物)+练(练体能)等基本形式相对应,也就相对合理。同时各类名称出自中国古语,以多种多样的“戏”类分杂技,能够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特色,是较为理想的类分方式。需说明的是广义“把戏”也作魔术、杂耍的俗称,此处以狭义的人体技巧做解。
三、“戏”而生艺——各类杂技艺术的历史演进
1. 假作真时真亦假,幻戏魔术古今谈
幻戏是中国传统戏法的代称,即现代魔术。魔术师运用反常规思维设计高超的技术手法,常为观众带来科技含量更高的超越视觉经验的体验。魔术运用了科学原理,却将科学原理深深地隐藏,非要如此方能使观众感受到化腐朽为神奇、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力量,所以在魔术表演过程中实质暗藏着观众与魔术师之间的智力竞赛。例如传统戏法《仙童戏绳》即利用重力与摩擦力原理使穿在绳子上的小木偶可以“听从”魔术师的命令即走即停。
汉代,西域幻戏传入,宫廷内将其归入百戏名下由乐府管理承载。这一生存环境为外来幻戏与中土乐舞相结合创造了条件,推动了幻戏的本土化进程。后魏、北齐时幻戏有《鱼龙辟邪》《鹿马仙车》《吞刀吐火》《剥车剥驴》《种瓜拔井》等表演项目。隋炀帝时期,宫廷大兴百戏,一时间幻戏盛行。数代以来,幻戏常以血腥刺激的场面博人耳目。例如东汉孙奴善使割头术,北魏悦般国来献“割喉献骨”,唐代曾上演生吃动物,传统幻戏吞刀吐火也同样险象环生。这些表演被史家指为“诡怪百出,惊俗骇观,非所以善民心,化民俗”[5],有悖儒家礼教思想,更指出隋代灭亡系炀帝大兴百戏所致。因此唐高宗曾一度“禁胡人为幻戏者”,但该时期传统乐舞幻戏仍然备受唐人青睐。例如宫廷中为武则天庆生表演的《圣寿乐》(后名《云韶乐》)即用“换衣术”呈现多彩舞姿。玄宗年间,教坊从太常寺独立出来专门承载娱乐用乐,散乐百戏再度大兴。宋代,随着市井文化的繁荣,幻戏的发展渐与方士幻术分道扬镳,与政治渐行渐远。瓦舍勾栏中,幻戏表演发展为一个艺术行当,藏掖撮弄等技术手法渐成体系。如图4李嵩《骷髅幻戏图》生动描绘了提线木偶(悬丝傀儡)的表演场景,画中可见幻戏已进入宋人的日常生活。元代,幻戏被称作“杂把戏”。明清时期本土化的幻戏体系趋于成熟。同期幻戏开始引进西洋魔术技法,名称也渐为“魔术”取代。

图4 《骷髅幻戏图》李嵩 南宋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
近百年来,较有代表性的魔术家有“傅式幻术”四代传人傅志清、傅天正、傅腾龙、傅琰东以及青年魔术家王亦丰、刘谦、王禹等。其中“傅式幻术”是唯一一个魔术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百年历史可以缩影式反映近现代魔术发展史的一隅。傅氏传人不仅重视表演技术,还注重理论修养。正如“傅式幻术”第二代传人留与族人的从艺要求所言“演象为体,精气为髓,译幻为表,文理为核。”[6]现任掌门人“中国魔王”傅腾龙的魔术代表作有《书画幻术》《心灵感应》《清华神韵》《神秘剪影》等,还有与姐姐傅起凤合著的《中国杂技史》《中国杂技》等。他们以局内人特有的视角为我国杂技理论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图5 陶楼彩画《优戏图》出土于河南荥阳汉墓[7]

图6 敦煌莫高窟156窟晚唐壁画 [8]《宋国夫人出行图》局部(左侧顶竿表演)
2. 嬉笑怒骂皆是戏,俳优谏言历千年
优戏,以谐谑为主的杂戏,也作滑稽戏,还可泛指演戏。杂技类下,优戏指运用简单的语汇或声响,以诙谐、幽默、夸张、机巧甚至怪异的表演风格在插科打诨中展现各种技艺,从而达到讽喻、嘲谑和娱乐目的的一类趣味戏剧。由于优戏中丑角戏份为主,故又称作“小丑”节目。较之其他类杂技节目,优戏的人物形象、情节情感以及肢体语言较为生动突出。根据表现形式,优戏又分为以表演为主的文滑稽和以技艺为主的武滑稽。
夏代,优戏已在民间兴起并进入宫廷,表演者被称为优人,侏儒居多。两周时期,优戏在多国流传并广为君王喜爱,史有“周成王近优”,齐桓公“近优而远士”(《韩非子》)等记载。先秦时期,优戏中开始加入劝谏的内容,称为优谏。艺人们巧妙地运用讽喻手法针砭时弊,鞭挞恶吏,使优戏在娱乐之余又多了一重社会功能与实用功能。汉代优戏更为盛行,各地出土的画像砖及文献记载可为见证。如图5河南荥阳汉墓出土的两组陶楼彩画《优戏图》,形象地刻画了男女优人和乐而作、踏盘飞舞的场景。曹魏时期,优戏《辽东妖妇》使用了“弄假妇人”(男扮女装)的表演手法。这一手法为后世承袭,周隋尤盛。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载有《东海黄公》《许胡克伐》等优戏表演。隋代,优戏进一步发展,在故事情节及歌舞和乐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化妆和面具,代表剧目有《踏瑶娘》。唐代,肇源于后汉的参军戏渐成格局。这是一种有角色装扮、科白及歌舞的滑稽戏,名目颇多,有“弄假妇人”“弄假官”“弄参军”“弄婆罗门”“弄孔子”等。诸多参军戏优人中,咸通年间的宫优李可及独出辈流。宋代,规范的宫廷礼仪及丰富的市民文化为优戏发展创造了条件。宫殿庙堂、勾栏台阁间,优戏逐渐走向成熟。其中参军戏继续向戏剧方向演化,发展为杂剧的一支——科白戏。明清以来,优戏与杂剧传奇并立而兴。有别于唐宋的是,明清官家对“弄孔子”优戏时禁时演,从侧面反映出了文化意识与社会政治之间的消长关系。
近现代以来,滑稽戏内涵有变,通常指民国时期形成于上海,由曲艺独角戏演变发展而来的吴地小戏,主要流传于上海、江苏、浙江部分地区。而杂技类别下的滑稽表演则主要指小丑节目。按表演场次分,杂技滑稽有单场或正场滑稽、串场滑稽、帮场滑稽等几种类型。20世纪50—60年代,滑稽表演稳健发展,中国杂技团的陈森良、陈腊本,武汉杂技团的吴卫民、向忠杰等著名滑稽演员的表演都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水准。但此后,滑稽表演在杂技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多以串场或帮场的形式出现,独立正式、结构完整的单场滑稽则较少。近年来,随着杂技艺术海内外交流与日增多,滑稽节目份量也逐渐随之加重。
3. 跑马献花戏娱众,人与动物谐与共
“马戏”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恒宽所著《盐铁论·散不足》:民间有“百兽马戏斗虎”。旧时马戏专指马上技艺及驯马表演,主要有马上技巧、舞马、马球等技艺。在发展过程中,随着驯化对象的扩展,“马戏”逐渐囊括了各种动物表演。按目的分类的马戏驯化有四种:拟人化驯化,训练动物模仿人的行为,例如教海狮模仿人直立行走并行礼等;智能化驯化,借助动物自身的智能特点加以训练,例如大象画画,发挥小狗的听闻技术,教猴子在表演过程中与人的交流互动等;技巧动作驯化,训练动物掌握一些特殊技巧,例如老虎钻火圈、狮子叠罗汉、小熊骑车等;动物本能驯化,展示动物本能及特技,例如狮虎腾跃、咆哮,猴子抓耳挠腮等。
马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因此不论在生活还是战争中,驭马之术都非常重要。周代王室驯马师被称作“趣马”,教马“六节”,即行走、停止、前进、后退、小跑、大跑六个基本动作。汉代,民间马戏已有多种技巧,各地出土的伎儿马戏图可直观反映当时马戏表演技艺之高超,例如有后世命名的“立马”“马上大站”“猿骑”等。同期,斗兽、驯兽活动种类繁多,例如驯虎、象、熊、鹿、鹤、猴、蛇、雀等不胜枚举。汉晋时期,曾流行“戏马书”,即马上书法表演。同期动物戏也有所发展,颇具代表性的有吴国驯象、东晋猴戏等。唐代的舞马、马球、猴戏、斗鸡、斗昆虫等多种动物戏繁盛。其中舞马尤盛,经典节目有“舞马登床”“舞马衔杯”“百马齐舞”等,此外骏马还可以踏着音乐节拍腾跃、跪拜、行礼。宋元时期马戏表演渐趋完善,不仅骑术增长且将骑射结合,成就辉煌。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录了当朝诸军马戏表演有引马、开道旗、托绣球、䄍柳枝、旋风旗、立马、跳马、騗马、跳马、献鞍、倒立、拖马、飞仙膊马、镫里藏身、赶马、绰尘、豹子马、马上轮重物、马上舞刀等马戏技术,这一系列表演足见宋代马戏的专业化水平。宋代动物戏多以小型动物为主,节目有“鱼跳刀门”“乌龟踢弄”“老鸦下棋”“七宝水戏”等。明清以来,马戏表演仍在中华大地普遍流传。但较之唐宋,宫廷马戏已逊色许多。近现代马戏发展过程中,动物戏表演项目迅速扩展。20世纪上半叶,狗熊站立行走、羊蹬花瓶、老虎钻圈等节目已经成熟。1988年上海杂技团筹资创建了我国第一所中等专业杂技学校——上海市马戏学校,结束了我国杂技有千团而无一校的历史。20世纪末,有“中国马戏第一城”之称的上海马戏城建成,为杂技演出交流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当代,较有影响力的马戏团有上海马戏团、埇桥马戏等。2006年埇桥区获全国唯一“中国马戏之乡”的荣誉称号,经典节目有《狮虎高空钻火圈》《狮虎过桥踏人》《羊蹬花瓶》《狮虎滚筒》《拳入狮口》《狮虎骑马》《蛇舞》《狗熊走钢丝》《狮虎滚球》《叼肉》等,著名马戏师有吴清云(1901—1960)、李正丙、杨志远、杨东等。
4. 扛爬投跳顶翻舞,挑战体能耍把戏
把戏,在杂技类下主要指以身体技巧为核心的杂技。人的身体既是生命的载体,也是生命的表现体。身体技术可以艺术化地展现人体与生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阐释灵魂存在的意义。因此把戏设计、训练、表演的过程实质也是人们对身体机能的开发与探索,蕴含着一种不屈不挠、勇于突破自我的精神内涵。
把戏表演以人体技巧为艺术语言,主要表达方式有技巧、道具、造型等。根据人体能力与道具掌控之关系,把戏又分为平衡类、柔韧类、腾翻类、攀跋类、力技类、口技类、乔装类等。平衡类杂技又有垂直平衡和倒立平衡之分,前者有走钢丝、踩球、晃物(如梯、板、圈、管、筒)、顶竿等,后者有椅子顶。柔韧类突出表现人体的柔韧度,古有“缩骨术”“折腰术”等技法,具体到把戏表演即钻桶、钻圈、柔术等。翻腾类根据力源又分为自力翻腾和借力翻腾,前者主要依靠自身技艺发力翻腾,例如虎跳、小翻等,后者则需借助软杠、蹦床、车辆等有弹性或能产生惯性的道具进行翻腾表演。攀爬类通常展示的是高空技艺,例如绸吊、爬竿以及演化出来的《空中芭蕾》《空中飞人》《高空走绳》等节目。乔装类主要指舞龙舞狮等借助道具装扮成某种事物进行技艺表演的把戏。
杂技中,最早发展的是完全依赖于人体技能的力技。早在原始社会,当人们为了获取食物而攀援腾跳举重之际,力技类把戏就已孕育其中。技高一筹的人们逐渐脱颖而出,在劳作之余玩弄把戏、切磋较量,角力随之诞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家豢养门客成风,身怀绝技的武士对把戏成形发挥了推动作用。秦汉时期,角力发展为角抵戏,表演扛顶的乌获被后人奉为力技之祖,后世“乌获扛鼎”逐渐演化为力技项目之一。同期力技项目还有“狄虎舞轮”、戴杆、搏虎、拔树、曳兽、举臼等。此外,腰功、腿功、顶功(倒植/倒立)、跟头、柔术等形体技巧在汉代已具雏形,另有“冲狭”“燕濯”“弄丸”“跳剑”“跳丸剑”“舞盘”“投壶”“顶球”“弄瓶鞭击”以及高空节目“侏儒扶卢”“戴竿”“陵高履索”等把戏表演[9]。两晋南北朝时期,多民族文化交流频繁,把戏艺术不断纳新融合。十六国时期的“齿上橦”即来源于西北羯族。隋唐时期,在隋炀帝、唐玄宗等几代帝王的扶持下,各类把戏迅速发展。“倒立”“瞋面”“叠罗汉”等身体技艺以及高空技艺“戴竿”“飞绳”“走绳”“舞狮”等在技术含量、表演花样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天宝年间和德宗时期有两位同叫王大娘的演员以及敬宗时期石火胡的顶杆技术表演炉火纯青,令人赞叹不已。宋代,瓦舍勾栏为把戏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当时的形体技艺有“擎戴”“舞绾”“倒食冷淘”以及辅以道具的“水秋千”“刷大旗”“悬倒进餐”等。而力技类杂技在宋代也称作相扑、摔跤,仍然活跃于各个阶层。该时期杂技的专业化发展逐渐凸显,例如北宋温哥奴、小掉刀、真个强等艺人专事手技,南宋姚润、赵喜等擅长抛接。同时期还出现了“弄斗”,这一技艺在明代发展为“空竹”。元代,角抵、武技等把戏被明令禁止,艺人们无奈投身戏班。而把戏技艺与戏曲的结合为元杂剧带来了新的生机。明清年间,把戏在民间以撂地卖艺等形式自由发展广泛流传,各种技巧层出不穷,例如筋斗、叠案、置地圈等,力技类主要有千斤担、耍石锁、舞大刀、布库等。近现代以来,在杂技艺术不断朝向团体化发展的形势下,把戏表演又有了新的突破。例如椅子顶从单人发展到了集体,顶杆也从单层发展到了双层顶杆。当代把戏技艺仍不断革新,较为突出的艺术家有浙江杂技团转碟演员吴民、安庆艺术团滚杯演员许梅花等。
四、中国杂技艺术的文化意义与精神内涵
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中国杂技既传统又现代。它揉合了多种艺术的精华,处处闪烁着东方哲理与智慧。古往今来,杂技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贡献不仅在于为人们带来新奇与欢乐,还对科技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例如四大发明中,火药最初并非专为军用,而是在杂技表演中制造音响与烟幕的道具;受中国走索杂技演员运用雨伞做防护道具的启发,法国科学家孟高尔费发明了降落伞。如此高技术含量的艺术常令其他门类艺术望尘莫及。杂技可以巧妙诠释并自如演绎科技与艺术的密切关系。在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之间,艺术与技术自然结合并以相互促进的方式循环转化。技术孕育着杂技,而杂技创作可能也是科学研究的前奏。杂技艺术在打破常规的同时或将从与众不同的角度为科学技术创新与发展注入新的能源与灵感,在不经意间激活技术潜能。
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之一,杂技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传递友谊、互通有无的纽带作用。早在汉代,东罗马、天竺的杂技艺人就曾到中原献艺,同时丝绸之路上中国杂技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艺术项目之一。唐代杂技艺术远渡重洋对亚洲杂技发展的影响深远。近代以来,杂技是最早走向世界的传统艺术。19世纪清代最为著名的戏法大师朱连魁曾带领一班人马到美国表演。他徒手变出一支装满水的巨碗,震惊了美国魔术界。朱连魁还将三国时代左慈为曹操表演的“堂下钓鱼”传授给美国魔术家威廉·罗宾逊。正是中国杂技表演艺术家的精湛技艺与慷慨大方成就了这段艺术交流史上的佳话。
作为人体文化的活化石,《顶碗》《飞刀》《走索》《椅技》《转碟》《空竹》《钻圈》《流星》《皮条》《舞狮》《舞龙》《口技》《舞流星》等经典杂技节目有着几百乃至数千余年的历史。这些节目立足传统,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创新,如同生物进化一般顺势而生、适世而存。杂技艺术承载着中华民族两千年来的文明基因,蕴含着中华民族勇于创新、博采众长、乐观向上的文化品格,反映了中华儿女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勇于开拓的人文精神,寄托着国人崇尚卓越、人物和谐、趣意盎然的灵魂追求,展现了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玄妙奇幻、精益求精的艺术特质与精神内涵。
历史的积淀、技艺的革新、文化的情怀使中国杂技艺术精彩而又精妙。纵观数千载杂技艺术发展史,先祖之智慧、技能与精神令人在赞叹感慨之余不觉斗志昂扬,激励国人敢于挑战、乐于创新、奋勇向前;横看中华大地上丰富的杂技艺术门类,“戏”与技的结合使中国杂技艺术别具一格,“戏”而生艺,其中蕴含的人文气息、科技含量与传统文脉不仅让中国杂技艺术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同时也赋予了我们深切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承载着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杂技艺术,以精湛的技艺、丰富的底蕴致敬五千年中华文明,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