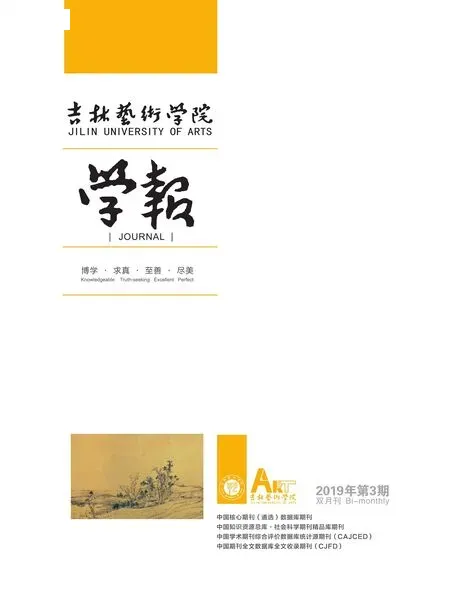哈萨克斯坦民族电影发展的思考
2019-07-27周艳
周艳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 晋中,030800)
2018年11月29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Abishevich Nazarbayev)在公开发表的《伟大草原治国的7个边缘》一文中,针对“历史意识现代化”提出了重点实施的几项举措,其中尤其强调了影视艺术在现代人们历史认知中重要的地位——“我们的英雄和学者及领袖们不仅应成为在哈萨克斯坦,乃至在全世界都值得效仿的人物。”[1]该国90年代独立前后的“新浪潮电影”,率先在独立前各加盟国中发出了“反殖民主义”的先声,以独立的民族电影形象引起了广泛关注。随着1998年哈萨克斯坦迁都后一系列政治变革,该国电影继新浪潮之后也开始了坚定不移的民族电影的探索与发展,从最初的文化反叛开始向历史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源泉,并力图由此缔造继往开来的民族神话和独立自由的崭新国家形象。哈萨克斯坦电影在文化意识形态建构方面远远走在了中亚五国前列,这和前苏联时期特殊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为此,从前苏联时期开始梳理哈萨克斯坦电影发展的脉络,对于理解该国当代民族电影风格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1928—1954:缔造国家神话的符号
在列宁著名的“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电影是最重要的”[2]13号召下,电影自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在广大工农群众中普及,逐渐成为了塑造国家神话形象和传播各种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当代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世界像照片一样被征服”,[2]134地图真实而又象征性地阐释这个新成立国家的地理与政治雄心。在前苏联“解放”全人类的宏伟蓝图上,作为东部地区的中亚成为电影中宣传政绩并继而对当地人民宣教的重要地域,由此产生了前苏联电影史上短暂而影响深远的“东方电影”(Vostokkino)计划。所谓“东方电影”是1926年在莫斯科由苏维埃东方协会的领导和知识分子发起,从电影协会(Sovkino)一个部门中分化出来的电影机构,并于1928年经过决议正式落实。[2]33这个电影机构到1935年就解散了,且迫于1928-1935年期间前苏联的文化政策而被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从生产到发行都受到严格的监管控制。
“东部人民不是用逻辑而是用形象思考,电影是唯一的宣传工具”。[2]44从成立伊始,“东方电影”就试图建立起前苏联的“东方”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中亚五国的电影制片机构就是在这段时间纷纷被建立,主要配合记录落后的游牧生活和日新月异的新生活。其中哈萨克斯坦作为“东方电影”的股东之一,从1929年开始被当局设置了12个电影院——一个影院(巡回或者一直放)就为52,003个哈萨克人服务。[2]381930年年初时,“东方电影”在雅尔塔(克里米亚半岛)、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喀山(鞑靼斯坦)和乌丁斯克(布兰亚特)有四个生产制片厂。阿拉木图电影制片厂不仅要必须服务于哈萨克斯坦,还包括吉尔吉斯坦、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区,以及其他从西伯利亚到中亚的区域。阿拉木图电影制片厂常常生产被称作“最新报道”(Poslednie izvestiia)的新闻纪录片,这是哈萨克斯坦最早的电影。
1935年“东方电影”被整治遣散后,出于二战前紧张局势的考虑,列宁电影制片厂(Lenfilm)、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Leningrad Film)、莫斯科电影制片厂(Mosfilm)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The Central Newsreel Studios)等电影机构纷纷并入阿拉木图电影机构,于1941年二战爆发前夕成立了中央联合电影制片厂(TsOKS),哈萨克电影制片厂作为重要的分支负责和各个并组的电影机构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段时间哈萨克斯坦生产了当时80%的前苏联电影[2]67,普多夫金、维尔托夫、爱森斯坦等电影大师都曾在这里工作,并亲自教导和培养当地电影工作人员,由此为哈萨克斯坦培养了很多优秀的电影人才。这些电影机构也为哈萨克斯坦电影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和影院放映设施的基础,为哈萨克斯坦民族电影的诞生创造了有利条件。直到1944年,中央电影制片厂被解散、阿拉木图电影机构被正式命名为哈萨克电影制片厂(Kazakhfilm),哈萨克斯坦人才有机会真正参与到拍摄本民族影片的工作中来。1945年,一些哈萨克斯坦电影工作人员开始亲自参与并负责部分的摄制工作,这期间哈萨克斯坦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阿拜之歌》(1946),是首部有当地人亲自参与摄制的故事片。但是紧接着从1946年至1952年,伴随着前苏联又一次紧张的文化政策下电影发展的枯竭,哈萨克斯坦刚刚诞生的民族电影随即进入了高压敏感的停滞期。直到1953年随着前苏联电影“解冻”后黄金时代的到来,哈萨克斯坦民族电影才迎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创作高峰。
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40年代中期,前苏联在哈萨克斯坦生产了著名的纪录片《土西铁路》(1929),乃至被假定为第一部民族电影的《哈萨克》(1938),哈萨克斯坦总体是作为前苏联国家神话缔造的一个“诠释”和“证明”。据史料统计,在“东方电影”几年里生产的科教片中,哈萨克斯坦一直是电影表现的重点。在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大概有10部电影描写哈萨克斯坦的生活。[2]40这些电影着重表现的是封闭落后的草原游牧生活经过启蒙教育和建设改造之后的变化,尤其是妇女得到了解放。其中哈萨克马队、传统服饰、草原生活、山河风光,……在前苏联电影美学的运用下充分发挥了异域文化的视听奇观作用,并结合其他偏远区域一起向中心城市的观众展示了神秘壮丽的大好河山。在30-40年代,因为政治的文化干预和严酷监管,电影进一步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有限的故事片中的主角,主要是敢于为国牺牲的革命或者战斗英雄,直到50年代初期体现的都是一以贯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
在这段漫长的民族电影草创期,由官方指派、统筹兼顾的哈萨克斯坦影片作为当时前苏联亚文化的一部分,是经由前苏联意识形态监控和管制视野之下的影像表达。不仅忽略了当地哈萨克人民的生活真相和真实感受,而且漠视了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成为经过有选择地裁剪编辑的一道电影文化花边。但是电影大师亲自收授当地学徒,却为哈萨克斯坦民族电影的诞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编剧、导演、摄影师等电影工作者,后来成为“哈萨克新浪潮”的中坚力量,深刻影响了当代哈萨克电影的美学风格。
二、1953—1979:潜在民族意识的自觉
199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议下,49个国家的电影档案馆选出了能体现各国文化和影史重要性的十五佳。作为中亚唯一提交影片的国家,哈萨克斯坦总共提交了20部正片,此外还提交了11部纪录片和3部动画片。在该国的提交片单上[3],人们会发现所选片目有意回避了同时代很多更为优秀的哈萨克题材影片,像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的《第一位教师》(1965)、马萨特·贝嘉林的《马梅·托娃之歌》(1974)等影片对哈萨克斯坦的精神价值与历史传统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漠视,故而都没有被选做该国民族电影的代表作。
在这份民族电影片单上除去纪录片和动画片,有7部故事片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在这之前除了纪录片未有任何故事片入选该国电影遗产十五佳,由此再次证明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也把这一历史时期作为民族电影第一个辉煌阶段的代表。这7部影片中包括萨肯·艾曼诺夫(Shaken Ajmanov)的《阿达尔》(1964)、苏丹·坎哈德嘉夫(Sultan Khodjikov)的《女子孜别克》(1972)两部根据哈萨克古老传说改编的影片;萨肯·艾曼诺夫(Shaken Ajmanov)的《父岛》(1966)、卡尼贝克·卡西贝克瓦(Kanymbek Kassymbekov)的《男孩和马驹》(1972)、阿卜杜拉卡·萨克巴耶夫(Abdulla Karsakbayev)的《我的名字叫科沙》(1964)三部儿童电影;还有马萨特·贝嘉林(Mazhit Begalin)的一部女性电影《痕迹消失在地平线后》(1964),以及他的一部哈萨克知识分子影片《即将到来的时代》(1957),集中代表了早期哈萨克斯坦作为前苏联亚文化时期一份子的电影美学风格,但又巧妙地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立场和独特的民族风格。
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批评的剖析》中指出,抒情诗、喜剧、悲剧和讽喻剧,分别对应着人类历史的神袛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颓废与死亡的时代。[4]126对比60年代前苏联时期的“诗电影”美学风格,这7部影片同样充满了诗意昂扬的气质。即便是具有悲情意味的《女子孜别克》和《父岛》,也是在看似悲剧的叙事中处处洋溢着对于故土以及游牧生活浓郁的诗情画意。但在抒情诗风格的背后,哈萨克斯坦电影却“有意味地”表现着民族意识的自觉。这种含蓄的表达是通过“正与邪”“对与错”“真与假”等二元对立的神话叙事,建构了哈萨克斯坦最初独具风情的民族影像。
概括起来,这7部早期的哈萨克斯坦民族电影所表现的主题都是土地与自由。哈萨克斯坦选定这7部影片作为该时代民族电影文化遗产,也是与当代国家精神相契合,既肯定了其高度的艺术价值,也强调了加盟国期间就已萌芽的自由独立意识。《女子孜别克》(图1)和《阿达尔》两部电影均源自于哈萨克斯坦的民间传说。前者讲述勇敢、聪明而美丽的哈萨克斯坦公主孜别克大胆追求自由爱情,在新婚之前舍生取义,让自己的爱人为了抵御侵略而冲锋陷阵,最后英勇的新郎被嫉妒者杀害的故事,哈萨克斯坦冰冷的河水里漂浮着孜别克新娘的头饰与悲情的歌声。《阿达尔》中的主角是传说中的智者,帮助哈萨克斯坦人反抗压迫,劫富济贫,惩强扶弱,乐于助人,是一个神话中的大义人。电影没有刻意神话阿达尔的超能力,而是着重表现他超群的计谋和智慧,以及如何在啼笑皆非的戏剧化冲突中声张正义。

图2 《父岛》海报 1966
如果说上述两部电影代表的是哈萨克斯坦动人的历史,那么其他五部影片则表达的是作为加盟国不屈的民族精神。《父岛》《男孩和马驹》《我的名字叫科沙》三部影片都是儿童题材影片。《父岛》(图2)讲述祖父带领着孙子一路乘坐火车,要把二战中牺牲的儿子骨灰带回故土的故事。他们在火车上碰到了一位考古学家和他的儿媳妇,还有一名和他们有着共同遭遇的红军,因为一路相伴获得了彼此之间的同情慰藉。对于哈萨克斯坦人来说,死无所依是难以接受和想象的事情,由此对战争的正义性发出了强烈的质疑和不满。《男孩和马驹》(图3)中两个小男孩亲自养大了一个小马驹,后来被人偷偷牵走卖掉,两个男孩难耐巨大的悲痛,翻山越岭找回了心爱的马。在一出波澜起伏的闹剧当中,表现了新时代哈萨克斯坦儿童在苏联教育体制中对于传统生活方式难以割舍的爱恋。《我的名字叫科沙》中科沙的名字拼写起来就是哈萨克斯坦的别称,也是完成了麦加朝拜而广受尊敬的一个哈萨克斯坦人的名字。科沙是一个调皮捣蛋、处处和老师作对、让人头疼的男孩,他总想着征服太空,后跟随朋友逃学,从苏联式的教育环境误入了哈萨克斯坦传统的草原聚会,在那里找到了归属和新生。这三部儿童电影中的“父亲”角色都是缺失的,“母亲”被迫远离,他们都是由祖父祖母养育。体现了当时哈萨克斯坦电影共同的特质,即因为共同的领袖“父亲”,电影中便不再有强大的父亲乃至男性的角色。英雄多是由俄罗斯演员演绎,或者只存在于《女子孜别克》和《阿达尔》这样古老的传说中。祖父祖母则象征着土地,祖国和传统,大量的儿童角色则意味着哈萨克斯坦就像是伟大领袖的孩子和学生。[2]166

图3 《男孩和马驹》剧照
《痕迹在地平线之后》和《即将到来的时代》两部电影出自同一位导演马萨特·贝嘉林之手。《即将到来的时代》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前,哈萨克斯坦知识分子带领军队抵御外族侵略的故事背景巧妙地绕过前苏联表达了民族的自由意志。《痕迹在地平线之后》用淡淡的情绪和含蓄细腻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哈萨克斯坦女人婚后和丈夫的隔阂压抑,后来在认清丈夫的怯懦卑劣之后毅然远走,勇于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两部电影大量采用前苏联大远景的镜头和动听的民族音乐来表现哈萨克斯坦的异域风情。在充满诗意的叙事中,对于民族自由的渴望、故土的热爱,以及对于全新未来的渴望油然而生,这种民族精神具有超越时代的共通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三、1980—1997:独立初期的神话解构

图4 《针》剧照

图5 《阳台》剧照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在莫斯科电影学院和各个制片厂学习的50、60后成年,这批在前苏联经典电影中耳濡目染,又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日本战后电影等美学思潮冲击下的新一代,在更加宽松和激荡的政治环境下开始了全新的电影探索与表达。为此,哈萨克斯坦“新浪潮电影”在独立前就已经让世界惊呼的拉希德·努格曼诺夫(Rashid Nugmanov),如同黑泽明一样首次用现代和后现代性等西方思潮与先进视听语言,让中亚走向了世界。[2]160他在1988年导演的《针》代表着“新浪潮”的发端,是对当代哈萨克斯坦电影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影片。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re Roszak)提出“在两个分裂群体(嬉皮辍学者和学生激进分子)中找到了契合点,那就是‘反文化’,即反抗以技术为主体的工业化社会。”[4]165相比之下,哈萨克斯坦“新浪潮电影”反动的不是工业化社会,而是专制统治。其中的分裂群体也从辍学者和学生激进分子变成了一致的叛逆和暴力青年,填补了该民族电影对于强大男性角色的缺失。哈萨克斯坦新浪潮向世界证明了“东方”人民不仅能用形象,而且更能够用逻辑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去思考。
同时不容忽略的是,哈萨克斯坦新浪潮电影的诞生与巨大影响力,和同时期从前苏联到俄罗斯的蜕变中同样反专制的电影文化是彼此呼应的。“当政党不再提供乌托邦,社会发展也没有前景的时候,英雄就从无法找到自我的现实中逃离,用一种幼稚和游戏的方式变得具有破坏性和攻击性,他的行为就像做梦一样。”[5]这种俄罗斯电影弥散的黑色、颓废和疯狂、梦呓乃至病态的电影美学特质,也从80年代开始影响着与其关系密切的哈萨克斯坦电影。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电影中死去的是同一个信仰,即“上帝死了”,充满了人的罪恶与恐慌。但是在哈萨克斯坦电影中,还充满了对于这一“信仰”强烈的反殖民主义倾向。这种长期压抑的反叛主要通过反讽和戏仿的方式,来隐喻和象征一个时代的荒诞、残暴与疯狂。对比弗莱的四个时代,哈萨克斯坦电影从80年代末期开始进入了颓废和死亡的时代,结束于1998年后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建与回归。
作为哈萨克斯坦批判思维觉醒、重构新时代价值的重要标志,哈萨克斯坦新浪潮的代表作品有拉希德·努格曼诺夫的《针》和《狂野东方》(1993)、达赫让·奥米巴夫(Darezhan Omirbayev)的《卡依哈》(1992)和《心电》(1995),还有其他导演的《触摸》(1989)、《阳台》(1988)、《两兄弟中间的女人》(1991)、《恋爱中的小鱼》(1989)等影片。在一致的暴力和犯罪等黑色电影主题中,这些电影以反讽、戏仿、象征与颓废的方式开始了对于神话的解构。
1. 前苏联“国家神话”解构
哈萨克斯坦新浪潮对当代电影影响最为深远的影片是《针》和《阳台》,[2]181二者所体现的“文化先锋”意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先于90年代亚洲国家的其他艺术先锋电影。《针》讲述一个反叛青年为了拯救陷入毒品的女友而不得不与各方势力周旋抗争的故事(图4)。该片由哈萨克斯坦著名摇滚歌手维克多·托索(Victor Tsoi)主演,他的Kino地下乐队音乐成为这部电影的重要文化象征。维克多·托索的“我们想改变”是这一代青年的宣言[2]166,他的精神也延续到了这部影片。在看似黑帮电影的叙事中,处处充满了戏仿和拼贴:在医生转移毒品和男人单挑毒品团伙的时候,用动画和木偶似的动作消解了看似严峻的时刻;当片中的反叛英雄莫罗(Moro)代替女友单挑毒品团伙时,对方站在荒凉的奶牛场模仿列宁朗诵诗歌,而其他人则像马戏小丑一样各自嬉戏玩耍;电影结尾是莫罗在漫天大雪中被暗杀的场景,他高举着打火机跪在地上戏仿不朽英雄,然后旁若无人地站起来向着他的爱情疾步走去。最后这一对于前苏联精神信仰的戏仿还沿用到了他的《狂野东方》中,戏仿了高尔基著名话剧《太阳儿童》,还在此基础上戏仿黑泽明的《七武士》。太阳儿童马戏团到了现代变成了一群生活在中亚的侏儒,电影一开始就戏仿列宁著名的“为自由而战”的演讲,但是侏儒的首领还没有讲完就被强盗枪杀了,侏儒于是以一日三顿饭的代价开始寻找战士,终于集结了七名战士为了侏儒的“乌托邦”故乡和梦想而战。
《阳台》(图5)这部影片中则大量采用反讽的方式,解构了一代人“阳光灿烂的日子”。外科医生在给病人做脑部肿瘤手术的时候,从他手上的编号认出这是自己少年时代的邻居,于是关于少年往事的回忆开始了。这段回忆并不是惯有的革命浪漫主义和青春战斗激情,而是政治高压下支离破碎家庭中少年的孤独压抑,被视为肮脏和猥亵的性的启蒙、歇斯底里意外死亡的邻居、青春帮派之间的街头打斗、隐藏在储藏室里的手枪,还有阳台对面死死盯着自己的巨幅领袖画像,拼贴成了一个真实压抑残暴时代的倒影。电影结尾,少年带领着一群跟随者盲目地向前跑去,直到跑进一个有着领袖画像的火车隧道,所有人即刻被黑暗窒息吞没,彻底否定和讽刺了那个如同太阳一般光芒灿烂的时代。
2. 前苏联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解构
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电影中的女性从30年代被解放的镜像和40年代工作与战斗的镜像,变为吸毒者、妓女等边缘群体,或者残废的残缺形象。就连《狂野东方》里唯一具有正义色彩的女战士,也是以戏仿少年先锋队队歌的女嬉皮形象出现的;在《触摸》中,盲女受尽凌辱艰辛,后与流浪汉相依为命,因为爱情而复明,但最终被流浪汉出卖,遭受侮辱而濒临绝境;《两兄弟中间的女人》中无来由的女孩,在两个兄弟之间游移不定,后终被杀死;《针》中吸毒的蒂娜,在父亲死后被医生诱骗吸毒,无以自控,还引发了几个帮派之间的斗争。这些女人并没有在时代更迭中变得更加自主和有力,反而成为更大的受害者,忍受更多的无序混乱乃至屈辱。女性美好形象的破灭,是对于前苏联大量影片中女性“英雄神话”的有力消解。
3. 独立前后一再鼓吹的“现代性”神话解构
哈萨克斯坦在独立前后的政治动荡中,面对前苏联解体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幻灭,同时也在寻求民族独立发展道路的艰难探索中踟蹰前行。这一时期的影片深刻反映了对于破灭“乌托邦”的痛苦,以及在迫切融入世界主流、追求经济快速发展后所造成的对于传统的冲击,和由此产生的对于未来的焦虑和恐慌。如《卡依哈》和《心电》里的青年人和儿童都那么热烈地渴望着传说中的现代社会,可是当他们因为长大或者因为生病真的被送进城市,却在这一象征“进步”的世界里迷失而堕落,最后再次被这个世界抛弃。在《恋爱中的小鱼》中,为了爱情而闯荡城市森林的年轻人,却被都市黑帮社会的游戏规则轻易出卖和毁灭,而只有停留在老电影中哈萨克斯坦故乡的陈年回忆,还在他孤零零的梦境里,无法走向现实,也无法完成他的救赎。那些在过去一再被鼓吹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以哈萨克破碎的现实完成了对于当代神话的消解。
与哈萨克斯坦新浪潮杰出的艺术成就和巨大影响相矛盾的是,“在20世纪末期,只有乌兹别克斯坦为自己的市场生产电影。当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电影在国际电影节获得无数奖项,家乡的观众却不能找到他们的电影。”[2]30哈萨克斯坦新浪潮导演似乎对曲高和寡的反响不屑一顾,他们的名言就是“没有人看我们,没有人听我们,但我们存在着。”[2]186但是电影工业毕竟不能只站在几个先锋艺术导演的肩膀上,更不能漠视庞大的本土观众群体,因此当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开始整个社会发展的转型时,秉承反叛的电影工业开始被纳入一个全新的国家发展计划中。
四、1998至今:当代电影类型的建构
当前苏联的神话已成“云烟”,面对空荡荡的“神坛”,哈萨克斯坦迫切需要民族神话的建构。于是,当代哈萨克斯坦电影呈现了几种分流的趋势。一种作为哈萨克斯坦的史诗,从悠久辉煌的传统文化中寻求与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共鸣。代表影片有总统三部曲、《游牧战神》(2005)和《无畏一千勇士》(2012)。另一种是在反殖民倾向中呈现前苏联加盟期被掩盖和扭曲的真实,同时在伤痛记忆中弘扬哈萨克斯坦的文化与精神信仰,巧妙地完成了当代主流电影的神话叙事。这一类电影传承了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诗电影的传统叙事风格,在诗意化的视听语言中,充满了深沉的诗意和感伤。其主要代表是鲁斯坦·阿卜杜拉舍夫(Rustem Abdrashev)的《复活岛》(2004)和《给斯大林的礼物》(2008)。第三种则师承哈萨克斯坦新浪潮电影,继续以先锋反观的姿态,以犯罪、暴力、颓废和堕落的反英雄姿态,完成着对于现实的反观和质疑。其代表影片有《舒迦》(2007)、《学生》(2012)、《拥有者》(2014)、《和谐课程》(2013)、《仇》(2007)、《斯佐的爱》(2004)、《小猎人》(2004)和《阿古苏埃特》(1999)等。第四种是商业类型片,其中既有现实主义类型,主要以喜剧式的手法来表现当代哈萨克斯坦人在时代剧变中面对传统和全球化文化冲击的矛盾与选择,其代表影片有《图班嫁给我》(2008)和《老头儿》(2012)等。此外还有以好莱坞类型叙事手法为主的黑帮、侦探、爱情等类型电影,比如《你是谁,卡先生》(2010)等。
从以上分流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电影在向成熟电影工业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开始扭转对于前苏联极端的态度,大量地向前苏联经典电影叙事和诗电影美学风格借鉴。作为哈萨克斯坦史诗电影的《游牧战神》和《无畏一千勇士》,与作为当代英雄传记影片的总统三部曲(《我童年的天空》《总统之路(上)》《总统之路(下)》),再次启用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大远景拍摄草原山河、象征性近景特写抒发诗情画意的电影风格;叙事传统也从新浪潮时期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和不可思议的人物,戏仿反讽似的游戏风格回归到有明确故事线索的经典电影叙事。而作为类型电影的第四种分流,则大量借鉴好莱坞的电影叙事,力图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中营造出电影的娱乐效果。作为母体建构的这三种电影风格,在新一代人中所塑造的民族神话,正如《无畏一千勇士》(图6)开篇引用的总统所述:“所有为了我们民族的独立、自主和无上自由,为了我们家园的完整,为了我们人民的尊严而浴血奋战的先辈,都将受到我们和我们后人永远的尊敬和爱戴。他们的精神将永垂不朽,并永远鼓舞着哈萨克斯坦人对自由的不懈追求,”——这一神话就是弘扬自由独立精神的民族神话。这些电影中的英雄作为哈萨克斯坦民族精神的象征,采用的依然是宏大叙事的讲述策略,忽略深层次的人性探索和多角度的历史风云,侧重于突出传奇的英雄气概。2018年由阿伊马诺夫哈萨克斯坦电影制片厂、中国“Shinework Pictures”公司以及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联合拍摄的,关于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同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动人友谊的影片《音乐家》[6],则是运用该美学风格的又一部哈萨克斯坦的跨国力作。

图6 《无畏一千勇士》海报 2012
与之相似但又不同的是,延续前苏联解冻时期电影叙事风格的《复活岛》和《给斯大林的礼物》等影片,则有意识地突破了古典英雄叙事的窠臼,通过带有批判反思意味的诗意叙事还原了加盟时期的真实历史,并在反殖民主义倾向中委婉地达到“自由独立”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教目的。在《复活岛》里,高压政策下被镇压后枪毙的哈萨克斯坦诗人,一生为了民族独立自由而斗争,留下了千古爱情绝唱;被他的禁诗所感动的少男少女,也遭遇了同样的政治拷问,最后留下了永远的青春遗憾;无限的怅惘和回忆,让曾经逝去的诗人和爱情复活,叩问着那个只允许“一种真理”存在的年代。《给斯大林的礼物》(图7)则通过讲述哈萨克斯坦老人和流放犯人抚养流放犯孤儿的故事,控诉了极权政治的专制残暴,歌颂了哈萨克斯坦的信仰和文化传统。与在批判中进行“宣教”的策略相比,《老头儿》和《图班嫁给我》则意在虚拟缝合哈萨克斯坦现代性与全球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并最终把“草原”作为最终的精神归属。《老头儿》中的孙子总是不愿意听爷爷话去城里好好读书,而爷爷勇斗群狼的英勇经历使祖孙俩再一次达成了精神上的高度共鸣。《图班嫁给我》中外出当水兵、回到草原想拥有自己羊群的男孩,浑身上下充满了西方文化的气息,但却因为这种外来文化的浸染,让他难以继续在草原被接纳,只能跟随姐姐的羊群辗转迁移。这种对于草原的坚守和外来文化的拒绝,从对于本土精神文化信仰归属和民族身份的认同出发,完成了一个成功的当代“现实神话”。 2018年10月10日,由哈萨克斯坦导演谢尔盖·德沃兹弗依(Sergei Dvortsevoy)执导,入围第9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初选名单的剧情片《小家伙》也是通过描述中亚女性在俄罗斯作为“打工妹”的悲惨经历,再一次表达了现代性与全球化中后殖民国家的困境。

图7 《给斯大林的礼物》海报 2008以上图片来源于豆瓣电影网
相比之下,哈萨克斯坦新浪潮电影影响下的先锋电影则以反讽的姿态,继续着对于“母体”的反观和思考。在前苏联时期大量涌现的中亚儿童电影,意在表现中亚人民是伟大领袖的孩子。哈萨克斯坦新浪潮在《狂野东方》和《心电》等影片里,反讽这群孩子就从来没有长大过。到了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全新阶段,这批新浪潮导演以及他们的学生们继续在影片中大量沿用叛逆青年亚文化题材和少年儿童题材。电影中的少年儿童不是过于性早熟,就是在各种暴力诱惑下堕落犯罪,这群还未长大就夭折的小孩,是先锋文化精英眼里的社会现实。影片中他们的老师,还有广播里的播音员则永远在宣扬“弱肉强食”的经济丛林法则,还有不断涌现的百万富翁与经济奇迹。对于物质的过分强调,使得殖民初期的混乱无秩序,已经延伸到了秩序内的学校和医院。在《斯佐的爱》《学生》等影片里,女人衷心的等待成为狱中青年的救赎。而在《小猎人》中,表现的则是彪悍的哈萨克斯坦猎人对于都市女科学家的征服,而他对于狼既膜拜又征服的精神,使得彷徨无助的叛逆男孩找到了精神的安宁。爱情的救赎和传统的回归,成为了当代哈萨克斯坦先锋电影的“乌托邦”神话,体现了面对“自由独立”的强势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之下的彷徨和迷茫。
达赫让·奥米巴夫等新浪潮时期的先锋导演通过剧组带班的方式,培养了21世纪新一代哈萨克斯坦优秀的电影工作人员。这批导演在拍摄电影时,深深地延续着新浪潮的电影风格。一个国家经过独立伊始的混乱动荡,向稳定发展转型时需要反观“母体”的他者——犯罪分子、律师、心理咨询师等,同时也需要作为当代神话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使之成为大众精神导引和身份归属的确认。达赫让·奥米巴夫在1998年拍摄了一部“有意味”的电影——《黑仔》。在这部电影开头,数学家抨击了“一切向经济看齐”的社会现状,并声称要用数学拯救在物质化中令人失望的现实,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数学是科技的本质。[4]155正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彻底终结了传统神话的使命。可是数学家在电台演讲没有多久,就在家里突发逝世,在大踏步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他的司机却走投无路而终于成为一个杀手。达赫让·奥米巴夫从此前对于前苏联国家神话的否定,发展到从根本上否定哈萨克斯坦当代的现实神话。
2017年哈萨克斯坦国产电影票房总额达4400万美元,国产电影票房占比达13%,增长6%。在新年档期,《哈萨克式商业在美国》更是超过《马戏之王》《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等电影获得了票房榜冠军。[7]伴随着哈萨克主流电影和类型电影的迅猛发展和日益成熟,哈萨克斯坦电影工业正在不断得到本土观众的认可与喜爱。其中对类型电影的大力推行、对艺术电影的宽松政策等重要举措,对当代哈萨克斯坦电影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在好莱坞进口影片一统天下之际,保持该国影片鲜明的民族风格,并达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成功建构与宣教,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巨大挑战。